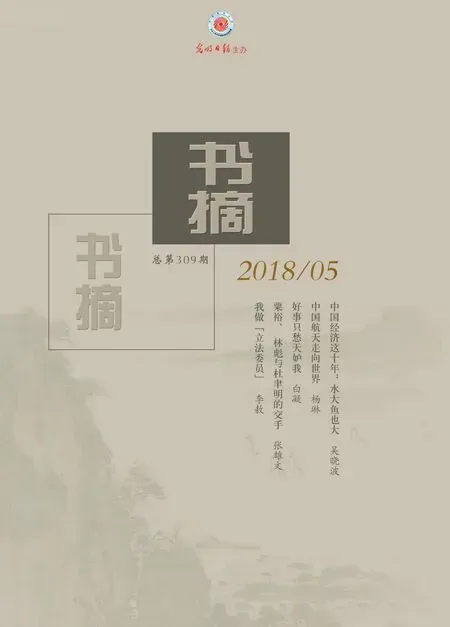大唐“公務(wù)員”柳宗元
☉楊葵
《柳宗元集》讀到一半,友人相約到清邁過(guò)圣誕節(jié)。覺(jué)得遠(yuǎn)在異國(guó)他鄉(xiāng),讀這么正宗的國(guó)粹有點(diǎn)不合時(shí)宜,就沒(méi)帶剩下那一半。可是真到了清邁,第一天逛逛古城就后悔了。巴掌大點(diǎn)兒的城,佛寺林立,三步一小,五步一大,進(jìn)去轉(zhuǎn)轉(zhuǎn),頻有僧人擦肩而過(guò)。不禁遙想柳宗元生活的中唐時(shí)節(jié),差不多也是這般景象吧。學(xué)者統(tǒng)計(jì),柳宗元時(shí)代,全國(guó)寺廟五千多座,蘭若幾萬(wàn)。長(zhǎng)安、洛陽(yáng)這樣的大城市不用說(shuō)了,就連柳宗元蟄伏11年之久的小小永州城,亦即今日湖南永州,也稱(chēng)零陵,當(dāng)時(shí)應(yīng)該和清邁古城差不多大吧,就有龍興寺、華嚴(yán)寺、開(kāi)元寺、法華寺等36處寺庵。如此,2013年底的我,在清邁寺廟間穿梭,某一瞬間不禁錯(cuò)覺(jué)變身柳宗元。
是寺廟之多惹我無(wú)端遐想,還是在北京讀柳宗元的余音繞梁?沒(méi)有細(xì)想。倒是另有一道閃電劃過(guò)腦海:柳宗元人生46載。而我過(guò)完這個(gè)圣誕節(jié),也要46歲了。
這么想,甚至還說(shuō)出來(lái),似乎有點(diǎn)不吉利,但這正是我重讀唐、宋文人著作計(jì)劃中一個(gè)不無(wú)怪僻的心理:我不僅想重讀他們都寫(xiě)了些什么,還想知道他們是在什么年紀(jì)寫(xiě)了那些,以及,可能是在什么樣的心境下寫(xiě)了那些,進(jìn)而再和我,以及我所身處的這個(gè)時(shí)代相勾連。比如讀柳宗元,如果柳宗元和我一樣生于1968年,而在2014年的農(nóng)歷十一月,他將客死蠻荒的柳州。
重讀計(jì)劃加入這一游戲之后,自他相換,時(shí)空大挪移,那些冷冰冰的歷史年代數(shù)字仿佛被激活,古今鴻溝貌似被填平了。除此以外,多少也有另外一層深意吧,標(biāo)準(zhǔn)說(shuō)法可以叫以古鑒今,更大膽的說(shuō)法是古今不二。
在清邁時(shí),泰國(guó)騷亂正盛,曼谷游行示威不斷,一副天下大亂之勢(shì)。清邁卻一派祥和,優(yōu)哉游哉。可是我看著電視里各種政府官員愁眉苦臉應(yīng)對(duì)記者提問(wèn),突然想到,雖然今天我們將柳宗元和韓愈并稱(chēng)“韓柳”,奉他為古文運(yùn)動(dòng)領(lǐng)袖,但那都是身后之名,他的職業(yè)只是個(gè)大唐的公務(wù)員。大唐盛世三百年,百姓除了安史之亂遭殃數(shù)年,其余時(shí)候大多歌舞升平,國(guó)泰民安,但是身為公務(wù)員的柳宗元,卻半生煎熬。
依我的算法,作為公務(wù)員的柳宗元粗略履歷如下:1984年開(kāi)始考進(jìn)士,連考好幾年,直到1988年登進(jìn)士第。1992年,24歲的柳宗元到離長(zhǎng)安不遠(yuǎn)的藍(lán)田縣當(dāng)縣尉(大致相當(dāng)于縣長(zhǎng)助理),正式開(kāi)始公務(wù)員的職業(yè)生涯。他從小便“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致”,“當(dāng)時(shí)流輩咸推之”,既進(jìn)了公務(wù)員系列,毫不吝惜才華,恣意揮灑。從他的著作年譜可見(jiàn),從政之后寫(xiě)了不少表、狀、碑、記、文、志,一時(shí)年少得志,名聲遠(yuǎn)揚(yáng)。當(dāng)時(shí)朝廷高層中,有兩個(gè)改革派大人物王叔文、王伾,他們瞄上了柳宗元。在二王的賞識(shí)與運(yùn)作之下,柳宗元升遷監(jiān)察御史。這一職務(wù)品級(jí)不高,僅僅正八品下,不過(guò)因?yàn)槁氃诒O(jiān)察內(nèi)外官吏,權(quán)限甚廣,是要繼續(xù)升官的前奏。2000年農(nóng)歷正月,王叔文、王伾侍讀多年的太子李誦終于繼承帝位,即唐順宗。二王開(kāi)始率領(lǐng)柳宗元、劉禹錫等人,推行全面政治體制改革,史稱(chēng)“永貞革新”。柳宗元也官升政客生涯的頂峰——禮部員外郎,大約相當(dāng)于今日部委的一個(gè)副司長(zhǎng),雖然品級(jí)仍然不高,一般為六品左右,但屬吏中要職。這一年他32歲,政壇新星,躊躇滿(mǎn)志。
可惜福禍相依,殘酷的政治斗爭(zhēng)中,一幫文人組成的革新集團(tuán),根本撼動(dòng)不了此前運(yùn)營(yíng)已久的宦官和軍隊(duì)的堅(jiān)硬根基,唐順宗只當(dāng)了不到一年的皇帝,革新集團(tuán)也只掌了短短146天的權(quán)便宣告失敗。二王中的王伾被貶為開(kāi)州司馬,不久病死;王叔文被貶為渝州司戶(hù),次年被賜死。柳宗元、劉禹錫等革新集團(tuán)的八個(gè)核心人物,先后被貶為邊遠(yuǎn)八州司馬,這就是唐史中著名的“二王八司馬事件”。
起初是被貶為邵州刺史的,赴任途中又接噩耗,加貶為永州司馬。永州一待11年,2010年,42歲的柳宗元接到詔書(shū)回長(zhǎng)安,本來(lái)有重新被重用的可能,可是遭遇小人搗亂,又被改派,雖然官職回升了一點(diǎn)點(diǎn),但是長(zhǎng)途跋涉了三個(gè)月,到了比永州更加偏遠(yuǎn)的柳州任刺史,即柳州的行政長(zhǎng)官。四年之后,郁悶地死于柳州任上。
經(jīng)過(guò)如此換算,拉近了作為讀者的你、正寫(xiě)此文的我,和柳宗元這個(gè)他了么?且不管,我繼續(xù)——
清邁沒(méi)有《柳宗元集》,但是隨處有Wi-Fi;無(wú)法持卷,卻不妨從網(wǎng)上搜出部分篇章,細(xì)讀細(xì)咂摸。既是佛寺如此之多的地方,就選了他佛教題材的詩(shī)文。更何況,“涉佛”也是柳宗元的一大特色,有學(xué)者專(zhuān)門(mén)統(tǒng)計(jì)過(guò),柳氏涉佛文章數(shù)量,在當(dāng)時(shí)士大夫中為最多,《柳宗元集》45卷詩(shī)文中,佛教碑文有兩卷,共計(jì)11篇;記寺廟、贈(zèng)僧人的文章各占一卷,共計(jì)15篇;一百四十多首詩(shī)里,與僧人贈(zèng)答和宣揚(yáng)佛理者共計(jì)二十多首。

碑文11篇全在網(wǎng)上找到,其中又以《曹溪大鑒禪師碑》最為著名。曹溪大鑒禪師就是著名的禪宗六祖慧能,唐代曾有三大文人為他作碑銘,王維、柳宗元、劉禹錫。慧能圓寂整整一個(gè)甲子之后,柳宗元出生。
說(shuō)到柳宗元與佛教,與唐宋時(shí)期諸多文豪的情況類(lèi)似,歷代佛家著作屢屢將他們拉作佛門(mén)弟子,歷代文人著作里則眾說(shuō)紛紜。前者乃是一種古今中外常見(jiàn)的拉名人充門(mén)面,后者則是各取所需,為做自己的課題,寫(xiě)自己的文章。具體到柳宗元,前者好比成書(shū)于宋朝的《佛祖統(tǒng)紀(jì)》中,把他列為永州龍興寺僧人重巽的俗家弟子,并將其《圣安寺無(wú)姓和尚碑》《龍興寺凈土院記》等文收錄在內(nèi),作為“發(fā)揚(yáng)光大佛教”的名篇。至于后者,說(shuō)法就更多了,網(wǎng)上隨便搜搜,當(dāng)今不少碩士博士論文都以此為題。
柳宗元能名垂青史,自有他可以塑像供著的一面,這個(gè)毫無(wú)疑義;但是老這么供著,再不斷往臉上貼金,時(shí)日一長(zhǎng),形象容易變形也是不爭(zhēng)的事實(shí)。而我把柳宗元時(shí)空大挪移到1968年出生的一個(gè)正常人,一個(gè)愛(ài)讀書(shū)、才華卓然的普通人,是寄希望剝?nèi)ヒ磺Ф嗄暝谒樕腺N的金粉,看看他常人面目。
重讀柳宗元,從北京讀到清邁,再?gòu)那暹~讀回北京,通讀他所有著作之后,要想描述這一面目,關(guān)鍵詞還是“公務(wù)員”。雖然他才華過(guò)人、文采超群、情懷廣大,但是縱有千般風(fēng)情,也都只是“公務(wù)員”一詞的定語(yǔ)而已。顯然我這并非旨在學(xué)術(shù)研究,與前文所謂古今不二一脈相承,我是嘗試著探探一千多年前一個(gè)人的用心。
細(xì)研柳宗元著作年表,會(huì)發(fā)現(xiàn)他風(fēng)華正茂、官運(yùn)亨通時(shí),撰文大多是明確的公文性質(zhì),那是他的日常工作。一些留存的詩(shī)作當(dāng)然更多個(gè)人化的性情抒發(fā),但其中也不少應(yīng)和之作。總之一副標(biāo)準(zhǔn)的有才華公務(wù)員的樣子。政治大變革中站錯(cuò)隊(duì)伍,被貶永州,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轉(zhuǎn)折,職業(yè)生涯被毀到底,一時(shí)也無(wú)望卷土重來(lái),只得另覓它途,尋求人生依仗。他在給友人的書(shū)信中說(shuō):“賢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貴于后。”如何“取貴”呢?他也想好了——“能著書(shū),斷往古,明圣法,以致無(wú)窮之名。”柳宗元的人生從此不同,也因此,唐朝的歷史也許少了個(gè)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卻多了個(gè)集文學(xué)家與哲學(xué)家于一身的了不起的人物。
將柳宗元置于大唐公務(wù)員這一普通人身份,也許可以解開(kāi)不少“柳學(xué)”中爭(zhēng)論不休的迷霧,比如他與佛教及道教的關(guān)系。我是同意融合之說(shuō)的,但是此融合非彼融合,儒道佛三家,都別急著往他身上貼標(biāo)簽,他既不是要用儒來(lái)融佛和道,更不是要用佛來(lái)統(tǒng)儒和道。儒道佛三家都只是他的素材,他要用這些素材畫(huà)一幅自己的大畫(huà),亦即建立自己的全景式的人生觀(guān)、世界觀(guān)和價(jià)值觀(guān)。這幅大畫(huà)能不能這么畫(huà),以及最終如何,我沒(méi)能力置評(píng),我能說(shuō)的是——至少在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內(nèi),他對(duì)佛道儒三家的精研,也許只是出自一個(gè)公務(wù)員的責(zé)任心。
大唐三百年,對(duì)佛、道、儒而言,都可謂鼎盛期,因?yàn)槌齻€(gè)別例外,基本上歷任皇帝都執(zhí)行了三教并舉政策。甚至在皇帝的直接詔示下,還上演了很多場(chǎng)三教論衡大戲。可是“并舉”這種事,當(dāng)國(guó)策口號(hào)喊喊容易,落實(shí)到具體人事上,常常是按下葫蘆起來(lái)瓢。相關(guān)事例太多了,可以讀張之洞的曾孫張遵騮編寫(xiě)的《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簡(jiǎn)明扼要,紙上一日閱盡幾百年人世滄桑。讀完就會(huì)發(fā)現(xiàn),這所謂的“并舉”,具體落實(shí)在一份接一份的詔書(shū)上,政策上有多混亂,又把社會(huì)生活攪和得多亂。從皇帝到重臣,都是忽東忽西,忽而抑佛抬道,忽而抑道抬佛,忽而儒家遭冷落,忽而又唯儒是尊,一出接一出,極盡戲劇化之能事。
柳宗元有過(guò)可謂輝煌的青少年時(shí)代,自然自視不低,目睹整個(gè)社會(huì)價(jià)值觀(guān)如此易變,內(nèi)心升起“我不琢磨誰(shuí)來(lái)琢磨,我不明白誰(shuí)會(huì)明白”的雄心壯志,也就不奇怪了。這一心理活動(dòng)當(dāng)然是我個(gè)人的猜想而已,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作為大唐公務(wù)員,無(wú)論身居要職,還是失意被貶,他有責(zé)任“把握時(shí)代的脈搏”。也唯有琢磨透“朝廷的意思”,才有可能重回長(zhǎng)安,仕途再度輝煌。當(dāng)然,這仍是我個(gè)人的猜想。
曾經(jīng)有人不無(wú)陰損地?cái)D兌漢唐時(shí)代的文人士大夫們,說(shuō)為何終南山隱士多呢?只因離長(zhǎng)安近啊,皇帝老哥一朝回心轉(zhuǎn)意有召喚,這些假裝看破紅塵、隱居山林的文人們春風(fēng)得意馬蹄疾,飛奔著就回到皇帝老哥身邊了。以我通讀柳宗元的觀(guān)感,他的品性絕不至如此不堪,但是去除掉這一說(shuō)法的陰損成分,那個(gè)時(shí)代的公務(wù)員們從小就把忠孝二字烙在骨頭上,隨時(shí)心系皇帝,也是很自然的事。
如果按照這一猜想來(lái)貼近柳宗元,他的大唐公務(wù)員履歷表一行行白紙黑字旁邊,似可加上心理軌跡變化圖作為注解——起初一路還算順利,考取公務(wù)員,學(xué)以致用,當(dāng)然主要是個(gè)齊家治國(guó)平天下的儒家心態(tài)。陡遭惡變,被貶蠻荒,加之又住在永州的龍興寺,與和尚們打成一片。消極點(diǎn)想,這是心中郁結(jié)需要排遣;積極點(diǎn)想,斷往古、明圣法;總之,他開(kāi)始重拾自幼就喜好的佛家理論。隨著日月更替,人也待住了,心也待穩(wěn)了,更重要的是,整體世界觀(guān)、人生觀(guān)、價(jià)值觀(guān)逐漸成熟,這才認(rèn)清形勢(shì),腳踏實(shí)地從頭再來(lái),開(kāi)始摸索三教融合之道,畫(huà)自己的那幅大畫(huà)。
但是,不管如何融合三教,柳宗元這幅大畫(huà)的底色,始終是儒家色彩,這是不容置疑的。這也充分彰顯了他的公務(wù)員身份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