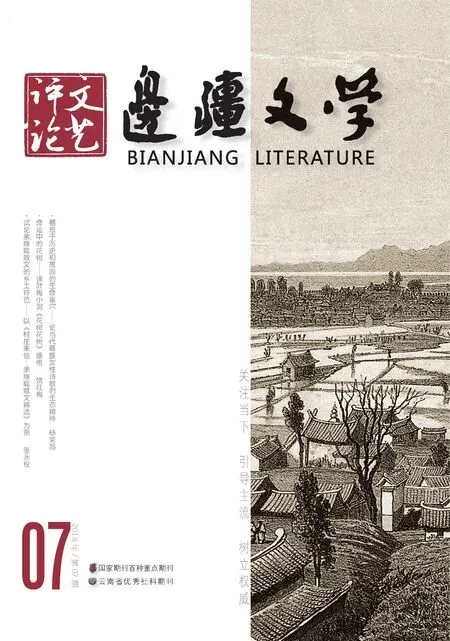雨天,讀《昆明的雨》
農為平
又到雨季。
今年的雨季來得偏早,且淅淅瀝瀝,纏綿不絕,遂想起汪曾祺的《昆明的雨》來。
汪曾祺與昆明是有緣分。十九歲就讀于西南聯大,1946年離開,前后在昆明生活了七年。離去時猶自戀戀不舍:“昆明的天氣這么好,有什么理由急于離開呢?”
走得那么不舍,懷念便如影隨形。“我想念昆明的雨”,《昆明的雨》的末句如此寫道。因了這份想念,汪曾祺把昆明的雨季寫得生動鮮活,搖曳多姿。
昆明的雨季一般較漫長,往往從五月份一直綿延至初秋。抗戰時期,巴金曾兩次來昆明探望未婚妻蕭珊。第二次是1941年七八月份,正逢雨季,“差不多天天落雨”,生活、出行均受影響,諸多不便,于是不免埋怨“聽到淅瀝的雨聲……真叫人心煩”,“這雨不知要下到哪一天為止”(見《龍·虎·狗》序)。然而又說,“但正是這雨使我能夠順利地寫成這些文章、編成集子”(見《關于〈龍·虎·狗〉》),在被雨阻住的日子里,在租住的先生坡一處寓所的小書桌上,巴金一氣寫作了《風》《云》《雷》等十九篇散文。——如此說來,昆明的雨也算是對巴金的創作多少有些功勞的。
巴金只是過客,他看到的雨不過浮光掠影,汪曾祺就不一樣,經年生活于斯,日久不知身是客,故能體味昆明雨季的獨特魅力。昆明的雨季雖漫長,“但是并不使人厭煩。因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連綿不斷,下起來沒完。而且并不使人氣悶”,并且補充說“人很舒服”。汪曾祺是江蘇高郵人,昆明雨季開始時,江南一帶正差不多步入梅雨時節,氣候濕熱粘黏,濡悶難耐;而昆明本以“花開不斷四時春,天氣常如二三月”的春城聞名,夏天不會太熱,下起雨來,更是涼爽怡人,難怪汪曾祺會對昆明的雨季情有獨鐘。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豐滿的,使人動情的。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長。昆明的雨季,是濃綠的。草木的枝葉里的水分都到了飽和狀態,顯示出過分的、近于夸張的旺盛。”在汪曾祺眼里,昆明的雨天是明麗動人、飽滿豐足的,有生命的歡悅在萌發。讀這樣的文字,仿佛滿目皆是草木在雨水浸潤下盡情舒展生長的盎然景象,心里也不由漾起淡淡的歡喜來。
在現代作家中,周作人也長于寫雨,他甚至以“苦雨齋”名其書房,聽上去有些清苦的意味,不過他筆下的雨境卻是令人舒暢的。“臥在烏篷船里,靜聽打篷的雨聲,加上欸乃的櫓聲以及‘靠塘來,靠下去’的呼聲,卻是一種夢似的詩境。”(《苦雨》)這樣的意境,與他所談的“喝茶當于瓦屋紙窗之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制閑,可抵十年的塵夢”,何其相似,表達的都是對一種寧靜、閑適又不乏詩意的生命境界的向往。自然,周作人筆下的雨是透著理想化色彩的,汪曾祺在這里所寫的雨則充滿了現世的生命氣息,各自傳遞著寫作者不同的人生意趣。
其實,在古往今來的文人筆下,雨所代表的意蘊又何止這兩種。“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是欣喜愉悅,“竹杖芒鞋輕勝馬,一蓑煙雨任平生”,是快意灑脫,“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是錐心孤獨,“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是人生凄苦……雨在文學中,實在是扮演了一種特殊的情感媒介作用。
昆明氣候宜人,物產豐富,汪曾祺寫到的也多:寶珠梨、石榴、楊梅、木瓜、葛根、菌子、糖炒栗子、灰菜、豆殼蟲、野菊花……有意思的是,他寫到的多為吃食,這自然是“吃貨”本性使然了。熟悉汪曾祺的人都知道,他好吃、善吃,對美食很有研究,與吃有關的文章在他的創作中占了不小的比重。這一特點在《昆明的雨》中也自然很突出。


在諸多菌子中,他寫得最好的是干巴菌。手法上就很獨特,先抑:“乍一看那樣子,真叫人懷疑:這種東西也能吃?!顏色深褐帶綠,有點像一堆半干的牛糞或一個被踩破了的馬蜂窩。里頭還有許多草莖、松毛,亂七八糟”,然后筆觸一轉:“可是下點功夫,把草莖松毛擇凈,撕成蟹腿肉粗細的絲,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會使你張目結舌:這東西這么好吃?!”手法、文字之精之妙,令人絕倒。李漁曾款宴友人,以蕈、莼二物做羹,加入蟹黃、魚肋,名“四美羹”。座中客人吃得不亦樂乎,說:“今而后,無下箸處矣。”以前讀到此處,不由拍手稱絕。如今來看,似乎汪曾祺更勝一籌。二者皆妙在不直接描繪味道如何鮮美,僅以食者極端的反應來襯托,為美味留下了一個極具誘惑力的想象空間。《論語·述而》載:“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此三者,均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過,在《昆明食菌》一篇中,汪曾祺到底忍不住,還是細細描繪了這令他吃了“半天說不出話來”的到底是怎樣一種味道:“干巴菌,菌也,但有陳年宣威火腿香味、寧波曹白魚鲞香味、蘇州風雞香味、南京鴨胗肝香味,且雜有松毛的清香氣味。”這樣的味道,估計除了自稱“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的蘇軾,自詡“越中清饞,無過余者,喜啖方物”的張岱等這般美食家外,普通人是不易品味出來的。而這幾樣東西中,除了宣威老火腿和松毛,其余皆為江南特色美食。從千里之外的異鄉食物中品出家鄉熟悉的味道來,這其中多少潛藏著一縷鄉愁吧?
文中寫到的物產還有楊梅和緬桂花。
昆明的楊梅個頭大,名為“火炭梅”,顏色黑紅黑紅,像一球燒得熾紅的火炭,味道也不酸,汪曾祺將之與蘇州洞庭山的楊梅、井岡山的楊梅相比,結論是“好像都比不上昆明的火炭梅”。他特意寫到賣楊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她們“戴一頂小花帽子,穿著扳尖的繡了滿幫花的鞋”。這樣的景象,對于中原漢文化地區的讀者來說,多少會有些新奇感。其實,昆明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區,司馬遷在《史記·西南夷傳》中提及漢朝時,生活于今滇池地區的有滇部落,及周圍“君長以什數”的眾多部落。歷史研究也表明,這一帶在古代就是百越、百濮各民族共同混雜居住的地方,因而多元的民族文化也便成為昆明的一個特色。這些賣楊梅的苗族女孩大多來自昆明周邊山區,她們從山上摘來楊梅,坐在人家階石的一角,不時吆喚一聲:“賣楊梅——”,“聲音嬌嬌的。她們的聲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氣更加柔和。”
在昆明,整個雨季總是彌散著緬桂花淡淡的幽香。緬桂花這一名字,似乎只有云南一帶這么稱呼,其他地方大多稱之為白蘭花,北京又叫“把兒蘭”。“緬桂花”之名,當是與云南和緬甸相鄰有關。自小見到的緬桂花大多高大,及至讀到汪曾祺不無驚嘆地說“我在家鄉看到的白蘭多是一人高,昆明的緬桂是大樹”時,才知道原來云南的緬桂花自有獨特之處。文中提到他當年住過的若園巷二號院內有一棵大緬桂樹,房東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寡婦,花開時節,每天便和她的養女搭了梯子摘花拿到市場去賣,也許是怕房客亂摘,時常也給他們送一些,“有時送來一個七寸盤子,里面擺得滿滿的緬桂花!帶著雨珠的緬桂花使我的心軟軟的,不是懷人,不是思鄉。”想起讀過的一個小故事,說一個盲人每天都會摸索著準時打開樓道的路燈,別人大惑不解,你自己又不需要燈,為何那么積極去開燈?盲人笑著解釋道,開燈能給別人帶來方便,也給我自己方便。燈亮了,別人也就不會撞到我了。這樣的事,遠比割肉喂鷹、舍身飼虎之類的故事更能打動人,只因它更真實,更貼近人性。這世上的圣人畢竟少之又少,而我們每一個凡俗之人都有自己卑微的欲求;有的善意,動機不見得是高尚的,但方法對了,也會給人以溫暖。
在《昆明的雨》中,汪曾祺還特別提到昆明的一個習俗:舊時人家會在門頭上懸掛八卦圖、小鏡子以及仙人掌以辟邪,因了空氣濕潤,仙人掌不僅不死,還能繼續生長開花。——多年前讀過之后,這一景象一直在腦海里揮之不去,卻不免遺憾這樣的景象在現實生活中已難覓蹤跡,如今昆明城處處高樓林立,仙人掌也成為花市里售賣的點綴品,大多數人恐怕沒見過汪曾祺描繪的那種生長在山間地頭“極肥大”的仙人掌了。不過在偏遠的郊區,偶爾會見到一些。一次去團結鄉那邊的山里游玩,驅車經過一個不知名的小村莊時,不經意瞥見路旁一個明顯有些年頭的老舊院落,門頭上掛著的正是一支仙人掌,圍墻上草蔓萋萋。一時竟有種不真實的感覺。
“蓮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濁酒一杯天過午,木香花濕雨沉沉。”這是汪曾祺離開昆明四十年后寫的詩,并說:“我懷念昆明的雨”。四十年的時光,蒼狗白云,世間已是多少滄桑,而依然能念念不忘的,該是一種怎樣的深情!
(作者系南京大學新文學研究中心在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