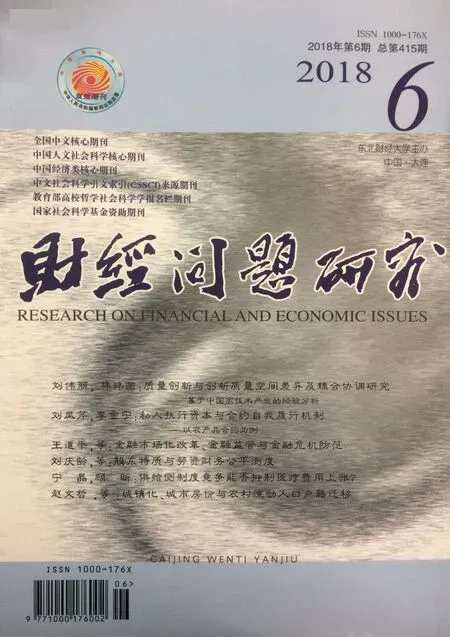生育水平下降的宏觀現(xiàn)象和微觀機理
——來自婚姻延遲和生育延遲的驗證
薛繼亮,鄔 浩
(內(nèi)蒙古大學(xué) 經(jīng)濟管理學(xué)院,內(nèi)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一、引 言
在經(jīng)濟增長、社會發(fā)展和計劃生育政策的共同作用下,當前中國低生育率的現(xiàn)實已被公認。Zhang[1]認為中國的真實總和生育率為1.5—1.6,計劃生育政策和市場經(jīng)濟力量使得中國生育率急速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2],但市場經(jīng)濟力量的作用更大[3]。侯佳偉等[4]認為2000年以后中國平均理想子女數(shù)基本穩(wěn)定在1.6—1.8人之間,“兒女雙全”的二孩生育意愿最為集中;1980年代人和1990年代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差異很大,前者生育水平高于生育意愿,后者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傅崇輝等[5]認為中國生育水平受到育齡婦女年齡結(jié)構(gòu)、婚姻狀態(tài)等結(jié)構(gòu)性因素的影響。改革開放以后出生的一代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表現(xiàn)出與父輩不同的特征,尤其是生育意愿與生育水平的背離現(xiàn)象比較突出[6]。Robert等[7]認為1990年代以來中國生育水平下降的原因,2/5歸因于結(jié)婚年齡的推遲,3/5歸因于婚內(nèi)生育率的下降。
中國省級空間和時間的生育水平下降存在擴散效應(yīng)。韋艷[8]認為生育率持續(xù)下降始于少數(shù)大城市和一些東部省份,廣大的西北地區(qū)和一些南方地區(qū)生育率轉(zhuǎn)變較慢;省內(nèi)生育水平下降顯示出比省間生育率下降更為明顯的擴散效應(yīng),并且不同時期生育水平下降的影響因素不同。擴散因素獨立于社會經(jīng)濟因素,其促進和加強了社會經(jīng)濟和計劃生育因素對中國生育水平下降的影響。易君健和易行健[9]認為社會經(jīng)濟因素對家庭生育行為產(chǎn)生累積效應(yīng)。韋艷和張力[10]從多個方面考察了翼城生育政策對生育行為和生育意愿的影響,認為翼城現(xiàn)有生育行為和生育意愿更多是政策干預(yù)的結(jié)果,是政策促成的外生性轉(zhuǎn)變,而非由于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導(dǎo)致低生育意愿的內(nèi)生性轉(zhuǎn)變。 周立群和周曉波[11]則從制度經(jīng)濟學(xué)角度分析了生育水平下降的原因,認為使家庭撫養(yǎng)孩子的私人成本社會化和使撫養(yǎng)孩子的社會收益部分內(nèi)部化可以提高生育率。
在中國生育水平下降的情況下,還出現(xiàn)了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背離現(xiàn)象。與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實際生育率大大低于意愿生育率的情況不同,中國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背離現(xiàn)象主要是行為高于意愿,其中性別偏好是造成生育行為大于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12]。茅倬彥和羅昊[13]對江蘇省的研究發(fā)現(xiàn),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婦女中40%婦女的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為,60%婦女的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為。卿石松和丁金宏[14]利用上海市夫妻匹配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分析“單獨兩孩”政策對生育意愿的影響,并對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背離現(xiàn)象進行解釋,認為生育政策對生育意愿的影響有限,“單獨夫妻”、“雙獨夫妻”和“雙非夫妻”之間的生育意愿的差異性極小,而生育機會成本低且有能力養(yǎng)育更多孩子家庭的生育意愿相對較高。由于生育決策無法單方面決定,盡管男女平均的生育意愿非常接近,因30%的夫妻生育意愿存在差異,使夫妻一致的生育意愿較低,從而抑制實際生育行為。
家庭生育理論的研究集中于生育數(shù)量而忽略了子女性別組合。1970年以來中國生育水平持續(xù)下降,在家庭層面上表現(xiàn)為兄弟姐妹數(shù)的減少,同時也影響了兄弟姐妹的構(gòu)成,進而影響家庭對子女教育的投資以及性別間的教育差異[15]。馬忠東和王建平[16]認為育齡婦女二、三胎次生育率在20世紀90年代初大幅下滑,二胎女孩生育率明顯低于二胎男孩生育率,反映二胎生育對性別的偏好明顯,造成女孩乃至整體生育水平下降。三胎生育率也持續(xù)下降到最低點。一女后選擇生男以達到理想子女組合,減少了多胎,卻釀成了社會男女孩比例嚴重失衡。同時,在低收入水平條件下通過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也可以實現(xiàn)人口轉(zhuǎn)變,但是需要付出高昂的經(jīng)濟政治成本,并造成“未富先老”等嚴重的人口社會經(jīng)濟問題。彭偉斌和陳曉慧[17]借助人口發(fā)展預(yù)測模型分析發(fā)現(xiàn),執(zhí)行“單獨兩孩”生育政策僅能產(chǎn)生較小的短期效應(yīng),長期來看無法阻止人口下降區(qū)人口總量持續(xù)下降和人口老齡化加速的趨勢。
綜上所述,從當前國內(nèi)已有研究來看,專門對生育政策、生育意愿、代際差異等的研究成果也比較多,從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的角度論證生育水平下降可以彌補已有研究的不足,且具有顯著的現(xiàn)實意義。
二、理論基礎(chǔ)
研究生育選擇的微觀機理,需要建立一個涵蓋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的生育模型,為此,本文選擇Diamond[18]的兩時期代際交疊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假設(shè)生育是一種投資,即子女對于父母來說是一種投資品,父母將養(yǎng)育子女作為一種養(yǎng)老的預(yù)防手段。借鑒王永華和彭偉斌[19]的模型,將生育孩子作為生育選擇的決策變量,同時假設(shè)贍養(yǎng)父母的支出固定。涵蓋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的生育模型在消費者部門中可以表示為式(1),預(yù)算約束為式(2)和式(3):
MaxU(C1t)+β·(C2t+1)
(1)
wt[1-dφ(ft)]=C1t+St
(2)
C2t+1=(1+rt+1)·St+wt+1·ft·d
(3)
在涵蓋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的生育模型中,個體需要在工作和退休兩期進行資源配置,實現(xiàn)效用最大化。其中,fi是t期的生育率,β是t+1期效用的貼現(xiàn)因子,φ(ft)作為撫養(yǎng)子女的成本函數(shù),為凸函數(shù)。d作為外生參數(shù)小于1 ,意味著年輕人對老年人的贍養(yǎng)強度是固定值,可以用工資的一個比例來表示,是年輕人人力資本收益的一部分。C1t和C2t+1在目標函數(shù)中是決策變量,可以用儲蓄St和生育率ft表示。在目標函數(shù)中對決策變量求導(dǎo)并使之為0,以實現(xiàn)效用最大化并消除跨時套利機會,得到式(4):
(4)
為了模型推導(dǎo)的簡便,本文假設(shè)代理人具有對數(shù)效用函數(shù)lnC,得到C2t+1=β·(1+rt+1)·C1t。假設(shè)子女的養(yǎng)育成本函數(shù)形式為式(5):
(5)

(6)
消費者的所有儲蓄都將作為下一期的資本存量,即St=ft·kt+1。求解得出生育率的解:
(7)
從家庭決策視角確立的生育模型,其核心在于討論生育的福利,即論證家庭時間利用、收入、儲蓄與生育之間的關(guān)系和規(guī)律。在生育模型中,特別強調(diào)跨期福利變化,尤其是儲蓄和生育的關(guān)系。在理清生育模型本身的機理之后,本文主要驗證影響生育的決定因素并探索其傳導(dǎo)機理,從不同代際間的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進行代際間的差異分析,論證中國生育水平下降到底是由財富、時間還是關(guān)鍵事件延遲(婚姻延遲或生育延遲)帶來的。
三、生育水平下降的宏觀觀察:結(jié)婚年齡的視角
中國分年齡別生育率總體呈現(xiàn)下降趨勢(如表1所示),其中,15—34歲的4個年齡別生育率存在下降的趨勢,35—49歲的3個年齡別生育率卻存在上升趨勢,雖然上升的幅度比較小。初育年齡在延遲,尤其從20—24歲轉(zhuǎn)移到25—29歲,30—34歲的年齡別生育率比較穩(wěn)定。

表1分年齡別的婚姻登記和生育率
注:數(shù)據(jù)由wind數(shù)據(jù)庫和《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整理所得,其中2010年數(shù)據(jù)為普查數(shù)據(jù)。
與中國分年齡別生育率總體趨勢和延遲相對應(yīng)的是,分年齡別婚姻登記也出現(xiàn)了延遲,尤其表現(xiàn)在20—24歲的婚姻登記在下降,25歲以后的4個年齡別婚姻登記在上升,尤其25—29歲的婚姻登記上升幅度最快。這實際上意味著婚姻延遲和生育水平下降可能存在因果關(guān)系,當然不排除這也可能是由于生育延遲帶來的。
四、生育水平下降的微觀機理的實證研究
(一)數(shù)據(jù)來源及其處理方法
考慮樣本的典型性和樣本廣度要求,以及數(shù)據(jù)獲得便利性,本文數(shù)據(jù)來源于2013—2015年連續(xù)抽樣調(diào)查,調(diào)查對象是20—50歲的婦女或丈夫,涉及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赤峰市、通遼市、錫林郭勒盟、包頭市、阿拉善盟、鄂爾多斯市、興安盟等7個盟市15個旗縣,獲得問卷872份,其中有效問卷806份,存在輕微的缺省。樣本涵蓋從東到西的人口聚集區(qū)的鄉(xiāng)村和城鎮(zhèn),樣本具有多樣性、典型性、干擾因素少的特征。數(shù)據(jù)真實為結(jié)論可靠奠定了基礎(chǔ),使得研究結(jié)論能夠?qū)?nèi)蒙古自治區(qū)以外的其他省份的人口可持續(xù)發(fā)展和人口治理提供一定的啟示和借鑒。
本文采用雙重差分法評價生育水平的政策響應(yīng)。雙重差分法作為一項非常重要的評估政策效果的研究方法,在勞動經(jīng)濟學(xué)中廣泛應(yīng)用。Eissa和Liebman[20]認為美國1986年稅制改革提高了單身有孩子婦女的勞動參與率;Baker等[21]研究了兒童撫養(yǎng)補貼對兒童母親勞動供給和家庭福利的影響。其基本思路是將調(diào)查樣本分為兩組,即受到生育政策影響的作用組和沒有受到生育政策影響的對照組。本文的對照組選擇祖父母和父母。根據(jù)作用組和對照組在生育政策作用前后的相關(guān)信息,計算作用組和對照組政策前后生育水平的變化,然后計算兩組生育水平的差值,即生育政策的政策響應(yīng)。
生育政策對生育水平產(chǎn)生作用,但是,我們需要清晰家庭對生育政策的響應(yīng)程度。在本文中,由于調(diào)查對象的平均年齡為30歲,剔除調(diào)查對象出生年份在1983年前的家庭(這一年全面實施計劃生育),所以調(diào)查對象作為計劃生育影響的作用組,而調(diào)查對象的祖父母和父母作為對照組。其中,變量P是衡量受到計劃生育政策影響的虛擬變量,受到影響則P等于1,反之則P等于0。變量T代表樣本數(shù)據(jù)是否是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后時期的虛擬變量,是則T等于1,反之則T為0。δ是計劃生育政策對生育水平的凈影響[22]。u為擾動項, 代表其他無法觀察到的、沒有控制的、影響生育水平的因素。為此,建立生育政策響應(yīng)的簡單雙重差分模型:
Y=α0+α1T+γP+δTP+μ
(8)
對沒有受到計劃生育政策影響的祖父母和父母而言,生育水平平均變動為:
dif1=(α0+α1)-(α0)=α1
(9)
對受到計劃生育政策影響的調(diào)查對象而言,生育水平平均變動為:
dif2=(α0+α1+γ+δ)-(α0+γ)=α1+δ
(10)
剔除調(diào)查對象及其祖父母和父母的系統(tǒng)差異,則受計劃生育政策影響的凈影響為:
dif=dif2-dif1=(α1+δ)-α1=δ
(11)
這樣,在模型(8)的基礎(chǔ)上將其擴展至模型(12):
Yit=α0+α1Tt+γPi+δTtPi+βXit+μit
(12)
其中,Yit是我們關(guān)注的t時期i調(diào)查對象的生育水平。Pi是一個二值變量,1 代表調(diào)查對象,0代表祖父母、父母。Tt也是一個二值變量,1代表受計劃生育政策影響后,0代表政策前。Xit是一組可觀測的影響生育水平的控制變量,本文設(shè)為收入。μit是特異性擾動項。α1、γ和δ是待估計參數(shù),用δ來衡量計劃生育政策對變量Yit的影響。β為待估參數(shù)矩陣,衡量控制變量對變量Yit的作用。對模型(12)進行一階差分,得到模型(13),Zi1-Zi0為因時而變收入因素的一階差分,然后對模型(13)進行回歸:
Yi1-Yi0=α+δPi+β(Zi1-Zi0)+(μi1-μi0)
(13)
(二)樣本的描述性統(tǒng)計
1.生育數(shù)量的代際差異
通過對生育數(shù)量的描述性統(tǒng)計可以發(fā)現(xiàn),祖父母、父母和調(diào)查對象的生育數(shù)量、生育存活數(shù)量、生育男孩數(shù)量和生育女孩數(shù)量存在遞減的趨勢,其中,祖父母生育數(shù)量、祖父母生育存活數(shù)量、祖父母生育男孩數(shù)量、祖父母生育女孩數(shù)量分別為6.011、5.474、3.041、2.501;父母生育數(shù)量、父母生育存活數(shù)量、父母生育男孩數(shù)量、父母生育女孩數(shù)量分別為3.93、3.764、1.849、2.075;調(diào)查對象生育數(shù)量、生育存活數(shù)量、生育男孩數(shù)量、生育女孩數(shù)量分別為1.567、1.553、0.854、0.87。調(diào)查對象的祖父母、父母和調(diào)查對象生育存活數(shù)量表現(xiàn)出存活率越來越高趨勢,并且男孩生育偏好越來越低趨勢。調(diào)查對象的祖父母生育水平體現(xiàn)出傳統(tǒng)的多子多福的觀念。此外,對于生育一個孩子的調(diào)查對象家庭來講,也沒有表現(xiàn)出較高的性別差異。
相對于其祖父母和父母的生育水平而言,調(diào)查對象因受到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導(dǎo)致生育水平出現(xiàn)下降趨勢,具有趨同性的特征;計劃生育政策對調(diào)查對象父母的沖擊最大,在這一代出現(xiàn)生育政策影響的民族差異。不排除祖孫三代生育水平下降的原因也可能是收入或其他的因素。為此,本文結(jié)合伊斯特林模型將收入、結(jié)婚年齡、初育年齡結(jié)合在一起,在控制政策變量的基礎(chǔ)上,估計生育水平下降的影響因素。
2.變量的描述性統(tǒng)計
本文擴展伊斯特林模型,選擇金融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等三個維度作為收入和財富的代表進行論證,其中,金融資本包括家庭信貸機會、是否借過高利貸、是否從親友處借錢、貸款方便否、個人總收入、存款和住房使用面積等7個變量,人力資本包括個人文化程度、是否接受過職業(yè)培訓(xùn)、家庭人口數(shù)量等3個變量,社會資本包括擁有特殊經(jīng)歷(鄉(xiāng)村干部、部隊退伍、國企職工)的家庭成員數(shù)量、婚喪嫁娶費用和對周圍信任情況等3個變量,其他特征變量包括年齡、性別、戶口性質(zhì)、獨生子女、職業(yè)和照顧老人數(shù)量等6個變量。為了表述的清晰,本文將樣本變量分為連續(xù)型變量和非連續(xù)型變量兩類進行處理,避免單一處理方式使樣本失真。
具體變量的數(shù)字特征如表2所示。調(diào)查對象的年齡平均為35.091歲,并且85.3%的調(diào)查對象屬于非獨生子女,而且72.9%的調(diào)查對象的戶口屬于農(nóng)業(yè)戶口,75.5%的調(diào)查對象從事農(nóng)牧業(yè)生產(chǎn)和家務(wù)勞動。個人文化程度基本都在初高中及以上,占比達87.2%。每個家庭需要照顧老人2.019人。從金融資本來看,調(diào)查對象的家庭存款平均為15 401.910元,個人總收入為40 170.833元,住房使用面積平均為105.084平方米,大部分家庭沒有信貸機會,這類家庭占比為56.8%,只有21.2%的家庭借過高利貸,81.3%的家庭從親友處借過錢,并且超過半數(shù)的家庭認為貸款不方便,占比為55.6%。從人力資本來看,個人文化程度低于初中(包括初中)的占比接近半數(shù),為47.0%,沒有接受過職業(yè)培訓(xùn)的調(diào)查對象為88.1%。從社會資本來看,擁有特殊經(jīng)歷的家庭成員數(shù)量為0.289人,家庭婚喪嫁娶費用為8 571.177元,超過93.1%的家庭認為周邊事物一半及以上可信任。

表2變量的描述性統(tǒng)計
(三)估計結(jié)果及其解釋
控制計劃生育政策變量,結(jié)合擴展的伊斯特林模型,本文采用一般回歸方法對祖孫三代生育水平(生育數(shù)量、生育存活數(shù)量、生育男孩數(shù)量和生育女孩數(shù)量)與收入的關(guān)系進行估計,結(jié)果如表3所示。對于調(diào)查對象的祖父母而言,收入與生育水平的關(guān)系呈現(xiàn)線性關(guān)系;而對于調(diào)查對象的父母而言,收入與生育水平的關(guān)系呈現(xiàn)U型關(guān)系;對于調(diào)查對象而言,收入與生育水平的關(guān)系呈現(xiàn)線性關(guān)系。但是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對祖孫三代都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實際上,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對生育水平影響的作用是內(nèi)生的,直接影響生育選擇,尤其是生育意愿到生育結(jié)果的傳導(dǎo)。

表3影響祖孫三代生育水平的因素估計
注:*、**和***分別表示在10%、5%和1%的顯著水平上顯著。下同。
1.祖父母生育水平的影響因素分析
祖父母生育水平與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的關(guān)系。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對祖父母的生育數(shù)量、生育存活數(shù)量、生育男孩數(shù)量、生育女孩數(shù)量均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而且具有明顯的一致性。
祖父母生育水平與收入的關(guān)系。從表3可以發(fā)現(xiàn),祖父母生育數(shù)量、生育存活數(shù)量、生育男孩數(shù)量與收入呈現(xiàn)線性關(guān)系,而生育女孩數(shù)量與收入的關(guān)系呈現(xiàn)倒U型關(guān)系,對應(yīng)方程的估計參數(shù)都很顯著。需要注意的是,收入與祖父母生育數(shù)量、生育存活數(shù)量、生育男孩數(shù)量的關(guān)系呈現(xiàn)的是負相關(guān)關(guān)系,即收入越低,生育數(shù)量、生育存活數(shù)量和生育男孩數(shù)量越多。在調(diào)查對象祖父母年代,貧困很容易導(dǎo)致家庭陷入生育困境,在觀念上生育決策越容易受傳統(tǒng)生育文化的影響,越容易追求生育數(shù)量和生育男孩數(shù)量,因為貧困意味著越?jīng)]有條件去改變自然生育狀況,意味著人生的希望越放在孩子的身上。此外,在能養(yǎng)活的前提下多生孩子的意愿是窮人的理性選擇,因為生育成本和撫育成本都比較低,并且可以抵御較高的意外死亡風險,能夠篩選出智力或體力優(yōu)異的孩子,是符合窮人長遠利益的。生育女孩數(shù)量與收入的關(guān)系呈現(xiàn)倒U型關(guān)系,越貧困實際上生育女孩數(shù)量越多。這意味著祖父母一代是存在男孩偏好的,這是一種源于家庭制度和個體社會行為模式、制度化的社會價值取向,因為在中國社會男孩具有女孩所不具備的價值,特別是家庭價值和社會價值。
2.父母生育水平的影響因素分析
父母生育水平與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的關(guān)系。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對父母生育數(shù)量、生育存活數(shù)量、生育男孩數(shù)量、生育女孩數(shù)量均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而且具有明顯的一致性。
父母生育水平與收入的關(guān)系。對于調(diào)查對象的父母而言,收入與父母生育數(shù)量、生育存活數(shù)量、生育男孩數(shù)量的關(guān)系呈現(xiàn)U型關(guān)系,但由于自變量不能小于0,同時又小于最大值,所以Model10、Model2和Model4均是U型曲線右側(cè)連續(xù)的一段,但存在最低點。同時,生育女孩數(shù)量與收入呈現(xiàn)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這就意味著收入越高,生育數(shù)量、生育存活數(shù)量、生育男孩數(shù)量和生育女孩數(shù)量是先下降再上升的過程。
3.調(diào)查對象生育水平的影響因素分析
調(diào)查對象生育水平與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的關(guān)系。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對調(diào)查對象生育數(shù)量、生育存活數(shù)量、生育男孩數(shù)量、生育女孩數(shù)量均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而且具有明顯的一致性。
調(diào)查對象生育水平與收入的關(guān)系。從Model7、Model19和Model23的估計結(jié)果可以發(fā)現(xiàn)收入越高,越不愿意生孩子,生育男孩的偏好不顯著,并沒有出現(xiàn)像父母一代那樣的正U型分布,而是更為明顯的線性關(guān)系,即調(diào)查對象現(xiàn)在的收入不能支持他們提高生育水平,即使有較高的生育意愿。這意味著調(diào)查對象生育水平具有較強的政策響應(yīng)程度。這種差異性的源泉在于收入會在生育成本和生育收益均衡中起到?jīng)Q策作用,導(dǎo)致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的代際差異。調(diào)查對象對于計劃生育有著比祖父母、父母一代更為深刻的感知,因為他們是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主要對象,導(dǎo)致他們更懂得抓住放開生育后增加子女的機會。這實際上為“放開二胎”政策實施后出臺更具代際差異的政策細則提供了可能和依據(jù)。
4.祖孫三代生育水平的影響因素比較
本文將祖孫三代生育水平作為一個整體,論證祖孫三代生育數(shù)量、生育存活數(shù)量、生育男孩數(shù)量和生育女孩數(shù)量與收入、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之間的關(guān)系,將祖父母、父母和調(diào)查對象作為虛擬變量,得到估計結(jié)果如表4所示。

表4收入、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與生育水平的代際差異
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對祖父母、父母和調(diào)查對象的生育數(shù)量、生育存活數(shù)量、男孩數(shù)量、女孩數(shù)量均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這種抑制作用具有明顯的一致性。但這種作用對祖父母、父母和調(diào)查對象卻具有明顯的差異性,其中,對調(diào)查對象的影響最大,影響最弱的是祖父母。這說明生育水平除了與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具有顯著的內(nèi)生關(guān)系之外,與社會經(jīng)濟的關(guān)系也非常緊密,具有顯著的時代特征;同時也間接驗證了借用伊斯特林模型的必要性和科學(xué)性。
此外,收入對祖孫三代生育數(shù)量、生育男孩數(shù)量和生育女孩數(shù)量的影響存在明顯的差異,收入導(dǎo)致生育水平的代際差異比較明顯。從生育男孩數(shù)量和生育女孩數(shù)量的影響因素上也存在較為明顯的代際差異。收入體現(xiàn)了家庭差異,并且能夠通過祖父母、父母和調(diào)查對象等三個虛擬變量將作用強度體現(xiàn)出來。從生育數(shù)量來看,收入顯著地影響生育數(shù)量,影響程度為負,其中,調(diào)查對象及其祖父母也是顯著影響生育數(shù)量,而父母對于生育數(shù)量的影響并不顯著。調(diào)查對象對生育數(shù)量的影響為負,其祖父母和父母對生育數(shù)量的影響為正,作用強度和作用方向存在差異。從生育存活數(shù)量來看,調(diào)查對象對生育存活數(shù)量有顯著的負影響,收入雖然也起負作用,但并不顯著;調(diào)查對象父母的作用顯著為正;調(diào)查對象祖父母的作用為正,但也不顯著。從生育男孩數(shù)量來看,收入、調(diào)查對象及其父母起到顯著的影響作用,其中收入的作用為正,調(diào)查對象的作用為負,調(diào)查對象父母的作用顯著為正;調(diào)查對象祖父母的作用為正,但也不顯著。從生育女孩數(shù)量來看,收入、調(diào)查對象起到顯著的負作用;調(diào)查對象父母的作用顯著為正,調(diào)查對象祖父母的作用為正,但是也不顯著。
(四)生育水平影響因素的判斷:結(jié)婚年齡還是初育年齡
為了判斷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對生育水平的影響,本文在擴展的伊斯特林模型基礎(chǔ)上采用雙重差分對生育水平進行多元回歸模型估計,除了包含金融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財富和收入因素之外,加入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等關(guān)鍵事件,同時選擇性別、戶口性質(zhì)、獨生子女和照顧老人數(shù)量等為控制變量,因為主要考慮與生育水平的相關(guān)性以及模型本身是否存在共線性。加入性別、戶口性質(zhì)、獨生子女和照顧老人數(shù)量等4個變量為控制變量并沒有出現(xiàn)共線性等影響模型本身要求的情況,結(jié)果如表5所示。

表5生育意愿和生育結(jié)果的一般多元回歸結(jié)果
通過一般多元回歸模型估計生育水平代際差異的影響因素發(fā)現(xiàn):在控制了性別、戶口性質(zhì)、獨生子女和照顧老人數(shù)量等變量后,金融資本中是否借過高利貸、個人總收入、存款、住房使用面積至少在10%的顯著水平上影響以祖父母為對照組、父母為作用組的生育數(shù)量,個人總收入的影響為正;個人文化程度和家庭人口數(shù)量等人力資本因素的影響為正并且顯著;對周圍信任情況越高越起到顯著影響作用。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對生育水平下降起到促進作用。對于以父母為對照組、調(diào)查對象為作用組的生育數(shù)量來講,金融資本中是否借過高利貸和貸款方便否至少在5%的顯著水平上影響生育水平,借過高利貸和貸款不方便是生育水平增加的主要原因;個人文化程度和家庭人口數(shù)量等人力資本因素對生育水平影響顯著,二者的作用方向恰好相反;社會資本中的擁有特殊經(jīng)歷的家庭成員數(shù)量和對周圍信任情況均不能顯著影響生育水平。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同樣對生育水平的下降起到促進作用。
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同樣對生育水平下降起到促進作用,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延遲可以顯著內(nèi)生影響生育水平的變化。金融資本中的借高利貸因素會促進生育水平提高。金融資本的脆弱性使得生育孩子成為投資的一種,即從生育孩子的性質(zhì)上判斷生育作為一種投資,只有投資率降低,才會帶來“改善門楣”的預(yù)期。提高收入和更為便捷的貸款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人力資本中個人文化程度和家庭人口數(shù)量雖然都顯著地影響生育水平,但作用差異較大,尤其是個人文化程度。這是由于育齡婦女的生育選擇和勞動參與以及工作機會之間存在沖突,生育的投資品性質(zhì)使育齡婦女的收入提高,導(dǎo)致生育的投資回報率較低,進而放棄或中斷生育,帶來較低的生育率[23]。社會資本對生育水平影響不大。
(五)生育水平影響因素的分解:結(jié)婚年齡還是初育年齡
為了進一步找出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對生育水平下降的作用,本文結(jié)合Oaxaca 和Blinder的分解模型對生育水平下降的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因素進行分解,按照24歲以下、25—29歲、30—34歲、35—39歲以及40歲以上等5個年齡段將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進行劃分,然后在Logit模型的基礎(chǔ)上對生育水平下降進行分解,結(jié)果如表6所示。

表6生育水平下降的分解結(jié)果
從表6可以發(fā)現(xiàn),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的延遲可以解釋生育水平下降63.6%的原因,超過一半的比率,遠遠超過了社會經(jīng)濟因素;年齡別間的差異(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不能解釋的影響)則解釋了36.4%的原因。此外,從組內(nèi)和組間的角度來看, 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的年齡別內(nèi)部影響占80.4%,年齡別間影響僅占19.6%, 則說明現(xiàn)有的生育水平下降主要還是存在于年齡別內(nèi)部,即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的延遲。
五、結(jié)論與建議
本文結(jié)合2013—2015年連續(xù)抽樣調(diào)查數(shù)據(jù),論證生育水平下降的宏觀現(xiàn)象和微觀機理,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婚姻延遲和生育水平下降存在因果關(guān)系,為此結(jié)合伊斯特林模型、Oaxaca-Blinder模型和雙重差分法驗證這一關(guān)系,結(jié)婚年齡和初育年齡的延遲可以解釋生育水平下降63.6%的原因;金融資本是帶來生育水平代際差異(生育水平代際間下降)的主要原因,生育成本和生育機會成本比較高是影響當前生育水平下降的因素之一;人力資本中個人文化程度和家庭人口數(shù)量也會影響生育水平。在這種情況下,提高當前生育水平,需要做到:
第一,減少學(xué)制,降低結(jié)婚年齡。可以考慮壓縮中小學(xué)學(xué)制,降低小學(xué)入學(xué)年齡,合并大學(xué)和研究生的學(xué)制,全面落實學(xué)分制。此外,降低結(jié)婚年齡,尤其在現(xiàn)有基礎(chǔ)上,女性降低1歲,男性降低2歲是比較可行的。
第二,建立多重補貼體系,間接提高居民家庭的金融資本。在家庭收入短期內(nèi)不能大幅提高的情況下,補貼是鼓勵生育非常好的方式。國際上政府拿出高補貼,盡力讓生育多個孩子的居民家庭沒有后顧之憂,提高生育水平的措施非常有效。因此,需要在生育補貼、減稅、父親假、無薪假等政策細則體現(xiàn)出生育的激勵性。
第三,生育的家庭擔負向社會擔負轉(zhuǎn)變。在居民家庭生計改善困難時,需要從完善生育保險制度、構(gòu)建工作與家庭的平衡機制等生育社會化負擔機制來提高生育水平。可以通過為育齡婦女創(chuàng)造生育條件,降低生育成本,同時降低女性工作責任與家庭撫養(yǎng)責任的矛盾,提高生育水平。此外,還要通過配套的勞動力市場政策來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包括更加靈活的就業(yè)時間、更長的生育假期,通過這種方式來提高生育水平。
第四,采取多種手段直接提高居民家庭的金融資本。面對撫養(yǎng)孩子的經(jīng)濟壓力,通過減稅和調(diào)整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間接提高居民家庭收入緩解撫養(yǎng)孩子的經(jīng)濟壓力和降低生育成本,在“放開二胎”政策下才能實現(xiàn)想生到敢生的跨越。此外,還要給予居民家庭更多在正規(guī)金融方面獲得貸款的機會和額度,幫助他們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新和改善生計,實現(xiàn)促進生育水平提高的目標。
第五,建立人力資本投資的個人、社會和企業(yè)共同承擔機制,保障勞動者學(xué)習和人力資本提高的機會。在健康、文化、遷移、培訓(xùn)等方面提高人口素質(zhì),達到提高勞動者人力資本的作用。應(yīng)通過加強平衡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利益的制度設(shè)計來完善人力資本投資體系,間接影響居民家庭生育決策,緩解生育壓力,保障新的生育政策順利實施并獲得較高的政策響應(yī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