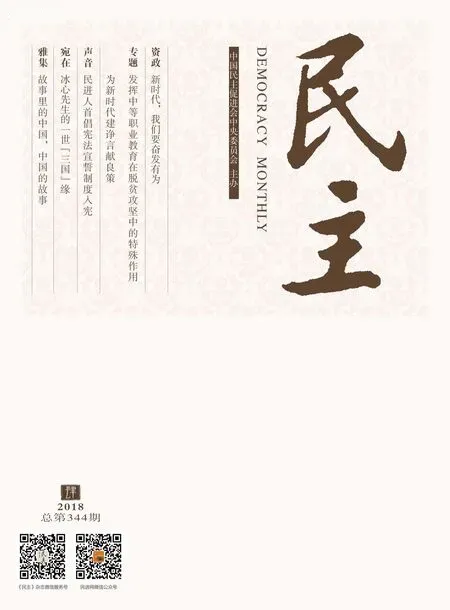梁實秋:一生戀家顯忠貞
□王 淼

梁實秋與程季淑
梁實秋是我國著名散文家、學者、文學批評家、翻譯家,在長達70余年的寫作生涯中,為中國文壇留下兩千多萬字的著作,編纂的英漢辭典影響了幾代中國人,其翻譯的莎士比亞著作更奠定了他在翻譯界的權威。
梁實秋在回憶譯完《莎士比亞全集》這一巨大工程時曾說:“我翻譯莎氏,沒有什么報酬可言,窮年累月,兀兀不休,其間也很少得到鼓勵,漫長途中伴我體貼我的只有季淑一人,最后37種劇本譯完。”在祝賀莎氏全集梁譯本出版的慶祝會上,他的友人也一致認為“《莎士比亞全集》的翻譯之完成,應該歸功于梁夫人”。
此話不假,梁實秋成功原因之一就是有個賢內助。梁夫人程季淑女士畢業于美術專科學院,在北京公立第三十六小學任教,兩人結婚于1927年2月11日,新郎26歲,新娘28歲。程女士以妻子以大姐的身份關懷著梁實秋,為其譯作、創作、教學的工作創造了一個極其和睦溫暖的家庭環境。
對老人,程季淑是一個孝順的媳婦。抗戰開始后,梁實秋特意從武漢趕回北京接自己和友人的家眷。只因高堂有病,無法成行,梁只身先歸大后方,留下夫人照料老人和三個兒女。直到1944年夏,歷經艱辛,長途跋涉,程季淑才率家趕到重慶北碚團聚。對二子一女,她是位慈善的母親,承擔起全部養育、 教育之事。作為丈夫和父親的梁實秋對此深有體會,一直懷有感激之情。
對丈夫,程季淑則是賢惠的妻子,梁實秋的生活起居,都由其安排。尤其是1958年間,身邊僅有的小女兒文薔留學去美定居后,兩人更是相依為命,互相關照。從此時至夫人逝世的16年間,梁能不顧年老,完成《莎士比亞全集》的最后譯稿,不間斷地進行寫作和辭典編寫,前8年還堅持課堂教學,實在得力于夫人的安排和支持。在慶祝莎氏全集出版之時,正逢文薔全家返臺探親和梁、程結婚40周年(結婚年按農歷算為1926年),到會各界人士趁此機會,一起祝賀梁家三喜臨門,祝賀梁和夫人白頭偕老。
1972年5月,梁賣掉在臺灣的住房,與夫人一起遷居美國西雅圖的小女兒處,沒有料到兩年后夫人離去。1974年4月30日上午,兩位老人去市場購物,豈知“市場門前一個梯子忽然倒下,正好擊中了她”,程季淑因搶救無效而不幸去世。
夫人的不幸,使梁實秋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40余年的夫妻生活,給生者留下了無限的懷念。3個月后,梁出版思念專集,因程女士埋葬于西雅圖北郊的“槐園”,故書名定名為《槐園夢憶》。在臺灣師范大學英語系舉行的追悼會上,梁實秋特意寄去挽聯:“形影不離,五十年來成夢幻,音容宛在,八千里外吊亡魂。”
梁稱自己是“古典的頭腦,浪漫的心腸”,他的大半輩子就是這樣。雖為文人,且接受過不少西方文化,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對待生活、對待情感卻是非常嚴肅的,“發乎情止于禮”,頗有古代學士君子的味道。他把那些以“浪漫”為名,“縱酒、狎妓、放蕩不羈”,“色情狂、駭俗震世、性欲橫流”等等行為,均視為“文人無行”的表現。他說:“我們不能因其人之無行遂誹薄其文,然亦不可因其人之文遂容忍其人之無行。我們批評文學,采取文學的標準;我們批評文人的行為,只能采取唯一的道德標準。”有人曾把關于他的花邊新聞“告密”于梁夫人,她只一笑道:男人嘛,隨他逢場作戲好了。夫人了解丈夫,不會做出有礙觀瞻的風流之事。
梁實秋對愛情的忠貞,可敬可佩,但也和另外兩位女性,結下難以忘懷的友誼。一位是龔業雅女士,她在抗戰期間梁夫人不在重慶時,默默地照料過梁的生活,成為先生的崇拜者。梁實秋在《雅舍憶往》中說:每當寫反映四川民情的雅舍類散記時,“每寫一篇,業雅已先睹為快,我所寫的文字,雖多調侃,并非虛擬。所以業雅看了特感興趣,往往笑得前仰后合。經她不時的催促,我才逐期撰寫按時交稿。我生平不請人作序,但是這個小冊子,我請業雅寫了一篇短序。”為感謝龔業雅女士的幫助和關心,梁先生特意把自己散文創作的精華定名為《雅舍小品》,“雅舍”并非他的書齋名,如此喜愛此名,一直沿用此名,可見他對這位女性朋友的思念之深。
另一位是名家謝冰心女士。兩人相識于赴美留學的郵輪上。到了美國,冰心女士在韋爾斯利女子大學,梁實秋在哈佛大學,兩校相隔一小時的路程,節假日兩人經常見面,磋商文學,并且曾同臺用英語在波士頓考普萊劇院演出過《琵琶記》,一個演宰相之女,一個演蔡中郎。后因演趙五娘的謝文秋女士與朱世明訂婚,謝冰心跟梁先生開玩笑說:“朱門一入深似海,從此秋郎是路人。”以后“秋郎”成為梁自己常用的筆名,書齋也取名為“秋室”。
回國后,梁實秋與程季淑、謝冰心與吳文藻結婚,兩家成為好朋友,時常來往,互相觸發對方的創作靈感,成為文學道路上的摯友。抗戰時《星期評論》上定期出現“小佳”和“男士”所寫的小品文,一時引起讀者的注意,紛紛猜測小品文究竟出自哪位名家之手,豈知“小佳”為梁實秋,“男士”即冰心也。
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梁、謝交往被臺灣海峽所隔開,兩人音訊斷絕。1968年12月,當梁聽到冰心夫婦自殺去世的謠傳時,無法核實,信以為真,特意寫下悼文《憶冰心》,遠在大陸的冰心得知后很是感激。當梁得知冰心女士健在時,又在刊登《憶冰心》的《傳記文學》上,發表《冰心尚在人間》,祝福老友。
1981年,梁移居美國的小女兒梁文薔探親回來,見到了闊別30余年的姐姐和哥哥,同時也向冰心女士轉達了其父的口信“我沒有變”。冰心老人也深情地對文薔說:“你告訴他,我也沒有變。”從幾十年的“沒有變”中,可以看到兩人心心相印。可謂是文壇知己,流水知音。梁先生突然病故后,冰心寫悼文,追思兩人之間純潔、高尚的友誼。

梁實秋與韓菁清
梁實秋還有過第二次美滿婚姻。夫人去世后,他和女兒全家住在一起。白天女兒文薔、女婿邱士耀、兩個外孫上班上學后,家里只剩下寂寞的老人,他不無風趣地說:“八個小時沒有說話,簡直是在關單間牢房。”故在1974年10月間返回臺灣,此時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遇見了昔日的歌星、影星韓菁清。
那是在回臺后不久,梁為聯系出版《槐園夢憶》一書,前往遠東圖書公司,正巧韓菁清也在那里查找一本梁實秋主編的辭書。兩人一見鐘情,一老一少開始了不平常的來往。熱戀中的70多歲的老人,煥發了青春,像小伙子一樣,“每天中午,梁教授必從下榻的華美大廈,抱著韓菁清愛吃的雞翅膀、鴨肫肝等零食去看韓菁清”。每天消磨到深夜兩三點,第二天一大早,梁又到韓家旁邊站崗等候。到1975年1月,梁實秋按計劃返回美國時,兩人已經難分難舍。韓女士曾談到過此事,在西雅圖,他每天兩封,甚至三封的給她寫信,“每封信都是密密麻麻的兩大張,背后,旁邊全寫滿了。每天,他都要走很遠到郵局發信,哪怕是冰天雪地。而他一天收不到我的信,就坐立不安,連飯都吃不下。”兩個月后,梁先生回到臺灣,下飛機時帶著兩個公文包,里面裝滿的則是韓的情書。
梁韓戀愛,轟動了臺灣,遭到群起而攻之。梁的許多弟子,甚至組織起“護師團”,反對這位新師母。旁人認為二人不能結合的理由不外乎是:一、教授對不起亡妻;二、二人年齡懸殊太大;三、二人中一人為讀書人,一人為文藝圈中人,無共同語言,無一起生活的基礎。總之要梁先生保全名聲,厲行“文人有行”,做到“古典”冷靜,不要浪漫無度,應當機立斷,忍痛割愛。無奈梁主意已定,堅定不移,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她是一位正直、善良、熱誠而又慷慨的女性,我知道,我們(指梁、韓)是屬于兩個不同圈子的人,可是,這有什么關系,愛的力量超過一切。”此時已無法分開兩人,梁實秋在返臺與韓菁清團聚之前,曾特意填詞一首慶賀自己的二度婚姻:“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贏得,天涯旅羈,教說與,春來要尋花伴侶。”5月8日,梁韓二人在“國鼎川萊館”正式舉行婚禮。
梁自己說過:“我是個喜歡家庭的人,14歲以前,舍不得離不開父母。結了婚后,我就一直無法離開太太,不幸她(程季淑)去了,于是,我又成了個沒有家的人。”韓菁清給梁實秋的晚年帶來了“家庭”的幸福,結束了自程季淑去世后開始的凄涼生活。
晚年的梁實秋,身體不算太好,每天早睡早起,從未停止過寫作。夫人韓菁清擔心地說:“八十歲的人了,還在榨腦汁,真可憐。”為此,她還跟出版界的友人開玩笑,請對方發表梁實秋的文章時應多給一點稿酬。
梁實秋80歲生日時,友人送上一首詩賀壽:“秋公八十春不老,敦厚溫柔國之寶,雅舍文光垂宇宙,窗前喜伴青青(指韓菁清)草!”妻子的愛戴、安慰和照料,增加了梁實秋的創作欲,延長了創作生命。夫妻相處的13年,被他們在臺灣文學界的友人稱之為“梁韓的四千多個春天,是令人羨慕的人間愛情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