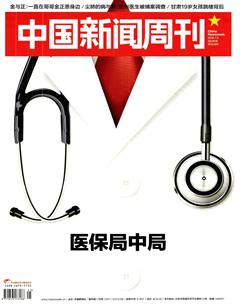誰在命運面前都無計可施
楊時旸
這身世里掩藏著宏大的歷史,濃縮的個人經驗,莊嚴的精神悸動和燥熱的性啟蒙互文,典籍與色情雜志呼應,這一切微妙的竊竊私語都化進了冰冷泥濘的現實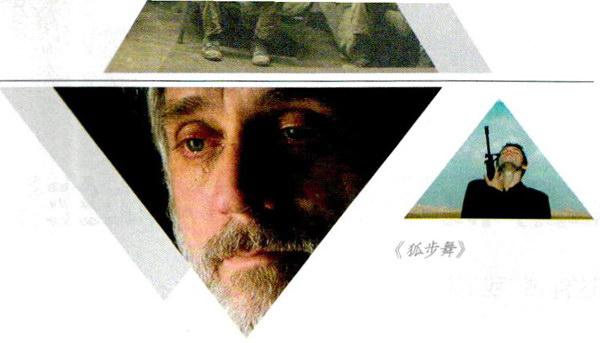
《狐步舞》
怎么說呢?《狐步舞》甫一開場就彌漫著一股荒誕不經卻又嚴陣以待的古怪氣質,它始終肅殺、陰郁,卻時不時斜刺入一截讓人們忍俊不禁的橋段,但似乎又讓人笑不出來,很快就被揮之不去的陰冷與凝重遮蓋掉了。它就這樣在不同的氣質之間跳來跳去,塑造出一種難以名狀的特殊腔調,混搭著家庭劇和戰爭片的類型,既沒有宣泄講述家庭中的情感,也沒有鋪排戰爭的現場,它似是而非,但意外因此力道十足。導演毛茨自己說,他想在這部電影中呈現出古希臘悲劇的氣質。確實,從某種程度上去看,它確實做到了,用一個現代故事呈現了古典的意蘊——悲愴的感情氛圍,宿命的輪回報應,無處可逃的命運之手。
故事是從報喪開始的。鏡頭緊緊盯住母親的臉,然后,人物暈眩,露出背后玄關的一幅畫作,抽象的線條,纏繞在一起,像胡亂揮就又像有條不紊,散發濃郁的精神狂亂氣質,鏡頭轉過彎,露出站在原地震驚不已的父親。這一層一層的顯露和剝落就像一次對之后故事的預言,一切都是一層藏著一層,有待于慢慢展開。
《狐步舞》是那種適合細細觀看細節的電影,相較于劇情的演進,那些豐沛細節中的象征、隱喻以及背后展現的精神危機,是更有趣的內容。玄關懸掛的那幅抽象畫,以及這所宅邸鋪滿的幾何圖案的地磚,還有方圓相稱的窗子,都在通過明確的構圖展現意義,一切層疊又排布,充滿眩暈感但又不停地強調秩序。這就是《狐步舞》想要顯露的特征,混沌與清晰,非線性與線性的干擾與纏繞。
那場報喪是肅穆的,軍隊的相關人士前來告訴父母他們的兒子死亡的消息,但旋即,這種肅穆被推到極致之后產生了間離的荒誕感,士兵們訓練有素地給昏死的母親注射鎮定劑,像在戰場上照顧傷員一樣,配合起來將她送到臥室,給男人設置每小時一次的鬧鐘提醒對方喝水。導演在一次采訪中提到,以色列軍隊去報喪時基本就是如此,有一套高效的流程。而當這套流程被藝術化地呈現在那幢充滿隱喻符號的房間里時,產生了一股難以言明的感受。死亡的降臨是急促的,但親人的接受過程應該是緩慢的,但在這里,這種應該緩釋吸收的悲傷被納入了一套軍事化的規訓,荒誕再一次被凸顯。而更荒誕的是,當悲傷即將被確認的瞬間,反轉又一次降臨,父母被通知,發生了錯漏,死難者是同名同姓的另一個男孩,但誰知道這不是喜訊,只是另一場命運玩笑的開端。
這故事分為三幕,空間,也就成為了《狐步舞》的另一層重要的敘事基礎。房間一戰地一房間,就像狐步舞,平移,后撤,平移,回歸。在一種看似對稱、平衡和閉合之中,袒露那些微妙的變化,一切從表層上看,已經回到原位,完成閉環,達成平衡,但實際上,內里一切都已徹底改變,這就是這部電影想傳遞的況味。所以,非要總結這部電影的情節,無非就是一次虛假的死亡和一次真正的死亡,以及夾雜在二者之間的私密與宏大交織的意識流。
如果說第一幕房間中呈現的是荒誕,那么第二幕戰場的荒誕感就更加濃烈,而在濃烈之外又平添一絲超現實的氣味。與其說那是戰地不如說那更像流放,而現實層面的流放之外更有精神意義的放逐,幾個人在—起討論著自己的身世,這身世里掩藏著宏大的歷史,濃縮的個人經驗,莊嚴的精神悸動和燥熱的性啟蒙互文,典籍與色情雜志呼應,這一切微妙的竊竊私語都化進了冰冷泥濘的現實。
這故事講了周而復始,以及無法掙脫的蒼涼,年輕人躲避于戰火,卻死于看起來人畜無害的駱駝,惹人發笑嗎,卻又無比凄涼。最不可言說的兩個字或許就是“命運”,在它面前誰都無計可施。這部電影的海報中,人臉上有一個橡皮膏交叉粘貼的×,那標記來源于色情雜志封面敏感部位的張貼,欲蓋彌彰的封條,看似禁忌實則充滿魅惑,就像這欲蓋彌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