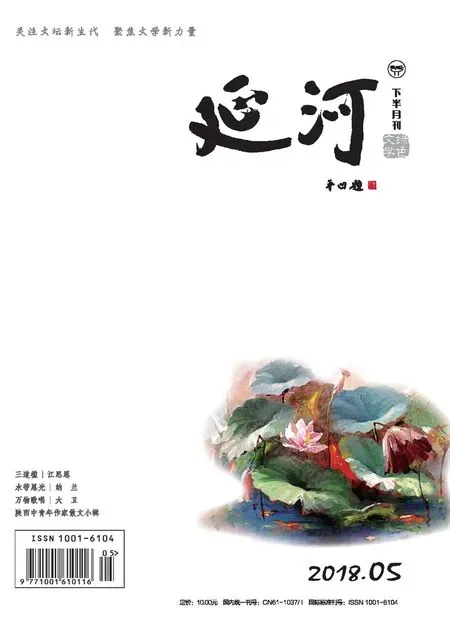無名氏
彭 月
汽車在黝黑的山間奔走,嚶嚶如迷路的孩童,視線無法逾越的山那邊,躺著一具被毒藥腐蝕的白骨。
那個一輩子沒走出過大山的女人,生前膽小如鼠,頭上長年裏著與山路一樣長的絲帕,他們說,她是繼承傳統的民族文化,我知道她不像他們所說的這般偉大,她連什么是民族文化都聽不懂,怎么會去繼承。
她是唯恐山里的落葉,砸斷她漸白的頭發。她說起話來,如同細微的山風,從耳邊拂過,你稍不留神,就會錯過。她告訴過我,聲音大了會驚擾山神的酣睡。那雙青筋凸起瘦弱的小腳,總是躡足輕行,時而駐足,待歸巢的螞蟻先行。
鄉間的忙活,除了地里的莊稼,圍欄里的豬牛,就是三五一堆聚在一起嚼張家酒甜李家酒酸了。我聽她們嚼過她,說起她的時候麻臉媳婦沖我努了努嘴,另兩個滿不在乎,不在乎的表情下更多是鄙夷又有點兒挑釁:又小,又傻。大有不足為患的意思。
她的過往像一本書,農婦們往指頭上呸口唾沫,翻開解讀了起來……
你知道吧?反正我是知道的,徐氏從小父母雙亡,十歲就被大嫂送去周家當了童養媳,說是童養媳,其實就是免費丫鬟。十六歲那年跟周成貴那半傻兒子成了婚,半傻不知是真傻還是裝傻,或許半傻就是有一半是聰明的。半傻吃飯也要她喂,成天抱著牌玩,廁所都懶得上,脹了就尿襠里,一尿就沖她喊:換洗、換洗,你個傻婆娘,聾子不是?她抱著褲子小跑進門,濕答答的褲子扔到她頭上,褲子領會了主人的意思,叉著兩條腿霸氣地騎在她頭上。半傻光著身子又叫又跳:沒用的死婆娘,再有下次滾回你自己家去餓死算逑。
聽說半傻后來被牛頂死了,公婆將半傻的死歸咎于徐氏的失職,他們罵她喪門星,白吃白喝浪費了他家口糧,后悔當年怎么沒注意她生著一副克夫相。將她趕進牛棚關了十多天,他們相信老天就是王法,王法是公正的,讓牛頂死她,這樣他們的半傻在陰間也有人侍候。
徐氏娘家大哥在周家大門口嚷嚷活要見人、死要見尸,圍觀看戲的人漸漸多了起來,有人等不及戲的拖延,就拉過他往牛棚指了指。
大哥拖出到餓得只剩半口氣的徐氏,她像塊棄置糞坑而撈出待瀝干的殘布,躺在院壩里長條條的散發著牛屎尿騷味。周家老兩口就是此時被這牛騷味通了竅的:半傻的死絕對是她與牛串通好了的,牛還是崽子時一直是她在喂,牛是通人性的畜牲,是她教唆牛對半傻痛下殺手的。殺人動機很明顯:半傻說到底還是個傻子,她的丈夫是個傻子,丈夫傻子該死。教唆牛的人更該死!
徐氏的大哥本來想讓周家賠償點兒什么:我妹還沒長成人形就給你家做牛做馬,如今死了男人你家還這么待她,道理上是說不過去的。你掂量掂量,一斗米或幾塊大洋也是個意思。他的目的類似于現在的精神賠償,在這一點上周家與徐家大哥雖是農民,但思想上還是覺悟上都挺超時代的。當周家也存在這個覺悟時,大哥明顯占不到上風,何況周家還是富農。
幾個婦人嘖嘖了一番,麻臉媳婦搞了一下類似文章的段落總結:不論你怎么想,人家死了個兒子,你妹再慘,也還是喘氣的不是。
徐家大哥背著奄奄一息的徐氏回了家,在門口喂雞的大嫂一腳踹向愜意吃食的老母雞,老母雞被突如其來的飛腳驚得返了祖,咯咯尖叫著“嗖”一下飛到了泥巴墻外。
徐氏回來后,徐家齜牙咧嘴的土墻房四周充斥著雞在慘叫狗在哀號的混亂狀態。
這種狀態持續到一個月后的早晨,大嫂左手提刀右手拎著試圖掙扎又動彈不得的老母雞,沖著正在掃地的徐氏大罵手里的母雞:沒用的東西,白吃食,蛋也不拉,抬臀就一屁眼雞屎,掃把星。
彭定康就是這時踏進徐家門坎的,他的到來,解救了差點儆猴的老母雞。
就這樣,全身上下至少掛了兩斤補丁的彭定康,在當天中午就以一把不足一斤的面條作為聘禮,領走了徐氏。
林二奶伸出樹皮樣的手擤了把鼻涕,扶著墻抬起右腳往解放鞋底擦了擦:就是,來了九年肚子都沒動靜,彭定康也是老實人,歹話不講半句,第十年她爸就落地了。林二奶往蹲在地上玩石子的我抬了抬下巴。也怪了,打那后就沒見她肚子癟過,愣是一口氣生了五個兒子一個姑娘。
六月,我赤足模仿旋轉的陀螺,她與周圍的山一起搖搖晃晃地出現在我還是如漆的眸子里,她的臉上被山風拂起漣漪,對著我招了招手,坐在滿地落葉里,解開土布圍裙,那里面躺著一群臉頰潮紅的桃子:“快來嘗嘗,甜。”我和她并排坐下,咬的蜜汁飛濺。
我說:“我想去你家山里玩,聽他們說你家床下都是凸起的青石頭,你家房前屋后全是山。”她望著遠處的山巒,小聲嘀咕道:“山里有什么好玩的,窮得耗子都不進門,還是你們有水田的地方好。”我站起來把桃核扔了老遠:“那你喜歡就來我家住吧。”她起身拍了拍屁股上沾著的枯葉,把我拉下來又坐在了地上,伸手把我的腳抱在懷里,用土布圍裙反面拭擦:“那是命好才住得起的。”
她在門口把我放了下來,額頭上滿是密密麻麻的汗漬,我走了幾步沒聽見她跟上來,回頭叫她,她揮揮手:“去吧,天要黑了,我還要趕路。”我轉身正要走,她的媳婦開門出來了,說來了怎么不進家,站在門口干什么。她靦腆地笑了笑:“不了,我上個廁所,廁所在哪?”我在窗下拿過一雙船一樣大的拖鞋趿在腳上,說走我帶你去吧。我站在廁所門口扯了根狗尾草來回甩著圈圈。她走了出來,邊系褲帶邊頻頻回頭張望:“你們這廁所,比我們住的房子還好。”我樂了:“你真好玩,廁所能住人嗎?喂,你的褲帶顏色怎么跟我以前穿的那件舊衣服一樣。”她把衣服往下拉了拉:“就是你的衣服改的啰。”
她兒媳婦還站在門口:“天黑了,要不就在這住一晚明天再回吧。”她把圍裙撩起一個角,手裹在里面輕輕地搓著:“你看……那……個……你們工作忙,要不以后我來做飯給她吃吧。”媳婦臉上客套的笑容沒了。她扯了扯嘴角寒暄道:“不用了,你去給他們幾家做吧,她沒這個福分。”她輕輕哦了一聲,轉身走了。我看著她淺藍色的背影,慢慢消失在小路轉彎盡頭。
我的眼睛,曾經在桃子的香味里接納了整個藍天。
凌晨三點的木窗,又像她出現時一樣抖動起來,我咽了咽口水,以為是她又送來了桃子。她的兒子推開了門,淚水灑在如水的月光里:“她走了,服毒自殺。”
我爬起床,站在窗前,那晚的月亮,吞噬了蒼穹與地獄。她曾經告訴過我,地獄是沒有光的,一片漆黑。可是那天晚上,我分明看見了月光穿透了窗外的地面,她的身體薄如蟬翼,在一群低著頭行走的人群里,轉過身看著我,手里捏著一個帶著綠葉的桃子,她大概是想遞給我,可擁擠的人群,把她擠的越來越遠。她的身影快要消失的時候,我大聲地問她:“你是要去地獄嗎?她好像點了點頭。”
锃亮反光的棺木前,我看著自己的影子:瘦小、干癟、營養不良的黃發軟塌在蒼白的臉上,我低頭用腳尖撥弄著一個黑癟的桃核。女人們哭的撕心裂肺,她們都把眼睛和鼻子隱藏在手帕里。唯一留下一張敞開的嘴,數落著棺材里那個人的殘忍、她的薄情寡義:怎么就那么心狠,丟下圈里那幾頭豬和馬遭罪?還有四十多歲以及三十多歲的兒子和已見面的、未謀面的孫子。她的罪名仿佛罄竹難書。她們急得集體哀號,嘴里又訟起了詩詞一樣的悼詞,我笑了起來:早晨她們神秘地聚在鄰居家的房子里,讓鄰居上初中的兒子拿著一本劣質紙張的地攤書,一字一句念給她們聽。她們微張著嘴,聽到不凄慘的詞句時,像一群落在曬谷場的麻雀,嘰嘰喳喳地交換了意見,說這幾句不行,跳過跳過。不行的意思大概就是句子表達不出她們的哀傷吧。
她們似乎在進行一場朗誦大賽。激情揚起的時候,她們伸出手,拼命地拍打著棺材,旁邊的人一擁而上,用上了背糞的力氣拉住她們,大概是擔心她們傷心欲絕,會撞棺同歸吧。
棺木我認得,是她在趕集天趕兩頭豬換回來的,因為她氣喘吁吁地走進我家,揭開一層又一層衣角,在貼身的褲腰里掏出幾張百元大鈔,遞給她的兒子讓他辨真假,她搞經濟工作的兒子鑒定鈔票那是相當官方的。
他問她:你把豬賣了干啥?她邊往褲腰里塞錢邊回答:買棺材呀,我看好了,王木匠這次打的棺材最起碼是十六年以上的松木。
她捋好了衣角,拍了拍確保錢的安全,抬頭看我在看她,她尷尬又靦腆地笑了笑:死后睡敝亮厚實一點的房子,舒坦。
我被擠出了外圍,一只鞋子與我的腳分離開了,我揉了揉腳,弓著腰想撿回鞋子,她的媳婦不知道什么時候把紅得干澀的眼睛從帕子里放了出來,狠狠地瞪著我:滾,小畜牲,沒人性,還笑的出來?她的聲音像她圍欄里那只被蛋卡住肛門的鴨子。我忍住了笑,看了看周圍,她們都默契地搖了搖頭,目光如炬,盯著我這個滿臉堆笑的未成年女人。
我局促地用裸露的腳趾搓了搓那顆跟著我一起擠出來的桃核,它那層薄薄的肉,已經被我搓的打了皺縮成一堆褶皺,露出了黃色的骨頭,骨頭縫里爬滿了彎彎繞繞的紅血絲。
我往后退了退,緊緊地貼著糊著《人民日報》的木墻壁。試著敲了兩下,薄、真薄。真害怕她們悲傷的失去理智,把我扔進棺材里。那里面雖然厚實,可一定很黑,也不知道她的袖子上,帶沒帶上那片藍天。如果帶著,我倒是可以進去,告訴她樹上的桃子,已經被這幫悲傷的女人瓜分了,我只能踩著她們因為悲傷而來不及吞下的桃核玩玩。趁她們不注意,扭過頭瞅瞅已經泛黃斑駁的報紙,那上面油黑的鉛字印著“同意胡耀邦辭去黨中央總書記職務的請求,推選趙紫陽代理黨中央總書記”。你看,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樣,不喜歡的事,不干就是了,可不像棺材里躺著的那人,用死來逃避。
我像一只陰溝里爬出來的老鼠,在人群中竄來竄去,偶爾駐足停留,他們三五成群壓低著嗓門,在議論著結束棺材里那個女人的毒藥,只有在意見出現分歧時,才稍微提高了分貝。她的鄰居,是個山歌皇后,她的發言,似乎很有權威,眾人禁了聲,她很滿意地揚起手,把垂在胸前的辮子甩往身后,辮子扎進我的眼里,我悶哼了一聲,它不屑地從我的鼻頭劃到嘴角,然后落下。她回了回頭,扁了扁那地包天的嘴皮:“是半瓶敵敵畏加一瓶白酒。”人群錯落有致地發出了“哦”的如釋重負。我揉著還在刺痛的眼睛轉身走了,他們大概是得到了滿意的答案,分頭散了過去回到自己的崗位;有的蹲在地上洗起了碗,有的抱出一匹白布,一人扯著一頭,“哧溜”一聲,揚起手里掛著線頭的白布:還有誰沒有得孝帕?有的拿著幾根蔥撕去了爛皮,蔥露出雪白的酮體,濃郁的香氣和靈堂前冉冉升起的香煙在空中纏繞在一起。
香灰卷曲出一個弧形,我盯著那根細簽,細微的火光再也承受不住它的卷曲,“啪”的一聲落進了插香的黃豆里。周圍人聲鼎沸,大概他們沒有誰聽見這聲巨響,太輕微之物,它的聲響是讓人聽不到的。
就如她,為土地、為傳宗接代而生的身體不行了,像一把挖卷了口的鋤頭,擱在哪都占地方。扔在石頭上,也只能發出一聲悶響。
我收回了目光,克制住想告訴他們供香發出了鞭炮響聲的沖動,有誰會相信我這個小畜生的話呢。他們肯定會哈哈大笑,樂不可支地指著我:“腦殼有病,傻子!”我可不想逗他們發笑,怕破壞了悲傷的氛圍。
我繼續無目的地游蕩著,走進她的房間里。她的男人,淚眼婆娑地坐在一張掉了漆的椅子上,我抱歉地笑了笑,轉身想退出來,他撩起衣角擦了擦眼角:“進來坐坐。”我又笑了笑走了過去,木床上褪了色的床單皺在了床中央。沒皺的那部分大概是為了應景,湊合地扭了幾縷,像手指的抓痕。我坐了下來,伸出手指往那抓痕上比了比。我的手指太短,怎么都合不上,便作了罷。
門外的镲聲響起,做法事的先生帶著徒弟念起了超度亡魂的佛經。不知道先生是不是怕別人聽清楚了搶他的飯碗還是怎么,我豎直了耳朵也聽不清楚他們念的究竟是啥。我聽不清可能因為我是凡人,神仙聽得清就行了,這是他們之間的暗號,就如同奪去她生命的敵敵畏和白酒,它們都有默契,知道怎樣才能把她的魂與肉體分離。菩薩和先生接上了頭,就會開后門把她的魂從地獄提出來,超鍍的金光閃閃,再為她打開天堂的大門吧。反正也不是我這小畜牲能懂的。

屋里的氣氛很靜謐,靜謐得只聽見她男人喉嚨里發出哧呵的呼吸聲,我知道葉子煙抽多了都這樣,我家的幾個鄰居呼吸聲也是這樣,他們的手上,常年不離手的竹斗煙桿和他手上這根一模一樣。他的眼睛又婆娑了起來。我扭著床頭柜的門鎖,吧嗒吧嗒和著他喉嚨里的哧呵聲:“你的風眼還沒醫好嗎?”他又抬手擦了擦:“嗯,這是老病,斷不了根。”
隔壁房間里,他的幾個兒子爭執了起來,聲音都有著刻意壓沉的慍怒,我跟他沒再說話,他的哧呵聲在爬到喉嚨之前也放輕了動作,憋得臉呈紫紅色。我們都在偷聽。也不是偷聽,聲音的速度快過光速就是這個道理。
他們爭執的大概意思就是因為她生前的最后一個月是輪流到誰家贍養,哪家執拗地向他的兄弟們扳著指頭數著那一個月的費用。零零總總大概是她有一次感冒,買藥用去了多少錢,她喂豬的飼料,他出了多少錢。其他的幾個兄弟表示抗議他這種說法,他們說這種錢他們也出過。甚至還為她添置了一件的確良的新衣,有一個好像真的發怒了,他低聲吼道:“那你把那件衣服拿回去吧,反正她也沒穿過,還是新的。”言下之意是安葬費得平攤,誰也別想占便宜。又一陣沉默過后,我聽見開門的吱呀聲,接著咣啷一下重砸,床頭上那張掛著油厚灰塵的蜘蛛網劇烈地抖了抖,又恢復了平靜。
他看著我的手指玩著鎖,站了起來掏出褲腰上掛的鑰匙串,哆嗦著捉雞似的拎住了其中一把,我把手縮了回來,看著他打開了鎖,揭開了柜子的蓋子。他把手伸進一個上面印著“化肥”紅色字樣的蛇皮口袋里。撐開掌心時是一把白色的米,還有蟲洞和白色的米掉子。我來回晃著雙腳,噔噔地拍在床檔板上:“你的米都蛀蟲了,不能吃了,拿去喂雞吧。”他的眼淚又溢滿了眼眶:“她舍不得吃,平時都鎖著,逢年過節舀一碗出來煮,你來這里也煮,怕你吃不慣苞谷飯。”我想掏出兜里的手帕讓他擦擦眼淚,看見他的鼻涕掉了出來,我又把手縮回了床沿:“你的鼻涕淌出來了,我去給你拿毛巾。”說著我便走了出去。
一只大手把我拉進了跪著的人群,我想著毛巾的事,轉身便要離開,那只手又把我摁了回去,聲音低沉不容反駁:跪下,先生要開路。我偷偷地瞄了旁邊跪著的人群,他們面色凝重哀慟。我低下頭,把表情調節的跟他們一樣,雖然我看不見自己的臉,但是感覺應該跟他們差不多的。
幾個穿著黃色長服的先生走了出來,領頭的頭上戴著一個和《西游記》中的唐僧一樣的帽子,他的頭上細下粗,兩只眼的眼角擠著兩砣白漿眼屎,帽子又臟又舊,上面的菩薩臉上還有一道黑色的東西,也不知道是墨跡還是炭灰。顯然沒唐僧好看。倒是他搖頭晃腦的顯了幾分滑稽。我剛調好的哀慟又消失了,我感覺到自己的嘴角上揚打了個括號。手背一陣痛襲來,尖三角的孝帽下又響起低沉的女聲:畜生,你很高興是不是?我摸著手背,搖了搖頭又點了點頭。便忍住不再抬頭看那先生。
我看著自己的腳尖和前面的黑布鞋后跟,跟著他們一起走到了村口,村口有兩座拔峭歪斜的山峰,白色的巖石,好像一個不高興,隨時都可以倒下來蓋住人似的。我下意識地往后面挪了挪位置。一個男人用手里的煙頭點燃了鞭炮扔了出去,捂著耳朵鼠竄的老遠,劈劈啪啪的鞭炮很憤怒的樣子。我感覺腳下的地皮都在發抖,又擔憂地看了看那歪斜的山峰。
以前她說過的那山神,我總覺得就是住在這座山里面,她說話都不敢大聲,怕驚擾山神,他們這樣吵鬧還得了。不過先生和菩薩已經溝通過了,她金光閃閃的魂也許已經在去天上的路上,她應該能看見我是這群人中唯一懼怕山神的。會在山神發怒的時候求他網開一面饒恕我的吧?這樣一想我就放心了,仿佛那山已經倒了下來,繞過我壓住了他們所有的人。想著他們毫無準備被突然塌下來的山壓住,我又開始同情這些人了。
先生這次念的又與以往的不同,雖然還是沒有聽清楚是什么,但是從他停頓的語調來看,應該是貌似芝麻開門的咒語。因為接下來我看見他的徒弟拎著一大包用床單裹著的東西,那塊床單我認得,是她床上的那塊。我敬畏地看了看那歪斜的山峰,往前湊了湊。徒弟松開了手,收攏的四個角往幾面散了開來,里面的東西露了出來,好像是她的舊衣服,還有那塊給我包過桃子的黑圍裙,隨著圍裙滾落到邊上的,還有一個黑棕色的像藥瓶一樣的東西,徒弟垮過去的時候,腳套住了一件衣服,“咣當”一聲,一個空酒瓶掉了出來,與那黑棕色的小藥瓶碰撞在一起,這次我看清楚了:那酒瓶上糊著“黃河大曲”字樣,黑棕小藥瓶上有“敵敵畏”字樣。
我有些害怕,眼前浮現出她系著那條黑圍裙,坐在那塊床單上把兩個瓶子里的液體仰頭往嘴里灌的場景,這絕對是她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暢飲,一個干癟的老農婦能把酒喝出英雄末路的悲壯,憑這點,也是值得敬佩的。倒盡最后一滴后她應該是平靜的,跟平時喝了水放杯子一樣,把這兩個瓶子整齊地擺放在那柜子上頭、躬腰、脫鞋,然后輕輕地仰臥在那塊床上。
藥效開始發作,像她燒柴火那般大的烈焰,燒灼著她的五臟六腑,她開始扭動,越來越劇烈,她應該是身體縮成了一團,內臟仿佛沾連到了一起,她又伸展四肢,粘連在一起的內臟又被迅速地撕裂開來,床單隨著她的伸縮聚攏到了床中央。這時她的內臟應該是流著潺潺的鮮血,在她的身體里橫沖直撞如同未泄的洪流,找不到出口。即將淹沒她的意識,她把眼睛睜得老大,無聲地張大了嘴。她想大吼一聲,把那股洪流引流出來。她這時大概是想到了酣睡的山神,又把嘴合上了,手指拽緊了床單,忍受著體內的洪荒沖擊,直到支離破碎,再也感覺不到疼痛,她便松開了手指,舒展了四肢。她看到了那張木床旁邊不知什么時候站著兩個人:他們的衣服一黑一白,手里拿著粗壯的鐵鏈條,他們慘白的臉,像她鎮上兒子家的石灰墻,他們遞上了鏈子,束上她的手腳:走吧,你的時辰到了,該上路了。
先生的徒弟手里拿著一只金屬材質的火機,“咣”地打開了蓋子,大拇指抹了抹旁邊的小齒輪,火苗“嗖”地躥了起來。他那姿勢挺瀟灑,大概是看過《上海灘》里的許文強學的,我也看過許文強,他的指甲是白的,這個徒弟指甲縫里裝滿了烏黑的東西,他那雙穿著塑料拖鞋的腳也是黑的,不像泥土,像幾年未沾過水,指甲縫里的那些烏黑的東西,應該來自腳上,它們看起來顏色很搭。
他點著床單的時候,眼睛往離他最近的那幾個少女臉上瞟了瞟,幾個少女米白色孝帕布下的臉飛起了紅暈,她們咯咯地笑了,低下頭互相推掐著往后閃了閃,隔著漸漸竄大的火苗,與那徒弟交換著羞澀又期待的眼神。的確良的布料助長了火焰的囂張,火焰伸出腥紅的大舌頭,很快吞噬了她在人間存在過的證據,打了個嗝,黑色的青煙升騰而起,四處逃竄,很快隱沒在那兩座斜峰的背后。
人群漸漸散去,灰燼里躺著兩個烏黑的瓶子,瓶子的名字,已經被火焰剝食。她自盡的證物,就這樣被他們付之一炬,毀滅,要不是她那二分之一的血液還在我的血管里流動,我會感覺自己只不過是做了個漫長的夢:這世上根本沒有這個人的出現,那桃子的味道,只是我嘴饞的幻覺。
送她上山的那天早晨,我蜷縮在她的床上睡過了頭,抬頭看看墻上分辨不出顏色的掛鐘,布滿鐵銹的時針和分針,指著三點半的方向。
我揉著眼睛來到堂屋里,置放棺木的位置已經空了,燃盡的香簽和凝固的蠟花散落在地上。他的男人拄著煙桿,坐在堂屋門坎上,眼里一如往常地淚水盈眶。
我撿了根未燃盡的蠟燭,走過去挨著他坐了下來:“她真是勇敢,毒藥都敢喝。”他的淚水終于滑落了下來:“我就沒那勇氣,還得繼續給他們當累贅。”我剝著手上的蠟燭,用指尖搓捏著碎屑:“是的,你有她的勇氣也不行,他們忙不過來會生你氣的。”他擦了擦眼角:“嗯,也不能像她這么死,外人會說是他們逼死的,對他們影響不好。”
燃了一半的蠟燭像個禿頭和尚,已經被我從頭部剝光了肉,我拿著光溜溜的竹簽在地上劃著圓圈:“你別問他們要大米了吧,苞谷面很好吃,比大米飯經餓,我吃過的,早晨吃了一碗能管一整天。”他點了點頭,淚水又流了出來,我說你進去吧,外面風大,你的風眼好像越來越嚴重了。
多年以后,桃子成熟的季節,我總是留戀于街頭巷尾,追尋著挑桃子賣的小販,尋找和那年的桃子長得相似的桃子,小販嘴里夸著他的桃子賽過王母娘娘的蟠桃,要多甜有多甜。邊夸邊用小刀切下一塊遞給我嘗,以證明他的話不虛。我咬了一口:他們都是騙子。根本不甜。這世上只有她不會騙我,她說甜,是真的甜。
群山漸漸變成了黑色,夜幕吞噬了夕陽最后一道晚光,我再也看不見山那邊,她曾經說過,地獄是沒有亮光的,她的膽子那么小,會不會害怕?
隔著群山,我突然心生恐懼:如果菩薩與我一樣,根本沒聽清楚當年為她度魂的先生說的話怎么辦?她孤身在荒郊野嶺的泥土里,躺了二十多年,無法動彈,在沒有月光的夜里,每天都要重復牛圈的經歷,挨著地獄的酷刑。
心里有些壅塞,又是一些垂墜之物,斑駁交雜,涌動著哀慟后留下的渣滓。
我加大了油門,往山那邊狂奔了過去,凌晨四點的山里,蟲蟻夢囈,鳥雀偶有鼾聲,我靠在車里,望著她墳塋的方向:她的墓碑上密密麻麻刻著孝子孝孫們的全名,也有我的全名,我卻不知道她的名字,上面只刻著“彭母徐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