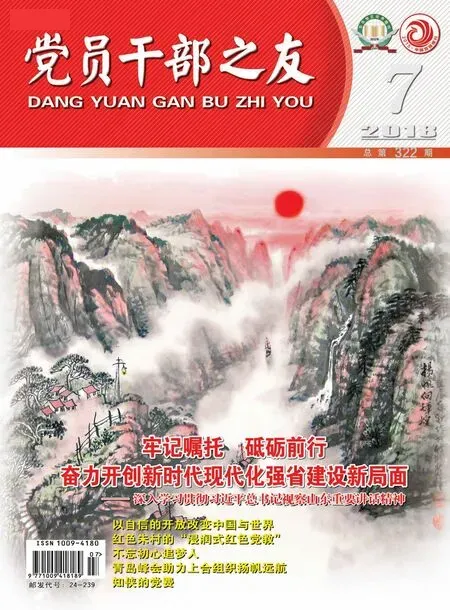不忘初心追夢人
—— 追記優秀共產黨員、復旦大學教授鐘揚
“倘若用一個詞來凝練鐘揚的一生,應該是‘追夢’二字,鐘揚就是一個一生追夢的人。”復旦大學副校長金力院士,始終對鐘揚懷有一份深深的敬重。
鐘揚生前系復旦大學研究生院院長、生命科學學院教授,2017年9月25日因車禍不幸去世。從教30余年,援藏16年,在野外收集上千種植物4000多萬顆種子,用心培育大批優秀學子……在他53歲的人生旅程中,留下太多不平凡的足跡。
鐘揚去世后,人們對他的思念未曾消減,他的感人事跡和崇高精神激勵著無數人。2018年3月29日,中央宣傳部追授他“時代楷模”稱號。
心里永遠裝著國家
“不是杰出者才善夢,而是善夢者才杰出。”鐘揚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他的心中有許多夢想:查清青藏高原植物種質資源的家底,為人類留下寶貴財富;為少數民族地區培養更多高層次人才……為了這些夢想,他對科研、育人和生態保護癡情付出,卻把個人名利看得很淡。
上世紀90年代初,鐘揚與妻子張曉艷赴美國留學。當時選擇回國的人并不多,但鐘揚從來沒有糾結過這個問題。回國時,別人往往帶生活中稀缺的彩電、冰箱等家用電器,鐘揚卻買了計算機、復印機。張曉艷回憶說:“我們一起去提貨的時候,海關都不相信,怎么可能有人用自己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錢給公家買設備?”然而,這正是鐘揚的做事風格。他頭腦里經常想的是:我應該為這個單位、為這個國家做些什么事?
2000年,鐘揚放棄了中科院武漢植物研究所副所長的崗位,到復旦大學做一名普通教授。他從來沒有把官位和職位看得很重。到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工作后,鐘揚和幾位老師一起承擔起重建生態學科的使命。他越來越意識到,許多物種在消失,保存種質資源已經成為一項基礎性、戰略性的工作,對國家發展、人類命運都意義非凡。
經過大量細致的文獻調研和實地野外考察,鐘揚發現西藏獨有的植物資源未受足夠重視,物種數量被嚴重低估。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種質資源庫中,也缺少西藏地區植物的影子。他開始把目光投向我國生物資源最為豐富的地方——青藏高原。
從2001年起,鐘揚堅持自主進藏開展科研,此后更連續成為中組部第六、第七、第八批援藏干部。他一方面收集植物種子,為保護生態存儲未來的希望;一方面致力于在西藏建設生態學科,培養人才。16年來,鐘揚在青藏高原艱苦跋涉50多萬公里,收集上千種植物的4000多萬顆種子,填補了世界種質資源庫沒有西藏種子的空白。他始終堅信:“一個基因可以拯救一個國家,一粒種子可以造福萬千蒼生。”
鐘揚和團隊還在西藏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采集的高原香柏已提取出抗癌成分;追蹤數年,最終尋獲“植物界小白鼠”擬南芥;帶領學生用3年時間,將全世界僅存的3萬多棵西藏巨柏全部登記在冊;通過研究,找到了可在制香功能上替代巨柏的柏木,為珍稀巨柏筑起一道堅固的保護屏障……
“這類工作學術成果‘顯示度’并不高。”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黨委書記陳浩明感嘆,“以他的聰明才智,大可坐在實驗室里驗證假設、發表論文,無須艱苦跋涉。”可在鐘揚看來,一個人一輩子留下的不在于論文、獎項,而在于做了多少實實在在的事。他動員學生去最艱苦的阿里地區時說:“只要國家需要、人類需要,再艱苦的科研也要做!”
打造高端人才培養的援藏新模式
剛到西藏時,鐘揚發現,西藏大學植物學專業是“三個沒有”:沒有教授,老師沒有博士學位,申請課題沒有基礎,學科底子十分薄弱。很多人對鐘揚的到來并沒有抱太大希望,畢竟學校來過一批又一批合作者,似乎都沒實現什么科研突破。但他們沒想到的是,鐘揚居然留下了,而且一干就是16年。
面對西藏大學教師申報國家級項目沒經驗、不敢報、沒人報的情況,鐘揚不僅幫老師們義務修改項目申請書,還提供申報補助。只要是西藏大學的老師申報項目,無論是否成功,他都補助2000元,用于支付申報過程中產生的費用。
2002年,鐘揚幫助西藏大學教師瓊次仁申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當時他常常一邊插著氧氣管,一邊連夜修改申請報告。這個項目成為西藏大學拿到的首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極大地增強了老師們的科研信心。兩年后,瓊次仁不幸罹患癌癥。彌留之際,他緊緊拉著鐘揚的手說:“我走時,你抬我,你來抬我。”簡單的話語,體現了藏族同胞給予朋友的最高信任。
西藏阿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氣候寒冷干燥,平均風速在每秒3.2米以上。有人勸鐘揚不要去阿里,那里海拔太高、生活條件太苦,而且物種較少,辛苦一天只能采幾個樣。鐘揚卻說,正是因為別人不愿去,我們才必須去!因為他深知,西藏每一個特有物種,對國家而言都是無價之寶。
鐘揚說,海拔越高的地方,植物生長越艱難,但是越艱難的地方,植物的生命力就越頑強,“我希望我的學生,就如這生長在世界屋脊的植物一樣,堅持夢想、無畏艱險。我相信,終有一天,夢想之花會在他們的腳下開放”。
上有老人,下有雙胞胎兒子,鐘揚也知道,家人希望他能夠留在身邊。在鐘揚成為援藏干部后,張曉艷寬慰自己,等3年援藏期結束,丈夫應該就回來了,應該可以多照顧家庭。可是每一期援藏結束,鐘揚似乎總有無可辯駁的理由開始新一期的援藏:第一次是要盤點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第二次是要把西藏當地的人才培養起來,第三次是要把學科帶到一個新的高度。
在鐘揚的帶領下,西藏大學實現了多項“零”的突破:2011年獲批生物學一級學科碩士點,成為該校首個理科碩士點;創建“西藏生物多樣性與可持續利用”科研創新團隊,成為西藏第一個生物學教育部創新團隊;2013年獲批生態學博士點,成為該校首批三個博士點之一;2017年更是帶領西藏大學生態學入選“雙一流”建設學科。鐘揚曾多次提到,56個民族都是祖國大家庭的成員,“我有一個夢想,為祖國每一個民族都培養一個植物學博士”。

讓生命燃燒起來
一個人成績的取得固然與天分有關,更重要的是持久勤奮的付出。鐘揚就是這樣,他不僅有長遠的眼光,更是一位善于執行的實干家。他把全部身心撲在事業上,讓生命燃燒起來,熊熊火焰照亮了一片天地。
鐘揚本來患有痛風,身體并不太好。2015年,他因腦溢血而住進了重癥監護室,昏迷了兩天。經搶救蘇醒后,他關心的第一件事是詢問同事:“原本我要上的課是否安排妥當?”
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博士生徐翌欽記得,2015年他在醫院陪護生病的鐘揚,夜里3點聽到手機響了,以為是有人打來電話,結果發現是鬧鐘。第二天他問老師這是怎么回事,鐘揚回答,這是提醒他該睡覺的鬧鐘。
鐘揚曾風趣地說,自己做科研有“四像”:像狗一樣靈敏的嗅覺,把握前沿;像兔子一樣迅速,立即行動;像豬一樣放松的心態,不怕失敗;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像牛一樣的勤勞,堅持不懈。
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經歷重病后的鐘揚會有所“收斂”,放慢工作的節奏。妻子和父母也勸他,鐘揚卻回答,“西藏的事情總要有人去做”。
“他真的是在搏命、玩命。身體嚴重透支,兩邊來回跑,對身體影響反而不好。”張曉艷說。但鐘揚不僅沒有放慢腳步,反而加快了。他總有一種使命感——讓復旦大學的研究生工作再上臺階,把西藏大學的人才梯隊真正帶起來。在鐘揚的推動下,復旦大學成立研究生服務中心,全年無休。他常對同事說:“寧可我們自己累一點,也要盡可能方便學生。”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鐘揚一直馬不停蹄地奔忙著。2017年9月25日清晨,噩耗傳來——鐘揚在去內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學院講課出差途中遭遇車禍,不幸離世。9月29日,鐘揚同志遺體告別儀式在寧夏銀川殯儀館舉行,其后,他的骨灰運回到上海。復旦大學近百名師生前往浦東國際機場,在雨中迎接鐘揚歸來。校園里掛著懷念鐘揚的橫幅,上面寫著:“留下的每一粒種子都會在未來生根發芽。”鐘揚生前曾說:“一名黨員,要敢于成為先鋒者,也要甘于成為奉獻者。”他做到了。鐘揚走后,張曉艷和家人商量,決定把鐘揚的車禍賠償金全部捐出來,用于支持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才培養工作。她說:“國家的教育事業是鐘揚一生的牽掛。這是我們家人能為鐘揚未竟的事業做的一點事,也是他所希望看到的。”
鐘揚走了,種子還在。他對祖國的那份深沉的熱愛,依然在悄悄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