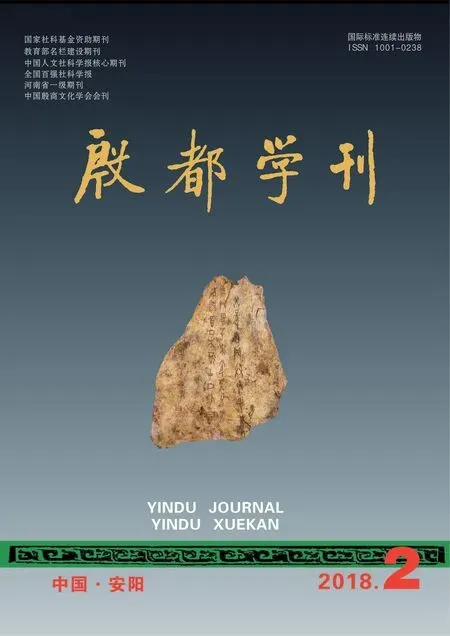說商代甲骨刻辭中的“方伯”
王坤鵬
(吉林大學 歷史系,吉林 長春 130012)
“方伯”這一概念常見于先秦禮書中,《禮記·王制》稱 :“千里之外設方伯”[1](p1325)。秦漢以后,主政一方的大員例如漢代的刺史、唐代的采訪史、觀察史以及明清的布政史等也常獲稱“方伯”。早在商代甲骨刻辭中已出現“方伯”稱謂。郭沫若《殷契粹編》中較早著錄了相關資料,其1316片載 :“方伯其酓于”(即《合集》28097),郭老據此認為“今得此片,知‘方伯’之稱實自殷代以來矣。”[2](P684)卜辭“方”前殘字郭老釋為“年”,金岳先生釋為“微”[3],陳夢家先生則釋為“羌”[4](p326),實則卜辭拓片殘損厲害,難以確認。
關于甲骨中的“方伯”概念,學界已有多方探討。一種觀點認為“方伯”當有特殊內涵,實力較強,即后世禮書中的“方伯”。例如董作賓先生在討論商代爵稱時,單列“方伯”為一類,認為像卜辭中的“盂方伯”其勢力甚強大,需要“多田”與“多伯”從王師一致聲討之[5]。張秉權先生認為卜辭中的方伯就是《禮記·王制》所說的“方伯”[6]。島邦男先生的意見略似之[7](p842)。李學勤先生指出卜辭中稱“某方伯”者甚少,方伯稱謂可能有特殊意義,其地位可能高于一般方國之君[8]。另一類觀點則認為卜辭中的“方伯”當是方國部落的首長,是甲骨刻辭中常見的“某方”的首領稱謂。例如陳夢家先生認為卜辭中“邦方”之長,稱之為“某方白”而往往附以私名。“方伯”乃所謂甸服以外的君長[4](P326)。王貴民先生在此基礎上指出卜辭中“方伯”稱謂之內涵前后有所變化,方伯多半與商王朝有武裝沖突,與商王朝沒有臣屬與宗親關系,只是到了殷商后期,方國與族地名發生了對流現象,“方伯”稱號也發生了浮動,反映了一些方國臣服于商,逐漸納入了王國政區[9]。
甲骨刻辭中的“方伯”概念與早期國家的疆域及治理結構有密切關系,學界的討論已取得不少有意義的認識。只是相關研究多為隨文所及,缺乏較詳細地專門論述。再者學界一般將甲骨中出現的“方伯”直接與后世禮書中的相關記載相比附,不易體現其間所存在的差別。故本文不揣簡陋,試在前賢的基礎上,對甲骨刻辭中“方伯”的相關辭例作專題研討,并進一步探究甲骨刻辭與后世禮書中“方伯”概念的差異所在,以求正于學界。
一、方伯的性質
方伯是伯稱謂的一種,這從部分甲骨刻辭中“方伯”又見稱為“伯”可得證明。例如 :

同為無名組類的卜辭中既有“盧方伯漅”,又有“盧伯漅”,沈建華指出盧方伯漅即是盧伯漅,《合集》33185又有“盧方”,方國與方伯同名又加了私名[10]。也就是說,在甲骨刻辭中,某方伯指的是某方國的首領。當然在有的甲骨語境里,方伯也可以指代整個族邦,并非僅指首領。
方伯即屬于伯的一類,其性質從根本上講則應與伯相同,是與商人不同的異族群體。朱鳳瀚先生指出在卜辭與商金文中,凡可確知屬商人者,包括子姓與非子姓貴族,均未見有稱之為“伯”者,這表明商人并無稱“伯”之俗。朱先生同時認為這種伯稱可能是其族群自己使用的稱呼,商人只是延用了這一稱呼,并將其擴大至所有異族群首領之泛稱[11]。實際上即指出商伯并非屬于商人所封的爵稱。

方伯雖屬于伯的一類,卻又不是普通的邦伯。首先,方伯之稱“方”當具有特殊的內涵。方伯之所以稱“方”,顯示其為方國,占有一定范圍的土地,而非普通的邦伯家族。甲骨刻辭中的方國、方伯之“方”其本義應為方域與幅員。西周銅器豳公盨銘稱 :“天命禹敷土、墮山、浚川,迺疇方、設正、降民。”[12]所謂“疇方”,正是疇劃地理范圍的意思。另一件西周早期銅器召圜卣器銘稱 :“王自嗀事賞畢土方五十里”(《集成》10360),貴族召受賜了五十里見方的土地。“方”均用來表示一些族邦人群所占據的一定方圓的地域,方伯、方國之“方”也應是這一內涵。方伯所占有的地域應比一般的邦伯家族大一些,朱鳳瀚先生曾推測方伯稱“方”也許是因為其族邦規模較大[11],這是有道理的。卜辭中出現的“某方”均當是同類性質。
其次,方伯多是一些王朝日常統治所不及的異族群體,與殷商晚期已納入王朝政制里的邦伯不同。甲骨刻辭中所見的“伯”,雖然均為異族邦伯,卻有不少經過商王朝的征服,最終臣服于商,成了商王朝的一股政治與軍事勢力,卜辭中稱為“多伯”(《合集》36511),也即《尚書·酒誥》所載殷商外服中的“邦伯”。裘錫圭先生認為 :“在商代晚期的黃組卜辭(即董作賓提出的第五期卜辭)里,屢次看到商王卜問跟‘侯田(甸)’、‘多田’或‘多田于(義同與)多白(伯)’一起去征伐方國,是否吉利……與‘田’并提的‘白(伯)’,大概就是《酒誥》、《召誥》所說的‘邦伯’,當是商王朝轄境內臣屬于商王的一些小國之君。”[13](p153-154)乙辛卜辭《合集》36511占卜商王聯合“多田于多伯”征伐盂方伯之事。可見到了商王朝末年,與進入商王朝政制的“多伯”不同,部分方伯仍在商王朝武力征討之列。
一直到周代,周人稱呼一些邊遠異族群時仍用“方”的稱謂。毛公鼎銘云 :“率懷不廷方”(《集成2841》),戎生鐘銘 :“遹司蠻戎,用倝不廷方”,“不廷方”即尚未臣服于周的方國族群,即銘文中的“蠻戎”。虢季子白盤 :“用征蠻方”(《集成》10173),梁伯戈 :“抑鬼方蠻”(《集成》11346),這些“蠻方”或“方蠻”都是處于王朝日常統治之外的異族方國,因此銘文中講到對它們的征伐與抑制。另外還有史墻盤銘 :“方蠻亡(無)不見”(《集成》10175),逑盤銘 :“方狄不(丕)享”,秦公鐘銘 :“以虩事蠻方”(《集成》262)等,這些顯示中央王朝勢力煊赫的銘文,都將異族方國的臣服作為重要標志。銘文中這些尚需中央王朝武力征服的異族方國顯然叛服無常,并未被納入周王朝的日常統治范圍。它們與金文中見到的四方諸侯恰成對比,令方彝銘記載周公子明保受王命到成周宣布命令,其宣命對象之一就是四方諸侯,所謂 :“眔諸侯 :侯、甸、男舍四方令。”(《集成》9901)銘文“四方”指四方諸侯,即侯、甸、男這些不同種類的封君,他們與上舉的“方蠻”、“方狄”不同,已經納入了周王朝政制之內。
據以上考述,甲骨刻辭中的“方伯”是伯稱謂的一種,商代的伯均指與商人不同的異族邦首領,在甲骨也常用來指稱異族邦。方伯之所以稱“方”,顯示其并非普通的邦伯家族,而是具有一定地域與規模的方國。商代的“方伯”多指一些王朝日常統治所不及的方國,從而有別于已納入王朝政制軌道里的“邦伯”或“多伯”。這種稱謂習慣一直延續到周代,兩周銘文中經常稱一些邊遠異族邦為“不廷方”、“蠻方”、“方狄”等,而且將征服這類異族邦伯作為王朝勢力煊赫的重要標志。
二、方伯的復雜情況
以上我們雖然就甲骨刻辭中方伯的性質作了簡要的考索,可實際上相關材料中所體現的商代方伯的情況是比較復雜的。在甲骨刻辭及相關銅器銘文中,方伯與商王朝的關系還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部分卜辭與方伯臣服、享獻的儀式有關系 :


辭3“延”,《爾雅》云 :“延,進也”。卿,通饗或享。卜辭中的“鄉”,屈萬里先生曾釋為“享”[14](p432)。饗、享,經籍中均常見,《說文·食部》“饗”字段玉裁注 :“毛詩之例,凡獻于上曰享,凡食其獻曰饗。”[15](p221)自異族方伯言之稱“享”,而自中央王朝言之則稱“饗”。因此,享與饗是一事的兩面。《詩經·商頌·殷武》說 :“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鄭玄箋曰 :“享,獻也。”[1](p627)詩中“來王”大約就是卜辭中常見的占卜各地族邦“其來”、“允來”之類的事情,“來享”也是類似的情況,指邊遠的族群前來進獻稱臣。又《國語·周語上》稱 :“賓服者享”,韋昭注稱 :“其見也,必以所貢助祭于廟。”[16](p7)可見異族方國稱臣納貢,是在宗廟之內,其間包含有商周王室祭祀告祖的內容。前引逑盤銘文稱 :“成受大命,方狄丕享”,說的也是同樣的情況。




以上幾條卜辭均反映了商王朝與臣服方伯之間的相關臣服禮儀及交往等方面的活動。另有幾條卜辭則反映了方伯勢力強大,受到商王朝的武力征討 :


辭9有關羌方的兩位方伯,陳夢家先生曾經討論過,認為是商王朝殺方伯以祭于先王[4](p326)。辭10、11兩條卜辭已到了殷墟末期,說的是商王朝與盂方伯炎之間的戰爭。商王發動了“多田”與“多伯”的力量一起征伐盂方伯。“田”即“甸”,“多田”指多位“田”類職官,商王朝在王畿內外設置了不少這類“田”,卜辭中稱為“在某田”(例如《合集》10989正中的在攸田武),裘錫圭認為其應為商王派駐商都外從事農墾的職官,由于擁有族眾與武裝,又在王都以外,很容易發展成諸侯一類的勢力[13](p19)。“多伯”指多位“伯”的合稱,商代所稱的“伯”于商人而言都是異族邦伯[11],臣服于商王朝而成為商王的武裝爪牙。
在殷商晚期,“盂方伯炎”這類勢力顯然要比“田”、“伯”等要大得多,而且不受商王的控制,因此商王聯合數位“田”、“伯”勢力對之加以征討,并祈求上下祖先神靈的保佑。與“盂方伯”類似的方伯勢力,在殷商晚期還有“夷方伯”(殷墟人頭骨刻辭[4]圖版13)與“周方伯”(周原甲骨H11:82[24](p62))等,夷方伯與商王朝進行了長期的斗爭,即《左傳》昭公十一年所稱的“紂克東夷而殞其身”。而周方伯更是最終滅亡了商王朝。可見方伯勢力在殷商晚期已經成為商王朝的心腹大患。

三、禮書文獻中記載的“方伯”
學界在討論商代方伯時,多引用后世禮書中所記載方伯加以類比。相關禮書文獻多為戰國秦漢時期的學者根據前代文書檔案概括綜合而來,其中不乏理想式的藍圖規劃,不少內容并非實錄。這一點是我們在研究中應當加以考慮的。與方伯有關的記載散見于《禮記》、《周禮》、《尚書》、《詩經》、《左傳》、《公羊傳》等文獻以及經學家的注疏中,不同的記載并非成于一時一人,故其概括的禮制系統是有差異的,并不能與商代的情況簡單比附。
文獻中關于方伯的記載大致可分為兩個系統 :第一是“二伯——州伯”系統,第二是“四岳——十二牧”系統。前者見于《禮記·王制》 :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1](p1325)。
據《王制》所記,天下分為九州,王畿占一州,畿外八州。畿外每州各設大小國家二百一十個,而且每州各選擇一個賢能的諸侯擔任州伯,因此天下一共有八位州伯。而這八位州伯又分屬于被稱為“天子之老”的左右“二伯”。
“方伯”究竟指的是州伯還是左右二伯呢?多數經解認為方伯即州伯。例如《詩·邶風·旄丘》孔穎達疏稱云 :“以一州之中為長,故云方伯。”[1](p305)孔穎達認為“州伯”為一州之首領,故稱“方伯”。這種解釋實際上并沒有解釋清楚為什么一州之長就被稱為方伯,畢意“州”與“方”是兩個不同的詞匯。實則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王制》并沒有明確講到“方伯”就是指八州之伯,漢代以來的經學家對此已有分歧。《周禮·大宗伯》云 :“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玄認為八命之牧對應于州伯,而九命之伯則對應于左右二伯。而鄭眾則認為“八命作牧”為“一州之牧”,“九命作伯”則是“長諸侯為方伯”[1](p761)。也就是說,在鄭眾的解釋中,“方伯”即《王制》中的“二伯”。
結合其他文獻來看,“方伯”指天子左右“二伯”更符合當時禮制的規劃。《禮記·曲禮下》云 :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于諸侯,曰天子之老,于外曰公,于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1](p1264)。
“五官之長曰伯”就是前所言天子左右的“二伯”,“九州之長曰牧”即前所言的“州伯”。鄭玄注“五官之長”就是王朝擔任三公者,分主東西二方[1](p1264)。對各地諸侯而稱“天子之老”,可見就是《王制》中作為天子之老的“二伯”。可見相對于“九州之長”來說,“五官之長”職掌一方,被稱為“方伯”,從邏輯上更能解釋得通。

“四岳”與“十二牧”形成了一個不同于“二伯——州伯”的政制系統。四岳分處于四方,《堯典》云 :“東巡守至于岱宗……南巡守至于南岳……西巡守至于西岳……朔巡守至于北岳”。四岳似處于四方,每一岳分別是各自方岳內的諸侯之長。由此可見,“四岳”在等級上相當于《王制》“二伯”,“十二牧”則相當于《王制》的“州伯”,只是由于文獻中所擬設的政制規劃不同,由東西兩方的諸侯之長變為了四方各有諸侯之長,八州伯也改變成為十二州牧。
概言之,早期禮書文獻中關于“方伯”的記載,由于擬設的政制系統不同,大致形成了兩套不同的規制。在“二伯—州伯”系統中,在州伯之上是左右“二伯”,負責東、西兩方之事。而在“四岳—十二牧”系統中,十二州牧之上設置四岳,擔任東、西、南、北四方的諸侯之長。至于“方伯”這一概念指“二伯”、“四岳”這一層級,抑或是“州伯”或“州牧”層級,文獻中并沒有明確地表述。從一些略模糊地敘述中,方伯似乎更可能指的是二伯、四岳這一層面,他們一般主掌一方,是為方伯。可以看到,禮書記載的相關方伯制度多是一種藍圖規劃,并非實際所實行,與我們從甲骨卜辭中所了解的商代方伯的情況有很大差異。最明顯的一點在于,甲骨刻辭中的方伯指的是與商人異族的方國首領,一般來講并未納入商王朝政制軌道,常受商王朝的征伐,并由此產生臣服、進獻等活動。而禮書記載的方伯則是王朝所設置的五官之長、諸侯之長等,是天子的左右手,分方向與區域負責各地區的邦國諸侯。
綜合以上所考,商代甲骨刻辭中見到的方伯是伯稱謂的一種,卜辭中有的方伯又可省稱為伯。方伯是方國首領,又可指代整個方國。從根本上講,方伯與伯的性質相同,都是與商人不同的異族邦伯。方伯之族邦具有一定的地域與規模,方伯之稱“方”,有其一定的特殊內涵,“方”指方域,說明其占有一定的地理幅員。而且方伯不同于一般的邦伯,而多是商王朝日常統治所不及的異族群體,與殷商晚期已納入王朝政制里的“多伯”不同。相對于殷商晚期已納入王朝外服的“邦伯”來說,方伯更為叛服不定,與商王朝的離心力更大。商代甲骨刻辭有數條記有“方伯”,反映的情況比較復雜。相關卜辭記載商王朝與方伯之間舉行享獻、宴飲或揖拜等禮儀活動,應與方伯的臣服禮有關。也有卜辭記載了商王朝征討方伯以及殺方伯祭祖等事,反映了商王朝與方伯之間的征戰與對立。材料顯示,到了殷商末年,方伯勢力越加發展,東方的夷方伯以及西方的周方伯等勢力已對商王朝構成了致命的威脅。后世禮書中記載的方伯制度,多為當日學者所作的藍圖規劃,并非歷史實際。因此,由于擬設不同,其規劃亦可粗略分為“二伯——州伯”系統與“四岳——十二牧”系統。其中,“二伯”分掌東西,“四岳”則分掌四方,是為方伯。其中稱“方”的內涵已與甲骨刻辭不同,而且方伯均作為天子的股肱大臣,是王朝所設置的五官之長、諸侯之長,與商代甲骨刻辭中所記載的內容并不能簡單地相比附。
[參考文獻]
[1]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M].北京 :中華書局,1980.
[2]郭沫若.殷契粹編[M].北京 :科學出版社,1965.
[3]金岳.微方伯歷史文化研究[J].文物季刊.1995,(2):60.
[4]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M].北京 :中華書局,1988.
[5]董作賓.五等爵在殷商[J],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36(6本3分):418-420.
[6]張秉權.卜辭中所見殷商政治統一的力量及其達到的范圍[J].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79(50本1分):190.
[7]島邦男著.濮茅佐、顧偉良譯.殷墟卜辭研究[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8]李學勤.周文王時期的卜甲與商周文化關系[J].人文雜志.1988,(2):72.
[9]王貴民.商朝官制及其歷史特點[J].歷史研究.1984,(4):115.
[10]沈建華.卜辭所見商代的封疆與納貢[J].中國史研究.2004,(4):9.
[11]朱鳳瀚.殷墟卜辭中“侯”的身分補證——兼論“侯”、“伯”之異同[A].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四輯)[C]:19.
[12]裘錫圭.豳公盨銘文考釋[J].中國歷史文物,2002,(6):13.
[13]裘錫圭.甲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衛”等職官的研究[A].裘錫圭學術文集·古代歷史、思想、民俗卷[C].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14]屈萬里.殷虛文字甲編考釋[A].甲骨文獻集成(第4冊)[G].成都 :四川大學出社,2001.
[15]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6]徐元誥.國語集解[M].北京 :中華書局,2002.
[1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M].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0.
[18]李學勤.殷代地理簡論[M].北京 :科學出版社,1959.
[19]于省吾.甲骨文字詁林[M].北京 :中華書局,1996.
[20]唐蘭.天壤閣甲骨文存并考釋[A].宋鎮豪,段志洪.甲骨文獻集成(第2冊)[G].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
[21]曹定云.殷代的“盧方”[J].社會科學戰線.1982,(2):121.
[22]嚴一萍.釋揖[J].中國文字.1985,(新10):105.
[23]劉桓.卜辭拜禮試析[A].殷契新釋[M].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
[24]曹瑋.周原甲骨文[M].北京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2.
[25]宋翔鳳.尚書略說[A].王先謙編.清經解續編(第2冊)[G].上海 :上海書店,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