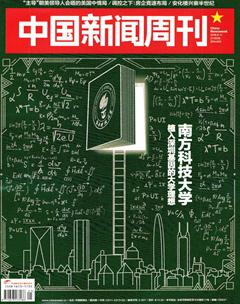不動聲色地記錄政治和災難的創痛
李行

汽車勻速行駛在波黑荒無人煙的盤山公路上,車窗外是能見度不足十米的迷霧。潮濕、陰冷是這個季節的巴爾干半島特有的風情。
“當地人都說斯拉夫語,你們找我太明智了。”開車的向導是鄰國塞爾維亞一位有著俄語口音英語的大叔。他一邊開車一邊轉身對著攝影師劉旭陽和蘇宇寒暄。畢竟接下來的兩個星期他要與這兩位來自中國的攝影師朝夕相處,還有每天100歐元的收入。
兩位攝影師都系好安全帶,緊緊握著安全扶手。對于這樣復雜的地形和氣候,他們顯得有點緊張。意外還是出現了,一個轉彎處,車輪打滑,沖向路邊的懸崖。向導拼了命地反打方向盤,直到車子橫亙在山路中間。
紀念碑與歷史
這個發生在2016年的場景,如今還時常浮現在劉旭陽眼前,1992年出生的劉旭陽沒想到過自己離死亡的距離只有30厘米。如果不是為了即將畢業的攝影作品,他可能不會去到那里。就讀倫敦傳媒學院攝影專業的他那時即將畢業,畢業作品就是提交一組主題照片。
在網絡上,他偶然看到BBC此前拍攝的紀錄片《南斯拉夫的死亡》。一百年間,從南斯拉夫王國、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演變到塞爾維亞和黑山,昔日的南斯拉夫最終分裂為六個共和國(塞爾維亞、黑山、波黑、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和馬其頓),還有科索沃爭議區,首都貝爾格萊德的身份也幾度改變。
給劉旭陽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影片中南斯拉夫地區充滿未來主義感的多座紀念碑。出發前兩個月,他經常在網上翻找資料,通過谷歌地圖,一次次搜索、放大,從衛星地圖上的每一塊綠色區域中,尋找灰色建筑的蹤影。最終,他找到了24個紀念公園的位置,還發現了一些具有歷史意義的戰爭遺跡,那些掩埋于荒煙蔓草中、一座座有如外星遺跡的烏托邦建筑。
為了可以在這幾個國家通行,他辦好了申根簽證。抵達塞爾維亞時,他看到此前的舊警察局依然斷壁殘垣,而對面矗立的新警察局看起來風光無限,側面卻還是被炮火轟炸得一片焦黑。十多年前,巴爾干半島爆發嚴重內戰,城市里被毀壞的區域還來不及修復,就又遭到襲擊。
在濃霧中,他們找到了波黑Kozara紀念碑,這是為了紀念1942年夏天數千名南斯拉夫游擊隊和平民被烏斯塔沙政權殺害而建。數十片建筑組成了一個圓柱形紀念碑,遠看剛好在樹林的空地上。
向導向兩人介紹了這段歷史:烏斯塔沙組織于1929年4月20日在保加利亞的索菲亞成立,想讓克羅地亞由南斯拉夫獨立出去,其領導人安特·帕維里奇與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黨有密切關系,并且領取其津貼。1941年納粹德國與意大利王國及其盟國進攻南斯拉夫,烏斯塔沙組織的軍隊便趁此時宣布克羅地亞獨立,并殘酷鎮壓當地平民。后來,烏斯塔沙被由鐵托率領的人民軍擊潰,克羅地亞再度并入南斯拉夫。但如今,這塊紀念碑屬于南斯拉夫分裂之后的波黑領土之上。
天色暗下來,向導開車帶領他們到波黑的一處山區小鎮,鎮子上有個小酒館,七八十平方米,五六張桌子,他們每人要了一份“切巴契契”,那是用肉末卷成肉卷后再進行烤制的一種肉食。此間,整間酒館里的人都一言不發轉頭盯著他們看,毫不掩飾自己的好奇。老板坐過來請求合影,“這樣一來我們也是國際餐館了。還可以把照片掛在餐廳里招徠客人。”
事后向導告訴他們,這個村子是塞族人的地盤,如果是克族人來到這里,人們恐怕不會那么友善。種族間的矛盾,雖然已經不如內戰時激烈,但仍然在每個人心中隱隱作痛。
出發前,劉旭陽計劃著要去拍攝一個名叫“StoneFlower”的紀念碑,最終卻未能成行。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向導是個塞爾維亞人。那座屬于塞爾維亞英雄的紀念碑,如今地處克羅地亞境內。如果塞爾維Ⅱ人想去參觀,就必須辦理一系列復雜而苛刻、近乎不可能完成的手續。向導的解釋是,現今的前南地區,克羅地亞族、塞爾維亞族、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那族的人民之間仍然矛盾重重,互不交流。
伊格曼(Igman)山脈里的1984年薩拉熱窩冬奧會奧運村,在濃霧里若隱若現。此地曾先后被塞爾維亞族和克羅地亞族武裝占領。現整個建筑已破敗不堪,除了墻體,內部構件都被附近的居民拆走。
南斯拉夫制造
在巴爾干半島拍攝紀念碑的半個多月里,向導也帶領他們接觸到形形色色的人。
摩拉維納人民革命紀念碑是他們此行最重要的拍攝對象之一。它是為了紀念摩拉維納地區的二戰勝利而建造的,巨大的石頭翅膀中間是一只金屬鑄造的眼球。它現在位于克羅地亞地區,在去往那里的路上,他們看到當年參與過解放戰爭的老人,戴著禮帽和老伴在散步,和他們說起硝煙里失去的朋友。
在塞爾維亞的城市里,他們碰到一位重新找到工作的中年大叔,他拿著一個很大的熱狗,開心地告訴向導他找到了新工作,小孩學習也挺好。在攝影師給他拍照時,他問能不能邊吃熱狗邊拍肖像,攝影師說當然可以。于是,他嘴里咬著大口熱狗的笑容被定格在了照片上。
至今,塞爾維亞的經濟還沒有完全回到1989年以前的水平。南斯拉夫曾是東歐最富足的國家,上個世紀60年代,前南斯拉夫的經濟水平達到巔峰,甚至明顯超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但在鐵托死后,他之前的民族政策也為之后南斯拉大的分裂埋下了伏筆。南斯拉夫在中東歐劇變大潮沖擊下于1991年后分裂。隨著沒完沒了的戰爭,食不果腹的貧民逐漸習慣了為幾片面包排隊等待。
在經過一片荒無人煙的山野時,攝影師劉旭陽和蘇宇發現一個多層樓房的廢墟。下車走近時,廢墟里卻走出兩個伐木工。其中的一位原本生活在塞爾維亞,因為戰爭的原因,不得不回到家鄉加入武裝部隊,轉而攻打自己曾經生活過的地方。在那場戰爭中,他的眼睛受了傷,視力受到嚴重影響,如今只能在山林里伐木謀生。伐木工說,其實塞爾維亞人都很好,只是大家都以為戰爭能讓生活變得更好。但是顯然,“命運跟大家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

在波黑中部城市亞伊采,一位撐著雨傘的婦女經過被子彈打得千瘡百孔的墻體。
半山腰上,他們遇到一位牧羊的老奶奶,她的大兒子在戰爭中去世,二兒子長大以后成為了工程師,參與了一些紀念碑的修復工作,雖然往往因為經費工程一直在拖延。獨居的老人則一直在山坡上牧羊。“其實還是有人會去紀念,并沒有被遺忘。”老人對劉旭陽說。
在去克羅地亞的路上,他們的車子不慎翻入了一條水溝。幸好路過的警察和農民幫助把車移了出來。淳樸的農民從來沒有見過亞洲人,特別是中國人,他們熱情地拉著劉旭陽和蘇宇合照。劉旭陽趁機提出請求為他們拍一些照片。“當我指揮他擺姿勢的時候,我看到他的拖拉機上寫著‘Made in Yugoslavia(南斯拉夫制造),這很應合我的拍攝主題,于是我叫他站到字跡旁邊并拍下了一張照片。這段文字最終也成為了整個拍攝主題的名字。”他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這些紀念建筑基本位于二戰時期巴爾干半島重大戰役的發生地、集中營舊址、烈士公墓等,曾經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吸引過百萬參觀者。比起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紀念碑,前南斯拉夫的紀念碑是絕對的抽象化風格,幾乎很少有表達政治的元素或符號。
“這些紀念碑就像歷史的見證一樣,可以經歷長時間的洗禮。我也喜歡用鏡頭去記錄這些痕跡,經過時間流逝后,戰爭、災難對當地人、環境的影響,就像我接著做的切爾諾貝利主題系列一樣。”劉旭陽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軍事區的一棟附屬樓內專門做意識形態宣傳的房間,角落里的一幅宣傳畫:在共產主義蘇維埃的領導下,海陸空三軍緊緊團結在一起。
軍事基地里,一幅關于冷戰時期蘇美軍備競賽主題的壁畫。壁畫上摹著蘇聯的太空計劃暢想,衛星、載人航天、甚至是更具來來感的星際穿越都在其上。
禁區探索者們的圣地——一輛廢棄的大巴。探索者們在此過夜,交換生活必需品并留下探索日志。核災難后政府設置了五公里、十公里等隔離區關青配有持槍士兵守衛;普通民眾被限制進入相關區域,不過仍有冒險者以他們的方式偷偷潛入。大巴內部,桌面上放有一位探索者留下的糖。
作為一個核工業附屬城市,普里皮亞季早已將核安全知識在方方面面普及,學校的宣傳欄也貼有安全疏散和防毒面具使用指南。
切爾諾貝利
繼《南斯拉夫制造》系列之后,劉旭陽將鏡頭轉向了自1986年沉寂至今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與普里皮亞季城,前者是當年那場震驚全球的核事故的發生地,后者則是前蘇聯政府為安置核電站員工及其家屬所建之城。
進入輻射區的第一個早上,劉旭陽與策展人周小登跟隨向導鉆進五公里封鎖區郊外一棟廢棄的民房,吱吱作響的木地板上散落著房主密密麻麻的病歷卡,營造了莫名的詭異氣氛。屋外的道路早就消失,零星的建筑隱在樹叢之中,就像雨后草地上星星點點的菌菇。而當他們經過一個堆放清除核廢料用的工具車的“墓地”時,隨身攜帶的輻射探測儀立即發出刺耳的警報。
畸形、輻射、死亡、污染,類似的詞語在警報聲中變得切實可感。
2016年之前,切爾諾貝利之于劉旭陽是一直是個遙不可及的存在。直到從新聞上得知,覆蓋爆炸點四號反應堆的舊“石棺”已老化,一旦出現裂縫或倒塌將導致輻射污染源進一步擴散,各國不得不攜手建設新的保護殼并拆除舊“石棺”,他們才決定動身前往。
切爾諾貝利現今依舊是一個禁區,僅在近些年才開放授權給烏克蘭境內極少的向導機構,任何游客都需要經這些公司辦理許可才能進入,他們通過當地旅游公司拿到了通行許可證。當他們翻入各個學校、醫院、實驗室廢墟時,輻射警報不時響起。每當向導停下腳步左右張望,便是要帶他們進一些“不該進”的地方。作為接收輻射傷員的場所,普里皮亞季醫院遭受了僅次于四號反應堆的輻射污染。曾經存放受污染防輻射服的地下室至今存有超量輻射,甚至繼續在向外擴散。當他們靠近角落的一雙手套時,探測儀再次發出了刺耳警報。他們二人不得不多次臨時上調了探測儀預警線的標準,用這種掩耳盜鈴的方法安慰自己。
但在接下的兩天中,劉旭陽和蘇宇碰到了一位仍生活在核心輻射區附近的老奶奶。院子被打理得井井有條,房屋也沒有破損得很厲害。屋內沒有開燈,老奶奶身穿帶著藍色碎花的傳統服裝坐在床上,能見到少見的客人她很開心。
老奶奶的名字是Galina Yavchenko,相熟的人也稱她為Galya奶奶。她在災難發生后的一年回到由祖父開墾的故土生活,最終,政府也沒有驅趕她。
這些年,她僅靠政府給的一點養老金生活。一位園丁每月幫她將錢取來,也幫她買一點生活必需品。這是她僅有的收入。一面墻上掛滿了照片,有她年輕時候的影像,以及與愛人、孩子及孫子在一起的照片。右上角的一個掛歷,撕到了當日日期。
在提及在房間內看到的一套蘇聯制服時,Galya眼神有些暗淡。她說那是她一個兒子的制服。在蘇聯解體前,她的兒子住在僅有一個小時車程外的白俄羅斯。蘇聯解體后,白俄羅斯變成一個國家,以前一個小時的路程現在因為要穿越不同的檢查站而變成了一天。而那套制服也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被兒子留在這里。
臨走之前,劉旭陽給她拍了一張肖像。考慮她的腿腳不便,劉旭陽讓她就坐在床榻上,背景是很具當地特色的掛毯,房間內極暗,他開大光圈到1.8,用手機手電筒作主光源,完成了那張照片。
所有人離開輻射區前都必須進行輻射劑量測試,以防污染源被帶出。因此,他們把衣物都留在了當地。檢查站五百米外就是白俄羅斯的國界,當值的士兵們對他們很友好,還熱情地請他們喝泡制的檸檬茶。士兵們在檢查站墻頭的禁煙標示下抽煙,喝完一杯檸檬茶劉旭陽才想起,進輻射區有條限令是不能在戶外飲食喝水。輻射區外的人把這些防核指南熟記于心,而輻射區內,從災難中幸存下來的人不愿再為延長壽命而忍受過多束縛。
“污染區內尚有幸存老者居住,動物正常友好,禁區探索者們建立了自己的社會網絡,新的教堂和圣母像被豎起。這是真實的切爾諾貝利,它正在緩慢地自我愈合。”劉旭陽說。
不帶情感的記錄
2013年,劉旭陽開始實施廈門的沙坡尾紀實拍攝計劃,他想記錄沙坡尾從一個漁港逐步被拆遷改造為城市文化商業地標的過程,希望借此記錄人類文明替代地貌運動對城鄉地形發生作用的過程。
紀實攝影是劉旭陽生活工作的中心,自倫敦傳媒學院新聞與紀實攝影專業碩士畢業后,他常往返于北京、廈門兩地。廈門是劉旭陽的出生地。因此,他在這座與其成長經歷相連結的城市,進行了研究生畢業后的第一場展覽。2017年4月他在廈門舉辦了《南斯拉夫制造》的首場個展,后來又舉辦了《野草:切爾諾貝利影像紀實展2017》的展覽,還在廈門、大理、成都、福州等地巡展。
從小受攝影發燒友的父親影響,劉旭陽一直與相機有著親密接觸。大學本科學習攝影,后來在選擇研究生課程時,選擇了紀實性攝影。他記得碩士導師Paul Lowe曾在課堂上提到:我們的照片不能有任何像素上的改變,比如把畫面中某個物體、元素抹除掉,或者在人臉上動手腳都是不允許的,因為這些都會給觀看者帶來偏向性引導。
“我拍的這些照片是不帶任何濾鏡的純粹,我沒什么社會責任感,我所做的事情就是盡量公平而不帶情感政治色彩地去記錄。并且,我害怕所謂的社會責任感讓我的作品產生立場偏頗,從而引導讀者到我所設想的環境中去。”劉旭陽這樣說。
(文章部分內容經授權摘取自周小登、劉旭陽拍攝日志)
一座未完工的冷卻塔內,涂鴉為澳大利亞藝術家Guido van Hclten向災難發生后首位進入輻射區的俄羅斯攝影師Igor Kostin(1936-2015)致敬所作
“莫斯科之眼”是蘇聯與美國太空競賽的產物——超視距雷達系統,其探測范圍高達1萬公里,作為當時蘇聯研制出的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系統,“莫斯科之眼”運作時,全世界短波頻段卻能接收到這個蘇聯雷達發出的聲音,故其又被厭煩地稱為“俄羅斯啄木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