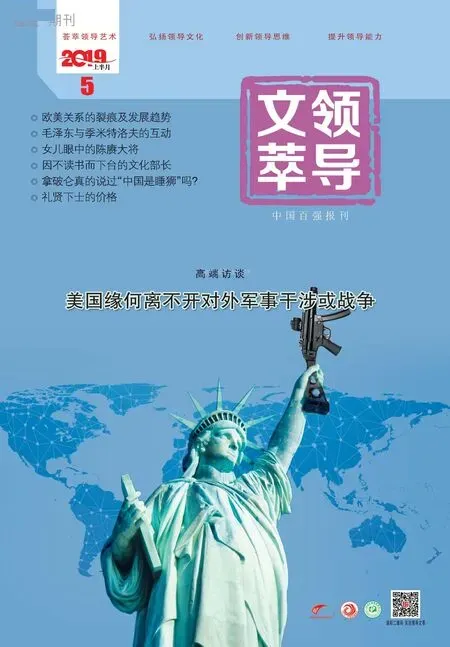日式公關大滲透
雪珥
在甲午戰爭中,日本遭遇了兩次公關危機。
第一次是在戰爭前夕,日本軍艦在朝鮮海面打沉了運送清軍援兵的英國商船高升號,導致千名中國軍人和歐洲船員死亡。當時中日兩國并未宣戰,高升號由英國船員駕駛,且飄揚著英國國旗。高升號事件引發西方社會嘩然,死傷慘重的英國更是群情激憤,軍方要求對日本采取軍事報復。
被海軍的魯莽行動弄得措手不及的日本政府,實施了一連串的緊急公關行動。在輿論對己相當不利的情況下,日本政府一是沒有回避,立即向英國表示,如確系日艦違反公法,則日本政府將給予賠償,先將英國官方穩住,避免事態惡化;二是全面收集情況,包括各種不利消息都在第一時間傳回大本營,以及時掌握真實動態,沒有出現報喜不報憂的情況;三是迅速進行官方調查,對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進行了有針對性的剪裁,形成了對自己極為有利的調查報告;四是舍得投入,在人力、物力、財力上下功夫,試圖引導和改變英國輿論。
日本的防守反擊策略十分有效。9月份大東溝海戰后,日本就明顯感覺到了“英國人民在牙山戰役前對我國所懷的感情,現在已是如何的大為改觀”。
日本人遭遇的第二次公關危機,是旅順大屠殺帶來的。
日軍攻占旅順后,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隨軍的西方記者們尤其《紐約世界報》(New York World)的克里曼( James Creelman)進行了大量的報道,震撼世界,一時有關日本是“文明國家”的聲調急劇衰退。
面對西方輿論的不利影響,日本政府開始全面公關。他們首先將這些屠殺行為解釋為對中國軍隊的殘忍行為進行的正常反應。西方報刊開始連篇累牘地報道說,日軍在攻占旅順時,發現此前被清軍俘虜的日本士兵,都被殘忍地殺害并遭到肢解。日本的辯護者們認為,旅順大屠殺只是一次過激了的以血還血的報復而已,那些“以為日本人回復到野蠻狀態的說法是荒謬可笑的”。
但克里曼對旅順大屠殺所進行的長篇揭露,影響極大,日本人憤怒指控他的報道夸大其詞,擔心其會影響美國及歐洲國家政府的態度,但并沒有記錄表明日軍對他隨后的采訪采取了任何限制。美國政府特別要求駐日本公使譚恩(Edwin Dun)對克里曼的報道進行核實,調查范圍遍及目擊慘案的在旅順西方人和隨軍的西方軍事觀察員,雖然都證明日軍暴行屬實,但美國政府并不贊同克里曼報道的“新聞導向”,其調查結論依然認為報道過于極端。
美國政府的態度激勵了日本當局,他們開始也更積極地形象重塑。在經過血戰攻陷另一大軍港威海衛后,日本實施了一場大規模的“行為藝術”式的宣傳。他們的戰地紅十字會給受傷的清軍提供醫療服務,并釋放了所有俘虜,還給他們發放了兩天的食物。對于戰敗自殺的丁汝昌,日本給予了很高的禮遇,準予北洋軍艦康濟號在北洋高級軍官們護送下,載運丁的靈柩離開威海。
所有這些,都在西方記者和軍事觀察人員的眾目睽睽下進行,并通過公開的報道和秘密的情報渠道向全世界傳播,大大扭轉了旅順大屠殺造成的惡劣形象。
值得注意的,這支“文明之師”中的很多成員正是參與了旅順大屠殺的同一批人。在日式危機公關的背后,不僅僅是對西方媒體的圓熟運用,也有更深層次的實力支撐。那就是當時日本國內已經相當成熟并獨立的媒體機制。
明治維新后,西方的媒體觀念和運作方式被引進日本。媒體獲得了相對獨立、不被政府(此處指狹義的行政機關)隨意干涉的地位,被稱為“第四種權力”(The Fourth Estate)。
媒體的相對獨立,對行政當局形成了巨大的制衡。陸奧宗光在其回憶錄中說,甲午戰前,在眾議院中占多數的反對黨,曾比政府更激進地鼓吹向朝鮮進軍,甚至準備彈劾“軟弱”的政府。不堪“干擾”的政府干脆解散了議會,但反對派卻利用媒體,更猛烈攻擊政府的“因循誤事”。官方對媒體的開明姿態,獲得了媒體的主動配合,美化戰爭、美化日軍,成為日本媒體的自覺行動,有效地凝聚日本的民心士氣。
反觀中國,官方和民間對國家形象的塑造、對媒體的運用均相當漠視和遲鈍。在高升號事件中,中國駐英國公使龔照瑗即提醒李鴻章,事件的解釋多出自日本人之口,這是危險的,中國應加強在海外的輿論宣傳,但清廷的作風相當僵硬,自以為正義在手,坐等英國對日興兵問罪,結果,眼看著日本人將原本親華的英國輿論徹底扭轉。
德國學者認為,中國對西方媒體完全持排斥的態度,不允許任何一名記者隨軍,軍事顧問是僅有的隨軍西方人員。而日本則不遺余力地抓住每一個能宣揚自己的機會,這導致兩國的國家形象出現了巨大落差。
中國媒體的對外宣傳、對內動員功能被棄置,導致中文媒體的報道甚至比西方媒體更滯后、更不可靠,甚至出現錯誤報道。鉗制媒體的后果是不僅封住了自己的喉舌,也導致了對政府更為反感的情緒蔓延。而當時各口岸的中文報業,正處于高速起步階段,多在租界內辦公,有的本身就是西方人經辦的,清政府要控制“新聞導向”是相當困難的,其報道的自由空間遠高于日本同行。但中文報紙依然自覺過濾新聞,熱衷于報喜不報憂。平壤之戰,清軍大敗,守將葉志超諱敗報捷,從官方到媒體一片聲地喝彩,成為國際丑聞。
即使面對戰敗恥辱,中文報紙仍有本事找到嘲諷日本的“新聞眼”。北洋舊艦操江號被日軍俘獲后重新使用,《申報》《字林滬報》等先后發文,嘲諷日本將“既小且舊,為中國所不甚愛惜”的破船當作寶貝,還為如此小事奉告先祖,“言詞夸誕欺及先人”,先人“泉下有知,當深恨子孫之國祚將傾,為之痛哭流涕矣,祭告胡為者?”對日本的無謂嘲諷充斥中文報章,而在日本報紙上常見的扎實的社會調查報告,卻難覓蹤跡。
平壤戰役的假新聞,通過路透社(Reuters)傳往全球,給這家通訊社帶來相當大的影響。真相澄清后,美國媒體轉而更多地依賴合眾社(United Press Service)供稿。假新聞對中國的形象造成進一步的傷害,美國《輿論》雜志(Public Opinion)對從波士頓到舊金山的主要媒體的編輯們進行了民意測驗,結果顯示日本贏得了普遍的尊重,并多被視為平等的文明國家。
所謂的危機公關,其能力固然體現在危機之中,其根源卻在危機之外。
(摘自《國家人文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