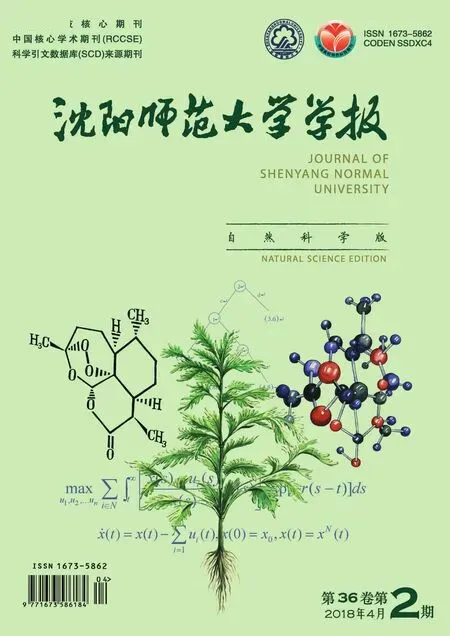遼南某村土壤重金屬污染評價與來源分析
張 蕾, 李 洋, 易佳瑩
(1. 沈陽師范大學 生命科學學院, 沈陽 110034;2. 沈陽師范大學 化學化工學院, 沈陽 110034)
0 引 言
土壤重金屬的人為污染主要來自于工礦業和農業活動,2014年發布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稱全國采礦區土壤超標點位為33.4%,主要污染物為鎘、鉛、砷和多環芳烴等。尾礦庫和礦渣堆不僅會造成土壤污染[1-3],同樣會對水環境[4-5]和周圍的農作物[3,6]質量產生不良影響,嚴重威脅著生態系統和人類健康。
遼寧南部某村,由于在該村的東南方向,即春夏季的上風向,建立了一座垃圾填埋場,當地居民飽受垃圾填埋場臭氣的困擾。而由于重金屬的污染無色無味,居民對垃圾填埋場旁露天堆放的礦渣堆卻不以為意。2005年起,不斷地有運輸車將“硼泥”礦渣運到這里,且沒有防水和防塵措施。為了調查該地區重金屬污染情況,本研究通過微波消解和電感耦合等離子發射光譜法分析該村土壤中鎳(Ni)、鉻(Cr)、砷(As)、鉛(Pb)、銅(Cu)和鎘(Cd)等重金屬含量,對該村的土壤重金屬污染現狀進行評價,以期為該村的環境治理與保護提供科學基礎。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域概況
調查區域位置如圖1所示,露天堆放的礦渣堆西側還有一所生活垃圾填埋場,它們大約于2005年建成。生活垃圾填埋場的固體廢物主要來源于周邊各大城市,例如鞍山、海城、營口、鲅魚圈和大石橋等的城市垃圾。礦渣堆的主要成分是硼泥,硼泥是生產硼酸、硼砂等產品產生的廢渣,露天堆放無遮蓋處理,Google Earth地圖可見礦渣堆分為南北2部分。垃圾填埋場和礦渣堆位于村莊東南方向,距村莊內最近一戶人家為503 m。用ArcGIS 10.2軟件手動矢量法描出垃圾填埋場和礦渣堆的邊界(圖1),并計算得到垃圾填埋場的面積約為65 962 m2,南部礦渣堆面積約為33 035 m2,北部礦渣堆面積為35 073 m2。居民生活飲用水來源于村莊西測距該礦渣堆2 000 m的位置的地下水,深約150 m。

底圖來自Google Earth,圖像來自于2016 CNES/Astrium, DigitalGlobe圖1 研究區域礦渣堆和垃圾填埋場位置Fig.1 Location of the slag heaps and the landfill in the study area
1.2 樣品采集
沿著礦渣堆到村界線最遠處采集礦渣堆及土壤樣品: 在礦渣堆、垃圾填埋場和礦渣堆中間、距離礦渣堆約35 m、200 m、500 m、800 m、1 000 m、1 200 m、1 300 m、1 400 m、2 000 m等不同距離處采集地表土, 其中500~2 000 m土樣屬于農業土壤, 土壤類型為棕壤土。 采樣點位置圖如圖2所示。 各采樣點地勢平坦,土質均勻, 每個點位取3個土樣, 采樣深度均為0~20 cm。 采樣的同時用GPS定位。
1.3 樣品的分析
1.3.1 樣品的預處理
土樣采集后風干,過10目篩,部分用于測定土樣pH值,用四分法取剩余的土樣約20 g, 用瑪瑙研缽研細, 使其全部通過100目篩,裝瓶封存備用。
1.3.2 樣品的測定
pH值測定于采樣后24 h內完成,土樣pH值采用風干土樣與去離子水1∶1混合懸液測定。樣品采用微波消解法消解,重金屬含量用電感耦合等離子體原子發射光譜法(ICP-AES)測定[7]。平行樣分析用于控制實驗的精密度。平行樣的相對誤差小于5%。
1.4 重金屬污染評價方法
為了比較不同污染物的污染程度,采用污染指數法評價重金屬污染程度,污染指數的計算公式為
式中:Pi為土壤中污染物i的污染指數;ci和Si分別為污染物i的實測含量和標準含量,單位均為mg·kg-1。若污染指數大于1即為污染,小于1即為未造成污染。研究主要評價農業土壤污染情況,故

表1 內梅羅指數法評價土壤環境質量評價分級
土樣中重金屬的標準值采用土壤環境質量標準(GB 15618)的二級標準。在單因子污染指數的基礎上對土壤采用內梅羅綜合因子指數法進行重金屬污染評價[8],計算公式為

式中:P綜是綜合污染指數;Pmax和Pave分別是各重金屬污染指數中的最大值和平均值。按照表1將土壤環境質量分級評價。
1.5 數據分析
所有數據均采用各重復樣的平均值±標準偏差來表示。數據分析采用SPSS 21.0,數據制圖采用Origin 9.1,空間制圖采用ArcGIS 10.2軟件。
2 結果與分析
礦渣堆樣品pH值為8.93±0.25,呈現弱堿性,研究區域土樣pH值范圍都在7.26~8.08之間。采用污染指數表示重金屬含量與標準值的倍數關系。不同土樣重金屬污染指數及綜合評價如表2所示。該研究區域Cd污染最為嚴重,其中礦渣堆的樣品Cd濃度達到了7.48±0.33 mg·kg-1,農業土壤樣品Cd點位超標率為100%,Cd濃度范圍在1.74~2.93 mg·kg-1,超出國家土壤二級標準2~4倍。在距離礦渣堆200~2 000 m距離內,Cd含量并沒有因為采樣點距礦渣堆距離的增長而降低。其次,該村超標最嚴重的污染物為As,點位超標率也為100%。對于As污染,礦渣堆并沒有表現出最高的濃度,而距離礦渣堆最近的農業土壤樣品(5號)表現為最高的As濃度,濃度為64.0 mg·kg-1,而對于農業土壤,在研究范圍內,隨著其距礦渣堆距離的逐漸增大,As濃度呈現遞減趨勢。其他研究的農田土壤重金屬中,僅11號的Ni顯著超標。

表2 不同土樣的重金屬污染指數及污染評價Tab.2 Metal pollution index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assessment of different soil samples
綜合污染指數顯示,土壤重金屬污染程度并沒有因為采樣點距礦渣堆距離而降低,在研究區域7個農業土壤點位中,4個點位是中度污染,3個點位是重度污染,首要污染物均是Cd。需要指出的是,對1~4號樣品評價時采用的是土壤環境質量標準的二級標準,但這些樣品并非農業土壤,故評價結果只做數據對比用,并不能表明樣品的實際環境質量,特別是1號為尾礦堆樣品,并非土壤樣品。
3 討 論
硼泥一般無嚴重重金屬污染[9],然而研究結果顯示礦渣堆除Pb外各種重金屬含量都較高,說明該礦渣堆可能混有其他重金屬污染礦渣。該村土壤的重金屬污染嚴重,土壤重金屬污染程度并沒有因為采樣點距礦渣堆距離而降低,這可能與土壤類型或耕作用途有關,如5號采樣點,雖然是距離礦渣堆最近的農業土壤采樣點,但其污染程度相對較低,可能是因為采樣時其表面覆蓋了密度很大的玉米,玉米正值成熟期,生物量較大,一方面降低了礦渣堆中重金屬在該采樣點的干沉降,另一方面也能提取大量的重金屬在玉米植株內,從而降低土壤中重金屬的含量。但同時也不排除存在其他污染源的可能。采用相關性分析法可以幫助了解土壤重金屬污染的同源性[10-11],確認其是否有可能來自礦渣堆,采用SPSS軟件對各重金屬元素濃度進行Pearson相關性分析,得到各采樣點在各重金屬之間的相關性,如表3所示。分析結果顯示土壤中重金屬Ni、Cr、As、Cd含量間呈顯著的高度正相關關系。說明在各采樣點Ni、Cr、As、Cd可能來自同一污染源。而Pb和Cu與其他污染物并無正相關關系,可能的原因為,礦渣堆鉛含量不高,為138.8 mg·kg-1,土壤Pb污染有一個很重要的來源是交通污染,該村汽車保有量較高,可能會影響到農業土壤中的Pb含量,使其濃度在村中心(6~10號采樣點)的濃度較高,所以與其他采樣點的Pb污染沒有相關關系。土壤中的Cu元素是植物營養的一種微量元素,雖然礦渣堆中Cu含量較高,為142.7 mg·kg-1,但在農田土壤中Cu可被農作物吸收利用,使其濃度降低。除去Pb,Cu這2種元素,對11個采樣點的Ni、Cr、As、Cd元素濃度進行Pearson相關性(表4)分析,發現礦渣堆的樣品與大部分土樣都呈現顯著的(p<0.05)極強(Pearson相關性>0.95)正相關,這進一步證明了土樣中的重金屬同源,考慮到礦渣堆Cd含量顯著高于其他采樣點,礦渣堆很可能是該村土壤污染的主要污染源。而除As外,Cd等污染物的濃度在距礦渣堆200~2 000 m范圍內,并不隨其距礦渣堆的距離增大而降低,說明礦渣堆的影響范圍可能遠大于該村的面積。

表3 研究區域土樣中不同重金屬Pearson相關性Tab.3 Pearson correlation of different heavy metals in soil samples in the study area
注: *表示在0.05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表示在0.01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

表4 基于Ni、Cr、As和Cd含量比較各采樣點土樣與礦渣堆土樣Pearson相關性
注: *表示在0.05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 **表示在0.01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
4 結 論
對遼寧南部某村土壤中Ni、Cr、As、Pb、Cu和Cd等重金屬含量進行了采樣分析,并采用污染指數法評價了重金屬污染程度,且采用相關性分析法分析了該村重金屬來源。得出主要結論如下:
1) 該村土壤的重金屬污染程度為中度污染和重度污染。其中農業土壤樣品Cd和As點位超標率均為100%,Cd的污染最為嚴重,濃度范圍在1.74~2.93 mg·kg-1,超出國家土壤二級標準2~4倍。農田土壤污染會導致食品安全問題,建議對礦渣堆進行封閉處理,該村土壤在修復后方可繼續投入農產品的生產。
2) Pearson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礦渣堆樣品中與大部分土樣中的重金屬含量都呈顯著的極強正相關關系,同時考慮到礦渣堆Cd含量顯著高于其他采樣點,判斷礦渣堆很可能是該村土壤污染的主要污染源。同時不排除存在其他污染源的可能。
參考文獻:
[1]ETTLER V. Soil contamination near non-ferrous metal smelters: A review[J]. Appl Geochem, 2016,64:56-74.
[2]宋鳳敏,張興昌,王彥民,等. 漢江上游鐵礦尾礦庫區土壤重金屬污染分析[J]. 農業環境科學學報, 2015,34(9):1707-1714.
[3]周楠,唐東山,鄧欽文,等. 湖南某尾礦庫周邊農田土壤及蔬菜重金屬污染與健康風險評價[J]. 綠色科技, 2016(6):1-5.
[5]鄒文佳,張淇翔,石林,等. 江西某銅礦排土場與尾礦庫重金屬釋放規律及其對地下水的污染風險[J]. 有色金屬工程, 2016,6(1):90-94.
[6]SUN Z,CHEN J,WANG X,et al. Heavy metal accumulation in native plants at a metallurgy waste site in rural areas of Northern China[J]. Ecol Eng, 2016,86:60-68.
[7]劉雷,楊帆,劉足根,等. 微波消解ICP-AES法測定土壤及植物中的重金屬[J]. 環境化學, 2008,27(4):511-513.
[8]郭笑笑,劉叢,朱兆洲,等. 土壤重金屬污染評價方法[J]. 生態學雜志, 2011,30(5):889-896.
[9]孫青,鄭水林,李慧,等. 中國硼資源及硼泥資源化綜合利用前景[J]. 地學前緣, 2014,21(5):325-330.
[10]JALEES M I,ASIM Z. Statistical modeling of atmospheric trace metals in Lahore, Pakistan for correlation and source identification[J]. Environ Earth Sci, 2016,75(9):842.
[11]孫春媛,趙文吉,鄭曉霞,等. 北京城區土壤重金屬空間分布及與降塵的關聯性分析[J]. 中國科技論文, 2016,11(9):1035-1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