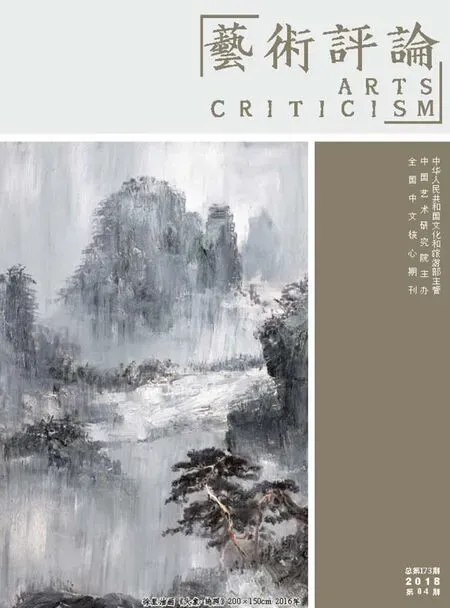當代好萊塢的非美屬性與敘述策略
——以第90屆奧斯卡金像獎獲獎影片《水形物語》和《三塊廣告牌》為例
峻 冰 夏 蕾
峻 冰: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影視藝術系教授、四川省電影家協會副主席
夏 蕾: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文藝與傳媒專業影視與新媒體傳播方向碩士生
由美國福斯探照燈公司出品,由墨西哥導演吉爾莫·德爾·托羅執導的科幻片(或曰其次生類型“魔幻片”)《水形物語》自2017年8月31日于意大利首映以來,已斬獲第74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獅獎,第75屆金球獎最佳電影導演和最佳電影配樂2項獎,第90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藝術指導和最佳原創配樂4項獎。而同樣由美國福斯探照燈公司出品(與英國Film 4公司聯合出品),由英國導演馬丁·麥克唐納執導的警匪片(或曰其次生類型“偵破片”)《三塊廣告牌》,自2017年11月10日于美國上映以來,則斬獲第74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最佳原創劇本獎,第75屆金球獎最佳劇情類電影、最佳電影劇本、最佳劇情類電影女主角(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德)和最佳電影男配角(山姆·洛克威爾)4項獎,第90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德)和最佳男配角(山姆·洛克威爾)兩項獎。截至2018年3月4日(美國當地時間)第90屆奧斯卡金像獎頒獎日,《水形物語》共獲得97項電影大獎,《三塊廣告牌》則獲得82項電影大獎。
《水形物語》與《三塊廣告牌》共斬獲第90屆奧斯卡金像獎6項大獎。不管二者在各大電影節或電影獎上的角逐何等激烈,作為它們的共同出品方美國福斯探照燈公司都是最大贏家。這兩部影片在題材、形式和風格上大不相同,但兩者的敘述策略顯然都采用多類型或多樣式敘事元素融合之法;它們在主題、人物形象等的建構上也突破了以往類型或樣式的界限,加之導演創新元素的植入,兩片頗有藝術化上升的態勢——或者說,它們已經由娛樂片統攝的類型上升為藝術片。正如斯坦利·梭羅門所說:“任何能夠多年存在的樣式都很有可能存在固有的電影特性。內在的電影價值與藝術地利用這些價值顯然是不同的”;“即使對于只用某種樣式拍過一次影片的導演來說,只要他用心使這種樣式的常見特征體現出某種新東西,那末,采用這種樣式也會有重大的好處”。很有意思的是,《水形物語》與《三塊廣告牌》均為外國導演執導;導演們在適應美國好萊塢的類型成規或樣式慣例的同時,也會將源于自我經歷、經驗的新東西或原籍國的民族、文化習慣悄然滲入——影片可能體現出一定的非美屬性;推及開來,眾多非美導演在好萊塢數十年的創作實踐,無疑會使這種非美屬性擴大。這就是說,好萊塢在本質意義上并非美國一個國家的好萊塢;作為一個因發達的經濟和文化軟實力所致的頗具開放性、虹吸性的平臺,它當然受到世界不少國家民族文化和創作者個人經驗、才智的滋養。在某種程度上,好萊塢具有泛世界化的意義。有鑒于此,之于好萊塢非美屬性及其敘述策略的考察,對得益于飛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和文化軟實力而致的產業飛速發展、創作日趨類型化的中國電影的未來實踐大有裨益。
一、好萊塢的非美屬性
(一)好萊塢的泛世界化態勢
英國學者湯林森在《文化帝國主義》一書中曾以迪士尼唐老鴨為例,批判了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策略。他以20世紀40年代美國迪士尼卡通風靡第三世界國家的現狀為研究對象,認為“迪士尼卡通即已風行第三世界國家,因此,把它當成是美國資本主義文化價值的潛在‘負載者’自無不可”。在本質層面上,觀之今之好萊塢的發展狀態,其顯然并非如20世紀迪士尼卡通所標識的文化輸出那么簡單。概言之,當今好萊塢電影風靡世界各國的原因需要更為具體深入的考察。縱觀世界電影史,20世紀三四十年代較為輝煌的舊好萊塢電影更多地表征了美國的生活方式,其所宣揚的富足的美國夢和充斥個人主義的美國英雄招搖于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但自20世紀60年代末(尤其是21世紀)以來的新好萊塢電影,則明顯地改變了文化輸出的常規范式和敘述策略;單從獲奧斯卡金像獎的影片來看,好萊塢電影所蘊含的文化價值和社會意義顯然已發生重大轉變,它通過對世界主要電影大國優秀導演的主動招納或被動接受,讓從美國本土影業公司出品的電影在宣揚美國夢和美國英雄的同時,更多地傾向于對益于世界其他國家接納的全球普世價值觀(人性、人道、自然、關愛、平等、民主等理念所織就)的塑造——盡管這在某種意義僅具有形式意義和宣傳功能,與它們表面上所褒揚(或者先批判后肯定)的美國的現實(種族歧視遍布、集體槍殺案件多發、大國沙文主義橫行)相去甚遠。然而,也由于這種策略,好萊塢已逐漸不再是“美國的好萊塢”了,它更多地具有了世界性的意義;在這一層面上,好萊塢成為“世界的好萊塢”——盡管大量的資本在實質上通過制片公司的美國化依然大量向美國本土聚集。
若從《水形物語》和《三塊廣告牌》這兩部外籍導演執導的影片于本屆奧斯卡金像獎上的“最佳影片”之爭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來看,《水形物語》的最終勝出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好萊塢電影文化價值轉型的注腳——《水形物語》演繹了美國偏僻的濱海城市因類似于神或魔的“水陸兩棲高等生物”的被動闖入(因人類的貪念)流溢出“普世的全人類的大愛”;而《三塊廣告牌》則再現了美國被繁華漸漸遺忘的小鎮圍繞犯罪事件所滋生的意識形態與作為主體的社會人之間以及作為個體的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人的寬恕與自我救贖,亦或是美國人對于意識形態及自身的思考、批判與再思考、再肯定。思及開去,除了第90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獎獲得者吉爾莫·德爾·托羅,在近五年的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獎的獲得者中,第84屆的獲獎者邁克爾·哈扎納維希烏斯,第85屆的獲獎者李安,第86屆的獲獎者阿方索·卡隆,第87屆和第88屆的獲獎者亞利桑德羅·岡薩雷斯·伊納里多均為外籍導演。可以說,正是由于外籍導演的貢獻,好萊塢才有了今天的世界性的好萊塢的“霸權”形態,它更加注重所謂普世的文化價值觀的輸出。
(二)活躍于好萊塢的外籍導演

電影《水形物語》劇照
其實,外籍導演涉足好萊塢的現象可以追溯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的大衛·里恩(代表作《桂河大橋》《阿拉伯的勞倫斯》)、勞倫斯·奧利弗(代表作《哈姆雷特》《理查三世》)、阿爾弗萊德·希區柯克(代表作《蝴蝶夢》《后窗》),德國的恩斯特·劉別謙(代表作《璇宮艷史》《天堂可待》)、弗里德里希·茂瑙(代表作《最卑賤的人》《日出》),奧地利的比利·懷爾德(代表作《失去的周末》《日落大道》)等都是這方面較為典型的例子。“二戰”以后,經過了由于“非美調查委員會”的恣意妄為與“反壟斷法”在電影界的重大影響所導致的外籍導演紛紛出走的較為沉默的“好萊塢之后”的時期(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尤其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隨著世界步入后冷戰時期以及美國經濟的復興,好萊塢的全球化影響吸引了不少的優秀電影人,一些來自世界各國的著名電影導演去好萊塢大展身手的狀況漸成常態。毋庸置疑,也正因有著源源不斷的外籍導演的加入,好萊塢才變得今天這般強大。

電影《三塊廣告牌》劇照
簡單地對2000年以來活躍于好萊塢的外籍導演進行梳理,可以看出,他們主要來自于歐洲、美洲、亞洲和澳洲的電影大國。來自歐洲的有:英國的克里斯托弗·諾蘭——代表作《記憶碎片》(2000)、《盜夢空間》(2011)、《敦刻爾克》(2017),大衛·葉茨——代表作《哈利波特與鳳凰社》(2007)、《哈利波特與混血王子》(2009)、《神奇動物在哪里》(2016),馬丁·麥克唐納——代表作《殺手沒有假期》(2008)、《七個神經病》(2012)、《三塊廣告牌》(2017),湯姆·霍伯——代表作《國王的演講》(2010,獲第83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獎)、《丹麥女孩》(2015),馬修·沃恩——代表作《X戰警:第一戰》(2011,獲第38屆美國電影電視土星獎最佳科幻電影獎),史蒂夫·麥奎因——代表作《為奴十二年》(2013,獲第86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獎);法國的邁克爾·哈扎納維希烏斯——代表作《藝術家》(2011,獲第84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讓·杜雅爾丹]等5項獎);德國的羅蘭德·艾默里奇——代表作《后天》(2004)、《2012》(2009)、《驚天危機》(2013),湯姆·提克威——代表作《香水》(2006)、《云圖》(2012);挪威的莫滕·泰杜姆——代表作《模仿游戲》(2015,獲第87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改編劇本獎);俄羅斯的提莫·貝克曼貝托夫——代表作《通緝令》(2008)、《最黑暗的時刻》(2011)、《吸血鬼獵人林肯》(2012)。來自美洲的有:加拿大的讓-馬克·瓦雷——代表作《達拉斯買家俱樂部》(2013,獲第86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男主角[馬修·麥康納]、最佳男配角[杰瑞德·萊托]等3項獎),丹尼斯·維倫紐瓦——代表作《邊境殺手》(2015)、《降臨》(2016)、《銀翼殺手2049》(2017,獲第90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攝影獎);墨西哥的亞利桑德羅·岡薩雷斯·伊納里多——代表作《通天塔》(2006,獲第59屆戛納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第64屆金球獎最佳劇情類影片獎)、《鳥人》(2014,獲第87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和最佳原創劇本3項獎)、《荒野獵人》(2015,獲第88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獎),吉爾莫·德爾·托羅——代表作《地獄男爵》(2004)、《潘神的迷宮》(2006)、《水形物語》(2017),阿方索·卡隆——代表作《哈利·波特與阿茲卡班的囚徒》(2004)、《人類之子》(2006)、《地心引力》(2013,獲第86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最佳攝影、最佳剪輯等7項獎);巴西的費爾南多·梅里爾斯——代表作《上帝之城》(2002)、《不朽的園丁》(2005)。來自亞洲的有:中國臺灣的李安——代表作《臥虎藏龍》(1999,獲第73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獎)、《斷背山》(2006,獲第78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最佳改編劇本等3項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2013,獲第85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最佳攝影等4項獎);馬來西亞的溫子仁——代表作《招魂》(2013)、《速度與激情7》(2015)。來自澳洲的有:澳大利亞的巴茲·魯赫曼——代表作《紅磨坊》(2001)、《澳洲亂世情》(2008)、《了不起的蓋茨比》(2013);新西蘭的安德魯·亞當森——代表作《怪物史瑞克》(2001)、《納尼亞傳奇》(2005),彼得·杰克遜——代表作《指環王3:國王歸來》(2003)、《金剛》(2005)、《霍比特人1:意外之旅》(2012)、《霍比特人2:史矛革之戰》(2013)、《霍比特人3:五軍之戰》(2014)。這些導演或是得益于母語英語的溝通便利,或是因獲各大電影節重要獎項,或是因擅長類型電影的拍攝并贏得不俗的票房而踏足好萊塢。實際上,他們不僅是當今好萊塢頗有影響的電影導演,同時也是擁有世界影響力的電影導演——正在也必將繼續促動好萊塢乃至世界電影的未來發展。
二、突破邊界與類型融合
大衛·波德維爾和克里斯汀·湯普森在《電影藝術:形式與風格》一書中寫道:“我們的電影經驗大部分是通過對電影的期待,以及電影本身確認我們的期待而來。”不可置疑,作為20世紀初便確立工業性、明星制并開始產業化的好萊塢來說,在經歷百年的發展之后,它早已形成屬于自己的一套風格、傳統和流行樣式,尤其是自20世紀30年代類型確立以來。有的研究者認為,在相對的意義上,“每一部電影都從屬于一種故事類型,即一個微型電影傳統,帶有其獨特的象征、傳統情節規則、價值觀、扮演定型角色的影星以及各國觀眾多年看電影學會的期待”。《水形物語》和《三塊廣告牌》盡管在類型元素的植入、藝術風格的建構等方面大相徑庭,但二者都十分注重影片本文的故事性、敘事奇觀(宏大奇觀與微奇觀皆具)和細節密度的營建,角色設置上也都選取了“并不完美的、有缺陷的”女主角作為性格刻畫的重心,雖然在敘事手法上,《三塊廣告牌》使用了不少的閃回,較《水形物語》更為復雜,但二者都在各自的言說場域完成了有一定社會指向性的較有深度的敘述。可以說,在影像表達的深層意旨上,《水形物語》和《三塊廣告牌》在繼承類型慣例與主導類型元素的同時,都有著明顯的突破邊界與類型融合的態勢。這種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觀眾的某些期待,頗為自由、新穎的敘述策略可以讓來自非美本土的創作主體輕松采用不同的電影類型元素,傳達不同的主題意蘊和文化內涵。
(一)《水形物語》的跨類融合
《水形物語》的故事背景被設定為1963年仍處于冷戰時期的美國。在政府秘密實驗室做清潔工的僅能通過手語與人交流的殘障女主人公伊莉莎(莎莉·霍金斯飾)與從南美洲荒野沼澤地抓來的渾身長滿鱗片的高等水陸兩棲生物(道格·瓊斯飾)的奇幻愛情,以及他們在鄰居查爾斯(理查·詹金斯飾)、同事澤爾達(奧克塔維亞·斯賓瑟飾)和科學家羅伯特·霍夫斯泰特(邁克爾·斯圖巴飾)的幫助下逃避實驗室保安部負責人瑞查德(邁克爾·珊農飾)的迫害的驚險經歷,被第一人稱的主觀敘事者(鄰居查爾斯的視點)講述為一出頗帶現實主義色彩的科幻(或曰魔幻)傳奇或童話。其實,片頭那個長達3分鐘的段落鏡頭對一個巨大的水下城堡中沉睡的公主的描繪,已經暗示了《水形物語》的科幻片的類型歸屬——不會說話的“公主”、可能打破一切的“惡魔”在某種意義上就帶有既有類型的超現實、超自然的意味,而隨著另一極能體現類型慣例的角色(非人類的兩棲奇異生物)的出現則進一步得到確認。顯然,這是向主角乃非人類的傳統科幻片——如《E.T.》(史蒂文·斯皮爾伯格,1982)、《現代美人魚》(羅恩·霍華德,1984)、《阿凡達》(詹姆斯·卡梅隆,2009)等——的致敬。
在科幻片的主導類型中,《水形物語》極大融入了愛情題材影片(也有學者將其視為“愛情片”類型)的敘事手法,張曉凌和詹姆斯·季南在《好萊塢電影類型》一書中將“愛情片”類型分為四類:“傳統好萊塢愛情片、短期關系的現代愛情片、‘談判式關系’的現代愛情片和‘受驅逐關系’的現代愛情片”四種類型。不論這種標準不甚統一、界限不甚明了的劃分是否還有進一步商榷的余地,《水形物語》中男女主人公的奇幻愛情卻也都符合所謂“受驅逐關系”的“現代愛情片”模式。伊莉莎的身體缺陷及性格、身份能指顯然標明了她是一個有別于主流人群的“邊緣人群”,而作為人類實驗對象的非人類的男主人公無疑更加邊緣化——他們的相愛必然有違社會成規或倫理準則。其實,《水形物語》明顯借鑒了《現代美人魚》的表述模式——其中亦有非人類的生物得到人類主角的喜歡和保護,亦有保守的反文化勢力欲殘害或研究這一非人生物,影片的結局也是男女主人公跳入海中快樂地在一起(不同的只是人類男性主角跳進海中與非人類的女性生物在一起罷了);兩片的不同之處在于《現代美人魚》中的美人魚有著人類的臉龐和人性,然《水形物語》中非人類生物既無人類的面容,也明顯地帶有獸性(這應是繼承了托羅《地獄男爵》一片中魚人的形象建構思路):他咬掉了瑞查德的兩根手指,第一次吃女主人公所送雞蛋時也是一種全然的獸態,而且他生吃了一只查爾斯所養的貓。顯而易見,《水形物語》的明顯植入性關系的“人獸戀”的奇思怪想與現實對象化,大大突破了以往愛情題材影片的樣式或類型邊界。

電影《三塊廣告牌》劇照
事實上,《水形物語》還植入了恐怖片的類型元素——男主人公令一般人毛骨悚然的非人形象及“獸性”呈現都說明了這一點。這類似于美國導演保羅·施拉德執導的融入恐怖片元素的驚險片《豹妹》(1982):擁有非洲豹血統的豹妹伊瑞納(娜塔莎·金斯基飾)和動物學家奧利弗·亞特斯(約翰·赫德飾)的愛情故事是令人感傷的,因為豹妹如和男人親吻或發生性行為就會變成一頭豹子殺死身邊這個男人,在她因和哥哥之間的激情碰撞而變成豹子并被關進動物園之后,與深愛自己的奧利弗只能進行“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而無法相擁而眠。盡管《水形物語》與《豹妹》兩片均涉及恐怖元素和愛情題材成分,但前者無疑比后者的想象更為大膽,后者只是將愛情、人性與欲望、獸性在非人非獸的豹妹身上物化(人型代表愛情和人性,獸型代表欲望與獸性)但不能并存共生,可前者卻將男女主角之間的“男女之事”直接以鏡頭語言展現——這無疑又是《水形物語》的一大突破,因為在以往的影片中是不多見的。
不僅如此,《水形物語》還巧妙植入警匪片的次生類型“諜戰片”的類型元素——羅伯特·霍夫斯泰特博士雖是一名來自蘇聯的間諜,但他因被非人類生物的“通人性”所打動而最終放棄殺死其的政治使命,選擇站在自然、人性、善良的一方,盡管為此獻出生命。當然,《水形物語》用那段伊莉莎幻想出來的優美的男女主角的舞蹈場景也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歌舞片的元素。這顯然既是向20世紀三四十年代歌舞片黃金時期的《海上戀舞》(馬克·桑德里區,1936)和《百老匯旋律》(哈利·博蒙特,1940)等片的致敬,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韓國導演李昌東所執導的《綠洲》(2002)一片的借鑒——在這部曾獲第59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獎的影片中,患小兒麻癖癥的殘障女恭洙(文素利飾)多次對與真愛自己的可謂正常人的男朋友忠都(薛景求飾)的歡快舞蹈的完滿性想象也是凄婉美麗的。

電影《水形物語》劇照
(二)《三塊廣告牌》的跨類融合
帶有明顯寫實色彩的《三塊廣告牌》顯然具有明顯的警匪片之次生類型“偵破片”的特征。影片以20世紀80年代生活于美國密蘇里州的一座小鎮上的女主人公米爾德里德·海耶斯(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德飾)的女兒外出慘遭奸殺然警方遲遲抓不住兇手為故事誘因,憤怒的母親租下小鎮旁邊的三塊巨型廣告牌質問患有胰腺癌的警察局長威洛比(伍迪·哈里飾)“為什么”并引起眾怒(因威洛比是小鎮公認的好警察)的率性行為,可以視為警察偵破奸殺案件的插曲。把插曲放大,凸顯每個利益相關者面對公眾惡性事件的性格演變與言行、心理表現以啟人深思、發人覺悟,無疑又是對傳統偵破片的突破——影片甚至沒有設定嚴格意義上的帶有二元性的好人、壞人,甚而也沒有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嫌疑人;奸殺案件的開放式結局直接指向曖昧、模糊的物質現實而具有逼真的紀實魅力。
《三塊廣告牌》還植入強盜片之次生類型“犯罪片”的類型元素。帶有一定的種族歧視傾向、表面上仿佛“惡警”的迪克森(山姆·洛克威爾飾)因維護警長威洛比的名聲或尊嚴對小鎮廣告商雷德·韋爾比(卡萊伯·蘭德里·瓊斯飾)大打出手的惡劣行徑,隱喻了現代社會犯罪根源的一種向度。自然,米爾德里德在自己租用的廣告牌被燒之后用燃燒瓶火燒警察局的行為顯然是傳統強盜片常見的視覺圖譜;它以激烈、殘酷的畫面配以舒緩、溫柔的音樂來凸顯人物人格嬗變的同時,也揭示了悲劇性性格(米爾德里德對女兒粗暴的態度和拒絕借車的簡單行為實是其女兒慘遭奸殺的直接動因)乃是犯罪根源另一向度的深意——這種逆向表達的音畫處理恰與好萊塢經典強盜片《教父》(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1972,獲第45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改編劇本等三項獎)中教父受洗的場景有異曲同工之妙。
當然,《三塊廣告牌》也帶有情節劇的某些特色。托馬斯·沙茨對“情節劇的敘事程式”作過這樣的表述:“它相互聯系的角色的家庭、它壓抑的小城鎮環境和它對于美國社會群體內性的道德的關注”。《三塊廣告牌》聚焦20世紀80年代末正值全球股災背景下的美國小鎮,它以“社會普通民眾與權威的二元對立矛盾”為外殼,深刻地揭示了母親與女兒對立沖突的家庭關系。在某種意義上,米爾德里德租用廣告牌、火燒警局等過激行為其實也是一位母親對自己無言的懲罰——她與女兒賭氣的言行卻讓女兒從此再也不可能回到這個接近裂解的家里。影片以較為復雜的人物關系配置,將家庭矛盾、婚姻糾葛、種族歧視、暴力、戀母情結等元素全部植入這個日漸沒落的偏僻小鎮,但影片也并不那么令人悲觀,片尾處迪克森與米爾德里德的和解其實也可看作另一種形式上的“家庭重建”——小鎮從沖突、對立到最后和諧、統一的轉變,實際上表征了影片作為美國人的自我批判與修復重構的能指本文。
另外,《三塊廣告牌》還具有一定的黑色喜劇片的幽默色彩。這主要體現于與警察局長一樣困于小鎮奸殺案的警察迪克森的性格刻畫上:有種族歧視和戀母情結傾向,總愛在警局看漫畫,隨時隨地帶著耳機、搖頭晃腦地沉浸于自己的頗為幼稚的音樂世界中——即使在剛剛驚聞局長自殺的警局里和夜晚的警局幾乎被大火包圍之時。一如《好萊塢電影類型》一書所指出的,喜劇人物幾乎都有“一種很強的滑稽觀點、缺陷、人性和夸張”。迪克森有著和周圍警察大不相同的世界觀,而且他非常可笑的言行也受到這種觀點的支配——因種族歧視而攻擊黑人、墨西哥人,因歧視同性戀而攻擊雷德·韋爾比,因自我的茫然無知與對母親的依戀而盲目聽從母親以暴制暴的建議而直接抓人、打人,因在黑人警察局長面前的狂妄自負而慘遭解職。誠然,米爾德里德腳踢兩個向自己的汽車扔飲料瓶的學生的襠部,以及其與前夫的19歲小女友兩次會面的場景等,也具有讓人忍俊不禁的黑色喜劇效果。
三、多元呈現與藝術創新
顯而易見,《水形物語》與《三塊廣告牌》可以被視作類型,但它們也是因創作主體的藝術創新而藝術片化了的典型。審慎探究,這種深入潛在本文的可謂導演自我的“新東西”,主要體現在題材的選擇、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主題意旨的開掘上。
(一)題材的多樣呈現
路易斯·賈內梯在《認識電影》一書中談到現實主義電影時這樣寫道:“在現實主義的電影中,不言而喻的作者實際是看不見的。各種事件‘為自己說話’,就像在大多數舞臺劇中那樣。故事情節好像是自動展開的,通常是按時間順序。”《水形物語》雖是科幻片,但其卻假定了一個現實主義的故事背景(美蘇1963年的冷戰時期),而且在片頭和片尾都以畫家查爾斯的畫外音一再證明了“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也因如此,《水形物語》的科幻題材則在一定程度上被涂上了現實主義的色彩。誠然,比較起來,《三塊廣告牌》的偵破題材則完完全全地建構在現實主義的基石之上。
從影像風格和潛在意義上來講,《水形物語》更像是一部暗黑童話,有著淡淡的朦朧的懷舊意味。影片整個影調偏水鴨綠色,節奏舒緩地充斥水的形狀的影像,表達著和水一樣的溫情愛意和人文情懷。邊界突破了的多類型電影元素的融合,展示著多樣化同時也是曖昧多義的題材:科幻、愛情、諜戰、恐怖、童話、民間故事等題材成分充斥其間,同時還涉及殘障人、黑人、同性戀、種族歧視等話題。當然,片中的“人獸戀”實是題材方面的最大突破。導演并沒在影片中忽略“性關系”的處理,而是以十分動人的畫面直觀展現了男女主人公發生性關系的場景。顯然,這可以被認為是基于對主題呼應的導演意圖使然,因為男女主人公都是不完整的,女主人公的人性因身體缺陷(不能說話,只能以啞語交流)而受到極大的抑制,而男主人公直到遇到女主人公時,其“獸性”才逐漸得以抑制,人類的意識方有所覺醒(如對人類語言、情感的認知等)。兩個有缺陷的人性漸漸得以張揚的“高等生物”的“性關系”鏡語似乎直接暗示了受眾:“不完整”因為不無人本意識的“愛”達成了“完整”甚至是“完滿”——倘如此,導演實將自我內心最狂野的想法展現在了銀幕。
同樣是多類型融合的《三塊廣告牌》亦涉及了警匪、犯罪、愛情、家庭倫理、同性戀、種族歧視等題材成分。在影像風格上,《三塊廣告牌》較《水形物語》更為硬朗,但也在不經意間流溢出絲絲柔情。影片以《夏日最后的玫瑰》(The Last Rose of Summer
)這首歌為開場曲,其中“所愛的人已經逝去,誰還愿意留在這荒涼的世上獨自凄涼”(And fond ones are fl own,Oh! who would inhabit,This bleak world alone?)的歌詞,無疑為故事情節的推演埋下了感傷的伏筆。影片在影像表達上并沒有回避暴力、血腥等話題,也涉及到一些邊緣題材,甚而把荒誕與痛苦、人性與道德、幽默與釋懷等基于多樣化的題材所延伸的多元主題并置雜糅,同時戲劇性地突出“暴力與憤怒”,從而使影片主題帶有更為深刻的社會批判和反思意識——盡管這也是非美本土的導演浸潤主體意識的一種現實構形。(二)人物形象的隱喻性建構
約瑟夫·M·博格斯和丹尼斯·W·皮特里在《看電影的藝術》一書中曾經提到:“另一種分析電影人物的方法,是將劇中人物劃分為以下三對:固定角色和模式化角色、靜態的和動態的角色、扁平的和圓形的角色。”以此觀照,可以發現,《水形物語》中的人物是固定的模式化角色,也是靜態的扁平角色;劇情的發展對于他們的性格沒有什么影響——他們不自我救贖,而是等待他者的救贖;而《三塊廣告牌》中的人物則是復雜多變的角色,也是動態的圓形角色;其性格隨著劇情的發展而變化——他們既等待他者的救贖,也自我救贖。
《水形物語》中的人物幾乎都是非主流的邊緣人群。正面角色——處于社會底層的有身體缺陷的女主人公和作為“實驗對象”的非人類的男主人公,無疑是極度邊緣化了的。作為正面角色的助手,女主人公的鄰居查爾斯雖是一名插圖畫家,但他又是一名為當時的人們極度歧視的同性戀者——其暗戀對象竟是一名歧視黑人和同性戀的加拿大人;女主人公的同事兼好友澤爾達卻是一名黑人——在1963年的美國,黑人反種族歧視和種族壓迫的高潮迭起(這也反向印證了她的邊緣處境);羅伯特·霍夫斯泰特博士盡管尊重自然、富有人性、同情弱者,但他又是一名蘇聯間諜,其身份是缺失的,最后被蘇聯和美國政府雙重排斥。片中的反面角色瑞查德亦是邊緣化的,他很早就失去了兩根手指,變成直觀上有缺失的“不完整的人”。審慎考察,這些有著固定性格的正反面角色其實都是一種隱喻符號,直接指向由人性、生命、自然(大海等象征)、人道、關愛等標識的“逃離無奈現實、回歸自然或回歸美好傳統和過去的渴望”(正面角色和幫手)的反文化動機理念與由殘忍、死亡、暴力、野蠻、貪欲等標識的“官僚制度的愚昧、貪婪,科學的保守,國家力量的野蠻、殘酷等”的保守的文化價值理念(反面角色)。
《三塊廣告牌》中的人物形象,不管是主要角色,還是次要角色,都是圓形豐滿的,其性格都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而呈現出變化的曲線。實如約瑟夫·M·博格斯,丹尼斯·W·皮特里所說:“有一定的復雜性和曖昧性、難以簡單歸類的獨一無二的個體人物則稱為圓形角色或三維角色”。片中米爾德里德和迪克森顯然就是主次圓形角色的典型代表。米爾德里德作為一名女兒慘遭奸殺的母親,一開始是極為憤怒的,她直截了當地買下三塊廣告牌并質問警察局長威洛比“為什么那么長時間還不破案”,盡管鎮上的人對其議論紛紛,但她絲毫不放在眼里,儼然一個瘋狂的、暴怒的、富有攻擊性的形象;隨著情節的推進,她的形象愈加鮮明,在她與丈夫的關系展示中影片隱約現出其曾是一名家暴受害者,而女兒的死也與其不肯出借汽車有著一定的關聯(她甚至在女兒離家時咒罵女兒被人強奸,結果一語中的)。實際上,米爾德里德的憤怒只是她對女兒死亡的無助和自責的外在表象;由憤怒、暴力、懊悔、自責直至性格轉變后與警察迪克森和解,則是她回歸理性和社會的表征。米爾德里德作為表意符號,她指向富有個性的平民英雄,有一種面對挫折不屈不撓的堅強性格。迪克森作為一個有缺點有個性的警察,無疑是比米爾德里德更為復雜的人物:他在故事開始時的暴力、愚蠢、種族歧視、同性戀身份、強烈的戀母情結,以及對威洛比的絕對服從,對米爾德里德和新任黑人警察局長的出言不遜,對雷德·韋爾比的暴打等,都將其銘文為一個“壞警察”。但威洛比的自殺和他死前寫給迪克森并確信其“好警察”潛力的信無疑對這個“惡警”的性格轉變產生較大影響;也因如此,迪克森勇敢地抱著奸殺案卷宗跳出火場,并開始對母親的建議有了自己的判斷,直至最后與女主人公一起去抓“強奸犯”,成為一個明白自己的責任并敢于擔當的“好人”——這種性格建構無疑在符號意義上指向了官僚制度的保守、粗暴及自我反思與修復。
(三)主題意旨的突破性開掘
按照約瑟夫·M·博格斯和丹尼斯·W·皮特里的看法,電影的主題“指的是將影片整合在一起的中心內容或特殊的關注點”。《水形物語》用想象力包裹了一個看似違反倫理但卻不違反道德的人獸之戀。電影無畏地直面生命本身的美麗或恐怖,將人獸之間的凄美戀情描繪得真切、生動。《三塊廣告牌》則聚焦于司法權力與普通民眾的現實矛盾,將性格的非理性所導致的個人或社會悲劇直觀呈現,令人深思。
然而,值得人繼續思考的是,《水形物語》的深層題旨在聚焦于男女之情以展示性格、人性由殘缺走向完整的同時,它還試圖以男女主人公的殘缺之美像喻同樣可能存有缺陷的生命之美;殘缺的生命對水(自然的具象符號)的依存(如女主人公在浴缸的水中自慰;男主人公不可能長時間地脫離水,否則生命就有危險;男女主人公在水中做愛等)也像喻了人與自然的依存關系:那些超現實的偉力或物事(如男主人公及其身體的創傷自愈功能等)僅屬于自然,人類不應動它;反之,人類的妄念(如片中以科研之名意欲竊取自然的偉力用作軍事目的,竊取失敗便毀滅之)便極可能招致自然的懲罰(如瑞查德之死等)——這盡管是一個歷久常新的話題,但在世界并不太平、局部戰爭頻仍的今天,顯然極具現實意義。另外,伊莉莎使用手語對瑞查德的蔑視性反叛及盜走可謂象征自然偉力的生命并將之放飛的英雄行為,也喻示著社會的弱勢群體或邊緣人群對于強權的非理性蔑視和挑戰。
顯見,《三塊廣告牌》在講述強制性意識形態與主體的現實矛盾與理性和解的同時,又以“無壞人”的中性角色建構(米爾德里德及其前夫、威洛比警長、警察迪克森和他的母親、廣告商雷德·韋爾比、牧師、胖醫生、小個子詹姆斯、廣告維護員等顯然都不是壞人;即使自詡犯有強奸前科的“嫌疑人”也被其出國執行國家任務的補充性說明洗去了壞人的嫌疑)明確地告訴觀影者:這種批判與反思是局囿于有限的場域內的;這個范圍是安全的,另類突兀的元素不可能顛覆社會秩序、道德倫理與家庭結構,理性、情感(親情、友情和愛情)和裂解的家庭必然得以重構(至少是文化意義上的,如片尾迪克森與米爾德里德一同上路的形式化標引)——這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非美本土的導演與好萊塢一直宣揚的美國意識(安全、富足、自由等)達成妥協的結果。此外,《三塊廣告牌》還打破了觀眾在偵破片中尋找壞人的邏輯思維定式和心理期待;作為有著開放性故事結局的影片本文,它以人物情緒及其情感效果為中心,演繹了普通人沖突、反思、批判與自我寬恕、自我認同、自我救贖的感傷心路歷程。
從外籍導演所執導的類型電影《水形物語》和《三塊廣告牌》不難看出,突破邊界和類型融合的敘述策略——創作主體利用既有類型成規及其慣用表達方式,預先建立觀眾對于影片的某種期待,同時在主導類型框架內融入多種類型元素和多樣題材成分——無疑可以滿足受眾的不同口味,克服原有類型的審美疲勞,擴大電影的接受范圍。這顯然是外籍導演同樣可以大展身手的當代好萊塢的自覺選擇。因為,隨著社會文化價值的轉變與觀眾觀影理念的多元化,單一的類型已經無法充分滿足受眾的喜好了。作為世界性的電影工廠,好萊塢深知多元化的電影市場之于類型建構的文化意義和實踐重要性。其實,無論《水形物語》《三塊廣告牌》,還是第89屆奧斯卡大熱影片《愛樂之城》(達米恩·查澤雷,2016,融合了歌舞片、喜劇片的類型元素和家庭倫理、愛戀糾葛等題材成分),抑或是創下中國56億國產票房奇跡的《戰狼Ⅱ》(吳京,2016,該片在戰爭電影的主題構架中,融入驚險片、強盜片、災難片、武俠片等類型元素及愛情、友情、道德、政治、反恐等題材成分;它實際上也是好萊塢類型電影中國本土化的實踐結果),都印證了好萊塢及好萊塢影響下的當代電影突破邊界、類型融合的創作態勢。誠然,多種類型元素的融合不僅能夠繼承經典的敘事模式和敘事手法,也能夠打破觀眾對原有類型的觀影期待,從而在電影的題材選擇、性格塑造和意義表達等方面呈現出更自由的想象力和更廣闊的藝術空間。在本質層面上,好萊塢突破既有類型傳統的類型融合也是在傳統好萊塢類型電影的基礎上對導演風格的彰顯,亦可謂“類型電影”與“作者風格”的有效結合。張曉凌和詹姆斯·季南在所著的《好萊塢電影類型》中對好萊塢類型電影的演變和混合做了這樣的預判:“電影類型的演變:長期趨勢;電影類型的混合:短期發展”。有鑒于此,類型融合的短期發展盡管能夠在較大程度上滿足受眾的觀影需求,但毋庸置疑,“突破邊界”與“類型融合”亦要有一定的限度(不是完全任意、無機的,因為過猶不及),否則便會陷入類型的迷局而迷失自我創作方向。從長遠的角度看,類型融合務必要與電影市場和目標受眾的需求相統一,同時還要不斷發現廣大受眾的新趣味、新需求,把握住不斷變化的意識形態所指和大眾文化心態趨向,進而促動電影類型的演變發展。
注釋:
[1][2]〔美〕斯坦利·梭羅門.電影的觀念[M].齊宇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3:218,217.
[3]〔英〕湯林森.文化帝國主義[M].馮建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82.
[4][14] 曹峻冰.中國主旋律電影類型化的有益探索與啟示[J].藝術百家,2017(5).
[5]〔美〕大衛·波德維爾、克里斯汀·湯普森.電影藝術:形式與風格[M].曾偉禎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115.
[6][7][9][15]〔加拿大〕張曉凌、詹姆斯·季南.好萊塢電影類型:歷史、經典與敘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1,486,646-647,747.
[8]〔美〕托馬斯·沙茨.好萊塢類型電影[M].馮欣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231.
[10]〔美〕路易斯·賈內梯.認識電影[M].焦雄屏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7:207-208.
[11][12][13]〔美〕約瑟夫·M·博格斯、丹尼斯·W·皮特里.看電影的藝術[M].張菁、郭侃俊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64,6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