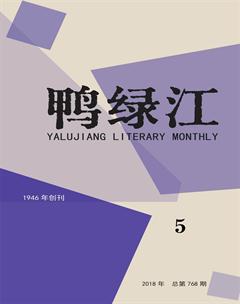燕園吾師嚴(yán)家炎
吳寶三
1984年春,嚴(yán)家炎先生出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我當(dāng)時(shí)在遼寧興城林業(yè)療養(yǎng)院工作,曾去信祝賀,很快接到他的回信。信中說:“雖然好久沒有聯(lián)系了,偶或看到你在《人民日報(bào)》《人民文學(xué)》等報(bào)刊發(fā)表的詩,總感到非常高興,給我?guī)砗艽蟮臏嘏c安慰。就像又回到了往日促膝談心的那種境界里,那么親切,那么令人神往。”
“你不該向我祝賀,而該為我一哭。搞上這個(gè)工作,每天少則五六個(gè)多則十幾個(gè)小時(shí)泡進(jìn)去,有時(shí)連星期天也不得安寧,哪里還有什么時(shí)間寫東西(近年發(fā)表的,都是前兩年寫成的稿子,或是利用節(jié)假日趕出來的),實(shí)在苦不堪言。如果我作出犧牲,能換來全系面貌大改觀,為全系師生創(chuàng)造較好的條件,那也值得。問題是連這一點(diǎn)也做不到。我們的許多設(shè)想,常常被碰回來,手腳被捆得緊緊的,簡直動(dòng)彈不得,怎么能打開局面呢!再過半年若還是這樣,那就只好要求辭職了!”信中引用了《莊子·大宗師第六》中的話:“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他動(dòng)情地回顧了我們開門辦學(xué),在密云縣穆家峪公社前栗園大隊(duì)朝夕相處結(jié)下的情誼,然后無可奈何地說,盡管魯迅不贊成莊子的話,但到了江湖也有江湖的難處,社會(huì)兼職太多,有許多想要做的事做不了,心甚不安。同時(shí)寄來了他新出版的論文集《知春集》,扉頁上端寫了一行書小草:寶三學(xué)弟指正。他生于1933年,長我一旬,雖同屬雞,卻是我的恩師,幾十年來,對(duì)我總以學(xué)弟相稱。手捧這本論文集,我沉思良久,心潮難平。可以說,在燕園,嚴(yán)先生是我最親密、最知心的師長之一。
文藝界許多人不會(huì)忘記,1961年,嚴(yán)家炎先生在《文學(xué)評(píng)論》上發(fā)表多篇評(píng)長篇小說《創(chuàng)業(yè)史》的文章,并引起一場大論戰(zhàn),后來導(dǎo)致全國公開點(diǎn)名批判所謂的“中間人物”論,邵荃麟、嚴(yán)家炎首當(dāng)其沖。揮舞大棒的急先鋒不是別人,正是其時(shí)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姚文元。那一年,嚴(yán)老師只有27歲。1972年在密云鄉(xiāng)下,我倆躺在一鋪大炕上閑聊,我問嚴(yán)老師:“你那時(shí)認(rèn)識(shí)姚文元嗎?”他并沒有感到意外,語氣極平和地說:“開文代會(huì)時(shí),我們見過面。我和他父親姚篷子先生更熟悉些,姚父總是稱其為豎子……”說罷,淡淡地一笑。粉碎“四人幫”之后,嚴(yán)老師把幾篇關(guān)于《創(chuàng)業(yè)史》的評(píng)論文章收入《知春集》中,他在“后記”中寫道:“為了保持歷史的原貌,關(guān)于《創(chuàng)業(yè)史》的幾篇評(píng)論均未做改動(dòng)。今天讀來,這些文章在某些觀點(diǎn)上也許不是沒有問題,有些措辭似嫌輕率,現(xiàn)在讀起來有幾分吃驚。”他只字未提自己和“四人幫”如何斗爭,也沒有標(biāo)榜自己是反對(duì)“四人幫”的勇士,這種客觀的、歷史的實(shí)事求是的精神,多么難能可貴!翌年,他出版了另一本論文集《求實(shí)集》,獲北京市首屆社會(huì)科學(xué)優(yōu)秀成果二等獎(jiǎng)。1988年與唐弢共同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獲全國第一屆優(yōu)秀教材獎(jiǎng),1992年專著《中國現(xiàn)代小說流派史》獲全國第二屆優(yōu)秀教材獎(jiǎng)。曾榮獲五一勞動(dòng)獎(jiǎng)?wù)隆?/p>
嚴(yán)家炎先生,筆名稼兮、嚴(yán)謇,上海人。15歲開始發(fā)表作品。1958年北大中文系副博士研究生提前畢業(yè)。歷任該校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研究生導(dǎo)師,系主任,曾任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會(huì)會(huì)長,第二、三屆國務(wù)院學(xué)位委員會(huì)學(xué)科評(píng)議員,北京市文聯(lián)副主席。他名如其人,文如其人,無論做學(xué)問還是為人處事,一向嚴(yán)謹(jǐn)縝密,嚴(yán)上加嚴(yán),一絲不茍。這些年來,他給我寫過三十幾封信,每封信的信封上,省市單位街道門牌號(hào)無一省略。郵票一律貼在右上角,無一破例。我清楚地記得這樣一件小事:在密云鄉(xiāng)下時(shí),一次吃過晚飯,天已盡黑,我倆從食堂摸黑回住地。路上,聽到大隊(duì)部正廣播通知開會(huì),嚴(yán)老師說播音員是房東家的何姑娘,我說大概不是,何姑娘的聲音要標(biāo)準(zhǔn)些。他堅(jiān)持說是,我堅(jiān)持說非,于是我倆打賭,誰輸誰買一斤糖請客。我以為不過說說而已,孰料他竟一個(gè)人跑到廣播室去核對(duì),回來后滿頭是汗,一邊從兜里往出掏糖,一邊連說:“我之錯(cuò)!”
“文革”期間,系里組織批斗“五一六”分子。我做夢也未料到,嚴(yán)老師竟被打成“五一六”頭子,依據(jù)是,全國大大小小的作家?guī)缀醵颊J(rèn)識(shí)他,無疑是“五一六”分子的總后臺(tái)。第一次批斗有百余人,只見他從一輛破舊自行車上緩緩下來,從容不迫地走進(jìn)會(huì)場,摘下口罩放在上衣兜里,平靜地坐在批斗席上,不管主持者和革命群眾如何狂轟濫炸,他總是那么兩句話:我實(shí)事求是地講,我不是。聲音很輕、很慢,口氣不像是在分辯,似乎在向?qū)W齡前兒童講清楚一件事。毫無疑問,嚴(yán)老師當(dāng)然不是什么“五一六”分子。我真不敢相信,軍宣隊(duì)、工宣隊(duì)怎么會(huì)在沒有任何證據(jù)的情況下誤導(dǎo)學(xué)生呢?!在這次批斗會(huì)上,我一言未發(fā),倒不是不相信軍宣隊(duì)、工宣隊(duì),而是直覺告訴我,像這樣一介書生(嚴(yán)先生自己也這樣說),只知埋頭勤奮做學(xué)問,怎么會(huì)成為組織什么打砸搶的“五一六”分子呢?散會(huì)后,我把他穿的舊棉猴大衣遞給他,他向我微微點(diǎn)了點(diǎn)頭,眼神里頗含謝意,彼此的印象恐怕就是這樣留下的。我欽佩他面臨這樣巨大的壓力,心境平和,從容鎮(zhèn)定,以至由此我聯(lián)想到革命者的視死如歸。后來嚴(yán)老師當(dāng)了文學(xué)專業(yè)的支部委員,還是我的入黨培養(yǎng)人。他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我似乎接受過什么反面教訓(xùn),少了一點(diǎn)年輕人的鋒芒。他不會(huì)知道,我也同他一樣被造反派批斗過,有幾分棱角似被磨光。在嚴(yán)老師的培養(yǎng)幫助下,我于1972年2月在校入了黨,黨委批準(zhǔn)之日易記,那一天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訪華到達(dá)北京。
1984年,我在《北方文學(xué)》發(fā)表了一組詩,名為《海濱抒情》,嚴(yán)老師讀后立即寫了一篇評(píng)論文章,刊登在遼寧的一家報(bào)紙上。沒想到,這篇評(píng)論在我所工作的興城引起強(qiáng)烈反響,縣委書記將此文批轉(zhuǎn)給主管領(lǐng)導(dǎo)和部門,主管文化的副縣長苗會(huì)田連夜給我寫了一封充滿感情的千言長信,邀我參與為宣傳興城——第二個(gè)北戴河造勢。這之后,名人紛至沓來,郎平任隊(duì)長的中國女排來興城集訓(xùn),喬羽、王酩、凱傳、曉光等為興城而歌,艾青、楊沫、峻青、王扶林等為興城鼓與呼,范曾、王遐舉、魏哲等為興城揮毫潑墨……著名評(píng)論家黃益庸先生在他主編的《北方文學(xué)》上,轉(zhuǎn)載了嚴(yán)老師的這篇評(píng)論,而我則把此文作為贊頌興城第一部詩集的序言。
畢業(yè)后,我每次去北京都要去看看嚴(yán)老師。他請我吃飯,大都選在北大對(duì)面的海淀飯莊。邊吃邊聊,不知喚起多少對(duì)艱難歲月的回憶,其中有歡樂,亦有悲傷,提起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我們禁不住黯然神傷。
那年盛夏時(shí)節(jié),嚴(yán)老師從美國哈佛大學(xué)作學(xué)術(shù)講演歸來,專程來興城看我。那時(shí)我的三個(gè)女兒還小,他給孩子們買了玩具,當(dāng)提起孩子的名字時(shí),嚴(yán)老師還記得,他一本正經(jīng)道,我寫給你的信說過,吳為、吳非,名字起得很有一點(diǎn)道家的味道。在興城,我倆無話不談,談得最多的還是在京郊鄉(xiāng)下那段日子,因我有胃病,可謂同病相憐,我感謝他給我買蘇打餅干,給我郵寄胃藥猴頭菌片,他說記不得了,只輕描淡寫地輕輕帶過,而提起興城卻興奮不已。談明代古城保存如此完好,令他流連忘返;談乾隆皇帝,詩多好的少;談努爾哈赤攻打?qū)庍h(yuǎn)(興城)唯一的一次敗北;談降將祖大壽成了英雄。回京后,他寫了一篇散文《祖氏牌坊》,刊發(fā)在《人民日報(bào)》上。同年秋天,我攜妻帶女去北大看望嚴(yán)老師,在他家里做客,他親自下廚,弄了十五六個(gè)菜。最讓我們夫妻倆難為情的是,兩個(gè)女兒從海邊來,對(duì)海鮮并不格外喜歡,可在嚴(yán)老師家里,拌海蜇皮卻被一掃而光,嚴(yán)老師看孩子們喜歡吃,又去做了一盤。這個(gè)菜是否做出了上海菜的風(fēng)味,現(xiàn)在也不得而知。最讓女兒驚嘆的是,嚴(yán)老師的家里,滿屋子滿桌子滿地都是書,沒有回身之地。嚴(yán)老師的夫人盧曉蓉稱先生是“書蟲”,或許再貼切不過了。
【責(zé)任編輯】 寧珍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