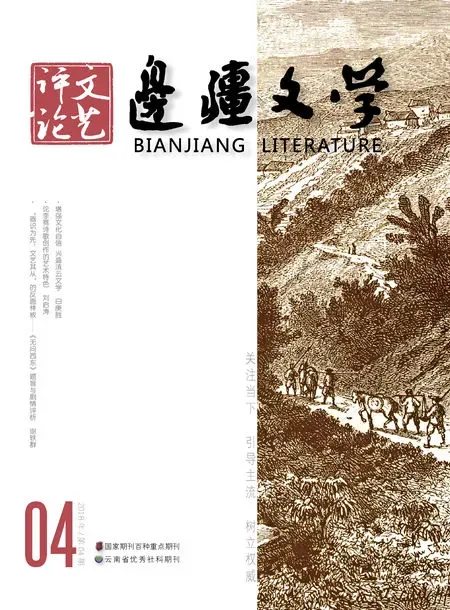扎根大地直抵人心的悲憫疼痛和大愛
——呂翼小說創作談
海 訊
不跟風浮躁,不媚俗淺薄,在艱難時世中開辟自己創作的道路。品讀呂翼的小說,不由為他的風骨操守和扎根大地直抵人心的悲憫、疼痛和大愛所感動。回望云南省東北部云嶺高原與四川盆地的接合部典型的山地構造地形,山高谷深,海拔高差大,有獨特的自然景觀、迷人風光民族特色的那片歷史星空,彝族作家呂翼在社會演進與自己創作中,體現出思想者和創作者的抗爭;在艱辛創作的砥礪奮進中,彰顯出精神的力量和思想高度;在理想與現實的巨大落差中,依然將自己的創作扎根大地,保持傲岸挺拔的文人本色,巍然成就了一個彝族作家的文字直抵人心的悲憫、疼痛和大愛。他無疑是滇東北這塊福地上一個具有自己深厚底蘊和底色的彝族漢語文學創作拓荒者。歷史的車輪,總是在永不停息的奮進中書寫進步和發展的軌跡。好的作品也總是力求表現底層廣大人民群眾的疾苦,替道德、良知和正義呼吁、吶喊和疼痛。回望呂翼小說創作的軌跡,品讀其小說,提純近乎絕版的精神內質,為的是讓過往不再煙云,讓曾經的思想深度和道德高度,與我們血脈相承,重新端正他那文學作品中高貴的精神內質,以便惠澤更廣的大地,更多的人們。
任何歷史的發展總是在一定規律支配下進行,亂事出英雄,亂世出思想家,早已經得時空驗證。我們腳下這片古老的大地不會忘記,當今蒸蒸日上,日新月異的這個繁榮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開拓創新者匯聚,呈現一派“空前趕超”的人文風景,尤其在文學創作領域一個個性格各異卻一樣純潔真誠的鮮明人物,儼然若普羅米修斯的不朽神話,開創一代新風,精神光耀后人。這其中,從纖弱氣息、媚態叢生中“沖出個仿佛敦厚黑臉氣勢奪人”的呂翼就是一位。
是時代塑造了這位不善言辭,初接觸還感覺有些木訥卻內涵十分豐富的新一代彝族小說家,還是呂翼以扎根大地直抵人心的悲憫與疼痛之風救治了羸弱的社會體質?我想答案已不重要。前人之鑒后人之師,品讀呂翼和我們這個時代,意義更在于準確地觀照我們這個時代,站在當代另一個社會轉型的關口,如何能于泥古與西化、保守與激進、淡泊與熱烈、疼痛與歡樂、奮進與墮落間揮灑自如,開拓真正屬于自己的路,這才是根本和關鍵。
與別的彝族作家詩人不同的是,呂翼是專以小說創作而擅大名,以蒼勁雄渾,悲憫疼痛筆墨成就一代“呂風”。呂翼筆墨精髓無疑得益于博大精深的彝族歷史文化和漢族傳統文化兩種或多種文化的浸染,他熱愛生命、熱愛生活,學習生命、學習生活,終從生命和生活中破飛而出,帶著高山大地泥土的芬芳縱連古今,橫通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學藝術精髓,卓然成為新中國成立后云嶺大地上繼第一代著名彝族小說家李喬后,可稱為當今云南彝族小說第一人的作家。而能成為第二代彝族小說家的典型代表人物,更在于呂翼的革命性和開創性。他走出彝族作家大多長于詩,短于小說的圈子,以后又越過彝族傳統文化和敘述方式,直窺漢語的內核,從漢文化中得沉雄圓勁力能扛鼎之筆,以其蒼潤遒勁的風神貫通文字,于彝、漢之外別開雄風,另張一軍,開創了新一代彝族漢語小說審美新紀元。分解看,在其小說創作上,呂翼得巧奪天工之勢,鐵筆雄健,字句硬入,創造性地將小說創作藝術中人物塑造與細節描寫效果產生的“現場感”,上升到悲憫、疼痛與大愛美的審美新境界,使小說創作顯示出不盡的藝術生命力,高揚起當代彝族漢語小說創作審美新風尚;他的小說創作不走“逢場”“快餐”人云亦云的一路,而取法蒼茫古勁的厚實敘寫,線條凝練遒勁,氣度恢宏古樸,貌拙氣酣,極富泥土氣息,民族特色,可以說他是當今中國彝族漢語小說創作為數不多的新一代代表性人物;他的散文亦以“苦鐵畫氣不畫形”“不似之似聊象形”為旨,以細膩洗練入文,“深入生活和民族內在作抒寫”,極力發揮小說“敘”的張力,以“塑造”為法,“惟任天機外行”,以達“心神默與造化能”的境界,“宣郁勃開心胸”以泄胸中悲憫疼痛和大愛之氣。
在社會轉型、良莠并存的社會環境里,內心的焦慮、惶恐、悲憫和疼痛是身在其中人的共同,知識分子的感知和憂患只會更深刻,于文化沖突與時代轉折地帶,難有真正的平和。很多知識分子將對社會變革的雄志與苛論、躊躇與愁苦賦予文學藝術上的突破,試圖在流動易變的表象尋找一種硬朗且永恒的精神氣質。對于呂翼,他尋找的姿態是回望,懷揣一顆赤子悲憫之心與疼痛相抗,一面直面現實投入時代潮流,一面又堅守書齋,在思想疼痛處尋找超越功利和世俗的精神。這表現在他的藝術風格竭力偏離妍美一路,流露出鮮明的不媚世俗的悲憫、疼痛和倔強,但又不以丑怪眩世,而是把悲憫之氣和疼痛的赤子之心融入小說創作,在世相流變中注入樸陋古拙蒼勁的意韻,構建新的審美——它寓氣魄與內力于圓渾單純,老辣雄健又不失俊逸的風格,恰如京劇名凈裘盛戎的聲腔藝術,黃鐘大呂中仍有一種雅趣。這一審美蘊藉一種剛正、悲憫和疼痛的風格,一掃當今某些文人畫纖弱荒寂的情調,洋溢著蓬勃生機和宏大氣勢。這一審美所折射出的藝術精神,正是身處劇烈碰撞和變革社會的士大夫知識分子的內心呼喚,良知覺醒和正義操守,然而,他呼喚的不是西方的科學技術與人文文化,而是曾經輝煌過的我們古老傳統與現代氣息相融的雄風。借筆墨鍵盤寄托凌云志,呂翼小說創作藝術在傳統中推陳出新,是當今這個時代相當一批知識分子的心理需求,是當今中國不少弱勢民族受到強勢文化和多元文化沖擊擠壓“山雨欲來風滿樓”震蕩下的精神堅守和自我突破。
當代學者許紀霖說:“一個知識分子的立場,說到底也是個性與愛好的立場,就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以知識良知為基點的獨立立場。”個性對于文人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一個性格平庸、性情虛偽的人很難有太大思想和創見。呂翼寫小說多年,已經出版有長篇小說《土脈》《寒門》《疼痛的龍頭山》,小說集《割不斷的苦藤》《靈魂游蕩的村莊》《別驚飛了鳥》《風過楊樹村》,《叫喊的村莊》《是否愛》,散文集《雨滴烏蒙》等。其小說有不少篇目在《中國作家》《民族文學》《北京文學》《大家》《邊疆文學》等多家全國有影響的刊物發表,并被《小說月報》《作品與爭鳴》等刊物選載。曾獲《邊疆文學》獎、云南省政府文學創作獎、云南日報文學獎、云南省優秀文學期刊編輯獎、云南省德藝雙馨青年作家獎等多種獎項。“筆底傳至情”的呂翼小說大多具有悲憫情懷和疼痛氣息,但不復古,不跟風,因而才有了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富有生命活力和溫度的文字里始終有鮮活獨特的自己。他強調藝術要創新,要表現自己真情實感,形成自我風格。他也寫散文和其他體裁的文字,但最愛寫的還是小說,因為“小說是可以任意放置另一個世界和自己靈魂”最寬松的一種形式。有關呂翼小說的經典篇什較多,最見風骨和影響的是長篇《土脈》《寒門》《疼痛的龍頭山》《云在天那邊》,中篇小說《冤家的鞋子》及小說集《割不斷的苦藤》《別驚飛了鳥》《風過楊樹村》《是否愛》等。評論家艾自由說:“文學作品需要的是真愛、大愛,是對底層有著關懷的那種愛。如果一個作品里表達的是對金錢、對權貴的愛,那種愛也是低級的、無聊的,被大眾所唾棄的。文學作品需要的是在黑暗里呼喚光明,在嚴冬里尋找火爐,在人心悖離、暗箭穿心的歲月里尋找握手、擁抱和以心換心。作品有了真愛,有了善意,才會溫暖人心,代代相傳。 ”呂翼的長篇小說“《土脈》中的土地情結有著濃厚而又特殊的感情,作者較為真實而準確地寫出了云貴高原大山深處的彝族農家的生活,刻畫了他們對土地刻骨銘心的熱愛和依戀,具體、形象地表現了圍繞土地而產生的期盼、歡喜、失落、困苦、傷悲、希望等情感的起伏變化。同時,呂翼也把他的土地情結、家園意識浸潤在字里行間,樸素而自然,作品中散發出他對本民族歷史和文化傳統的自豪感、使命感和認同感,其擁有的民族意識和責任感增強,在他身上有一種為民族發展滯后的焦灼感,他用文學藝術向人們傳達出他內心對農村發展和農民心理變化的關注和思考。”——李卓燕。“呂翼長篇小說《寒門》伴我大半年了,一讀、二品、三回味,是我想寫讀評的前奏。掩卷后,《寒門》里那些莘莘學子的影子,一直縈繞腦際,揮之不去。”——王明生。“呂翼寫出了面對這個背景與社會問題下一代人的精神狀態,一代人的命運遭際,這足以讓人起敬,他是一個有勇氣,有良知的作家。我了解呂翼,他這些年在很多崗位上經過了歷練,寫了大量的作品,變得更加成熟了,我相信,一個作家的成熟便是一部成功作品的開始。顯然,呂翼具備了這樣的實力與品質。”——朱子青。“呂翼在《別驚飛了鳥》《雪落楓橋》《仙鶴湖紀事》等小說中,展示自然生存條件惡劣,并呈現出貧瘠的土地、惡劣的氣候以及莊稼、苦藤等苦難意象,寄予著作家對苦難的抗爭和吶喊。且構建了一個屬于自己的文學村莊——封閉、落后、偏遠、貧窮的楊樹村,新聞報刊送到那里早已成為舊聞,農民為避免饑餓和解決生計努力珍愛土地,但生活舊貌難改。呂翼筆下的農民對土地有一種偏執的熱愛,而土地是苦難的載體。老龍頭對土地的熱愛近乎癡迷,他認為擁有田地就擁有了人生的全部,歷盡千辛將玉米收回,結果因包谷太多壓斷了支架垮得滿地,龍壩也被砸斷了腰;烤煙債才還清,新修的房子卻著火,破碎的家庭一次次瀕臨崩潰。《土脈》中人們看著干裂的土地,焉黃而枯焦的莊稼,毒辣的熱頭,眉頭緊鎖,人們甚至為了土地而發生流血事件。一到冬季,滇東北大地裸露在黃土之中,萬木凋零,冷風干烈刺骨,沒有生機,處處透著荒涼。自然環境的惡劣增加了農民的憂慮,給他們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的痛苦。作者在《割不斷的苦藤》中營造了一個‘苦’的氛圍,苦寨、苦水河、苦竹、苦菜、苦藤,苦寨出了一個縣長叫辛苦。苦寨的老輩人說苦寨人要過上好日子,苦寨的苦藤要斷根。苦寨人做夢都想有一天能將這里的苦藤全部割掉,可是辛苦到死也沒有將那厚不見底的苦藤連根鏟除。呂翼在深深的責任感中,以魯迅式的揭示貧瘠引起人們對滇東北生活進行改革的思考來表達著自己的思考。”——李丹。“呂翼是新時期昭通作家群中民間立場卓有建樹的作家之一。他始終在寫底層農民,以農民的立場,以現實主義的方式,寫農民生活的艱難,物質與精神的匱乏,反映民間生活的真實面貌和底層人民的心靈世界及他們對命運的掙扎。其創作中的鄉村小人物,在生活中都有原型,都是作家熟悉的人或事,他們卑微但有溫情,愚昧但很樸素,自私卻很善良,他們都在艱難的條件中勇敢的活著:馮敬谷,春草,配種人王矮三,羅二嫂,唐禿頭,陳巫婆等等。呂翼熟知鄉村現實,以局內人的身份,含淚敘述著小人物們為生活所迫而苦苦掙扎的故事。通過作家對小人物生存狀態的苦難敘事,我們可以直接從生活的表象去感受苦難。呂翼的苦難敘事中,真實反映出鄉村人的粗鄙和劣根性,雖然這種哭笑不得的同情中飽含著諷刺,但更多的是作家對他們的理解和寬恕。”——李丹。“《疼痛的龍頭山》,有著非常典型的現實意義,也有著可以拓展挖掘的空間。它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情感飽滿、大氣。這也是呂翼作品的風格與特點,可以感受到,作者內心積蓄著太多激情,渴望傾訴。”——湘女。“在呂翼的筆下,龍頭山的疼痛,是相愛的疼痛,是思念的疼痛,是離別、尋找、內疚和刮骨療傷的疼痛,是愛與恨碰撞之后的疼痛。這是
一部成長的童話,主人公逐漸成長;這是一部團結的童話,災區的民族互相包容、互相促進;這是一部精心培育愛與擔當的文學作品,將烏蒙山區的高原品質抒寫得淋漓盡致,體現了作者多年來一如既往不拘小節、包容坦蕩的文人情懷。”——艾自由。“《疼痛的龍頭山》講述了人們心里一場撕心裂肺的疼痛,但是這場疼痛的背后卻是無限深情的愛。鄰居的友愛,朋友的關愛,親人的疼愛,師生的互愛,就連小偷和強盜身上都彌漫著善意的愛,就連一條狗,一只雞,一群羊都充滿了人性化的愛。可以說這本書里充滿了人間所有的愛,讀來讓人感到溫暖,讓人變得寬容,心里對一切懷著慈悲。”——柴玉米。“《村莊的喊叫》揭露了小人物悲慘的命運,社會的不公,底層勞動人民艱辛的生活。看似作家平靜書寫,實則文字中到處透露出血與淚的哭泣。”——劉仁普 。呂翼的小說,無論長篇、中篇、還是短篇,始終以最拿手的絕活記敘底層民眾的疼痛、苦難和掙扎,并非無病呻吟,而是以悲憫、寬容、理解和同情的筆觸抒寫民眾的疼痛,這種疼痛便是作家自身的疼痛,也非他一個人的疼痛。呂翼小說藝術中的悲憫疼痛和大愛之氣,更來自他的靈魂深處,他認為“人比山川高貴,人比動物復雜,人比大海和天空廣闊,就是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內心,每個人都有與別人不一樣的個性,每個人都有著在不斷成長和放大的視界。小說就是要在表現人物的豐富和復雜上下功夫,怎么寫是作家的事,寫什么是讀者更關心的事。”正是作家將其人生和藝術追求熔鑄在寫作之外的“呂式”藝術特有的風神上,才巍然成就一粒粒扎根大地直抵人心的悲憫、疼痛與大愛,讓一篇篇、一部部極具溫度的文字慰藉著廣大讀者的心靈,這正是呂翼小說卓然而出,風生水起,并不寂寥的地方。
我以為當今中國這個魚龍混雜的文壇,一個作家,尤其是少數民族作家能夠以此作為和擔當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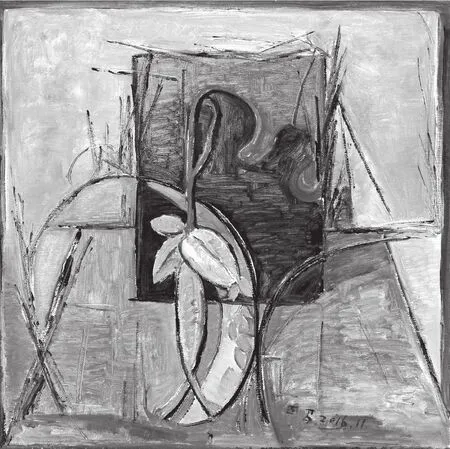
張紅兵 布面油畫 作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