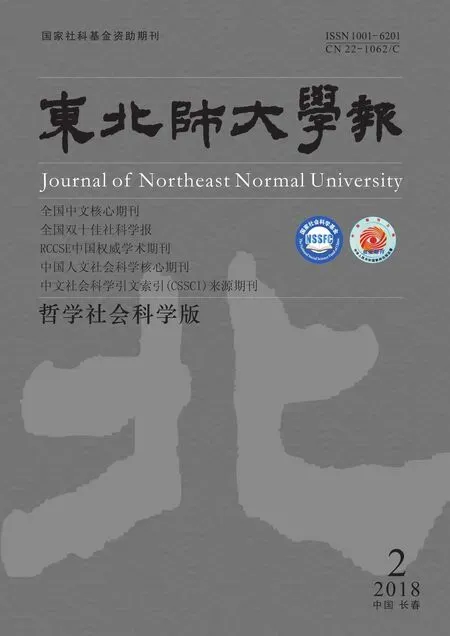他者鏡像中的自我困境
——《他人的臉》之拉康精神分析學解讀
任 麗
(1.吉林大學 文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2.長春理工大學 外國語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2)
安部公房被譽為20世紀最受歡迎的日本作家和世界級文學大師。從《墻壁》對日本戰敗后徒勞反抗的悲劇性象征,到《砂女》時期審視現代性條件下人們的生活狀態和精神面貌,安部公房的文學創作里,最顯著的特點便是他敏銳的洞察力、豐富的想象力和由此引發的批判精神。從題材來看,無論是早期創作中荒誕變形的“非理性”景象,還是現代化沖擊下被充滿敵意的社會所包圍的異化和孤獨,對自我的思考一直是安部文學作品中從未間斷的主旋律。
自我意識是20世紀哲學思潮的一個極為重要的主題,它體現在現象學、存在主義等哲學流派的反思中。在與他者的關系中如何確立“自我”,安部公房的中后期小說中對主體的思索可以說是對這一哲學問題的有力回應。在《他人的臉》中作者采用回溯的手法,以三本手記的形式刻畫了自我與他者的沖突,呈現了一個分裂、矛盾的主體形象。以往的評論家大多以戰爭記憶、人種為視角剖析了在充滿矛盾和扭曲的世界里主人公異樣的孤獨感和恐懼感,而當我們探究作品背后作者的創作脈絡和創作動機時,這種解讀方式無疑局限了我們對安部文學中有關自我的思考。本文基于《他人的臉》并依據拉康的鏡像階段及相關主體理論,從身份危機中的自我、具有二重身份的分裂自我、走向毀滅的自我三個方面,分析日本20世紀60年代現代化進程下的自我與他者的關系以及自我被異化時的主體意識,并追索安部公房創作思路的哲學理據。
一、身份危機中的自我
人類對“自我”的探尋可以追溯至古希臘,蘇格拉底指出哲學應當從研究自然轉向研究自我,他提出的“心靈的轉向”可以說在哲學意義上發現了人類理性的力量和價值。到了文藝復興時期,笛卡爾的我思哲學確立了人的主體地位,他把自我與客觀的外部世界相分離,并使得理性成為主體身份的重要保障,至此古希臘以來的本體論哲學模式開始轉向為主體的認識論哲學模式。然而以“我思”為基礎建構的主體,其一切體驗從自我而出又折返于我,因此這一思想又具有濃厚的“唯我論”特征。進入18世紀,啟蒙思想家把蘇格拉底視為先驅和戰友,要求人們以理性的方式追求自由和平等,并以理性判斷和思維作為衡量自我存在的標準。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世界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工業文明的發展導致人性被扭曲,人被異化成了物的奴隸。在孤獨和絕望中人們對一切傳統的理性價值產生了懷疑,非理性主義思潮在此時應運而生,柏格森宣揚的“直覺主義”、尼采的“權力意志”論等都是其具體表現。作為現代哲學的重要表征,非理性主義認為理性和科學不適用于道德范圍,強調僅憑非理性的直覺就能認識外部世界,并要求把人的情感、欲望、本能當作人乃至世界的本質。從總體上說,非理性主義是人類文化危機、精神危機和社會危機的最深刻、最激進的哲學體現。而當人們回到自我的內心世界去尋找生命的本質時,最終會導致個人中心主義和主觀唯心主義。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人們看到,社會的表面穩定、安全和物質進步,同一切人間事物一樣,都是建立在空無的基礎之上的。以至于歐洲人像面對一個陌生人一樣面對自己。”[1]33至此,在非理性主義思潮下主體已陷入了深深的自我迷失之中。
安部公房關注現代社會和現代人的生存處境。面對戰后影響及現代性條件下的自我迷失,作為一名深受存在主義哲學影響的戰后派作家,安部公房中后期的文本世界里,幾乎都探討過來自他人的“威脅”:《砂女》(1962)中仁木順平面對“妻子”的無形壓力而出走,《箱男》(1973)中為躲避他人視線而變身為箱男,《密會》(1977)中被他人監視的困擾,《櫻花號方舟》(1984)中為了躲避他者而逃離故鄉……可以說安部公房筆下的主人公們,在主體的“我”對世界的知覺關系中,總感到有一個先行存在的凝視者在注視著“我”,正是這一來自他者的世俗壓力常常使主人公們不堪重負最終繳械投降。正如梅洛-龐蒂所言:“在這些動作后面的某處,或毋寧在它們面前的某處,或者更是在其周圍,不知從什么樣的空間雙重背景開始,另一個私人世界透過我的世界之薄紗而隱約可見。一時間,我因它而活著,我不再是這項向我提出的質問的答復者……至少,我的私人世界不再僅是我的世界;此時,我的世界是一個他者所使用的工具,是被引入到我的生活中的一般生活的一個維度。”[2]20-21
20世紀60年代,戰敗后的日本處于一個特殊時期:經濟高速增長,然而社會、文化以及人們的思想狀態陷入了深重的危機之中。安部公房敏銳地察覺到這一時期人與人之間產生了難以逾越的鴻溝。與前現代的那種封閉、自足的社會不同,工業化進程下的日本社會不再使人有一種歸屬意識,人被拋在了這一特定情境中時刻感受到外在的強力和威脅性。置身于這樣的社會鏈條中,就需要一種力量去消解自我意識以適應外部環境,當這一欲望無法得到滿足時,人們就會呈現一種焦慮、恐懼的邊緣人格特征。
安部公房在其長篇小說《他人的臉》中刻畫了陷入身份危機的現代主體形象。小說是以第一人稱的視角展開敘述,然而題目沒有使用“我”而是“他人”,實際目的是為了拉開與敘述者的距離,以一種旁觀者的姿態來審視這一現代性條件下的“自我”。小說主人公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臉部受損,起初會“直面并習慣于整個事態”“按照自己的方式進行某些努力”[3]9,可當女助手拿起克利的題為《偽裝的臉》的鋼筆素描畫給“我”看時,“那幅畫儼然化作了映入她視線中的我自己的臉……”[3]9,在遭遇他者的視線時“我的心也被撕了個粉碎。我的內臟從那撕開的裂縫中如同腐爛的雞蛋一般往外流淌著。”[3]9在“我”看來,臉部喪失是一種無法掩飾、無法擺脫的心里苦痛,而妻子的冷漠與拒絕,電車里五歲男童的驚詫表情更深深刺痛了“我”。這一來自于他者的凝視、評判,使“我”不停地追問“我到底是誰”“我來自哪里”。為了擺脫這一他者視線中的自我困境,“我”開始尋找某雜志的撰稿人K先生,期待得到一種外在的指引。正如K先生所言,“即使在幼兒心理學等等當中,這也成了一個定論,即人這種東西只能借助他人的眼睛才能確認自己。”[3]24這一富有哲理的言論可以說與拉康的鏡像理論形成了相互映照的關系。拉康指出人類從出生就開始尋求自我之路,面對鏡中的成像進行想象性認同,產生了關于自我的概念,并維持了在自我與成像之間異化的關系。源于在嬰兒期對自我的錯誤認識,同時為了獲得他人和周圍環境的認同,建立自我身份,人類不得不自我異化,以試圖探尋迷失的主體。因此,自我必須得到他者的承認,即我們自身必須借由他者的目光來確認自身的存在。這樣一來,我們既要依賴于確認我們自身存在的他者,又要對這一外在的他者展開充滿仇恨的抗爭。不僅僅是面部喪失的“我”,安部似乎也暗示我們人人從生命之初就處于這樣的二律背反的境地,而面部喪失的特殊事例,會愈發使“我”尋求他者的認同,也愈加彰顯這一人生二律背反之境地。
通過文本細讀的策略我們發現,《他人的臉》中主人公的異化焦慮,是一種社會異化焦慮的體驗。拉康認為,主體的第二次分裂,是指進入語言體系時就意味著主體性的確立。在主體性形成的實在、想象和象征的三個秩序中,象征秩序起著決定作用。“要完全作為人類主體而存在,我們就得‘受制’于這個象征秩序——亦即語言或辭說的秩序;雖然我們無法逃離它,但是它卻作為一個結構逃離了我們。盡管作為個人主體,我們永遠都無法充分地掌握這一構成我們世界總和的社會的或象征的總體性,然而對于身為主體的我們,這種總體性卻具有一種結構性的力量。”[4]62在拉康眼里,人一旦進入象征秩序,就要求主體對社會能指體系的服從,而這一象征秩序也有其相應的能指鏈,即話語體系。因此,人類進入社會大他者的話語體系中,也就意味著無一例外地進入了自身的牢籠。喪失臉部的“我”永遠被限定在與自己異化的境地,是被一種外在的、無法為人類自身掌控的力量所決定。即拉康所說的“大他者的話語體系”。“我”渴求在充滿他者的世界里找到自我的鏡像,建立一個自我的身份。面對以妻子為代表的他者,在回憶的手記中到處呈現出自我的焦慮和苦痛,“漫不經心的視線里都藏匿著涂滿毒素的針。那毒素帶有可怕的腐蝕性。”[3]33“……救救我!……別再用那種眼神來看我!如果老是被人用那種眼神瞅著的話,不是真的會變成怪物嗎?”[3]58正是對這一異化的過分擔憂,使“我”行為異常乃至精神焦慮,“我”害怕被他者“腐蝕”,更擔心自己會成為現代化進程中一個只有皮相而無心智的軀體,正如拉康眼中的自我與他者,在本質上是一場有關欲望與承認的博弈,我們都深陷于一個相互的、不可劃約的異化辯證法中,即每個人都存在于他者的存在。
在資本主義的物化世界里,“我”遭遇了主體進入象征秩序的異化,而“我”的社會異化焦慮實際上就是對象征秩序的排斥。主人公置身于充滿他者的街道“就像是在獄中”,面前的墻壁和鐵窗都變成了“研磨一新的鏡子,映照出自己,無論在哪個瞬間里都不能逃離自己,這的確是一種被囚禁的痛苦。”[3]63“我”已被嚴實地囚禁于“自己”這一口袋中,正拼命地掙扎著,而掙扎的最終結果是“我”徹底的異化,帶上假面把自己變成陌生的他者。《他人的臉》中安部公房打破了寫實主義的傳統,對其筆下人物的容貌、表情、性格及過去經歷,不肯多費筆墨,而是致力于探尋人物的各種處境,靠其豐富的想象力塑造出實驗性的“自我”。小說文本世界中,主人公“我”相關資訊的缺失并不會降低人物的生動性,那個失去面部的“我”作為活生生的人,其生動性完全超乎讀者想象,以至于我們完全進入主人公“被囚禁的痛苦”,并將之與現實混淆在一起。如果作家進行的只是局限于對一個人物的描寫和刻畫,就意味著他不是一位劃時代、開拓性的小說家。小說中對他者視線的逃避、對迷失自我的探尋、“囚禁”自我又懼怕被疏離等創新性文學表現手法,都意味著安部在他的小說世界中不斷地探尋著超乎個體的抽象的主體形象,這與當時占主流地位的精神分析哲學不謀而合。
二、具有二重身的分裂自我
作家安部公房出生于日本東京,在中國沈陽(當時稱作“奉天”)長大,其故鄉又是日本的北海道,源于對身份有著敏感的認識,同時又作為一位負有責任感的作家,安部公房在其文學作品中大量采用了二重身的文學模式,訴說現代人身份迷失的焦慮與苦痛。《墻壁》(1951)中的卡爾瑪氏和名片卡爾瑪氏、打字員Y子和櫥窗模型Y子、鄉村父親和都市主義的于爾班教授這三組二重身形象,均以名字為“鏡面”折射出分身人物的相異性,而《他人的臉》則以假面為棱鏡,呈現的是“我”與“假面”源于同一軀體卻具有不同價值判斷的“二重身”。這一具有二重身的主人公形象,圍繞自我和妻子關系折射出現代城市中喪失身份的恐懼。當“我”被他人的視線步步緊逼,感受到了自我被“囚禁的痛苦”,但隨后就“心急化作了焦躁,焦躁進而發展成陰暗的憤怒”[3]63,使“我”飽受精神折磨的是“我”的內心始終感受到兩股對峙的力量。“我乞求著接近你,同時又乞求著遠離你。我想了解你,同時又對了解你大加抵觸。我希望看見你,同時又對看見你感到屈辱,在這種進退維谷的狀態中,龜裂越來越深,最終深入到了內部”[3]86。20世紀60年代的日本,似乎每個人的心里都藏著一個自我認知缺失的黑暗角落,而文學的二重身大多情況下都是源于心里黑暗而衍生的另一個自我。正是主人公內心兩種斗爭的聲音造成了主體的“意識崩裂”,當假面制作完成時,帶上假面的“我”正式以二重身登場。
二重身源于德語“Doppelganger”,其原意為“兩人同行”,也指隱藏在人們心中的另一個自我,這一“二重身”往往是人們內心欲望的最真實的表現。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人有兩個自我,一個是和原來自己一樣的自我,另一個是和原來的自己不一樣的他人。18世紀末德國哲學家在此基礎上,開始了二重身文學理論的構建。杰·保羅于1796年首次使用與“自我”相對應的“非自我”,并在小說《塞賓卡斯》中運用了“二重身”的人物塑造方式。在文本分析中我們經常使用“二重身”“雙身”“變身”等,具體是指人物的內心中常常有另一個自我,它無時無刻不監視著原身的活動,并把自身的意志、想法強加于原身。當人物內心遭受外部的壓力而扭曲變形時,這“另一個自我”就出來試圖掌控原身。
就安部的小說創作而言,在《他人的臉》中以手記、書信等心理呈現方式的載體,對現代性條件下的自我身份危機采用二元對立的雙重人格和自我分裂模式進行探討。在拉康看來,“主體本質上是分裂的或割裂的實體:主體被他所服從的那些語言法則分裂開來,分裂到了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程度。”[5]63從存在的角度看,這一雙重自我呈現的是喪失面部的自我和帶有假面的“他者”的分裂。當假面制作完成,“我”對房東說“假面”是“我”弟弟時,這張假面作為現代社會中的匿名者成為一張通往他人世界的通行證。然而由于帶上假面導致“水蛭窩”愈發嚴重,“我”清楚這一行為將會導致毀滅性的結果,于是就徘徊在雙重身份之間,一邊享受著不顧忌視線的優越感,同時又深陷囚禁臉面的牢籠之中。帶上假面“從心靈的羈絆中解放出來”[3]72,變得“無限自由”的同時也變得“無限殘酷”,沒有恥辱的必要,更無須辯解,“假面”拋開了自我的道德約束而肆意妄為。這一極端的自我意識和感受,模糊了主人公的自我人格界限,此時的“假面”在象征世界中已然將原本的“我”消解為碎片而消失;回到出租屋,呈現素顏的“我”,則期待修復與妻子的關系,渴求他者的認同來證明自我的存在。這部小說的張力就體現在“我”在假面和素顏的表象下的兩種心理和行為之間的逡巡。這一來自于人物自身的主體性分裂,深深印證了20世紀60年代人們內心深處的非理性。在出租屋內,當“我”摘下假面在鏡中審視自己的臉時,正是對自我身份的凝視和探尋,“我”已被形塑為一個非此即彼的二重身份,這是對自我的固化,更是對現代性條件下自我真實存在的扼殺。
在安部公房的筆下,主人公從肉體到精神上都經歷了雙重人格的裂變,喪失面部的敘述自我在手記中追溯其過往的經驗自我時,二重身的“假面”已經呈現出一個獨立的姿態,這一自我二重身的對立和對話關系,在主體的意識和潛意識層面引發不同角度的價值判斷和指向。一種是事后對過往的回憶和反思,與素顏的“我”保持一致,而另一種則是凌駕于“我”之上的“他者”立場。“我”和被稱作“弟弟”的“假面”之間很難達成和諧統一,在與“假面”思想交鋒中的詢問與回答、贊同與反對的過程中,雙方意識的碰撞往往以二重身另一半的勝利而終結。從理論上講,二重身的“另外一個人”用人們的肉眼是無法捕捉到的。在《他人的臉》中只有在“我”審視鏡中的“自我”時,二重身的另一人才出現在“我”視線中,而日常生活中則是站在“我”身后,監視著“我”的一舉一動,并將其想法滲透到“我”的大腦思想中。當玩具店老板試探性地向“我”出售手槍時,雖然“我”的內心驚恐萬狀,而“假面把我的驚恐拋在一邊,向長著野兔嘴臉的店主點頭示意。”[3]117顯然“假面”在關鍵時刻已然凌駕于“我”之上,操縱著“我”的意志。
安部在文本中多次暗示處于同一身體的“自我”和“假面”具有一體性,是分裂自我的體現和互為“二重身”的關系。這二重身都試圖擺脫對方的束縛,卻又統一于我的身體之中,與自我與他者雖然相異卻又統一于社會中呈現一種暗合。在小說中,素顏的“我”代表著現代社會下被疏離的個體,而“假面”則象征著侵入“我”世界的他者。安部在文本中刻畫的棲息于主體內部的二重身,就是來往于內心世界的神圣與邪惡,描繪在自我和“他者”之間糾纏的苦痛和清醒。這一哥特式的二重身亦表明了人類在他者中找到了自我,自我就是他者。
三、走向毀滅的自我
如果說上述的分析和闡釋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二重身”的運用體現了主體與其自體之間的競爭,那么這一競爭也被建立在主體“我”與妻子之間的關系上。本韋努托與肯尼迪曾說過:“在對他者的認同和競爭之間存在著一種原始的沖突,正是這一沖突開啟了辯證統一的過程,從而把自我與更為復雜的社會情境聯系起來。”[6]58在拉康的體系中,“欲望”很好地詮釋了自我與他者的關系。拉康認為,“被壓制的他者是‘言說’的欲望對象。”[7]122這一欲望既包括對他者的渴望、被他者渴望,又包括對他者所渴望的東西的渴望。對于主體與他者來說,成為欲望的主體或愛的對象是遠遠不夠的,他們必須成為欲望的動因。同時拉康強調,人的欲望永遠是“大他者”的欲望。“大他者就是語言,亦即象征秩序;這個大他者永遠都不會與主體完全地同化;它是一種根本的相異性。”[4]61齊澤克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在人們交往中顯在的符號規則與隱形的不成文的規則,都由拉康意義中的大他者標示出來[8]89。顯性規則的重要性顯而易見,而隱形規則在自我與他者的關系中也尤為重要。
按照拉康的觀點,主體“我”只有在與他者的關系中才能確認其存在,那么在20世紀60年代安部筆下的他者是以妻子為代表的他者,更是一種“大他者”。起初“我”遭遇身份危機,應當向妻子敞開心靈,然而“我”卻囚禁于自我的世界中;當“我”試圖坦白假面計劃以求修復二者關系時,妻子也沒能對“我”做出積極回應,而是留下一封“訣別信”。上述行為顯然違反了社會交往中的隱形規則,雙方關系發生動搖,并陷入難以挽回的境地。《他人的臉》中,得不到他者的認同是造成自我困境的根本所在,然而渴望他者采取背離其自身的思維習慣、行為方式,則更是一件難以實現的任務。當“我”把三本手記交給妻子時,渴望得到一種作為“鄰人”的回應,而“妻子”的回信卻遠遠消解了“我”的主體性。“知道你的假面劇的人,并不只是那個玩悠悠的姑娘。就連我也從那最初的一瞬間起,即從你稱之為磁場傾斜并自鳴得意的那一瞬間起,就已經徹底識破了一切……我不想再折回到那種鏡子的沙漠中去。”[3]213-215當主體欲望的指向變成虛無,“我”體驗的正是對喪失自身的喪失,而“我”此刻也進入價值缺失狀態。正如張一兵指出的:“我們無家可歸,如果一個人想重拾自己的原在,他就會失去主體間的能指意義關系,如果他不把自己用無(象征符號)貼到大他者的空無上去,他反倒會作為完全無法在場的負存在從此世上消失。”[9]61
在存在主義哲學中,這一被現實追趕到的邊界狀況被稱作“墻壁”,雅斯貝斯把這一狀況命名為“界限狀況”。在面對界限狀況時,人們一般會采取兩種行為:一是沒察覺到界限狀況或者是故意回避,導致了我們喪失自身的存在;二是直接接受這一界限,承認自己的軟弱和無力,一旦精神陷入絕望中,也能很快在心理上超越。然而小說中的“我”不屬于上述情形的任何一種,由于長期遭受他者的冷漠和拒絕,“我”的心理早已不堪一擊,再加上收到妻子的“訣別信”,可以說遭遇了生存的危機。科熱夫曾說:“與使人處于消極的靜止狀態相反,欲望會使他打破平靜,激發他去行動。”[10]74在這場博弈與掙扎中,“我”最終展現出激進的姿態,拿起手槍、帶上假面挑戰這一社會秩序,即挑戰以妻子為代表的他人所象征的權威,這一行為無疑是擾亂性的、徹底瘋狂的。至此,“我”已徹底淪為他者之他者,這也正是薩特的“他人即地獄”的癥結所在。
一旦我們在精神世界的探索中被卷入了大他者的欲望,就要遵循拉康的指引“不在自己的欲望上讓步”,因著這一大他者的欲望而去探尋自身的欲望,以便擺脫大他者對我們的影響。齊澤克承襲了這一思想,并引用海德格爾理論指出了當人們抗爭社會秩序與習俗中的持續而緊迫的陷阱時,不得不采取暴力[8]90。在這場殊死搏斗中,自我與他者都受困于這場較量,自我的死亡也將是他者的死亡,“我”只有冒生命的危險去斗爭才能向他者證明自我是具有超越性的主體。這一激進行為會把人們從安穩的日常狀態中脫離出來,同時也會向大他者傳遞一個信號,即表達主體“我”自身的哀憐、警示和承認自身有罪,因此,“我”始終無法擺脫大他者的掌控。用布朗肖的話來說:“絕對的他者和自我直接統一了起來,自我和他者在彼此之中迷失了自己……但這里的‘我’不再是至尊的:至尊性處在那唯一絕對的他者身上。”[11]12420世紀60年代,安部沒能找到自我迷失的出路,其文本中主體自身的對立面是內在的,異質性似乎難以消除,“我”以二重身的決絕姿態對社會秩序進行顛覆抗爭并走向毀滅。而這一象征秩序內的抗爭,也暗示了現代性的資本主義條件下主體的本質就是異化。主人公由于自我身份恐懼而引發的邊緣人格特征,折射了現代人徘徊于新秩序和舊秩序之間的尷尬處境,安部也借此抨擊將他們異化和邊緣化的社會。
日本的戰后文學,一般不會對社會問題提供一個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而是會回到原點,以出發點和終點重合的方式來落下自己的大幕。對于安部公房來說,所謂原點,就是對自我存在進行賭注的主體嘗試,就算一個主體消亡了,在其消亡的同時也意味著新的開始。
安部在《他人的臉》中通過“二重身”的文學模式展現了人類內心深處的瘋癲與理性、和善與兇惡、勇敢與膽怯的二元對立,而這種對立統一關系又蘊含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即把一切事物的矛盾本質置于最突出的地位。這一矛盾既包含著其自身的對立,又包含對事物本身的否定,在這永無止境的轉化過程中,會呈現出某種新的東西,在此意義上,安部公房對“主體”的認知哲學得到了印證。其處女作《終道標》中“我就是我自己的王”,既是對自我生存決心的高度概括,又表明了自我始終無法到達自身的終點。在主體內部萌發的意識脫離了自身并變成支配“我”的一種力量,此時主宰“我”自身的,就不是最初的“我”。然而,只要“我”還持續做“我自己”的王,并在其內部生根、繁育,就會通過連續的自我否定,成為主宰自我的主體。安部公房就是用這一方式向我們宣告自我主宰的強烈決心和勇氣。總體來看,在小說中,安部公房始終將自己擺在與現實社會相平行的位置上。作為小說家,他并不是一個創造者而是一個發現者。安部沒有著力闡明和揭露現存的社會體系,而是要探尋歷史長期以來懸而未決的人與外部世界的可能性問題。殊不知這一存在的展現更是一種偉大的預見,而這一問題也必將恒久地與人類共存下去。正因其與現實世界所保持的距離,才展現了這個時代本來的樣子,小說中閃耀著的光輝的價值才更具普適性和深刻的哲學和社會意義。我們說安部公房作為作家和藝術家的偉大之處或許都是源于此吧。
[1] [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M].楊照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2] [法]莫里斯·梅洛—龐蒂.可見的與不可見的[M].羅國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3] [日]安部公房.他人的臉[M].楊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
[4] [英]肖恩·霍默.導讀拉康[M].李新雨,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4.
[5] [英]達瑞安·里德爾.拉康[M].李新雨,譯.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
[6] [美]Benvenuto,B.& Kennedy,R.TheWorksofJacquesLacan:AnIntroduction[M].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86.
[7] 張劍.西方文論關鍵詞——他者[J].外國文學,2011(1).
[8] 于琦.西方文論關鍵詞——行動[J].外國文學,2014(11).
[9] 張一兵.能指鏈:我在我不思之處[J].社會科學研究,2005(1).
[10] [英]愛德華·凱西,麥爾文·伍迪.拉康與黑格爾—欲望的辯證法[J].吳瓊,譯.外國文學,2002(1).
[11] [法]莫里斯·布朗肖.無限的談話[M].尉光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