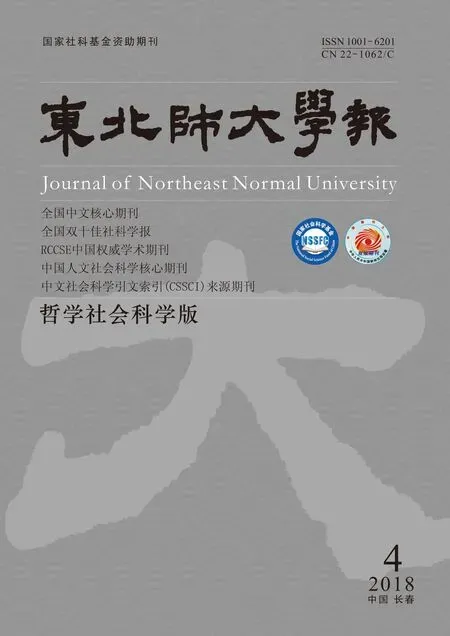嬰兒移情的研究綜述
劉秀麗,朱宇寧
(東北師范大學 心理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移情是體驗一種與他人一致的情感狀態的情感反應,它源于對他人情緒狀態的理解或領悟,在社會交往中起著重要的作用[1]257-267[2]131-149[3]126-136。移情加工過程通常會激發親社會行為、抑制攻擊性,為基于關懷的道德提供基礎[4]1-24。目前各個學科的研究者越來越多地關注到移情的重要作用。但是,移情能力在人類生命的早期是怎樣發生和發展的?受哪些因素影響?了解嬰兒期移情的發展特點以及發展機制,對于理解個體早期社會化有重要意義。本文結合現有的實證研究和理論研究,對移情這種關鍵社會能力在個體嬰兒期的發展進行總結闡述。
一、嬰兒移情概述
從進化的視角,移情是自然選擇的產物,是群居動物的一種親社會能力。這種能力由最初的本能進化而來,隨著人類發展不斷提高,是社會適應所必需的能力之一。在發展心理學領域,移情是個體由真實或想象中的他人情緒、情感狀態引起,并產生與之相一致的情緒情感體驗的能力,還是一種對他人的情緒情感的感受、理解以及產生替代性情緒情感的反應能力[5]557-562。
關于移情的成分結構,不同的研究者擁有不同的觀點。一部分學者認為,移情主要包括情感移情(affective empathy)和認知移情(cognitive empathy)[6]150-165。情感移情是個體能夠對他人的情緒情感進行直接反應的能力,嬰兒期個體通常表現為被他人的情緒情感所感染,嬰兒早期表現出移情悲傷,或相似的面部表情;認知移情是使個體能夠對他人的情緒情感進行知覺和理解的認知能力,嬰兒期個體通常表現為試圖理解他人的情緒情感,也即是假設嘗試(hypothesis testing)。Decety及其團隊成員則認為移情應包含更精細的三種成分:情緒共享(emotional sharing)、情感觀點采擇(affective perspective-taking)及移情關懷(empathic concern)[7]525-537[8]337-339。這三成分本質上分別對應情感移情、認知移情和親社會動機或行為。情感神經科學和發展科學領域的研究者同樣提出類似的觀點,認為移情主要包含三種分離的神經認知成分,也就是情緒成分、認知成分以及動機成分。其中情緒成分類似情感共鳴(affective resonance)或情緒蔓延(emotion contagion);認知成分是一種類似情感觀點采擇的概念結構;動機成分是一種符合關心他人福利的沖動欲望[9]493,是親社會行為的重要基礎之一。可見,目前研究者對于移情成分的界定表面上看起來雖稍有差異,但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為移情除了情感移情和認知移情成分,還應有親社會性成分(動機和行為)。
關于嬰兒移情發展的理論,其中最具有影響力和代表性的是霍夫曼(Hoffman)移情發展階段理論。該理論將移情發展與認知機制的發展相聯系,指出個體出現區分自我與他人的認知能力是產生移情的關鍵因素[10]。霍夫曼提出個體移情發展應包括四個階段,其中前三個階段是關于嬰兒期個體移情發展的描述。第一階段為自我中心移情階段(0—1歲):處于該階段的嬰兒由于不能清楚地區分自我和他人,當看到他人痛苦時,往往不能區分究竟是自己還是他人處于悲傷或痛苦之中,從而使嬰兒自身出現綜合的痛苦反應。但是,到了6個月時嬰兒通常不再自動地對他人的哭泣做出反應,而是首先表現出憂傷的表情,而后哭泣;而9—12個月的嬰兒看到其他嬰兒受傷并且哭泣,同樣也會哭泣,并爬向母親,向母親尋求安慰。可見,此時的嬰兒雖然能夠覺察到其他嬰兒發生了悲傷的事情,但仍不能區分誰在真正悲傷,于是自己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憂傷,這也叫移情悲傷。第二階段為準自我中心移情階段(1—2歲):此階段的嬰兒開始逐漸學會區分自己與他人的痛苦與悲傷,但是,年幼嬰兒仍不能清楚地區分自己與他人的內部狀態,仍然經常把自己的痛苦與他人的痛苦相混淆。所以,此時個體的助人行為仍是“自我中心”的,即嬰兒表面上試圖通過自己的行動以減輕他人的痛苦情緒,但這或許僅為了減輕嬰兒自己的痛苦。第三階段為認知移情階段(2—3歲開始):該階段的嬰兒已經具備了區別自己與他人的情感和觀點的能力。由于隨著年齡增長,嬰兒學會了理解與搜尋那些和他人痛苦或悲傷相關的信息,并依此形成有效的助人策略[10],所以此階段的嬰兒的助人行為相較于年幼嬰兒則更準確地反映了他們對他人的情感和需求的恰當理解。
嬰兒移情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自然觀察法、看護者報告法以及母親和陌生人假裝受傷的情境法(研究者在場進行視頻錄像)。目前關于嬰兒移情的實證研究主要依據Zahn-Waxler等人創設的研究方案:現場設置母親和陌生人成人悲傷(或痛苦)情境,用視頻記錄嬰兒面對自己的母親以及陌生人成人悲傷(或痛苦)情境的反應,然后由兩名研究者同時對視頻進行編碼[11]447-458。因許多研究者認為移情是一種旨在減輕他人痛苦的顯著的親社會行為(如幫助、分享以及安慰行為)近端動機[12]1-12,而對于嬰兒,測量其親社會行為也是可行的,所以研究者通常根據以下規則從情感移情、認知移情以及親社會行為三個維度指標對嬰兒的移情反應編碼:第一,情感移情的指標為情緒感染,是嬰兒對受傷者的情緒情感表達,涉及語言表達、面部表情、手勢以及身體姿勢,分4點評分,從1到4分別表示:沒有,輕微的(比如皺眉頭但時間比較短暫),中度的(相對長時間),大量的(持續的皺眉、悲傷表情或同情的語氣等);第二,認知移情的指標為假設嘗試,是指嬰兒使用語言或肢體動作等試圖探究受傷者,它反映了嬰兒試圖探測痛苦或嘗試從認知上去理解受傷者,也是4點評分,從1到4分別表示:沒有,簡單的非語言動作(嬰兒撫摸與受傷者相似的自己的身體部位或看著受傷者的臉)或者是簡單的語言問詢,非語言和語言的單一結合(簡單的結合),重復的或者相對復雜的嘗試;第三,親社會行為的指標為嬰兒試圖幫助或者安慰受傷者的行為,該指標也是4點評分:1表示沒有,2表示輕度的(比如一次輕拍或撫摸),3表示中度的(幫助或安慰行為持續3—5秒,或者重復的親社會語言),4表示大量的(幫助或安慰行為超過5秒)。
二、嬰兒移情的發展
當前,嬰兒移情的發展研究主要是以霍夫曼移情發展理論為基礎,分別對嬰兒情感移情、認知移情及親社會行為的發展特點進行考察。大量研究都發現,嬰兒期個體的移情能力存在著一定的年齡發展趨勢:隨年齡不斷增長,嬰兒的情感移情、認知移情和親社會行為能力均逐漸提高,但三成分各自呈現不同的發展軌跡。一方面是因為隨年齡增長,嬰兒的大腦發育逐漸成熟即移情的神經生理機能不斷完善的結果;另一方面則是由于嬰兒自身的社會互動經驗越來越豐富,從而促進嬰兒移情的發展。
(一)嬰兒情感移情的發展
嬰兒情感移情呈現出從自我中心的移情反應到他人中心的移情反應的階段發展特點。前者主要是指嬰兒的移情悲傷,指嬰兒在面對他人悲傷的情境中,自己也變得悲傷并沉浸其中,例如新生兒的反應性哭泣;后者則是指嬰兒在面對他人悲傷的情境中產生他人定向的反應,主要包括對悲傷他人的直接注視以及簡單的安慰。
1.嬰兒自我中心的移情反應
霍夫曼認為人類個體擁有天生感受他人痛苦情緒的移情能力,如移情悲傷。即便是新生兒在聽到他人哭泣時,自己也會跟著哭泣,這也叫新生兒的反應性哭泣。在有關新生兒聽到或觀察到其他嬰兒哭泣時的反應的相關研究[13]418-426[14]3-9[15]175-176[16]136-150中,研究者普遍發現,嬰兒會對同齡人的哭泣表現出反應性哭泣。這些研究直接證明了嬰兒期個體普遍存在的移情悲傷。除此之外,許多研究也發現,嬰兒早期出現的反應性哭泣的產生還具有一定的選擇性,如在聽到機器模擬產生的哭聲時,出生2到3天的新生兒并不會哭泣;也有學者發現,嬰兒能區分自己的哭聲與他人的哭聲,并出現不同的反應,如當給嬰兒呈現預先錄制的嬰兒自己哭聲的錄音時,他們不會產生反應性哭泣,即嬰兒沒有表現出移情悲傷[13]418-426。還有研究發現嬰兒對其他嬰兒哭聲的反應性哭泣也不是快速的自動反應,他們平均是在1.5至3分鐘之后才開始出現反應性哭泣[16]136-150[17]279-288。
綜合分析上述的研究結果可見,盡管嬰兒對他人悲傷同樣表現出了移情悲傷,但是并不能認為新生兒的反應性哭泣就是簡單的情緒蔓延,嬰兒極為有限的情緒調節能力可能也影響著嬰兒的移情悲傷。其實已有研究者指出,當他人悲傷比較強烈或持續時間比較長時,嬰兒由于無法調節由他人悲傷引起的移情悲傷而出現反應性哭泣[18]126-131。
2.嬰兒他人中心的移情反應
霍夫曼移情發展理論第一階段認為0—1歲的嬰兒分不清自我和他人,移情是自我中心的。但后來的許多研究發現,在第一年的中期以后,嬰兒面對他人悲傷時,已逐漸出現了他人中心的移情反應,而不再僅僅是反應性哭泣。如Hay等人發現,6個月大的嬰兒面對同伴的哭泣和煩惱時,其移情悲傷很少出現,嬰兒會以一種他人中心的方式進行移情反應,比如,對哭泣同伴進行直接地注意,或者對哭泣同伴的一次撫摸等[19]1071-1075。Liddle等人以8個月的嬰兒為研究對象發現,在嬰兒看到同齡同伴(有其母親在場)悲傷時,嬰兒首先注視對方,緊接著會表現出一些簡單的安慰行為,如用玩具輕觸或撫摸一次該同伴,然后注視悲傷同伴的母親,最后才看向自己的母親,而且很少出現自我悲傷[20]446-458。可見,霍夫曼移情發展理論低估了嬰兒他人中心的移情反應能力的發展,嬰兒早在6個月時就開始發展出了此能力。
(二)嬰兒認知移情的發展
隨著嬰兒月齡的增長,嬰兒大腦得到一定程度的發育,嬰兒與成人互動經驗也增加了,嬰兒逐漸表現出認知移情。2011年Roth-Hanania等人以8至16個月嬰兒為研究對象進行的一項聚合交叉研究發現,月齡為8至10個月時嬰兒表現出中度的情感移情(即嬰兒出現相應的悲傷的面部表情)的同時,還能夠一定程度地表現出認知移情(嬰兒試圖探索以理解他人的痛苦)。在此研究中他們還發現,不同移情成分的發展趨勢各不一致:隨月齡增長,雖然嬰兒情感移情能力不斷發展,但是月齡差異并不顯著,即情感移情能力的發展較為穩定;而認知移情(假設嘗試)的發展則存在顯著的月齡差異[11]447-458。也就是說,嬰兒對他人的情感移情在第一年出現并在第一年基本達到成熟;而嬰兒的認知移情雖然也是開始于第一年,但在第二年中仍然不斷發展。
(三)嬰兒親社會行為的發展
根據Roth-Hanania等人的研究結果,嬰兒的親社會行為也是從第一年開始,在第二年逐步增長。雖然親社會行為與認知移情呈現出相似的發展軌跡,但與認知移情相比,親社會行為不但發生頻率較低,而且出現的時間也稍晚,親社會行為在第二年才會增長迅速[11]447-458。之所以親社會行為的發展會呈現出與情感移情以及認知移情不同的軌跡,是因為親社會行為需要情感、認知和動作的復雜整合[3]126-136[18]126-131。如相關的雙生子研究發現,嬰兒的親社會行為(幫助,安慰等)在14個月到36個月期間迅速增加[21]737-752[3]126-136。早在1992年相關的研究也發現,個體穩定的移情反應出現在兒童2歲時[22]126-136,而且在第一年觀察到的嬰兒情感移情和認知移情能夠對第二年嬰兒的親社會行為表現做出系統地預測。
綜合上述眾多的研究可見,嬰兒移情各成分的發展趨勢以及發展特點各不一樣,情感移情始于新生兒,在生命第一年發展迅速并達到穩定;認知移情發展始于第一年,并在第二年逐漸達到中等程度;移情的動機成分即親社會行為等則發展相對較晚,在第一年末開始,第二年內迅速增長。這些研究結論與霍夫曼關于嬰兒移情發展理論的階段性論述并不一一對應。霍夫曼認為第一階段(0—1歲)的嬰兒是自我中心移情,但研究者發現第一年中嬰兒能夠產生他人定向的反應,如注視、簡單安慰痛苦中的他人[18]126-131。霍夫曼認為第二階段(1—2歲)的嬰兒是準自我中心移情,但目前研究證明第二年的嬰兒已經能夠對痛苦中的他人進行語言和行為上相對復雜的移情反應[11]447-458。霍夫曼認為嬰兒移情悲傷是因為嬰兒分不清自我和他人,混淆了誰在悲傷,但是并沒有考慮情緒調節在情緒喚醒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他低估了嬰兒移情的能力。對于這些不一致,還需后繼研究者的進一步思考和探討。此外,研究所發現的不同移情成分的發展速度各不相同的研究結論也進一步證明了,Decety等人強調的在研究嬰兒移情時區分不同移情子成分的觀點是非常必要的。
三、嬰兒移情的影響因素
目前,嬰兒移情的影響因素研究主要從個體因素(性別、氣質以及遺傳)和社會因素(移情對象的熟悉性、母親撫養方式以及依戀)兩方面進行考察。
(一)個體因素
1.性別
目前,關于嬰兒移情是否存在性別差異仍有爭論。一部分研究者認為移情存在性別差異,并且從出生到整個生命進程中移情的這種性別差異始終保持一致和穩定,即女性的移情能力始終高于男性[23]604-627[3]126-136[21]737-752[22]126-136;但另一部分研究者認為嬰兒移情不存在性別差異,盡管有研究者發現女嬰的移情能力略高于男嬰,但是這種差異并沒有達到統計學上的顯著水平[24]70-97[25],因此,仍認為嬰兒移情不存在性別差異。可見,性別是否影響嬰兒移情仍需進一步的研究進行探討。
2.氣質
個體氣質擁有許多不同的屬性。大量研究發現氣質特征能夠影響嬰兒的移情,但不同的氣質屬性與嬰兒移情的關系并不一致。一些研究發現,氣質的特定屬性如學步期嬰兒的抑制性、恐懼和悲傷傾向與移情以及安慰行為負相關[26]111-134[27]125-146。個體發育早期,嬰兒的抑制性氣質雖不影響嬰兒對母親的移情,但影響嬰兒對不熟悉成人的移情[28]1189-1197。研究者還發現,在生命的第一年嬰兒善于社交的氣質與情感移情以及工具性幫助呈正相關[29]367-383。近期有研究發現,嬰兒消極情緒性與嬰兒對母親的移情呈顯著負相關,嬰兒的情緒性能夠對嬰兒對母親的移情做出顯著地負向預測,但嬰兒消極情緒性與嬰兒對陌生人移情相關不顯著[30]97-121[25]。相對于非易怒的嬰兒,情緒易怒的嬰兒對他人通常表現出較少的親社會行為;但是,如果易怒嬰兒的母親在日常母嬰互動活動中對嬰兒是高反應性的,那么這些易怒嬰兒則會比非易怒嬰兒表現出更多的親社會行為[30]97-121。Schuhmacher等人研究發現18個月嬰兒的恐懼氣質與嬰兒安慰行為相關[31]124-134。而Gross等人在18至30個月的嬰兒中沒有發現嬰兒氣質(恐懼、羞怯和社交恐懼傾向)與親社會行為(幫助、安慰或分享)的關系[32]600。可見,嬰兒氣質對嬰兒移情的關系并不遵循簡單的模式,具體的關系還需研究者進一步深入探討。
3.遺傳
移情具有遺傳效應,如Zahn-Waxler等人以雙生子為研究對象,發現移情具有中等強度的可遺傳性[3]126-136。不同的均以雙生子為研究對象的研究發現移情能力的遺傳影響力從20%[33]369-391至69%[34]112有所不同。近期,劍橋大學自閉癥研究中心的Simon Baron-Cohen與著名基因檢測公司(23andMe)合作,采用全基因組關聯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GWAS)對46 861名被試的共9 955 952個遺傳位點(SNPs)基因檢測結果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在移情能力的影響因素中,在測定的SNP范圍內的遺傳因素占比達到11%±1.4%。考慮到研究并未對全基因組數據進行分析,聯系其他研究結果,遺傳在移情中的影響可能會高達30%以上。可見,無論是在雙生子研究還是非雙生子研究中,移情的遺傳性是相一致的,表明移情的遺傳效應是明確的。
(二)社會因素
1.移情對象熟悉性
移情對象的熟悉性會影響嬰兒的移情,表現為嬰兒對熟悉的對象更容易產生移情。對于大多數嬰兒來說,母親是其主要看護者,所以目前,在有關移情對象熟悉性對嬰兒移情影響的實證研究中,研究者設置的移情對象通常是嬰兒母親與陌生的成人(主要是研究者)或陌生嬰兒同伴。研究發現,與陌生的研究者相比,嬰兒對自己母親的移情反應最為強烈,表現出的親社會行為也最多[35]1081-1092[36]249-265[37]613-637[38]319-330。有些研究同時設計了母親、陌生成人和陌生嬰兒痛苦情境,結果表明,嬰兒對自己母親比對陌生成人以及對同齡人都表現出更多的關注以及安慰行為[3]126-136[11]447-458。
2.撫養方式
父母撫養方式被定義為父母典型的育兒策略、行為、態度和價值觀的整體的、一致的模式。在日常生活中父母與嬰兒互動質量對嬰兒社會能力的發展能夠產生重要影響。從社會化角度來看,嬰兒的移情可以被看作是特定養育行為的產物[38]319-330[39]3263-3277[40]17-25。Robinson等人發現,母親溫暖的撫養方式與14至20個月嬰兒的安慰行為變化模式顯著相關:母親高溫暖的撫養方式能夠預測女嬰20個月時的安慰行為;母親高控制的撫養方式會導致嬰兒安慰行為的減少,母親低控制的撫養方式能夠顯著提高嬰兒的安慰行為[27]125-146。有學者發現母親對嬰兒的移情看護(empathic caregiving)(當嬰兒給他人造成痛苦時,母親向嬰兒富有情感地解釋他或她自己的行為帶給他人的痛苦情緒)與嬰兒的補償行為及利他行為呈顯著正相關[38]319-330。Schuhmacher等人發現父母養護的日常出席能夠顯著地解釋18個月嬰兒安慰行為的個體差異[31]124-134。研究者還發現早期父母的敏感性與學步期嬰兒對他人(看護者和陌生的研究者)悲傷的移情行為反應有積極的橫向以及縱向聯系[30]97-121[35]1081-1092[37]613-637。為探討母親積極溫暖的撫養方式對嬰兒移情的真實效應,研究者控制了兒童困難氣質、性別和年齡變量,研究結果同樣證明母親對嬰兒悲傷做出積極溫暖的反應性能夠顯著地正向預測嬰兒對他人(自己的母親和陌生實驗者)痛苦的移情以及親社會表現[41]44-58。Massoff指出積極敏感的反應性的撫養方式對兒童心理理論和移情都有促進作用[42]。
3.依戀
依戀是個體在嬰兒期與主要撫養者之間形成的一種特殊的情感聯結,對個體個性發展和社會性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盡管至今有關嬰兒期依戀和移情關系的研究不多,但這些研究仍為早期個體的安全依戀與移情的關系提供了初步的證據。Mark與其同事使用自然觀察方法評估了16至22個月嬰兒在母親痛苦及陌生成人痛苦兩種情境下的移情反應,實驗控制了嬰兒的氣質變量,研究結果仍發現嬰兒的不安全依戀能夠負向預測嬰兒會對陌生人的移情[43]451-468。相似地,Bischof-K?hler的研究發現,嬰兒的安全依戀可以預測嬰兒對悲傷的實驗者有著更多移情關注和親社會反應[44]142-158。采用母親報告的嬰兒移情評估方式,研究也發現移情得分最高的是在陌生情境程序中被分類為安全型依戀的嬰兒,其次是回避型依戀和矛盾型依戀嬰兒,移情得分最低的是混亂型依戀的嬰兒[45]375-392。
四、反思與展望
盡管目前嬰兒移情研究已積累一定的成果,但該研究領域仍存在一些問題亟待探討、改進和加強。
第一,嬰兒移情研究需要更可靠、穩定的嬰兒移情評估程序,并保證這些評估程序的可操作性。由于嬰兒的語言能力比較低,在研究范式方面研究者必須考慮實驗刺激的類型和水平設置是否合適;目前嬰兒移情的行為研究絕大多數使用的是Zahn-Waxler等人設計的嬰兒移情評估程序,但是該評估程序在實際操作使用中存在一些問題,首先是每位嬰兒母親在實驗中表現的痛苦程度無法統一嚴格控制,加上現場的拍攝者也會影響嬰兒的情緒和行為,所以這些均可能不同程度影響實驗評估結果。因此,在未來研究中,為保證實驗中的刺激適用于嬰兒,實驗情境不能超出嬰兒期個體的社會知識范圍,并且盡量減少實驗中對嬰兒被試的無關干擾。因此,研究者需盡可能做到在自然狀態下誘發并記錄嬰兒的移情反應[25]。
第二,為了更好地了解個體早期的移情發展與個體社會化的關系,研究者應該結合社會依戀、道德和公平等社會心理學相關因素,探討人類早期的移情發展與社會性發展的關系。因為人類的高級移情是建立在基本的移情形式之上,并且與一些核心神經機制相聯結,而這些核心機制與情感交流、社會依戀以及親代撫育相關,是影響嬰兒移情潛在的重要變量。因此,在探究嬰兒移情的社會功能方面,個體早期的移情能力很可能是個體社會性和道德敏感性發展的基礎。所以,嬰兒移情的未來研究應重視與社會依戀、道德和公平等社會心理學因素的結合。
第三,神經功能成像、病變研究以及認知神經科學研究證據都表明,移情是一種復雜的社會認知能力,成人移情的生理基礎涉及大腦的多個腦區。成人移情過程涉及包括原始腦區,如杏仁核(amygdala)、下丘腦(hypothalamus)以及海馬(hippocampus)等;進化而來的新腦區皮層相關額葉皮層區域,如腹內側和內側前額葉(vmPFC和mPFC,在自我意識方面有重要作用,涉及意圖理解)以及后顳上溝(pSTS,涉及意圖理解)等區域;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皮質(HPA)系統和交感神經—腎上腺髓質(SAM)系統[4]1-24。目前沒有關于嬰兒移情生理機制的研究,嬰兒與成人移情的生理機制的區別和聯系仍不清楚。因此,結合腦成像以及fMRI技術對嬰兒移情的腦機制進行研究,將是未來嬰兒移情的重要研究取向。
第四,目前對于嬰兒移情的個體差異情況以及影響嬰兒移情的潛在變量研究仍不夠深入。嬰兒移情影響因素比如撫養方式和依戀影響嬰兒移情的具體機制需要進一步證實;嬰兒氣質與嬰兒移情的關系并不遵循簡單的模式,具體的關系仍需深入探討;性別對嬰兒移情的具體影響研究結果仍不一致。可見,對于嬰兒期個體移情能力的影響機制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和證實。
最后,當前嬰兒移情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嬰兒對痛苦這一較為籠統的情緒的移情,嬰兒移情發展特點也是基于嬰兒對他人痛苦情緒的移情結果得到的,而很少有研究涉及嬰兒對他人的具體情緒類別的移情。因此,目前仍不清楚嬰兒對他人的高興、憤怒、傷心和害怕這四種不同的基本情緒的移情是否存在不同的發展特點,這也是未來嬰兒移情研究的一個拓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