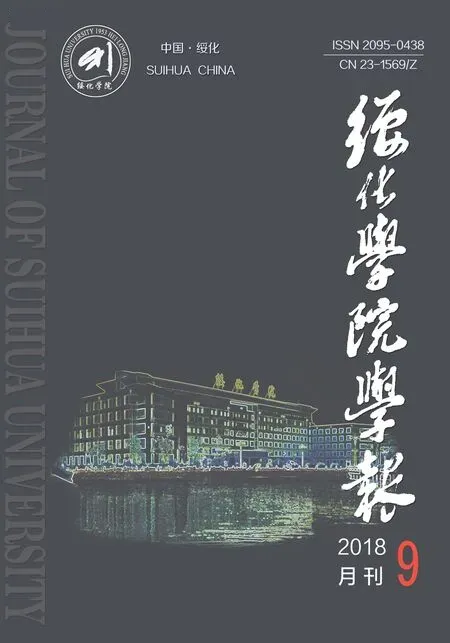復線歷史視域下的治理模式研究
——基于歷史觀的視角
李美婧
(成都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四川成都 610059)
“治理”一詞最初出現在企業當中,指的是公司的治理,旨在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利益的企業之間得以調和。隨后“治理”一詞被應用于各個領域,在政治上的治理主要體現為旨在使政治高效的運轉,從而促進國家的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1]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對于推進我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具有深遠的意義。
一、線性與復線:中國治理模式的探索
“復線歷史”是后現代歷史研究下的產物,最初由印度的漢學專家杜贊奇在《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一書中提出,傳統的線性歷史觀下歷史是按照時間來編排的,線性時間被理解為連續的、單向的,并提出線性歷史觀表現為:一種是建立在漢民族為中心的表述,另外一種是建立在精英主義的結構之上的表述。然而這種線性歷史觀極易造成人們的恐慌,極易造成歷史的集權與封閉與進化論史觀的擴張,使落后地區只能成為順從西方意志演進的歷史,因此,杜贊奇試圖解構傳統民族國家的“線性歷史”的敘事范式,發現這種線性歷史觀下的歷史真相,提出“復線歷史觀”。他指出:“在復線的歷史中,過去并非僅沿著一條直線向前延伸,而是擴散于時間和空間之中是一種試圖既把握過去的散失,又把握其傳播的歷史。”[2]筆者認為,復線歷史觀的視域下歷史研究急需構建一個可以與過去與未來產生聯系的連接體,即“民族國家”,民族國家作為現代化的產物與根植在傳統中的特性可以實現歷史連續性與穩定性。以復線歷史觀看治理模式有利于擺脫以往線性歷史觀下一元的治理模式,進而對于中國的治理模式上的把握與探究具有重要意義。
由民族國家來集中考察中國的治理模式中的話語與政治,近代中國政治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政治與基層民眾的脫節。蔣介石所持的歷史觀就是傳統的線性歷史觀,當時他僅看到鞏固自身的統治的需要,無條件地按照精英主義的上層史觀進行治理,這種歷史觀念帶有普遍的“進化論歷史觀”。相同的,近代以來隨著俄國革命的發展,平民主義傳入中國,傳統的上層治理模式隨即瓦解,平民主義亦可理解為民治主義,是由人民全體所行的民主民權的政治,然而在治理模式上不能一味地追求多數人的治理,這種多數人治理的模式表面上代表著民主與自由,實則被操控利用,淪為精英階層糊弄大眾的假象,同時大多數的民主也難免淪為暴政。由此可見,以上兩種治理模式由于都只看到了治理的一方,沒有團結民族國家中的各個階級進行治理,因而是一元的片面性的。
不同于國民黨政府的線性歷史觀的精英主義治理模式,早在革命時期毛澤東根據中國現狀認識到中國農民占大多數的實際情況,提出“農村包圍城市”等路線,這當中包含了對農民的重視。如果說蔣介石時期的錯誤的治理模式將中國淪為一盤散沙,那么到了建國時期毛澤東則明確指出:“我們應當將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組織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其他各種組織里,克服舊中國散漫無組織的狀態,用偉大的人民群眾的集體力量,擁護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建設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新中國。”[3]毛澤東在革命與建國時期沒有順應從中國傳統向西方模式的直接過渡的線性歷史觀,而是基于復線歷史觀的理論視野,注意到被歷史敘事中占優勢的表述掩蓋其他身份的表述,著眼于中國時下的國際環境與國情情況認識到了群眾力量的強大以及團結群眾的必要性,將基層與人民群眾建立起血肉聯系,致力于改善民生并將其組織起來用于國家發展與建設。隨后改革開放時期,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更是在此基礎上認識到僅僅團結人民群眾還不夠,人民群眾之中情況各異仍然需要加強黨的帶頭作用,因此鄧小平明確提出要“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4],集中體現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具體現實情況的把握,形成了適應新時代發展的治理模式。
二、新時代治理模式歷史觀原理蘊涵
唯物史觀中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經濟具有反作用。”[5]在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作為上層建筑的核心,政治治理現代化既受經濟基礎現代化的制約,又對經濟基礎現代化有著巨大的反作用。以蔣介石為領導的國民黨之所以失敗,是由于蔣介石為了維護其統治,害怕民眾的參與會威脅自己的政權,所以他所實行的是線性的上層治理路線,然而他沒有認識到現代化是國家的、民族的。正是由于蔣介石所實行的上層治理路線,所以,以軍政為主導的治理模式不能保障民權,以上層的精英階級與群眾所屬階級相對立不能保障民生,在抗日方面不愿應戰也不能保障民族,正是在國民黨的上層治理模式之下,由于國民黨內上層腐化嚴重,因此不能帶動并保障經濟的發展,到了后期在全國范圍內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危機,進而使其統治逐漸走向失敗。
而反觀中國共產黨,治理是建立在人民民主專政之上,1982年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6]憲法中規定人民民主專政意味著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因此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二戰之后的各國實際發展來看,一個強有力的政治團體是客觀和諧發展的堅實基礎。具有精英主義性質的政黨團體是建立一個高效運轉的政府的前提,但同時也不能離開群眾的參與。要想實現發展,必須構建以政黨為首的政府與群眾溝通參與的模式,也就是說,政黨和民眾要在發展問題上達成協議進行協商,讓民眾參與到社會事務的管理中去,改變以往“我為你好,你就接受”的傳統觀點。中國共產黨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因此在治理上強調上層治理是必要的,所以在此基礎上要加強聯系下層治理,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納入治理當中。
因此,黨的十九大會議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擴大人民有序的政治參與,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4]以習近平為代表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將“民主協商”新增在政治報告中,將民主協商擺在了一個新的高度。伴隨著互聯網的廣泛使用,網絡平臺所具有的開放性特征成為了我國協商民主實踐的主要途徑,網絡協商民主使多元的主體參與到社會治理之中。然而一個毫無管制言論機制的網絡平臺是不可想象的,但這也并不意味著政府可以為所欲為,問題的關鍵不是我們要不要管制而是如何管制,管制僅僅需要政府的執行還不夠,我們應當實現政黨與民眾的溝通,構建一個“協商民主”的民主機制,有效地避免政府的管控過重所帶來的弊端。隨著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到來,迫使我們需要廣泛的運用協商,最大限度地將人民動員起來,通過協商貢獻彼此的智慧,有效地解決發展中所帶來的矛盾。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基于對唯物史觀的掌握,多次強調黨的帶領作用和緊密聯系群眾的重要性,正是在這樣的唯物史觀的指引下,習近平總書記大膽而又創造性地探索和發展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模式。
三、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治理模式構建
傳統溝通方式中黨群溝通一般是通過宗教、意識形態或權利的方式進行的,然而在現代社會意識形態的溝通中,其效果已經大打折扣了,由于人們對以意識形態的方式對群體利益掩蓋的利益集團效應極為敏感,導致了現代社會意識形態作為溝通粘合劑的失效,特別是在互聯網社會的環境下,這個問題顯得尤為的突出。習近平總書記在4.19講話上明確強調在網絡時代的治理關鍵在于“為人民、靠人民”[7],因此在網絡信息時代如何實現政黨與群眾的溝通顯得尤為重要。
王岐山在《2014大國印記》系列報道第三期曾說:“嚴格執紀監督,加大懲戒問責力度,及時查處違紀違規行為,就是不處理也要爆你的光。”[8]王岐山認識到,傳統社會層級式的社會治理之所以失敗,其根本原因在于信息在上下級溝通過程中產生的磨損效應。對于這個問題,中國從以往傳統皇權時代便開始進行探索,正如朱元璋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設立了東廠機構給皇帝收集信息,然而這種機構的設立卻不能防止東廠的權力擴大,從而影響當權者所知消息的真實性。王岐山的反腐成功正是利用了網絡,實現了黨群之間的直接溝通,并且通過將違紀行為曝曬在互聯網上的一系列措施,對貪污腐敗重拳出擊,充分利用了互聯網所帶來的便利。因而網絡時代的治理要充分利用互聯網的優勢,通過網站宣傳互動,健全網絡信息管理,盡量避免人為因素的參與,避免信息的失真,逐步加強政黨與群眾之間信息的有效溝通,以此構建一個合理的馬克思主義現代化治理模式。
而從長期實踐來看,工會就可以作為這樣的治理模式,即構建“黨—工會—群眾”的治理模式非常必要。正如黨的十八大提出:“支持工會、共青團、婦聯等人民團體充分發揮橋梁紐帶作用,更好反映群眾呼聲,維護群眾合法權益”。[1]可見工會作為一個重要的人民團體受到了黨中央的重視。隨后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進一步完善政府、工會、企業共同參與的協商協調機制,構建和諧勞動關系。”[4]工會作為工人階級的群眾組織可以在黨和群眾之間架起溝通的橋梁,但工會必須接受黨的領導。正如列寧所說:“現在我們僅僅宣布無產階級專政已經不夠了。工會必定要國家化,工會必定要和國家政權機關合并起來,建設大生產的任務必定要完全轉到工會的手里”。[9]發揮黨對工會的帶領作用可以有效起到橋梁紐帶作用,準確反映人民群眾的呼聲,維護好群眾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