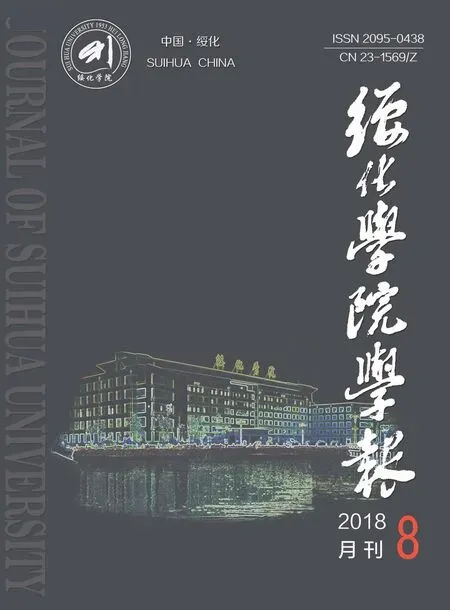淺析猶太人的散居對早期基督教擴展的影響
蓋 彤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四川成都 610064)
在歷史長河中,猶太人以“流浪的民族”著稱,從公元一世紀開始,羅馬人便征服了猶太人的家園——巴勒斯坦地區,圣殿被毀之后猶太人就沒有了祖國和自己的生存之地,開始了漫長的漂泊。他們首先來到埃及,而后又由于當地埃及統治者的壓榨和剝削而返回巴勒斯坦,但不久因其地又被其他強國所占,繼續流亡。總體來看,歷史上猶太人主要散居在埃及,之后轉為南歐、東歐、西歐,直至中世紀,猶太人已經大部分移居到歐洲生活,另外還有小部分生活在小亞細亞地區。作為一支外來民族,猶太人必然受到當地社會文化的排擠,發展空間受限,尤其是猶太人擁有自己的信仰,與當時占主流地位的希臘羅馬文明的神學信仰迥然不同,所以在最初,猶太人只在私下追求自己的信仰。但從另一角度來說,不同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也為兩種不同的信仰提供了相互借鑒和發展的可能,為二者提供了新的發展方向和可能性,脫胎于猶太教的早期基督教就是這種交互作用下的結果。
在長期的宗教學研究中,歷史學家們就猶太教與基督教的關系已經基本達成共識,即二者擁有著同一淵源,但二者本質上是相互沖突而又相互吸收的,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中,極為重要的就是猶太民族的生存狀況對基督教發展的影響。本文將先簡要介紹古代猶太人散居的歷史,而后從自然基礎、理論基礎和社會基礎三個方面來簡要分析猶太民族的散居對早期基督教發展的影響。
一、古代猶太人的遷徙歷史
猶太民族在世界民族史上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從民族誕生之初直至今日,統一時日少,流散時日多,在民族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處于動蕩不安、顛沛流離之中。盡管處在這樣一種幾乎是居無定所的狀態之中,猶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依然昂揚屹立,其文化傳統對當今世界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如今西方主流宗教,即對世界文明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基督教,其源頭就是猶太人的民族宗教——猶太教。此外,猶太民族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均對世界歷史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然而正是這樣一個民族,從古至今,卻始終面臨民族遷徙、建國等問題。
據人類學和語言學的研究表明,猶太人的祖先是自兩河流域逐漸遷徙到迦南的閃米特人的一支,作為外來人口,這支閃米特人在迦南當地人稱為“希伯來人”,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演變成為一支獨立的民族。率先帶領人民遷入迦南的領袖是亞伯拉罕,幾經輾轉將民族定居在迦南,但在之后,由于饑荒等各種因素,猶太人被迫遷往埃及尼羅河三角洲以東的地區,并淪為埃及統治者的奴隸,在埃及生活了幾百年后,猶太人再也無法忍受殘酷的迫害,由領袖摩西率眾人出埃及,經過40多年的長途奔波,終于抵達迦南附近,在這次著名的出埃及遷徙過程中,形成了猶太民族精神的雛形并奠定了猶太教的基礎,其中,摩西律法更是被猶太民族至今奉為寶典。但是,摩西并未將猶太人真正帶回迦南就去世了,繼任者約書亞帶領人民長期與外族進行斗爭,保護領地和人民的安全。至公元前1028年,猶太民族終于在掃羅的領導下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國家,并且在大衛和所羅門時代,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階段:大衛建都耶路撒冷,憑借其優秀的軍事才能擴大了猶太民族國家的版圖;所羅門則特別重視對耶路撒冷第一圣殿的修建,并且加強城市內部基礎設施的建設,完善社會制度,發展海上貿易,極大地提高了社會發展水平和文明程度,二人在位的時代可以當之無愧地稱之為猶太民族統一國家的黃金時代。但在所羅門去世后,由于后繼乏人,兄弟反目,國家陷入內斗,給外族入侵以可乘之機。公元前722年,北方王國被亞述帝國所滅,國民大多被掠走,從此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之中,而南方王國的猶太人則在激烈殘酷的戰爭中幸存了下來,延續猶太民族的歷史。但是,弱小的國家終究難以與強大且野心勃勃的鄰國相抗衡,南方王國逐漸淪為埃及、亞述、新巴比倫王國分爭的魚肉。公元前586年,新巴比倫王國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入耶路撒冷,焚毀了猶太民族的精神象征——第一圣殿,將居民掠至巴比倫,史稱“巴比倫之囚”。從此,猶太人又開始了流亡的命運,雖然后來又返回了耶路撒冷,但猶太民族國家建國的希望已不復存在,先后經歷了托勒密王朝、塞琉古王朝、羅馬帝國以及阿拉伯人的統治,猶太人流散世界各地,直至現代才建立起自己的國家。
流散、奔波的命運對于猶太民族來說是悲劇性質的,但也正是在這不平凡的命運中鍛煉出來一個不平凡的民族,它的精誠團結、奮斗不息、民族氣節乃至民族文化,并未因猶太人散居世界各地而沖散,反而對世界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自然基礎
筆者認為,散居首先是一種地理概念,地理上的分散為早期基督教的傳播帶來了空間上的更大可能,同時也就擴大了文化交流的接觸面,帶來了文化交匯的更大可能。文化上的交流大致有兩種主要形式:一是間接交流,即通過文字資料、貿易互動等物質的面對面;二是直接交流,即通過人本身進入一個不同的文化環境來進行人的面對面。這兩種“面對面”都是文化交流常見的基本形式,但收效卻不同,顯然,作為文化行為的基本個體,人真正融入新的文化環境才會使文化的交流更加深刻,不同文明的價值觀才會形成最全面的交融與碰撞,才會對更加客觀地看待自身和其他文明發展的異同。“廣泛的散居使猶太人可以近距離的切身體驗不同文明價值觀的異同,審視自身的信仰和傳統……猶太人的散居在文化上對整個地中海地區產生了深刻影響,促進希臘羅馬文明與猶太信仰之間深入地互動,使希臘羅馬社會對于早期基督教有了初步的了解。基督教發展初期,希臘人和羅馬人是從猶太教的角度來認識基督教,從猶太會堂來了解基督信仰。”[1]猶太人的散居實際為猶太人及猶太文明在空間上進行了拓展,將原來局限于巴勒斯坦地區的文化帶入希臘羅馬文化圈,這種人口上的遷移為文明的發展提供了自然基礎,是一種自然條件,縱觀歷史上各個帝國,幾乎都是先有地域上的擴展然后才有文化上的擴展,猶太人的散居為基督教希臘化提供了空間上的便利條件,也就為早期基督教的擴展邁出了最基本的一步。
三、理論基礎
由于基督教與猶太教有著共同的淵源,早期基督教與猶太教可以定義為“共生一體”的關系,這就意味著,最早的幾批基督教信徒中必然會有猶太人,或者絕大多數是猶太人。在猶太人群眾,基督教的信仰逐漸形成自己的系統并擴展,但在這一過程中,早期基督教并沒有完全擺脫猶太教的影響,并且伴隨著猶太人向希臘羅馬世界的遷徙,希臘羅馬文明對猶太教和早期基督教的滲透日益加強,兩種宗教都出現了希臘化的趨勢,而猶太傳統作為早期基督教希臘化的中介,它既是早期基督教向外擴展的工具,同時也是向外擴展的束縛。“基督教與猶太教本質上相互沖突,但又相互吸收,我們將從下述幾個方面來分析猶太傳統與早期基督教的關系:第一,猶太教尤其是希臘化猶太教是基督教希臘化的中介。猶太教身處多元文化背景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希臘文化的影響,由于早期教會對猶太教有一定的依附性,因此受到希臘化猶太教的影響,并在其影響下緩慢希臘化。第二,猶太人的散居使早期基督教傳播的基礎,影響早期教會的普世性建構。早期基督教絕大多數是猶太人,基督信仰的擴展在猶太人中間現行展開。第三,早期基督教與猶太教在共生的情況下沖突、分離,朝希臘化方向發展。”[2]結合當時當地的歷史發展階段來看,猶太人的散居具有廣泛性和普世性,而希臘化時期的希臘文化在東地中海地區也同樣具有廣泛性和普世性,這兩種不同文化的相同特性使得猶太人的散居成為了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重要因素,也就成為促進早期基督教傳播的重要因素,使得早期基督教也具有了相應的廣泛性和普世性。“猶太人的散居與早期基督教發展關系密切。猶太人散居的普世性、希臘化時期希臘文化和語言影響的普世性、地中海地區靈性追求的普世性,構成相互呼應的歷史格局。這種特殊的歷史處境,使得猶太人的散居地成為了基督教初期傳播的自然基地,哪里有猶太人,早期基督教首先就傳播到哪里,因此早期基督教的普世性應該從猶太傳統來理解。”[3]
四、社會基礎
經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已得知,猶太人的散居為早期基督教的發展和傳播提供了自然基礎和理論基礎,既然猶太人的分布狀態是“散居”,那就意味著猶太人廣泛分布于地中海沿岸的各個地區,猶太人的散居也正是猶太教和早期基督教及其信徒的散居,而每個地區,甚至說每個城市,發展程度和希臘化程度都不盡相同,自然早期基督教在每個地區、每個城市所受到的猶太傳統影響和希臘化影響的程度是不同的,“在基督教誕生并借助猶太人散居地為母體傳播之前,猶太教已經有各種本土化形態并且呈現出多元性。因此,不同的散居地、不同的猶太傳統勢必影響早期基督教神學,使它呈現出多元化的態勢。”[4]
這種多元化的態勢可以通過當時三大希臘化城市——亞歷山大里亞、安提阿和羅馬中的猶太傳統對早期基督教的影響的不同體現出來:首先,在亞歷山大里亞,希臘哲學填融合了猶太教,使希臘哲學成為基督教神學發展的合適路徑,從此在亞歷山大里亞的基督教發展過程中,希臘式的形而上學占據了主導地位;而在安提阿,希臘化風潮與舊有的猶太傳統形成某種程度上的競爭關系,在二者的相較之下尋求希臘化與猶太傳統的均衡點,在兩個陣營的沖撞下,思想與理論的交鋒使得安提阿成為的新觀點誕生的搖籃地;與前兩者激烈而明顯的競爭關系不同的是羅馬,在這座城市中,猶太傳統與希臘化風潮的交融較為保守、溫和,重社會實踐和社會關懷而輕神學思辨。
結語
綜上所述,猶太人的散居對其宗教信仰及脫胎而出的早期基督教有著多種方面的深刻影響,人口在地理上的擴散和移動,帶來了文化上的深度交流與融合,猶太民族的散居正是猶太文化、猶太教和早期基督教的散居,并且猶太傳統在希臘羅馬文明和猶太文明之間架起了橋梁,為后世西方文明的發展奠定基礎,它們孕育了人類文明早期的萌芽和未來的巨大輝煌。雖然,猶太民族的散居,很大程度上由歷史的、社會的因素所致,并非自愿散居和遷徙,并且,以我們今天文明發展歷程的視角來看,作為創造主體和傳播主體的猶太人為人類的發展做出來巨大的貢獻,而這種輝煌的背后卻是以猶太民族幾千年來的奔波遷徙為代價的,正所謂苦難造就輝煌,當我們深入了解任何一種文明時,在看到它們帶給我們今天的成就的同時,不要忘記這些創造者在背后經歷的艱辛與困苦,猶太民族可歌可泣的歷史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和研究,并向之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