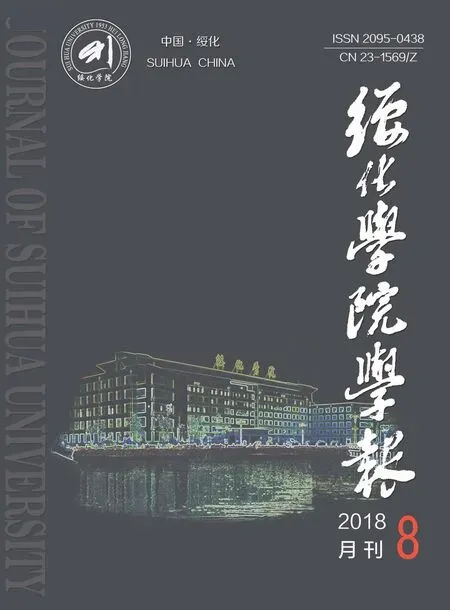燕然如可勒 萬里愿從公
——縱橫論戎昱邊塞詩
吳昌林 李 琦
(華東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江西南昌 330013)
戎昱(740—787),中唐詩人,新舊《唐書》皆無其傳,但《唐才子傳》為其立傳,《本事詩》《云溪友議》和《新唐書·藝文志》等亦載其事。本文僅從文學史的視角,“縱”(從歷史的維度)“橫”(從作者同時代詩歌的維度)淺論其邊塞詩作的特點,以期對其邊塞詩作給出合理的評價。
一、秉開元之余暉
戎昱雖出生于盛唐,但其詩歌創作卻集中在安史之亂后的大歷、貞元兩朝,故文學史常將其詩歌劃分至大歷詩歌中。他的很多詩歌確實體現出了大歷詩人們孤冷哀怨、苦心雕琢的特點,但其部分邊塞詩卻色彩明朗,風格雄渾,更帶有一種積極進取的昂揚斗志,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盛唐邊塞詩的余暉。
(一)慷慨豪情與進取精神。戎昱的部分邊塞詩突破了時代悲苦氛圍,展現了盛唐才有的慷慨豪邁本色和盛唐詩人身上具有的進取心。如其作品《從軍行》開篇便是:“昔從李都尉,雙鞬照馬蹄。生擒黑山北,殺敵黃云西。”追隨英勇的將領,騎著駿馬步入戰場,生擒敵酋,大破敵軍,一開始就給人斗志昂揚的感覺。緊接著描寫邊塞苦寒意境:“太白沉虜地,邊草復萋萋。歸來邯鄲市,百尺青樓梯。”“邊草”“萋萋”等意象頗具寒意苦感,但一個“青”字使得景色明亮許多,也似乎暗示下文氣氛會有轉折,果然,“感激然諾重,平生膽力齊”,重然諾者為俠,有膽力者為豪,而“這種豪俠之氣屬于建安,盛唐;屬于李白,崔顥,道大歷來就只在戎昱詩中還勃郁了”[1]。這等豪俠意象往往只會出現在盛唐李白的詩歌中,但在戎昱的邊塞詩中我們卻同樣看到了類似的人物,接下來則描寫了一連串完整的事件:“芳筵暮歌發,艷粉輕鬢低。半醉秋風起,鐵騎門前嘶。遠戍報烽火,孤城嚴鼓顰。揮鞭望塵去,少婦莫含啼。”獲勝的將士回營享用美食,欣賞歌舞,照常理詩歌在此處就已然作結,但詩人又別處心裁地安排了后續的劇情:酒酣之時秋風忽起,斥候在門口報告敵軍來襲,夜中孤城迅速響徹集合的戰鼓,主人公毫不猶豫,上馬揮鞭向著敵人入寇的方向奔去。全詩氣氛高亢,格調昂揚,只見報國殺敵之熱忱,不見怨戰畏敵之哀愁。盛唐邊塞詩人詩歌中常見的慷慨豪情和樂觀進取精神清晰可見。
(二)以苦寒寫雄壯。受到我國邊疆地理環境的影響,我國古代邊塞詩自漢代開始就具有重視運用苦寒意象的特點。終唐一代無論是盛唐積極進取的邊塞詩,還是中晚唐保守哀怨的邊塞詩都極愛用苦寒意象。戎昱的邊塞詩之所以具有一定的盛唐氣象,就在于他的一些作品同樣是以苦寒寫雄壯,試看《涇州觀元戎出師》:“寒日征西將,蕭蕭萬馬叢。吹笳覆樓雪,祝纛滿旗風。遮虜黃云斷,燒羌白草空。金鐃肅天外,玉帳靜霜中。朔野長城閉,河源舊路通。衛青師自老,魏絳賞何功。槍壘依沙迥,轅門壓塞雄。燕然如可勒,萬里愿從公。”“寒日”“覆樓雪”“黃云”“白草”“朔野”等意象無一不是西北邊地獨有的苦寒意象,這些意象在中晚唐詩人筆下也常常出現,典型的如鮑溶在其詩作《塞下》中描繪的:“寒日慘大野,虜云若飛鵬。”但同鮑溶詩作中營造的“漢卒馬上老”的悲苦意境不同,這些意象在戎昱詩中卻如同在盛唐邊塞詩中那樣起到了欲揚先抑,烘托氣氛的作用:盡管天大寒,風蕭蕭,但征西大將率領的軍隊卻斗志昂揚,燒盡白草,金鐃肅天,將塞外虜寇滌蕩一空,使得河湟一帶多年因戰亂難行的大道再度暢通。而作者更是在詩歌的結尾豪邁地表示如果可以為國家掃除邊患,燕然勒石,那么就算征戰萬里也愿意追隨將軍。在這首詩中,苦寒的意象反襯的是昂揚的壯志,面對塞外苦寒惡劣的生存環境,詩人不僅沒有感到恐懼和絕望,反而被激發出了殺敵報國,揚名塞外的慷慨抱負,這“與唐代中葉的一些情緒消沉、低落的邊塞詩迥然不同,表現了雄健豪放的鮮明特色,這是頗為難得的”[2]。
(三)明朗的意象與開闊的意境。除了以苦寒寫雄壯外,戎昱的邊塞詩還常常運用色彩明朗的意象進而營造出氣勢恢宏的意境,如其詩作《塞下曲》:“漢將歸來虜塞空,旌旗初下玉關東。高蹄戰馬三百匹,落日平原秋草中。”高大俊美的戰馬奔馳在一望無際的落日時分的大草原上,這種壯闊之景極有盛唐“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的氣象。又如《出塞》:“龍繞旌桿獸滿旗,翻營乍似雪中移。中軍一隊三千騎,盡是并州游俠兒。”據考證,戎昱與岑參關系密切,其詩集中專門有一首《贈岑郎中》寫給岑參,其中“天下無人鑒詩句,不尋詩伯重尋誰”。清楚地表明了他對岑參的敬佩和仰慕。這首《出軍》就頗有岑參“好奇”的風采,作者描寫軍隊前行時旌旗隨風舞動用了“龍繞”和“獸滿旗”的意象,好像隨著軍隊前進旌旗上的神獸都有了生命;而“翻營乍似雪中移”更形象的再現了大軍在雪地行軍的壯觀場面。最后兩句則表明僅僅是中軍中一隊人馬就有三千騎兵,還都是并州善戰的游俠組成,盡管沒有明確描寫戰爭過程,但可想而知這樣一支強軍必然無堅不摧。意象奇異又不詭異,風格嚴肅卻很樂觀,透過這些詩作中宏大的意境和明朗的意象,盛唐風骨可見一二。
(四)延續歌行創作。戎昱邊塞詩對盛唐邊塞詩的繼承還體現在他的體裁選擇上,邊塞詩至中晚唐大都以律詩和絕句為體裁,但戎昱的邊塞詩卻好用歌行,《從軍行》《苦哉行》(五首)《聽杜山人彈胡笳歌》等都是歌行邊塞詩,盡管語言不如律詩那樣錘煉,但卻立意清晰,情感充沛,成就也不凡。“《苦哉行》《贈別張駙馬》《聽杜山人彈胡笳歌》均屬本色當行,在大歷時期同類作品中可列為佳作”[1]。
戎昱的邊塞詩在一定程度上秉承盛唐余風,這并不是說他在邊塞詩的創作技巧上達到了盛唐高岑等大家的創作水平。他的很多邊塞詩在錘煉字詞,塑造意境等方面遠遠未及盛唐邊塞大家的高度,但他為數不少的邊塞詩中透露出斗志昂揚的精神意志卻繼承了盛唐邊塞詩那雄渾高亢的時代精神。正是從這個層面上,蔣寅先生才會評價他:“是唯一真正得到盛唐精神遺傳的詩人。”[1]
二、奏中晚之序音
安史之亂使得唐王朝元氣大傷,唐代宗廣德元年,吐蕃攻陷隴右,入據長安;唐德宗建中四年,涇原鎮兵變,叛軍再陷長安。這一時期唐朝對外頻繁戰敗,大唐雄風不再;對內叛亂多發,黎庶水深火熱。亂世之下,戰爭帶來的就不再是榮耀,而是殺戮與毀滅,因此中唐以來邊塞詩與盛唐邊塞詩相比開始有了自己的特點。戎昱是中唐初期的詩人,他的邊塞詩在一定程度上奏響了中晚唐邊塞詩憂郁傷感,蒼涼悲怨的先聲。
(一)強烈的反戰厭戰情緒。戎昱雖然有部分邊塞詩在情感上昂揚進取,與盛唐類似,但仍有占比相當大的一部分邊塞詩是純粹反映戰爭的殘酷并體現出作者強烈的反戰厭戰情緒的,在這些詩作中,作者選擇的切入點通常是邊塞將士極其悲慘的生活境遇,試看其作品《塞下曲》其一:“慘慘寒日沒,北風卷蓬根。將軍領疲兵,卻入古塞門。回頭指陰山,殺氣成黃云。”在這首詩中,作者并沒有直接描寫戰爭殘酷,而是先塑造了一幅凄涼之極的畫面:寒冬太冷,日光顏色都覺慘淡;北風太烈,地上野草連根莖都被吹上天。在這種惡劣無比的天氣下,將領帶著疲憊至極的軍隊跌跌撞撞地走入城門,但陰山山后殺氣又起,敵軍再度來犯,將士們的厭戰情緒可想而知。《塞下曲》是一部組詩,這首詩作為其開篇之作開始就為全詩奠定了悲劇基調和厭戰情緒。果然,在《塞下曲》其二中就寫到“胡馬馳驟速”“意又向南牧”,面對敵人入侵,老將只能領著疲兵再度出發:“嫖姚夜出軍,霜雪割人肉。”盡管都是夜戰,但《塞下曲》中的軍隊早已沒有了《從軍行》中的那種豪情與瀟灑,剩下的只是對無休無盡戰爭的厭惡:“戰卒多苦辛,苦辛無四時”“修岸沙礫堆,半和戰兵骨”。然而連年的征戰并沒有換來任何實質性的收獲,敵軍仍然是“單于竟未滅,陰氣常勃勃”。苦寒的天氣,滿地的尸骨,疲憊的身心和仍然強大的敵人,這種種因素使得絕望之感充滿士卒心頭:“試問左右人,無言淚如雨。”在組詩的結尾,作者發出了心底的呼聲:“何意休明時,終年事鼙鼓。”反戰厭戰之情充斥全詩。中晚唐詩人對于戰爭的主旋律始終是厭惡與批判的,這種思想在中唐初期戎昱的邊塞詩中已然得到了明確體現。
戎昱還有一部分邊塞詩同樣是抒發戰爭對人的殘害,表現自己的厭戰思想,但卻是從一般百姓甚至作者本人出發表達這一觀點,如其作品《入劍門》:“劍門兵革后,萬事盡堪悲。鳥鼠無巢穴,兒童話別離。山川同昔日,荊棘是今時。征戰何年定,家家有畫旗。”戰亂使得鳥鼠的巢穴都被毀壞,涉世未深的兒童都因為要躲避戰亂經受離別之苦,山川滿布荊棘,家家盡遭兵禍,昔日的天府之國因為戰爭已然成為了人間地獄。在《收襄陽城》(二首)中,作者前半部分描寫:“暗發前軍連夜戰,平明旌旆入襄州。”看似戰事順利,意氣風發,但在后半部分則筆鋒一轉:“五營飛將擁霜戈,百里僵尸滿浕河。日暮歸來看劍血,將軍卻恨殺人多。”縱然戰爭勝利又能帶來什么呢?無非是滿河尸首罷了,就連戎馬一生的將軍都覺得殺戮過重,作者對戰爭的怨恨一目了然。如果說前幾部作品作者都是借他人之口表厭戰之情,那么他在《逢隴西故人憶關中舍弟》中就直接以自己的遭遇表達對戰爭的控訴:“莫話邊庭事,心摧不欲聞。數年家隴地,舍弟歿胡軍。每念支離苦,常嗟骨肉分。急難何日見,遙哭隴西云。”作者自己的兄弟戰死疆場,飽受骨肉分離之苦乃至于提都不愿提及邊疆戰事。戰爭對人的戕害,對生命的摧殘都在詩中得以體現,作者對戰爭的厭惡和憎恨表露無遺。
(二)蕭條慘淡的凄冷意象。在意象的選擇上,戎昱選取的很多意象均為日后中晚唐邊塞詩中常見的意象,這些意象同盛唐時慣用的苦寒意象又有不同,更多地給人以蕭條慘淡,恐怖凄涼的感覺,引發的情感也不再是盛唐時的雄渾悲壯,而是徹底的憂患哀傷。如前文提及的《塞下曲》五首中就出現“疲兵”“僵尸”“戰兵骨”“割肉霜雪”等盛唐邊塞詩中罕見的慘淡恐怖意象,在《收襄陽城》中,“僵尸”意象再度出現的同時,作者還增加了“慘慘悲風”“愁苦草木”等意象;到了《苦哉行》(五首)中,又出現了“塞垣鬼”“北荒”等意象,至于其他如“心摧”“淚如雨”“哭”“斷魂”“強笑”等直接表達作者情感的詞語更是屢見不鮮,這些意象與情感詞語共同促使戎昱的邊塞詩中常常充滿了蕭條悲涼的氛圍,也是日后中晚唐邊塞詩的共同特點。
(三)對樂府古題的大量選用。戎昱邊塞詩能稱為中晚唐邊塞詩序曲的原因還在于他極好選取樂府古題上,邊塞詩好取古題乃是慣例,但盛唐邊塞詩人卻往往能突破古題,即時即事自由命題,如王維《使至塞上》《榆林郡歌》、高適《使青夷軍入居庸三首》《登百丈峰》《登隴》、岑參《逢入京使》《安西館中思長安》等均為新創題目,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盛唐詩人所具有的創新意識和強烈的文學自信。中晚唐邊塞詩對樂府古題選擇的比例相比盛唐有了明顯上升,戎昱作為中唐之初的詩人已經具有了這種風氣,其現存25首邊塞詩中有15首均取自樂府古題或漢代舊題,分別是《從軍行》《苦哉行》(五首)《詠史》《塞下曲》(七首)《塞上曲》等,與之后的中晚唐邊塞詩類似。
總之,戎昱的很多邊塞詩已經沒有了對戰爭崇高性的描寫和戰爭必然勝利的自信,更多充斥著日后晚唐邊塞詩中常見的凄慘、冷淡意象,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奏響了中晚唐邊塞詩憂患凄慘的哀聲,故嚴羽在《滄浪詩話》中稱其詩歌為“已濫觴晚唐矣”和“有絕似晚唐者”是很有道理的。
三、破大歷之藩籬
戎昱的邊塞詩除了在縱向的文學史維度上具有承上啟下的特點,在橫向的大歷詩歌中也有自己獨特的價值,這集中體現在他的邊塞詩對大歷詩風的突破上。所謂大歷詩風,是指安史之亂后受國力衰微,社會動蕩等環境影響形成的唐代宗大歷年間的詩歌風氣。胡應麟一言以蔽之曰:“氣骨頓衰。”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在于“沒有杜甫那種反映戰亂社會現實的激憤和深廣情懷,大量的作品表現出一種孤獨寂寞的冷落心理,追求清雅高逸的情調”[3]。而戎昱身為大歷詩人,其詩歌對大歷詩風卻有明顯突破,尤其集中體現在他的邊塞詩上。
(一)大量創作邊塞詩。戎昱是大歷時期為數不多的大量寫作邊塞詩的詩人。大歷時期,隨著唐王朝國力衰微,絕大多數詩人對戰爭的態度也由美好的幻想變為厭惡與反感。以“大歷十才子”為代表的大歷詩人群們更愿意把創作目光投向山水田園和自我本身,其詩歌內容也以懷才不遇的苦悶和羈旅送別,或文人間的互相唱和為主。但戎昱卻依然堅持把目光投向邊塞,投向戰爭,仍然堅持大量創作邊塞詩歌。據統計,大歷時期百余位詩人中創作邊塞詩超過20首的僅兩人,戎昱便是其中之一。在大歷大部分詩人都癡迷于自我哀憐和交際生活時,戎昱能依然關注著邊疆烽火,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擴寬了大歷時期詩歌題材的領域。
(二)關懷現實,揭露黑暗。戎昱在自己的邊塞詩中體現出了對社會現實的強烈關懷與對社會黑暗的揭露與控訴,這更是對大歷詩歌局限的突破。大歷詩風與盛唐最重要的一點不同就在于這一時期詩人不再注重詩歌的現實意義,詩歌僅僅成為了詩人們互相唱和,稱幽道隱乃至拜謁王侯追求功名的工具。在大歷詩人的筆下,我們很難看到杜甫那種關懷黎民百姓的胸襟與悲憫,也很難看到高適那種對邊疆士卒的觀照與同情。然而戎昱一定程度上繼承了杜甫、高適等人的詩歌創作態度,特別是在其邊塞詩中明顯地體現出了對現實社會的強烈關懷。
戎昱與杜甫的關系十分密切,“戎昱不但是大歷中杜甫的唯一傳人,在貞元期間他也是唯一傳人”[4],他的《問笛》《入劍門》等詩歌在藝術上均體現了對杜詩的模仿,而其邊塞詩批判黑暗揭露現實的風格更是明顯承襲杜甫。如《塞上曲》:“胡風略地燒連山,碎葉孤城未下關。山頭烽子聲聲叫,知是將軍夜獵還。”敵人已然入侵,邊疆烽火正急,但將軍卻只知打獵不知御敵,作者對其昏庸無能的批判一目了然。
更為難得的是,戎昱的邊塞詩還敢以紀實的方式展現了民間疾苦,對當時朝廷的某些政策進行直接抨擊,這點在大歷詩人中尤為罕見。如其《苦哉行》(五首)就直接尖銳地抨擊唐王朝借回紇兵平亂這一政策,組詩在一開始就明確表達了作者對這一政策的態度:“彼鼠侵我廚,縱貍授粱肉。鼠雖為君卻,貍食自須足。冀雪大國恥,翻是大國辱。”因為國家發生叛亂,叛賊兇狠,就要請更兇狠的敵人來制服他,但制服叛亂后的結果呢?請賊御賊本身難道不就是在引狼入室,割肉飼虎嗎?故而作者明確指責這樣的政策只會導致“翻是大國辱”的惡果。在詩歌的后半部分,作者借一位家住洛陽的士人女子的悲慘遭遇說明了唐王朝引狼入室的惡果:“官軍收洛陽,家住洛陽里。夫婿與兄弟,目前見傷死。吞聲不許哭,還遣衣羅綺。上馬隨匈奴,數秋黃塵里。生為名家女,死作塞垣鬼。鄉國無還期,天津哭流水。”安史叛軍盤踞洛陽時女子一家尚且得活,但恰恰是唐王朝的政府軍“光復”東都后殺害了女子的父兄并把女子擄走。這里尤其觸目的是,盡管唐王朝與回紇約定收復洛陽后“財帛子女皆歸回紇”,但詩中竟然是唐軍自己把女子掠走送入回紇軍中,甚至連哭泣都不被允許。詩人對唐軍平亂無術,害民有方的無能與殘暴揭露得淋漓盡致。除了《苦哉行》組詩外,作者在《聽杜山人彈胡笳》中也描寫了“回鶻數年收洛陽,洛陽士女皆驅將”的類似慘劇。值得注意的是,聯合回鶻剿滅安史叛軍乃是唐王朝國策,戎昱的這些反映黑暗現實的邊塞詩歌明顯就是在指斥朝廷弊病,這種不平則鳴的文人骨氣遠遠勝過了同時期以大歷十才子為代表的一大批只知追求富貴,作詩為樂的豪門詩人。
(三)精辟的政論見解。戎昱邊塞詩對大歷詩風的突破還體現在對國家政策的精辟議論上,大歷詩人們主要關注的是自身的境遇,對國家大事的熱情相對較低,詩歌中很少出現富有見解的政論,但戎昱卻突破了這一點。前文中提及的《苦哉行》《聽杜山人彈胡笳》等作品表明了他對借回紇平叛這一政策的批評,而其《和蕃》更表達了對和親的反對:“漢家青史上,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擬靜胡塵。地下千年骨,誰為輔佐臣。”漢唐政權為了平息邊患常常將宗室年輕女性遠嫁少數民族政權,和親現象頻繁。而關于和親一般人往往認為是利于和平的事業,但戎昱在此卻指出和親之舉乃是“計拙”,把江山社稷托付與一位普通的女性這本身就是君王和重臣們的過失。《云溪友議》甚至記載憲宗以此詩駁斥大臣們請求用和親來討好吐蕃的言辭,沈德潛在《說詩晬語》中也稱其為“議論之佳者”。如此精辟的政論見解,在大歷詩歌中非常少見。
總之,戎昱的詩歌雖然藝術水平在其所處時代并不出類拔萃,更無法與盛唐諸公相比,但他的一些邊塞詩在精神和意象選取上確實繼承了盛唐風氣,在另一些邊塞詩作品中則開中晚唐邊塞詩凄婉哀怨風格的先河。他的邊塞詩關注戰亂帶給人民的傷害,揭露社會黑暗,敢于對時局政策中不當的方面加以批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大歷時期詩歌普遍聚焦自身境遇、無視黑暗現實的藩籬,在唐代文學史上有著獨特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