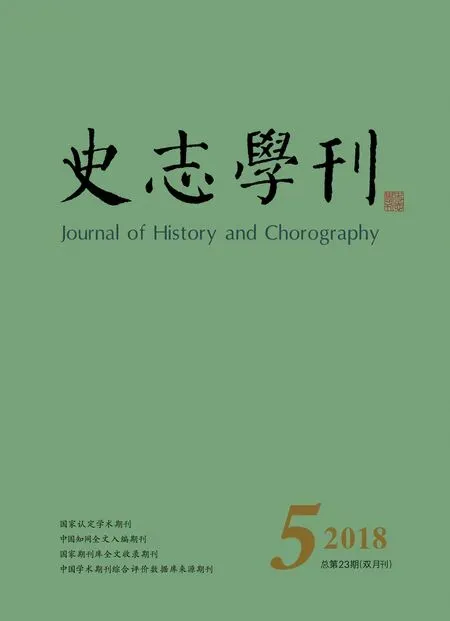河南新密古城寨遺址考古發現與研究
郭榮臻 郭昊晟
(1.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山東濟南250100;2.河南大學法學院,河南開封475000)
古城寨遺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曲梁鄉大樊莊村古城寨村民組,是新密地區史前時期的一處重要遺址,也是目前所知新密歷史上最早的城邑。該遺址于1988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為河南省文物保護單位,并于200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繼考古調查、發現、發掘以來,學界對該遺址尤其是龍山時代晚期王灣三期文化時期的城邑展開研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近年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單位又對該城址開展新一輪的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對該遺址相關考古發現、學術研究情況進行綜合梳理,以期對更加深入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古城寨遺址的考古發現
199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新密市炎黃歷史文化研究會、新密市文物保管所等單位調查洧水流域史前遺址時,對“鄶國故城”(古城寨遺址舊稱)的城墻給予較大關注,在該城址及其周邊展開大范圍的考古鉆探和調查,并對南城墻局部墻基進行試掘解剖,確定城的年代屬于龍山時代[1]蔡全法,馬俊才,郭木森.河南省新密市發現龍山時代重要城址.中原文物,2000,(5).。1998—200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黃歷史文化研究會等單位對遺址進行科學考古發掘,發現遺址以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堆積為主,揭露出王灣三期文化時期的城墻、城壕、城內夯土建筑基址、廊廡基址、灰坑、奠基坑、墓葬等遺跡,各種材質的生產、生活用具等遺物。此外,也見有仰韶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二里頭文化、二里崗文化、殷墟文化、戰國、漢代等多時期的遺存[1]蔡全法,馬俊才,郭木森.新密市古城寨龍山城址.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年鑒2000.文物出版社,2001.(P190-192)[2]蔡全法,馬俊才.新密市古城寨龍山城址.中國考古學會編.中國考古學年鑒2001.文物出版社,2002.(P193-194)。
城墻、城壕、城內夯土臺基、廊廡建筑等是這座龍山時代城邑最重要的發現。城址位于整個遺址的中部,平面呈矩形。東西長約500米、南北寬約460米,面積逾17萬平方米。西墻被溱水沖毀,僅存北、東、南三面城墻。城墻由地下墻基、地上墻體組成,系夯土版筑而成。城壕在原報告中稱“護城河”,北、東、南三面皆存,引溱水、無名河水入其內,形成城墻外的另一道防線。夯土建筑基址編號為F1,可能為城內的宮殿建筑,南北長約28.5米、東西寬約13.5米,面積約383.4平方米,成排柱洞將其分隔為7間房屋。廊廡基址編號F4,圍繞夯土建筑基址而建,是宮殿建筑外部的組成部分[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黃歷史文化研究會.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龍山文化城址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02,(2).。
2016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該遺址重新進行考古調查、鉆探與發掘,取得一些新的成果與認識[4]張小虎.2016年新密古城寨遺址考古新發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17年度考古工作匯報與交流會發言.河南鄭州,2018.。隨著考古發掘資料的不斷公布,學界對該遺址的認識將更加清晰。
二、學界對古城寨遺址的研究
21世紀初,這座中原地區龍山時代城邑一經報道,即引起國內史學界(文獻史學界、考古學界)的極大關注。多年來,考古學者、文獻史學者對其展開較為充分的討論,主要涉及城的族屬、相關遺跡性質、城垣建筑技術、器物、聚落形態、社會復雜化進程、生業模式、環境考古等方面。
(一)城的族屬
城的族屬是古城寨遺址研究中的重要議題。在考古發掘之前,學界一般將古城寨視作西周時期的鄶國都城[5]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地圖集·河南分冊.中國地圖出版社,1991.鄭州市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鄭州市志·文物卷.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在試掘以后,學界持此見的學者漸少。許順湛先生以史學問題入手,結合諸多史料考證了《五帝本紀》中“黃帝居軒轅之丘”的地望問題,認為軒轅丘在今新鄭、新密,兩地仰韶時代遺址以古城寨為首,龍山時代遺址以新砦為首。古城寨城址是證明軒轅丘地望的有力證據[6]許順湛.黃帝居軒轅丘考.尋根,1999,(3).。
隨著考古發掘工作的開展與發掘簡報等材料的刊布,越來越多的學者就這座史前城邑的性質發表觀點。曹桂岑先生撰文探討古城寨龍山古城的始建年代,結合相關史料,認為古城寨的地望與黃帝之都的記載相符,該城址即黃帝的軒轅丘所在[7]曹桂岑.新密市古城寨龍山古城始建年代與黃帝軒轅丘的探討.中國古都學會編.中國古都研究(第二十一輯).三秦出版社,2007.(P98-107)。蔡全法先生則根據考古發現對城的性質作出兩種推測:一則史前的鬼氏族南下至今新密,為安全防范的需要,在古城寨遺址修筑城垣;二則中原的華夏部落俘獲鬼部落的戰俘,命他們修筑城垣。蔡先生認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8]蔡全法.一夜“鬼”修龍山城: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遺址.文明,2003,(1).蔡全法.溱洧交流處,黃帝軒轅丘.大河報,2003-11-5,(第29版).。馬世之先生結合古代史料與相關考古發現,否認古城寨為“禹都陽城”的可能,提出其與祝融之墟的地望相合,并認為該城到西周時繼續作為鄶國都城使用[9]馬世之,新密古城寨城址與祝融之墟問題探索.中原文物,2002,(6).。
繼古城寨龍山城發現后,另一座龍山晚期興建的新砦城也被揭露出來,學界普遍將后者視為傳說中的夏啟都城,周書燦先生審慎地提出質疑,認為長期以來學界對《穆天子傳》中所載的“啟居黃臺之丘”的考證闡釋歧見紛出,結合《左傳》《國語》《世本》《漢書》《后漢書》《帝王世紀》《水經注》《太平御覽》等一系列文獻考證了夏啟活動的地域范圍,提出“黃臺之丘”在禹州的觀點,與新密新砦、古城寨城址無關[1]周書燦.《穆天子傳》”啟居黃臺之丘”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5,(2).。排除了古城寨與夏啟所居的關系后,周先生又針對學界流行的古城寨為黃帝軒轅丘、祝融之墟、鬼方等觀點,引證《左傳》《國語》等一系列史料梳理了祝融之墟的地理問題,根據王玉哲先生考證的鬼方活動區域否定了鬼方與古城寨的關聯,進一步結合相關史料,分析了屬于黃帝集團的大隗氏在此筑城居住的可能,并論及黃帝與祝融兩大集團相互通婚、逐漸融合的可能[2]周書燦.大隗氏與新密古城寨龍山古城.河南科技大學學報,2005,(4).周書燦.新密市古城寨龍山古城的族屬及相關地理問題.中原文物,2006,(1).。
綜上,就城的性質、族屬而言,學者們先后提出了不同的認識。研究路徑上基本是根據考古發現情況,結合一系列先秦及后世史料,考證史事,再將考古發現與文獻史料記載相結合。何以對同一處遺址,會有不盡一致甚至殊異的認識,是在史前史構建、史前考古與文獻史料相結合中需要引起注意與思考的。
(二)相關遺跡性質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宗廟、宮殿的有無長期以來被作為都邑判斷的標準。一般認為,史前有垣、壕的聚落未必皆為城市,有宮廟類建筑者則可別論。古城寨的夯土臺基、廊廡等建筑的性質作為判斷遺址性質的重要依據受到學界的重視,前已提及,發掘者對這些建筑作過解讀。近年,杜金鵬先生進行專文探討,分類剖析夯土臺基F1及其附屬建筑F4的柱洞、柱礎、磉墩、基槽等遺跡,對這兩類建筑進行了復原,認為二者僅是建筑群中的一處院落,F1為無堂室分隔的大型主殿,可能是城的統治者施政場所與原始宮殿,F4為對FI起到屏蔽作用的廊廡[3]杜金鵬.新密古城寨龍山文化大型建筑基址研究.華夏考古,2010,(1).。就已有的研究來看,學界普遍認同F1、F4的宮殿、廊廡性質。
(三)城建方式
長期以來,筑城技術是古代城址研究中的熱點問題。馬俊才先生前后兩次發文,就古城寨龍山城的城建技術展開討論,認為該城的城防系統由城墻、城門、護城河三部分組成;并論及墻基的處理方法、城墻主體的分層分段夯土版筑等方法[4]馬俊才.四千年古城風塵抖落現真容——河南新密古城寨龍山古城發掘記.文物世界,2000,(6).馬俊才.新密古城寨龍山城筑城技術的初步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學會編.中原文物考古研究.大象出版社,2003.。張玉石先生認為,古城寨城垣版筑技術較鄭州西山有較大進步[5]張玉石.中國古代版筑技術研究.中原文物,2004,(2).。曹桂岑先生亦論及該城城墻建筑中的基礎槽、坐底夯、版塊疊筑等現象,提出改成城墻存在始建、擴建、維修三個時期[6]曹桂岑.河南早期古城建筑考古.河南省古代建筑保護研究所編.文物建筑(第1輯).科學出版社,2007.(P174-187)。郭榮臻在對史前筑城技術的研究中也著力探討了古城寨的城建方式,認為該城存在基槽式城墻與版筑技術孑遺,系史前筑城技術流派“中原模式”下“河洛亞模式”的重要組成與代表性城址[7]郭榮臻.簡論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的城垣建筑技術.史志學刊,2017,(4).郭榮臻.河洛與海岱地區史前筑城技術的考古學觀察.”唐嘉弘先生九十誕辰紀念暨中國古代民族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國許昌,2017.。就城垣的建筑方式而言,學界幾無歧見,相關論者一致認為該城建筑技術高,在早期城市建筑史中占有較為重要地位。
(四)器物研究
關于古城寨器物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考古類型學和器物制作方法兩個方面。發掘者根據該遺址陶器形態,將古城寨龍山文化分為四期五段,第一期屬于龍山時代前期,與廟底溝二期器物近似,后三期屬于龍山時代后期的王灣三期文化[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市炎黃歷史文化研究會.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龍山文化城址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02,(2).。魯曉珂等運用化學分析等科技手段,分析古城寨遺址部分仰韶至龍山時期的陶器,得出三點認識:(1)陶器原料為易熔黏土;(2)部分器物輪制而成,部分器物上的紅彩、黑彩系鐵、錳元素成色使然;(3)陶器燒成溫度多在850℃—1000℃,陶胎吸水率、氣孔率較高[2]魯曉珂,李偉東,王海圣等.新密古城寨龍山文化遺址陶器的研究.”2009年古陶瓷科學技術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中國北京,2010.(P40-46)。由于簡報公布材料有限,以器物為本位的傳統考古研究所占權重有限。
(五)聚落考古與社會復雜化
城邑是經濟發展、社會分化、社會變革的產物,有學者就古城寨遺址的文明現象、聚落形態等進行過討論。蔡全法先生針對城址、城墻、城內相關建筑、施釉陶、石器、陶器、卜骨、刻畫符號、熔銅爐塊等現象,論及該城的政治、經濟生活狀況、土木建筑技術、意識形態等,認為該城為研究中國文明起源與國家形成提供重要依據[3]蔡全法.古城寨龍山城址與中原文明的形成.中原文物,2002,(6).。趙春青先生認為龍山時代已出現主從聚落群的分布格局,古城寨龍山城是城市與鄉村分野的重要證據,在聚落小群中占據主導地位,甚至承擔著保衛主體聚落群的職責[4]趙春青.鄭洛地區新石器時代聚落的演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P161-163)。高江濤先生根據學界早年調查材料,認為古城寨及其周邊分布的12處龍山文化時期遺址構成古城寨組聚落,或謂古城寨聚落群[5]高江濤.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的考古學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P228-231)。王震中先生進一步認為新砦、洪山廟晚于古城寨,不應作為古城寨聚落群的組成;根據古城寨遺址的社會生產狀況、經濟面貌、社會分層、復雜化程度等,提出古城寨龍山城邑是早期國家邦國都城的認識[6]王震中.中國古代國家的起源與王城的形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P334-336)。李龍對新砦城址從微觀、宏觀兩個維度的聚落形態分析,提出有別于其他學者的見解,認為新砦城址是同時期聚落中的最高等級,古城寨是聚落群中的次中心,可能是該區域的軍事城堡或戰爭指揮中心[7]李龍.新砦城址的聚落性質探析.中州學刊,2013,(6).。雖然學界在論及史前城市、文明起源時以此城的考古發現作為證據[8]學界關于史前城址的研究論著極多,涉及古城寨龍山城的亦為數不少。囿于篇幅,此處不再一一列舉。,但由于所在地的區域系統調查力度有限,宏觀聚落形態研究中對該城地位、作用等的認識還有待更多證據支持。
(六)生業模式
生業考古是考古學中的重要研究領域。所謂生業經濟,包括以農業、養殖業為代表的生產性經濟和以狩獵、采集、捕撈等為代表的攫取性經濟[6](P300)。植物考古、動物考古等是生業考古研究的重要方法。古城寨遺址進行過系統的植物考古研究,據陳微微等分析,龍山、二里頭、二里崗、殷墟4個時期出土農作物比重高于非農作物。龍山文化時期,存在粟、黍、藜三種作物,以粟為主,黍次之;二里頭文化時期,增加小麥,農作物仍是以粟類為主;二里崗文化時期、殷墟文化時期大致承前,惟小麥麥、藜的比重有提升[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鄭州周邊地區進行考古調查時,采集一批仰韶文化時期遺址的土壤樣品。據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張居中先生團隊研究,古城寨遺址仰韶時代樣品中出土有粟及禾本科的野生植物,龍山時代樣品中出土有粟、稻及麥瓶草屬的野生植物[8](P49-50)。總的來看,該遺址植物考古數據反映以種植業為主的生業模式,惟不同時期的作物組合、構成存在一定差異。此外,該遺址出土有狗、豬、黃牛、綿羊等家畜,熊、梅花鹿、麋鹿等野生動物,成堆成片的田螺殼、零星的蚌類等水生動物[9]欒豐實主編.考古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郭榮臻在對河南新密史前先民食物結構的研究中,對古城寨遺址的既有研究成果進行綜合梳理,認為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地處中原腹地的新密地區已經融入史前食物全球化、青銅時代全球化的浪潮之中[1]陳微微.河南新密古城寨遺址出土植物遺存分析.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陳微微,張居中,蔡全法.河南新密古城寨城址出土植物遺存分析.華夏考古,2012,(1).。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該遺址不同時期先民的生業模式和食物結構。但同時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樣遺跡有限,關于炭化植物遺存比重的認識還不能坐實。此外,由于發掘年代較早,如今常用的微體植物遺存考古方法淀粉粒、植硅體等,人與動物骨骼穩定碳氮同位素等研究手段尚未使用。
(七)環境考古
在上述研究以外,第四紀環境學界對河南省新密市及其臨近的溱水、雙洎河等流域開展多次環境考古工作。張震宇等對雙洎河流域的地質、地貌及32處考古學文化遺址進行野外調查,認為古城寨屬于分布在受水流作用痕跡明顯的馬蘭黃土臺地遺址[2]賈世杰.鄭州商城炭化植物遺存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許俊杰等對新密市溱水流域進行野外考察,分析相關地層剖面,認為古城寨遺址位于溱水下游東岸的二級階地上,西靠溱水,東望溱水、黃水兩條河流之間的平緩黃土梁[3]蔡全法.雙洎河流域史前農業及人類膳食結構之探索.黃河科技大學學報,2008,(5).。這些研究多是廣域范圍內的調查取樣分析,就古城寨遺址本身的環境考古個案研究亟待展開。
三、相關思考
總的來看,近20年來,學界對新密古城寨龍山時代城址展開了較為詳實、深入的研究,多數研究者將歷史文獻與考古材料相結合,在既有的文化面貌、性質族屬、筑城技術等基礎上,又開創環境、生業、社會、聚落等方面的研究領域,從中提取大量的古代社會信息,獲得較多的研究成果與階段性認識。但需要指出的是,囿于種種原因,目前對整個遺址的研究尚未能充分展開,在個別問題認識上,短期之內也難達成共識。
1.就田野考古工作和發掘材料公布程度來看,發掘多年來,僅有龍山時代城址的材料得到較大程度披露。學界對該遺址其他幾個時期文化面貌、聚落布局、社會經濟狀況等諸多方面的認識還很有限。隨著新的考古工作的開展與發掘資料的逐步公開,該遺址及其相關的社會歷史狀況將更加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2.就多學科合作研究的力度來看,由于發掘時還處在20世紀末,為數不少的新方法尚未在考古發掘中得以推廣、運用。以生業考古為例,植物考古方面,雖然采集了部分樣品進行浮選工作,但采樣數量有限,微體植物遺存層面的植硅體、淀粉粒、孢粉等方面的研究暫付闕如;動物考古方面,系統的骨骼鑒定、統計分析結果并未公布;人與動物骨骼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方面的工作亦未展開,在今后的發掘研究中,若能有針對性地開展這些工作,有利于對先民生業模式與食物結構的深入認知。又如環境考古方面,就單個遺址的環境考古工作尚未開展,在后續的考古發掘與研究中,若能盡可能多使用地質學、環境考古的相關方法[4]郭榮臻.河南新密史前先民食物結構的考古學觀察.農業考古,2018,(3).,結合發掘工作科學系統采樣,或能對遺址本身的環境演變與人類回應有更新的認識。此外,隨著學科的發展,其他領域的多學科方法[5]許俊杰,莫多聞,王輝等.河南新密溱水流域全新世人類文化演化的環境背景研究.第四紀研究,2013,(5).可以在新的發現與研究中發揮更大作用。
3.就聚落考古研究來看,在社會組織結構的視角下,微觀聚落形態、宏觀聚落形態的分析亟待展開,聚落內部人與人的關系、聚落之間人群的關系有待解答;充分發掘聚落考古潛力,對科學采樣所獲的動、植物遺存及人工制品進行空間分析,以便對資源、環境、生業、社會進行綜合研究,最大限度地發揮人工、自然遺物的潛力,最大程度地提取信息,或許有利于對當時社會的進一步認識。
4.就公共考古教育來看,還有待進一步加強。眾所周知,向公眾宣傳考古發現、普及考古知識,在提高公眾文化遺產保護意識、傳承弘揚歷史文化方面有重要意義。近年來,新密地區的考古發現日漸增多。如何將這些考古成果向公眾推介,使考古學發揮更加重要的社會職能,是需要予以思考的。
結 語
河南新密古城寨遺址發現以來,學界對其開展了較為詳實地研究,涉及多層次、多維度、多方面,取得一系列階段性認識,尤其是對該遺址龍山時代城址的認識已經很深入。這些研究對我們認識、了解該遺址的相關社會歷史狀況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囿于發掘較早,部分新的科技手段、新理念、新方法尚未在該遺址的研究中發揮作用,隨著新一輪發掘工作和研究的開展,該遺址的面貌將更加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