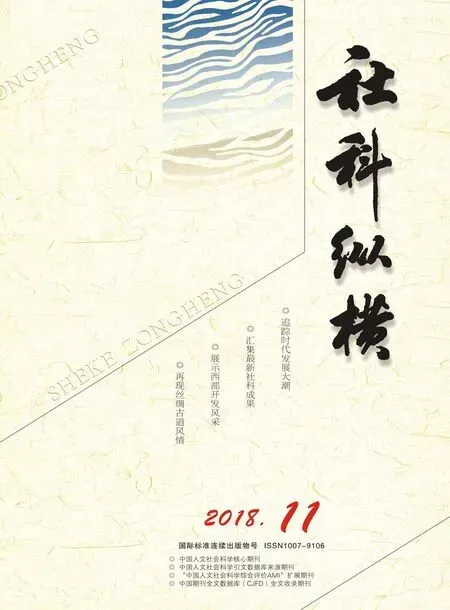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書寫方式批判
——基于羅伯特·揚后殖民理論的考察
黃成華
(廣東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廣東 東莞 523808)
進入20世紀30、40年代以來,國際局勢跌宕起伏,激流涌動。伴隨著世界范圍內力量的此消彼長,殖民地國家紛紛加入了爭奪民族自決權的斗爭中,從而開啟了全球范圍內的去殖民化。“被殖民者不再等待帝國列強的工人階級的解放;相反的,被殖民者現在扮演一個重要而主動的角色,要在各殖民地啟動歐洲和世界革命。殖民地必須先有民族主義,才能觸發國際革命,而殖民地就變成革命潛力的一大關鍵。”[1](P108)殖民地國家的人民通過艱苦卓越的斗爭,紛紛掙脫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枷鎖,在政治上獲得民族自決權。爾后,后殖民國家不斷加強社會各方面的建設,使整個社會面貌發生了重大變化。后殖民國家作為國際社會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其作用日益凸顯。殖民主義統治由鼎盛走向衰落,陷入令人窒息的低潮期。“后殖民是西方開始沒落的標記。”[1](P66)殖民主義統治在世界范圍內逐步降下了帷幕。“如果殖民歷史,尤其是19世紀的殖民史,是一段帝國的侵占史,那么,20世紀的歷史已經見證世界上各民族紛紛討回屬于他們自己的權力和掌控權。后殖民理論本身就是這段認證過程的產物。”[1](P5)殖民地國家雖然經過政治獨立、發展民族經濟、法律賦權等獲得獨立的政治、經濟和法律地位,但是在文化心理上卻依然屈從于西方國家,處于壓迫性的文化境遇之中。西方國家與后殖民國家之間的文化勢差并沒有隨著后殖民國家取得政治獨立而消失,并且有日趨擴大的趨勢。這種不平衡的發展狀態引發了諸多學者的批判。作為后殖民主義批判的代表——東方主義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展壯大的。東方主義批判旨在喚醒后殖民國家人民的身份意識,捍衛其文化身份的獨特性。然而,東方主義并不能為后殖民國家進行文化脫殖提供科學的理論指導。后殖民國家的一些學者將來自于西方國家的話語系統炒作為思想變革和學術創新,而無視甚至拋棄了自身的文化傳統。這些學者不自覺地進行了文化上的自我閹割,擔任了自身文化傳統的掘墓人。
一、歷史書寫權斗爭的凸顯
(一)后殖民國家歷史書寫權的旁落
后殖民國家在被殖民時期,其歷史書寫就受到殖民者的話語浸淫,“語詞和思想邏輯”受到霸權思維的污染,歷史書寫權旁落,導致其歷史文本不能客觀公正地反映其歷史發展進程。后殖民國家在歷史書寫上存在著主體缺位的悲慘現實。“殖民主義不但涉及物質上的領土,而且涉及心理上的殖民主體關系,不但涉及經濟和工業化,而且涉及文化關系。羅伯特·揚對于西方歷史進行了深入的考察,發現那里存在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對于‘他者’的欲望。”[2](P11)長久以來,西方國家一直致力于將經濟和政治優勢轉變成文化優勢和話語優勢,通過源源不斷地生產出霸權性的話語而掌控世界歷史的書寫權。世界歷史書寫一直隱藏著西方中心主義的預設話語邏輯。西方中心主義支配了全球史的書寫方式,全球范圍內的權力格局通過知識話語傳達出來。只不過在殖民主義時期,西方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優勢顯得更為直接裸露。而在喪失國際政治優勢之后,西方國家干脆將國際斗爭的重點放在文化領導權上,宰制與把持“建制化知識場域”,開創出“殖民主義的語言政治”。頗具歷史反諷意味的是,后殖民國家雖然獲得了政治獨立,但在經濟上依然依賴宗主國,在文化上還難以改變對宗主國的依附性關系。由此可見,盡管西方國家的海外殖民地不斷減少,但是對后殖民國家的文化滲透卻一直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著,并且在文化領域形成了宰制與被宰制的關系。這既是西方國家一貫的政策使然,也是其當下的優化選擇。在殖民主義統治結束以后,后殖民國家勢必將反殖民斗爭從政治領域拓展到文化領域,把如何重奪歷史書寫權提上議事日程。“我們現在要在理論上做的事,是重新認識整個殖民現代性的計劃與實踐,它不單是西方資本主義所進行的特定軍事與經濟策略,同時它也透過對知識的特定歷史論述不斷地自我建構與被產生出來,而這種論述扣連政治權力的運作:簡而言之,殖民不只是實體的暴力,也包括在知識上的暴力。”[1](P391)
(二)西方國家推行的文化帝國主義
“反殖民主義除了是一種政治的工作之外,也是一種經濟的、科技的和文化的工作。”[1](P383)這意味著對殖民主義的批判是一項系統性的基礎工程。由于殖民主義不但推崇實體暴力,而且推崇知識暴力,這使得殖民地的解放具有多重內涵,即不但要贏得政治獨立,而且要獲取文化自主權。“政治上的去殖民一旦開始,跟著就必需是文化的去殖民;將西方去殖民,將它解構。”[1](P67)換言之,進行文化批判具有歷史的順延性和邏輯的合理性。西方國家對后殖民國家赤裸裸的外在殖民盡管已經不多見,但是在經濟剝削、政治壓迫之外強化了文化壓制這種新的殖民主義方式,使得文化帝國主義成為奠定西方國家全球霸權的重要基點。文化帝國主義是知識與權力合謀的典型表現。東方主義成為“西方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并為帝國主義殖民行徑進行哲學辯護,長期參與到對東方的抹黑事業中。“薩義德有關于知識話語條件的最有意義的觀點是,東方主義‘不但創造了知識,而且創造了他們所描繪的現實’。與此同時,他最為重要的政治論述是,作為一個有關東方的知識系統,東方主義與社會經濟和政治機構有著密切的聯系,我們能看到,它預先為殖民主義辯護,同時又促進它的成功運作。”[2](P185)東方主義勾勒出了西方與東方之間的不平等的歷史書寫格局。理性支配下的宏大秩序確立了西方/東方、先進/落后、殖民者/被殖民者、主權者/民眾之間的秩序體系。“任何在西方被視為是知識上或政治上重要的東西,不可能與(所謂的)第三世界有關聯,即使它本身是由三大洲里眾多地點與位置中的某一個為基礎,進行對西方的批判。換句話說,后殖民理論‘必然’是歐洲的,倘若它曾對西方造出如此大的沖擊。”[1](P421)歷史編纂學中充斥著西方對東方的歧視性話語,存在著西方對東方的偏見。世界歷史被書寫成基于歐洲文化意識的歷史。
二、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書寫方式之批判
羅伯特·揚是當代的后殖民知識分子,執后殖民主義理論之牛耳。《白色神話:書寫歷史與西方》、《后殖民主義——歷史的導引》等是其扛鼎之作。以薩義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為代表的東方主義對標榜歐洲中心主義的西方知識進行了批判。羅伯特·揚繼承了東方主義的批判風格。如果說薩義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人是從西方外部開啟了對西方霸權話語的批判性反思,那么白人出身的羅伯特·揚卻顯然是從西方內部對西方霸權話語的批判性反思,是“西方反思性的學術話語”。他們都致力于矯正不平等的歷史書寫權力,解構話語霸權背后的西方立場。
文化殖民一直是殖民侵略的副產品。“關于文化帝國主義,有兩種不同的認識:一種認識強調經濟控制的首要地位,認為文化支配的目的是為了經濟控制;另一種認識則強調文化支配的首要地位,認為經濟控制的目的是為了文化支配。”[3](P122-123)羅伯特·揚顯然認同后者。這樣一來,文化帝國主義的興起并不意味著西方國家的根本意圖發生改變,而只是采取了更為隱蔽的方式。殖民主義批判對歐洲中心主義的白人歷史書寫提出了挑戰,其興起有利于“重置歐洲的知識系統”,顛覆歷史書寫中的中心-邊緣結構。“據賽薩爾觀察,僅有的歷史都是白人的歷史,在這種情形下,怎樣書寫一部新的歷史呢?與文學與文化理論中的主流政治問題相比,殖民主義結構的批判似乎只是一種邊緣的活動,只是迎合了少數群體或者那些對于殖民歷史有特殊興趣的人。不過,雖然只是涉及了大都市歐洲文化的地理邊緣,它的長期策略卻是引起歐洲思想、特別是歷史編纂學的根本重建。”[2](P171)
(一)知識與權力的合謀
“福柯在《知識考古學》等著作中提出,不存在絕對客觀的知識,知識的生產、傳播和消費始終與權力糾葛在一起。”[3](P121)福柯創造性地開拓出“知識——權力”的分析路徑。“根據傅柯所言,論述總是涉及一種暴力的形式,即它會把自身的語言秩序強加于世界:為了被承認為正當合法,知識必須符合論述的范型。”[1](P393)知識與權力相互糾纏,難解難分。“薩依德運用‘論述’的概念分析東方主義,使他得以證明在某些特定的觀念、語言及各種再現的形式中,都具有一致的論述對應印記,這是各式各樣的文本中常見的,其范圍之廣橫跨人文與社會科學的領域——從旅行見聞到歷史,從文學作品到種族理論,從經濟學到個人自傳,從哲學到語言學。所有的文本的分析都可以從它們的語言及主題中共有的,一致的殖民意識形態著手,這種知識形式是在權力結構——也就是殖民宰制——的配置與運用之同時發展出來。”[1](P395-396)然而,知識與權力的聯姻并不是在平等基礎上進行的,而是權力借用了知識貌似客觀的外殼。權力的狡猾套用了理性的狡計。“德里達在《結構,符號和操作》一文中所實行的著名解構,向我們展示了人類學知識是如何構成的,它雖然常常以科學客觀的面目出現,事實上卻受到了它仍未意識到的問題的制約:中心的哲學范疇——德里達繼續將其表達為歐洲中心主義的問題。對于中心和邊緣的辯證法的分析,既是地理的,也是概念的,表達了大都市和處于地理邊緣的殖民地文化的權力關系。”[2](P26)顯然,權力支配了知識的生產與再生產機制。權力對知識話語的滲透既改變了話語的存在樣態,也改變了權力的運作方式。我們以前很少意識到知識所隱藏的潛在暴力。知識與權力的聯姻產生出諸如“東方主義這種片面知識”的怪誕物,強化了對社會控制的力度,但對“知識共謀形式的無情剖析”削弱了“對于知識整體系統基礎的不信任”。
福柯的話語構成理論可以應用于殖民話語的分析。“作為地域的東方是一種客觀實在,文化視野中的東方則有賴于人們的建構。”[3](P123)殖民話語體現出“自我”對“他者”的壓制。“采用階層化語言的制度性權力結構,將(過去或當前的)殖民勢力的宰制語言強加在當地語言之上。”[1](P401)“殖民話語并不僅僅是表現他者,毋寧說它同時在設計和否定其差異,一種按照拜物教的無法協調的邏輯所制造出來的矛盾結構。”[2](P203)“《東方主義》分析迫使我們承認,所有的知識,即使在其非常正式或‘客觀’的結構中,都可能被污染了。”[2](P182)東方主義“既是一個知識(薩義德所說的‘顯性的東方主義’)的意識體,又是一個夢想和欲望(隱性的東方主義)的無意識體。”[2](P201)東方主義人為建構出東西方之間的文化差異,使得殖民地國家對自身的文化身份的認同深陷東方主義的理論旋渦。知識與權力的合謀扭曲了真的表現形式。殖民霸權向真的領域的擴展和蔓延,使得殖民地國家的話語系統深深地打上“知識暴力”的烙印,在殖民地國家的文化領域野蠻生長出帝國主義霸權之果。殖民主義將權力領域的斗爭轉引到了知識領域,將經濟和政治干預發展到了文化干預,在“壓迫性的政治經濟權力結構”之外建立了非對稱的話語壓制系統,建構了“帝國主義認識論暴力”及“支配性的東方主義話語圖景”,從經濟帝國主義發展到文化帝國主義。這種擴張既符合擴張范圍逐步擴大的自然本性,更凸顯資本的貪婪本性。資本為了確保其能夠始終增值,夯筑起從經濟、政治到文化(知識系統、話語系統等)的堅強堡壘。知識之所以受到權力的污染,是由于資本與強權的結合。有關東方主義的理論知識成為帝國主義殖民行徑的辯護工具。“殖民論述絕不是只涵蓋一套意識形態的(錯誤)再現:它的陳述過程永遠是做為歷史行動在運作,在殖民統治的高壓機制下產生特定的物質效應,殖民論述陳述過程的位址與權力的形成也同時在被殖民的從屬身上引發物質與心理效應。”[1](P417)
(二)“自我”對“他者”的新壓制
殖民者不但要占領殖民地國家的領土,控制其經濟命脈,而且要搶占其歷史書寫權,建構與帝國主義工程相稱的敘事模式。這是“帝國主義生產空間”的需要。“在這一點上,斯皮瓦克和巴巴是相同的,即認為帝國主義不僅關涉領土和經濟,而且不可避免地還是一種主體構建工程。”[2](P225)而這種主體構建是與認同“自我”與否定“他者”的野蠻界分相關聯的。“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關系,依然按照黑格爾主人/奴隸結構(雖然第二世界的問題從未弄清楚)進行分析,黑格爾對于農業社會(不具有歷史)和工業社會(具有歷史)的描繪,被運用到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上。”[2](P164)
“政治和知識已經按照黑格爾的辯證法以及陽物-邏各斯中心主義運轉,無論是馬克思主義歷史、歐洲殖民主義統治,以及伴生而來的種族主義、東方主義知識還是典型的父權制與殖民主義的結合,以及弗洛伊德將女性視為未開墾的大陸的概括(‘在他的心目中,她是男人喜歡占有的陌生之物’)。”[2](P4)自我中心主義與邏各斯中心主義、種族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歐洲中心主義、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等具有邏輯上的同構性。東方主義理論延續了二元對立的認識論框架,使得歷史成為“自我”的歷史,“他者”沉默不語、消失不見了。“東方的他者毋寧是一個幻想與建構的對象。”[1](P406)而在遵循這種原始而粗獷的歷史書寫邏輯中,則滲透著“自我”對“他者”的權力壓制。“這種結構不像開始想象的那樣,來自于一種模仿中世紀騎士搏斗的權力關系的幻想,而是來自于按照主體想象客體、同一/他者的辯證法結構進行運轉的知識構成的現象描述,在這種結構中,他者首先由被吞并之前的同一的否定而構成。在這里,不可能有對話和交換。”[2](P8)“自我”為“他者”預設了發展傾向,從而從根本上剝奪了“他者”的本體論尊嚴。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對類似圓形監獄的權力裝置進行了描繪。在福柯的權力裝置中,主權者與囚犯之間不但存在著監管與被監管的關系,而且通過有效的權力結構設置提高了監管效能。這種權力裝置在話語領域表現為以“自我”為中心,不斷強化“自我”對“他者”的監督與控制。而充滿污蔑性的殖民話語顯然就是權力裝置的重要表現形式。殖民者對東方的書寫充斥著歧視性的話語。“根據物質上的不平等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沖突來構筑。國家借由直接的武力來維持權力,隨之而生的司法與法律結構也是將國家的宰制合法化。國家的論述強化了其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而這上層建筑在殖民的情況下將包括一套利于殖民者的語言和文化的價值體系,并貶抑被殖民者的這一切。”[1](P401)“自我”對“他者”的矮化和丑化都屬于殖民話語的策略性動作,以促使“他者”自我辯解的話語趨于湮沒和滅絕。“自我”對“他者”的策略性盲視,始終滲透著“自我”對“他者”的排除和邊緣化的努力。“在何種意義上,‘另類他者’只是簡單地表現了尋找西方自我想象的他者的自戀欲望。”[2](P233)
文化領域承載了權力斗爭方式轉移的空間需要。這樣一來,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形成的權力結構中,不同領域在權力斗爭中的位次序列也在發生此消彼長式的變化。“從主體的社會生產來看,傅柯的《瘋癲與文明》(1961)是一個奠基型的研究,探討社會如何生產出排他的形式。”[1](P406)在“自我”與“他者”之間言說與被言說、書寫與被書寫的關系中,話語移居前臺,而權力則退居后臺。在話語與權力的一進一退中,則是權力技術的提高。伴隨著權力機制從顯性控制向軟性控制、從硬性統治向軟性治理的轉變,以及權力樣態從經濟和政治控制權力向文化控制權力的轉變,“他者”的主體意識則被遮蔽得嚴嚴實實,遞減法把“他者”剝離得體無完膚。“在等級組織的關系中,他者正是被統治、命名、定義和指派的東西。按照黑格爾所建立起來的秩序運轉的可怕的簡潔性,社會在我眼前走過,它完美地復制著垂死掙扎的機制:從‘人’到‘無足輕重的人’到‘他者’這樣一種減法——一種無情的種族主義故事。”[2](P3)如果說在知識與權力聯姻之前,“他者”的反抗有明確的指向目標,那么,在知識與權力聯姻之后,“他者”的反抗則變得漫無目的。不但反抗從有的放矢變成無的放矢,而且反抗也從集群行為變成散兵游勇的單兵作戰。因而,權力技術的提高,不但表現在“自我”的狡猾上,而且表現在“他者”的削弱上。“自我”對“他者”采取排除式掠奪的方式。“簡言之,詹姆遜常常引用的‘歷史自身’是誰的歷史呢?很明顯,沒有人允許歷史存在于‘我們’之外——那是西方文化及西方視角,對于詹姆遜來說似乎就是美國。就這樣,這種修復工程簡單地復制了歐洲殖民主義的歷史和宏大的資本主義規劃;在這里,歐洲以外的世界,歐洲的他者,被逐步地吞沒于帝國之中,不同的文化被詆毀,不同的歷史被否
定。”[2](P163)
同一性哲學采用排除性納入的方式施展同一性暴力。要實現“自我”對“他者”的合并,殖民話語的生產機制就需要持續不斷地運行下去,讓來自“他者”的認識論批判還未興起就已夭折。一旦這種偏執性的話語生產變得不可持續,長期精心營建的文化帝國主義就會瞬間坍塌。西方發達國家致力于建構和維持不平等的制度,以便合法合規地享有制度所帶來的紅利。阿爾都塞在一篇文章中“提供了一種依賴于主體和意識形態范疇的制度權力理論。福柯對這種理論的不滿,不僅僅是因為它建立在科學/非科學區別的基礎上(在福柯看來,它只是某種特定話語形態的產物,這種話語形態聲稱追求真實,卻不涉及任何有關于真理或客觀性的認識論問題),而且也因為它在權力的決定者和個人主體之間的內在/外在結構中,建立了一種作為次等中介的意識形態概念(正如阿爾都塞所質詢的)。”[2](P115)在日積月累的生產情境下,“他者”被覆蓋上層層遮蔽物。文化帝國主義不但使得西方能夠建構東方,而且使得東方依賴于西方的文化建構,最終從外殖民轉向內殖民,文化帝國主義最終變成西方與東方內外共謀的事業。“自我”盡管對“他者”實施著訓導的策略,而“他者”在對訓導的演練中也在進行著解構。而福柯對書寫“他者”歷史的愿望,對傳統歷史編纂學的批判,就隱含著對“自我”與“他者”之間平等地位的呼喚,以及要重構書寫與歷史的關系。“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福柯對于常規歷史形式的不信任,成了他的研究規劃中的不變線索,就像他堅持認為,他的歷史方法僅限處理歷史文獻和實踐中的特定問題,以便使它們容易理解——這與社會科學所提出的問題可以構成比較。”[2](P111)
(三)本體論的潛在暴力
殖民主義淵源于西方悠久的本體論傳統。“獨特的后殖民認識論和本體論的發展,和政治行動主義并不沖突。”[1](P284)本體論預設了“自我”與“他者”的關系模型,將二者之間的對立絕對化。“在西方哲學中,當知識或理論理解他者的時候,他者的差異就會消失,成為同一的一個部分。列維納斯認為,這種‘本體論帝國主義’至少可以追溯到蘇格拉底,而在最近的海德格爾那里也可以發現。在所有的情形下,他者都被同化為一種壓制的形式:本體論成為一種權力哲學,在與他者關系中的自我中心論,通過將他者吸收為自我而完成。”[2](P18)哲學領域中的普遍整體性與政治領域中的霸權體系具有邏輯上的同構性,即本體論、種族和性別理論、東方主義具有邏輯上的同構性。“西方女性主義話語不但是種族中心主義的,而且在特定的語境中,它自身就顯示出一種殖民主義話語的當代形式。”[2](P229)
“后現代主義可以被最恰當地定義為一種歐洲文化意識:它再也不是世界上無容置疑的統治中心。”[2](P27)“后現代主義早已被視為對歷史的回歸,盡管只是作為一種再現的范疇。”[2](P932)“可能正如我們更早時候所提出的,后現代主義——在其中老帝國主義地圖已經失去了——不但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條件,也是歐洲中心主義條件。用詹姆遜的術語來說,后現代只不過是東方主義的辯證顛倒:一種迷失方向的狀態。這意味著歷史不可能再是一個單獨的故事,盡管西方仍在繼續密謀其‘巨大的、未競的拓殖大業’。”[2](P169)列維納斯在批評西方本體論傳統時,也批判了西方自由觀念的狹隘性和虛妄性。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等觀念都是建立在本體論的哲學框架之上的。“因為自由是由自我占有來維持的,而這種自我占有會擴張到任何威脅到其身份的東西。在這種結構中,歐洲哲學復制了西方外交政策,其國內民主是經由國外的殖民或新殖民壓迫而維持的。列維納斯反對建立在自我利益基礎上的自由能夠達到正義,在他看來,正義尊重他者的差異性,只有通過對話的不平衡才能提出。”[2](P19)列維納斯擊垮了西方世界的自戀心理。“列維納斯將自我中心卻外向擴張的知識形式,與清晰地體現在西方自我迷戀之中的自我中心的哲學聯系起來。”[2](P24)作為知識的歷史同樣重復了知識的敘述方式。“因為本體論涉及一種對于他者的倫理-政治暴力,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一種威脅,列維納斯倡導恰當位置的倫理學,以對于他者的尊重代替對于他者的控制看,也倡導一種不是作為否定和吸取而是作為無限分離的欲望理論。”[2](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