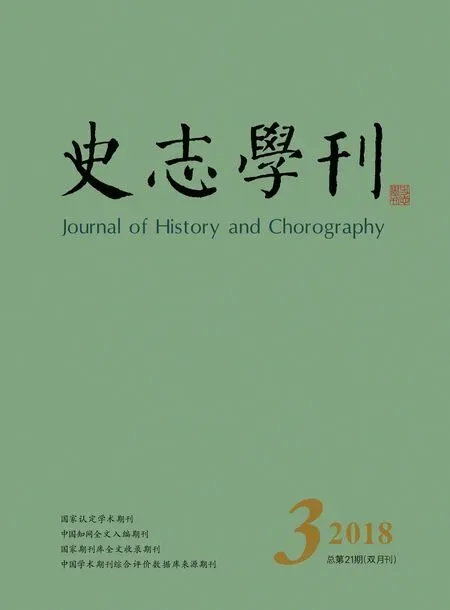關于侵華日軍在山西施放生化武器的調查研究
張泓明
(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太原030006)
生化武器是細菌生物武器與化學武器的簡稱,顧名思義就是通過致命性、致病性的有害細菌生物或化學物質,致人于死命的特殊武器。生化武器與核武器一起,被簡稱為NBC,即Nuclear,Biological,and Chemical weapons(“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1]亦被稱為ABC,即Atomic,Biological,and Chemical weapons(“核、生物和化學武器”)的英文縮寫。的英文縮寫。生化武器是近代科學技術在戰爭中的創造品,其殺傷力驚人,且造價低廉,被譽為窮國的核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戰(簡稱“一戰”)之后的1925年,各國商議之下,起草了一份《關于禁用毒氣或類似毒氣及細菌方法議定書》,禁止生產和使用生化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戰(簡稱“二戰”)時日本清楚知曉其國力不足以支撐其擴張野心,從而尋找特別手段來跨越這一鴻溝,這一特別手段就是化學武器和生物武器。二戰后,日本對曾經是否使用過生化武器一事諱莫如深,而史學界也為缺乏詳實證據,一直就日本是否在戰爭中使用過生化武器一事爭論不休。而上世紀80年代之后,立教大學教授粟屋憲太郎、中央大學教授吉見義明等日本進步史學家陸續發現日本化學戰資料,日本國內也陸續對日本開展的細菌實驗進行追蹤揭露。
而單就生化武器這一課題,國內史學界給予了長期跟蹤關注。南開大學俞辛焞教授早在1985年10月就發表了題為《侵華戰爭時期日軍的化學毒氣戰》[2]俞辛焞.侵華戰爭時期日軍的化學毒氣戰.日本研究,1985,(3).的論文,內容除揭露日軍在侵華戰爭中的罪行之外,重點介紹了日本史學界關于日本侵華毒氣戰研究的進展。隨后各地都陸續開展了對日本侵華時期生化武器的研究,其中中國東北作為最早遭受日本侵略的地區,相關研究積累尤為厚重,成果也頗為豐碩。大致說來,生化武器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六個層面的問題:日軍關于生化武器的研究;日軍生化武器的使用;日軍生化武器的動物與人體實驗;生化武器戰場上的使用證據以及對平民的暴行;戰后盟軍對于日本生化武器使用的追責;生化武器相關的訴訟與賠償請求。
而國內長期針對生化武器的研究現狀主要包括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專業性強,研究深入。國內關于日本侵華生化武器的研究常就其中某一個議題,如細菌(生物武器)或毒氣(化學武器)進行比較深入和翔實的論證與探討,很多內容如“731部隊”的人體試驗甚至為一般大眾所熟知[1]此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有:謝忠厚.侵華日軍細菌戰研究述論.抗日戰爭研究.楊彥君.掩蓋與交易:二戰后美軍對石井四郎的調查.抗日戰爭研究,2013,(2).2013-5-26.。第二,涉及面廣,上述六個方面都有涉及,特別是重點反映日本侵略暴行,關于日本生化武器研究、人體試驗,以及對于平民的暴行方面的研究最為充實。
然而問題在于,以上研究生物武器、化學武器的研究通常是分別獨立進行的,這樣做的有益之處在于便于深入探討某一問題,也同時可以深刻認識加害方的主觀罪行,但同時忽略了受害方的認知和感受。第二,地域層面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深入。現有從事研究的主要地區是東三省,由于東北受日本侵略時間較長,日語教育與日本研究機構的人才儲備較多,從而研究也開展得比較深入。而同樣是遭受日本軍國主義荼毒的重點地區,山西省對于日本生化武器的已有研究很少,且很多是在其他資料中順便提及的。這一現狀使得對于山西所遭受的生化武器傷害,有必要專門擬文進行探討,從受害者角度深入挖掘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行的同時,也為地方史研究資以必要的補充。
一、日本生化武器出現的背景
眾所周知,核武器最早為美國開發、使用,而化學武器最早被德國使用,而日本則是細菌武器最早開發和使用的國家。三者都為20世紀以來創制和使用,作為特殊秘密武器都被期望在戰場上取得意外效果,且都需要科學領域相當程度的積累,鑒于使用效果和威力,進而都成為了強國對付弱國的武器。
日軍在一戰中并未直接赴歐洲參戰[2]一戰期間,日本曾應列國要求,派遣海軍艦隊前赴地中海與印度洋擔任警戒和護送任務.,但卻時時刻刻關注著一戰的走向。一戰中,參戰國為了在戰爭中取得勝利,都采取了動員全國所有資源的總體戰體制。戰爭之殘酷、時間之長、動員資源之多都遠遠超乎想象。某日本軍人曾比喻道:如果說中日甲午戰爭是壓拇指,那么日俄戰爭就是掰手腕,而總體戰更是遠遠超過之前的規模,可以說相當于兩位力士兩手相交、竭盡全力的大相撲[3]戶部良一著.韋平和孫維珍譯.日本陸軍史—近代化的異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P227)。對于當時的日本而言,差距是全方位的。工業制造能力、基礎科學、資源動員能力方面都與世界先進國家有著全方位且難以彌補的巨大差距。為了縮小與世界一流國家之間的軍隊差距,唯一的辦法就是增加軍費預算,推進日本軍隊的近代化和科學化[4]日本陸軍內存在著爭鋒相對的意見,一方面以宇垣一成為首,主張強化經濟實力,儲備力量為未來的總體戰爭作準備,而另一方則強調盡量保持軍事實力,一旦開戰時則通過速戰速決方式解決戰斗,而實力的不足則通過用精神、信仰補充。這兩種意見后成為日本陸軍中“統制派”與“皇道派”思想分歧的來源.。但一戰之后日本政治局勢不穩,經濟上經歷多次衰退,無力支撐巨額軍費。在這樣的背景下,生化武器進入了日本陸軍上層的視野。
對于生化武器,以下三個背景值得注意:第一,國際上已經達成基本共識,這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應予絕對禁止,導致生化武器的研究和實驗都必須秘密進行;第二,生化武器的使用開發針對國都是軍事實力強于日本的國家,既需要在戰場上不斷檢驗、改進,又要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第三,有大量科學工作者、醫學家參與生化武器的研究開發,對其所從事的工作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這也為搜集生化武器的使用證據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僅就現有資料判斷,侵華日軍的確使用過生物化學武器,且山西遭受生化武器侵害尤其嚴重。日本學術團隊赴山西調查受害者情況得到的口述調查信息證明了這一點。
二、日本生化武器的開發與演練
日本開發生物武器與化學武器的背景相類似,都是在一戰戰場上見證生化武器巨大的殺傷力而激發的,其中化學毒氣武器開發的時間略早。
早在1917年10月,日本陸軍軍部就命令陸軍技術審查部進行毒氣研究,同時在陸軍軍醫學校設置化學武器研究室。1921年,炮兵中佐久村種樹在參觀歐美的毒氣相關設施后回到日本,向陸軍首腦報告了毒氣研究的必要性,又在陸軍科學研究所第二課內設置化學武器班,久村種樹任主任。1923年成功合成光氣和芥子氣,1924年又成功合成路易斯氣。
1925年,陸軍大臣宇垣一成將裁撤下的部隊經費用于充實新武器的研究,以及部隊現代化裝備,即日本以“宇垣裁軍”為契機,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生化武器開發。隨后在這一背景下,日本掌握了毒氣武器和毒氣戰的基礎方法,化學武器班也升格為陸軍科學研究所第三部。1928年7月,陸軍在廣島縣大久野島開設了毒氣武器工場“忠海武器制造所”,并于1929年5月開始生產。與此同步進行的則是毒氣戰的相關教育問題,1933年8月1日,陸軍習志野學校作為毒氣戰教育和毒氣武器運用研究的基地成立。1939年,以東北齊齊哈爾關東軍技術部化學兵器班為基礎成立化學部(516部隊),此外為進行毒氣戰的實驗和演習,又在富拉爾基成立了練習隊(526部隊)。由此,陸軍實施毒氣戰的系統基本完備。
而日本生物細菌武器的開發則稍晚于化學毒氣武器,是由軍醫石井四郎[1]石井四郎(1882-1959),日本陸軍軍醫中將,畢業于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在微生物研究領域取得博士學位,也是最早提出創建細菌戰部隊者.一手促成的。石井四郎在學術界暫露頭角后,1928年赴歐洲考察,回國后四處宣傳研制細菌武器的重要性,得到了日本陸軍上層部分人士的認同。1932年東京陸軍軍醫學校設立“防疫研究所”,后又在哈爾濱市北陰河附近設立細菌兵器防衛研究所,石井本人化名東鄉初,研究所也以東鄉部隊為代號。1936年以此為基礎升格成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隊,按照日本陸軍習慣,這一部隊同時也被稱為“石井部隊”,1941年被冠以“滿洲731部隊”的稱呼。731部隊由8部分組成,其中第1部至第4部是核心部門,分別為細菌研究、實戰研究、容器設備制造[2]對外稱為制造石井式濾水器,也是作為為防疫給水部隊的招牌機構,但同時也參與制造鼠疫桿菌的容器.、細菌制造;除核心部門之外,還包括教育部、總務部、材料部、診療部,診療部除擔當相關部隊人員的診療服務之外,還在收容人員中進行人體實驗。隨著戰線的擴大,1940年12月2日又正式設立四支部,即牡丹江643部隊,林口162部隊,孫吳673部隊,以及海拉爾543部隊。以上部隊作為對蘇戰爭的預備部隊,被統稱為659部隊。而除此之外,還有作為731部隊第五支部的大連衛生研究所,在長春還成立731部隊的兄弟機關“關東軍軍馬防疫廠”,簡稱100部隊,這一機構在研究動物防疫細菌研究的同時,也涉及人體研究。
而1940年前后,在731部隊的指導下,分別在北支那派遣軍、中支那派遣軍、南支那派遣軍下設立防疫給水部,即北京“甲”1855部隊、南京“榮”1644部隊、廣東“波”8604部隊,后又設立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簡稱“岡”第9420部隊,這些部隊之下又成立幾個或幾十個支部。這些部隊在731部隊的業務指導下,與該地區的陸軍醫院、同仁會醫院、滿洲醫科大學進行合作研究細菌戰。此外731部隊還通過石井四郎本人,與東京新宿區的戶山陸軍軍醫學校保持著密切聯系[3]『朝日新聞』1988年8月21日介紹了由山中恒發現的『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報告』61冊,明確證明了石井四郎與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的關系.。
日本生物武器與化學武器有以下幾方面相似點:第一,都是試圖通過低成本方式獲取大規模殺傷性的效果,都得到陸軍上層的大力支持;第二,日本大力研發生化武器是在國際公約明文禁止之后,生物細菌武器和化學毒氣武器的研發都是隱秘進行著的;最后,生物武器與化學武器的研發過程中,交叉性很多,如都需要相關學術界領域的研究人員和科學知識,都得到陸軍軍醫學校的大力支持,同時都需要進行反復嚴密的實驗等。從這幾個方面而言,生物化學武器開發利用,成為了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的幫兇。在生化武器具體研究實驗的過程中,516部隊與731部隊進行緊密協作,一方面聯手使用人體試驗可以更充分利用活人實驗材料,如凍傷實驗后再進行毒氣實驗;再者,兩者都為背負特殊使命的秘密部隊,戰后消滅罪行證據方面也進行了緊密協作[1]王宇王天蛟.略論516毒氣部隊與731細菌部隊的罪惡勾結.黑河學刊,2017,(5);此外,日本軍人回憶錄中也曾見到相關的口述記錄.。
但同時雙方又有一些不同之處:首先,毒氣武器已經在一戰戰場上進行過實踐檢驗,技術相對成熟,實戰配備、教育也準備得較為充分,但卻已為世界所熟知,很難達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反之,生物武器雖還只是停留在實驗階段,但卻在這一領域取得了部分領先。其次,化學毒氣武器機構、人員遠遠大于生物武器,已經具備一定實戰能力,且在掃蕩敵后根據地時收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而細菌武器的實戰效果欠佳。
三、日本化學毒氣武器與山西
日軍化學武器準備時間長,技術成熟,為了盡快檢驗實戰中的效果,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后,化學武器部隊于7月下旬被派往華北當地。7月28日支那駐屯軍發動總攻擊,追剿北京、天津附近的中國國民政府軍(宋哲元軍)。在此期間,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大將簽發署名日期7月28日的“臨命第421號指令”,向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發出指令,平津地區討伐戰中“可以適當使用催淚筒(綠[2]“黃”“紅”“綠”為毒氣制劑顏色,分別稱為糜爛性毒氣、窒息性毒氣,以及催淚性毒氣的代稱.其中,黃劑為致死性毒氣,而紅劑與綠劑根據使用量多少也有致死危險.筒)”[3]吉見義明,松野誠也編.解説『毒ガス戦関係資料Ⅱ』(不二出版、1997年)所收.(P244),這是現階段已確認的,最早準許使用化學武器的指令。參謀本部為對全華北的日軍進行統一指揮,1937年8月31日設置北支那方面軍(方面軍司令官為寺內壽一大將),原支那駐屯軍改編為第1軍,并與新編第2軍一起編入北支那方面軍麾下。隨后似乎北支那方面軍也得到了“綠劑”使用許可。可以確認的是,第二軍麾下的第10師團在1937年10月中旬至1938年5月之間,使用了“催淚筒”1619個[4]陸軍大學校『北シナ作戦史要』第三巻、防衛庁防衛研究所図書館所蔵.。
使用窒息性毒氣“紅劑”的案例則是第1軍在晉南進行的肅清戰,目標是遏制國民政府軍對山西省南部的反攻意圖。1938年4月11日,閑院宮參謀總長向北支那方面軍和駐蒙軍下達指令,指出山西省內可以使用“紅劑”,這一指示如下面現存全文所示:
一
大陸指第百十號指示
基于大陸命第三十九號及第七十五號,詳如左示
左方記錄范圍內可使用紅筒輕迫擊炮用的紅彈
(1)使用目的用于針對盤踞山區地帶匪徒的掃蕩戰
(2)使用地域山西省及其相鄰地區的山岳地帶
(3)使用方法 盡量與煙混用,對毒氣使用的情況嚴格保密,尤其注意不要留下痕跡
二
另附紅彈與紅筒交付情況
昭和13年4月11日
參謀總長載仁親王
北支那方面軍司令官伯爵寺內壽一閣下
駐蒙兵團司令官 蓮沼蕃殿[1]吉見義明,松野誠也編.解説『毒ガス戦関係資料Ⅱ.不二出版,1997.(P253)
從文件中可以看出,毒氣僅限于在難以發現使用痕跡的山西省及其附近的山地使用,這種特別在意使用隱秘性的作法,是大本營陸軍部(參謀本部)充分意識到國際法之后表現出來的。第一軍接到指示后,立即開始著手開展毒氣戰教育,其中就有“將使用地區的相關人等全部消滅,盡量不留任何痕跡。”以及“盡快將時間、地點、戰果等內容上報軍總部”等重點強調的內容[2]五月三日の第一軍命令「一軍作命甲第二三五號」の「別紙第三 特種資材使用ニ伴フ秘密保持ニ関する指示」、第一軍參謀部「第一軍機密作戦日誌」巻十四.同前所収.(P287-288)。施放毒氣后突擊,用常規武器“一舉消滅”受到毒氣困擾的中國士兵成為常用戰術。
1939年5月13日閑院宮參謀長向杉山元北支那方面軍司令官下達的“大陸指第四百五十二號”。大本營陸軍部指示,山西省內可以試驗式地使用糜爛性毒氣“黃劑”。
大陸指第四百五十二號 指示
基于大陸命第二百四十一號,詳如左指示如下
一 北支那方面軍司令官應在所屬占領地域內,研究黃劑等特種資材在作戰運用方面的價值。
二 右面所述研究應在左面的范圍內進行
1.使用時采取多種辦法盡量保密,特別是絕對不使第三國人受害,保密方面絕對不能留下瑕疵
2.盡量使中國軍隊之外的普通中國人少受害
3.山西省內偏僻處,為達到實驗研究目的,盡量限于特定地區,控制到最小限度。
二 以空投方式進行
昭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參謀總長載仁親王
北支那方面軍司令官 杉山元殿[1](P258)
從文件中可以看出,實驗地選擇在“山西省內偏僻地方”,且竭力強調使用的隱秘性。這里值得注意的是,“絕對不讓他國人受害”與“盡量不讓一般中國人受害”的對待方式有著明顯區別,從這一點也不難想象,普通中國人會被卷入到“黃劑”的攻擊中。
針對敵后八路軍的化學戰也使用了毒氣,迫擊第5大隊第2中隊在山西省和順縣萬山附近與八路軍129師約200人展開激戰,日軍為切斷八路軍退路,用2門迫擊炮向八路軍后方村莊發射“紅彈”,結果“敵人對毒氣并無基本常識,且無相應防護裝備,敵退路被我軍所布下的毒氣地帶所阻,迷失方向,我步兵部隊未失戰機,將其一舉包圍攻擊殲滅之。”從這次化學戰中也吸取了少許經驗,即“只要往村莊中射入少量毒氣炸彈,則會形成有效的毒氣地帶,可以肯定的是,這種化學戰戰術對于共產軍隊效果極佳。”[3]第36師団「小戦例集(第一輯)1942年12月」防衛庁防衛研究所図書館所蔵.吉見義明氏発見.
此外,敵后戰場的軍民也經常陷入毒氣攻擊中,民眾支持八路軍游擊戰,從而日軍對村落進行“殲滅”,斷絕該地區的戰斗能力就成為作戰的終極目標。為使殲滅戰進行得順利徹底,獨立混成第4旅團在初始之際就指示“各部隊應適當攜帶特種彈藥”,實際共使用“紅彈”43發,以及與“紅彈”有所區別的山炮“特種彈藥”3 發[1]獨立混成第4旅団「第一期晉中作戦戦闘詳報」、防衛庁防衛研究所図書館所蔵.吉見義明氏発見.。
這種結果的出現與陸軍上層鼓勵使用化學武器是分不開的。1941年4月,教育總監部整理的“警備勤務與討伐參考”[2]防衛庁防衛研究所図書館所蔵.的小冊子中,竭力推薦在“討伐”時使用化學武器,第170頁記述:“安排部分兵力切斷敵退路,主力從另一方進攻;或者一部使用特種彈藥,主力則在風口處埋伏,伺機攻擊退卻的敵人,運用手段可取得戰斗有利態勢”。
此即為教育總監部所指導的“殲滅”戰的內容,毒氣的使用過程是怎樣的呢,小冊子中如下敘述關于“討伐居民區”情形。
第197頁:“如遇村莊“敵匪”頑抗,提前派強力部隊遏制敵之退路,用炸彈、迫擊炮、擲彈筒、特種煙等射擊,首先將敵匪驅出村外,趁機將敵捕獲殲滅。”
第199頁:“對于憑借居民村落頑抗的敵匪徒,掃蕩中使用普通特種煙易取得有利作戰態勢。(作要362—2)”
對“居民區”“掃蕩”,使用化學武器容易取得效果。到1943年為止,北支那方面軍在“討伐戰”和“肅清戰”中持續使用化學武器對共產黨根據地進行“殲滅”和“消滅”,而教育總監部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四、侵華日軍生物細菌武器與山西
雖然山西關于細菌戰的直接資料很少,但現階段可以肯定的是,侵華日軍實施細菌戰的罪魁石井四郎曾在山西任職,這也是其在細菌戰中樞——滿洲731部隊以及陸軍軍醫學校之外唯一擔任的職務。現階段山西可以讀到的相關信息有:石井四郎本人除1943年8月至1945年3月以陸軍軍醫學校的秘密身份返回東京之外,一直擔任731部隊的部隊長,其間的唯一例外則是1942年8月至1943年8月在山西短暫任職第一軍軍醫部部長。公開記錄將石井四郎調任山西的原因稱之為其將親信安排把持要害部門,大量貪污研究經費,遂被降職調往山西[3]持此觀點者為日本推理小說家森村誠一,而后在張樹純.石井四郎在山西進行的細菌戰實驗.山西檔案,1998,(1).以及章書、王洪慶在.日軍在山西也進行過細菌戰實驗.蘭臺世界,1998,(3)等文章中都引用此說法。。而史料來源則是日本暢銷歷史圖書《惡魔的飽食》一書作者森村對于若干不愿透漏姓名的原731部隊隊員的采訪調查。從而石井四郎因貪污瀆職被解除職務調往山西成為了公認的說法。
但此說并非完全沒有爭議,按照文獻資料《井本日志》1942年7月26日記載:“因為8月1日的定期人事調動,石井轉任第一軍軍醫部長。”[4]井本日志(第19卷).見吉見義明,伊香俊哉.「日本軍の細菌戦」『季刊戦爭責任研究』,1993,(2):18.井本熊男本人歷任參謀本部作戰課參謀、支那派遣軍總參謀,以及陸軍大臣秘書等關鍵職位,其業務日記等資料1993年為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公開,其中記載有“細菌戰”等重要資料。后防衛廳以涉及個人隱私原因重新變更為非公開.否認了石井四郎由于貪污瀆職而被解職的說法。而石井四郎本人對職務變更的解釋為:為了獲得升任中將的資格,必須在陸軍野戰部隊服役,而且這一調任的另外原因則是“上面”不想讓他繼續從事細菌戰的研究[5]陳致遠,朱清如.1942年石井四郎被“撤職”原因新探—日軍細菌戰戰略的調整變動.民國檔案,2012年1月.。但如何理解這種說法依然存疑,其在第一軍的直接上司,原北支那方面軍司令岡村寧次處則記錄了如下說法:“石井機關的創設是高度機密事項,(陸軍)省中只有陸軍大臣、次官、軍務局長、軍事課長、醫務局長,以及關東軍的小磯參謀長等少數幾人知曉。由于升職的原因,石井有時也從事普通軍務。”“我在北支方面軍司令官時,他作為我麾下第一軍的軍醫部長來山西就任。在完成其本職工作的同時,也在進行其使命中的特殊研究,并取得了諸多成果。”[1]『岡村寧次大將資料(上)』.原書房,1970.(P388-389)此處岡村的資料無意中透漏,石井在山西并未脫離其本行,繼續從事相關的人體實驗。而關于石井為何會被派往山西,岡村寧次的回答則是“完成本職工作的同時,從事特別研究。”
究竟如何理解石井這一職務的異常變動呢,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理解:第一,1942年,隨著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軍戰略重心已經由向北邊對蘇聯完全轉向對南邊的英美等國,而細菌戰假想國本來為蘇聯,這也使得細菌戰脫離了最初的設想軌道;第二,石井并未得到陸軍總部的認可。最早在參謀本部負責石井四郎聯絡的井本熊男回憶,參謀本部忌憚國際輿論,并未積極響應細菌戰設想,只是將細菌研究作為儲備戰術使用。對于石井部隊的經費支持也停留在研究的合理范圍之內[2]共同通信社社會部編:「インタビュー井本熊男」『沈黙のファイル』.共同通信社,1996.(P355-356)。但對于石井部隊而言,急需取得戰場上的成果來獲取陸軍上層的認可,但其作戰效果不佳,特別是在湖南常德等地,對于普通民眾傷害較大,甚至對于自身部隊也有相當程度的誤傷[3]七三一部隊國際シンポジウム実行委員會.『日本軍の細菌戦毒ガス戦―日本の中國侵略と戦爭犯罪-』.明石書店,1996.(P188)。1942年冬,石井調任山西之后,陸軍省還陸續收到希望使用細菌武器的提案,當時同時兼任首相、陸軍大臣的東條英機對此反應消極,未能如其所愿[3](P358)。石井這一時期在山西的活動,很大可能是為了驗證和實踐其在細菌戰領域的理論,將其付諸實踐。
華北方面直接從事細菌戰的甲1855部隊,下轄5個支部與8個派出機構,其中太原支部長軍銜和人數都相對高于其他一般支部[3](P164)。而石井所調任的第一軍軍醫部駐扎于太原,以此條件為基礎,當時設在山西的大同陸軍醫院[4]大同陸軍醫院進行過培訓駐蒙軍軍醫將校的課程,現存大同醫院的短期課程表,以及冬季衛生研究的“冬季衛生研究班”的報告書,由谷村一治軍醫少佐與三浦理平軍醫中尉共同實施,時間大約為1941年.以及潞安陸軍醫院就成為了這一時期培訓和實施細菌戰的教育與實驗基地。
在石井四郎的“指導”和推動下,山西地區的人體實驗及活體解剖活動在華北諸省表現得最為活躍。時任潞安陸軍醫院中尉軍醫的湯淺謙供認:在石井四郎的教育“鼓舞”下,1942年8月至1945年3月,他在該病院先后六次參加活人的解剖演習,殺害抗日軍俘虜11人。期間,1944年1月,湯淺謙還做出了1944年度的解剖計劃,同年又于12月提出1945年度的解剖計劃,計劃是依每兩個月解剖一次,每次解剖兩人[5]湯淺謙的口供.1955年8月31日.日本侵略華北罪行檔案卷2——戰犯供述.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P170)。而石井獲得認可的37度溫水的“凍傷療法”,也是其在山西使用人體試驗多次得出的成果[5](P170)。
石井上任后利用所賦予的特定條件,加強細菌戰教育與研究,并親赴各地巡查,作細菌戰的講演。1943年7月,他在太原第一軍司令部對參加太行作戰的日軍軍醫們講:“斑疹傷寒怎樣傳染?……實際上是虱子傳染,是患者在抓癢時,使細菌進入皮層內致病。……這是在太原防疫給水部用中國人做過斑疹傷寒實驗予以證明的。”[6]張樹純.石井四郎在山西進行的細菌戰實驗.山西檔案,1998,(1).(P36)同時石井四郎還通過培訓班、經驗交流會、登臺授課等多種方式進行“業務技能”培訓,提高對細菌戰的認識。作為潞安陸軍醫院的湯淺謙即接受過石井四郎5次細菌戰教育[6](P171)。也正是這一時期,日軍在山西的細菌戰顯著增多。
配合“掃蕩”“圍剿”,由其所謂的“防疫給水”部隊實施細菌作戰,其方式、方法主要有:所到之處向日常用具、糧食、食器、水井或附近河流中涂抹、投放,暗中向村落中施放注射過病菌的疫鼠等[7]晉察冀軍區司令部通報,1942-5-9.(P171)。日本學者笠原十九司在其所著的《日中戰爭全史》(下)中寫道,“日軍在華北使用的生物武器給華北民眾帶來了巨大的犧牲。細菌武器使用的真實情況仍尚待考證,但據不完全統計,日中戰爭的8年間共使用細菌武器70余次,其中有具體死亡者共25次。使47萬士兵、普通民眾感染傷亡。山西盂縣所做的調查中,1942—1945年間,因日軍所發射的糜爛性毒氣以及斑疹傷寒細菌武器,就使得全縣16萬人中的95%感染患病,其中1萬1千人被日軍所殺害,將近3萬人病死。”1942年日軍“掃蕩”晉綏邊區后,當地衛生機關即在河曲、保德一帶發現散在性鼠疫患者,死數十人。經當地軍政衛生機關協助人民隔離,斷絕交通,始免于蔓延[1]二野后勤工作人員指控日寇散播病菌毒害華北各地人民.人民日報,1950-2-10(第4版).。據資料考察統計,整個華北五分之三以上的細菌戰發生在石井四郎到任后的山西[2]尹子平.石井四郎與華北細菌戰.河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8.(P20),由此可見山西所受毒害之深。
五、山西生化武器受害者的口述調查
抗戰期間,由于侵華日軍實施生化戰,給民眾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對于普通民眾而言,由于缺乏化學武器以及生物武器的基本常識,平民幾乎很難分辨,應對這種殺人于無形的特種武器。傷寒霍亂、鼠疫、瘧疾各種疾病反復肆虐傳播。
1999年8月和2000年9月日本學者(包括日方學者粟屋憲太郎、宮崎教四郎、豐田雅幸、松野誠也、小田部雄次等人)組織的實地調查團兩次到山西,進行山西毒氣受害的實地調查。在受害者的口述中,發現很多受害事實。
口述調查的主要目的是了解毒氣使用的有關情形從而確認日軍在山西省使用毒氣,由于調查時間有限,每次只能在特定的某幾個地區收集關于毒氣受害的口述。1999年8月的調查地點為山西省定襄縣、榆社縣、武鄉縣、襄垣縣、左權縣、黎城縣、沁源縣七縣的十多處具體地點,這些地點大部分都為離山西省中心地帶太原較遠的農村與山區地帶。而2000年9月的調查遍及了平魯縣、榆社縣、武鄉縣、壺關縣、平陸縣的五縣十多處地方,與前述的地方相同,這些地方也是農村和山區地帶。
集中調查的結果發現,口述中隨處殘留著日軍打算隱藏毒氣戰痕跡的證據。
調查的主要目的是調查是否有致死性毒氣“黃劑”的使用例,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樣,在輝教村、武軍寺村、蟠龍鎮、韓北鎮、石臺頭村等地都發現了使用致死性毒氣的痕跡。而當時的輝教村中,很多村民沒有毒氣和醫學方面的知識,只記得癥狀,認為是“腫起的包”“癩病”,描述與現在的“農藥中毒”比較貼切。從“不知道因為什么原因死的,但所有的人身上都腫起了包。”的口述中,估計是致死性毒氣起的作用,而村民們至死也不知道受害原因。
另外一個調查地點蟠龍鎮還有連“病情”起因也不清楚的事例。蟠龍鎮中的三種病是“疥癬、斑疹傷寒、瘡”。被調查者村民武桃兒說,直到調查團說起都不知道為什么自己的身體會起水泡。另外一位村民安培茹一直以為是傳染病。蟠龍鎮協助調查的年輕村長同時也是一名醫生,他說道“疥癬是傳染病的一種,但不可能在那么廣的范圍傳播”,從而一直懷疑傳染病的說法。村民們在很長時間都不清楚自己的受害原因,只是在已知病癥的范圍內治療。且村民們大多不具備醫學知識,只大概記得自己的癥狀。
關于疥癬,韓北鎮的韓俊鴻講了當時流傳的一首歌謠。“疥癬像龍,手上有了,在腰上纏上2、3圈,在兩條大腿上才算完”。疥癬1940年左右出現,1941年蔓延,1944年開始逐漸變少,1946年以后才最終消失。被稱之為“疥癬”的“病”在1940年后的抗日戰爭中蔓延,這種癥狀還殘留在村民們的歌謠里,證明村民們受到來歷不明的病癥困擾。
八路軍士兵以及軍隊相關人士具備毒氣知識,武軍寺村由八路軍來消毒,衛生隊的人告訴他們這是“糜爛性毒氣”。赤峪村教給怎么防毒,指導村民“用尿弄濕毛巾,塞住口鼻防毒”。防毒的方法多樣,輝教村是“喝草藥和綠豆湯”,蟠龍鎮則是“用胡椒水洗”“涂火藥”等。這些處置方法的醫學效果不明,但在沒有藥品的情況下也是不得不為之的舉措。關鍵在于,村民們中間,這種防毒方法傳播范圍很廣,證明日軍毒氣攻擊如何之猖狂。
榆社縣河峪鎮輝教村的調查得知,日軍飛機在每年夏、秋及年末、年初時都會前來撒毒,村民石新華(65)的口述中說,飛機飛來就會出現2種癥狀:一種是浮腫,另一種是被稱為“癩病”的皮膚病,沒有醫生,只能忍耐等待自愈。
而左權縣麻田(八路軍總務部紀念館)趙慶(70歲)的口述中,當時得肺結核、斑疹傷寒、“癩病”的人很多,因此而死的人也很多。武鄉縣蟠龍鎮安俊茹(88歲)的口述中:1500人人口的村落戰后只剩865人。日本兵在一年中會來3、4次,時間大致為春播、夏秋天收割時,以及冬天的年末年初(舊正月)時候,有時一駐半個月,當時流行三種病是疥癬、斑疹傷寒,以及浮腫。楊春旺(77歲)的口述中,日軍最初攻來時殺了50多人,房子也被燒了很多。日軍走后,村民腳和身體都起了疥癬。1943年,或是1944年的陰歷2月,因為疥癬死了30多人。
另外1999年8月調查組在武軍寺調查訪談中,據說日軍曾在麻田播散斑疹傷寒病菌,而麻田一位婦女因為斑疹傷寒原因“失去雙手”。
雖然這些受害情形都沒有明確的日方資料可以印證,但可以清楚證明的一點是山西遭受日軍生化武器荼毒受害之重,以及對于普通民眾生活影響之深。
六、結 語
山西是遭受日本生化武器侵害最嚴重的地區之一。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二:第一,山西山地丘陵地形不容易留下生化武器的使用痕跡,成為了日本生化武器的演練場。陸軍中央明確下命令使用毒氣,以及石井四郎調任山西初衷大致都與此有關。第二,山西敵后抗日運動給侵華日軍造成了很大的困擾,為了解決共產黨與民眾的聯合抗日態勢,日軍不惜采用三光政策,進而使用生化武器來對付抗日軍民。
生化武器的整個研究、實驗、生產、使用、善后鏈條隱蔽性強,痕跡難以發覺,同時日方戰后又多方藏匿銷毀資料,從而使得揭發清算這一戰爭罪行就顯得異常困難。日本使用生化武器對平民的侵害,對于當時歷史條件下缺乏生化武器常識的平民而言,并無能力分辨,這也為進一步挖掘日本罪行帶來困難。
但就已有資料而言,日軍生化武器對山西傷害甚多,山西遭受到很大程度的傷害。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雖然行為主體、實施方式都有不同,但對于受害者的傷害卻是無一二致,山西的生化武器受害情形是確鑿無疑的。但山西地區關于生化武器,特別是細菌武器的具體使用細節方面還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和追蹤,而這才是真正尊重歷史、面對歷史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