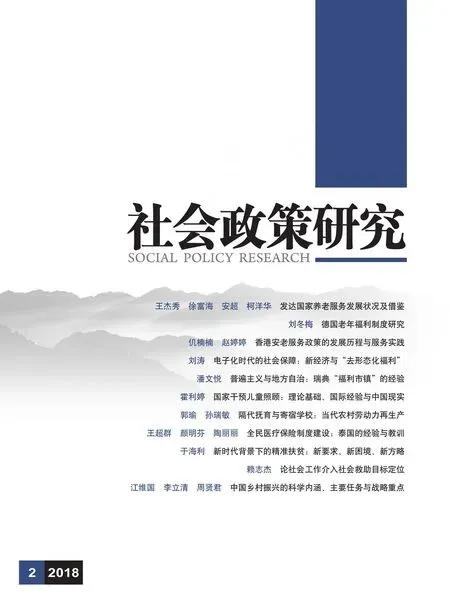隔代撫育與寄宿學校:當代農村勞動力再生產
郭瑜 孫瑞敏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城鄉人口流動自由度的增加、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吸引了大量農民進城務工。據統計,2015年中國流動人口規模達2.47億,占總人口數的18%(張尼,2016)。2017年3月,人社部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末,全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82億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69億人,分別比上年增加424萬人和50萬人(人社部,2017)。據此,農民工依然是我國流動人口的主要構成。然而面對戶籍制度的阻隔和高昂的遷移成本,農民工群體難以享受到與城市居民相同的住房、養老、教育、醫療等方面的福利與保障。這讓城市在獲取農民工帶來的發展利益時,能夠名正言順地回避承擔其勞動力再生產的責任,將勞動力使用與勞動力再生產從空間上割裂開來。這種勞動再生產方式的直接后果就是農村留守兒童數量的急劇增長。數據顯示,2015年留守兒童占農村兒童的35.6%。其中安徽、河南、四川跨省流出集中地區留守兒童比例達到了43.8%(張尼,2016)。如此龐大的占比表明農民工子代的生存和發展是勞動力再生產和社會再生產不容忽視的重要議題。在社會發展的宏觀背景下,本文主要探討當代中國農村家庭的勞動力再生產的機制,以及在微觀家庭系統中,勞動力再生產、家庭分工和代際關系之間的互動關系。
一、概念框架與文獻綜述
(一)國外勞動力再生產的相關研究
勞動力再生產,即勞動者通過個人消費把勞動過程中消耗掉的勞動能力重新生產和恢復起來(林振達,2004:50),具體內容概括為三點:第一,補償和恢復勞動者自身的體力和智力,實現勞動力自我再生產;第二,補充和培育新一代勞動者,實現勞動力代際再生產;第三,積累和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勞動技能,提高再生產的質量(馬克思,2004:193-195)。馬克思和恩格斯強調勞動力再生產和物質資料再生產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決定條件,“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工人階級的不斷維持和再生產始終是資本再生產的條件”(馬克思,2004:628)。勞動者的價值由生理、歷史和社會要素構成(馬克思、恩格斯,2006:199),因此實現勞動力再生產要滿足其生活資料、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的消費(馬克思、恩格斯,2012:107),后兩者的重要性越來越凸顯。
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勞動力再生產的完成都主要依靠勞動者出賣勞動力賺取勞動價值來維系,而工廠中的勞工越來越難以依靠微薄的薪水在城市中獲得安逸體面的生活。巴黎的工人家庭聚居在郊區的貧民窟;保守派對于發展義務教育的阻撓,阻礙了貧困工人家庭子女接受教育,工人子女的教育就在家庭中進行,并主要依賴女性充當勞動力再生產的管理者;家庭中只依靠男性勞工獲取收入越來越不能滿足生存需求,女性急需工作以解決家庭財務危機,家中幼兒無人看管的難題困擾著工人家庭(哈維,2004:206-219)。20世紀中期,Burawoy(1976)通過對南非礦工和加利福尼亞工人的調查揭露了在制度歧視下,勞動力自我再生產和代際再生產在地理上分離,勞動力的再生產主要依靠勞動力自身和家庭來完成。國家和企業責任的缺位為移民工人的生活帶來了繁重的壓力,加劇了階層分化和社會不公平。
Burawoy對于這種不合理的再生產模式進行批判,認為國家應該提供制度安排(產業制度、福利制度、就業保障制度等)甚至是采取直接治理的手段來促進勞動力自我再生產和代際再生產的合并,結束這種不合理的移民勞動力再生產方式。Castells(1978:3)認為國家的直接或間接干預對于化解由于工業資本發展的內在邏揖所導致的社會不平等、城市問題以及政治危機意義重大。由于勞動力再生產存在于資本生產領域之外,國家干預并不會直接影響資本生產方式(Hansson,1979:175-185),因此資本主義國家逐漸建立起與保障勞工工資制度并存的社會福利制度,二者共同構成國家保障勞動力再生產的制度前提。盡管西方國家的福利制度與福利標準存在著差異,但是社會福利制度在改革過程中一直將保障勞動力再生產的內容考慮進來,國家也從未放棄對勞動力再生產的宏觀調控(Haylett,2003:765-788)。
(二)國內勞動力再生產的相關研究
國內關于勞動力再生產的研究最初主要闡述了馬克思勞動力再生產相關理論的內容和意義,強調國家應當構建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滿足勞動力的發展需求;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同時不斷提高勞動力的質量(王永江,1984:38)。人們消費的過程就是勞動者的勞動力再生產的過程,通過對生活資料的消費,工人獲得了體力和智力的補償與維持(王永江,1985:18)。有學者認為,勞動力再生產過程實際上就是物質文化生活資料和勞務的消費過程,物質文化生活資料和勞務的數量與質量決定著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季相林,2003:60)。此后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民工群體。有研究指出,目前我國勞動力再生產模式存在的最主要的問題就是農民工勞動力自我再生產與代際再生產的分離(屠晶,2014:134;吳煒,2013:43)。造成這種拆分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戶籍制度將農民工排除在城市住房、子女教育、工作保障以及其它環境基礎設施等集體性消費資料之外,城市在享受低成本勞動力帶來的發展優勢時,依靠制度阻隔不負擔其勞動力再生產的責任(任焰、潘毅,2007:182-190)。
現有研究主要探討制度性因素對農村勞動力再生產方式的影響,卻較少探究家庭系統內部因素與勞動力再生產相互影響的機制。本研究以農村勞動力再生產為切入點,通過實地調查來展現目前社會發展背景下,農民工家庭通過何種途徑實現勞動力再生產,以及家庭系統內部這種勞動力再生產模式與各部分之間的互動。
二、研究方法與背景介紹
(一)研究方法介紹
“個人的思想和行為以及社會組織的運作是與他們所處的社會文化情境分不開的”(陳向明,2014:7),要想了解農村勞動力再生產的實際情況,就必須置身于他們生活的社會情境,通過與行動者的溝通來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態,獲得他們的真實想法。因此,作者以居住者的身份進入A村,進行田野調查。主要通過立意抽樣和滾雪球的方法抽取15個農村(農民工)家庭作為個案,采用訪談法和觀察法來收集資料。通過對家中祖輩、父母輩和孩子三代以及學校的班主任老師和教務主任進行訪談,了解當地農村如何完成勞動力再生產過程中孩子的撫養和教育任務,而該過程又對他們的生活帶來了什么影響,在此基礎上對當前農村勞動力再生產的模式以及存在的問題進行總結和反思。訪談資料的整理基于筆者在訪談中獲得的錄音和筆記,并做出匿名處理。
(二)A村的基本情況
A村位于內蒙古赤峰市元寶山區,近年來受征地政策和工業結構調整的影響,當地出現了大量的失地農民和剩余勞動力,在很短的時間內當地居民的就業形式被迫從務農為主轉換為非農就業為主,大量的勞動力進入城鎮謀求生計,父母和兒童城鄉分離的情況比比皆是。社會的變遷對當地居民的生活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城市對農民工群體的政策排斥,讓農村家庭的勞動力代際再生產和勞動力自身再生產的矛盾空前激化,因此A村可以被視為工業化和城鎮化背景下,中國農村如何進行勞動力再生產的縮影。探究當地如何緩解因父母外出務工而造成的勞動力再生產難題,有益于了解當下我國農村勞動力再生產的真實情況。
(三)家庭人口構成與居住情況
隨著大量農村勞動力向外轉移,當地幾乎沒有常年在家居住的年輕人。外出務工的需求與對城市生活的向往將年輕父母從鄉村吸引到城市,因而A村的人口結構出現了明顯的空心化,當地家庭的主要常住人口是老年人和留守在農村的學齡前兒童。年輕人常年在外工作,所以A村的日常生活比較冷清,只有逢年過節之時熱鬧一些。
被訪的15戶農民工家庭中有兩戶是四代同堂,其余均是由祖孫三代構成的主干家庭。祖父母一輩的年齡分布在55-65歲;父母一輩的年齡分布在25-45歲,作為外出務工的中堅力量,肩負養家糊口的重要責任。子女的年齡主要在18歲以下,正處于勞動力再生產的積累時期,分為學齡前階段和學齡階段,受到祖父母、父母的照料并接受正規的教育和培訓。
(四)家庭成員就業與收入情況
過去幾十年A村的經濟發展主要依賴煤炭資源的開發,村辦煤廠、磚廠和火藥廠是吸納本村勞動力就業、推動本地經濟發展的三輛馬車。就業崗位自給自足,使當地人對上世紀九十年代掀起的“民工潮”、“打工熱”感觸并不深。十年前因為安全事故,國營煤礦企業的打壓和產業結構調整,當地出現大量失業人員,于是村民們逐漸離開鄉村到城鎮找工作。自此,進入城鎮從事非農職業成為當地人的主要職業去向。當地耕地資源比較豐富,年紀大的村民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兼營副業,中青年一代完全從事農業生產的十分少見。據被訪者出去打工的年輕人大多從事服務業、運輸業、建筑業或個體經商。整體上來看,從事農業生產對A村家庭來說仍然很重要,而年輕人的就業選擇則呈現多樣化的特征。
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因職業的不同呈現出差異。對于祖父母來說,主要收入來源仍然是農業收入,其次是副業和社會保障收入。對于父母來說,職業收入取代農業收入成為他們主要甚至唯一的收入來源。
三、A村勞動力再生產實地調查
(一)勞動力再生產的兩條途徑
學齡前兒童:隔代撫育取代親子撫育。當兒童處于0到6歲時期,即學齡前階段,外出務工的父母一般會選擇將孩子托付給祖父母照顧,由祖父母負責孩子的日常照料,擔當起孩子的“臨時父母”。一般情況,孩子的父親會一直在外打工,而孩子的母親大多在孩子滿一周歲之后離開農村的家去城里找工作,這之后照顧孩子的任務就會落在祖父母肩上,撫育的主要內容包括照顧孩子的日常起居,保障孩子的溫飽、健康以及人身安全。這種由祖父母和孫輩組成的“假三代家庭”在A村十分普遍,隔代撫育成為當地農民工家庭的主要撫育方式。A村中完全依靠祖父母來撫育孫輩的情況大多會持續到孩子入學前。孩子進入學齡需要接受教育時,隔代撫育就不再是實現勞動力再生產的主要途徑。
學齡兒童:義務教育完成于寄宿學校。當兒童達到六周歲時將面臨上學的問題,勞動力再生產的內容在撫養的基礎上增添了教育的部分。在我國很多城市,為解決流動人口子女的受教育問題,政府要求流入地設立農民工子弟學校,城市中有些公立學校也會接納外來務工人口的子女就學。在實地調查中,筆者發現城鎮公立小學按照片區招收生源,對于不在城鎮居住的附近農村居民家的兒童來說,大部分只能進入一所被稱為“山前五中”的寄宿學校就讀。“山前五中”成立于2009年,是合鄉并鎮的結果,設立的初衷就是為了滿足附近農村兒童的就學需求,一貫制的教學體制能夠保證他們順利完成九年義務教育。”①來自于“山前五中”初中部教務主任的訪談。筆者訪談當時,A村家庭所有學齡兒童都是在這所學校就讀,學齡前孩子的家長表示他們的子女未來也將在此完成義務教育。
(二)家庭分工與勞動力再生產
在實踐中,農民工家庭勞動力代際再生產的完成絕對無法僅僅依靠一代人的力量,祖父母的介入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通過田野調查,筆者發現隔代撫育行為體現出了家庭內部分工協作的思維:年輕父母進入城鎮務工賺取勞動力自身再生產和代際再生產的物質資源,用于供給家中子女和替代父母承擔撫養責任的祖父母們日常生活所需。如此代際分工成為隔代撫育的前提,農民工家庭的勞動力再生產正是基于這樣的家庭分工才得以有序進行。
這種家庭分工的安排一方面是理性選擇的結果。“現在村子里沒有啥發展前景,年輕人不出去工作的話根本不夠一家吃喝的,在外面打工忙起來根本顧不上孩子,老家伙就幫著看孩子唄,農村消費也不高,孩子總得有人管①來自個案1家庭中祖母的訪談。。”賺取生活費用是勞動力生存的客觀需要,年輕人明白走出農村掙錢是唯一出路。外出務工的年輕父母收入水平較低而且不穩定,城鎮消費水平較高,他們的生活開支較大,有限的經濟條件不允許他們把孩子帶在身邊撫養。相比之下,農村生活成本較低,祖父母在身體健康的前提下照看孫子女是節約再生產成本的最佳策略。年輕夫婦在城鎮打工賺取勞動力再生產的物質資源,而農村的祖父母承擔撫育孫輩的責任,這種家庭分工是保障勞動力再生產有序進行的前提。
另一方面,這種家庭分工受到傳統家族觀念的驅動。“在農村,生了兒子就算是完成傳宗接代的任務,把兒子養大了,就得給他蓋房子娶媳婦,媳婦生了孫子,我們就得照顧孫子②來自個案4家庭中祖母的訪談。。”祖父母將為家庭奉獻視為應然和高尚的事情,并將照顧孫子女看作一種應盡的責任和義務。當被問及“您是主動承擔這個責任嗎”,被訪家庭中祖父母無一例外地給出了肯定的答復。這種農村傳統的家庭生育觀和家族觀已經深深地扎根于老一輩的思想深處成為思維慣習——即一種不言自明的行動指南,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已被這種文化觀念影響至深。“年輕人在外面工作不容易,我們能做一點是一點,互相幫助這個家才能過好啊③來自個案10家庭中祖父的訪談。。”這種深遠的家族觀念是農村家庭分工協作的思想內核,由此為隔代撫育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礎。
盡管有研究指出這種家庭分工塑造的再生產方式其實是對老一輩的“代際剝奪”(陳鋒,2014:57),很可能為祖父母帶來身心壓力和經濟負擔(趙梅,2004:95;Blackburn,2000:30-36)。但是在實地訪談中,有60%的祖父母表示能夠從照顧孫子女的過程中獲得成就感和滿足感,他們視家庭和家族的發展為重中之重,這種家庭分工和勞動力再生產方式并沒有為他們的生活帶來明顯的負面影響。
如果家庭分工中缺少父母或者祖父母任意一方的參與,農村勞動力再生產將呈現完全不同的局面。而這種勞動力再生產之所以如此依賴于家庭分工,很大程度上與社會支持不足有關。從社會支持的角度來看,由于職業流動性強、參加社會保險意識淡薄、用人單位的利益取向等多種原因,農民工群體的生育保險參保率極低,特別是女性農民工往往要獨自承擔因為生育而帶來的失業風險。此外,我國在生育和育兒方面的配套支持福利政策幾近空白,沒有為育有幼兒的困難家庭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因此由于懷孕造成的經濟損失和分娩之后孩子的撫養問題最終都在農村家庭內部消化。再者,撫育后代更多被看作一種私領域的問題,而不是社會責任,農村家庭難以尋求社區或者社會組織的幫助。就像訪談中反饋出來的擔憂,請育嬰嫂照顧孩子價格昂貴,而且保姆行業的監管力度不夠,虐童事件屢見報端,農村家庭往往不會選擇保姆照看;而正規幼托機構的稀缺與高價更是讓農村家庭無法尋求來自社會方面的幫助。由此看來,相關制度和社會資源無法為農村家庭提供社會支持,農村家庭只能在有限條件下進行內部分工以實現勞動力再生產。
(三)勞動力再生產與代際關系
代際關系是家庭諸多關系中最為重要的關系形式,也是社會關系的基礎,其核心是親子關系(費孝通,1983:8)。代際關系的維系不僅以血緣為基礎,同時也依靠社會制度來維系。因此,不同階段的社會發展及制度變遷,將為代際關系帶來直接的影響。同理,在社會發展背景下誕生的當代農村勞動力再生產方式,必然會對農民工家庭的代際關系帶來深刻的影響。
被調查家庭中,大部分祖父母身體強健,不需要父母的贍養,而父母已成家立業,不再需要祖父母的撫育,這個時期的代際關系處于“撫育-贍養模式”的過渡階段,而且呈現出代際關系向下傾斜的特點。費孝通所定義的“反饋模式”的代際關系發生傾斜,表現為贍養功能的減弱和撫育功能的增強。這種代際關系的失衡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并不會引起農民工家庭的震蕩。然而,實地調查反饋出,當下農村家庭勞動力再生產方式存在著打破這種中國特色代際關系的隱患,動搖著和諧代際關系的建構。
隔代撫育在實踐的過程中很容易引發代際關系的緊張甚至家庭矛盾。祖父母和父母之間極易產生經濟矛盾,即因孩子的撫養費問題而發生爭議,“孩子吃喝啥的都花我們的,我們過得摳摳巴巴的,人家倆人甩手掌柜啥都不管,連孩子上幼兒園的學費都是我們交。因為這個事兒每回回家都吵架①來自個案7家庭中的祖母訪談。。”祖父母因為照顧孫輩需要付出更多的經濟投入,因此往往希望父母能夠從經濟上予以補貼。出于不同的原因,如果父母沒能做出經濟補償,從祖父母的角度來講,他們付出的勞動就沒有得到對等的回報,矛盾因此滋生。除了經濟糾紛,還有因為生活習慣和教育觀念不同而產生的代際矛盾,“我在外邊工作的時候給我婆婆打電話,讓她給孩子多吃蔬菜水果,她答應挺好的,但是老不照做,一點也不講究,搞得孩子老便秘。現在孩子學說話呢,大人說啥他學啥,我媽我爸他倆也不避諱,弄得孩子現在張口就說臟話②來自個案9家庭中的母親訪談。。”這些生活當中的細小問題日積月累,就成為家庭紛爭的導火索,婆媳矛盾也因此經常發生,有的母親就干脆賭氣把孩子送到自己娘家去照顧。另外,如果在祖父母的看護下,孩子發生了意外,兩代人的關系會變得十分尷尬,老人會抱怨照顧孩子不是好差事,但如果不交給老人照顧,年輕父母就會陷入兩難的境地,這種進退維谷的情況經常發生在農民工家庭中。
當孫輩進入寄宿學校就讀,原本由祖父母承擔的撫育責任轉移到學校和老師身上,祖父母則在代際關系中發揮著輔助作用。此時,勞動力再生產方式的弊端逐漸外顯,表現為核心家庭中代際關系的冷漠和代際沖突。調查顯示,很多父母因為長期外出務工,疏于對孩子的照料和溝通,留守兒童和父母之間的交流變得越來越少以至于沒有共同話題,就算父母和孩子都在家里,也幾乎無話可說。長期分離造成父母和孩子之間關系冷漠,有的父母認為把孩子放在學校就可以完全依靠老師教育,卻沒有意識到家庭教育對孩子的重要性。“很多父母經常對孩子說‘你讀書我就供你,你不學我也沒招兒’,把學習的責任都拋給孩子,我雖然經常在微信群里反饋孩子的信息,但是主動找我了解情況的家長寥寥無幾,就像完全把孩子丟給學校了一樣①來自山前五中初中寄宿班班主任的訪談 。。”就像隔代撫育一樣,寄宿學校被很多家長當作逃避撫育責任的工具,他們把教養孩子的責任全權托付給學校,而讓孩子承擔成績好壞帶來的任何后果。感受不到父母關懷的子女自然不會對父母的要求做出響應,特別是進入初中后,很多孩子進入青春期,自我意識不斷增強,幼年時期由于早早開始寄宿生活以及親子溝通不及時造成的心理問題,在這個時期漸漸被放大。“原來小的時候他們不管我,現在對我指手畫腳,讓我好好學習,那他們為啥不早點管我,我都要畢業了,還來得及嗎②來自個案10家庭中孫女丁丁的訪談。。”長期積累的對父母的不滿在這個時期便會爆發,被訪的農民工父母表示孩子不聽管教,行為叛逆,難以溝通。“她天天追明星,鬼迷心竅一樣,讓她好好看書準備考試也不聽,嘴皮子都磨爛了,人家該干嘛干嘛③來自個案15家庭中的父親的訪談。。”因此,寄宿體制對于代際關系的健康發展反而起到一定的負面作用:父母與孩子之間長期缺乏溝通,感情交流不到位,容易產生代溝,而此間兩代人之間的不滿和矛盾沒有及時化解就會產生代際關系冷漠甚至引發強烈的代際沖突。
四、總結與討論
城鄉二元戶籍制度造成農民工勞動力自身再生產與勞動力代際再生產的分離:為了獲得收入,農民工父母需要留在城市工作,而下一代的撫養和教育則由鄉村來承擔。通過對以外出務工為主要收入來源的A村農民工家庭進行調查,發現農村家庭主要通過隔代撫育和送孩子上寄宿學校的方法,以保證家庭內勞動力代際再生產的順利進行。這種勞動力再生產方式建立在特定的家庭分工基礎上,并對農民工家庭的代際關系產生深刻影響。
事實證明,在正式制度無法保障農村勞動力再生產順利進行的情況下,這種非正式的解決方法在農村具有普遍性,而且確實有助于緩解外出務工父母的后顧之憂。這種勞動力再生產方式之所以能夠有效運行,得益于農民工家庭內部的分工協作:隔代撫育替代親子撫育,可以讓父母專心投入于工作,確保獲得穩定的勞動力再生產的物質資源;祖父母則主要負擔撫育孫輩的任務,為其提供穩定安全的成長環境。家庭分工構成了農民工家庭再生產的前提條件,體現了理性選擇和傳統家庭觀念對個體行動的引導作用。
工業化和城鎮化背景下形成的農村勞動力再生產方式,或直接或間接地型塑著農民工家庭的代際關系。A村農民工家庭在解決勞動力代際再生產過程中的實踐可以視為我國農村勞動力再生產的縮影,但是不可否認這種民間慣習對家庭成員個體發展和構建良好的代際關系具有一定的負面作用。務工父母在撫育過程中的缺席,讓祖父母再次擔當家長的角色,此時代際關系向下傾斜,出現了代際關系失衡的情況。勞動力再生產實踐中,蘊含著引發代際沖突和矛盾的因子。由于生活費、生活習慣、教養觀念等因素,隔代撫育過程中祖父母和父母易發生代際沖突。將孩子送入寄宿學校后,親子之間因為疏于交流溝通,傾向于發生代際關系冷漠甚至激烈的代際沖突。長期來看,這種方式并不具有可持續性:當子代變為祖父母時,未必會像他們的父母一樣兢兢業業地撫育孫輩,通過個體的付出和犧牲來獲取家庭的更大福祉。
事實上,伴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與進化,“國家成為現代家庭生活的一個要素,家庭對國家會產生越來越深的依賴性”(桑格利,2012:30)。因此,盡管每個農民工家庭都是在權衡利弊之后選擇勞動力再生產的方式,但國家和政府不能將這個過程視為應然而不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更不能讓農民工及其子女成為制度不公的犧牲品。實現鄉村振興,解決農民工子女的撫養教育問題,形成可持續的勞動力再生產模式,仍然需要國家從宏觀角度完善制度設計,關注農民工群體的社會福利,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對該群體的利益剝奪,繼而為勞動力再生產掃除障礙。只有農村勞動力再生產問題的順利解決,才能實現城鄉和諧發展,才能為社會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創造長期穩定的環境與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