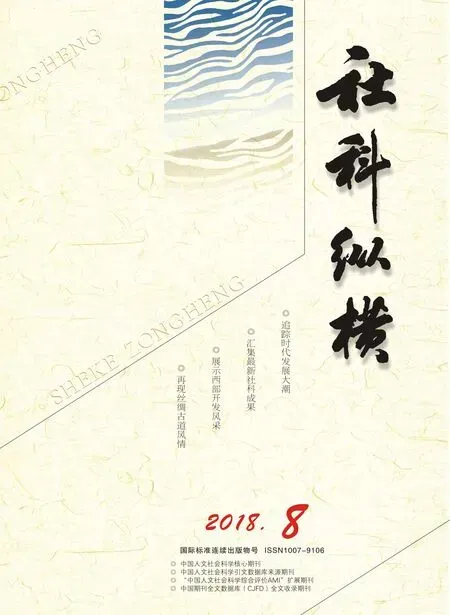概念及其意義:卡西爾與馬克-沃高之爭
石福祁
(蘭州大學哲學與社會學院 甘肅 蘭州 730000)
一、導言
在20世紀德國哲學中,要數最具新聞效應的爭論,恐怕必須提及1929年在海德格爾與卡西爾之間圍繞康德解釋而發生的“達沃斯論辯”。不過,盡管這場爭論在一定意義上催生了海德格爾《康德與形而上學問題》這部重要著作,但從卡西爾一側來說,他認為這場爭論無異于“各說各話”,甚至他明確地拒絕參與這樣一場“純屬爭論性質的討論”。[1]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兩位哲學家從一開始就沒有進入到一個共同的問題域中去。
那么,卡西爾是否在同一個問題域中與他人發生過公開爭論呢?如果把這個“問題域”具體化為“德國科學哲學”(這個標簽是胡塞爾貼給卡西爾的)[2],那么答案是肯定的!事實上,在卡西爾四十余年的哲學生涯中,真正的一次哲學爭論就發生在他和烏普薩拉學派(Uppsala School)成員馬克-沃高之間①。這場爭論涉及對概念的本質和作用的不同理解,也涉及傳統邏輯、知識、經驗等一般哲學議題;既涉及烏普薩拉學派的基本立場,也涉及卡西爾本人的“符號”概念及其符號形式哲學體系,并且間接涉及到作為當時哲學主流之一的邏輯實證主義。因此,這一爭論為檢閱當時不同哲學立場提供了一個絕佳案例。本文在對爭論的過程和內容予以介紹的基礎上,試圖對涉及的概念問題予以反思和討論。
二、爭論的背景
這場爭論之所以能夠發生,是與卡西爾流亡瑞典、成為瑞典公民期間與烏普薩拉學派的思想互動有關的。1933年納粹上臺后,身為猶太人的卡西爾于同年3月離開德國,輾轉到達英國,執教于牛津大學全靈學院。同年秋,受昔日學生、瑞典人雅各布森(M.Jacobsson)的邀請,卡西爾來到烏普薩拉大學講學。1934年,卡西爾成為雅各布森在哥德堡大學的哲學教席的繼任者。他用德語授課,學會了用瑞典語交流和寫作,頗受瑞典學生和同事歡迎,并在1939年成為瑞典公民。1941年,卡西爾離開瑞典赴美國講學,因故逗留,直至1945年在因心臟病發作在課后卒于哥倫比亞大學校園。[3][4]
在此期間,卡西爾與瑞典哲學界過從甚密。除了在哥德堡的正常教學之外,他經常在隆德、斯德哥爾摩和烏普薩拉等地演講。值得一提的是,卡西爾和他的年輕同事佩策爾(A.Petzll)結下了深厚友誼,而后者正是《理論》這本著名的瑞典哲學期刊的創辦人和長期主編(1935-1957)。瑞典哲學界們經常以《理論》期刊為舞臺展開爭鳴,卡西爾概莫能外。根據卡西爾專家克羅伊斯(J.M.Krois)的統計,卡西爾共在該期刊上發表8篇文章(含書評等),“所有這些文章都是對烏普薩拉學派的反應,每一篇文章都反映了卡西爾與烏普薩拉哲學家們的個人爭論。”[3](P34)一般而言,烏普薩拉學派是一個深受維也納學派邏輯實證主義影響的學派,它以海格斯特羅姆(A.Hgerstrm)為領袖,旨在建立一門不同于觀念論的實在論哲學。它和維也納學派一樣激烈地反對傳統形而上學,但是不同于后者的是,它并沒有把哲學建設的重心放在科學哲學上,而是放在了倫理學和法哲學上。在一定意義上,烏普薩拉學派體現了整個瑞典學界重視邏輯和語言分析、輕視傳統形而上學主題的氛圍。按照克羅伊斯的說法,卡西爾本人并不反感這一氣氛,事實上,盡管他對維也納學派的某些學說提出了不少批評,但是并沒有妨礙他對后者之批判精神的欣賞。“在瑞典的那些年里,卡西爾對實證主義者的欣賞與日俱增,因此,盡管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他與后者有分歧,但是還是愉快地與烏普薩拉學派保持了交往。”[3](P34)
在與瑞典哲學界的對話中,卡西爾的哲學思考在符號形式哲學之后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他發展出了旨在避免傳統形而上學和邏輯實證主義之弊端的現象學,即關于基礎現象(Basisphnomen,包括 Ich,Du,Es)的基礎現象學;寫出了流亡期間第一本哲學著作,即《海格斯特羅姆:瑞典當代哲學研究》,[5]這標志著某種實踐哲學轉向。對此,巴斯特(R.A.Bast)在其為卡西爾文集《知識、概念、文化》所寫的長篇“導言”中已經做了詳盡的介紹,[6](PVII-L)這里不予贅述。
但是,這不等于說,卡西爾就完全接受了烏普薩拉學派的立場,反之亦然。良好的交往乃至私人友誼,并不能掩飾卡西爾和烏普薩拉學派的思想分歧。而最能展現這些分歧的,就是他和馬克-沃高之間的爭論。
在《理論》期刊上,卡西爾和馬克-沃高共發表了7篇爭論文章,它們依發表時間順序分別是:
第一篇:卡西爾:“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對馬克-沃高同名著作的評論”,發表于《理論》2,1936,(第 2冊),S.207-232.現收入巴斯特所編《知識、概念、文化》一書。[6](P165-197)
第二篇:馬克-沃高:“恩斯特·卡西爾哲學中的符號概念”,發表于《理論》2,1936,(第 3冊),S.279-332.
第三篇:馬克-沃高:“內涵與外延——對恩斯特·卡西爾書評的評論”,出處同上,S.335-342。該文是對卡西爾第一篇文章的反駁。
第四篇:卡西爾:“符號概念的邏輯”,發表于《理論》4,1938,S.145-175.該文是對第二篇的反駁。現收入卡西爾:《符號概念的本質與作用》一書。[7]
第五篇:卡西爾:“什么是‘主體主義’?”,發表于《理論》5,1939,S.111-140。現收入《知識、概念、文化》一書。[6](P199-229)
第六篇:馬克-沃高:“什么是‘主體主義’?——對恩斯特·卡西爾同名文章的評論”,發表于《理論》6,1940,S.66-74。該文是對第五篇的反駁。
第七篇:卡西爾:“新近的康德文獻,以及對馬克-沃高《康德判斷力批判四論》(1938)一書的書評)”,發表于《理論》6,1940,S.87-100.
上述文章中,第一至第四篇涉及的核心主題就是:如何理解概念,尤其是卡西爾符號形式哲學中的“符號”概念?這一問題占據了卡西爾和馬克-沃高爭論的核心地位。而第五、第六篇涉及卡西爾對烏普薩拉學派的整體批評,以及馬克-沃高基于這一學派的立場而做的反駁。至于第七篇,則涉及到兩個人對康德審美判斷力的不同理解。因此毫無疑問的是,第一至第四篇是兩個人爭論的關鍵文本,因而也是我們重點考察的對象。同時要指出的是,由于馬克-沃高在第三篇文獻中并沒有對其論點提出強有力的反駁或修正,第四篇的主要內容主要是卡西爾對其符號形式哲學而非其概念論的重新表述,因此我們的敘述主要集中于第一、二兩篇爭論文獻上。
三、卡西爾在“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對馬克-沃高同名著作的評論”一文中對馬克-沃高的批評
卡西爾首先認為,對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之關系的追問,屬于邏輯學的根本問題,是哲學概念論的開端。作為康德批判哲學的繼承者,他主張,一切批判的哲學工作都要努力使概念的這一雙重關系不致于破壞概念意義的整體性。但是他也看到,如果這個意義是由兩個完全不同的要素構成的,而且二者不能回溯到彼此,不能相互重合,那么其危險就在于,這一方法論上的二分性將會導致形而上學的二分性。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一個“辯證法”就是難免的了。[6](P165)
在他看來,馬克-沃高在《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一書中的成就就在于,他清楚地看到了這一辯證法。“這一研究旨在證明:迄今為止的全部邏輯學史都在這里展示的問題上[即辯證法問題]上失敗了。”[6](P166)按照馬克-沃高的觀點,所有邏輯學理論都不能承受嚴格的分析,除了放棄迄今為止的提問形式之外,沒有走出這一困境的任何出路。
在這里,卡西爾對馬克-沃高在《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一書中的主要觀點作了簡要介紹。馬克-沃高主張,對概念的邏輯分析必須以其內涵為出發點,只有在內涵之中,我們才能洞見概念的本質。只要主張外延是概念的構成部分,那么就會導致“對立思想之間的某種辯證聯結”。在馬克-沃高看來,沒有一個傳統概念論走出了對概念和外延之關系的比喻式描述。內涵與外延、普遍與具體既相互構成整體,又相互分離。總之:概念規定和被統攝在概念之下的東西具有歧義性。他認為迄今為止的全部邏輯理論(形而上學的、現象學的、先驗邏輯的、心理學的、唯名論的、卡西爾的功能論的,等等)都具有這一歧義性:它們以不同方式來回答內涵-外延問題,但是都沒有擺脫辯證法的陷阱。馬克-沃高主張,既然各種手段都不能將概念論中的這個“惡”連根拔起,那么只能割斷內涵和外延的聯結。[6](P168)
對于馬克-沃高的上述觀點,卡西爾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第一,針對馬克-沃高關于“比喻式描述”的批評,他持贊成態度,但是認為,產生這一困難的源頭在于語言領域。“一切語言表達就其真正的基礎和心理學起源而言都是具體的對象表達,一切對象性都是與時間和空間交織在一起的。”[6](P168-169)因此,語言概念在表達特定的邏輯或科學問題時,不免混入特定的時空伴生表象。語言的這一“具象”現象不僅存在于原始語言之中,同樣也存在于成熟語言之中。他舉例說,就連“概念”(Begriff)這個概念本身都具有“用手抓取”這一具身性質,而“內涵”(Inhalt)和“外延”(Umfang)都無非是時空比喻。在他看來,這也不是什么缺陷,而是人類語言的真正成就。因此,被馬克-沃高視為概念之弊端的“比喻式描述”,在卡西爾看來不僅符合人類語言發展的特定方向,而且甚至是有益的。
第二,對于馬克-沃高所指責的內涵與外延之關系中的“辯證法”問題,卡西爾同樣提出了自己的詰問。馬克-沃高的觀點是:任何一個假設了概念內涵與外延的邏輯學說都會陷入錯誤的辯證法。這是因為,這一辯證法是由一個雙重思想構成的:概念是一個規定,但是,歸之于它之下的東西一方面不能被思考,另一方面卻必須與這一規定有關系。馬克-沃高認為,要避免這一辯證法,就必須犧牲掉其中一個思想。他主張放棄掉第二個思想,也即外延這一要素,只按照內涵來理解概念。對此卡西爾則認為,內涵與外延的問題古已有之,而馬克-沃高的方案與其說是在治病,不如說是在破壞概念這一有機體,意味著“概念的終結”。[6](P174)
和馬克-沃高僅僅以“橫向視角”考察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之關系的做法相反,卡西爾訴諸的是把概念與對象和現實性關聯起來、并在這一關系中看待概念之作用和功能的“縱向視角”。他認為,誠然每個概念都代表著確定的“意義整體”,但是,概念同時也包含著與雜多性與特殊性的關系。“如果沒有這一關系,那么概念就以邏輯的、知性的方式停留在隨便某種意義之中,但是它不再能夠傳遞任何客觀知識。”[6](P175)概念的積極作用根本不在于其“被思”,而在于通過它認識對象,“與對象發生關聯”。這一“對象關聯”是不能從真正的概念中抹殺掉的東西,只有通過這一關聯,對“外延”的審視才會必然地、不可避免地進入到對概念的考察之中。概念的純粹知識意義恰恰在于,它使我們能在規則之下把握、規定經驗-特殊之物。因此,如果拆散了內涵與外延的聯系,那么盡管可以避免錯誤和矛盾,但是卻決不能設定任何“真理”,也不能設定任何經驗有效的、經驗可用的知識。在卡西爾看來,概念不僅要保證“普遍”與“特殊”的統一,更要成為打開“特殊”王國的一把“鑰匙”,而這,正是擺在一切概念論之前的根本要求。[6](P176)
在卡西爾看來,實際上我們一直在尋求在“普遍”與“特殊”之間建立起嚴格相關性。如果說,馬克-沃高認為,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是相互獨立的,各自有其意義的話,那么卡西爾則以為,即便在概念的形式和內容之間“完全可以從思想上區分開來”,這也絕不意味著可以在某種素樸的、物化的意義上把它們分開來。一種介于形式和內容之間的“間層”是不存在的,“因而對二者而言不存在相互分離,而只存在相互共在——一種互為條件性的關系。”[6](P178)總之,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是相互需要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共同完成認識對象的任務,而且它們也只有在這一共同作用中才能相互區分開來。
實際上,卡西爾正確地看到,馬克-沃高的懷疑針對的是概念一般的可能性,即:在嚴格的邏輯分析之下,每一個包含著兩個要素的概念都是異質性的,是彼此難以協調的,因此我們的經驗概念難以向我們傳遞物的真理。但是在卡西爾看來,自然科學中的概念和定律對此構成了最有力的反駁:“沒有一個定律不是已經在其表達中包含著對某個完全確定的經驗對象之領域的指涉,不是與具體的、對此領域有效的諸規定聯結在一起。”[6](P178)而且,表達定律的概念只有從某個物理現實的整體中抽出某個特定的范圍時,它才能獲得真正的、具體的意義。如果像馬克-沃高一樣反對概念的經驗運用,那么自然科學從一開始就是成問題的了。而且,自然科學概念構造中的內涵與外延之關系,在其他領域中也是適用的。[6](P183)
因此,馬克-沃高揭示的前科學思維中的邏輯問題,即概念外延的不確定性問題,不能被普遍化并簡單地被轉渡到自然科學知識的邏輯上,因為后者的使命就在于去克服這一不足。而這正是一門具有批判指向的知識論不同于一門具有形而上學指向的邏輯學的區別所在:前者中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之間具有動態關系,而后者則視其為靜止不前的。[6](P186)卡西爾用黑格爾在行星定義上所犯的錯誤和科學史中對化學元素表、放射活動認識為例,表明自然科學知識中的概念之內涵與外延處在一種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關系之中——而且它們必須處在這種關系之中:
經驗和思維在這里保持平衡,并持續地相互完善。借助觀察及其持續作用,理論通過不斷將新的規定和關系納入自身的方式改造著概念的內涵;正是通過這一改造,它才有能力對概念的具體運用情形予以越來越完善的概觀,越來越精確的整飭。通過這一整飭,外延不再成為單純的堆積——它變成了體系,變成了一個不僅通過概念得以統握、而且從某個確定的中心點出發而得以理解和構造的整體。[6](P192-193)
卡西爾進一步指出,當我們從經驗概念進入到純粹的數學概念之中時,就會發現在內涵和外延之間的可能關系之間存在著同樣的多樣性。總之,不論從數學知識還是從自然科學知識來看,馬克-沃高的主張,即內涵與外延的關系不屬于概念的本質,因此要從邏輯學中剔除出去,是難以實現的。“概念的本質只有通過它在知識構造中所充實的功能才能得以定義。當我們切斷內涵與外延的紐帶并進而宣稱,這一關系只屬于包含在這一概念中的東西,而不屬于概念自身時,這一功能毫無疑問就枯萎了,甚至它原則上都成了問題了,概念便會失去其真正的生命力。”[6](P196-197)
四、馬克-沃高在“恩斯特·卡西爾哲學中的符號概念”中的反駁
當卡西爾在寫作“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對馬克-沃高同名著作的評論”一文時,他只注意到,馬克-沃高在其著作的結尾處預告說,他要寫一篇解釋卡西爾的符號概念的論文。[6](P174)由此判斷,他在寫作這篇文章時,他還沒有讀過馬克-沃高“恩斯特·卡西爾哲學中的符號概念”一文。反過來說,當馬克-沃高寫作此文時,他已經讀過卡西爾的上述書評了。因此,這篇文章雖然看起來是要評論卡西爾的符號概念,但其實重點卻在反擊卡西爾對其概念論的批評。
我們跳過他對卡西爾符號形式哲學的一般介紹,直接來看他對后者的符號概念的批評。在他看來,卡西爾的符號概念中包含著要素的雙重性問題,即存在于感性給定和意義充實、質料與形式、記號和記號活動之間的對立性問題。[8](P289)如何理解二者之間的關系?在他看來,對卡西爾符號關系的積極闡釋是辯證法式的:在兩個要素的對立性之側,還有二者之間的同一性思想。第一個思想是明確表達出來的,而第二個是作為結論從特定的概念規定中推論出來的。[8](P291)
為此,馬克-沃高做了如下證明:
第一,卡西爾把感性給定和意義充實、質料與形式的關系刻畫為嚴格相關的關系。這一思想的結果是這一假設,即交織在一起的相關要素具有同一性。按照卡西爾的觀點,記號和記號過程不是實在的兩個要素,而是具有“互為條件的關系”,因此,其中一個要素必然包含著對另一個要素的思想。用A和B來代指這一關系的話,那么A和B相互規定,因此難以區分開來。這一思想是與卡西爾認為A和B在思想上可區分的觀點難以調和的。
另外,如果認為兩個要素的對立性只是“思想上的”,那么這就意味著,形式可以忽略關于質料的思想而自為地有其意義。但是,卡西爾對相關依賴性的主張則認為,只有通過與質料的關系,形式才能獲得確定的思想內容,它的意義是通過質料而獲得的。也就是說,形式并不具備獨立的意義。這一點反過來也適用于質料。這樣,對立性和同一性就同時存在了,然而這是不可以接受的。[8](P292)
第二,對記號和記號物的分析也可以得到類似的結論。馬克-沃高認為,卡西爾認為記號關系的特征就是:對記號的理解同時就是對記號物的理解。這一思想對卡西爾對“再現”的闡釋是關鍵性的。但是,這同樣會產生二者的同一性問題,就像之前對A和B所做的分析一樣。[8](P295)
第三,通過具體分析卡西爾提出的符號功能的三個類型(表達、再現、純粹指義)[9],馬克-沃高認為,上述雙重思想的矛盾在這三個類型中都是存在的。對此,我們簡述如下。
在表達現象中,實際上存在著兩個思想:對特定神話表象中的表達知覺而言,記號和記號物處在實在的同一性之中;在對他者的神話表象、主要是在對陌生心靈的把握中,它們處在具體的整體之中。前者是說,當我們以反思的方式、在神話思維之外看待神話時,就會發現,諸如“圖像”和“物”等區分,其實對神話而言都是陌生的,實際上它們處在某種“實在的同一性之中”。這就意味著,表達意義附著于神話知覺本身,表達現象作為被意義充實的整體,是自己解釋自己的。馬克-沃高指出,如果表達知覺中不存在感性和意義的區分,那么這就是與他對“符號”的定義是不一致的:符號是被意義所充實的感性存在。[8](P298)后者是說,如果像卡西爾主張的那樣,表達知覺乃是一個具體的整體,是一個感性與意義、記號與記號物之間的“不可分離的關聯”,那么這一關系同樣適用于對陌生心靈的把握。而這同樣存在著類似于上述“實在的同一性”所面臨的困難。總之,不論是哪一種關系,都難以避免兩個要素之間既同一又區分的“辯證法”。
在再現功能中,馬克-沃高同樣認為,卡西爾的思想面臨著雙重思想的困難。一方面卡西爾認為,存在于感性給定和作為意義充實的再現之間的區分,實際上是一種理性的區分,不是實在的區分;另一方面,如果二者之間是“具體的整體”的關系,那么就不能在二者之間做出區分,但是卡西爾的意思恰恰是:一個再現之所以是再現,只是因為一個當下只有通過再現才獲得其規定,也就是說,這里存在著“意義借予”、“意義”充實的活動。在質料與形式、當下與再現之間,這里同樣存在著既同一又區分的“雙重思想”。[8](P300-319)
在純粹指義的符號功能中,也就是科學知識的構造概念中,馬克-沃高認為,“嚴格說來,全部符號形式哲學無非就是卡西爾概念論基本思想的擴展和深化。”[8](P324)他認為,卡西爾概念論歸結起來就是:“多中之一”。不過,這個“一”不僅是屬種意義上的“一”,更是關系意義上的“一”。卡西爾一方面認為,必須在“質料”與“形式”、“特殊”與“普遍”等等不同要素之間做出區分,另一方面又在強調,這種區分僅僅是“理性的區分”或“思想的區分”。在馬克-沃高看來,這仍然是“雙重思想”。[8](P328)
在這里,我們也順便簡單介紹一下第三四篇文獻中的爭論情況。在第三篇文獻,也即馬克-沃高的“內涵與外延——對恩斯特·卡西爾書評的評論”中,作者重申,任何一種關于概念的理論都在內涵與外延之關系上難免矛盾,這迫使他主張在二者之間“徹底了斷”,而且這是解決概念問題的唯一方式。此外,他還對卡西爾提出的一些具體批評做了回應。[10]總之,馬克-沃高在這篇文章中并沒有提出真正的反駁或對其思想的深化。
而卡西爾在其“符號概念的邏輯”一文中,也沒有對馬克-沃高提出的“辯證法”問題、“雙重思想”等要害問題提出新的、真正的答辯或反駁。他聲稱,在進入到具體的符號形式哲學之前,首先要再一次澄清概念自身的結構及其可能性這一基本邏輯問題。有意思的是,卡西爾在這里提出了分析的邏輯和綜合的邏輯、同一性邏輯和關系邏輯的區分。總之,對嚴格科學意義上的邏輯而言,邏輯經歷了從追問思維與存在之同一性的分析邏輯,到追求二者之可能聯結與關系的綜合邏輯的演變。[7](P204)這是理解其符號概念和符號形式哲學的基本立場。而接下來的文字,則是對其符號形式哲學的再表述。
五、對卡西爾與馬克-沃高之爭的再審視
卡西爾與馬克-沃高圍繞概念展開的爭論,涉及到如何理解概念本身,以及如何理解卡西爾的“符號”概念及其符號形式哲學等問題。對此爭論,國內外學界鮮有討論,僅有的少數文獻,也多集中于邏輯學或與此緊密相關的分析哲學領域,從其他角度切入的探討少之又少。可以說,這一爭論為我們的后續討論留下了大量空間,無論是從哲學史、邏輯史的角度,還是從知識論、科學哲學的角度,都有可繼續闡發的豐富可能性。在這里,筆者只就幾個基本問題提出自己的初步理解。
第一,需要把這場爭論放在一個特定的邏輯發展背景中去看待。馬克-沃高關于放棄概念外延以保全概念內涵的主張,無疑應和著邏輯學從傳統邏輯到數理邏輯演變的趨勢。在這一演變中,概念的外延由于與經驗世界的聯系而面臨著公理化的困難,而且就連“概念”這一概念本身也面臨著羅素悖論的難題,因而放棄概念的外延,似乎成了在現代邏輯語境中處理概念問題的一個必然選擇。然而,馬克-沃高沒有看到的是,如果科學知識中的概念不能在內涵和外延之間(或類似于內涵與外延的要素之間)建立起一種動態的、功能性的關系的話,科學知識就根本不可能產生出來,因為科學知識的概念究其根本是與經驗對象有關的。因此在這場爭論中,卡西爾的立場無疑是更為可取的。
第二,不過,這場爭論也引出了一些值得進一步思考的重要問題。其一,如何理解概念的內涵與外延之間的“同一性”和“對立性”所造成的“雙重思想”問題?按照馬克-沃高的觀點,內涵與外延之間要么只具有同一性,要么只具有對立性,任何主張兩種不同的思想要素之間既同一又對立的立場都是難以成立的。這一觀點在邏輯上是難以成立的,研究表明,事實上就存在一些概念,它們不必彼此同一,但卻可以彼此規定對方。[4]其二,上述問題牽涉到一個更為根本的哲學問題:內涵與外延、形式與質料、感性與意義等對立的思想要素之間的區分到底意味著什么?如果馬克-沃高的指責并非空穴來風的話,那么我們一定要問的是:既然這些要素本來就是同一的,是同屬一個整體的,那么又如何談得上它們的“聯結”、“意義給予”等基于對立性假設的溝通活動?卡西爾把這些區分統統歸之于“思想的區分”,這雖然契合于他的符號理論的初衷,即強調符號和符號性的知覺所具有的將感性和意義先天地融為一體的功能,但是也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很大的懸念:是不是所有的概念對子都可以用一個“思想的區分”來打發掉呢?顯然,問題并非這么簡單。當然,對這一更大問題的探討顯然已經超出了本文的范圍,只能留待后續的思考。
注釋:
①馬克 -沃高(Konrad Marc-Wogau),1902年生于莫斯科,1918年遷居于瑞典,1991年卒于烏普薩拉,瑞典哲學家。他于1932年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康德空間學說研究》(德文)。1946年之后一直是烏普薩拉大學理論哲學教席持有人。馬克-沃高主要從事康德哲學研究,但其研究進路受到邏輯實證主義、羅素等較大影響。在與卡西爾爭論期間,他曾擔任《理論》(Theoria)期刊共同主編,并在1958—1964年間擔任責任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