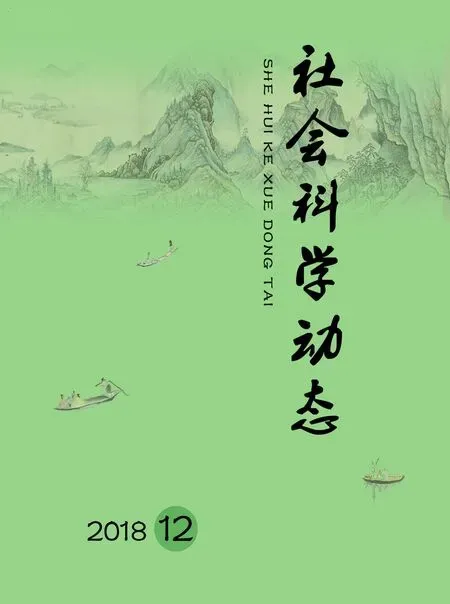中國傳統生態思想資源綜論之儒家篇(二)
胡 靜
(接上期)
二、儒家生態思想研究的重點方向
(二)各時代諸子學說
從知網的學術文章及相關學術會議的論文集來看,目前對于儒家諸子的生態思想的分析主要集中于先秦的孔孟荀、漢代的董仲舒、宋明張載、二程、朱熹、王夫之、王陽明等。這些人物往往具有劃時代的思想史意義或者其思想對儒家生態思想觀念的形成、體系的建構等具有特殊貢獻。從學者們研究的情況可以發現,越往近代,諸子生態思想的線索越清晰、內容越豐富、體系越完整。具體歸納如下:
1.孔子
學者們對孔子生態思想的考察主要切入的角度在其“仁”學思想,主要引用《論語》、《孔子家語》、《禮記》等文獻中孔子(或者借孔子名義發表)的有關言論來說明。如《論語·學而》的“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述而》的“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孔子家語·弟子行》的“啟螫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等等。主要突出的是孔子對自然生命的尊重與愛護的態度及其由此對人的生活方式特別是統治者提出的為政要求。對天人關系問題的生態意義的理解,孔子代表性的觀點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能“言”、有“言”是人類的特點①,而“天”卻無聲無臭,不喜不悲,所以“四時”之“行”、“百物”之“生”都是自然而然的現象,其背后并不是由某種人格意義的主觀意志主宰的,而是由其自然本身內在規律決定和推動的。這種天道的自然運行是一種不由人的意志改變的力量,而人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動的范圍、方式、內容、成果等也要受到這種力量的制約。因此,一旦人類的行為違背了自然天理,就必然會受到懲罰,所謂“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八佾》)。很明顯這其中蘊含著值得思考的生態意義。
2.孟子
孟子對人與自然關系已經有比較明確的表達,如學者們經常引用的《孟子·盡心上》中的句子:“君子之于萬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在這段話中,孟子清楚地指明了在愛、仁、親之間存在事實上的層次差異與邏輯關系,不僅突出了人及其社會生活在天人關系中的核心地位,同時也彰顯了生生才是仁道的起點和根本。因為親親就是基于由“生生”之道而產生的自然情感和自然現象。沒有對親親中生生之道的深刻領悟,則難以行忠恕于他人,做到仁民。而如果連自己的同類都無法推恩,那么就更不可能產生護生萬物的意愿和行動。反過來,如果先愛物而不仁民,或先仁民而不親親,則是將愛與仁的行動直接建基于人的個性化的感性或理性,而抽掉了作為人性之普遍性來源的自然基礎。這就與儒家仁道本于天道的邏輯相違背了。這是孟子生態思想的第一個層次。孟子生態思想的第二個層次是探討了人如何才能夠完成天賦的養護萬物從而維系人類的生生責任。孟子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盡心上》)這里的邏輯前提是確定人來自于自然,因此只要人運用自身的認知和反思能力,由認知人性始,則能夠達到對自然本質和萬物之性的認知。而發展這種認知和反思能力,使人性得以涵養、保全、充盈,就能夠自然而然地處理好天人關系了。孟子生態思想的第三個層次是法度的保障:“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洧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梁惠王上》)在這個政令性的觀點當中包涵了對萬物生長有“時”的自然規律的認知,強調只有尊重自然規律才能確保自然的生機勃勃,從而才能滿足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需要。由以上三個層次的分析可見,孟子的生態思想已經具有比較清晰的理論邏輯和比較完整的理論結構。
3.荀子
與孟子一樣,荀子也強調萬物生長有“時”,人類在生產生活中對自然資源的利用必須以時禁發。此觀點在《荀子·王制》的“圣王之制”中有清楚的論述。但是,荀子最重要的生態思想貢獻在于他對天人關系的理解更加細致,論述更為明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本體論層面強調天是萬物生命的源頭,是萬物生長變化的根本原因,指出“天地者,生之始也”(《王制》),“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禮論》)“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天論》);二是既具有天人感應的觀念傾向,指出“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荀子·宥坐》)②,又認為天沒有主觀意志,不會主動干預人事:“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也輟廣”(《荀子·天論》)。兩種觀念結合起來看,說明荀子認為天道無私,真正對人事發展起決定作用的乃是人本身③。人的行為能夠與天道相符合,就是為善,不符合則是為惡。為善或為惡所得到的福禍不過是自然進程在人為的順應或干擾下產生的必然結果,也就是福禍自招的意思。所以人類的活動才應當特別謹慎;三是認為天人職責相分。荀子指出:“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如是者,雖深,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謂不與天爭職。”(《天論》)但是,“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圣人然后分也。”(《禮論》)也就是說自然對于萬物包括人雖然有生育之功,且萬物之間存在互養共生、相須相資之實,但是真正能夠使自然萬物的存在價值得到體現和實現的卻是人。這就確立起了人在與自然的關系中的主體地位與責任根據。四是強調制天命而用之。荀子認為,“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性惡》),強調知天的目的在于致用于人事,這表明其在天人關系問題上堅持人本主義的生態觀。在他看來,盡管自然力量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是人卻可以通過主動作為參贊天地。所謂主動作為就是順天時盡地利,使萬物達到“治”的狀態。這種以人及其活動為中介而獲得的“治”的狀態,簡單來說就是使進入到人類視域中的自然世界,或者說人化自然界及其中的萬物,仍然如同在自然條件下一樣,能夠各安其位、各行其是、各得其所、各正性命。這就要求人的活動必須建立在對天道具有正確認知的前提下,以正確的認知為指導而進行的參贊天地的人為之“治”,才能做到成物之性、盡物之利,而人類自身也才能獲得更好的生存與發展的機會和空間。所以他說:“天有其時,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謂能參。舍其所以參而愿其所參,則惑矣。”“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原于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天論》)五是高揚人性的力量。荀子認為人與萬物一樣都是稟賦了天道而產生的,“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人性就是人所稟賦的天道,它內在地蘊含了人類活動的合理、正當的傾向。因此,人只要涵養人性,就自然能夠感受到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正當的,從而在人類活動中將這種合理性與正當性實現出來,達到參贊天地化育萬物的效果,使萬物各正性命、各得其宜、生生不息:“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也,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天論》)
4.董仲舒
董仲舒的生態思想資源最為學者們稱道的就是正式提出了“天人合一”理念:“以類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陰陽義》) 盡管他對天人關系進行了神秘化解釋,但細究起來,在他的思想體系中,自然其實已經擺脫了純粹自然意,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化自然,換句話說,人與自然是在人文意義上合而為一的。他說:“事物各順贊名,名各順于天。天人之際,合而為一。”(《深察名號》)“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立元神》)可以看到“名”這一人文化的事物,具備了作為萬物與天之間的媒介的作用,也正是因天道而正“名”④,天人合一的關系才能夠得到理解和表達。所以在這樣一個人文世界(包括人化自然)中,人與天地一樣成為萬物之所以是其所是的根本。萬物離開天地固然無法孕育成長,但是離開人,離開建立在禮樂基礎上的“名”,萬物就不是其所實然的存在狀態。可以說,董仲舒的這一思想是極其深刻的,從生態意義上講,我們所講的自然與人的關系確實是以人的存在為前提加以理解的。從根本上講,人是無法脫離人的立場去界定萬物的存在的,當然也就不可能脫離人的存在去討論生態保護的問題。這是董仲舒生態思想的重要貢獻,也是我們認知自然與人的關系時必須客觀地面對的現實情境。此外,董仲舒將以近取譬的語言傳統發揮到極致,其對天人關系的描述極其經驗化,其思想的核心范疇之一“人副天數”,就是將人與天進行非常直接的對應比附,使人變成了天的異形復制品,就好像神仙化成凡人模樣,形態上雖不同,但本質上沒有變。這樣的天與人在本質上當然是合一的,而且是必然能夠感通的。既然人性即是天性,仁道即是天道,人動與天動兩相應和,那么人就必須隨時修養自己的天性,反思自己的行為,使之不背離天性、天道,從而實現與天之間積極正向的互動。董仲舒還進一步發展了孔子的“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 的思想,將仁道推及自然萬物,為儒家仁學賦予了明確的生態意義。他說:“泛愛群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為仁也。”(《離合根》)“質于愛民以下,至于鳥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謂仁?”(《仁義法》)
5.張載
雖然前有董仲舒首提“天人合一”的理念,但是作為一個范疇提出并作出更為深刻論證的是張載。因此張載及其思想在儒學乃至中國哲學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張載的生態哲學思想包括以下邏輯層次:其一,解釋宇宙(自然)生成及其運動機制。與儒學的“天”觀一脈相承,張載認為自然界本身有其內在價值。所謂內在價值不僅是指自然界為萬物包括人提供了存在和活動的場域及其條件,而且其天然地具有使萬物包括人生生不息的本質力量或運行機制。這種內在價值并非由人賦予而是客觀存在的,并且成為人類一切價值的根據,構成人類一切活動最根本的價值原則。其二,通過“性”與“能”范疇構建了天與人之間的基本格局與動態關聯。所謂基本格局就是指確定了自然(物)與人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是建立在“性”之一源的基礎上的。在中國文化中,性生相通,生性不離。也就是說自然(物)與人之間從存在性上講是平等的,這就等于確定了自然(物)與人共生格局的合法性。所謂動態關聯就是指天人合一不是既成性的,而是生成性的。張載提出:“天能謂性,人謀謂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圣人成能’。”⑤這就是說物是性能一體的,所以天物合一可謂是既成性的,但人之性與能卻有天人之分,而天人合一就是“盡性”,就是“成能”,是人發揮主體能動性實現自身天性或本質的過程。這種盡性成能的狀態可以借用馬克思所謂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得到很好的理解。這種對天人合一關系的生成性的理解意味著,人如果不能朝向成就自性⑥的方向作積極的努力,天人關系就可能面臨相背離的危機。其三,揭示了自然對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價值的規定性。張載的生態思想將《周易》的自然必然性與儒家的仁學倫理精神有機地結合起來,通過論證萬物之間同根不同質的客觀實在,確立了尊重多樣性的民胞物與的和合關系原則;通過揭示自然的內在生機,及由其所決定的萬物之間的相生關系,確立了人對自然萬物護生成全的責任擔當與道德使命,正所謂“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正蒙·誠明》)。不難發現,在這樣一種生態思想下,人的存在方式就只可能是關系式的而不是原子式的,其存在價值也必須表現為手段與目的的統一。由此可以說,正是通過張載的生態思想的邏輯展開,使《易傳》以降儒家參贊天地的思想獲得了更為全面深入的表達。
6.二程
二程(程顥、程頤)作為理學的創始人,其生態思想是與其天理觀相貫通的。二程的“天理”觀是其原創的范疇,正如程顥所說,是“自家體貼出來的”。其所謂“天理”是貫通自然萬物包括人類及其社會的,是整個世界得以存在和運動變化發展的根本原因。而儒家的“仁”則與此天理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是天理通過人所顯現的價值形態。所以天理流行處,仁道亦當流行。由此邏輯,仁道必然也會從人與自然萬物的關系的處理中體現出來。二程以天理觀為基礎的生態思想包括四個方面,一是“萬物一體”,二是生生為仁,三是自然審美,四是存理制欲。
與張載對天人關系生成性合一的認識不同,二程更加強調天人在本體上的絕對同一,認為“天人本無二,不必有合”(《二程遺書》卷六)。既然無二,那么就意味著人的社會存在實際上是自然生態存在和運動變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人與自然關系的應然狀態就是共生共振的,其所作所為與自然生態息息相關。自然生則人生,自然長久則人長久。如果人能體認到與自然的一體相通性,愛自然萬物如同愛己之四肢百體,則天人長久就是必然的發展趨勢;而如果局限于一己之私就無法體認到這種同體共生關系,使物我相互隔絕對立,將滿足私欲建立在傷害自然萬物的基礎上,其最終結果必然是玉石俱焚、同歸于盡。以這種天人關系認知為基礎,天理與人理、天道與人道當然也就是一致的。所以程顥進一步指出“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如果失去這種渾然一體的貫通性,就是不仁。人道之仁與天道之理由此達成了統一——由于“天以生為道”,所以“繼此生理者”的仁的本質就是“生生”,即仁者或者說儒家對于人的存在價值的理想規定就在于將這種天地自然的生生之理推行于人類社會生活當中。也是在天理仁道相統一的意義上,程頤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觀點。學者們已經論證,程頤此言當中的“滅人欲”并不是否定人的正當合理的需要,而是指克制或摒除超出正當合理需要之上的刻意需要或過度欲求。原因就在于與天理的中正平和相一致,人道也應該是中正平和的,所以人就應當堅持“理”所當然的存在方式,而摒除非“理”的、與“理”相違背的傾向。以此原則關照自然與人的關系,當然就要求用之有節,取之以時,存物之性,涵養生意。
此外,程顥生態美學思想也受到了學者們的關注。生態美學的核心就是人與自然互動而產生的美感。這種美感既源于自然的客觀呈現,又依托人的心理加工,從根本上體現著人與自然的和合關系。因此生態美學是生態哲學重要的理論形態。儒家自孔子就有“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論語·雍也》)的生態審美觀,董仲舒則有“仁之美者在于天”(《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的美學本體論。而程顥則將《易傳》所描繪的生生不已、大化流行的宇宙和諧而生機蓬勃的狀態作為美的最高境界,并由此產生了以“生意”為核心的自然審美觀念⑦。這是程顥生態思想獨具特色的內容。
事實上,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到北宋時期,由于人為活動引起自然災害頻發使生態危機成為儒家學者強烈關注的社會問題。對此,程顥曾有措詞嚴峻的論述:“圣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于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河南程氏文集》卷一,《論十事劄子》)這段話程顥是從國家治理的角度去談的,但是從中可以發現其所堅持的生態思想。首先是“圣人奉天理物”,使“各有常禁”而“財用不乏”,這是與儒家一貫的尊重自然規律、參贊天地的思想相一致的;其次是人“用之無節,取之不時”導致“物失其性”,這種行為違背了儒家節用、以時、成物成己的生態實踐原則;再次是只有“將養之”才能“有變通長久之勢”,提出了生態修復和可持續發展的思想。
7.朱熹
朱熹是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對前人,如周敦頤、二程、張載等皆有繼承與發展。朱熹通過對理、氣、仁、心、性、命、情等范疇體用性質和相互關系的分析揭示了天人關系的本質及其表現,此亦成為其生態思想的理論基礎。“理”是朱熹思想的核心范疇。朱熹認為萬物雖然眾相殊異,但是歸到理上卻是一,而這個“一”從事實來說就是“生”,從價值來說就是“仁”,所以他說“仁是個生理”(《語類》卷二十)。這種“生理”,不僅是指創生(新陳代謝、生生不息)是一種自然而必然的運動趨勢,也是指驅動創生趨勢形成的內在機理,所謂生之“心”。而后者更為重要。前者可以理解為具體的規律,比如四季的轉換帶來的生態變化,生命的繁衍與生老病死等現象,都是由這種意義上的“生理”所規定或決定的。而后者則強調在具象層面的“生理”之上還存在一種使這種“生理”產生的驅動力,類似于物理學上的第一推動力。也就是說,后一種“生”理是前一種“生”理得以產生的根據,或者可以稱之為“生欲”。正是因為從這兩個層面去講“理”,所以朱熹既說“天地以生物為心”,又說“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天地生物就是前一種“生理”的流行,而“以生物為心”或者說“生物之心”則是強調此“生理”的流行源出于其背后的自然“目的性”⑧。由此朱熹的生態思想便可以展開來說了。首先,從理一的層面來說,“天地之間,萬物之眾,其理本一”⑨,所以“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⑩。即自然萬物包括人雖然形態各異,但是其得以存在和生生不息之“理”據都是一樣的,這種生存本質上的共性決定了其相互之間本不應有隔閡與對立,而應該能夠感通移情、惺惺相惜。其次,從分殊的層面來看,“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此即是說,萬物包括人都是由天理流行而產生的造物,并且因此成為涵容天地之“生理”與“生欲”的載體,即具有“生”性。這種“生”性并無“偏全”之分,而是在萬物身上表現為對生或生生的共性追求(欲望)和本能維護。由此則可以得出:萬物與人在存在上具有平等性,或者說具有平等的生存權。再次,從物與人的差異性上說,朱熹認為,雖然萬物與人皆具“生”性,但是其他生物往往為“形體所拘”,不僅難以實現或只能部分實現與外界其他生命之間“生”性上的感通交流,而且無法體認其內在的天理?。人則獨具靈性,不僅能夠在生存實踐中體認到“天地怏然生物之心”,而且能夠自覺地“合內外之理”,使己、人、物之共性的“生理”得以貫通,在追求成己之性的同時,成人之性、成物之性。正所謂“此心愛物,是我之仁;此心要愛物,是我之義”?,“此心何心也?……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正如蒙培元先生所說,“實現理性自覺,實現‘天理流行’的境界,是朱子哲學的根本使命。所謂‘天理流行’,就是人與自然的完全統一,生生不息,萬物的生命因而得以暢遂,人則盡到人的責任,完成人的使命,從而體驗到生命的意義,感受到人生的快樂”?。
總之,朱熹的生態思想是通過其所構建的完整的“理—仁”學體系得以闡發的。基于理與仁的內在統一,朱熹構造了天理生物與人仁愛物兩條相向而行的邏輯線索,一方面,人物皆因生而得其理,理在人即為仁,理在物則為理,仁理本一,物與人因此具有了相通互愛的自然根據;另一方面,物不能自通通人,而人能自通通物,人的特殊資質使人自任了參贊天地“生理”的責任,這種參贊責任不僅表現為對每個人的生生與整個人類社會的生生負有責任,而且表現為對自然萬物之生生負有責任。所以人需要格物致知,正確認知物理人仁之本然,既要成物之性盡物之利以為人,又要成人之性盡人之能以愛物,此即《易·泰·象》所謂“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8.王陽明
王陽明的生態思想是與其心學立場緊密聯系起來的。首先,“心”是王陽明探討一切問題的基本視域。所謂“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這就是說,一切存在性都由心出發,由心的照應而顯現。自然與人的關系問題,同樣也是如此。在“心”的照應空場的情況下,自然的存在只是“寂”,也就是不顯、不動的狀態,因而其存在與否、如何存在等都脫離于人的意識之外,對人而言,這種存在即使存在也是毫無意義的,當然也就無法與人構成關系。反之,凡與人之間構成關系者,都意味著受到了“心”的照應,即是已經顯現其存在意義的存在者。與《周易》揭示的天地之一陰一陽生成自然世界的機理不同,“心”的照應是意義世界的生成機理。但是在王陽明,這兩個世界又并非是各自獨立的,因為“人者,天地之心”,也就是說,以人的存在為前提,我們對自然世界生成機理的“一陰一陽之謂道”的描述本身已經是一種為“心”所照應而賦予了意義性的結論。這實際上就取消了純粹自然世界存在的現實性。從這個視角來看,自然與人的關系本質就是意義的,即是以人為坐標來界定的,一方面,人以自身為立場,則需要在自然與人之間劃出分界,體現人的獨特存在性;另一方面,人以超越自身的立場,則可以認識到自然與人之間的同質性?。這兩種性質不僅是“心”所照應到的自然與人關系的全面本質,也是人自身的存在本質。因此人的活動的完整意義就在于同時滿足或實現這兩種性質。在王陽明看來,這不能理解為某一個體刻意的道德行為,而是所有人的“心”之明德。所以王陽明說:“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
其次,心是天理良知呈現的介質。王陽明認為“良知即天理”、“良知即道”,而由上文可知,天理是通過“心”來顯現其意義的,而良知可以理解為是天理在人心的全面映射。因此要使天理良知在每個人的“心”上光明地呈現出來,成為指導人的活動的依據,就必須保持“心”的干凈和敏銳,所以王陽明的致良知與朱熹的“格物”是不同的。王陽明將天地萬物包括人均納入到“心”的范疇,認為人們只需要將“心”打掃干凈,去除私蔽蒙昧,保持其照應天理、映射良知的功能能夠完全地發揮出來,那么天理良知就會自然地呈現在人之“心”幕上,而無須刻意追求。這樣人的首要活動就是對自身“靈明”之心的照顧保養。王陽明指出:“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這就非常清楚地說明了人的良知就是人心對天理的全面把握,在這一基礎上,當天理化入具體物象當中而成為物象自身的物理時,良知也就隨之成為其物理之意義化的表達——即理而命名,這樣,萬物的意義投射才得以完成,萬物才成其為它在這個意義世界中的自身,并與人發生關系。由此,人“心”只要能夠完全地呈現天理良知,在天理良知的引導下,便無需刻意算計思考就能夠遇事而化事、遇物而待物,無所不至,無不合理,“圣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圣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既然如此,人與自然在相處過程中如果存在矛盾,就說明“心”的作用沒有很好地發揮,以致于天理不彰、良知蒙蔽,而要解決矛盾,就必須修養人“心”,恢復“心”應有的功能,當此時,則“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見鳥獸之哀鳴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此所謂“必”說明的就是人在“心”如明鏡的情況下,必然能夠天理昭彰,從而循順良知、參贊天地,使萬物化育、成性存存、和諧共生。
由于王陽明將人“心”作為介質,使天理經由人“心”而照應為良知,人繼以良知為“明鏡”照應現實,在社會活動中實現體用合一。因此王陽明心學生態思想的重要意義就在于突出了人在自然與人關系中的主導地位,使自然的現實性存在成為一種人為性的存在。這種人為性,不僅是說現實的自然是一種意義性的存在,而且說明人的活動對于自然的現實存在狀態具有根本性的影響。人成為解決一切關系,包括自然與人關系問題的關鍵,人心明則關系順,人心昧則矛盾生。這樣,在萬物一體的認知前提下,人就不得不擔負起對己、對人、對物的全部責任。反過來,人履行對人、對物的生態責任——維護社會生態與自然生態之和諧共生關系的過程,在本質上也就是修心養性、使自身明德昭彰的過程,“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由此,人與自然各正性命、各得其所。
9.王夫之
王夫之是明清之際的思想大家,其研究通貫儒學各個方面,不僅集前人思想之大成,而且自成一嚴密體系。與中國古代哲學家一樣,天人關系問題也是其思想的邏輯起點。從生態視角看王夫之的天人關系思想及其整個思想體系,可以發現其基本的理論邏輯與構架。其一,氣本論。王夫之的思想基礎是氣本論,其與張載的氣本論有非常明顯的承繼關系。通過確立氣本,不僅解決了萬物之源與萬物之生的問題,也解決了世界應然的存在狀態(動態、均衡、和諧)的問題。“天下之物,皆天命所流行,太和所屈伸之化,既有形而又各成其陰陽剛柔之體,故一而異。惟其本一,故能合;惟其異,故必相須以成而有合。然則感而合者,所以化物之異而適于太和者也。”?其二,天人之間本和質異、由分致合的邏輯關系。王夫之由氣本論論證了天人關系在本質上的同源性與和諧性,又通過對質、氣、理等范疇及其關系的闡釋說明具體人物性命的差異,突出人的理性之可貴與責任之必然,指出要解決天人關系因質異而造成的失和,必須經由相天、竭天、以人造天?的過程,將被拘蔽的“天人合一”?解放出來,實現由分致合。
具體來說,王夫之的生態思想有幾個重要的方面值得注意。其一,王夫之天人論域中的“天”徹底擺脫了傳統天人之學中的人格神意,成為無意向性、目的性、獨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具有普遍性的客觀存在。由此天人關系真正落實為自然與人的關系,表現為二者之間具體而現實的因應關系。“天不可以體求也,理氣渾淪,運動于地上,時于焉行,物于焉生,則天之行者爾。天體不可以人能效,所可效者,其行之健也。”?其二,天人之間的因應關系是一種互動關系。這包括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方面意味著天人是相分的,所以才會有互動性;另一方面說明天人具有相合的可能性,所以因應互動才能實現。天人通過因應互動,人以其氣質稟賦天理而成性,通過盡人之性而發展、發揮認識與實踐之能,以其能而從天之治,盡人道以成參贊自然化育之功,從而合于天道,成己成物。“因天之能,盡地之利,以人能合而成之。凡圣人所以用天地之神而化其已成之質,使充實光輝者,皆若此。”?其三,人的活動之自為性。王夫之對自然與人的認識較之前的學者更為深刻。他不僅認識到自然造物的無意向性,而且認識到人的認知與實踐的有限性。王夫之認為,“天無為也,無為而缺,則終缺矣”,而“人有為也,有為而求盈,盈而與天爭勝”。也就是說,自然萬物并非按照人的需要形成的,因此從人的視角來看其各有缺陷,且容易導致“吉兇常變”。在這種情形下,人類活動就不會止于一般意義上的因應互動,而會通過主動改造自然,追求實現更加圓滿的生存狀態。但是受到“血氣心知之所限”,改造自然、與天爭勝的結果往往是成敗相乘,所以“固盈”是不可求的。可見王夫之認識到,雖然人的主體自覺自為是人的可貴之處,但是這種自覺自為最終會受到“自然之秩敘”的限制。這種“自然之秩敘”的限制,一方面表現為人的認識和實踐能力先天地具有有限性,只能對于那些切近自身需要的事物加以認識和追求,“不切于吾身之天地萬物,非徒孔、孟,即堯、舜亦無容越位而相求”?,所以“人心不可以測天道”?;另一方面表現為人作為氣聚而化成的具體物,其質各不相同,對天道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拘蔽”。因此即便只是因應互動,人的活動也無法做到完全地合乎天道,更不用說自覺自為的與天爭勝的活動更會受認識上的“拘蔽”影響而導致實踐結果的偏差。在王夫之看來,嚴格意義上,只有圣人才能夠“退藏于密,上合天載”,真正實現天人合一?。對于大多數人,包括君子賢人來說,都只能通過窮理盡性,使人與物的先天缺陷通過人的合乎物理人性的自覺有為而實現揚長避短、優勢互補:“故緝裘以代毛,鑄兵以代角,固有之體則已處乎其缺,合而有得,而后用乃不詘。”?也只有這樣,人才能不斷糾正、減少和避免不合乎天道的行為偏差,使自己的活動臻于天人合一之至善,接近圣人所達到的天人境界,從而擔負起參贊天地之化育的責任。其四,處理天人關系的基本原則或精神。王夫之基于其自然觀與人為觀,提出盡性、盡人道的關鍵最終還是要落實到繼天之道:“天人相紹之際,存乎天者莫妙于繼。”?這一“盡”一“繼”的基本精神或原則就是“發己自盡”與“循物無違”。所謂“發己自盡”,就是“凡己學之所得,知之所及,思之所通,心之所信,遇其所當發,沛然出之而無所吝”。而“循物無違”,則是指“依物之實,緣物之理,率由其固然,而不平白地畫一個葫蘆與他安上”。說到底,“發己自盡”、“循物無違”就是要求人要效法自然“不復吝留而以自私于己”,“不恣己意以生殺而變動無恒”,“順其道而無陵駕倒逆之心”,使“物之備于我,己之行于物者,無一不從天理流行、血脈貫通來”,那么就能夠實現天人和合的美好圖景:“物之可以成質而有功者,皆足以驗吾所以行于彼上之不可爽”,“方春而生,方秋而落,遇老而安,遇少而懷,在桃成桃,在李成李”,“道以此而大,矩以此而立,絜以此而均,眾以此而得,命以此而永”。反之,“內不盡發其己,而使私欲據之;外不順循乎物,而以私意違之。私欲據乎己,則與物約而取物泰;私意達乎物,則芻狗視物而自處驕。其極,乃至好佞人之諛己,而違人之性以寵用之;利聚財之用,而不顧悖入之多畜以厚亡。失物之矩,安所失絜,而失國失命,皆天理之必然矣”?。此段文字中,王夫之對于人在處理自然與人關系時應堅持的原則與精神給予了清晰的表達。
三 儒家生態思想的邏輯構架與基本觀點
在中國古代,生態問題并不只是一個現實層面的社會治理問題,它還包涵著對人類自身何來何往的根本價值追問和對生命的美感體驗,因此在梳理古代生態思想資源,理解和把握古代生態思想的內在意蘊的時候,必須同時考慮到這些方面。整體來看,儒學是圍繞“人”來展開的。向上,強調知命與樂道,關注人之所從來與所將往的問題;中間,強調修身養性,關注個體現實的安身立命問題;向下,強調治事以禮法,關注社會生活的秩序性與和諧性問題。如上文分析所見,儒家討論自然與人關系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決儒學的立論基礎與終極追求問題。也就是說,在儒學中,天人關系是作為對“人”的存在從以上三個層面展開思考的必要條件納入其中的。通過對天人關系的界定,并根據這種界定,儒學得以完成對人的存在性質、存在價值、存在境界等的解釋。由此決定了我們對儒家生態思想的把握及其基本觀念的歸納也必須遵循這樣一種邏輯構架。簡要陳述如下。
首先,在第一個層面上,儒家生態思想回答了人之所從來與所將往的問題。儒家的基本觀點是,第一,自然是人類生命的起點與終點,自然與人本源于一。關于自然與人的生成問題或者說本源問題,最早是由《周易》的《易傳》作出了明確的解釋,即陰陽(乾坤、天地)的相互作用是萬物生成的根本原因。先秦時期,已經有將陰陽作氣解的思想,氣本論逐漸成為解釋萬物生成、變化的基本范型。到宋明以后,儒學的本體論更加精致化,以張載為代表,對自然萬物包括人的生成及變化作出了系統的解說。由氣本論立場,萬物之生乃氣之聚,萬物之滅乃氣之散;氣之聚散的差異形成了萬物之差異,萬物之差異不僅表現在各自具體的存在形態、存在方式、存在機制等方面,更表現在天性的差異上。但是就根源來說,這種具體的差異終將消失,回歸到氣的原初狀態。由此可以證得,自然與人在本源上是同一的,其根本質性也是一致的。進一步來說,自然與人在均氣同體的意義上一定是和諧統一的。第二,自然性是萬物包括人類的基本性質,自然的天性是純樸合理的。在中國古代各思想流派中,自然具有天然的正當合理性是一個基本的共識。而在儒家,關于人性的解釋雖然有精粗之別,但是都肯定人性當中自然而然的那一部分具有客觀的合理性。比如人自然而然的生理欲求都是得到肯定的?。反過來,超出人的自然天性規定的欲求則是不合理的。儒家認為人的天性是自然天道在人身上的體現,即明德。明德是人在后天的社會生活中能夠選擇正確行為的內在根據。不合理的欲求,包括生理層面與心理層面的,都是明德不明造成的,而不合理的欲求則是導致自然與人、人與人關系失序惡化的根源。同時,就其他生命來說,其天性欲求也都具有合理性,都應當被尊重和保護,因此人在自身的生存活動中不僅不能放縱自己的欲求對自然予取予奪,而且還要能夠成全萬物的天性欲求。即所謂成物成己。第三,自然為人類美好價值的衍生提供了依據,天人合一包涵著自然與人的情感交融。自然對于人類來說是一種先在的、強大的、豐富的、神奇的存在。盡管人類早期在自然力量面前過于弱小,但同時人類也發掘到了自身的生存優勢——認識與實踐能力,而這種能力恰恰又是自然賦予的。特別是對農耕民族來說,人們對自然是既敬畏又贊美的。自然也是人類認識和實踐的對象,人類從自然獲得生存的必要知識,領悟建構人類社會的基本原則,幾乎一切美好價值的源頭都在自然那里或者與自然有關。所以自然以及自然而然的狀態也成為中國古代先哲欣賞、體悟的對象。而在欣賞體悟自然美的過程中,人的明德之性也得以涵養、保全、充盈。此外,自然與人本源上的同一,使得二者之間存在天然的相親關系,如同親子同胞之間的血緣關系一樣。所以自然能夠成為人類寄情之所。而也正是這種情感的皈依使得自然與人的關系充滿互動的生趣。
其次,在第二個層面上,儒家生態思想指明了人類安身立命,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儒家的基本觀點是,第一,自然是人類生存活動展開的空間場域,自然條件是影響人類活動及其發展趨勢的重要因素。在《周易》中已經傳達了這樣一種基本思想。《易經》的卦象體現了陰陽運動所構成的環境條件的變化,從萬物包括人皆出于陰陽來看,這就實際上指向了自然條件與人文條件的變化。《易傳》則以文字的方式解說了卦象的意蘊:上天下地的立體空間、動態的自然條件構成了人類安身立命、上下求索必須充分考慮的前提條件。人類活動只能在這個前提下開展,并且受到這個大前提的制約。人類對這個空間場域及其自然條件的認識越充分,互動越良性化,其展開的活動成功的機率越大,反之則越小。第二,自然與人是相生相成的關系,從長遠來看,自然的存在質量與人的生存質量成正比。儒家以人為貴,強調人的自覺自為性。這一觀念在《周易》已經得到申發。《周易》經傳不僅揭示出自然與人的統一關系,而且揭示出二者在人類生存與發展中的不同意義。自然作為先在的客觀條件,對人類活動的開展既具有支撐性也具有制約性。而人類則需要因勢利導、因地制宜,將順應與改造有機結合起來,使自然以人化的面目轉換到人類社會這一場域中來,實現天人在這個場域的再和諧。所以事實上,在儒家,自然歸根到底是作為人類存在的條件而存在的,具有為人性。而儒家與人類中心主義的差異則在于,它是從一種倫理的視域去認識這個問題的。儒家將自然的這種為人性理解為一種仁的品質,將自然與人的本源關系理解為親子性的生生關系,從而使仁也成為人性的一種規定性。人類仿效自然之道即天道開展活動,就形成了人道。天道生生,人道亦生生;天道生人,人道生天。人道之生,就是所謂的參贊天地之化育,成性存存。由此,自然與人之間形成物質與能量交換的封閉循環,天人在更高層面實現了合一,獲得了生生不息發展的內在動力。反過來,人類如果為了自身利益的滿足而違背天道、踐踏人道,就是斬斷了生生鏈條,破壞了循環的封閉性,使天人相隔絕,物質與能量相互對抗、相互抵消、難以為繼,則天災人禍必然接踵而來。
再次,在第三個層面上,儒家生態思想強調對自然資源進行有效管理和合理利用,并將其作為執政者政治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的基本觀點是,第一,必須對自然資源進行有效管理。自然資源的管理是執政活動的重中之重。中國古代是農耕社會,對于自然資源管理的重視猶為突出。在《易傳》中就有古代圣王如何通過卦象利用和改造自然事物,教化民眾從事生產生活的例證。同時《周易》非常關注“時”,強調人類活動必須在合“時”的情況下開展,這其中就包涵了對自然資源取之以時的思想。而如前所述,在《周禮》中更詳細地記載了我國古代對于管理自然資源的職官設置及其職責的要求。后來程顥也指出北宋朝廷因為忽略了自然資源的管理而導致生態惡化。自然生態的狀況關乎人類個體與社會發展的質量。因此歷朝歷代都十分重視這項工作,不僅有各種政策保障,而且從禮法上也對民眾和政府的資源使用予以規范,形成了“以時禁發”等重要的生態治理觀念。第二,仁政的基礎就是使百姓能夠占有和享用維持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資源。在中國古代,土地資源及其上的產物是維持個人和家庭生活所必需的條件。儒家認為,只有那些能夠使百姓擁有這些條件,安居樂業的人主才有可能得民心而王天下。也就是說,占有和享用維持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資源是中國古代重要的民生問題、政治問題,社會管理者應當以保障并實現這一民生基本權利作為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孟子甚至將此作為衡量執政合法性的重要標準,人主王或不王,國家亡或不亡,首要就是看執政者能否解決好百姓的自然資源分配問題,因為有恒產者有恒心。如果解決得不好,使百姓流離失所,缺衣少食,上不足以贍養父母,下不足以供養妻子,那么就會帶來社會矛盾,威脅社會的安定與和諧。
總之,在儒家生態思想中,自然與人類的關系具有“合—分—合”的過程性。第一個“合”是指二者在本質上是統一的,“分”是指二者在表象上是有區別、有矛盾的。這種區別不僅是存在形態上的,而且是個性功能上的。自然大美無為,卻決定了人類是一種有限的存在,規定了人類活動的可能空間,提供了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必要條件;而人類則自覺有為,通過認識、利用和改造自然不斷突破局限,確證自身的優越性,并將自然納入到人類世界,賦予其人文意義。二者之間的矛盾則表現為人類活動對自然規律的背離,這同時意味著背離人自身的天性、明德和良知,其結果是導致自然、人類兩個世界產生危機。第二個“合”是指二者在人為的基礎上實現再統一。現實的人類社會與自然世界具有動態生成性,是自然規律與人類意志的結合體。隨著人類對自然規律的認知與把握不斷接近自然的本質,也就會同時接近人類自身的本質,反過來,人類對自身本質的不斷探索也會帶來對自然規律更全面深入的理解。當此時,人類活動就趨向合理化發展,而這種合理化發展必然是與自然規律相一致的。這就是人類與自然的再統一。由此,自然與人類進入相得益彰、相輔相成、持續發展的良性軌道。(完)
注釋:
① 如果從廣義而言,可以將生物之間“主動”的信息交流均稱為“語言”,甚至將人機之間的信息交流也稱之為“語言”。比如我們已知的計算機語言。但是在此我們僅僅只特指人類語言。
② 這與《易傳》中“天佑之”之說具有相同的意思。
③ 這同樣與《周易》的三才觀念是一致的。
④ 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論語·子路》)。董仲舒這里可以說與孔子的正名思想保持了一致,并且進一步將“名”之正的根據歸于天。
⑤ 《張載集》,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21頁。
⑥ “自性”在此是指源于自然、天道充盈的完整人性。
⑦ 《宋元學案》記載:“明道書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勸之芟,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唯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自得意,此豈流俗人所共見。”[明]黃宗羲撰,[清]全祖望補:《宋元學案》,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578頁。
⑧ 通常來說,目的性僅僅用來說明人類意識的傾向性,所以自然應當是無目的性的。但是在這里采取一種擬人的方式說明在自然創生萬物的背后,還有一種類似目的性的“意識傾向”。正如人類的意識傾向是有力量的,自然的“意識傾向”也是一種力量,正是這種力量推動著創生之天理的流行。
⑨ [宋]朱熹:《孟子集注》卷8,《四書集注》,中國書社1994年版,第271頁。
⑩ [宋]黎靖德:《朱子語錄》第2冊卷17,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87頁。
?? 《雜著·仁說》,《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卷第67,《朱子全書》第2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79、3280頁。
? 參見《朱子語類》相關論述。
?《大學二·經下》,《朱子語類》卷15,《朱子全書》第1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75頁。
? 蒙培元:《朱熹哲學生態觀(上)》,《泉州師范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
?《答季明德》,《王陽明全集(上)》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14頁。
? 同樣,從自身立場或超越立場,人也在人與人之間劃出分界或者認識到人與人的同質性。
? 《續編一·大學問》,《王陽明全集(下)》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68頁。
?? 《語錄三·傳習錄下》,《王陽明全集(下)》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106頁。
? 《續編一·大學問》,《王陽明全集(下)》卷2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68頁。
? 《張子正蒙注卷九》,《船山全書》第12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365頁。
? 參見鄧紅蕾:《王夫之“纟因缊—太和”和諧觀及其現代啟示》,《江漢論壇》2006年第1期。
? 參見張云江:《論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社會科學研究》2015年第1期。
? 《周易大象解·乾》,《船山全書》第1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698頁。
? 《張子正蒙注卷八》,《船山全書》第12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317頁。
?《讀四書大全說卷二·中庸》,《船山全書》第6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475頁。
?《思問錄內篇》,《船山全書》第12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423頁。
? 參見張云江:《論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社會科學研究》2015年第1期。
? 《尚書引義卷四》,《船山全書》第2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341頁。
? 《周易外傳卷五》,《船山全書》第1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1007頁。
? 參見《讀四書大全說卷一·大學》,《船山全書》第6冊,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445—446頁。
? 宋儒提出的“存天理、滅人欲”并不是對人的欲望的全面否定,而是否定那種超出自然而然的合理性的過分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