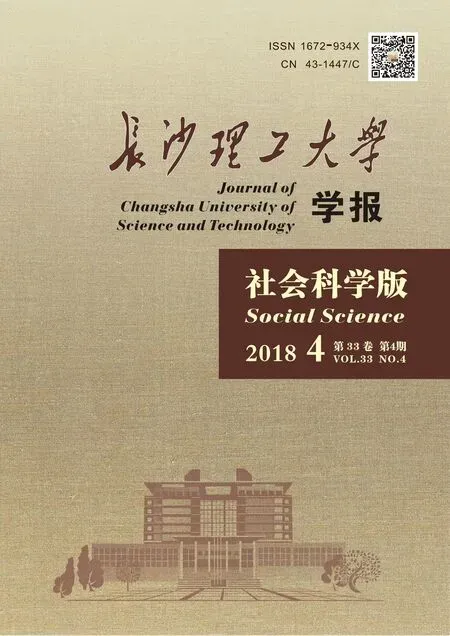工匠精神與工程理性的哲學認知
黃正榮, 張 浩
(重慶建工九建公司,重慶 400080)
一、引言
工匠作為一種職業始于手工業時代,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工具理性開始復蘇,工匠精神在機器大工業發展的基礎上不斷升華,以更加關注形式的、結構的、美學的和屬性的東西為特征,對于助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制造業的轉型升級發揮了重要作用。工匠精神中“工匠”注重匠人的專業操作技能,而“精神”則強調人的理性或理念的職業價值追求。所謂工匠精神,是指工匠對自己的產品或服務耐心專注、執著堅守、精雕細琢、精益求精、愛崗敬業、追求完美的精神理念,從本質上講,是一種職業精神,是職業品行和道德的體現,是工匠的價值取向和行為表現。長期以來,我們忽視了對工匠精神的認識與思考,沒有注意過或者意識到工匠精神超物質性的理性力量和核心價值,從而陷入一種經驗主義的窘境。
2016年,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工匠精神”,并在報告中指出:“鼓勵企業開展個性化定制、柔性化生產,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1]。近年來,工匠精神已開始成為學界和產業界討論的熱點,很多學者和企業界人士從不同的角度對工匠精神的內涵、性質、特征、價值、意義、培育路徑,工匠精神與工匠文化之間的關系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2]。 “更為重要的是,‘工匠精神’作為一種優秀的職業道德文化,它的傳承和發展契合了時代發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與廣泛的社會意義。”[3]工匠精神具有普世意義上的核心價值,無疑是當代學術界和產業界的焦點議題,將會占據哲學社會科學譜系的顯要位置,對工匠精神的思考和踐行必然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一項重要思想任務。目前,工匠精神的理論研究還處于零散、淺層、表象的肇始階段,尚未提升到哲學(精神哲學)的學理層次對工匠精神進行較為深刻而系統的思考和研究。為此,本文試圖從哲學的視角探析工匠精神的哲學內涵、工匠精神與工程理性的關系,以期達到對工匠精神更深入的理論認識。
二、工匠精神的哲學內涵
哲學作為理論化、系統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時代精神的精華。縱觀哲學史,哲學幾乎都是圍繞形而上學、邏輯學、認識論、倫理學以及美學等哲學門類來展開其理論與實踐問題研究的。工匠精神既是哲學的理論問題,又是哲學的實踐問題,它跨越了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兩大領域,這當中不僅涉及到純粹理性問題,而且也關聯到實踐理性問題,最終通過精神哲學將其統合起來。工匠精神是人的精神,人是理性的動物,古往今來都是哲學思考的對象。關于精神的哲學研究,黑格爾將人的精神發展分為主觀精神(一般心理學)、客觀精神(法哲學、歷史哲學)和前二者高度統一的絕對精神(美學、宗教哲學、哲學史)三個階段,從內容上講,這也是精神哲學的三個組成部分。精神之成為精神,或者精神之所以是精神,其區別于自然,就在于它里面所實現的對外在事物的外在性的揚棄和克服的觀念化活動,精神是理念的實現,其根本屬性是它的觀念性。從康德理性哲學開始,經過費希特、謝林,直到黑格爾精神哲學才真正建立起系統的關于人的理論學說。
一般意義上講,精神哲學的研究對象是人的精神,既要分析人的精神個體或自然本質,也要分析人的精神的共同(類)本質,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哲學問題,黑格爾在《精神哲學》著作(緒論)中指出:“關于精神的知識是最具體的,因而是最高和最難的”[4](P1)。在黑格爾看來,主觀精神指個人的精神,是“在與自己本身相聯系的形式中”的精神,即只在自身內存在的、尚未與外物發生關系的精神,因而主觀精神就只是一種主觀自由的精神。客觀精神是主觀精神之表現在外部世界(法的、道德的、家庭的、政治的、社會的等制度和組織)中的精神,即“在實在性的形式中”的精神。而絕對精神是主觀精神和客觀精神的統一,是“在其絕對真理中”的精神,即最終在人的哲學思維的最高階段上實現了對自已的完全認識的、主體與客體絕對同一的、完全顯示了自身的、完全達到了自由境地的精神。“絕對精神是永恒地在自身內存在著的、同樣是向自身內回復著的和已回到自身內的同一性;是作為精神性實體的唯一的和普遍的實體,又是分割為自己和一種知的判斷,而它對于這個知來說就是實體。”[4](P325)實際上,工匠精神已超越了主觀精神和客觀精神,它不是對主觀精神和客觀精神的否定,而是揚棄或否定之否定,從而上升到一種絕對精神,它反映了人的精神的類本質、主觀精神與客觀精神的統一,是人的精神之“自在存在著的普遍性”和“自為存在著的無限性”。工匠精神除了具有精神的成分外,它還包含著一個很重要的成分——實踐的成分。毋庸諱言,工匠精神的根本標志是凸顯人性或人道主義,而不是人的工具化和異化。
工匠精神作為一種實踐性很強的絕對精神、一種存在方式,其真實的、必然的形態只能是一個科學的、倫理的、美學的精神體系,它把主體與客體、思維與存在、意識與物質的關系從對立的范疇中統一起來,從精神哲學的高度來得以認識與建構。工匠精神的哲學內涵可以概括為祈真、至善、唯美,三位一體,從而成為一種職業信仰。
其一,祈真。祈真是指工匠基于產品制作而形成的崇尚科學、認真負責、耐心專注、精雕細琢、精益求精的職業品質和行為準則。正如老子在《道德經》所云:天下大事,必作于細。在中國古代,與“科圣”墨子同時代的魯班是土木建筑工匠的鼻祖,被譽為“百工圣祖”。魯班以手工木作為職業,鉆研營造技藝,精雕細琢,集大工匠和發明家于一身,把工匠營造法式發揮到了極致。以魯班為代表的中國傳統工匠,以其聰明才智和動手能力創造了燦爛的物質文明,正是這種文明支撐和延續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這當中既有工匠營造技藝的延續,更有工匠精神文化的傳承。這種傳承與孔孟儒家思想一樣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珍貴的瑰寶。孟子曾稱贊魯班“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魯班祖師是第一個講究規矩的匠人。
對于每件產品、每項服務、每道工序精心打造,求真務實,追求極致。專注一事,不浮不貽,堅定一種“真知、慎獨”的工匠精神。祈真意味著凝結工匠的智慧和力量,堅持真理,講求科學,不因循守舊,敢于突破,勇于創新,不斷超越自我,“術業有專攻”。正如黑格爾所講:“精神的整個發展過程無非是它自己本身提高為真理的過程,……精神就既是一個真實的東西,又是一個活生生的東西、有機的東西、系統的東西。”[4](P7)
一個只有8 000萬人的德國把工匠精神發揮到極致,創立了奔馳、寶馬、巴斯夫、西門子、阿迪達斯等2 300多個世界知名品牌,躋身世界制造業強國,對此,西門子公司總裁維爾納·馮·西門子說:“這靠的是我們德國人的工作態度,對每個生產技術細節的重視。我們承擔著要生產一流產品的義務”[5]。美國、日本、德國、法國等發達國家之所以取得巨大的經濟成就,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各自的行業和領域秉承祈真、精益的工匠精神。央視八集系列節目《大國工匠》講述了長征火箭焊接發動機的國家高級技師高鳳林等八位不同崗位勞動者,追求高超職業技能、巧奪天工的故事,為工匠精神的弘揚塑造了中國的行業典范。他們技藝極致、精湛,其中滬東中華造船集團焊工張東偉能在牛皮紙一樣薄的鋼板上焊接而不出現一絲漏點;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第702所顧秋亮可把密封精度控制在頭發絲的五十分之一;中交港珠澳大橋項目部鉗工管延安檢測手感堪比x光般精準,海底沉管對接做到零縫隙,嘆為觀止。工匠精神有著明確的技術邏輯(合理性),在技術邏輯上要求普遍的有效性和可實現性,這樣的技術邏輯是以科學的客觀性為其基礎和前提條件的。
其二,至善。至善是指工匠在道德理性(善)基礎上對其產品或職業一種熱愛、癡迷的精神狀態,即所謂“藝癡者技必良”。試想,一個人帶著厭惡、仇恨的心態,會產生工匠精神嗎?愛崗敬業、忠于職守是工匠精神的核心價值觀和道德規范。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一書中說:“行為的發生不僅僅應當合乎職責(作為快樂情感的一個結果),而且應當出于職責,這必須是一切道德教養的真正目的。”[6](P148)在生產、服務活動中,工匠們幾乎都會面臨各式各樣的道德困境問題,解決辦法一般要從理性、善、倫理、責任、權利、義務、理想等方面來考慮,作出道德抉擇。工匠的美德(包括態度、傾向和行為)就是對負責任的工匠精神的弘揚,體現為忠誠、勝任、謙虛、公正、敬業、誠實等職業品行,從而提升形成一種稱之為美德倫理(善行)的實踐理性,特別是對工程倫理中的義務-責任而言,至關重要。“一個理性的行為,受到善意驅動,即受到責任驅動的行為,才是道德意義上善的行為。”[7]工匠精神蘊含著工匠的一種職業的快樂(道德快樂),而不是痛苦和厭煩。
實際上,“責任”的概念是與“善的意愿”緊密相聯、內在一致的,善意與責任的結合產生善行,與善行相關的行為,必然伴隨著快樂,因為理性(善)本身是一切道德價值(快樂)的源泉,工匠精神則意味著這樣一種道德理性的核心價值所在,離開了道德理性,也就無所謂工匠精神。康德說:“至善在現世中的實現是一個可由道德法則決定的意志的必然客體。然而,在這一意志中,意向與道德法則的完全切合是至善的無上條件。”[6](P155)善的東西,并未超出道德行為,而是內在于道德行為之中。
其三,唯美。唯美是指工匠對產品或服務的勞動美學意義上的審美體念。工匠精神的美的對象表現為制作(或生產、服務)的過程和產品(或者作品),通過以理性為行動基礎而制作(或生產、服務),一方面要合目的性,另一方面則要合情感性。黑格爾說:“美一般地就僅僅成為精神東西對直觀或意象的滲透,——即成為某種形式的東西,以至于思想的內容或表象就像它在想象時所使用的材料那樣,只能是極其各種各樣的甚至極其非本質性質的,而作品卻可能是某種美的東西和一個藝術品。”[4](P327)工匠精神的美學意義強調工匠在生產或服務的操作過程中技術與藝術的完美結合,充分利用材料、結構、工藝等來展現質感、形態、功能、色澤、線條等方面的技術美,即屬于對審美對象超出表象的實踐性反思的美學范疇。它基于在一種美的對象上感到愉悅,而自然流露出的純粹的、自由的精神情感,這種情感既有來自心理學的,也有來自社會學的審美評判。被全球譽為“白金工廠”的LEXUS雷克薩斯九州工廠,以“匠”修心,以“心”煉技,每一位工人都是“匠”文化的踐行者,他們把對完美的追求融入到每一個生產環節,以“匠心”打磨每一件作品,為“自働化”加上人字旁,精益求精,從人性化、自然化角度出發,呈現超越用戶期待的美的體驗和創造。
工匠精神作為一種對美的藝術的塑造形式,它必然要考慮審美理念在人的精神狀態及物化的產品中固化、侵蝕和延伸,這也是它的目的所在。正如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提到:“人們可以一般地把美(不論是自然美還是藝術美)稱為審美理念的表述:只是在美的藝術中,這個理念必須通過關于客體的一個概念來誘發,但在美的自然中,為了喚起和傳達那個客體被視為其表述的理念,僅僅對一個被給予的直觀的反思就夠了,無須關于應當是對象的東西的概念。”[8]工匠精神內涵中的真和善最終要通過美的形式表現出來,美既是真和善的終結,同時也是真和善新的起始,它們都是以理性或者說理念為其前提條件的。
三、工匠精神與工程理性之間的關系
為了獲取知識或者采取行動,除了感性、知性外,還需有理性。理性作為一個哲學概念,是人類系統思考的傾向和能力,為每一項“知其然”提供“所以然”,是精神或意識的范疇,理性最初起源于希臘語詞“邏各斯”,開啟于柏拉圖的理性主義,是西方傳統形而上學的主題。啟蒙理性的提出,沖破了神學的羈絆,理性以其它的產物——科學知識,成為了消解當時盛行的神學的世界圖像最有力的工具,推動了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歷史進程,人們深信理性具有無限的精神力量。黑格爾曾在其著作《精神現象學》中說:“理性之所以成為精神,在于‘知道自己是全部實在性’這一自身確定性已經提升為真理,理性意識到自己就是世界,世界就是自己。——精神的轉變過程揭示出了此前剛剛發生的那個運動,在這個過程中,意識的對象,亦即純粹范疇,已經提升為理性的概念。”[9]
理性既不是本能的、情緒性的或帶感情色彩的,也不是傳統的,它具有深思熟慮和現代化的特征,理性的原則表現為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理性在康德哲學中有系統而深刻的研究,康德重點從先驗理性與實踐理性兩個方面探討了理性問題。如果說,先驗理性揭示理論的活動規律,那么,實踐理性則提供用來處理各類事實的方法。在康德看來,“理性,作為種種原則的能力,決定著一切心靈力量的關切以及它自身的關切。它思辨應用的關切在于認識客體,直到最高的先天原則;而它實踐應用的關切則在于就最終的和完整的目的而言的意志決定”[6](P152)。受康德實踐哲學的影響,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使用理性這個概念是為了規定資本主義的社會活動方式,他最早將理性劃分為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兩類,據以理性二分法用之于社會行為和社會現象的分析。
工程理性也可劃分為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兩種類型,是二者的辯證統一,其涵義、分析方法和適用范圍與社會學不同。工程理性從本來意義上講是實踐理性,實踐性是包括工程理性在內的工程活動方式的本質特征,其主要行為方式是通過有理性的行為者,按照經過自己理性思考而選擇的原則進行有意識的造物實踐行動,包括價值合理的行動和目的合理的行動。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文中指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10]價值理性通常考慮的是行為者某種信念、價值和意義的追求,如人本的、倫理的、精神的、美學的、宗教的等方面的價值,這當中,價值可以是主觀的,同時又不失其客觀性。價值理性行為注重行為的內在價值,涉及到“應然”領域。工具理性則更多地關注行為者的技術有用性和效率(功利)最大化,以及可計算、精準、精確、完美等極致性籌劃。以可計算性為特征的工具理性著眼于行為的客觀性和中立性及計算帶來可驗證性的技術化過程,這一切都與價值無涉。
工程理性是工匠精神的源泉。追溯人類的文明史,工匠精神伴隨著西方工業革命和文化啟蒙的理性而產生、勃興和成熟,工匠精神始終充滿理性原則。應該看到,工程理性是工匠精神論的核心范疇,是工匠精神分析與重構的邏輯起點,同時,也是工程哲學的根本性問題。工匠精神本質上呼喚人類的理性,唯有理性才能提供精神領域普遍的和必然的原則,無論是提供給知識,還是提供給行動,莫不如此。因為理性的原則與精神或者意識彼此是相關聯的,精神受到理性的支配,并通過理性而呈現,黑格爾認為,“精神對之擁有一種理性的知的那個東西,正由于它以理性的方式被知,就成為一個理性的內容”[4](P222)。用黑格爾的話來說,理性作為有自我意識的,確信它的存在是精神或意識的本質規定,又是它自己的思想,這樣的理性就是進行著知的真理,即精神,可見,精神的實存是知,其知以理性的東西為目的。這個精神領域經歷了從人的純粹的思想狀態向實存的轉化,并揚棄有限的實存形式而達到人的絕對精神的理性化過程。作為精神存在物,人類又是超自然的,以其自己的理性選擇,來建構起理性的生活世界和意義世界。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說過:“精神的基本活動是雙層的:一種力量是欲望,它驅使人去做這做那;另一種力量是理性,它教導和解釋什么事情應該做,什么事情不應該做。結果就是,理性指揮,欲望服從。”[11]
確切地說,作為一種精神的形式和類型,在工匠精神的演變過程中,價值理性旨在預設一種對特定行為內在價值的判斷和肯定,而工具理性則表征一種特定行為可計算性的計量和確定,兩者都以此作為理性化的方向和路徑。應當看到,在技術發展的背景下,技術催生了工具理性。在工匠精神里,技術與操作、制作、使用等實踐活動之間的聯系大多集中體現為匠人的技能或技藝,作為一種可選擇的手段,工具理性的成分會更多一些,因為技術往往與工具理性聯結在一起,共同支撐著工匠精神的完善和升華,技術為溝通工具理性與工匠精神開辟了一條道路,它們有著內在的相通性和滲透性,通過技術的運用來達到效用最大化。每一次的技術革命和技術創新都為工匠精神提供豐富的養料,有助于提高工匠精神的技術(理性)水準,擴大工匠精神的浸潤和影響范圍。隨著技術的進步,精雕細琢、精益求精等工匠精神就不斷凝聚著工具理性中的精準性、精確性等成分而得以提升,工具理性的成分既包括設備、工器具等的更新,也包括新理念、新技術、新工藝的涌現。工具理性自身無所謂善惡等倫理標準,它是技術中性的或者中立的,其目的的實現依賴于人的意志活動,但要受到價值理性的約束。
四、結語
在精神與理性的討論中,如何闡明工匠精神、工匠精神與工程理性之間的關系問題應當成為工程哲學的一項重要任務。只有從哲學的高度廓清工匠精神的意涵及其本質特征,才能在理論上提純工匠精神的職業理念,使其具有一種理性的自我意識,嵌固在人的精神形態里。工匠精神蘊含了真、善、美等三個最基本的哲學要素,受到工程理性決定并具有時代特征的精神哲學體系。在工程理性中,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互為條件,相得益彰,共同支撐著工匠精神的完善和升華。失掉了理性,工匠精神是殘缺的、不可持續的,進一步講,是難以上升到哲學意義上的絕對精神層面。無論是自然工程,還是社會工程,總之,作為改變物質形態或者社會形態的工程,它們都交織著主體與客體、物質與精神、精神與理性、存在與意識、理論與實踐、形而上與形而下之間的關系問題,因此,亟待從哲學上來回答這些問題。總之,工程問題歸根結底就是一個哲學問題,工匠精神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