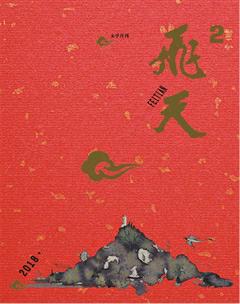人性的探尋和書寫
宋雅璇
擁有詩人和小說家等多重身份的葉舟,將詩人的敏感融進了小說,他的小說從紛擾的俗世中來,直觀的生存狀態直指人的靈魂深處。對于人性的探尋和書寫是葉舟小說的內核,其小說在平靜與庸常的表層下,涌動著欲望和不幸、無奈和艱辛,以及溫暖和救贖。作者將視角深入一個城市的底層生活,用旁觀者的冷靜審視其中的人性善惡。蘭州的城市記憶通過碎片化的意象潛入作者筆下,城市與欲望的勾連使得人性的幽暗再也難于遮蔽,作者以先鋒者的姿態將城市倫理的混亂一一呈現,并留給讀者無限的想象空間,小說敘事成為倫理反思。然而,作者也完成了一次“痛苦的轉身”,書寫靈魂的救贖與自救是對人性之光的重新體悟。葉舟以時代先鋒的身份認同關注著現代生活中的個體生命和生存,其中對于人性的深層拷問和書寫顯示出作者面對世界的態度與誠意。
本文從人性的角度出發觀照葉舟的小說創作,彌補其小說研究中整體把握的不足,并將評論界對其單個作品的解讀加以整合,能夠發現其小說內蘊的時代意義。作品論的形式也將更加全面地展現其小說創作的內核與關鍵,并進一步探索文學中的人性書寫,理解人性的多樣性和復雜性。
一、城市底層的冷靜書寫
底層,作為一個群體性的稱謂,近些年逐漸受到寫作者的關注。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寫實小說的勃興帶動了底層敘事的發展,作家們對小人物跌宕人生的書寫使得底層逐漸浮出了水面。“在現代性神話帶來的啟蒙、自由、民主、發展等宏大敘事話語背后,中國現代文學關注的多是國家的、民族的、家族的、種族的話題,缺乏對個體生命意義和生存尊嚴的書寫。”[1]因此,書寫底層反映出在關乎國家、民族、種族等宏大敘事話語之外,個體生命存在也應受到重視。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人們開始重新定義“人”作為個體的存在意義。底層與個體的人密切相關,可以說一個社會的底層便是由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組成,這里我們不去對底層予以階級層次上的劃分,而將它視作無數為生活所累,以及處于社會邊緣的人。葉舟的小說就是以這樣的目光觀照城市底層中的平民生活、截取常態化的生活場景、在瑣碎的市井生活中展現其中的人性善惡,個性化的生活折射出時代性的色彩。
底層總是與苦難相關,底層人民身上背負著沉重的生活枷鎖,在孤獨與重壓中踽踽獨行。評論家白燁說:“葉舟寫小說,視點放得很低,節奏也很從容,那就是淺吟低唱,平流緩進。讀葉舟的小說,感覺有如體味生活薄物細故之間,多是生活褶皺;家長里短之中,盡顯人生百味。”[2]也是在這生活褶皺中,作者以一種冷靜的旁觀者姿態將底層生活最真實的一面解剖在讀者眼前,現實的殘酷與無情橫陳,沖擊著讀者的雙眼。《三拳兩勝》中農民工石瓜與妻子吃飯時的拮據和攝影師喬頓多年心血的丟失令人惋惜,老板娘看似光鮮的生活背后卻充滿著背叛與無奈。作者將三段故事并置,通過三種聲音表達,敘事時間空間化,使得原本統一的故事時間被消解而變得雜亂無章,小說敘事獲得了立體的空間容量。因此,多重敘述語調在不同空間中的相互碰撞充盈了底層生活的立體感,生活于城市底層的各類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承受著生活的不幸。《兩個人的車站》更是將這種不幸擴展到了極致。石華一家不僅遭遇著生活上的艱辛,女兒心惠未婚先孕更加劇了這個家庭的苦難。小說結尾喬萃喜收養了小羚羊,心惠的戀人也如約而至。作者在底層生活的不幸之外,還發現了人性的美善。
同時,底層又與現代性話語密不可分。“現代性不僅是一場社會文化的轉變,環境、制度、藝術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轉變,不僅是所有知識事務的轉變,而根本上是人本身的轉變,是人的身體、欲動、心靈和精神的內在構造本身的轉變;不僅是人的實際生存的轉變,更是人的生存標尺的轉變。”[3]因此,現代性的敘事應當建立在個體生存的基礎之上,將目光轉向人的實際生存,探尋時代發展對人生存現狀的改變,這本然地要求底層中的個體進入文學史的視野。在城市現代文明不斷演進的過程中,城市中涌現出一批外來打工者,他們在時代浪潮的鼓動下,以奮進者的姿態進入城市打拼,但卻往往被現實吞噬。他們從未真正地融入城市,只能成為在夾縫中求生存的邊緣人。葉舟的小說《緩期執行》深刻展現了進城打工者的生存境遇。他們住在“罐頭”車廂里,得知拿不到工錢后,因誤殺工友使三羊、石頭和跟兄三人陷入窘境,生存上的危機和心理防線的奔潰,使得三人失去了理智,作者將三人在城市求生時所面對的苦痛與辛酸以原生態的方式展現出來,發人深省。在“城鄉二元對立”的龐大空間結構中,作為現代城市的對立面,底層打工者的身份第一次被建構,“落后的農村人”成為其自我身份的確認。在進入城市后,他們又在“罐頭”、“集裝箱”的城市邊緣空間中完成了第二次身份定位,城市生活的冷漠迫使他們主動建構自己“打工者”的身份,他們將“我”與“他”深刻地對立,將自己視作得不到肯定的邊緣人,失落、茫然和焦慮成為他們普遍的心理狀態。因此,在自己微薄的利益受到損害后,他們便不顧一切地要求償還,甚至采取極端的行為,人性中的自私、冷漠與殘酷也由此滋生,為此小說中的石頭丟掉了性命。對底層打工群體生存境遇的真實再現,反映了作者對他們生存命運的高度關注,這一群體在生活面前的弱小與不安記錄著在現代化、城市化的過程中,傳統鄉村和現代城市激烈碰撞所產生的時代轉型陣痛。現代性話語將底層囊括進敘事中,但也隱含著作者對于當代中國城市化發展的質疑和反思。
作者在對城市底層進行冷靜書寫的過程中,混跡于街頭的城市少年成為體察人性的另一扇窗口。《少年行》中“堅決鎮壓反革命”的語錄仿佛已經告訴讀者屬于那個時代的獨有特征。船橋街上整日打架斗毆的少年讓人想起了蘇童筆下“香椿樹街”的少年故事,但與蘇童不同的是,葉舟的小說沒有突如其來的血腥氣息,他著意表現少年們的混亂生活,暴力與破壞背后是少年們對那個時代狂熱社會革命的模仿。但作者也展現了街頭少年的冷酷與邪惡,《少年行》中的蒼蠅為了給死去的哥哥鐵公雞報仇,在得知兇手兔子免于死刑后,誓死要將兔子親手了結。《丹頂鶴》中的何澎甚至冷靜地想象軍刺吃進對方皮膚里的殘酷景象。暴力和死亡變成了獨立的生存景觀,少年們的邪惡成為“性本惡”人性觀的替換和放大。作者通過少年的視角,以冷靜的筆觸書寫普遍意義上人性的畸變,展示了他對于人性黑暗的洞察。小說中的少年將暴力視作證明自己地位的象征,以此確認處于社會底層和邊緣的自我存在感,生存的真相令人哀痛與無奈。
葉舟掀開了遮蔽生活的虛偽面紗,他將目光探進民間底層的生存現場,對底層人物的個體書寫實現了“集體話語”向“個人話語”的轉變,底層人物面對現實時的彷徨與掙扎在作者超乎冷靜的筆觸下擁有了一種直擊內心的震撼力量。
二、幽暗人性的倫理反思
反觀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發展,“無名”已經取代“共名”,文學由建構“理性”的人類變成展現人性的全部可能性。劉再復在《性格組合論》中這樣談到文學對人性的書寫:“人性的深度包括兩層意思:一是寫出人性深處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雙重欲求拼搏和由此引起的‘人情的波瀾和各種心理圖景,二是寫出人性世界中非意識層次的情感內容。”[4]人性書寫已經超越展現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間的矛盾沖突,而將觸角涉及人的精神和情感維度,新生代作家們以其先鋒般的精神對文學傳統加以顛覆甚至反叛,其中對城市倫理混亂的展現,映照出現代文明演進中傳統價值觀的淪喪,以及欲望、背叛、出賣背后人性的幽暗一面。葉舟的小說對人性的復雜和深邃進行重新挖掘與審視,作者以道德倫理批判的“不在場”和刻意缺席應對人性多元化的現實狀況,小說對城市倫理混亂的書寫反映出作者對人性問題的深層思考,幽暗人性背后蘊含其對現代欲望社會的倫理反思。
現代城市已經變成了欲望的聚合體,人們在欲望中生存,甚至被欲望束縛。其中對待愛情的態度揭示出現代文明中趨近于零的情感溫度,現代人根據物質與利益的定位重新界定情感的意義,兩性關系變得更加微妙。葉舟的小說將現代城市人面臨的情感困境以冷峻的筆觸展示出來,作者基于城市人身份對倫理現象進行審視,小說中的男女對待感情的背叛、不忠和冷漠,以及面對性的隨意使得城市倫理中的混亂與不堪真實再現。在《風吹來的沙》中,看似堅固的友誼卻暗藏“殺機”,朋友對“我”表現出的友好只不過是為了報復他對自己的奪妻之恨。而“我”和朋友妻子之間的所謂感情也只是表面文章,當看到自己的姐夫也是朋友妻子的另一情人之后,我只能“像一尊雕塑那樣,啞口無言了”。[5]被欲望操控的現代兩性關系變成了快餐式的各取所需,背叛更成為家常便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變得岌岌可危。《目送》中作者解構了愛情原本的崇高,王力可苦苦等待的目擊證人,正是丈夫的情人,而她卻被蒙蔽在美滿、幸福的家庭與婚姻中不自知。李小果努力經營的愛情也是情人背叛家庭的結果,情人李佛對待愛情的態度更是消極不堪。小說中的人物面對婚外戀,不僅要求得到肉體欲望的快感和滿足,同時也希望獲得精神上的安慰,但最后主人公只能無奈地發現靈魂的相交何其之難,愛情變成了男女雙方的角力追逐,虛妄背后所能實現的只有肉體上的交流。《向世俗情愛道歉》中男主人公苦心追求的愛情不過是他人精心設置的圈套,愛情被解構甚至褻瀆。現代社會中的人面對情感的選擇往往陷入倫理混亂中,“由于身份是同道德規范關系聯系在一起的,因此身份的改變就容易導致倫理混亂,引起沖突”。[6]背叛與欺騙使得個人身份發生了變化,在家人身份和情人身份之間進退兩難的現代人不可避免地滑入了倫理混亂的深淵。
城市文明中的愛情倫理已經崩塌,背叛與不忠是現代人對本能生理欲望的放縱。人們在婚外戀情中尋求刺激,希望為重復和厭倦的生活尋找出路,但也表現出城市生活中現代人情感的匱乏及心靈的焦躁不安。葉舟筆下兩性關系所體現出的倫理傾向是對傳統情感倫理的顛覆,同時也展現了現代倫理與傳統倫理在觀念、思想方面的沖突。在沖破倫理禁忌的基礎上,物質和欲望成為兩性關系發展的前提,擺脫傳統束縛的現代都市人并沒有在身體的狂歡之外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精神自由,反倒加劇了人性的沉淪,陷入了選擇與倫理的困境。
人性的幽暗一面不僅體現在都市愛情的混亂中,還體現在都市生活的迷茫與無序,甚至懷疑中。于是,《低溫》中的丈夫才會在欲望的控制下,劫持妻子;《步行街》中的看似熱絡的老同學都以虛偽的面具偽裝自己,彼此的寒暄背后是對生活本真面目被撕去的恐懼。生活在非理性的現實中,物質、欲望和金錢成為城市人的人生信條,甚至逼迫出了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告密史〉及其作者之死》中秦枝山歪曲的歷史觀便體現了傳統倫理觀念和價值體系瓦解之后人的精神迷失。作者聚焦于告密這一行為,力圖揭開掩蓋人性之惡的面紗,剖析生活的陰暗面。葉舟作為創作主體,主動地審視城市文明在演進過程中人們心理和精神狀態的波瀾變化,他的書寫表達了其對物欲時代人性之變的焦慮和反思。
葉舟在其小說集代后記《街上的事物》中寫道,他過的是“一種類似小說的生活,充滿了市聲和油煙氣,帶著踟躕與隱秘的欲望”。[7]他的小說也描繪了生活中的“油煙氣”,并且混雜著人內心深處的欲望。作者不吝于對身體欲望的表達,欲望成為現代城市的符號和洞察城市的窗口,其間折射出傳統倫理與現代倫理的交鋒。葉舟把對人性的考察放置于情感和欲望的掙扎、道德和責任的沖突中,其小說冷酷地揭示出人性的麻木和冷漠,人性幽暗面的書寫反映出現代人情感的焦慮和生存的困境。葉舟窺見了生活的本真面目,在對城市文明倫理觀的審視中,進行著自己的倫理反思。
三、救贖背后的人性體悟
“作家的靈魂命中注定就是永不歇息,永遠漂泊,永遠在失望與希望的交織中向前行走。”[8]作家的靈魂往往在漂泊中探尋人性的意義與價值,當然,也會在漂泊中完成自我身份的認同與建構。葉舟曾說:“小說和詩歌,在我的具體寫作中并沒出現過分裂,并不沖突和糾纏,也不頭疼;相反,我覺得它們溫潤地合二為一。”“直到最近,我才開始慢慢理會到小說的真容,才開始熟悉小說的路數。這不是謙虛,因為浸淫詩歌太久,在開始侍弄小說文本時,有一次痛苦的‘轉身。”[9]“痛苦的轉身”是作者對自己創作轉變的一次確證,也是在“痛苦的轉身”后,作者慢慢收斂了先前如先鋒者般的尖銳目光,而在洞見世事時流露出溫情與希望。這是作者在人性體悟中獲得的全新感受,溫暖的救贖背后蘊藏著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對人性的終極關懷,映照出生命的厚度。
救贖是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的重要母題,五四時期啟蒙者企圖實現對苦難民眾的救贖,十七年文學則高揚革命英雄般的政治救贖。尋根文學之后,救贖的范圍擴大到了整個民族,根性意識的凸顯反映出文化救贖的迫切要求。一直到新世紀,救贖依舊是文學的主題話語并被不斷加以言說。作為新生代的作家,葉舟在對現實社會的逼視中解構了生命存在的崇高意義,但也從最初“厭惡和仇恨的情緒”中出走,對生命開始了平靜的思考,對人性進行著更加深刻的體悟。救贖成為其探索人性更多可能性的關鍵,無論是靈魂的救贖還是自救,都蘊含著寬容與理解,體現著人性的美好與溫暖。
葉舟生活在蘭州,用他自己的話說,這里的“日常生活波瀾不驚,與其他的城市毫無差別,但在日常生活的內里,則是湍急的宗教,是信仰的走向”。[10]于是,蘭州獨特的城市風貌滋養了其創作中宗教的情懷和信仰的力量。《我的帳篷里有平安》以少年侍僧的視角描寫了一個祈求幸福平安的藏地故事。簡短的描述充滿敘事的張力,作者“在驚愕中寫安詳,在喧囂中寫靜謐,在帳篷中寫無邊人間,在塵世中寫令人肅然的恩典”。[11]在小說中,作者并沒有對藏人的宗教儀式鋪陳式的展開,反倒在充滿張力的情節中刻畫藏人對平安喜樂的追求和信仰的虔誠。宗教在作者筆下擁有了無限的救贖力量,藏人祈愿的背后是人對精神家園的追求,和對信仰的呼喚與渴望。宗教救贖在葉舟這里獲得了普遍意義上人性的深度,不同于北村將上帝拯救作為出路的救贖書寫和張承志以哲合忍耶的“清洗精神”實現靈魂的救贖,葉舟將宗教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形式融入寫作中,描繪出人對于信仰的無限追求,神秘悠遠的地域性書寫蘊含著人性的溫暖,宗教救贖擁有了全新的敘事方式。
自我救贖是人作為個體無法逃避的生存狀態,人在自我救贖中沖破生存困境的束縛與阻礙,實現生命個體的升華。自我救贖在葉舟筆下是《姓黃的河流》中外國人李敦白執著的漂流,小說中李敦白的救贖之路與艾吹明陷入的情感漩渦對比鮮明,黃河也因施洗之河而具有了深刻的象征意義,作者企圖為處于欲望都市中的現代人指明自我救贖的方向。無論是《兄弟我》中老人們對信念的執著堅守,《汝今能持否》中父女親情的修復,還是《在熱烈的掌聲》中女主人公對自我價值與獨立的確證。葉舟寫處于迷茫焦灼中現代都市人的自我救贖,其中不乏對現代都市頑疾的展現,他以深刻的自省意識,體察隱藏在其中的人性溫暖,小人物的自我救贖涌動著愛與理解的力量。作者在對生活投以寬容態度的同時,人性中的善意與溫情也緩緩流露。
葉舟在對人性的多重探索中實現了寫作的轉型,無論是高揚信仰的宗教救贖還是生命個體的自我救贖,作者從書寫人性落入幽暗境地轉向描繪其奮力向上的姿態,以及蘊含其中的力量與希望,也開始了基于人性之美的新的寫作路徑。救贖向度下的生存景觀為讀者帶去溫暖與安慰,同時也具有了靈魂救贖的普世意味。
對葉舟來說,作為詩人的敏感和浪漫燭照了其小說創作,作者在一個個小人物的呢喃中審視著生活的真諦和人性的意義。對底層人物的觀照與現代城市倫理的呈現是作者書寫人性的基本視點,而于救贖和寬容中發現溫暖,是作者對人性的更深洞見。葉舟在生活的真相中反復咀嚼個體生存所面對的威脅,他以冷靜的筆觸書寫現代生存中的焦慮和不安,并投以倫理的反思,溫暖的救贖蘊藏著巨大的人性力量。他將底層的不幸和人性的幽暗毫不掩飾地呈現在讀者眼前,又向著人性的深邃處前行,努力挖掘黑暗背后的人性之光,探尋和書寫著人性的更多可能。
參考文獻:
[1]葉舟.葉舟小說[M].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9.
[2]葉舟.我的帳篷里有平安[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5.
[3]葉舟.兄弟我[M].上海:文匯出版社,2017.
[4]葉舟.葉舟的小說[M].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4.
[5]葉舟.漫山遍野的今天[M].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14.
[6]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
[7]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8]葉舟,楊梓.一顆詩心的轉身[J].朔方(A版),2006,(第4期).
[9]唐翰存.葉舟之頁[N].中國藝術報,2014-08-18(008).
[10]楊明巍.葉舟:底層書寫的執著者[J].金田,2015,(第6期).
[11]張懿紅.甘肅小說八駿:擁有的和欠缺的[N]. 文學報,2014-09-18(007).
[12]南帆.曲折的突圍——關于底層經驗的表述[J].文學評論,2006,(04)
[13]陳博.新世紀文學的底層書寫與敘事倫理》[J].蘭州學刊,2014(4):93-97
[14]張慧.新時期婚外戀題材小說對人性書寫的多維透視[D].廣西師范大學,2008.
注 釋:
[1]陳博.《新世紀文學的底層書寫與敘事倫理》,《蘭州學刊》,2014(4)
[2]白燁.《細微之處見精神》,《文藝報》,2011-12-28(005)
[3]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第19頁.上海
[4]劉再復.《性格組合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第409頁
[5]葉舟.《葉舟小說》,敦煌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377頁
[6]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57頁
[7]葉舟.《葉舟小說》,敦煌文藝出版社,2009年,第441頁
[8]王光東.《現代·民間·浪漫: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專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1頁
[9]葉舟,楊梓.《一顆詩心的轉身》,《朔方》,2006年,第4期
[10]葉舟.《漫山遍野的今天》,青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5頁
[11]《獲獎作品<我的帳篷里有平安>授獎詞》,中國作家網,2014年9月22日
http://www.chinawriter.com.cn/2014/2014-09-22/219180.html
(作者為蘭州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