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荊州』的是非曲直
文/孫啟祥

“借荊州”說的是建安十三年(208),左將軍、名義上的豫州牧劉備與討虜將軍、會稽太守孫權結成同盟,在赤壁之戰中大破曹操,分別據有了荊州的一些郡縣,而隨后劉備面見孫權,“求都督荊州”,孫權應允,并將自己占據的一部分地區轉歸劉備管轄。對于劉備“借荊州”,長期以來人們心目中認為實有其事,因而民間有“借荊州”故事,戲曲中有《借荊州》劇目,就連尊劉貶曹抑孫傾向十分明顯的小說《三國演義》也不回避這個內容。但自清人趙翼力主“借荊州”之非后,這件事變得撲朔迷離。其真相究竟如何呢?
一、“借荊州”其事之有無
趙翼在《二十二史劄記》卷7中力證“借荊州之非”:“借荊州之說,出自吳人事后之論,而非當日情事也。……夫借者本我所有之物而假與人也。荊州本劉表地,非孫氏故物。……赤壁之戰,(周)瑜與(劉)備共破(曹)操。華容之役,備獨追操。其后圍曹仁于南郡,備亦身在行間,未嘗獨出吳之力,而備坐享其成也。……迨其后三分之勢已定,吳人追思赤壁之役,實藉吳兵力,遂謂荊州應為吳有,而備據之,始有借荊州之說。”今人呂思勉《呂著中國史話·劉備取益州和孫權取荊州》(中華書局,2006年),陳顯遠《劉備“借荊州”質疑》(《成都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張兆凱《論吳蜀荊州之爭》(長沙《求索》,1992年第5期),李殿元《“借荊州”的是是非非》(《成都大學學報》,1994年第 3期),張作耀《劉備傳》(人民出版社,2004年)、《孫權傳》(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論文專著,或否定借荊州其事,或否定“借荊州”之說,或持趙翼之說,認為站在劉備的角度,說“借荊州”沒有道理,系吳人一面之辭、事后之論。有的學者甚至認為,趙說“澄清了一千多年來之謬論。”(見楊耀坤《陳壽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160頁)這些觀點并不符合當時實際。
“借荊州”是漢末三國時的一樁公案,長期以來人們以為實有其事,但自清人趙翼力主“借荊州”之非后,這件事變得撲朔迷離。本文依據史料分析,揭示了“借荊州”其事之有無、“借荊州”所“借”為何地,以及為什么要“借荊州”,以饗讀者
首先,“借荊州”并非吳人一面之辭。劉備一方故然未有“借荊州”之語,但對孫權“還”荊州之說,并沒有給予反駁。建安二十年(215),孫權以劉備已得益州(治蜀郡,今四川成都),遣使索要荊州,劉備的回答是:“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三國志·蜀書·先主傳》)實際上表明了應該將“荊州”給孫權。而孫權的反應是“忿之”,認為“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三國志·吳書·吳主傳》)假者,借也。劉備和孫權對荊州歸屬的認知是一致的。隨后魯肅和關羽交涉時的對話則更能說明問題。當時魯肅說:“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三國志·吳書·魯肅傳》)關羽的解釋是:“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三國志·吳書·魯肅傳》裴注引韋昭《吳書》)魯肅明確使用了“以土地借卿家”和要求“奉還”的概念,但關羽的回答只是指出劉備作戰有功,應該有一塊土地,沒有否定“借”“還”問題。其間,關羽方有一人插話:“夫土地者,惟德所有耳,何常之有!”(《三國志·吳書·魯肅傳》)這本是一句很有力的話,卻受到關羽的斥責,并暗示其離開。關羽的態度,除顧及外交禮儀,亦或自覺理虧。同時,插話者之語也暴露了問題,“何常之有”,流露出本為孫權所有的意思。曹操對“借荊州”也有反應。《三國志·吳書·魯肅傳》載:“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于地。”業者,資業,以(土地)資助也。曹操亦認為孫權以土地資助劉備。顯然,孫、劉、曹三方對孫權“借”土地給劉備程度不同的都予以肯定,并非孫權一方之言。

其次,“借荊州”非吳人事后之論。除了前引《三國志》魯肅本傳中魯肅對關羽當面所言之“以土地借卿家”語,程普本傳中還有“(孫)權分荊州與劉備”語,《江表傳》中亦有“(劉)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復從(孫)權借荊州數郡”之說。此外,魯肅在孫權召集部屬研究“劉備求都督荊州”的對策時,還說過“將軍(指孫權)雖英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劉)備,使撫安之。多(曹)操之敵,而自為樹黨,計之上也”的話。這條記載出自習鑿齒《漢晉春秋》。如果說魯肅、程普本傳系史家采自吳官修史書的一家之言,《江表傳》之說系對孫吳有感情的不實之辭的話,《漢晉春秋》關于“借”之記載應屬可信,因為習鑿齒曾著文歌頌劉備、諸葛亮,“黜魏帝蜀”感情濃厚。正因為魯肅有“宜以借(地于劉)備”等語,后來孫權與陸遜論魯肅時才說:“勸吾借玄德(劉備字)地,是其一短”,(《三國志·吳書·呂蒙傳》)否則,孫權豈非在大臣面前無故污蔑已逝的重臣。這些都表明當初即有借地之說而非事后之論。重要的是,陳壽一定是在掌握了除韋昭《吳書》之外的確鑿資料,認為有“借”土地之實,才在《三國志》中多處使用“借”字來表述這期間的糾葛。司馬光《資治通鑒》卷66亦謂“魯肅勸(孫)權以荊州借劉備。”陳壽、司馬光是站在史家角度,以客觀態度反映歷史,而非以孫吳的口氣傳述史事。后世南宋陳亮,元胡三省,清袁枚、王夫之等注史論史時皆以有借地之實。
其三,“借”字含義本身具“彈性”。后人理解“借”,或指“暫時使用別人的東西”,或指“把自己的東西暫時給別人使用”,含義是明確的。趙翼所論即指后一層意思。孫權、魯肅等當時使用“借”字亦為此意。劉備不一定這樣理解。因為當時把“巧妙地占有別人的東西”也婉轉地稱為“借”——劉備或許如是理解。前兩種“借”是要“還”的,而后一種“借”是不需要或不安心“還”的。所以劉備、關羽不反駁孫權、魯肅說“借”,但是也沒有想“還”。《九州春秋》載,龐統初受劉備重用,就獻計說:“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于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而劉備以“今以小故而失信義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予以拒絕。明明是侵占,龐統卻謂為“借”;劉備心領神會,之所以拒絕,是因為它不是指“暫時使用別人的”土地,而是占有,而這樣會“失信義于天下”。
綜上所述,歷史上孫權、劉備、曹操三方,吳國的國史、其他雜史和陳壽、司馬光等史家都認可“借荊州”或孫權“借”土地給劉備之事,只是理解有所不同。
二、“借荊州”所“借”為何地
同“借荊州”其事之有無史料簡約、眾說紛紜一樣,“借荊州”所“借”為何地,史籍記載更加模糊。《三國志·吳書·魯肅傳》載:“后(劉)備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三國志·先主傳》裴注引《江表傳》的記載較之詳實又略有不同:“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劉)備。備別立營于油江口,改名為公安。劉表吏士見從北軍,多叛來投備。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從(孫)權借荊州數郡。”《資治通鑒》卷66概括表述為:“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上述記載中,“荊州”、“荊州數郡”所指為何,首先得弄清荊州建置的沿革和赤壁之戰后荊州各郡的歸屬。
荊州為漢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東漢時治漢壽縣(今湖南常德市東北),漢末劉表任荊州刺史、荊州牧,駐襄陽(今湖北襄樊),赤壁之戰后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時,劉琦在夏口(今湖北武漢漢口),劉備為荊州牧,治公安(今湖北公安縣西北),孫權襲奪南郡后,荊州治所在江陵(今湖北江陵)。曹操南下時,荊州共有八郡:南陽,治宛(今河南南陽);章陵,治章陵縣(今湖北棗陽縣東);南郡,治江陵;江夏,故治西陵(今湖北新洲縣西),黃祖為江夏太守時屯沙羨(今湖北武漢市西南),劉琦駐夏口;武陵(治臨沅,今湖南常德市西);零陵,治泉陵(今湖南零陵);長沙,治臨湘(今湖南長沙市南);桂陽,治郴(今湖南郴州)。其中,南陽、章陵、南郡、江夏為江、漢間四郡,武陵、零陵、長沙、桂陽稱江南四郡。赤壁之戰后,曹操保住了南陽、章陵二郡,又占據了南郡、江夏二郡之北部地區,旋廢章陵郡,以南郡北部和章陵之地置襄陽(治襄陽縣)、南鄉(治南鄉縣,今河南淅川縣西南丹江南岸,已成水庫)二郡,以江夏北部地置江夏郡(治上昶城,今湖北安陸市西南);劉備攻據了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四郡;孫權奪取了南郡、江夏二郡之南部地區,以故江夏南部為江夏郡,治沙羨。所以,“借荊州”是以荊州各郡都“借”出嗎?顯然不是,因為南陽、章陵和南郡、江夏的北部并不為孫劉所有。究竟為何地,大抵有五說:
(一)“江、漢間四郡”說。元人胡三省在注《資治通鑒》時稱:“荊州八郡,(周)瑜既以江南四郡給(劉)備,備又欲兼得江、漢四郡也”,(《資治通鑒》卷66注,中華書局,1956,2102 頁)劉備“求都督荊州”、魯肅勸孫權“以荊州借劉備”即指“江、漢間四郡”。今人林成西《重評劉備東征》(《史學月刊》,1984年第6期)即持此說。
(二)“江南四郡”說。近人盧弼在《三國志集解》(中華書局,1982)中引姚范之語:“(荊州數郡)若非(孫)權借者,權安得使使報欲得荊州”,并引申說:“先主之有荊州數郡,實為(孫)權所借也。……據此二《傳》(指《三國志》之《先主傳》《諸葛亮傳》——引者),四郡皆為先主自力征服,非為吳借可知。然推究當日情勢,……孫權聽其自取荊州數郡,不加阻力,無異假借,遂各持一說,即為孫劉異日構釁之因。”(728頁)張作耀《孫權傳》謂:“‘借荊州’的決策,確切地說,就是允許劉備收取江南四郡”,(180頁)就是姚范、盧弼觀點的反映。
(三)“江陵”說。張大可《三國史》(華文出版社,2003)謂:“所謂劉備借荊州,實際上是借南郡江陵”,“孫權答應用江東健兒的生命和鮮血換來的江陵借給劉備。”(187頁)
(四)“江夏郡”說。胡覺照《異說三國》(三秦出版社,2007):“所謂的‘借荊州’之說,不過是夸大其辭的說法,劉備只借了江夏郡一郡。”(50頁)葉哲明《論關羽和荊州之爭》(浙江《臺州師專學報》,1983年第2期)亦謂劉備借了江夏:“劉備取得荊州偏西南四郡,……又向孫權借得江夏和南郡一個部分。”
(五)“南郡”說。《三國志集解》引王懋弘之語曰:“(周)瑜卒,(孫權)以南郡借先主”,(1023頁)明確提出“借荊州”所借為南郡。由于當時南郡的襄陽等地為曹操所據,此說又表述為“南郡之一部。”此說為后世廣為接受。王仲犖、張傳璽、呂思勉、余明俠等人的專著和朱子彥、何茲全、趙國華等人在論文中都持此說。
“江漢間四郡”說和“江夏郡”之說顯系謬誤,一則江漢間的南陽郡、章陵郡自始至終為曹魏所有,如何能“借”;二則江夏郡一直屬孫權,從未“借”出。《三國志﹒程普傳》的記載顯示,程普在赤壁之戰后即以裨將軍領江夏太守,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借荊州”后,又復領江夏太守,可見劉備從未染指江夏。“江南四郡”說以孫權聽任劉備收取江南四郡來解釋“借荊州”,認為純屬孫權、劉備對“取荊州數郡”理解不同、“各持一說”,亦有疏漏。前已論及,“借荊州”在孫、劉、曹三方是有共識的,并不簡單地屬于孫、劉理解問題。“江陵說”縮小了劉備所“借”的地盤,江陵為南郡之一縣。“借荊州”事件后,不光孫權任命的南郡太守程普改任江夏太守,原來駐守夷陵的甘寧也隨魯肅鎮益陽,夷陵地區亦歸劉備,劉備遂使襄陽人向朗督秭歸、夷道、巫、夷陵四縣軍民事,改曹操分南郡置于夷道(今湖北宜都)的臨江郡為宜都郡,先以張飛,次以孟達,后以樊友為太守。四縣亦系劉備所“借”。“南郡”說觸及了實質,即所借為孫權攻占的故南郡南部江陵、夷陵等大片土地。這里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其一既然是“借南郡”,為什么要說是“借荊州”;其二既然“借”出了南郡一郡,為什么有“荊州數郡”之說,為什么后來孫權要討還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并因此挑起戰端。
“借荊州”的含義,實則包括兩個方面內容:一則指孫權將南郡的管轄權轉給劉備,二則指孫權對劉備占據江南四郡給予認可。赤壁之戰中,劉備參與了追擊曹操,進攻南郡,但堅持作戰的是周瑜,他將兵數萬人與曹仁決戰,“瑜、仁相守歲余,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三國志·吳書·吳主傳》)顯然,南郡是周瑜攻克的。周瑜任南郡太守后,奉命將南郡江水南岸孱陵(今湖北公安縣西南)一帶劃歸劉備駐防——這也許是對劉備先前參與進攻南郡的回報,劉備在油江口立營,更地名為公安,被限制在一個狹小區域之內。劉備為向北發展,就以歸服者眾、難以容納為理由,“求都督荊州”,一來取得對荊州各郡的軍事統轄權,與他“荊州牧”的行政職權一致,二來矛頭直指周瑜,以“(周)瑜所給地少”,要求將南郡歸屬自己。漢末的南郡在被曹操分置臨江郡后,這時合起來已轄十多個縣,“周瑜所給”的南郡江水南岸,充其量一兩縣之地,故劉備抱怨“地少”。為什么不以江南四郡“安民”,一來當時這些地區還未開發,條件很差,不足以“安民”,二來江南四郡的政治傾向一向從屬于江漢間各郡,劉表、曹操、劉備和后來的孫權,都是在占據江漢地區以后,對江南地區通過招誘或小規模作戰而取得。正像當初蒯越對劉表所言:只要“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三國志·魏書·劉表傳》裴注引司馬彪《戰略》)劉備只有在據有南郡后,才能保住江南四郡。總之,劉備“求都督荊州”,使其據有了南郡曹操所據地之外的各縣(即以宜都太守張飛駐守南郡),并對江南四郡的占據“合法化”,至此,劉備取得了孫劉聯合作戰時所占據的荊州六郡除江夏郡之外五郡的軍事統轄權,這也是“荊州數郡”之說的來由。至于江夏,看來劉備并未提出要求,或許他明知孫氏覬覦江夏已久,縱然要“借”,孫權也不會答應。之所以時人和后世將劉備的行為稱為“借荊州”,是因為劉備以此取得了孫劉所據六郡中的五郡,且當時荊州的治所公安和隨后孫權荊州的治所江陵都在所“借”之列,以行政治所地名稱謂行政區域,古今皆有這個習慣。《三國志》中多處稱南郡江陵之地為荊州,如《呂蒙傳》:“遂據南郡,撫定荊州”,《程普傳》:“(孫) 權分荊州與劉備”,《陸遜傳》:“破(曹)操烏林,敗(劉)備西陵,禽(關)羽荊州”,不獨針對劉備借地之事。孫權所襲、關羽所失地為公安、江陵,并不含夷陵和江南四郡,但史家多稱為“襲荊州”、“失荊州”,劉備先前的行為當然可稱為“借荊州”,何況劉備自己的要求就是“都督荊州”。所以,“借荊州”之說是符合史實和習慣的。至于劉備自己奪取的江南四郡還需孫權認可,則與赤壁之戰的背景和孫、劉角色的轉換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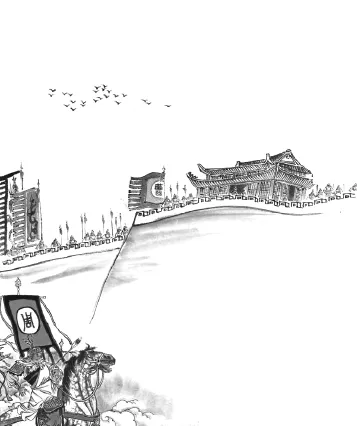
三、為什么要“借荊州”
既然在赤壁之戰中孫劉聯合破曹,江南四郡又系劉備遣將攻據,但都督荊州、接管南郡,為什么卻被認為系“借荊州”呢?緣于赤壁之戰前后時局的變化、孫劉角色的轉換和戰斗中雙方的作為。
赤壁之戰初始,對手主要是曹操和劉備,對此,史籍記載和史官認識是一致的,《三國志》之《魏書》《蜀書》《吳書》亦無大異。《武帝紀》作:“公(指曹操)至赤壁,與(劉)備戰,不利”;《關羽傳》為:“孫權遣兵佐先主據曹公”;《吳主傳》載:“(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與赤壁,大敗曹公軍。……備、瑜等復追至南郡……”;陳壽在《上諸葛亮集表》中亦將此役概括為:孫權遣兵三萬人,“(劉)備得用與武帝(指曹操)交戰”。此外,曹操還有“劉備者,吾儔也”(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裴注引樂資《山陽公載記》)之語。這些都表明,曹操認為他的進攻對象是劉備,孫劉一方的主角是劉備。
但是,戰爭靠實力。孫劉聯盟時,劉備的軍力是關羽的水軍精甲和被曹操打散歸來的士卒共萬人(這個數字系諸葛亮對孫權所言,可能還被夸大),江夏太守劉琦的戰士萬人,共計兩萬人;而孫權的兵力則遠過于此。《江表傳》謂,當周瑜向孫權求精兵五萬時,孫權說:“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眾,多載資糧,為卿后援”,《三國志》諸葛亮本傳亦有:“(孫)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據曹公”之記載。看來孫權首次出兵即三萬,后來確也“續發人眾”,因為僅與曹仁決戰南郡,周瑜即“將數萬眾”,這還不算孫權在夷陵、江夏地區和揚州戰場投入的兵力。赤壁之戰確如趙翼所說乃“藉吳兵力”。更重要的是,孫劉取勝的關鍵是火燒曹操的戰船營壘,此計系孫權方所定并實施,全與劉備無干。后來曹操欲貶損周瑜,致書孫權說:“赤壁之戰,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三國志·吳書·周瑜傳》裴注引虞溥《江表傳》)雖為挑撥之語,卻反映了周瑜在赤壁之戰中的決定性作用,這些都加重了戰后孫權的“話語權”。因而,戰后劉備、孫權在聯盟中的地位產生變化,劉備戰前的主要地位和主角角色難以保持,孫權已居于主導地位。換句話說,在孫劉聯盟的“蜜月”階段,孫劉“綢繆恩紀”,實為一家,先前,這個大家庭的“家長”是劉備,赤壁之戰后卻成了孫權。
劉備也想保住自己的地位,所以戰事正酣,他即果斷上表以劉琦為荊州刺史。這是一個正確、及時的行動。荊州系劉表的地盤,按當時的習慣,靠實力奪取的地方是可以父死子繼的。劉表死,劉琮降,參與赤壁之戰的劉琦繼任荊州刺史理所應當。以劉表生前與劉備的關系和劉琦對劉備等人的倚重,劉備在荊州刺史劉琦麾下是可以左右逢源、反客為主的。劉備隨后即遣將招降和攻據江南四郡,對此孫權也無可奈何,并不存在如盧弼所說“孫權聽其自取荊州數郡,不加阻力”或張作耀所謂“允許劉備收取江南四郡”問題。因為當時是同曹操爭地盤,且荊州的故主是劉琦。可是好景不長,劉琦很快病死,孫劉雙方就荊州主權相安無事的平衡局面被打破。劉備盡管被屬下推為荊州牧,但他明白孫劉具有的荊州六郡是以孫權為主力的聯合力量在打敗曹操后取得,他對荊州的“領導權”必須得到孫權的認可,且北向面對周瑜的挾制,南面四郡的歸屬需孫權承認這些問題都得解決,于是直接到孫權住地,主動提出“都督荊州”,從而演出了“借荊州”的話劇。余明俠《諸葛亮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謂:“劉備所得荊南四郡,在吳國君臣看來,只是暫時借給他棲身,早晚是要取回的”。正因為劉備占據江南四郡需孫權承認,才會有數年后孫權變卦,索要長沙、零陵、桂陽之事。從魯肅和關羽交涉時“但求三郡”語氣不難理解,孫權認為劉備占有的五郡均屬自己。
孫權方面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優勢和劉備的弱勢。本來,在協商聯盟時,諸葛亮就對孫權說:“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指劉備)協規同力,破(曹)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諸葛亮的話很清楚,你幫我們打敗曹操,我們站穩腳跟,你們解除威脅,就能與曹操形成鼎足之勢。面對曹操“會獵于吳”的恐嚇和“議者咸曰”降曹的內憂,孫權以聯合抗曹能保住父兄基業、保住江東六郡,于是斷然接受。但是,當在赤壁之戰中發揮關鍵作用、曹操戰敗北還以后,爭奪荊州則成為必然之舉,于是以周瑜、程普分別駐守南郡、江夏。劉琦病逝后,孫權本人及其部屬都認為孫權是聯盟的主宰者,應該決定荊州的命運。所以,盡管戰后劉備表孫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而孫權卻能夠“越俎代庖”,插手荊州事務,分劉備攻據的長沙郡而置漢昌郡。而劉備這個荊州牧,盡管已據有江南四郡和南郡之一部分,也不得不屈尊向“盟主”請求承認,并認可分割長沙。好在劉備不看重虛名,不論是“借”是“給”,只要實際據有、有利于今后發展即可,這也是其“非唯競利,且以避害”(陳壽評劉備語)之一端。

孫權一方之所以強調劉備“借荊州”,還與認為劉備對他們是一種依附有關。的確,劉備在赤壁之戰前,漂泊半生,卻一直無立身之地。他投公孫瓚、附陶謙、歸曹操、奔袁紹、依劉表,無不具有依附性質。赤壁之戰中,孫、劉本以兩股獨立的政治軍事力量聯合,但也許是由于實力強弱、戰功大小對比分明,也許是由于“思微慣性”,孫權部屬仍然視劉備對他們為依附。戰前,周瑜就對劉備說過“豫州但觀瑜破之”這樣輕視劉備的話。戰后以南郡江水南岸地劃歸劉備駐守,本為互利,周瑜在臨死前致書孫權時卻視此為“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就連對待聯盟關系十分理智的魯肅,也對關羽說:“主上(指孫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使有所庇蔭以濟其患”,(《三國志·吳書·魯肅傳》裴注引韋昭《吳書》)完全視劉備為從屬。劉備方對此似乎也不太在意。關羽在回應魯肅的責難時,有“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之語,看來劉備的主角地位戰爭一開始就失去了,只是“身在行間”而不是統帥,被人視為依附也無可奈何。
但是,荊州問題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劉備的立國戰略是“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孫權的發展方向是“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及,據而有之”,(《三國志·吳書·魯肅傳》)雙方都視荊州為必得之地。赤壁之戰前,劉備在荊州已經有了一定的發言權,而孫吳屢屢染指荊州(主要是進攻江夏),卻所獲甚少。赤壁之戰后,孫權雖然在荊州具有了主導權,但荊州名義上的軍政長官卻是劉備。在這種形勢下,孫權不可能“大公無私”地“借荊州”,劉備也不會俯首貼耳地“還荊州”,“借荊州”是在強敵面前孫劉雙方互相利用的產物。孫權既不想長期“借”下去,劉備也不想輕易“還”給他。“劉備借荊州——有借無還”則勢所必然。論者或曰:“《隆中對》規定‘外結好孫權’,(劉備)卻又賴著借人家的荊州不還,道義上說不過去”,(尹韻公《從荊州爭奪戰看三國前期的外交斗爭》,載《文史哲》,1981年第5期),“劉備借荊州不還,遭了現世報”,(張大可《三國史》,183頁)屬情緒化地判斷,不足為據。因為,荊州問題的糾纏,并不是借與還的道義問題,而是軍事形勢上的實質性的斗爭。荊州在誰手里,軍事上的地理優勢條件就掌握在誰手里,劉備、孫權都不會輕易放棄荊州。因此,不必諱言劉備“借荊州”,也不必高估孫權借出荊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