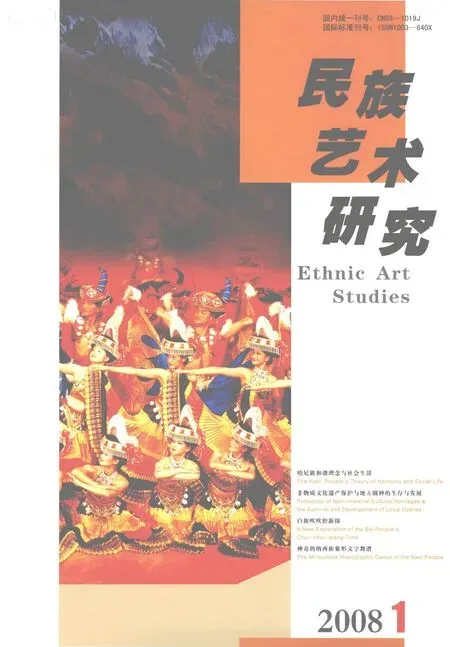從維護文化資源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回返”
【德】吉婭·賈妮珍文,鄧曉彬 蕭 梅譯
譯者簡介:鄧曉彬,上海外國語大學商務英語專業,廣東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蕭梅,上海音樂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未來,文化資源將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任何程度的人工智能都無法取代這些資源所傳遞的信息及其與人的關系。文化資源的維護和創造性發展,不僅代表著一個民族、國家、地區或族群的身份特征,更重要的是它延續了人類的個性、多樣性和存在感。與原有的擔心不同,早前認為人類學和社會科學中專注于歷史、文學、視覺和表演藝術的部分,或許會給嚴謹的學術環境帶來不好的影響;音樂學家或人類學家這樣的做法也被認為是“沒有面包的藝術”,即一種無利可圖的藝術,所以對文化資源的研究需要更多的支持。即使你并非滿腹經綸,但也應該對文化資源有更基本的認識,人類的現實生活才能平衡長遠的發展。反過來說,也只有通過這種方法,即充分利用這些資源才能幫助人類社會進步。
我對文化資源在知識積累方面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感到非常興奮。不少精干的決策者認為他們對早期錄音的保護有著職業責任,其中的一些錄音資料也是本次研討會的焦點。然而,我對這個轉型期中因認識和狹窄的思想所展現的另類特征感到擔憂。在本文中,我將列舉當下的某些認識,盡管它們并不完善,但卻利于我們展開討論。
1.一些熱衷于早期錄音工作的人,往往對此并沒有真正的需求。也就是說,只有少數“怪人”對此感興趣,而他們卻并非那些最該獲取早期錄音的人。
2.從事這項事業需要大量的時間和人力,需要有人為此給予足夠的付出。同時,維護這些錄音的成本也非常高。所以,如果有人希望從這項事業中獲益,那么應該首先承擔一部分前期維護的成本。
3.實際上,這些錄音的文化所有者應該對它們的存在感到慶幸。否則,他們將對自己的過去知之甚少。然而,我們對于這些錄音的了解并不充分,無法確定它們的意義,所以也不值得太過興奮。
4.為什么這些人不去等待下載資源的體驗呢?把老錄音轉化為數字化文檔,并上載于一個漂亮的有形載體,以獲得那種“失而復得”的感覺是否真有那么重要?這看上去似乎有些荒謬。并且,人們并沒有失去老錄音,相反,他們應該為老錄音得到妥善的保管而心懷感激。
這些或有冒犯的觀點,盡管不是對大眾公開的,但卻非常直觀。這些觀點,集中代表了一部分從事“歸家”事業的專家們的看法。討論“歸家”的字面意義或者從文化資源的角度討論文化境遇,似乎對于未來的工作更為重要。而就當下來說,與其來討論這些,不如說討論如何“歸家”和為什么要“歸家”,才應該是工作的核心。諷刺的是,這些言論也是一種文化資源,而且也可能隨著未來的人類發展而占一席之地。
接下來,我將以“魏斯收藏”(Weiss Collection)工作為例,逐一討論這四個論題,并涉及更深層次的問題。
1.熱衷于早期錄音工作的人對早期錄音并沒有真正的需求。也就是說,只有少數“怪人”對此感興趣,但他們卻并非那些最應該獲取早期錄音的人。
聆聽古老的音樂無疑是振奮人心的。對于當今知識群體來說,最可怕的是很多人認識不到自己對工業、文化或人類社會最新成就的無知。毫無疑問,噪音、人造聲音或者自然聲音已經發生了改變。簡而言之,如果不了解時間長河里的各種聲音,根據大多數聲音都已消失的現狀,我們無法想象以前的聲音。因此任何過去的聲音,都可以豐富我們的見識并讓我們大開眼界。盡管錄音的質量不好,但如果聽眾足夠專業,這些錄音的出現,對他們來說就會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當然,那些對聲音研究或音響設備非常熟悉的人,肯定是對這些錄音最先產生興趣的人。然而,盡管隨著時間流逝,具有文化歸屬感的人也會發生轉變。他們借助現代技術,開始對環境探索,也逐漸對這些錄音產生了興趣。政治抱負或許是發掘歷史錄音最微乎其微的理由。更為嚴肅的問題在于,人們收集錄音的意義不僅是以物質去承載信息,更重要的是傳達收集的態度。早期錄音的收藏者通常是有權力的人,而且擁有受訪的被記錄者所無法企及的技術資源。采集者一般代表著某個機構或政府,他們被上級賦予了相關權力,他們似乎看不起這些藏品,而且并不關注表演者的姓名或者性格特征,因為在他們來看,被記錄的人只是屬于某個種族、某種實踐、某個地方或某個事件的“附屬品”而已。這個事實雖然殘酷,但史密斯還是把它記錄了下來(1999年)。專業的認知方式中一直強調“方法論”這一源于殖民文化的神奇詞匯,這樣的傳遞仍然沒有改變不同程度的再殖民帶來的方法論,這種認知并不在于東西方之間,而在于多數人和少數人之間,在于有權的少數人和不那么有權的少數人之間,在于男性和女性之間,在于年輕人和老年人之間,在于現代和傳統之間,也在于那些實踐方法論的先行者和后來者之間。
盡管如此,我們對早期錄音還是有強烈的需求。雖然人們并沒有過多地在自我認識之外去思考它們的未來,但得益于早期錄音所創造的新錄音成果,依舊呈現了更多的歷史感。在經歷了不同錄音質量的歷史時期后,可以預見未來的錄音質量會有相當的變化。在了解了過去的錄音之后,現在的錄音則顯得并不那么占據主導地位了。如果說只有一些“怪人”對此感興趣,也只是延續了一種區分精英和群眾的殖民導向。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會被他們的榜樣所影響,其余沉默的群眾也只是模仿表面現象,并沒有展現出真正的興趣。
2.從事這項事業需要大量的時間和人力,需要有人為此給予足夠的付出,同時維護這些錄音的成本也非常高。所以,如果有人希望從這項事業中獲益,那么應該先承擔一部分前期維護的成本。
這個觀點可能會讓人困惑,因為它無法完全脫離對歷史的責任,卻會施加一定經濟壓力,這種經濟壓力恰恰是為了延續歷史的一種自主行為,我們需要為此付出很多努力,況且目前還有尚未解決的倫理問題。
在急速全球化和同一化的環境中,這一工作過程交織著倫理途徑中的文化模式差異性需求與彼此宗教、傳統和個性等的價值判斷,這屬于應用倫理學的問題。哪一個維護方有這樣的要求?對于誰來說費用太高?誰是最后的投資方或盈利人?難道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既是投資者也是獲益方?
只有當探究到這些問題的答案后,我們才能進行詳細的分析。對經費敏感或有壓力的檔案管理機構,肯定不是最終的決策者。就這一點而言,整個問題是具有全球沖突屬性的,而遠超任何檔案館的視野。與此同時,那些接受過簡單倫理教育的檔案管理員,那些維護錄音資料并投入智慧的人則任重道遠。雖然一些重要的機構缺乏完善的制度,如果那些努力從事早期錄音事業的人們不被另眼相待,成果應該更為豐富。但是,制度是可以通過實踐得到建立的。據我觀察,盡管大部分的抱怨都來自于那些決策者,但這也不會引發在更高層面上導致政治決策的廣泛運動。循此思路,多數學者已經指出(Carpenter & Riley 2014, Meskell 2013, Soderland & Lilley 2015, Smith 1999),這項事業將成為強有力的、公開推進的去殖民化的新方法。而方法的改變,或許也會帶來學術界自身的去殖民化,并最終改變對經濟效益的看法。
有趣的是,我發現了這個問題的另外一面。當我在一個地處偏遠閉塞的內陸地區,完成一項歸檔項目時,這個項目遠離了早期殖民者,也遠離了學術界。當項目中的很多工作尚在進行時,資金就已經耗盡。我決定自己私下資助那部分最需要資金的工作。不久之后,該機構附屬的政府部門要求我提供適當的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因為如果這部分費用得不到資金,項目就難以繼續運行。雖然我對此感到十分失望,但我在此之前就應該深入思考到這一點。是我、我的學生以及職員們認為需要繼續運行這個項目,然而,當我們站在自認為正確的角度,卻并不意味著對方也認為它正確。在早期錄音這項事業里,我們需要根據文化互動不斷吸取教訓。對于那些“被幫助的人”認為自己是“幫助者”這件事,我便不感到意外了。
論點2與論點3緊密相關。
3.錄音的所有者應該對這些錄音的存在感到慶幸,否則我們就會對他們的過去知之甚少;然而所有者卻并不真正了解這些錄音的深刻意義,所以也就不值得那么興奮了。
這是由專業人士和熱心人士提供的一種內向型觀點。基于其他人類學家和民族學家,在多種渠道和多種場合表達的對保護和記錄的經驗,似乎變成了求助的呼吁。
其實雙方都有合理的地方。當局者希望運用表面的熱情和目標,而不是文化知識的積累對公眾興趣施加影響。同時,新的問題是那些有權的采錄者的后代是否太固執己見,他們不考慮自身的學術經歷(是否適合于收藏整理工作),以至于忽略歷史錄音的要求。這個倫理道德問題亦將與那些經不起推敲的學術方法并行。
舉個例子,我從魏斯的采錄中獲取了一段早期錄音。關于這段錄音的所有信息都來自于采錄者的描述,這些信息是普羅大眾獲取不到的。我嘗試根據這些僅有的信息去尋找真相,聯系當地人,并與其他同類早期錄音作比較,還咨詢了專家和文化當事人的意見等等,但結果卻讓人沮喪。采錄者提供的信息與最新獲得的信息相差甚遠,以至于我開始懷疑這是其他的收藏,至少是同一藏品中的其他早期錄音。
也正因為如此,我并沒有參加檔案機構在收藏家的文化和學術圈向專家尋求更多信息的工作。就目前來說,我的研究結果或許較少受到背景環境的影響。
如同任何一位民族音樂學者,我首先對聲音感興趣。第二步則顯得與常規做法不太一樣,我嘗試用五線譜記譜法來記錄樂句,來描繪聲音的音樂性,并把它們的結構視覺化。記錄的結果舉例如下:

圖1 該譜例是根據“魏斯南中國收藏”的蠟筒13找到的錄音記譜,從0:00開始到40:02結束(這首歌用元音唱,但歌詞沒有意義)

圖2 從已發行的蠟筒錄音目錄中獲取可用信息(Ziegler 2006)以及第一次聆聽所考慮到的方言體驗。*譯者注:圖片中以英文標記該錄音為彝 “歌”,用吹奏樂器的音調并使用云南北部方言,節奏自由,并伴隨一些有趣的歌詞。德語部分描述該錄音為:采錄于1913年11月份,在長江的四川段,被采錄者為倮倮部落的一位叫作Wu Pao Chia的人,模仿木制笛子的音調,一板一眼的言說。
這是一段以彝語唱出的類似畢摩音調*畢摩是彝族的祭司,及宗教及文化活動的執儀者.的人聲*云南的學者蘇毅苗在2017年9月30號于越南第一次聆聽這條音響時說: 有點像畢摩的調子。她聽出的唱詞是:“哩…哦 哩哦…哩啊…啊…哩…依依依啊依…嘞額嘞(00:06-00:22)。啊…哎羅哎羅啊哈啦…啊依…(-0032)哎…哩哩啦啊…啦…依…啦(-00:41)把燈亮著,把火燒著……依…哎依……”(人聲,一人演唱)。。該歌詞內容簡單,大部分是襯詞。在歌曲中間約41秒的地方,歌手唱到“把火燒起來吧”等歌詞。來自四川涼山的彝族歌手阿鐵說日證實這首歌的旋律類似于一種被稱為“馬布”的吹管樂器,這個樂器是一種豎吹的單簧管樂器。阿鐵說日指出,這是一段哼唱,學的是當地的馬布曲,這個曲調流行在越西和甘洛一帶。歌詞大約是“我會學唱馬布曲,馬布曲的意思是:把火燒起來,我要烤火。把火燒起來,我要烤火”。該曲調包含了“我要烤火”的重復片段。這似乎與原始記錄有抵牾之處。有關燒火的內容是歌曲的一部分而非歌曲之外的請求。有趣的是,文本的識別在這段表演的認定中占據了主導的地位,唯一能應對這段聲音的線索是歌手夸張的“亂喊亂叫”,這對于今天的彝族人來說,如此“亂唱”不被認可。而這個刺耳的喊叫,或許就是在模仿簧管樂器而非笛子。
從這段錄音中可以推斷,這個歌手可能是村莊里的畢摩,他的歌唱也像是一種想象,并沒有其他樂器在吹奏,而是人聲在模仿樂器的聲音。這位歌手可能只是要展示他的歌喉(也可能是在模仿管樂器的聲音)。他這么做或許并非一種習慣,而是要顯示出他在面對陌生人時所做的突出表現。
這段錄音的信息是如此模糊而不清晰,以至于對它的內容難以斷定。從今天大眾的觀點看,準確的含義可能是最有趣的。然而,從檔案管理者和錄音師的觀點看,這個歷史錄音并不清晰,整個的錄音可能提供出的恰恰是一個缺席的可能性。因而,對于來源和聲音的描述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縝密的對待。而早期錄音也并不意味著是一份最為“原始”的錄音。
就此收藏而言,接著這首歌的下一首也是由同一位歌手演唱(魏斯南中國蠟筒14)。然而,這段錄音是一首非單人演唱的婚禮歌曲。由于是婚禮歌曲,所以由一群人一起唱*如同蘇毅苗的描寫(2017年9月30日,越南):這是結婚場合用的,類似于漢語中的諺語和經書。結婚的晚上,新娘和新郎家里人坐在一起,派出雙方老人或者會唱歌的人對歌,現在涼山一帶民間還在使用,一直延續下來都是結婚場合使用的。現在有些轉變,訂婚時也在用。翻譯唱詞比較困難。。
雖然早期錄音面臨缺乏可靠記錄文檔的問題,但錄音本身卻能夠展現真實情況。蠟筒13被認為是對一種樂器的模仿。在錄音剛剛開始的地方進行適當的分析,如把一小段聲音記譜,可以發現錄音至少模仿了兩種樂器,一對旋律樂器而非一件。在第五行,第二件被模仿的樂器在較高的音區進入,并標志著相對自由節奏的切入。緊接著,歌手唱到了燒火烤火的重復部分,如同“馬布曲”音調那樣被識別為傳統歌詞的一部分。
總之,這位歌手演繹了一對或一件可能在不同場合常常一起使用的樂器。他也從未表示這是一次真正的音樂表演。假定的“表演者”已經概括、“翻譯”并“打包”了所有信息,這些信息很難在日后以描寫的方法來辨認。沒有人能確認所有的事情,因為總是有一些超然于空間、時間或載體的知識。但是,這是否意味著不值得我們再去挖掘細節和恢復當時的情形呢?當卡亨德(Kahunde 2012)通過大英圖書館的可用歷史錄音恢復宮廷傳統時,他亦曾試著來討論一個類似的修辭問題,盡管他的角度不盡相同*《把它帶回家》BBC廣播電臺第3頻道2016年4月3日18:45,2017年8月4日22:15。
另一個我們親身經歷并在最近發生的例子也令人震驚,這是為了尋找蘆笙這一為貴州和廣西侗、瑤、苗族人民用在大型表演中的吹管樂器的不同制作方法而生發的想法。如果我們運用社交媒體去尋找以前的樂器制作者,把從各種民間博物館所收集到的有限的照片傳播出去,情況會怎么樣呢*這個問題是由廣西藝術學院的楚卓和張老師在2017年9月4日于南寧提出的。?認真來說,我們認為這樣的做法并不是為了通過發動大眾(所謂大眾外包方式)去尋找真相,而是希望通過這樣的方法,以激發那些住在邊緣地區的人們意識到歷史的發展和公共的知識,畢竟他們正是那些遠離社交媒體的人。這個聽著像是尋找信息的問題,對于跨越代際以及近期遷移的社群來說有著重要的影響。有時候,似乎方法才是目標。現在,很多人知道只有少數幾位蘆笙制作者仍舊在世,也有一些年輕的村民開始考慮參與到這些早期技能的重建中。
這個例子直接引出最后一個論點:
4.為什么這些人不去等待下載資源的體驗呢?把老錄音轉化為數字化文檔,并將之上載到一個漂亮的有形載體上,以獲得那種“失而復得”的感覺是否真有那么重要?這看上去似乎有些荒謬。并且,人們并沒有失去老錄音,相反,他們應該為老錄音得到妥善的保管而心懷感激。
俗話說:“只有兩件事不會因為給出而丟失,那就是親吻和歌曲”。揣摩這句令人鼓舞的說法,只有在被給予相同價值觀的文化條件下,這個觀念才是有效的。如果每個親吻變成一顆制造出來的玻璃珠給予受吻者,那么親吻的舉動就不再被視為與施吻者有關;它將被視為一種產出物,且無關乎經濟角度上對他人利益有多珍貴。因此,歌唱,音樂以及其他被記錄的聲音也是一樣的。假如這個產品早已被數字化,我們直接下載就行了。但是,事實并非如此。就此而言,過去已非那個“過去”。因為在這個時間的過程中,那些過去制作的錄音產品已在產出它的多種方式中丟失了。
當然,數字化體驗有助于提高對無形事項的授權與控制。然而,非數字化時代也曾存在。這個時代的意識,象征著一種重新獲得可以將任何類型的知識銘刻于任何載體上的想象力。在這一實踐過程中,某些東西以非數字形式返回似乎是合法的。從技能繼承的角度來看,這無疑是一個“不可選擇”的事實。盡管如此,也并非沒有協商妥協的余地。以數字資料返還的載體,事實上跟原本承載已知信息的那個載體,有著本質的區別。這個協商結果表明,給予的行為比給予的項目形式更為重要。事實上,有意識的行為才是關鍵,而非技術上如何實現。
我清楚地記得自己接受公開采訪經歷的感受,廣播電臺壓根兒不告訴我什么時間以及何種方式可以獲得這個采訪錄音的最終副本。盡管我仍然擁有這些經歷,但我卻感到受損。如果這不算是損失,我則感到被利用了。只有在我經濟上更為穩定以及學術上更為成熟之后,我才不會被這些所困擾。但至少,我并沒有為自己在節目中被廣泛報道而開心,因為我并沒有參與和接受與這一節目有關的任何反饋中。
這個清晰的例子可以與獲得數字拷貝的、令人驚訝的請求作類比,與資料傳輸的方式一樣,它包含了一種儀式,并直接接觸那個被認為是藏品來源的社區。麥斯克爾(Meskell,2013)認為,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來說,很難以找到簡單的解決方法:所有的無形物都存在于一個來自人們活動著的有形環境中。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處境。我很開心這一步驟將會成為現實。對文化資源的維護,包括從多方面進行更為細致和深入的理解,而未來亦會不斷給予我們新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