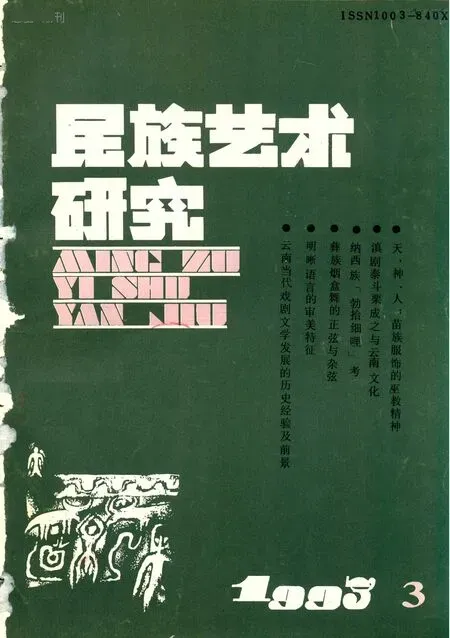寫意精神與中國油畫的當代性建構
馮民生
寫意精神自中國油畫誕生之日起就成為其核心命題。時下,隨著中國美術人文化自覺意識的增強和油畫民族特色建構的加強,使寫意精神成為中國油畫發展的當代性命題。寫意精神作為體現中國油畫民族特色和中國風格的重要理論支撐,是我們思考中國油畫現代發展的本土視角和民族文化價值的所在。
在中國油畫百余年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經過幾代人的努力與探索,使中國油畫逐漸形成了比較完整和具有鮮明特色的民族藝術形式。審視中國油畫百余年的發展歷程,其不可回避的一個特點是,作為舶來品的中國油畫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地浸潤中國文化精神和吸納民族藝術基因,使其從總體上漸漸獨立,愈加凸顯中國特色和中國風格。在中國油畫由舶來品轉變為民族藝術樣式的過程中,作為中國藝術表達方式和創作思維的寫意精神,在其發展進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成為中國油畫當代性建構的重要精神凝聚和理論支撐。
一、寫意的含義
寫意,作為中國藝術的核心內容和重要范疇,它不但是一種風格樣式,而且是一種藝術的思維方式,是一種中國藝術家建構畫面視覺圖式的先行意識,也是體現中國藝術精神的重要表現內容,甚至可以將其看作藝術的系統方法論。尤其在中國油畫實踐中,寫意更為突出地體現了方法論的意義。從中國油畫發展的宏觀歷史視角審視寫意精神,它就是中國文化的精神凝聚和藝術基因的鮮明體現。如果從中國畫的風格看,在中國繪畫中有“寫意”與“工筆”之分,從這方面看,寫意就是一種藝術風格,一種畫法。但是寫意作為一種藝術范疇,它已經超越風格層面成為包含藝術思維方式和表現方式的具有體系性的方法論知識,承載著民族文化的質地和藝術精神。
“寫意”作為傳統美學概念的出現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先秦時期,《左傳》中的“鑄鼎象物”和《周易》中的“立象以盡意”就已經有寫意的含義。中國繪畫理論中出現“寫意”內容的表述是在唐代,張彥遠就有:“意存筆先,畫盡意在”。宋代的歐陽修也有:“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張彥遠和歐陽修則認為寫意就是作畫的目的。在中國繪畫史上直接表述“寫意”這一概念則是在元代。其時,夏文彥在《圖繪寶鑒》中對北宋僧仲仁所畫梅的評價中就曾出現過這一詞:“以墨暈作梅,如花影然,別成一家,所謂寫意者”。夏文彥的寫意含義更多的指一種風格。但是從“寫意”這一詞的本意來看,它包含了“寫”與“意”兩層意思:“寫”是“抒發”和“書寫”,有“表達”的成分;而“意”則包含“意志”“意圖”“思想”等含意。除此之外,如果從繪畫的層面理解,意還有神韻和精神的含義。寫意也可以看作寫事物的神韻與精神。在這一過程中,“寫”是“意”的物化和顯現,是手段;“意”是“寫”的目的和旨歸。沒有“寫”,“意”就無法顯現;沒有“意”,“寫”就沒有了生命和精神,因此寫意是互為表里的,共同構成不能分割的整體。從其呈現狀態分析“寫意”正好就是作畫的過程與方式。概括地講,寫意主要是指藝術家通過藝術形式表現思想感情和對社會、生活、藝術的感悟,體現精神情懷。從中國傳統詩歌創作的角度看,寫意就是比、興,是觸物生情,借物以起興。如果從中國油畫的實踐層面理解寫意,它已超越了風格流派的范圍而體現為思維方式、表現方式、審美趣味、藝術精神等諸多的文化意義。
寫意作為一種藝術的思維方式,它從“觀物取象”到“意象表達”都與西方油畫的思維方式和表現方式被明顯地區分開來。寫意所包含的“觀物取象”就是中國文化觀照事物的方法。正如《周易·系辭下》中所指出的:“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李來源,林木:《中國古代畫論發展史實》,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7年版,第7頁。后人把這種“仰觀俯察”的觀察概括為“觀物取象”。這種“觀物取象”的“觀”,就是一種對客觀物象的直接觀察和感悟;而“取”就是在“觀”的認識基礎上,對“象”的提煉和創造,并以形象模擬的方法加以體現,其中也包含了意象化的過程。這種“觀物取象”的特點,主要表現在注重對客觀物象的全方位認識和感悟,充分地調動知覺的因素去感悟,講求直覺。寫意就包含了觀物取象的內容。唐代晈然在《詩式》卷一中寫道:“取象曰比,取義曰興,義即象下之意。”其中“取象”就是選擇與情、意相契合的物象,從而將思想與情感寄寓于形象之中。寫意在藝術思維中充分顯現了畫家與表現對象的情感交融,以及對物體與對象的理解和直觀認識,同時要把表達的情感融入對象之中,使物體和對象成為飽含情感又保持對象特征的意象之物;寫意滲透在作畫的整個過程之中,包含“心物融合”和“意象營構”以及抒發表達等多個層面的內容,既體現思想、觀念等精神因素,也體現表達方式和創作方法等實踐因素,是一種整體顯現的系統的方法論體系。
二、中國油畫的寫意性
對中國油畫的發展歷史進行考察,對其從思維方式和表現方式加以系統探究,我們發現寫意性因素不但存在于表現性油畫中,而且也明顯地體現在寫實油畫中。從我國油畫家徐悲鴻和吳作人兩位畫家的寫實風格作品中我們依然能感受到寫意因素的存在。在徐悲鴻的油畫作品《田橫五百士》《徯我后》中盡管畫面寫實、人物造型嚴謹、空間效果真實可信,但是我們依然可以看出整體畫面在色彩和形體處理上的寫意特征,尤其是在主題氣氛的表現上,體現出鮮明的感情色彩與審美取向,充滿著中國藝術精神和文化價值;而吳作人在油畫作品《齊白石》《三門峽》中,雖然以寫實的表現手法進行描繪,但是對整體畫面的處理和氣氛的營造明顯體現出寫意的特點,在色調和空間處理上已經超越了寫實的局限。也有人把中國油畫實踐中的寫意簡單理解為與寫實背道而馳的隨意變形,甚至胡涂亂抹,這樣的說法既不符合中國油畫實踐的實際,也明顯歪曲了作為承載中國藝術精神和文化內涵的寫意的含義。
作為系統方法論體系的寫意,不僅包含藝術思維方式、表現方式和一系列的思想觀念,也包含意象這一范疇。如果說寫意是中國藝術表現的旨歸的話,那么意象就是實踐這一旨歸的重要環節。意象也是一種藝術思維方式的集中體現。
從中國藝術的歷史去梳理意象,我們發現意象更多地體現為一種藝術創造的方式,甚至包括一些藝術觀念。意象有著“意”與“象”兩部分內容的含義,其中“意”就是指畫家的主觀情感和思想。在一些研究者看來,“意”還指主體因悟道而產生的一種感覺、感受、思想,體現著主體對客觀事物的理解,是一種可以直觀把握的精神意識。“象”是指畫家對客觀對象進行概括與提煉后所產生的形象。是畫家主觀情感、思想與客觀對象的有機結合,并依照藝術規律創作的藝術形象,這既不同于客觀對象,又不脫離客觀對象而造就藝術形象。從審美意象產生的動機和過程考察,其以象達意,以象抒情,因象而獲得感性愉悅。在意象創構過程中,主體起著主導作用,無論是有感而發,還是情不自禁,都是主體受到客觀物象觸動后的精神狀態的一種呈現,這種狀態盡管是一種物我交融的狀態,但是主體在其中的主動性并沒有被模糊化。因此,意象生成的過程是通過主體積極的能動作用來完成的。意象在中國藝術中更為明顯地體現為一種思維方式和一種表現方式,是寫意的核心內容。作為寫意核心內容的意象,是其藝術思維活動中的基本內容,是以藝術化和審美化指代事物,以喚起存在于事物的美感與藝術因素,使得客觀對象幻化為藝術形象。意象是外在對象與信息在主體內部依照藝術規律所建構起的精神體,是藝術思維和藝術形象建構的本質所在。因此,意象創造成為寫意的關鍵環節之一,沒有意象化的過程寫意也就成為簡單的概念而無法獲得其旨歸。
在中國油畫實踐中,“寫意”往往和“寫實”“表現”等概念聯系和交織在一起,更為突出地體現為思維方式和表現方式,并集中體現出意象化特點。中國油畫的寫意性能夠成為思考和理解中國油畫實踐歷程和發展特點的精神因素,它帶有明顯的文化質底和藝術基因。在油畫表現中,寫意與寫實成為相對的兩個概念,主要是從風格特點上劃分的。如果說寫實在表現中注重對客觀對象的真實再現,使畫面空間成為現實空間的真實幻象的話,那么寫意則是突出主觀與客觀融合后的感悟與情感表達,使畫面成為表達主觀感情和承載文化意義的載體,但在視覺展現上卻不失真實的成分。如果說寫實是偏向于再現的話,那么寫意就偏向表現。需要指出的是,寫意在表現中強調主客觀融合所生產的新的意象,注重感悟和直覺,它是對畫面進行現實和主觀理解相融合的改變和處理的,而這種改變和處理符合中國藝術的創造規律,在“似與不似”之間進行取舍,重視“傳神”“意境”“趣味”“氣韻生動”的體現。另外,在中國油畫的發展過程中,寫意和寫實不是完全對立的,寫實風格的作品中也體現著寫意的特點。寫意在中國油畫的創作實踐中更為突出地體現在油畫表現中對中國文化精神和審美趣味的自覺融入,以其統帥表現的整個過程,使油畫表現成為中國藝術的思維方式和表現方式、審美趣味、藝術理想的自然流露和視覺展現。除此之外,在中國油畫中,寫意不能離開客觀對象以臆造形象。
作為具有深厚文化內涵和體現藝術精神的寫意表現手法,也是藝術表現的制高點,不是一蹴而就的淺薄學問。對于中國油畫的實踐者來說,要達到體現寫意精神的境界,不僅僅只是掌握寫意的理論知識就可以的,而是要將其化作藝術實踐的表現手法加以運用。對于在中國油畫表現中體現寫意精神,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要熟練掌握油畫的表現技巧,諳熟油畫的創作特點和規律;同時,也要掌握中國藝術的特點和規律,并能將中西藝術融會貫通,在油畫表現中自覺體現中國藝術的美學價值和藝術精神。以上兩點缺一不可。如果沒有掌握好油畫的表現技巧和了解油畫的表現規律,寫意精神就只能是觀念而不能轉化為油畫語言。試想,一個沒有熟練掌握油畫技巧和油畫歷史的人,肯定連油畫都畫不好,何談在油畫實踐中體現中國藝術的寫意精神?相反,如果有良好的油畫表現技巧,又熟悉油畫的特點和歷史,但不了解中國藝術的寫意內涵和意義,對中國藝術的特點和規律不熟悉,也不能在油畫表現中傾注寫意精神。
三、寫意與表現
如果從寫意的意象化思維分析,它與西方油畫表現中的思維方式有較大區別。意象化的思維是一種始終不離具體形象的主體化過程,其狀態就是主客融合,將對客觀事物的主觀感悟和闡發放在首位,依照對客觀事物的感悟進行主體化處理,而這種主體化就是要進行事物的傳神寫照并營造意境,更多地體現出直覺把握對象的特點。正如元代畫家張退公提起畫竹的體會時所言:“得之心,應之手,心手相迎,則無不妙矣。”*俞劍華:《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上、下冊,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7頁。這種將形象化跡于心、以手托出、心手相應的過程就是一個由意象描繪到寫意的過程,充分表現了畫家的思想和感悟,也符合“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中國畫的創作意旨。就鄭板橋的“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的繪畫理念而言,“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就是注重客觀到主觀的情感注入,使客觀之物變成意象化的對象;而從“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則是由對象意象化到藝術形象客觀顯現的過程——由此完成由意象到寫意的創作過程。其實這個過程充分體現了中國藝術中意象化的思維方式,始終把客觀對象作為感悟、闡發的根本,并注入主觀情感;在思維方式上體現出主客融合的狀態。因此,中國畫創作更多地體現為“心識目記”地表現“心中丘壑”,甚至可以“以大觀小”,通過知覺感悟抒情達意。正如李可染所講的:“中國畫不只包括視覺,也包括知覺。應包括所見、所知、所想。”*李可染:《李可染論藝術》,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頁。這種調動人的全部身心的感知在一定程度就是一種意象思維。意象化的畫面處理是緊緊依附表現對象展開來表達的,就像王履的體驗,“我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俞劍華:《中國古代畫論類編》上、下冊,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年版,第798頁。始終心物不離,相互交融,成為一體。寫意依照主客融合、心物交融后的感悟遵照中國藝術的“傳神”“意境”“氣韻生動”等審美理想進行表現,其中不乏概括和抽象的因素,但是它絕不是變形和夸張。主客融合思維主導下的寫意是知覺為先的整體把握。
從寫意的表現特點看,其狀態是主客交融的,具有知覺抽象的特點;而西方油畫中的表現,主要體現為畫家站在表現對象的對面進行審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主客二分的思維特點,在表現中注重畫家的主觀感情,依照主觀情感對客觀對象進行概括、變形,甚至夸張處理,具有理念和情感為先的直觀抽象特點,其中心和立足點是主體本身。艾布拉姆斯認為,“表現說的主要傾向大致可以這樣概括:一件藝術本質上是內心世界的外化,是激情支配下的創造,是詩人的感受、思想、情感的共同體現。因此,一首詩的本愿和主題,是詩人心靈的屬性和活動。”*[美]艾姆拉姆斯:《鏡與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頁。以理念或者情感為先去表現對象,會以主體為中心把個人意志強加于對象身上,使對象成為任意變形,甚至夸張、扭曲的形象,與客觀對象愈加分離,這其實就是一種主體精神的無限膨脹,是主體精神對自然對象的吞沒,完全拋棄感性的自然形象的原始外形,以主體感情為主導的抽象化表現,其主旨就是表現內在的情感沖動。
另一個突出的表現特點就是以表達主體的內心情感為主要特征。首先內心情感是由主體的情緒和思想所駕馭的,在這樣的表現中更偏向于自我的表現,其狀態是使主體與客體分離。而表現是通過對物象的夸張、變形,甚至歪曲來實現的,包含情感為先的直觀抽象化因素,凸顯了唯我獨尊的主體性。我們看美國抽象表現主義畫家德庫寧的作品,畫面上的女人是被丑化的,畫面給人的就是恣肆的筆觸和強烈的色彩,仿佛主體對客體的有意歪曲,這顯然是主客二分的思維所致。我們從法國印象派畫家莫奈的作畫過程可以感覺到其理念和思想為先的抽象過程。莫奈深有體會地說:“當你出去畫畫時,要設法忘掉你面前的物體:一棵樹,一片田野……只是想:這是一塊藍色,這是一條粉紅色,這是一條黃色,然后準確地畫下你所觀察到的顏色和形狀,直到它表現了你最初的印象時為止。”*[英]貝納·頓斯坦:《印象派的繪畫技法》,平野、陳友任譯,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82年版,第50頁。他在大自然中寫生時,把自然物體看成是粉色、藍色、綠色等不同的色塊,最后依照自然形狀把不同的色塊畫上去,就完成了其畫作。可以肯定的是,莫奈在作畫前就有一個理性的概念引導其完成畫作,而這種概念是設定在對感性物體進行感覺之前的。20世紀初挪威表現主義畫家蒙克在表述他創作《吶喊》的體會時寫道:“我和兩個朋友沿路前行。太陽正在下落。我感到一陣憂郁,——突然天空變得血紅。我停下腳步,依靠著欄桿,死一般的疲倦——放眼望去,燃燒的云朵像血和劍一樣,懸掛在藍黑色的峽灣和城鎮之上。我的朋友繼續往前——我站在那里,恐懼地顫抖著。然后,我覺察到一聲巨大的吶喊劃破天際。”*[荷]曲培醇:《十九世紀歐洲藝術史》,丁寧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514頁。這種由主體情感引發的對客觀對象的抽象表現,使主體和客體分離與對立,是自我意識的無限放大。因此,表現主義畫家都是以情緒為主來對事物進行變形和夸張,也進行情感、理念為先的直觀抽象。而中國的寫意則從主體對客觀的感受中觀照,把主體融入客體或者人化的自然中,由此進行表現,這與西方的表現又有本質區別。中國藝術的寫意始終不離可感的對象,也不以變形來實現寫意,而是在心物融合中觀照對象;而西方的印象派和表現主義始終使以情感為先的抽象化對描繪對象進行變形與概括甚至夸張。這也就構成了寫意與表現的區別。如果說寫意在表現對象時,主觀與客觀是渾然不分的,那么表現則體現出主客觀之間的分離與對視。當然中國藝術的寫意與西方的表現不是絕對地截然不同,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之處,如注重對感情的表達和以對象為依據的闡發,都有相同之處。寫意與表現的真正區別還是思維方式與表達狀態的區別。
四、寫意精神與中國油畫的當代性建構
寫意作為藝術范疇,是由諸多藝術范疇相互凝聚而形成的一種方法論體系。它既包括精神性因素,體現為思想、觀念、思維方式;也包括形態性因素,體現為表現方式、表達方式、實踐運用等諸多方面——這為中國油畫的當代建構,不但提供精神和思想源泉,也提供思維方式和表現方式,成為中國油畫當代建構的主要理論和實踐基礎。
隨著新時代社會文化建設的需要,中國油畫的當代面貌的特征無疑是中國油畫的民族風格和民族氣派,這樣的寫意精神在中國油畫的當代性建構中就顯得十分重要和必不可少。從中國油畫的發展歷史來看,其無疑把寫意精神的體現作為發展目標加以實踐。在中國油畫的本土化發展歷程中,寫意成為精神性因素使中國油畫在發展中不斷向民族藝術回歸。可以說中國油畫的寫意精神追求與20世紀以來中西藝術融合的時代背景緊密相連,中國油畫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汲取西方油畫的知識,同時不斷注入民族藝術精神。從20世紀上半葉起,盡管中國油畫還在向西方學習,但是有志向的第一代油畫人在學習中已經開始思考和踐行油畫的寫意性。林風眠以“中西調和”的觀點,把中國民間藝術的趣味融入油畫表現中,甚至以彩墨作為表現形式,來體現寫意精神和進行意象化表現。劉海粟則以意象化的處理,在表現中十分注重線條和墨色的表現力,使得油畫作品更加概括化和富有中國藝術的精神氣質,體現出寫意精神。我們看他創作于1929年的《快車》和1931年的《雪霽》,畫面表現中盡管是色彩和筆觸的膠合,但卻體現出筆墨意味,寫意特征非常明顯。正如他發表在1924年12月1日《晨報》上的《藝術與生命的表白》中寫道的 :“我常常看見一種瞬息的流動的線,燦爛的色彩,心弦便不惜地潛躍,自己只覺得內部的血液要噴出來一樣,有時就頃刻間用了色彩或線條表白出來。表白出來了,自己覺得生機盎然,異常高興。”*趙力,余丁:《中國油畫文獻》,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2年版,第469頁。從劉海粟表述的狀態來看,這依然是寫意的心身體驗。既是提倡寫實繪畫的徐悲鴻,在他的油畫作品中,加強線的作用,把中國畫的筆墨意味融入油畫表現中,以體現寫意精神和民族特色。他于1931年創作的《徯我后》和1940年創作的風景畫《喜馬拉雅山遠眺》,其中人物的處理和色彩意味的表現及其空間的營造,已經體現出明顯中國繪畫的特點,尤其在主題的表達上寫意色彩濃郁。當然我們從當時的顏文樑、王悅之、汪亞塵等人的油畫創作中也依然能看到寫意性因素。當中國油畫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油畫民族化所展開的實踐之路,就是以體現民族特色為追求的,其中所包含的寫意精神則是明顯的。隨著中國油畫的發展,寫意精神融入中國油畫表現之中愈加成為油畫家的自覺追求。董希文、吳作人、羅工柳、艾中信、吳冠中、詹建俊、靳尚誼、朱乃正、妥木斯等藝術家的油畫作品中無不體現出明顯的寫意精神。而這種寫意精神就是在油畫表現中融入民族藝術精神和人文價值。
從中國油畫的當代現狀來看,無論是具有寫實特點的油畫實踐和表現性油畫實踐還是在寫實與表現之間的油畫實踐,都不約而同地追求中國油畫的本土化與民族特色,而構成中國油畫本土化與民族特色的一個主要建構內容就是寫意精神的注入。無論是詹建俊、鐘函、靳之林、諶北新、戴士和、閆萍等具有表現性特點的油畫作品,還是靳尚誼、楊飛云、朝戈、張祖英、郭北平等具有寫實性特點的油畫作品,都或多或少地體現出中國的民族審美趣味和藝術精神,具備寫意精神的特點。
中國油畫的寫意性,更多的是精神性體現。以系統的方法進行寫意,以凝聚中國藝術精神。但是要在中國油畫表現中體現寫意精神,畫家不但要掌握油畫藝術的表現規律,而且要研究民族藝術,諳熟中國藝術的規律,將中西藝術融會貫通。油畫的寫意精神只能體現在中國油畫家的油畫表現中,而且這種寫意特征的顯現是依靠畫家的意象化表現來實現的。如果僅僅依靠對油畫表現技巧和規律的掌握,而沒有對中國文化與藝術的研究,也許能畫出較為優秀的油畫作品,卻不能創作出具有寫意精神和特征的油畫作品。對中西藝術的全面學習與修養也成為寫意性油畫實踐的基礎,尤其是油畫家對中國藝術的修養。正如尚輝先生所言:“油畫的中國寫意性追求首先應當是以書卷氣的文靜、儒雅和內斂為其審美品格的總攬,這意味著那些完全著眼于形色的視覺沖擊而缺乏文化內涵與心性修養的畫作被排除在寫意性之外,以此,便界定了西方印象派之后的畫作為何不可能完全歸入中國寫意性審美特質的緣由。”*尚輝:《困擾與重返:圖像時代的造型藝術》,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7年版,第48頁。其次,油畫性寫意精神的實現還體現為,油畫表現除表現技巧外的思維方式、審美趣味的中國化介入,使表現的全過程統籌在“民族化”的駕馭之中。為什么我們談起中國油畫的寫意精神總會與中國油畫的民族化和本土化實踐分不開,總會以林風眠、劉海粟、顏文樑、倪貽德、吳大羽、王悅之、董希文、羅工柳等具有本土化實踐特征的油畫家聯系在一起,因為他們的作品更加明顯地體現出中國藝術的審美趣味和精神。這也成為他們的油畫作品更具寫意精神的原因所在。
從中國油畫的歷史來審視寫意精神,專家都會不約而同地認為,寫意性在中國油畫中的體現與其歷史進程是同步的。中國第一代油畫家徐悲鴻、林風眠、劉海粟、顏文樑等的油畫實踐就已經包含了寫意精神和建構意象油畫的實踐。尚輝曾在《意象百年》這篇論文中寫道:“中國油畫歷史有多久,意象油畫的歷史也就多久。”*尚輝:《意象油畫百年》,《美術》2005年第6期。其實這種判斷是對中國油畫總體特點的一種概括,是對其寫意精神的揭示。縱觀中國油畫發展的實踐歷程,不能否認的是,中國油畫寫意精神的生成離不開中西藝術融合的時代背景,也是在中西藝術融合的背景中強化的。寫意精神地融入一直是中國油畫人追求的目標和理想,是凸顯中國油畫民族特色的有效途徑。
寫意作為中國藝術的核心范疇,它不但是一種風格,而且更為明顯地呈現為出一種系統的方法論體系,其核心內涵是中國藝術的精神和品格。它不僅有實踐層面的整體要求,也有形而上的系統觀念,兩方面互為表里,相互依存,構成了完整的方法論體系。因此,在當代中國油畫民族特色的構建中,寫意將會成為不可或缺的,既包含精神性因素又包含實踐性因素的體系性知識深深地融入中國油畫的實踐之中,也將成為思考中國油畫未來發展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