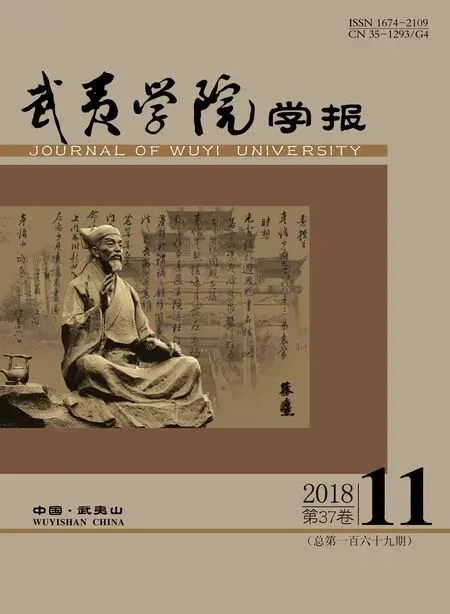中國民間故事中儒家傳統(tǒng)道德的沖突研究
周 彬
(安徽師范大學(xué) 文學(xué)院,安徽 蕪湖 241002)
目前學(xué)界對于儒家傳統(tǒng)道德的研究有從關(guān)系維度角度去研究的,如貴州大學(xué)鄧力的《儒家倫理“仁義禮智信”關(guān)系維度新探》,從倫理學(xué)的角度去研究儒家傳統(tǒng)道德之間的關(guān)系;有對儒家傳統(tǒng)道德進(jìn)行批判的,如劉清平寫的《忠孝與仁義—儒家倫理批判》,“儒家角色倫理藉由具有復(fù)雜的政治、經(jīng)濟(jì)和宗教功能的家族譜系得以延續(xù)。”[1]這其中任何一個角度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批判是為了更好的繼承,去其糟粕便于取其精華;也有從具體道德層面挖掘其內(nèi)涵的,這方面的論文還有著作比較多,在此便不贅述了。從學(xué)界對儒家傳統(tǒng)道德的研究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儒家的傳統(tǒng)道德對中國社會影響至深,這些道德不僅規(guī)范著人們的日常行為,而且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儒家的傳統(tǒng)道德對民間故事創(chuàng)作與傳播也產(chǎn)生極大的影響。民間故事中的相關(guān)內(nèi)容正是儒家道德倫理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反映,因為“民間故事是廣大人民創(chuàng)作并傳承的反映人類社會生活以及民眾理想愿望的口頭文學(xué)作品”[2]。中國民間故事題材廣泛而又充滿幻想,雖然大多數(shù)民間故事是在想象的基礎(chǔ)上產(chǎn)生,但創(chuàng)作民間故事的創(chuàng)作者來源于現(xiàn)實生活,其想象的基礎(chǔ)也離不開現(xiàn)實生活。民間故事中所展現(xiàn)的一切是對現(xiàn)實生活世界的一定反映,在這樣的世界里,民眾將現(xiàn)實生活的倫理道德思想投射其中,民間故事世界中的道德倫理也是對現(xiàn)實世界實際存在的倫理道德的表現(xiàn)。有些民間故事為了表現(xiàn)某一具體的道德往往與其他道德進(jìn)行比照,在其比照的沖突之中,主人公最終的選擇則代表著他的道德取向,或者說這樣的道德取向也是人民選擇的結(jié)果。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人民的“代表”,在這些道德沖突之下我們可以窺見具體道德在人們心中的地位;在道德與不道德的較量之中,我們看到優(yōu)秀傳統(tǒng)道德對于社會發(fā)展的作用;在這些道德沖突及較量之下,其過程到結(jié)果也折射出人們的倫理觀。從理論上看,傳統(tǒng)道德的感召力和生命力生生不息,和諧社會的發(fā)展與構(gòu)建依舊離不開它們,儒家傳統(tǒng)道德更是中華傳統(tǒng)道德的代表,對其傳統(tǒng)道德的價值體系進(jìn)行不同角度的研究與考量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一、民間故事中的“孝義”沖突
“孝”從字面上解釋就是孝順的意思,這是家庭父母與子女的倫理規(guī)范,更為精確的說是子女對父母要遵守的道德規(guī)范。鐘茂森說:“這個孝,刑昺在《孝經(jīng)注疏》里面,是這樣解釋的,說‘事親之名’,能夠侍奉雙親這叫孝,所以這個字就是事親的意思。”[3]古人說:“義者,宜也。”言下之意就是適當(dāng)、應(yīng)當(dāng)、適宜的意思。 義自古以來就被人們所重視,也是儒家所提倡的“五常”之一。“傳統(tǒng)思想認(rèn)為,義是人之為人的根本,一個人如果不講義,就和禽獸差不多了;義還是組成社會的一種根本原則,社會、國家之所以能夠維持下去,主要有賴于正義的存在。”[4]
“孝”與“義”都是儒家道德倫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既能共存也會發(fā)生沖突。孝義兩全的情況并不多見,在民間故事中孝與義往往難以共存,二者的沖突也是迫于無奈。民間故事中的主人公往往只能選其一,沖突之下,他們的道德選擇同時也反映出民眾的道德價值觀。安徽民間故事《孫叔敖舍己為人》[5]中主人公孫叔敖就面臨著“孝”與“義”的選擇,故事大意如下:年幼的孫叔敖與母親相依為命,有一天他下地干活時發(fā)現(xiàn)一頭正在爬行的雙頭蛇,在他們那里,雙頭蛇是大災(zāi)星,見到它的人就會死去,為了避免它害人,孫叔敖拿起鋤頭把雙頭蛇打死,但他也會受到詛咒死去不能侍奉母親,不能盡孝道。母親為他的選擇而感到自豪,能夠舍己為人是為大義。最后孫叔敖也沒有受到詛咒而死,反而做了大官。從血緣關(guān)系上來說,無疑孫叔敖與母親是至親關(guān)系,有著不可割裂的血緣紐帶,孫叔敖與村民是社會關(guān)系,他的這種選擇成其“義”卻不能成其“孝”,選擇之下,他選擇了舍己為人的“義”。因為這樣,他可以救更多無辜的人,傳統(tǒng)道德更為注重天下以及人民的整體利益,反對私利主義。孫文靜曾在其碩士論文中說:“在處理和看待義與孝的關(guān)系時,為全義行,則應(yīng)該舍棄父母親人,行大義滅親之舉。”[6]可見,“義”在本質(zhì)上便是一種舍棄的精神,舍棄的可以是物質(zhì)也可以是精神,有形和無形都在舍棄的范圍里面。在《長嫂如母》[5]的故事中,包拯為彰顯正義,不得不大義滅親。包拯幼年喪母,長嫂如親生母親一樣待他,包拯處決了為非作歹的包勉,包勉作為其嫂子的獨(dú)子,處決他無疑會給自己的嫂子帶來極大的傷害,包拯雖感不孝,在萬般矛盾之中,為了顧全大義,毅然選擇大義滅親。孝是以血緣為紐帶的家庭倫理,重孝成為一種家庭規(guī)范有利于家庭和諧;義是社會倫理道德,它作為一種社會道德標(biāo)準(zhǔn),必然在某些時候會與個人利益發(fā)生關(guān)系。當(dāng)二者有沖突時,我們應(yīng)當(dāng)有所辨明。“孝”這種道德規(guī)范在處理與子女倫理關(guān)系時,并不全然是正確的,它也有不合理的一面,這其中就包含著壓抑子女獨(dú)立自主、拘于家族的親情等狹隘因素。上述的《長嫂如母》如果包拯偏袒其嫂之子,便是一種“愚孝”,這必然為“義”所不容。不合“義”的孝行應(yīng)當(dāng)舍棄,“大義滅親”這樣的孝義觀為大眾所接受也正是這樣的原因。當(dāng)孝義關(guān)系一致時,它們之間的沖突則是個體利益與整體利益之間的沖突,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便是舍小利而求大義的民族,個體利益要服從整體利益的要求,當(dāng)二者出現(xiàn)沖突時,為了顧全整體利益,舍棄自身的個體利益也是合情合理之舉,所以民間故事《孫叔敖舍己為人》中的孫叔敖也毅然選擇“義”,并且也得到了母親的贊賞,結(jié)局圓滿。
民間故事孝義沖突之中,擇義而舍孝是一種社會性的傾向,民間故事來源于生活,來源于人們的生產(chǎn)勞作之中,是民眾的創(chuàng)造。民眾自身的選擇在有意無意之中也滲透到了他們創(chuàng)造的民間故事之中,口耳相傳的過程中久而久之形成了社會約定俗成的道德準(zhǔn)則,在現(xiàn)實生活中如此,在民間故事的世界之中也是如此。不同的是,藝術(shù)用不同于生活的方式表達(dá)出來。現(xiàn)實中,孝中的“愚孝”的糟粕因素也是導(dǎo)致民眾傾向擇義舍孝的重要因素,其決定性因素當(dāng)然還是整體之于個體的重要度。“孝”在處理家庭倫理關(guān)系方面是道德至理,甚至是根本性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家庭作為社會的細(xì)胞,家庭的和諧有利于社會的和諧,但是家庭行為威脅到社會穩(wěn)定和諧時,作為處理家庭倫理關(guān)系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孝”便位居“義”之下,在兩者沖突之下便以“義”作為評判標(biāo)準(zhǔn)了。
二、民間故事中“仁孝”沖突
“仁”也是中國傳統(tǒng)道德最重要的規(guī)范之一,包括儒家在內(nèi)的許多學(xué)派對這一道德都有不同的解釋,例如“仁”在墨家那里可以理解為兼愛,這是博愛的道德規(guī)范,《論語·顏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7]在儒家看來,“仁”作為五常之首其內(nèi)涵是講述人與人的相處之道。“在儒家那里,仁被視為‘全德’。它的核心內(nèi)容就是對人愛,即對人同情、關(guān)懷、愛護(hù)和幫助。”[4]封建君主施以仁政則為仁君,仁者愛人則為仁人。儒家的這種“仁”是以愛人和愛物為主要內(nèi)容,但是這樣一種“仁”所表現(xiàn)出的愛卻是有著鮮明的區(qū)分,這樣的“仁”依據(jù)階級、親疏而定。儒家的“仁”是以“孝”為根本的,所以當(dāng)這兩種道德發(fā)生沖突時,民眾的選擇不言而喻,這一點(diǎn)在民間故事中有著鮮明的表現(xiàn)。
河南民間故事《袁世凱殺人保墳》[8]說的是這樣一個故事:袁世凱的母親去世,袁世凱陪葬了許多金銀財寶以表其孝心,他又怕人盜墓,讓自己的母親泉下不得安寧,所以設(shè)計讓看守的營長朱連寶將自己母親的墓假意挖開,制造墓已經(jīng)被盜的假象。朱連寶依計行事,第二天他又把這消息放出去,聚集了許多看熱鬧的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袁世凱借此將朱連寶殺害,原來袁世凱為了確保其母的墓遭人計算,表面授意朱連寶挖開其母之墓,對外宣稱財寶已經(jīng)被盜,實則殺雞儆猴以此震懾那些企圖盜墓之人。故事中袁世凱對其母親盡顯孝道,但是其孝卻是在對部下不仁的基礎(chǔ)上。故事中袁世凱在“孝”與“仁”之間選擇“孝”,在現(xiàn)實中,我們會發(fā)現(xiàn)“親親相隱”造成結(jié)果就是“損人利親”,損的人大多是對自身無關(guān)緊要的人,而在中國封建社會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觀念很強(qiáng),往往以“血親之心有所不忍”的理由來“損人利親”,家族之中也常用“家丑不可外揚(yáng)”的外衣將真實隱瞞。各個地區(qū)都有這一類民間故事,那就是后母對繼子或者繼女不仁,但繼子和繼女往往不計前嫌,以孝報之。如甘肅民間故事《舜的傳說》[9],舜生下來沒多久,親生母親就死了,舜的父親又娶了一個老婆,舜的繼母經(jīng)常打罵舜,一心想要置舜于死地,舜的父親不明情況也幫著妻子打罵舜。舜后來被公選為統(tǒng)治者,但是舜卻沒有報復(fù)其繼母和父親,而是以孝報之。古代的那些圣賢身上都有這樣一種品質(zhì),那就是以德報怨。雖然舜的繼母一心想要置他于死地,對舜“不仁”,但舜卻還是行孝道。究其原因,首先是舜的個人原因,他自身的品質(zhì),作為圣賢,他“以德報怨”;其次便是“家丑不可外揚(yáng)”,家中的“丑事”被外面知曉后不利于整個家族的形象,古代的家族觀念很強(qiáng),維護(hù)家族形象是極其重要的;最后,“家和萬事興”的觀念,作為統(tǒng)治者,統(tǒng)治民眾首先自己的家庭得和諧,所以舜得為這份和諧作為自己道德上的犧牲,不能讓自己的“后院失火”,為臣民作出表率。故事中的圣賢如此,民間故事中的平常人家也是如此選擇,如吉林民間故事《丁香花的傳說》以及河南民間故事《后娘》中,繼女對繼子或者繼女投之以不仁,但故事中的繼子繼女卻報之以孝道。雖然故事中繼母不仁手段之多,有些情況下他的丈夫還知曉內(nèi)情,但大多數(shù)情況下都是睜一眼閉一只眼,也并不對外宣揚(yáng),繼子繼女在忍受之下還要以“孝”來對繼母,有些繼子繼女在不堪忍受的情況下都以“變形”而結(jié)局,變形為動物或者植物。《論語》這部儒家最權(quán)威的經(jīng)典,在涉及到仁與孝沖突之時,都“舍仁以成孝”。例如《論語》中有這樣一段對話:“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子為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7]無論從何種角度看,父親偷了羊都是一件不光彩的違法行為,應(yīng)當(dāng)受到法律的懲罰,但兒子因為孝卻不得不幫父親隱瞞其罪。劉清平說:“雖然孔子很重視仁與孝的統(tǒng)一,但在他看來,只要二者出現(xiàn)沖突,兒子就應(yīng)當(dāng)不惜放棄對他人的仁愛之心,以維系對父親的孝心。更重要的是,這種“舍仁以成孝”的態(tài)度同樣屬于孔子的一以貫之之道”[10]。從這里我們就可以看出孔子把孝看做是比仁更加重要的人生價值。“孝,緣于生物性的血緣關(guān)系,伴隨著人類社會的進(jìn)化和發(fā)展而演進(jìn)。”[11]中國歷來重視血緣關(guān)系,認(rèn)為“血濃于水”,那么順理成章的,受到這樣思想的影響,在民間故事中,仁孝之間的沖突最終民眾選擇了“舍仁以成孝”。
“舍仁以成孝”作為兩者沖突的結(jié)果,在解釋“仁”的內(nèi)涵時我們應(yīng)當(dāng)就可以看到這樣的一種結(jié)果,因為儒家的“仁”是以“孝”作為根本的,儒家所講的“仁”,首先是要愛自己的親人,要“親親為大”,要遵循“出則孝,入則悌”的原則,所以在二者的道德價值導(dǎo)向上,民眾的選擇是在道德價值導(dǎo)向上做出的價值判斷。
三、民間故事中“忠仁”沖突
“忠”也是中國傳統(tǒng)道德最重要的規(guī)范之一,它的字典釋義是“忠誠無私,盡心竭力”。李建生曾說:“從傳統(tǒng)文化的范疇來看,它既是倫理道德的首要內(nèi)容,也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內(nèi)容之一。”[12]“忠”涉及的范圍比較廣,如忠君愛國、待友等。在民間故事中,“忠”涉及最多的還是“忠君愛國”方面,它是處理個人與整體、個人與國家、天下與人民之間關(guān)系的基本規(guī)范。封建社會的統(tǒng)治者一直致力于“忠君愛國”思想的推崇,并把它作為封建社會道德教化的核心內(nèi)容來推廣。最理想的君臣關(guān)系是君仁臣忠,但在封建社會中這樣的情況很難兩全,民間故事中也是如此,君可以不仁,但是臣一定要“忠”。民間故事中當(dāng)“忠仁”出現(xiàn)沖突,故事中主人公的選擇就給了我們回答,給出了民眾的道德選擇。
安徽民間故事《卞和獻(xiàn)玉》[5]中:卞和得到一塊璞玉,他的鄰居告訴他只要鑿開就能得到一塊曠世美玉,他不敢私自擁有,虔誠的想把這塊璞玉獻(xiàn)給國家,以振國威。當(dāng)朝國君楚厲王認(rèn)為這是一塊石頭,就削去卞和的一足以示懲戒。等武王繼位后,卞和已經(jīng)窮困潦倒,但是還是下定決心將這塊璞玉獻(xiàn)給國家,但是武王也認(rèn)為這是塊石頭,于是又削去卞和的一足以示懲戒。一直到最后文王繼位,卞和的璞玉才被國君所認(rèn)可,但是獻(xiàn)玉之后,文王的封賞他卻不要。這個故事中,卞和一而再再而三的把自己的璞玉獻(xiàn)給國家,但是不識得寶玉的兩代國君都將卞和的腳削去,并沒有一點(diǎn)仁心,但卞和并沒有將璞玉用作他用,一直到獻(xiàn)給國家為止,這樣的“忠”對比兩代國君的不仁,不由得讓人贊嘆卞和忠君愛國之心有多么強(qiáng)大。故事中的卞和在第一次獻(xiàn)玉后完全可以不用再獻(xiàn)第二次,但是他的忠心把私心壓制下來,即便國君不仁,但是他不能不忠。雖心向明月月照溝渠,但“忠”心還是要將明月向。“臣事君以忠”就是要用忠心侍奉君主,這是孔子在“事君”問題上的基本觀點(diǎn),并且這樣的觀點(diǎn)得到了后代儒家的推崇。在中國古代不乏有不賢明仁愛的君主,但是依舊有許多忠臣愿意付出生命去護(hù)主。這其中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封建社會的“忠”具有局限性,這是由私有制社會所決定的。封建社會的統(tǒng)治階級將“忠于君主”作為“忠”的根本,封建社會的局限性讓民眾“忠于君主”而非君主要忠于人民、忠于道義;另一方面,雖然“忠于君主”會有一定的狹隘性,但是在封建社會的統(tǒng)治者看來“忠君”與“愛國”具有一致性,所以“忠于君主”既具有道德約束也具有法律約束。統(tǒng)治階級的某些思想家營造輿論,統(tǒng)治者利用這些輿論進(jìn)行宣傳,將“忠君”寫進(jìn)他們制定的法律之中,從而維護(hù)君主和整個剝削階級的統(tǒng)治。古代君王推行“君權(quán)神授”的思想,君主又是國家的象征。
李建生說:“‘忠君’思想在歷史中又衍化為報效國家的愛國主義思想,忠君和愛國成為互為表里的同義詞,忠君就是愛國,愛國就要忠君。”[12]之所以如此還是因為中國封建社會是政教合一的國家,帝王既是國家民族的象征又在思想道德的上起示范作用,同時還是文化和價值觀的代名詞,這樣的身份至高無上,無可取代。所以民間故事中即便君主不仁,但是臣民不能不忠,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視為不忠”,這在封建社會對于臣民來說既是一種道德綁架也是法律上的約束。
儒家的傳統(tǒng)道德——“忠孝仁義”兩兩之間既相融又相沖,民間故事中雖然儒家的傳統(tǒng)道德之間時常發(fā)生沖突,但正因為有這樣的沖突才啟發(fā)我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遇到這樣的情況應(yīng)如何去取舍,當(dāng)然儒家思想作為封建社會的正統(tǒng)思想,其倫理道德也需要迎合統(tǒng)治階級的需要,以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為根本,所以儒家傳統(tǒng)道德本身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我們予以甄別才能加以弘揚(yáng)。張岱年在《中國倫理思想研究》中說:“在中國歷史上,統(tǒng)治階級的道德一般要起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維護(hù)當(dāng)時的統(tǒng)治秩序,力圖顯示階級統(tǒng)治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要保證被統(tǒng)治的人民的一定程度的生活,使他們安于受統(tǒng)治的地位,能夠‘安居樂業(yè)’。”[13]儒家傳統(tǒng)道德在民間故事中的沖突及其選擇說明有些道德規(guī)范統(tǒng)治者與人民大眾都加以宣揚(yáng),但是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與勞動人民的利益卻大不一樣,他們對于道德的實際要求不同,所以會發(fā)生沖突,這是一方面的原因;其次就是儒家的各個傳統(tǒng)道德本身有所涵蓋,道德與道德之間本身有一定的交集,道德與道德本身既可以兼顧但也存在矛盾;最后,儒家的傳統(tǒng)道德所創(chuàng)建的道德維度并不是完美的,因為當(dāng)時社會與環(huán)境的局限性,其本身也存在矛盾和局限性,其道德內(nèi)涵與標(biāo)準(zhǔn)在歷史發(fā)展中被不斷賦予新的內(nèi)容和內(nèi)涵,這就造成了“新道德”與“舊道德”之間的矛盾。儒家傳統(tǒng)道德在民間故事中的沖突過程及其結(jié)果有助于我們更好的理解和學(xué)習(xí)儒家傳統(tǒng)道德的文化內(nèi)涵,在學(xué)習(xí)儒家傳統(tǒng)道德的過程中我們既要學(xué)會兼顧也要學(xué)會取舍。沖突是一種矛盾,權(quán)衡之下的理性選擇有利于我們做出正確的價值判斷,有助于我們解決現(xiàn)實生活遇到的道德矛盾,但這樣的選擇還要依據(jù)實際情境,與時俱進(jìn),將富含時代正能量的元素融入其中,更有效地幫助我們構(gòu)建和諧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