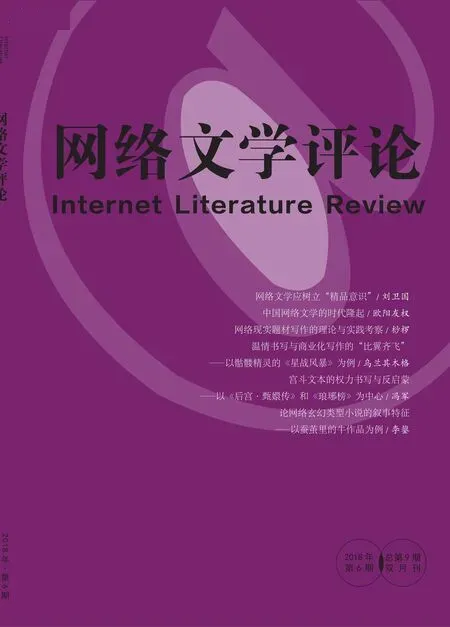宮斗文本的權力書寫與反啟蒙
——以《后宮·甄嬛傳》和《瑯琊榜》為中心
電視劇《后宮·甄嬛傳》于2011年11月開始首播,這部主打“權力”和“女性”的電視劇的收視率獲得了巨大的成績,網絡播放次數更破百億。電視劇《后宮·甄嬛傳》由流瀲紫刊載于晉江文學城的同名網絡小說改編,小說后被浙江文藝出版社、花山文藝出版社等出版。小說講述女主人公甄嬛入宮為妃,并在一系列爾虞我詐的權斗后最終成為皇太后的故事。無獨有偶,最早刊于起點女生網的海晏《瑯琊榜》也被孔笙、李雪拍成同名電視劇,于2015年9月首播,無論是小說還是電視劇,同樣反響巨大。《瑯琊榜》講述男主人公梅長蘇憑借權斗之術而復仇的故事。
《后宮·甄嬛傳》和《瑯琊榜》除網絡小說和電視劇之外,尚有漫畫、同人小說和游戲等形式傳播。筆者以網絡小說為核心,向外衍射其他藝術形式如電視、電影、漫畫等,一概稱之為文本。如果把后宮爭斗、朝堂爭斗、王府爭斗等都納入這一系統,那么這類文本可稱之為宮斗文本。可以說,宮斗文本如火如荼地流行在整個文化市場:網絡小說有匪思我存《東宮》、沐非《宸宮》、寐語者《帝王業》等;電視劇有戚其義《金枝欲孽》、于正《延禧攻略》、汪俊《如懿傳》等。大眾興起以權力斗爭為主題的閱讀熱潮。值得提出的是,《延禧攻略》本是電視劇,大火后很快被改編成網絡小說。這意味著網絡小說與影視劇之間已然形成有效的互動關系,兩者相得益彰,加大某一文本的影響力。
極大的受眾與權力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關系?文本對“權力”又有怎樣的描述?文本的“權力”書寫對接受者能產生什么影響?簡而言之,事關權力為主題的小說和影視劇大量被接受,對當下社會而言意味著什么?
一、作為權力附庸的情感
以《后宮·甄嬛傳》和《瑯琊榜》為代表的宮斗文本的典型敘事模式為“情感+權斗”。這類文本的情感描述有其自身的內在邏輯。
一是情感的暴力性。在宮斗文本中,情感是權力的表達手段,它被賦予武器的功能。無論是愛情、親情、友情等,還是同情、悲喜、疼痛等,在需要的時候都可能成為權斗的手段;恰恰是那些擁有健康情感和充滿感性力量的人物反而在權力的反復碾壓下成為犧牲品。比如,甄嬛得知自己在雍正眼里不過是純元皇后的替代品,傷心欲絕而出宮甘露寺。健康的情感欲望使甄嬛與權力中心的氛圍格格不入。然而,再回宮后的甄嬛舍棄情感的牽絆,親手毒死心愛的果郡王達到消除雍正懷疑自己的目的,利用保不住的胎兒順手誣陷并扳倒宜修皇后。可以說,甘露寺后的甄嬛熟練地操縱自我情感,以愛情的名義行謀權奪勢之實。反觀沈眉莊之死,安陵容利用其與甄嬛的友誼設局,引發沈眉莊擔心甄嬛,心急則亂,難產而死。
二是情感的脆弱性。權力洪流內部的情感極度脆弱,隨時可能變形、失效和錯位。《后宮·甄嬛傳》雍正對太后頗有芥蒂,因為太后曾與人私通,這不僅是雍正對先皇尊嚴的守衛,更為重要的是“私通”這一行為是對至高無上皇權的挑釁。吊詭的是,太后私通是以愛情為代價換取雍正登基,卻由此失去了親情。幾乎所有宮斗文本中的權力都具有規訓的力量,“它不是把所有的對象變成整齊劃一的蕓蕓眾生,而是進行分類、解析、區分,其分解程序的目標是必要而充足的獨立單位……規訓‘造就’個人。”①以權力而非情感的群體分類或者說聯盟完成之后,情感只能在利益群體內部變態滋長;而一切愛情、親情和友情,一切慈悲喜舍在斗爭面前一觸即碎。當然,群體內部具有流動性,唯一堅固的是權力的利益,這印證了情感的脆弱性。
三是情感的畸形性。《瑯琊榜》一經開播以來,以梅長蘇為代表的一干男女被貼以“禁欲”②的標簽。事實恐怕并沒有那么簡單。如果把“欲”單向度地理解為“情”,那么幾乎所有的宮斗人物都可以為權力而無情。電視劇《延禧攻略》乾隆反復重申“帝王無情”,《瑯琊榜》梁帝也說“朕也并非生來就是無情的人”。可以說,以《瑯琊榜》為代表的文本,并非“禁欲”而是“禁情”,因為“欲”還包括權力的向度;對權力的執著而“禁情”,這正好折射出權力對情感的畸變或者遏制,梅長蘇就是“禁情”的典型。人性的力量不單純是權力,更是感性的、情感的力量。宮斗文本放大權力而遏制權力的力量,使身處權力旋渦的個體“黑化”或者說喪失道德底線。宮斗文本反復出現妃子千方百計想憑借“懷孕”而“上位”,并千方百計地害對手“流產”。人之本性的生育和人之常情的母愛畸變成為宮斗的籌碼。
之所以出現情感的暴力性、脆弱性和畸形性,是因為情感與權力結盟,而權力以強大的上位話語將情感鎖進逼仄時空。情感的感性特征注定在宮斗中沒有發芽、生長的可能,人際關系善的一面往往被遮蔽和被壓抑。《瑯琊榜》靖王意氣用事救衛崢而引發的后果說明了這一點。權力不一樣,它擁有“有序/無序”互變的能力。無論是梅長蘇、甄嬛還是魏瓔珞,他們都將原本和諧的秩序體系打破后,通過權力的手段將秩序重新恢復到有利于自己的平衡狀態。這些曾經善良的且具有理想的青年人們,被刀光劍影的權力斗爭撕裂之后,最終都成為權力的中心人物,原本的天真、善良、純真成為不可追憶的“往事”。
宮斗文本“權力壓制情感”的現象,對接受者而言意味著什么呢?《后宮·甄嬛傳》有句“賤人就是矯情”的經典臺詞廣為網友傳播。“矯情”自然有違情感的正常表達,但是以“矯情”的名義抹殺情感的正常訴求,卻成為這類文本接受者常見的思維,這也是為什么這句話流傳甚廣的原因之一。雖然宮斗文本中的情感是一個被權力重新編碼后的“器物”;但是,情感作為人性最為本質的要素之一,它有維系社會個體間的人際的和諧與溫存的功能。在普羅大眾的社會場域,情感不可或缺。宮斗文本影響下的社會環境容易將一切情感都“被矯情化”。微博、微信公眾號等平臺充斥著各種“看……,學……”的網文,諸如《看〈甄嬛傳〉學職場生存之道》《看完電視劇〈甄嬛傳〉之后,從中學到什么東西?》《看〈甄嬛傳〉學職場十大生存術》;《看〈瑯琊榜〉學梅長蘇談判技巧》《看〈瑯琊榜〉的人生感悟》《看〈瑯琊榜〉,學說話技巧》。“學”意味著對宮斗文本的倫理秩序的認同,并且有意識地模仿。很多時候,“學宮斗”技巧的現實意義是運諸于職場。
宮斗文本的情感關系影響社會現實的接受者,舉案齊眉、相敬如賓隨時可能變成紅杏出墻、謀害親夫;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隨時可能變成父子反目,兄弟鬩墻;肝膽相照、患難之交隨時可能變成背恩忘義、恩將仇報。權力標識了當今時代職場男女在社會中的坐標。“沒有永恒的利益,只有永恒的敵人”的論斷在資本急速運轉的職場中廣為流傳,成為不刊之論;社會的情感必然會因缺乏“善”的一面而趨于“惡”化,社會關系因溫情的難以為繼而趨于陰騭化,身處其中的社會個體因情感的單薄而趨于局促化。
二、虛化歷史與特寫權力
《后宮·甄嬛傳》和《瑯琊榜》這類宮斗文本對待歷史的態度含混曖昧,或者說,這類文本普遍存在歷史維度缺失的問題。文本多涉及為獲得權力而明爭暗斗的宮廷生活的題材,例如王子奪嫡、妃子爭寵、黨派爭權等;當文本涉及到歷史時,常常虛化背景的帷幕。
一方面,宮斗文本或者架空/半架空,或者篡改歷史。《瑯琊榜》即為半架空的宮斗文本,其故事發生的時間場域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朝南梁。通過查證歷史,我們發現南梁存在于公元502-557年,共55年歷四朝皇帝,為蕭衍、蕭綱、蕭繹和蕭方智;以此比對小說和電視劇《瑯琊榜》,帝王不符合史實。同樣,電視劇《瑯琊榜·風起長林》發生在《瑯琊榜》后約半個世紀,歷史上的南梁已然亡國。創作者們借用南梁框架而不追求歷史的細節,是因為文本內部的權力斗爭與歷史事實(國際關系、地理位置等)之間存在不可協調的矛盾,故此選擇保留權斗,歷史僅剩下個模糊的影子。如果說《瑯琊榜》屬于半架空文本,那么小說《后宮·甄嬛傳》應該屬于架空小說,其朝代定為“大周”而無史可證,其中的人物、故事基本上源于作者的想象。在架空的背景下,作者天馬行空地制造權力的爭端。小說改編成電視劇之后,歷史對權力的讓步則表現為篡改歷史。故事定位在雍正年間,其中的大部分人物都有了歷史原型,也確實一筆帶過提到一些歷史事件,比如講到雍正立愛新覺羅·弘歷為帝、年羹堯被削官奪爵而賜自盡、準噶爾叛亂等。然而,當遇到史實與權斗敘事互相拮抗時,創作者選擇篡改歷史,以“服務”權斗。文本中雍正懷疑果郡王允禮與甄嬛私通,逼迫甄嬛親手毒死允禮。然而,歷史上的允禮并未被賜毒酒而死,他甚至比雍正尚晚三年去世。可以說,篡改歷史的文本,保存“強調和記載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有重大影響的人與事的歷史,比如戰爭、革命、英雄、國際關系、社會變革、政治風云”③的“大歷史”,而反復鋪陳虛構和權斗相關的細節的、個人的、生活的“小歷史”。
另一方面,歷史不具備能指意義。宮斗文本的歷史并沒有形成具有結構性能指的內涵,它為權力服務,亦或者說歷史幾乎等同于爾虞我詐的權力。于是,在文本中,帝位歸屬無關國家前程和天下百姓,只不過是黨派或者后宮爭斗理所當然的結果。此外,歷史喪失能指意義,故事發生的背景具有可置換性。例如,接受者們稱“太后”為“上一屆宮斗冠軍”,戲謔的語言背后暗示著,“上一屆”與“這一屆”之間的差別,僅在于出場人物的不同,“宮斗”的套路、結果等都具有可復制性,可移植到任何一個朝代。
虛化歷史不僅僅是因為作者對歷史的體悟和認知達不到可以復述歷史的地步,也不僅僅是接受者普遍對歷史不感興趣,更主要的是虛化歷史是一種敘事策略,以達到特寫權力的目的,從而增強故事的沖突性。宮斗文本中的人物大體可以分為兩種,一是以帝王為代表的“主宰者”,二是“沉默的大多數”的普通民眾。帝王幾乎不管朝政,只是充當各利益共同體的裁判者,是權力的最高表征。“臣子們”和“妃子們”的才華、能力甚至是個體意識,通通都是附庸于權力并“爭寵”的手段,它們都不具有主體性存在的價值。宮斗文本將鏡頭聚焦在權力中心的帝王家事,還因為在大眾文化的想象中,普通民眾并不屬于權力結構內部的成員,只依附或隱身在權力主體的背后。即使民眾出場、發聲,也是為權力者代言。《瑯琊榜》的“朝堂論禮”情節,譽王和梅長蘇請鴻儒周玄清出山,江湖之人在廟堂之上,“禮為何物?”這一問題周玄清并不在乎也不執著。“禮”不過是權力斗爭的一枚棋子,這枚棋子傳達完梅長蘇關于“禮”的見解后匆匆退場。鴻儒尚且如此,更遑論來來往往無名的“沉默者”。普通民眾如果想進入權力中心,常常被冠名“野心家”而以反面形象出現,結局往往不得善終。例如《延禧攻略》中的袁春望,他通過權力運作從辛者庫凈軍的小角色苦心經營成為太監總管。袁春望的權力憑借嫻妃獲得,但最終功虧一簣,一無所有。普通民眾只能充當王權秩序裂縫中的填充物。
置身于權力中心的每一個個體,都被權力撕扯、肆虐,一旦他們放棄爭斗,將面臨或者自殺一如葉瀾依(《后宮·甄嬛傳》)和富察皇后(《延禧攻略》);或者他殺一如方淳意(《后宮·甄嬛傳》),或者加入爭斗。《瑯琊榜》的舊派“領袖”祁王失勢被賜死源于他政治的幼稚性。雖然他正直不阿、據理力爭、為民請命、不惟皇是從,擁有一切大眾想象所賦予權力者的美好德性;但是,這些可能使祁王成為一個優秀帝王的品行卻不能讓他成為帝王。相反,繼承祁王品行的靖王被邊緣化,直到一步步放棄自己的天真。無疑,是權力使靖王上位;否則,他依然是一個權力的“局外人”。
宮斗文本以上的權力認知,對接受者的歷史體認而言有頗多誤區。一則,誤以為權力就是歷史。歷史是“多面的歷史”④,就如錢穆先生所言“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于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⑤中國歷史富含獨特的文明氣質和品格精神,等待后人挖掘使用,但這些因素在宮斗文本看來都是無關緊要的背景。當接受者信以為真的時候,產生“這部劇幾十個女人簡直是大鬧清宮啊,這年頭看花美男演電視不如看一群女人清宮撕逼大戰,作為一個女人值得我學習的地方還是很多的,比如罵人不帶臟字,殺人不見血,如何高雅的撕逼,學問真是太多了”⑥的閱讀體驗就不足為奇了。
讀者對宮斗文本或有意接受,或潛移默化,因為缺乏對歷史的理解、認同和反思,導致個體與社會對歷史的縱深感淺薄化,從而消解了歷史的意義張力。這恰恰與錢穆先生警醒我們的“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二、所謂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有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三、所謂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抱有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與古人。四、當信每一國家必待其國民具備以上諸條件者比較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⑦的啟蒙歷史觀背道而馳。
三、權力邏輯的道德向度
權力具有道德性嗎?大部分的學者應該都愿意對這一問題取肯定的答案。學者們普遍“從決策權、政治行動者和主觀動機、道德乃至于激情的角度”⑧來理解權力。
宮斗文本的“斗”,并非正義與非正義之間的“斗”。“斗”的目的是獲得權力,所以文本中的宮斗并無是非善惡的德性,只有“誰擁有權力”這一邏輯起點。《后宮·甄嬛傳》中為人津津樂道的情節莫過于“華妃之死”。網絡語境給“華妃之死”冠以“悲劇”。事實果真如此?華妃的“悲劇”表現上看是其性格囂張跋扈的缺陷、兄長被賜死的外戚失勢、雍正寵幸的轉向、無子嗣且不孕的“女性使命”的缺失導致的,更深層的原因是她與眾嬪妃斗爭失敗的結果。對于華妃的死,網友表現出極大的同情心,認為華妃的悲劇源自帝王無情而忽視華妃的愛,說“他心中最愛的是江山,女人不過是點綴而已”⑨。讀者往往為華妃的失寵自殺而悲哀,為其權力的喪失而同情。殊不知,人們紛紛忽略華妃曾為權力而做出的那些有違道德倫常的惡行。再如,梅長蘇的自我身份認同指向赤焰團體的“林殊”;但這僅限于他“私域”⑩的身份認同,“公域”?的合法身份只能是“江左梅郎梅長蘇”,“林殊”出現在“公域”則是一塊靈位。作為“林殊”的隱性與作為“梅長蘇”的顯性是二而一的共同體:林殊是“金陵帝都最耀眼最明亮的少年”,梅長蘇是“心中充滿毒汁的魔鬼”。一明一暗的身份證明梅長蘇想要復仇或者重建舊權力體系就必須犧牲道德,在暗處操控權柄。
在宮斗文本中,權力是一種價值取向,它是最直接和最有效地評判道德的天平,比如《瑯琊榜》中梅長蘇等人執著于必須在梁帝蕭選在位時重審“赤焰舊案”,梁帝就是評判的天平。《瑯琊榜》“王子復仇”和“重整朝綱”的背后潛藏著“王子奪回王位”的政治目的,這一目的有著華麗的道德襯里,即“清君側”與“換明君”。然而,文本確保新君不變昏君、新臣不變貪官的解決方案竟然是人物的道德高度,這顯然是一種理想。作為道德的個體能否確保當他成為政治個體時依然具有道德理性和政治理性?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疑問。作為最高權力擁有者的裁判又如何能確保自己的決策具有正義性呢?當天平失衡時,就需要“他者”或“神”來主持正義。《瑯琊榜》中,“祁王/靖王體系”看似無力回天之際,一個“來自內部、回歸內部的‘外人’/他者”?進入權力系統內部。有趣的是,梅長蘇重回權力中心依靠“得麒麟才子得天下”的權力想象。“外人/他者”是一個介入“太子/譽王體系”內部的正義的主持者,審判權力內部的道德舊賬,而介入所運用的手段卻并不具有道德性。《延禧攻略》中,魏瓔珞發現殺死姐姐的兇手是裕太妃,但是裕太妃位高權重,非時為宮女的魏瓔珞所能撼動。評判制度在權力面前處于失效狀態,主持正義的權力中心人物的道德身份掌控不了政治身份。魏瓔珞的復仇方式是擺小動作設計讓裕太妃被雷劈死。一方面,權力外圍的個體想要審判權力,要么依靠“見不得光”的權謀,這與梅長蘇復仇路徑完全一致;要么與魏瓔珞一般,借“神”的名義以絕對正義的客體介入評判。
還值得提出的是,電視劇《后宮·甄嬛傳》和《瑯琊榜》,乃至于后來的《延禧攻略》《如懿傳》等,都以服裝制作精美、禮儀動作考究等作為宣傳的噱頭和觀眾的好評點。華麗固然有利于提升電視劇的質量,華麗同時充當道德之惡的“遮羞布”。“掌握權力的人們根據必須的禮儀說出的話語;它是提供正義的話語”?。作為劇中掌握權力的人物和作為劇外的導演和制片人,都必須以最為華麗的“禮儀”說出“權力的話語”,以掩蓋道德的缺席。
如果按照福柯給我們的提示:“要研究權力的策略、網絡、機制和所有這些決策賴以實施并迫使其得到實施的手段”?。我們拋棄主角光環就事論事,并以現代性的視野觀照之,宮斗文本中的人物在權力的實施手段上都屬于有違道德倫理和觸犯法律。這是一個因網絡文本傳播而導致的新的文化癥候。宮斗文本以“權力”的形式再現中國古代社會,這種再現并非是原樣復制,它將權力觀點滲透到文本日常生活的道德倫理中。接受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容易將“我”代入主角身份,無意識錯認為主角的行為和意識無論如何都具有正義性,因為主角是主角。這種想法衍射到現實世界,作為“我”的接受者在應對現實世界的各種紛爭時,放大“自我”的光暈,以宮斗文本主角的行為方式而行動,這對社會人際關系和個體自我的影響具有“勸誡”和“教化”的意義:宮斗文本反復告訴“我”,善良的德行并不可取。例如豆瓣網網友對電視劇《后宮·甄嬛傳》的評價為“宮斗典范,我喜歡嬛嬛黑化之后的,過癮,刺激,而且有些地方猜不到,這點我喜歡。”?閱讀宮斗文本的情緒體驗,接受者們普遍產生“過癮”的“爽”的感覺。這確實有利于社會壓力的釋放;但是,一方面,我們享受宮斗文本給我們帶來的“爽”,這種“爽”是知識性和情感性的雙重認同,另一方面,我們可能意識不到宮斗文本給我們的知識體系、精神思維和道德倫理造成難以彌補的裂縫。
結 論
宮斗文本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它的盛行則有成為文化事件的可能。我們在“娛樂至死”的時代對文本的接受,可能連自已也沒有意識到宮斗的權力意識在悄然改變我們的個體情緒、個體認同,改變我們日常生活的社會結構、社會觀念。
接受者先是以預設的形式幻想當下生活環境隨處可見權力斗爭。根據福柯的觀點,權力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每個人都應該時刻以權力的視閥看待、處理生活現實。日常生活的本相是否真的充斥著權力的明爭暗斗,爾虞我詐?宮斗文本的“權力游戲”能否給現實世界帶來經驗的價值?這種權力的遷移對接受者的人性、人際關系;對歷史、政治有怎樣的影響?在這些問題尚還需深入思考之時,宮斗文本對現實世界的負面影響已經露出頭角。
閱讀的過程,是潛移默化地接受文本世界觀的過程。在電視劇《后宮·甄嬛傳》的豆瓣網評論里,有一條評論說道:“看完這劇我媽就把店里的一個小姑娘辭了,理由是:奴婢就是奴婢,怎么能和主子頂嘴呢?”?這樣的一條評論,稍加分析就知道其邏輯的謬誤,竟然得到網友大量的贊同。電視劇《延禧攻略》播放期間,接受者“痛恨”袁春望的手段卑劣,竟然到扮演者王茂蕾微博中痛罵之,導致演員不堪重負關閉微博評論?。這種看似追求道德正義的行為不免令人憂慮。這絕非好事。這顯然是反啟蒙的。
五四新文化知識分子的啟蒙,通過對社會、對歷史和對文化的思考尋找民族的出路,嘗試改變專權的封建政治權力結構。五四知識分子的所有努力,最后不過也是一場自我懷疑其有效性的啟蒙?。反觀權斗文本卻輕而易舉地憑借網絡媒體做到了將一種思想“塞到”另一個人的思想中。首先,傳統權力觀的慣性影響應該負一部分責任。其次,文本的生產者因為資本介入的原因不可能愿意加入更為深入的啟蒙思考,其大部分人的能力應該也無法企及。最后,市場的反饋機制及時有效地將市場的需求反饋給文本的生產者,他們隨意妥協、深入琢磨市場需要什么,并竭盡全力投其所好。這就意味著這種“娛樂啟蒙”注定與以魯迅為代表的“理性啟蒙”背道而馳。
注釋:
①(德)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劉北成、楊遠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第193頁。
②薛英杰:《欲望的缺席與在場:電視劇〈瑯琊榜〉的性別機制》,《婦女研究叢刊》,2016年第1期。
③趙靜蓉:《抵達生命的底色:老照片現象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6頁。
④(美)唐納德·R·凱利:《多面的歷史》,陳恒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
⑤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11頁。
⑥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4922787/comments?start=80&limit=20&sort=new_score&status=p。
⑦錢穆:《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1頁。
⑧李猛:《福柯與權力分析的新嘗試》,黃瑞祺編:《再見福柯》,松慧出版社,2005年,第117-164頁。
⑨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 556031110770881&wfr=spider&for=pc。
⑩(德)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王寅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頁。
?(德)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王寅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頁。
?戴錦華:《坐標與文化地形》,《華中師范大學學報》,2017年第3期。
?王治河:《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03頁
?(德)米歇爾·福柯:《福柯訪談錄:權力的眼睛》,嚴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8-29頁。
?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4922787/comments?start=20&limit=20&sort=new_score&status=P。
?https://movie.douban.com/subject/4922787/comments?sort=new_score&status=P。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0029080097716409&wfr=spider&for=pc。
?黎保榮:《啟蒙無效體驗與魯迅的思想轉型》,《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