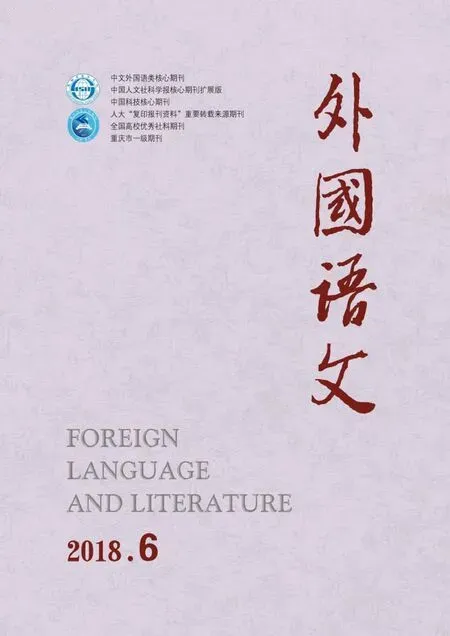論羅伯特·瓦爾澤童話劇《灰姑娘》和《白雪公主》的文本游戲
豐衛平
(四川外國語大學 德語系,重慶 400031)
瑞士德語作家羅伯特·瓦爾澤在生前一直不為德語文學界認可,對他的重新發現是從20世紀下半葉開始的。對瓦爾澤小說、散文、小品文等作品的研究,使人們驚訝地發現這位作家及其作品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本文選取瓦爾澤的微型劇——童話劇的《灰姑娘》和《白雪公主》——作為分析研究對象,探討瓦爾澤在其中的互文游戲。瓦爾澤顛覆式的改寫顯然不局限于文本游戲,根據格林童話創造的虛構形象自有其藝術本質,目的在于消解固定意義的生成,嘗試把握處在流變中的現實,在虛構與幻想中追求美和自由,從中亦可管窺瓦爾澤文學創作的主題。
1 文本游戲
伽達默爾在《美的現實性》中根據游戲的特征闡釋了解釋美學的原則,認為讀者/解釋者(伽達默爾稱為同戲者)對文本的閱讀、解釋與欣賞也是一種游戲,是一種與文本的對話,并且在作品中主動灌注了自己的生活積累(伽達默爾,1991:40)。要使這種游戲似的對話得以進行,文本必須為解釋者讓出一個游戲的自由空間,解釋者需填充這一空間。任何經典文本都為讀者/闡釋者留下了對話的空間(伽達默爾,1991:42-43)。因此,可將瓦爾澤對格林童話文本的改寫看作是一個閱讀、解釋與再創作過程。下文的文本分析將呈現這一過程,嘗試考察瓦爾澤對格林童話游戲般改寫及與之互動的意義所在。
1.1 《灰姑娘》
瓦爾澤的童話劇開始于灰姑娘的獨白。在格林童話中,灰姑娘在母親的墳前哭泣,而在瓦爾澤的舞臺劇中灰姑娘拒絕哭泣。在她的獨白中,她認為:“哭泣令人討厭,而責罵沒有。”(Walser,1998:7)她容忍姐姐們的責罵,還伺候她們。灰姑娘奉承、恭維姐姐們,但她表現得不卑不亢、自信并且有自己的想法。在姐姐們的眼中,灰姑娘是一個“妄想者”,同時還是個“促狹鬼”和“偽君子”。灰姑娘看起來逆來順受,事實上她很快樂、信心滿滿,她“懶散、狡猾、機靈”,甚至在暗地里嘲笑她的姐姐(9)。雖然在她兩個壞姐姐面前,她扮演著給她預設的仆人角色,可她是“笑著”扮演這個角色。如此而看,與兩個姐姐相比,灰姑娘已勝出一籌。灰姑娘向她的姐姐們述說她的忠心,并一再表示心甘情愿為她們效勞。對她來說,干活是“一份甜蜜快樂”和“幸福”(16)。灰姑娘特別喜歡說話,并且滔滔不絕,姐姐們因此說她“喋喋不休”。在此,說話——語言似乎對灰姑娘來說是一種救贖:“歡樂的話語”能使手里的活計倍增。
當王子與灰姑娘相遇時,灰姑娘自信又聰明地問道,王子是誰,到此的目的是什么(21)。王子直接、肯定地對灰姑娘說,她是他的新娘。灰姑娘似乎并不了解她在格林童話中的命運,于是,王子講述了童話中之前就預設的故事,并說:“……你只需保持安靜,走進那嚴酷的命運,一切都將做出解釋。”(21)可是灰姑娘并未聽從王子的安排。她仍然返回平日的生活中,繼續她的仆人工作,同時也樂此不疲地繼續她的語言游戲。緊接著,童話作為一個角色登場了,并給灰姑娘帶來一個皇室新娘的新更衣間,說她值得擁有童話,因為灰姑娘繼承了她美麗而又善良的母親身上“最可愛”的東西(33)。童話編排了接下來的情節發展,隨后消失,灰姑娘理應走進格林童話幸福的結局。可是,她一開始不愿順從童話為她設定的命運。猶豫之后,灰姑娘穿上了新娘的服裝,并認可了童話的邏輯。不過,她沒有理所當然地屈從命運,而是提出懷疑并追問個中原因。
灰姑娘了解宮廷生活:“簡直就是一只被捕的夜鶯,顫抖著坐在陷阱中,忘記了鳴叫。”(49)宮廷里的生活就如同被困在金絲籠里的鳥的日子,這意味著身份的缺失,灰姑娘“不再是灰姑娘”了(50)。寬闊、奢華的宮殿實則狹窄、逼仄,夢想的實現限制了灰姑娘發揮想象的自由。所以她更喜歡以前的身份,因為生活更自由,還總能充滿夢想。甚至在壞姐姐們面前,灰姑娘也感受到了愛:“我愛她們,她們對我冷酷無情又嚴厲。我愛上了不該受到的懲罰和惡言惡語,為的是愉快地微笑。這給與我無盡的滿足,填滿我漫長的白日,讓我去跳躍,去觀察,去思考,去夢想。這就是我為什么是一個夢想家的原因……”(53)
可是,王子毫不猶豫決定訂婚。他不再是格林童話中的救世主,而是童話的執行者,他試圖說服灰姑娘確信那不可避免的結局。灰姑娘堅持說:“一則更快樂的童話的本質就是有夢想,而在你身邊我無法夢想。”(53)盡管如此,灰姑娘最后屈服了,她順從王子并讓自己的感覺與童話的必然性一致。有意思的是,灰姑娘在屈從的同時,對王子說:“為您服務,先生。”(55)顯然,灰姑娘直到最后還試圖保持著女傭的角色。在此,灰姑娘并沒有獲得拯救,而是被童話的形式俘獲。
一反格林版《灰姑娘》中的人物形象,瓦爾澤筆下的灰姑娘讓人耳目一新,她自信、聰明,充滿求知欲,有自己的思想。她表述了做仆役、夢想和卑微是她的人生愿望,女傭的工作帶來快樂,是夢想、思想和懷抱愿望的前提條件。與此相反,身為公主就沒有前景(Hübner,1995:65)。顯然,瓦爾澤所創造的灰姑娘形象置格林童話的意義于懷疑之中。灰姑娘、王子和兩個姐姐遠離了經典文本的故事情節,也遠離了原有的人物設置。
1.2 《白雪公主》
一如他的灰姑娘,一開始出現在讀者或觀眾面前的白雪公主就已經是一個有思想的女孩了,完全不同于格林童話中的白雪公主——總是消極、被動、默默無語地聽天由命。第一幕,王后、白雪公主、陌生的王子和獵人談論過去的真相。白雪公主對繼母和她之間的沖突以及格林童話中的故事一清二楚,她諷刺并直截了當地譴責繼母。王后看似親切并且想竭力忘掉過去和所有的罪孽,而白雪公主一想到過去的經歷就悲傷哭泣、痛苦不安。獵人站在王后一邊,他對白雪公主說,童話是謊言。王子堅定地贊同白雪公主的說法:王后一如既往地“沒有母愛”(65)。如此這般,白雪公主不知真相何在。
第二幕,王子向白雪公主表白自己的愛慕之情,同時他又朝三暮四、口是心非。王子親眼看見王后和獵人之間的愛情場面,他心中燃起了愛的欲火,因此拒絕白雪公主的愛。顯而易見,他毫無專注之心。原本應該是拯救者的王子在這里表現得如此軟弱、不可靠。在此種情況下,無助的白雪公主再次嘗試和母親對話,并請求王子去尋找母親。
第三幕與第一幕截然相反,白雪公主已經準備好忘記過去,她甚至想到童話是杜撰的、非真實的。可是此時,王后固執地堅信格林童話,還奇怪地責備白雪公主對真相的排斥。她打算將自己對女兒所犯的罪行供認不諱。白雪公主表示自己寄希望于母親的信任,并表白自己對母親的愛。在接下來的第四場中,王子向王后表白自己對她的愛慕之心,王后指責王子的花心,并提醒他,他對白雪公主的愛情是一種責任。她要求獵人和白雪公主表演格林童話中森林里的那場戲,在這場戲中,獵人按照王后的指令本該讓白雪公主陷入困境。在此,正如格林童話一樣,獵人對白雪公主沒干任何壞事,王后卻干預其中,命令獵人跳出格林童話中的角色,把女孩殺死。在這嚴峻的情況下,王子這次沒有忘記他的救世主角色,他揭露了王后的陰謀,并匆忙前去幫助白雪公主。可最后,王后大笑著說這一切是一場游戲(86)。
在第五場中,白雪公主又經歷了一次“無聲的改變”(87)。她不能忘記童話故事,故事里母親的仇恨讓她生不如死。一想到這些,她就痛不欲生,所以她寧愿回到小矮人那里去。對白雪公主而言,小矮人所在地是一個理想國,那里白茫茫一片真“干凈”, 那里“喜悅”和“快樂”常在,那里就像白雪一樣純靜、安寧,那里愛讓仇恨消失(88-89)。更重要的是,那是一個“五彩繽紛的夢想王國”(88),而不是像在如現在所處的世界里“鮮活的內心必定枯萎、死去”(88)。繼母想方設法讓女兒冷靜下來,她把獵人叫過來,并要求他將一切向白雪公主說清楚。獵人一字一句地解釋,童話故事就是人們編造的謊言。白雪公主內心對此充滿了疑惑:“是的,而又不是。”(92)她請求獵人說點“新鮮的”,獵人回答說:“盡管開端尚未結束,但結尾以親吻告終。”(98)很有可能,真相和謊言循環往復是一個圓圈,一如開端和結尾。劇終,白雪公主已疲于尋找真相,她無論如何都想將關于罪惡和過去的一切拋擲腦后。此時,王后重新提起罪責問題,白雪公主毫不客氣打斷說:“請你沉默吧,噢,閉嘴。童話僅是如此說說而已……”(103)—— 童話劇就此結束。
瓦爾澤《白雪公主》中的人物反反復復地探討童話中真實的過去以尋找真相。真相和謊言、有罪和無罪之間的沖突推動著童話劇的情節發展。白雪公主不能擺脫格林童話中的過往,最后屈服,并以恭順的姿態不僅嘗試與繼母和解,而且也接受過去及現在。當王后再次說出預示危險的話語時,白雪公主與獵人一樣選擇了沉默,因為似乎只能在沉默無語中穩定這表面上的和諧。白雪公主請求繼母沉默,關于真相的爭論也以此休止,矛盾最終似乎得以解決。在對話中經常出現的過去以及關于過去各不相同的表達方式并未從言語上有所定論,過去的一切是對是錯不得而知。不同于格林童話故事的結局——王子和公主結婚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瓦爾澤的童話劇是一個開放式的結尾。劇終時,人物都轉向沉默。如獵人所言,開端和結尾、真理和謊言沿襲循環往復的軌跡,所以關于她所處時刻的討論也不會產生有意義的結果,那么就沉默吧。瑞士音樂家海因茨·霍林格(Hollinger, 2009)將瓦爾澤的童話劇《白雪公主》改寫為一部歌劇。在歌劇的結尾,觀眾看到,舞臺上幕布緩緩落下,那是一張白紙,被燈光從后面照射著,上面空空如也。如同瓦爾澤的童話劇,霍林格的歌劇也是一個開放的結局,音樂家恰如其分地闡釋了瓦爾澤的童話。
瓦爾澤作品的互文性不容置疑。從形式上而言,人們可以將瓦爾澤的改寫稱作是對傳統文學形式的解構或戲仿(Hübner ,1995:29)。瓦爾澤一直偏愛“渺小”,他喜歡在作品中塑造渺小的角色,也喜歡短小的文學形式,他一生的創作除了幾部小說外,很多都是短小的散文、小品文等。“渺小”是“瓦爾澤的基本美學品格”(范捷平,2011:71)。如此而看,格林童話也契合了瓦爾澤游戲的樂趣。在文本游戲中瓦爾澤意欲解構語言和文學傳統的固定模式,表述自己的懷疑。正是因為童話這種體裁的純樸性、直線式的故事情節以及封閉性,童話才成了瓦爾澤具有高度藝術技巧的、反思自我和現實的最佳文學形式。對童話這種短小文學體裁的改寫使他獲得更大的語言空間,從而滿足他對世界可述性的需求。
在瓦爾澤看來,人們面對世界應該采取一個靈活的視角,才能描述世界并發現其中的秘密,因為現實是多變的,而用于描述現實的語言具有程式化的遮蔽性特征。瓦爾澤對童話的理解和改寫目的在于否認不加思考的接受所有觀念的有效性,并讓人們意識到意義指派、產生的普遍過程。瓦爾澤通過提取著名的童話素材及童話元素,進行模仿,并且將其置入一個陌生化的關聯之中。在這一模仿游戲里,瓦爾澤在想象與虛構中獲取了新的象征符號,“先前文本的象征符號就能夠成為后來文本的調節適應的組成部分”(伊瑟爾,2011:301),同時也揭示了普遍性的話語意義生成機制。與格林童話相比,瓦爾澤文本中白雪公主和王后之間的爭執(尋找真相),灰姑娘對王子問題肯定或否定的猶豫回答,他另一部童話劇《睡美人》中睡美人被王子拯救后前后截然不同的行為,這種對立的姿態表現出人們無法對現實作出一個隨時有效的、有約束力的解釋(Hübner,1999:172)。在格林童話里,人物的角色是被分配的,在瓦爾澤的童話劇里,他放棄了這種被分配的角色。劇中,角色經常被調換位置,這明確地表現了現實的不穩定性。瓦爾澤筆下的人物不再是靜止不變的角色,也不再是簡單的童話人物,而是不斷反思自我、具有鮮明個性的個體。他們置疑被強加的、預設好的角色和故事情節,他們的身份特征是變動的,這一切都阻止一個固定的、連貫性的意義生成。
瓦爾澤顛覆式的改寫是對原文本的解釋并與之互動,他將自己的生活經歷和對現實的認識以及對語言、對文學創作的反思融入到原文本之中,使解釋變成再認識、再創造。瓦爾澤的灰姑娘雖認可童話的安排,卻表示質疑,白雪公主愿意結束真理與謊言無休止的爭論,但陷入沉默,睡美人最后因王子的一吻而定終身,但失去了這一形象浪漫的光環。瓦爾澤對格林童話文本的解釋并未生成一個確定的意義,格林童話觸發他繼續提問,在游戲似的解釋互動中他不斷超越原文本的歷史視界,而最后生成的文本又默許“無限多未言說的東西”(杜任之,1983:454)。就此而言,瓦爾澤的文本也讓出一個讀者/觀眾必須去填滿的游戲空間。
2 游戲生存
按照弗洛伊德的分析,作家的幻想等同于兒童的游戲,作品就如同白日夢,是游戲的繼續。作品非作家自己的創作而是對現成素材的再創造,作家的獨立性則在于對素材的選取。而神話、傳說和童話等民間故事隱藏著所有民族的心理結構,其中可尋找人們寄托愿望的幻想和人類祖先長期夢想的痕跡(弗洛伊德,2002:320)。這或許可以解釋瓦爾澤為何選擇童話作為文本游戲的對象。對于瓦爾澤而言,散步、幻想和寫作是一體的,他生存于其中。在自己的想象活動中,在幻想的游戲里,他思考人生和現實,完成他對世界的認識。倘若將成人的幻想看作是兒童的游戲,那么作家憑借想象活動創造了一個屬于他自己的世界,用一種新的方法重新安排他那個世界的事物,來使自己得到滿足。作家幻想的動力是未得到滿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是一個愿望的履行,它與使人不能感到滿足的現實有關聯(弗洛伊德,2002:317)。
《灰姑娘》的主題契合瓦爾澤有關幸福的辯證法:一旦擁有,再無夢想 (Schilling,2007:18)。倘若考察瓦爾澤的生平,會發現這與他的生活有相似之處。瓦爾澤不能適應社會環境,不擅長與人相處,作為邊緣小人物他為了生計也做過幫工、仆役等。他三本著名的具有自傳色彩的小說《唐納兄妹》《幫手》和《雅考伯·馮·貢滕》就是以主人翁與市民社會的不適應為主題,“小人物”也是他筆下常見的人物形象。在他看來,謙卑順從和做仆役是一個特殊的立足點,它有可能開啟另一番前景。為了自由地反思這個世界,他需要和社會保持距離,以此保留自己的自主性,他筆下的灰姑娘在兩個姐姐面前不就是謙卑得異常固執?20世紀初,瓦爾澤生活在德國的文化、思想、政治中心柏林。在柏林的知識分子圈子里,人們津津樂道尼采的權利哲學。尼采的“權力意志”或者“超人”論都是中心概念。在人們夸夸其談追求宏大、頌揚慶典式的權力和強權意志的氛圍里,不融于主流的瓦爾澤萌生了卑微的想法。于是,做仆役是瓦爾澤作品中常見的慣用語,瓦爾澤提出了與尼采截然相反的“軟弱意志”,在瓦爾澤看來,“做仆役實則是秘密的統領,是一種由下而上翻轉的貴族統治”(Schilling,2007:46)。因此,這部舞臺劇被視為解讀瓦爾澤在其作品中堅定捍衛自己的理念——做仆役是幸福的——的關鍵性文本。
《白雪公主》以沉默告終。瓦爾澤盡管否定由語言確定的最終意義,但他終其一生都在找尋真理。在找尋真理的途中,這位漫游者一無所獲。他于是遠離人群、遠離喧囂的世界離群索居。由此出發,人們也許能夠理解,為什么瓦爾澤從1929年到1956年去世之前有23年都待在療養院和精神病院,盡管并無他患有精神病的醫學診斷。在那里,他有空間和時間思緒紛紛。有很長一段時間,他停止寫作,沉默不語。可是作為漫游者,他總是在散步,在散步中幻想,直到在皚皚白雪中死去。
瓦爾澤《喜劇》的序言提到,他曾經遵從一位文學家的建議,放棄了依據森帕赫戰役創作劇本的意圖,而“寧愿創作一些發自內心的東西”(M?chler,1986:244)。灰姑娘做一個夢想家的心愿、白雪公主重回小矮人那里的渴望以及睡美人想沉睡不醒的愿望,或者瓦爾澤經常表露的對死亡的向往,這都是他退避、回歸內心的合乎邏輯的結果,以便在他自己所描述的矛盾的世界里逃離一種徹底的自我異化。瓦爾澤童話劇的主題是“恐懼、生存恐懼、懷疑”(Unseld,1998:110),作品里表達的對生存的不安具有人類的普遍性,是“茫茫人流的漩渦中、大城市文明技術的、技術文明的大城市中,個體和孤獨者的大主題”(Unseld,1998: 114)。瓦爾澤這個獨來獨往的我行我素者是如此看待自己的:“或許是不安、不確定以及對自己獨特命運的預感促使我在俗務中拿起筆嘗試表達我自己,不知是否成功。”(Unseld,1998:111)對于瓦爾澤而言,寫作就是證明自我的方式,將自己內心的愿望付諸筆端。他將自己與荷爾德林相比,當他在精神病院生活了10年之后,關于荷爾德林,他寫道:“……荷爾德林在他生命最后30年里根本沒有像文學教授們描寫的那么不幸。能夠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里自由夢想,而不必去滿足沒完沒了的要求,這不是一種痛苦,只不過人們把它當作一種痛苦。”(Schilling,2007:144)如同荷爾德林一樣,瓦爾澤遠遠地逃離這個世界。他需要和這個社會保持距離,然而這僅是“從這個位置上挪開”,以便他能“以一種令人難以想象的謙卑——并非指手畫腳——闡明人之生存那深不可測、苦難至極的裂痕”(Hollinger,2009)。針對瓦爾澤作品中那些人物形象,本雅明有如下論述:
(他們)瘋了,因此而離開了一個令人分裂、如此非人性的而又不可逆轉的淺薄。倘若人們想要用一句話來描述他們身上令人喜悅而又令人不可名狀的特質,那么可以這樣說:他們所有人都被治愈了。可是我們從未了解這個治愈的過程,除非我們敢于嘗試去解讀《白雪公主》這部近代文學作品中最意味深長的作品之一,僅僅是《白雪公主》就足以解釋,為什么這位看似所有詩人中最貪玩的詩人是冷峻的弗蘭茨·卡夫卡最喜歡的一位作家了。(Benjamin,1977)
在本雅明看來,瓦爾澤的人物瘋了,不再在這個世界言說,而“治愈”在沉默中也許是可能的。在童話劇里,瓦爾澤顛覆了傳統的基本價值觀念,但他并非代之以新的價值或構建新的價值體系。對瓦爾澤而言,互文的游戲既是否定原文本所要表現的意義,也是要否認固定意義的生成。20世紀初的瓦爾澤經歷了自身戲劇夢的破滅、文學夢的不可實現——作品不被認可,他的文學價值在五六十年代才得到承認,為了生計他當過仆人、學徒等等。此時的歐洲也經歷各方面的飛速發展和災難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瓦爾澤對自我、人生與世界產生了新的認識,尤其是個人與世界的關系。世界的多元化、多變性本身不能用固定的概念和體系來把握,個人由于歷史和社會限制也不可能完全展現自我。因此,人沒有能力把握整體的聯系,人類每一次嘗試認知現實的努力或許是突發奇想的游戲。由于現實的不可把握、意義的不確定性,人的認知也是瞬息的、點滴的,不可能是永恒的,也不可能具有普遍性。在瓦爾澤看來,人在如此困境中有了“基本的虛構需求”(Hübner,1999:184),通過虛構至少能形成表面的定位,因為虛構是“建立世界圖式的創始性構想”(伊瑟爾,2011:5)。
在虛構中,瓦爾澤擺脫文化符號——童話及童話文本中的價值觀念——的束縛,也表示了對世俗成功觀念的質疑,所以灰姑娘對披上嫁衣成為王子新娘表示疑惑,甘愿當永遠的仆人。這其實是瓦爾澤一再在作品中表述的觀點:不成功具有更高的價值(Borchmeyer,1987: 131)。猶如他作品中的角色大多是失敗的英雄或者是現代都市的無用人,瓦爾澤對所謂的成功持有強烈的懷疑和批判的態度:否定主體觀,即在失去所有世俗的成就感壓迫之后方才能夠獲得真正的自由(范捷平,2011:193)。瓦爾澤同情失敗者,反感所謂的英雄、勝利、宏大,反對主流教育模式和教育理念的驕橫以及高高在上的“文化”,這些主流的價值觀念無視社會不適應者的思想、語言和內心世界。瓦爾澤自己是主流社會的邊緣人物,他也是所有那些被理性占主導地位的文明社會所遺棄者的代言人。在他看來,主流社會的成功人士和統治者沒有情感:在《睡美人》中,王子作為勝利者卻是“陌生人”,神情凝固、呆板、冷漠,舉止僵硬。
如此而看,瓦爾澤通過文學創作在虛構和幻想中讓自己的內心得到滿足,在互文的游戲中擠壓他在現實中隱匿的情感和思緒。這不僅僅是一種文本游戲,更是他生存的游戲。
3 美和自由的追求
瓦爾澤這位孤獨的漫游者“總是在散步的時候不由自主地幻想、進行文學創作”(Unseld,1999:20)。散步、幻想和文學創作應當是瓦爾澤畢生存在的基本狀態。
瓦爾澤對格林童話極富創造力的改編,與格林童話的互動對話是思考他自己、思考他人及世界的游戲空間。他窮其一生都在尋找真理,盡管他厭惡每一個最終的真理,厭惡語言的模式化;他尋找著安定,盡管作為一個漫游者他總是不安寧;他尋找著雪地里純凈的世界,在散步時殞命于皚皚白雪中,他終于在此找到了安定和最終的沉睡。于他——一如他在他第一部小說中描寫詩人塞巴斯蒂安之死——這是 “美妙的安寧,在樅樹枝下、在雪地里,如此躺著,一動不動”(Walser,1986:131)。瓦爾澤期望的是散步的時候在雪里死去,這是“幸福的死亡,倘若人能夠直到最后一刻堅守住自己自身生命的結果”。這位漫游者走得離這個社會越來越遠,直至和世界徹底決裂:“就這樣我活著我自己的人生,在市民社會的邊緣,這有什么不好嗎?我的世界不也有權利存在,盡管它看起來是一個更加可憐的、弱小的世界。”(Schilling,2007:144)
用世俗的觀點看瓦爾澤其人,他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沒有令人稱羨的職業和家庭,而后在精神病院終結余生,他的人生是失敗的。可是,如上分析,他一再在文本中表述的觀點、他所享受的心情寧靜和最終獲得的“美妙安寧”以及多年以后他的文學創作得到的認可,我們可以認為,他與這個世界的決裂不是一種逃避,而是“藝術家用藝術去克服困難”(席勒,2005:284-85)。如果說瓦爾澤在精神病院處于一種寧靜的狀態,在他樂意的散步中可以得到最后的安寧,這是一種幸福、自由的狀態。而在這之前,他一直在通過文學創作從現實的藩籬中解脫、追求一種自由,現實的不完美以及他在現實中的挫敗感導致他產生一種“內在驅動力”,即游戲的內在驅動力——“自由的至高無上的形式”(席勒,2005:8)。他由此構建了他的文學世界,即便是他在精神病院后來停止了文學創作,他也在鐘愛的散步中展開想象的翅膀,仍然延續這種美學自由。由此,他的自我得以呈現。瓦爾澤在童話劇中表述了自己對成功、真理的質疑 ,也揭示了語言程式的遮蔽性,他在閱讀格林童話文本獲得的愉悅感或者審美的快感實則是自己判斷力潛能的激活,因而促使他產生了文本游戲的需要(伊瑟爾,2011:323)。
瓦爾澤總是寫一些“虛無、卑微、少數。但是,當他散步的時候,他先是如此的渺小,然后他敞開他的內心、越來越開懷地敞開他的內心,最后他幾乎是一個宇宙”。瓦爾澤以此種方式與世界相遇、與自己相遇,追求美和自由,因為美“沒有任何目的關系,沒有任何預期的利益,美自身充滿了一種自確定的特性而且洋溢著對自明性的喜悅與歡樂”(伽達默爾1991:21)。他呈現給讀者的作品在表達他的幻想時以純粹形式、美的享受或樂趣,使讀者也感到愉悅(弗洛伊德,2002: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