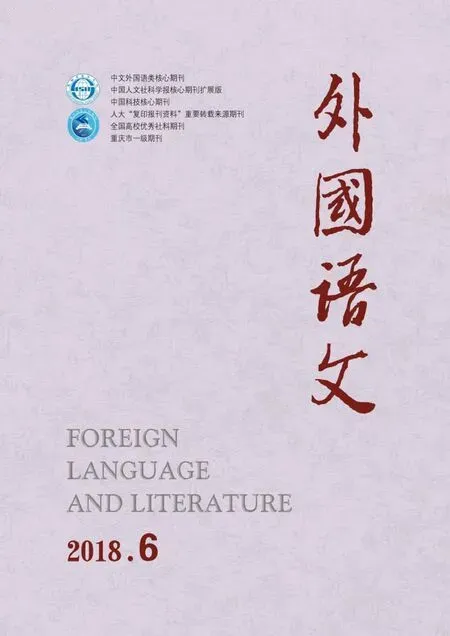英語對高水平漢-英雙語者漢語同譯近義詞加工的影響:來自ERPs的證據(jù)
潘雪瑤 姜 孟
(四川外國語大學(xué) 研究生院/語言腦科學(xué)研究中心,重慶 400031)
1 文獻回顧
雙語或多語者所掌握的幾種語言之間,由于共性和差異,所發(fā)生的在使用中的彼此影響,被稱作“語言遷移”。母語對二語的影響(即所謂“順向遷移”,forward transfer) 一直是研究的熱點,為學(xué)界所熟知。相比之下,二語(包括三語、四語等)如何對母語發(fā)生影響(即所謂“逆向遷移”, backward transfer),一直關(guān)注較少,研究有限。從歷史來看,Weinreich (1953)最早論及了二語對母語的影響問題,他將“語言干擾(language interference)”定義為“雙語者話語中背離第二語言和母語規(guī)范的事例”,暗含了二語對母語使用的影響。Odlin(1989)在定義“借用遷移(borrowing transfer)”時也論及了這一問題。他指出,二語在詞匯層面會對母語產(chǎn)生影響,導(dǎo)致母語詞匯的磨蝕現(xiàn)象。近年來,國內(nèi)外學(xué)者開始著手從語音、詞匯、句法、語用以及概念認知等多個層面探討二語對母語的影響即“逆向遷移” (Ulbrich et al., 2014;Khachatryan et al., 2016; Kasparian et al., 2017; Aveledo & et al., 2016; Baus et al., 2013; 董燕萍等, 2010; 張愛萍, 2014)。單就詞匯層面的逆向遷移研究而言,主要從二語對母語詞匯“使用”與“加工”的影響兩方面展開,著眼于獲取詞匯語義逆向遷移存在的證據(jù)。
第一類研究大多對雙語者的母語使用情況與單語者的語言使用情況進行對比,將兩者在詞匯使用上的區(qū)別視為二語詞匯語義逆向遷移的結(jié)果。例如,Collan (2011)等和Sadat(2012)等人研究發(fā)現(xiàn),與單語者相比,雙語者在語言產(chǎn)出時的速度更慢,單詞產(chǎn)出量更少。Laufer (2003)通過詞語搭配可接受度判斷任務(wù),考察了希伯來語對俄-希雙語者的影響,結(jié)果發(fā)現(xiàn),與俄語單語者相比,生活在以色列的蘇聯(lián)移民對希伯來語式“不地道”俄語搭配有著更高的可接受度。此外,Malt等(2015)、Pavlenko等(2011)分別考察了漢英雙語者、俄英雙語者用母語進行物體命名的表現(xiàn),結(jié)果顯示,與漢語單語者或俄語單語者相比,雙語者更傾向于用二語(英語)的表達方式進行命名。這些結(jié)果表明了二語對母語造成的語義或概念方面的影響。
第二類研究致力于揭示母語詞加工中的同源詞效應(yīng)、同形詞效應(yīng)以及同譯詞效應(yīng),以此證明詞匯逆向遷移的存在。Nakayama等(2013)采用掩蔽啟動范式和詞匯判斷任務(wù),考察英語詞對低頻日語同源目標詞(片假名方式呈現(xiàn))及非同源目標詞(漢字方式呈現(xiàn))的啟動效應(yīng),結(jié)果發(fā)現(xiàn),高、低水平日-英雙語者加工同源目標詞的反應(yīng)時均顯著快于非同源目標詞,證明了日英同源詞加工中的逆向遷移。Nakayama等(2016) 進一步采用掩蔽啟動范式和詞匯判斷任務(wù),對比高水平日英雙語者在英語翻譯對等詞啟動條件下,對相關(guān)日語目標詞或無關(guān)日語目標詞進行詞匯判斷的反應(yīng)時,結(jié)果發(fā)現(xiàn)了顯著的英語翻譯對等詞啟動效應(yīng),證明日英非同源翻譯對等詞加工中也存在逆向遷移現(xiàn)象。Wang (2013)在類似的實驗中,也發(fā)現(xiàn)了平衡漢-英雙語者漢語加工中的英語翻譯對等詞啟動效應(yīng)。Khachatryan等(2016)首先采用荷語詞匯啟動范式,通過語義關(guān)聯(lián)判斷任務(wù),發(fā)現(xiàn)了荷-英雙語者同形詞加工中的逆向遷移現(xiàn)象。在此基礎(chǔ)上,他們進一步對二語(英語)意識進行顯性操控,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同形啟動詞對同形無關(guān)詞(以荷語方式呈現(xiàn)的同形詞的英語語義相關(guān)詞)的加工產(chǎn)生了顯著的促進效應(yīng),與控制條件相比,被試對該類詞進行語義關(guān)聯(lián)判斷時誘發(fā)的N400波幅顯著降低。
除同源詞效應(yīng)與同形詞效應(yīng)外,二語同譯效應(yīng)也被視為詞匯語義逆向遷移的重要證據(jù)。在語言遷移研究文獻中,“母語同譯效應(yīng)”一直被視為詞匯順向遷移的證據(jù)。例如,Jiang (2002, 2004)讓被試對語義相關(guān)的英語同譯詞對和英語異譯詞對進行語義關(guān)聯(lián)度判斷,結(jié)果發(fā)現(xiàn),與英語單語者相比,漢-英或韓-英雙語者在同譯詞對上的語義關(guān)聯(lián)度評分顯著高于異譯詞對,且反應(yīng)時更快;Tagashira (2017) 采用相同的實驗范式,在日-英雙語者身上發(fā)現(xiàn)了同樣的同譯詞效應(yīng);張萍(2016)通過在線語義相關(guān)性判斷任務(wù)和語境化辯詞任務(wù)也發(fā)現(xiàn),與英語異譯詞相比,被試對英語同譯詞對進行語義關(guān)聯(lián)判斷的反應(yīng)時更快,且詞類、具體性和語境均未對實驗結(jié)果產(chǎn)生影響;張萍、盧雅睿(2016)采用類似的語義相關(guān)性判斷任務(wù),發(fā)現(xiàn)了中-英-日三語者英語及日語加工中的漢語同譯效應(yīng)。采用相似的研究范式,一些學(xué)者致力于考察母語詞匯加工中的“二語同譯效應(yīng)”,以證實詞匯逆向遷移的存在。Degani等(2011) 首次發(fā)現(xiàn)了母語詞匯加工中的二語同譯詞效應(yīng)。他們的實驗證實,與英語單語者相比,無論是希伯來語-英語雙語者還是英-希雙語者都認為,本應(yīng)處于同一語義關(guān)聯(lián)水平的英語“同譯詞對”比英語“異譯詞對”有著更緊密的語義關(guān)聯(lián)。這表明二語也會對母語詞匯的加工產(chǎn)生影響。在另一項研究中,Degani (2011) 用英語同譯詞或無關(guān)詞替換句子中的目標詞,以比較被試對不同詞類替換引起的違例的敏感性,結(jié)果發(fā)現(xiàn)與英語單語者相比,西-英雙語者與英-西雙語者在兩類替換違例情況下的眼動指標都有所不同,再次為詞匯語義的逆向遷移提供了有力證據(jù)。
以上研究主要以平衡雙語者或在二語環(huán)境中生活多年的熟練雙語者為研究對象,另有一些針對非平衡二語學(xué)習(xí)者的研究也發(fā)現(xiàn),母語環(huán)境中高水平非平衡晚期二語學(xué)習(xí)者在母語詞匯加工時也會受到二語詞匯語義的影響(Khachatryan et al., 2016; Kasparian et al., 2017)。
除了實證研究外,一些理論模型也預(yù)測了詞匯語義逆向遷移的存在。例如,Cook (1991) 的“復(fù)合能力”(multi-competence)模型認為,一語系統(tǒng)和二語系統(tǒng)并非完全分離,而是在雙語者大腦中形成一個綜合的、動態(tài)的語言體系,由于兩種語言系統(tǒng)的聯(lián)系性,二語便會對一語產(chǎn)生影響。雙語詞匯通達的“非選擇性加工觀”也認為,一種語言的詞匯語義系統(tǒng)的激活會擴散到兩種語言的詞匯系統(tǒng)。因此,無論是在單語或雙語環(huán)境中,雙語者在進行母語詞匯加工時不可避免地會激活其二語系統(tǒng)中的對譯詞及相關(guān)詞,導(dǎo)致一語和二語詞匯產(chǎn)生競爭, 從而相互影響(Soares et al., 1984; Moon et al., 2011)。
綜上所述,詞匯語義逆向遷移得到了一些理論模型的支持,更獲得了不少實證研究的支持。然而,這些實證研究總體上還比較有限,研究方法也主要限于詞匯測驗與行為加工方法,從二語同譯詞效應(yīng)角度開展的研究更是鮮見。鑒于此,本研究擬運用ERPs實驗技術(shù),采用句子尾詞違反范式,考察英語對中國高水平漢-英雙語者漢語同譯近義詞加工的影響。
2 實驗研究
2.1 實驗一
2.1.1 研究問題
中國高水平漢-英雙語者在加工漢語同譯近義詞對時,是否會受到二語英語的影響?
2.1.2 被試信息
隨機選取四川外國語大學(xué)英語專業(yè)二、三年級18(3男15女)名碩士研究生,年齡為22-28歲,母語均為漢語,均通過英語專業(yè)8級考試,身心健康,無神經(jīng)損傷史,右利手,視力正常或矯正后視力正常。實驗前所有被試均簽署知情同意書,實驗結(jié)束后給予一定的報酬。
2.1.3 實驗材料與設(shè)計
實驗材料的選擇與Jiang(2002) 類似。首先從《漢語近義詞詞典·漢英對照版》(第一版)中選出58對可譯為同一英語詞的近義詞對,隨后將以上漢語詞以亂序的形式呈現(xiàn)給三名不參加正式實驗的漢-英雙語者,要求他們寫出漢語詞的英語翻譯對等詞。若至少兩名被試將同一對漢語近義詞譯為同一英語詞,則將其歸入漢語同譯近義詞對。按此流程,最終篩選出30對漢語同譯近義詞對。隨后將以上漢語詞輸入北京大學(xué)中國語言學(xué)研究中心(CCL)現(xiàn)代漢語語料庫,查詢每個詞獨有的搭配情況,并據(jù)此將各詞置于句子中,形成尾詞范式的句子。以“道理”和“原因”兩詞為例,兩個詞均可譯為reason,經(jīng)語料庫查詢可知,常見“講道理”,未見“講原因”;同樣,常見“調(diào)查原因”,未見“調(diào)查道理”。另外,選取30個與漢語同譯近義詞對無關(guān)的漢語詞作為填充詞,參照正式實驗材料的方式編寫成句子,最后得到60組材料。每組材料均包含尾詞與句子主干搭配一致句、搭配不一致句以及填充句各一句,包含同一對漢語同譯近義詞的兩組句子實現(xiàn)交叉平衡。實驗材料樣例如下:
(1)a. 劉敏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竟然這樣不講道理。 (搭配一致)
(1)b. 劉敏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竟然這樣不講原因。 (搭配不一致)
(1)c. 劉敏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竟然這樣不講錢包。 (填充)
(2)a. 葡萄牙方面已任命了一個委員會調(diào)查這次事故的原因。 (搭配一致)
(2)b. 葡萄牙方面已任命了一個委員會調(diào)查這次事故的道理。 (搭配不一致)
(2)c. 葡萄牙方面已任命了一個委員會調(diào)查這次事故的錢包。 (填充)
實驗為3水平(句子類型:搭配一致、搭配不一致、填充)被試內(nèi)設(shè)計,因變量為被試理解關(guān)鍵詞(尾詞)時的腦電。 實驗預(yù)期,漢-英雙語者被試在“搭配一致”與“搭配不一致”條件下加工作為尾詞的“漢語同譯詞對”時,會激活共享的英語翻譯對等詞(即其共享的英語詞匯語義知識),導(dǎo)致被試易對兩個漢語同譯近義詞產(chǎn)生一定程度的混淆,造成兩種條件下相似的腦電表現(xiàn)。
2.1.4 實驗程序

圖1 實驗一基本流程圖
實驗在四川外國語大學(xué)“外語學(xué)習(xí)認知神經(jīng)重點實驗室”完成。采用E-Prime2.0編寫程序。首先在屏幕中央(背景為黑色,刺激為黃色)呈現(xiàn)持續(xù)時間為600ms的注視點“”,隨后呈現(xiàn)句子的主干部分。當被試認為已完全理解該部分句子的意思后,即按任意鍵繼續(xù)。在500ms的空屏后,呈現(xiàn)“尾詞”,持續(xù)時間為500ms。實驗記錄被試對尾詞進行理解的腦電信號。最后再呈現(xiàn)600ms的空屏,隨即進入下一試次。每30個試次設(shè)置一次休息。所有實驗刺激均以完全隨機方式呈現(xiàn)。具體實驗流程如圖1所示。
2.1.5 ERPs記錄與分析
實驗使用Neuroscan EEG/ERPs工作站,通過64導(dǎo)電極帽記錄EEG信號。參考點擊位于雙側(cè)乳凸,位于左眼上下眼眶的電極記錄垂直眼電(VEOG), 位于雙眼1-1.5cm處的電極記錄水平眼電(HEOG)。濾波帶通為0.05-100Hz,采樣頻率為500Hz, 頭皮電阻小于 5kΩ。完成連續(xù)記錄EEG后離線處理數(shù)據(jù),根據(jù)垂直眼電矯正眨眼偽跡,并進行30-60Hz(24dB)的無相移帶阻濾波。腦電分析時程為-150ms-1000ms,波幅大于±100μV 被視為偽跡自動剔除,分別疊加并平均刺激誘發(fā)的EEG信號,得到鎖時的ERPs總平均波形。
實驗結(jié)果通過SPSS16.0軟件進行統(tǒng)計學(xué)分析。實驗對被試理解尾詞時的N400(280-510ms)波幅(Amplitude)進行三因素重復(fù)測量方差分析,對不滿足球形檢驗的統(tǒng)計效應(yīng)的采用Greenhouse-Geisser法進行校正p值。統(tǒng)計分析中的三個因素分別為:句子類型(搭配一致、搭配不一致、填充)、 腦區(qū)(前部:F3/FZ/F4;中部:C3/CZ/C4;后部:P3/PZ/P4)、半球(左側(cè):F3/C3/P3;中線:FZ/CZ/PZ;右側(cè):F4/C4/P4)。對句子類型主效應(yīng)進行事后多重比較。
2.1.6 結(jié)果與討論
最終對15名有效被試的腦電數(shù)據(jù)進行統(tǒng)計分析(有3名被試的腦電數(shù)據(jù)由于偽跡過多而沒有被納入結(jié)果分析)。根據(jù)被試對目標詞進行理解時的ERPs波形圖(見圖2)可知,在目標詞出現(xiàn)400ms左右出現(xiàn)了一個峰值達到最大值的負波,根據(jù)其出現(xiàn)的時間窗280-510ms,該負波被認定為N400。

圖2 實驗一三種句子條件下誘發(fā)的ERPs平均波形圖
N400通常被認為是反映語義加工的標志,在語義違反情況下容易受到誘發(fā)(Kutas et al., 1980;孟迎芳 等, 2016)。此外,有學(xué)者指出,N400的波幅對刺激的變化最為敏感(Kutas et al., 2011)。本研究對被試在三類句子條件下的N400(280-510ms)波幅進行了重復(fù)測量方差分析,結(jié)果如表1所示。句子類型主效應(yīng)顯著,F(xiàn)(2, 28)=32.144,p=.000。句子類型與半球的交互效應(yīng)顯著,F(xiàn)(4, 56)= 4.994,p=.004; 句子類型和腦區(qū)的交互效應(yīng)顯著F(4, 56)=12.238,p=.000,但句子類型、腦區(qū)和半球的交互效應(yīng)不顯著(p=.141)。

表1 實驗一N400波幅(uV)的三因素重復(fù)測量方差分析結(jié)果
Note:*p<.05, **p<.01, ***p<.001
對句子類型主效應(yīng)進行事后多重比較分析(見表2),結(jié)果顯示,三類句子條件下的N400波幅均存在顯著差異。具體而言,“搭配一致句”與“搭配不一致句”的N400波幅相比,差異顯著(p=.000);“搭配一致句”與“填充句”的N400波幅也具有顯著差異(p=.000);“搭配不一致句” 與“填充句”仍具有顯著差異(p=.000)。

表2 句子類型主效應(yīng)事后多重比較
Note:*p< .05,**p< .01,***p< .001
根據(jù)以上結(jié)果可知,被試能夠辨析實驗中漢語同譯近義詞對的語義差異,英語翻譯對等詞并未對漢語同譯近義詞的加工產(chǎn)生影響。然而,根據(jù)雙語詞匯通達非選擇性加工觀的雙語詞匯提取模型(如雙語交互激活BIA模型、BIA+模型),一語和二語的詞匯表征共同存儲在一個整合的心理詞庫中,并且詞匯的通達是非選擇性的,在兩種語言間存在著目標語的競爭(Dijkstra et al., 1988; Dijkstra et al., 2002)。當被試對字符刺激進行加工時,會同時激活存儲于同一心理詞庫的兩種語言信息。由于成對的兩個漢語同譯近義詞共享同一個英語翻譯對等詞,則對這兩個漢語詞的加工會導(dǎo)致該英語翻譯對等詞的語義信息的伴隨激活,從而使得這兩個漢語同譯近義詞在詞匯語義上聯(lián)系更為緊密,造成被試在一定程度上對其產(chǎn)生混淆,甚至完全“混為一談”。但如實驗結(jié)果并非如此,對此該作何解釋呢?我們認為,這可能是由于漢語同譯近義詞對共享的英語翻譯對等詞的詞匯語義信息激活程度過低(甚至完全沒有受到激活),因而不足以使兩個漢語同譯近義詞在詞匯語義層面趨同化所致。再考慮到本試驗中的被試雖然英語水平較高,但仍實為母語優(yōu)勢的漢-英雙語者,又處在漢語(母語)環(huán)境下,其二語詞匯語義信息激活較低,不足以影響母語詞匯加工的可能性更大。
文獻回顧部分Khachatryan等(2016)的有關(guān)研究曾表明,二語意識是二語影響母語詞匯語義加工的一個重要因素。為此,我們設(shè)想,當喚起被試的英語(二語)意識時,英語便會對漢語(母語)詞匯加工產(chǎn)生較大的影響。鑒于此,本研究以實驗一為基礎(chǔ),進行后續(xù)實驗二,通過顯性操控漢-英雙語者被試的二語(英語)意識,考察被試在加工漢語同譯近義詞對時是否會受到英語的影響。
2.2 實驗二
2.2.1 研究問題
在英語誘導(dǎo)條件下,中國高水平漢-英雙語者對漢語同譯近義詞的加工是否會受到英語的影響?
2.2.2 被試信息
同實驗一。
2.2.3 實驗材料、設(shè)計與程序
實驗材料、設(shè)計及程序與實驗一基本相同,唯一不同之處在于,在呈現(xiàn)句子主干部分之前,先呈現(xiàn)漢語同譯近義詞對的共享英語對譯詞作為誘導(dǎo),以激活被試的英語(二語)詞匯語義知識。實驗二的具體實驗程序如圖3所示。實驗一與實驗二的時間間隔為兩周。

圖3 實驗二基本流程圖
2.2.4 ERPs記錄與分析
均同實驗一。
2.2.5 結(jié)果與討論
15名有效被試的腦電數(shù)據(jù)進入最終統(tǒng)計分析。與實驗一相似,在目標詞呈現(xiàn)400ms左右,誘發(fā)了一個峰值達到最大值的負波N400(280-510ms)(見圖4)。重復(fù)測量方差分析顯示(見表3),句子類型主效應(yīng)顯著,F(xiàn)(2, 26)=19.732,p=.000;句子類型與腦區(qū)交互效應(yīng)顯著,F(xiàn)(4, 52)= 7.114,p=.002;句子類型和半球的交互效應(yīng)顯著F(4, 52)=3.418,p=.023;句子類型、腦區(qū)和半球沒有顯著的交互效應(yīng)(p=.536)。

圖4 實驗二三種句子條件下誘發(fā)的ERPs平均波形圖

因素dfF sig.η2句子類型219.732.000???.603句子類型×腦區(qū)47.114.002??.354句子類型×半球43.418.023?.208句子類型×腦區(qū)×半球8.829.536.060
Note:*p<.05, **p<.01, ***p<.001
對句子類型進行事后多重比較分析表明(見表4),“搭配一致句”與“搭配不一致句”的N400波幅差異不顯著(p=.064),“搭配一致句”與“填充句”的N400波幅差異顯著(p=.000),“搭配不一致句” 與“填充句”差異顯著(p=.001)。

表4 實驗二句子類型主效應(yīng)事后多重比較
Note:*p< .05,**p< .01,***p< .001
這表明,被試在理解漢語同譯近義詞對時,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兩個詞的詞匯語義信息,二語英語對漢語(母語)同譯近義詞的加工產(chǎn)生了影響。該結(jié)果與Khachatryan等(2016)關(guān)于“二語意識是二語影響母語詞加工的重要因素”的結(jié)論一致。在本實驗中,英語誘導(dǎo)材料使被試處于英語加工模式狀態(tài),直接增強了其二語意識。當被試對兩個漢語同譯近義詞加工時,對應(yīng)的英語詞詞匯語義信息不僅同時受到激活并且激活程度大大增強。受到強勢激活的共享英語對譯詞信息,使得兩個漢語同譯近義詞在詞匯語義上趨同化,從而使得被試模糊了兩個詞的語義差別,導(dǎo)致“搭配不一致”的句子的語義可接受度得以提高,趨近于“搭配一致”句的可接受度,在腦電上反應(yīng)為相近的N400波幅。
3 總討論
實驗一通過尾詞違反范式,采用在線句子理解任務(wù),考察英語對中國高水平漢-英雙語者漢語(母語)同譯近義詞加工的影響。結(jié)果顯示,被試在搭配一致和搭配不一致條件下加工漢語同譯近義詞(尾詞)時,所誘發(fā)的N400波幅具有顯著差異(p=.000),被試能夠根據(jù)詞匯的不同語義搭配區(qū)分兩個漢語同譯近義詞,其共享的英語對譯詞未對漢語同譯詞對的加工產(chǎn)生影響。實驗二進一步探討英語誘導(dǎo)條件下英語(二語)對母語同譯近義詞加工的影響,結(jié)果顯示,當呈現(xiàn)英語對譯詞作為誘導(dǎo)詞時,被試在搭配一致和搭配不一致條件下加工兩個漢語同譯近義詞時的N4000波幅差異不顯著,共享的英語對譯詞的詞匯語義知識使被試混淆了兩個漢語同譯詞的細微語義差別,使搭配不一致的句子在語義上合理化,表現(xiàn)出與加工搭配一致句相似的腦電表現(xiàn),英語影響了被試對漢語同譯近義詞的加工。
以上研究結(jié)果與以往的研究結(jié)果相一致。一方面,不少研究已經(jīng)證明,在二語環(huán)境中生活多年的高水平二語學(xué)習(xí)者或平衡雙語者,會受到二語逆向遷移的影響 (Degani et al.,2011; Wang, 2013; Malt等(2015 )。究其原因,長期處于二語環(huán)境中二語學(xué)習(xí)者,其二語系統(tǒng)與母語系統(tǒng)同樣發(fā)達,兩種語言加工模式激活程度相當,在一定條件下二語系統(tǒng)的激活甚于母語系統(tǒng),因而在加工母語時易發(fā)生二語的詞匯語義逆向遷移。Malt et al. (2015)的研究似不支持這一結(jié)論,因為該研究發(fā)現(xiàn)德語單語者在接受一段時間的西班牙語教學(xué)后,其命名模式也產(chǎn)生了變化。但深入分析后發(fā)現(xiàn),該實驗中被試接受的語言教學(xué)為沉浸式教學(xué),且教學(xué)結(jié)束后的調(diào)查顯示,被試日常生活中運用西班牙語的比例高于德語。另一方面,不少研究也表明,在母語環(huán)境中的高水平非平衡二語學(xué)習(xí)者,由于其二語系統(tǒng)與母語系統(tǒng)相比,完善程度較低,且所處母語環(huán)境制約了二語系統(tǒng)的激活,這就使得這類二語者在加工母語時優(yōu)先激活了母語系統(tǒng),母語的使用不受二語系統(tǒng)的影響。但一旦某種特殊條件使被試有意識地調(diào)用其二語系統(tǒng)時,二語詞匯語義知識便會發(fā)生逆向遷移。Khachatryan等 (2016)的研究便是明證。該研究中的被試為英語水平較高的荷英雙語者,被試一直處于荷蘭語環(huán)境中,且荷語為日常交流的優(yōu)勢語言,因此,只有當被試意識到啟動詞為荷語-英語同形詞時,才會產(chǎn)生同形詞對同形無關(guān)詞(以荷語方式呈現(xiàn)的同形詞的英語語義相關(guān)詞)的啟動效應(yīng),即發(fā)生英語詞匯語義知識的逆向遷移。同樣,在本實驗中,雖然所有漢英雙語被試都為通過英語專業(yè)八級的英語專業(yè)研究生,英語水平相對較高,但由于其漢語仍為優(yōu)勢語言,因而只有在有意激活英語系統(tǒng)即實驗(二)的英語誘導(dǎo)條件下,才會發(fā)生英語詞匯語義知識的逆向遷移,即發(fā)生英語(二語)對漢語(母語)詞加工的影響。
本研究結(jié)果與Cook (2003) 提出的整合的連續(xù)統(tǒng)(integrative continuum)模型的預(yù)測也相一致。該模型認為,雙語者大腦中存儲著一語和二語兩個語言系統(tǒng),這兩個系統(tǒng)處在從完全分離到完全整合的一個動態(tài)變化過程中。當兩種語言系統(tǒng)處于部分整合的狀態(tài)時,就會相互影響,此時,二語詞匯語義信息就可能對母語詞匯加工產(chǎn)生逆向遷移。基于此模型,結(jié)合Dijkstra 等人(Dijkstra et al., 2002; Dijkstra, 2005)提出的“BIA+”模型對詞匯識別系統(tǒng)的描述,我們對兩個實驗的結(jié)果解釋如下(圖5所示)。

圖5 誘導(dǎo)條件下漢-英雙語者英語詞匯語義逆向遷移過程
對于實驗一,非平衡漢-英雙語者被試的漢、英兩種語言系統(tǒng)共存于同一心理詞庫中,各系統(tǒng)的亞詞匯、詞匯、語義信息在不同的階段以不同的融合程度分布在各層次中。雖然被試的英語水平相對較高,但在母語環(huán)境中,漢語仍為其優(yōu)勢語言。當漢語同譯近義詞呈現(xiàn)時,被試優(yōu)先選擇了漢語加工模式,在亞詞匯、詞匯、語義層面都優(yōu)先選擇激活漢語詞匯特征信息,而抑制英語詞匯信息的激活。同時,由于漢語為象形文字,英語為拼音文字,兩種語言在正字結(jié)構(gòu)上有著明顯的區(qū)別,因此亞詞匯層面便優(yōu)先對漢語節(jié)點進行了激活。由于兩個漢語同譯近義詞有著不同的亞詞匯、詞匯特征,因而激活的語義信息也各不相同。在這種情況下,被試便能夠完全辨析漢語同譯近義詞對的語義區(qū)別。
實驗二中,當呈現(xiàn)英語刺激作為誘導(dǎo)時,漢英雙語者被試的英語意識得以喚醒,使其預(yù)先處于英語加工模式中,此時,各層面中兩個系統(tǒng)的信息都融合分布。當漢語同譯近義詞呈現(xiàn)時,漢語、英語信息在亞詞匯層面受到同等程度的激活。盡管根據(jù)刺激的正字結(jié)構(gòu)特征,在詞匯層面上,漢語、英語信息激活的強度或有不同,但在語義層面上,由于漢語同譯近義詞對共享同一個英語翻譯對等詞,兩個詞的語義信息都包含在同一英語詞的語義信息中,在經(jīng)濟加工策略的驅(qū)使下,優(yōu)先選擇對包含范圍廣的英語翻譯對等詞的語義信息進行了激活,由此,兩個漢語同譯近義詞在語義層面激活了同樣的信息,因而使得漢-英雙語者在一定程度上“誤認為”漢語同譯近義詞對在語義上相同,英語翻譯對等詞的語義信息發(fā)生了逆向遷移。
盡管本研究獲得了以上有價值的發(fā)現(xiàn)結(jié)果,但也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本研究只考察了由兩個同譯詞構(gòu)成的同譯近義詞對的情況,未考察由多個同譯詞構(gòu)成的同譯近義詞組的情況;第二,本研究在選取同譯近義詞對作為實驗材料時,由于實驗設(shè)計上的限制,未考慮“詞類”“ 詞匯抽象性”等潛在的影響因素;第三,本研究只考察了漢語同譯近義詞的加工,未涵蓋到漢語異義詞的加工;第四,在實驗設(shè)計中,我們雖然設(shè)置了“填充”條件作為“搭配一致”與“搭配不一致”的對照條件,但理想的做法還應(yīng)設(shè)置一個 “漢語單語組”者作為對照。此外,今后還應(yīng)從交叉驗證的角度,通過測驗、語料庫等多種方法手段,對學(xué)習(xí)者學(xué)習(xí)使用同譯近義詞的行為做長時深入的考察。
4 結(jié)語
本研究采用EEG/ERPs研究手段,運用尾詞違反范式,考察了中國高水平漢-英雙語者漢語同譯近義詞加工中的詞匯語義逆向遷移。研究結(jié)果表明,中國高水平漢-英雙語者在加工漢語同譯近義詞時,英語詞匯語義知識一般不發(fā)生遷移,但當學(xué)習(xí)者受到誘導(dǎo),英語意識被提升時,英語詞匯語義知識發(fā)生逆向遷移,英語影響學(xué)習(xí)者對漢語同譯近義詞的加工。
本研究為漢-英雙語者漢語同譯近義詞加工中的英語詞匯語義逆向遷移提供了初步的電生理學(xué)證據(jù),其基本結(jié)論有助于揭示雙語者兩種語言心理表征、存儲、提取與變化的規(guī)律與特點,有助于深入探索雙語學(xué)習(xí)與使用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