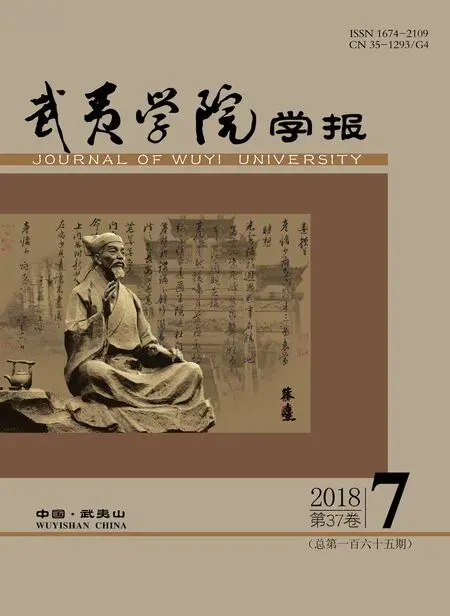義利之辨:傳統義利觀的嬗變及其啟示
——從朱熹到康有為
許 彬
(1.武夷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2.武夷學院 朱子學研究中心,福建 武夷山 354300;3.福建省統戰文化武夷山研究基地,福建 武夷山 354300)
義利之辨是貫穿著歷史與現實的重要話題。南宋朱熹在繼承先秦儒家重義輕利觀念的基礎上,引理入義,賦予“義”以本原地位,在義利觀念上主張重義輕利和以義制利的價值取向。時至清末,康有為在救亡圖存的時代境遇之下,批判宋儒徒陳高義,忽視功利的傾向,并在此基礎上提出重利兼義和以義生利的思想觀念。義和利源于人的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義利之間是辯證統一的,同時作為社會道德原則,崇尚道義又具有超越功利的普遍意義。
一、重義輕利,安貧樂道———朱熹義利觀的主要內涵
眾所周知,在義利之辨問題上,先秦儒家就已經形成了比較豐富的思想主張,這是朱熹義利觀形成的主要來源。朱熹繼承先秦儒家義利觀念,并結合其理學體系,更加系統地闡發了義利觀念。
(一)引理入義,重義輕利
在義利問題上,朱熹將理引入義中,賦予義以同屬于天理的地位。他說:“義者,天理之所宜。”這就是說,判斷一個人的心理和行為是否合宜,就看其符不符合天理。朱熹引理入義,并沒有將“義”懸置于形而上的世界,而是將其納入活生生的現實生活之中。他說:“義者,心之制,事之宜”[1],“義如刀相似,其鋒可以割制他物”[2]。“義”就像一把利刃,裁制由于“人情之所欲”[1]而產生的種種功利。朱熹引理入義,將義與理相統一,在義利觀的理論預設上,構建了“義”的本原性地位,目的則是確保義對于利的主導作用和優先地位。不過,對于“利”,朱熹并沒有一概否定,正如他言:“利,誰不要”,“利不是不好”。[2]雖然如此,他對未經省思的欲望卻表示出深深地擔憂,因而他在論及義利之辨時,往往更加強調道義的衡量與裁制作用,總體上呈現出重義輕利,以義制利的價值取向。他說:“凡事不可先有個利心,才說著利,必害于義……蓋緣本來道理只有一個仁義,更無別物事”,“義利,只是個頭尾。君子之于事,見得是合如此處,處得其宜,則自無不利矣。但只是理會個義,卻不曾理會下面一截利。小人卻見得下面一截利,卻不理會事之所宜”。[2]朱熹先義后利的觀念與荀子“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荀子·榮辱》)的思路一脈相承。循著以義為先的主張,朱熹推出以義生利的效果,他說,“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圣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著。才說義,乃所以為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2]言下之意,若是向義而行,利便不求自來,義中必有利。
(二)尚公輕私,安貧樂道
雖然說“利”是人人想要獲得的東西,但朱熹更多論及的卻是為人之公利。他在注解《孟子·梁惠王》篇中說:“梁惠王問利國,便是為己,只管自家國,不管他人國。義利之分,其爭毫厘。”[2]即便如梁惠王是求一國之利,在朱熹看來也不值得肯定,因為這僅僅只是為一諸侯國之私利,與為天下之公利有根本性的區別。“義利之分,其爭毫厘”,毫厘只差,恰在于公私與否。朱熹又言:“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為己為人之分,才為己,這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為己,天理也是為己。若為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2]從功利的角度看,朱熹認為應該追求為人之公利;從恪守道義的角度說,他認為應該做好修身為己之學。相反相成,無非就是要牢牢把握道義的準則,對于這一點的強調,朱熹可謂是樂此不疲,不遺余力。他從內外之維加以闡明,他說:“大凡為學,且須分個內外,這便是生死路頭……從這邊便是為義,從那邊便是為利;向內便是入圣賢之域,向外便是趨愚不肖之途。”[2]朱熹持守內圣之道,強調反躬內省的工夫論,這與永嘉學派向外務實的事功主義路向懸殊。
朱熹又從“存天理,去人欲”的角度,指出:“仁義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殉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己隨之。所謂毫厘之差,千里之繆。”[1]朱熹認為人應當循天理、依仁義、持義心,這樣便無往而不利,而判斷君子與小人之別,關鍵就在于對義心與利心的領悟上,他說:“小人之心,只曉會得那利害,君子之心,只曉會得那義理。見義理的,不見得利害;見利害的,不見得義理。”[2]具體來說,“且如有白金遺道中,君子過之,曰‘此他人物,不可妄取。’小人過之,則便以為利而取之矣。”[2]可見,朱熹所肯定的利只是踐行天理與仁義的自然結果。縱觀其一生,大多處窮困潦倒之境遇,但是他卻能夠安貧樂道,怡然自得,這正是其堅守道義的真實寫照。他說:“君子之于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于利,亦是于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亦深好之也。”[2]安貧樂道是儒家的價值理念和精神境界的追求,朱熹在注解《論語》“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時,說:“圣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云之有無,漠然無所動于其中也。”[1]圣人之心渾然天理,具備至高的道德境界,對于不義之榮華富貴,視作枉然,不滯于心。朱熹持守的淡泊名利,安貧樂道之精神,與簞食瓢飲的孔顏之樂一脈相承。
二、重利兼義,以義生利——康有為對朱熹義利觀的批判與改造
清末民初之際,遭受西方堅船利炮的欺凌,康有為身處三千年未有之變局,肩負救亡圖存的時代訴求,他批判朱熹等理學家重義輕利、以義制利的價值取向,主張自然人性論,強調人欲的合理性和功利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義利兼顧和以義生利的價值觀念。
(一)天欲而人理,“性全是氣質”[3]
朱熹重義輕利、以義制利的觀念與其“存天理,去人欲”的哲學思想相統一。康有為對朱熹義利觀的批判就是從批判理欲觀開始的,他甚至將天理和人欲顛倒過來,轉而表述為“天欲與人理”。他說:“嬰兒無知,已有欲焉,無與人事也。故欲者,天也。程子謂‘天理是體認出’,此不知道之言也,蓋天欲而人理也。”[4]人欲在康有為這里得到了極大的肯定,乃至上升為天欲,他進一步認為,“凡為血氣之倫必有欲,有欲則莫不縱之,若無欲則惟死耳。”[4]實際上,在朱熹“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中,“人欲”指的是不符合天理的不良欲望,比如私欲、貪欲等,而符合天理的欲望,朱熹則是完全肯定的,如他所說的“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2]。康有為未加審視朱熹道德倫理學中“人欲”概念的真實內涵,他的“凡為血氣之倫必有欲,有欲則莫不縱之”的“縱欲”言論,對于宋儒“絕欲而遠人”[5]的批判,實有矯枉過正的局限性。然而,在“萬馬齊喑”的晚清社會,康有為對欲望的倡導,卻又是有思想解放和推動社會發展的積極意義。
康有為“天欲而人理”的判斷,與其自然人性論主張密切相連。他不贊同人性本善,認為“性全是氣質”[3],進而批判“宋儒每附會孟子性善之說”[6],認為告子無善無惡論近于理。他說:“人性之自然,食色也,是無待于學也。”[7]在康有為的論述中,不管是“天欲而人理說”還是“性全是氣質論”,其視角都是基于批判朱熹理欲對立、性有二分等的理論預設而進行的,其目的是希望通過強調氣、欲、情等主體地位的理論闡發,將朱熹的天理論化為人理論。因此他批判“宋儒專以理言性,不可”[5],認為“‘性即理也’,程子之說,朱子采之,非是”[7]。他認為程朱理學中“以禮信為性,是不識性也”[7],理由在于“實則性全是氣質,所謂義理自氣質出,不得強分也”[3]。綜上所述,康有為通過對朱熹理學及道德倫理學的批判,建立了天欲而人理,性全是氣質的斷言,為其宣揚重利兼義的觀念打下基礎。
(二)重利兼義,以義生利
康有為批判“宋儒不知,而輕鄙功利,致人才恭爾,中國不振”[9],這既是評價歷史,更是希望汲取歷史經驗教訓,改變社會“輕鄙功利”之弊,從而實現救亡圖存的使命,故而他肯定“利者,人所同好”[9],對于富與貴,“人不能無取”[9]。為了論證人趨于私利的根源,康有為不惜放棄他先前肯定的自然人性論,進而強調人性之私及其在社會發展中的動力作用。他說:“人之性也,莫不自私。夫惟有私,故事競爭,此自無始已來受種已然。原人之始,所以戰勝于禽獸而獨保人類,擁有全地,實賴其有自私競爭致勝之功也。”[8]對于朱熹尚公去私的觀念,康有為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看來,當面對有限的資源時,人性之私便油然而生,但恰恰是人性蘊藏之私,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很顯然這其中是受到了進化論的一定影響。他說:“凡挾才智藝能之人,其下者,利祿富貴之欲必深,其高者,功名之心必厚……淡于爵祿、淡于功名之士,雖有德行志節,其于趨事赴功也必遲且鈍。”[4]因此,“薄為俸祿,而責吏之廉;未嘗養民,而期俗之善……蓋未富而言教,悖乎公理,紊乎行序也。”[9]這與朱熹引理入義,重義輕利的觀念形成了明顯的反差。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康有為對先前“縱欲”的言論,已有所糾正,對于道義更加重視,如同朱熹嚴格劃分義心與利心的區別,他也同樣注重區分二者的不同。他說:“懷義心者,雖日為利,而亦義。懷利心者,雖日為善,而亦惡”,“若必懷利心,是亂世與平世之所由異,而太平終無可望之日矣”。[10]在這一點上,他與朱熹持守的重視仁義道德的價值觀基本一致。平心而論,作為深受傳統儒家文化浸染的康有為,并沒有走到見利忘義、唯利是圖的絕對功利主義的立場。他繼承了“利者,義之和也”的道德命題,借子貢之口,說:“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義之和也。如此,則利可也。”[10]他擔心若完全以利為本,則將容易導致天下大亂,他又借司馬遷之口,說:“利誠亂之始也。”[10]
三、傳統義利觀在近代的嬗變及其啟示
康有為的義利觀折射出中國近代思想家們對中國傳統治理理念現代轉型的思考,面對西方現代化的強勢入侵,他認識到,中國只有走出傳統義利觀的束縛,重視功利,富國強兵,才能有力回應西方的入侵,這充分體現出近代救亡圖存的時代任務,而朱熹的義利觀則代表了先秦以降,傳統儒家“正其誼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的重義輕利的道德選擇。進而言之,康有為通過對朱熹義利觀的批判,是對義利之辨這一問題的理解和詮釋,而在這樣的創造過程中,義利之辨所蘊含的真理及其啟示也得到更加全面和深刻的闡釋。
(一)義利統一源于人的雙重屬性
人的雙重屬性指的是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一方面,自然屬性決定了人對物質和精神的需求,如渴則飲、饑則食、安全之需等。在這一點上,可以說人同地球上其他生物沒有本質的差異。康有為說人具備“求樂免苦”的權利,“愛惡仁義,非惟人心有之,雖禽獸之心亦有焉”[8],多是出于人的自然屬性而言的。先秦儒家和宋明理學家不否認人由自然屬性而帶來的基本需求,如“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論語·里仁》),“飲食者,天理也。”[2]另一方面,社會屬性又決定了人必須要遵守一定的社會道德規范和原則。秉承仁義禮智,是人之于物的根本區別。孟子說:“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離婁上》)荀子把學與義比較后,得出“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荀子·勸學》)的忠告。朱熹則以道學家的眼光,從德性純粹與否的角度,指出:“物物運動蠢然,若與人無異。而人之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也。”[2]人受到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雙重作用,與此相應,也離不開對義與利的追求。無論是朱熹所持的重義輕利還是康有為所論的重利兼義,皆是源于這一雙重屬性。義利之間是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不是顧此失彼的沖突與對立。一味強調道義或功利,都失之片面,并可能會造成泛道德主義或極端功利主義的問題。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如果沒有義利統一,人們的利益追求以至全部行為就不能得到有效的規范與引導,從而也會導致以合理化為特征的現代化破產。”[11]
(二)義利統一需要與時俱進
隨著社會經濟結構和思想文化的發展變遷,義與利的內涵也必然要適應時代的發展。“所謂‘義’亦即社會道德準則是一歷史范疇,具有鮮明的時代性。”[12]朱熹重義的觀念雖有合理性,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其自身所包含的局限性也逐步顯露出來。康有為說:“朱子之學在義,故斂之而愈嗇。而民情實不能絕也”[14];“蓋天下義理,無非日新”[6]。在康有為看來,朱熹過度強調精神層面的道義,勢必阻礙和限制社會大眾對物質層面的需要和追求,這與社會實情和歷史發展趨勢相背,以至于造成“宋儒不知,而輕鄙功利,致人才恭爾,中國不振”[9]的歷史結局。朱熹重義的價值取向具有可貴的道德意義,但是其重之“義”,最終指向的是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封建綱常倫理,其重義輕利的觀念與維護宗法社會秩序的穩定緊密相連。他對功利意識和人欲追求的謹慎態度,在其理學思想被官方化后,逐漸對個體和社會求利的動力產生了消解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功利意識和功利原則對社會發展的動力和杠桿作用。當代學者陳來就曾指出:“儒家或理學面臨的矛盾在于,它自身最多只能保持倫理學原理的一般純粹性,而無法判定‘義’所代表的準則體系中哪些規范應當改變以適應社會發展,因而可能會把規范僵化。”[13]
康有為指出理學家的重義輕利觀念已不能適應急劇變化的社會現實時,說:“夫以天地,不變則不能久,而況于人乎?且人欲不變,安可得哉?”[9]因此,康有為在對傳統義利觀揚棄的基礎上,賦予義與利新的時代內涵。其“義”已經包含了求強求富,人人自主、人人獨立等新的價值觀念,對利的追求不再一味“罕言”之,而是推崇工商實業的發展。有學者已經指出:“在許多愛國的近代商人看來,最大的義已不是恪守封建倫理道德,而在于通過發展工商實業,為救亡圖存,富國利民盡自己的一份力量。”[15]
(三)崇尚道義具有超越功利的普遍意義
“義”作為具體的道德準則,具有時代變化的特征,但是它作為社會道德原則,則又具有超越功利的普遍意義。“‘義’代表了社會性的道德要求,具有規范和引導行為的普遍意義。”[17]朱熹引理入義,重義輕利,尚公輕私的價值取向,具有超越功利的普遍意義。朱熹說:“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2]孔子篤信:“君子義以為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孔子、孟子甚至提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道德追求。質言之,儒家倡導見利思義,反對見利忘義的道德觀念,具有恒久性、普遍性,是跨越時代的,這不僅是超越功利,更是超越生死,是一種高尚的道德境界。平心而論,若是能夠揚棄三綱五常所包含的落后性的一面,以義格利的價值觀無疑具有倫理學原理的純粹性以及可貴的理想維度。康有為重利兼義的主張,是對朱熹的重義輕利觀念的完善,而不是絕對反對。他對理學家“徒陳高義”提出批評,但是在維護“義”作為社會道德原則的總原則上,卻是保持一致的。他將人欲改為天欲,并非就是承認人欲的絕對性,在義利之間,他也屢次言及尊重道義的重要,他說“不可枉己求利”[4],“有恥心,則可使路不拾遺矣”[4],“利心不可懷也”[10]。就此而言,康有為與朱熹的義利觀念是統合于儒家義利兼顧,反對唯利是圖的道德倫理之中的。相對于“義”的普遍意義,人對功利的追求雖源于自然屬性的內在要求,但是作為用來滿足個人或組織需求的各種層次和類型的功利,離不開具體的對象。“‘利’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是個別的、特殊的,哪怕它是某個集體(家庭、部落、團體、國家、民族)之利,它總是與‘我’有關才能是‘利’。”[16]利的特殊性決定了人對功利的追求必然是要有限度的,而這種限度不僅需要道義的規約,亦需要尚義的超越性加以守護和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