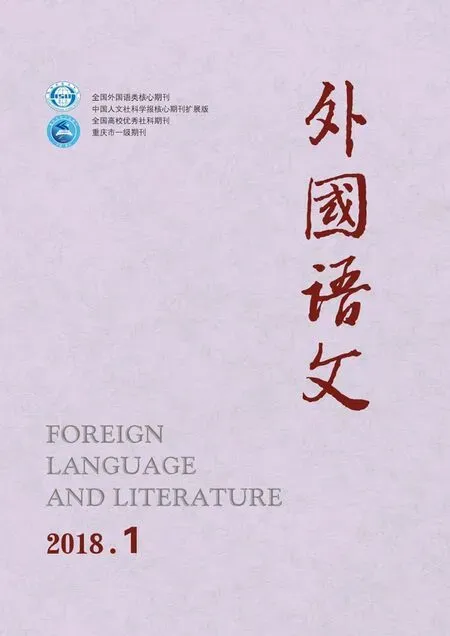符號互動論思想下的具身認知研究
王慧莉 崔中良
(1.大連理工大學 外國語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4;2. 大連理工大學 哲學系,遼寧 大連 116024)
0 引言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具身認知成為認知科學研究的潮流。具身認知的倡導者嘗試從各個層面上擺脫以笛卡爾為代表的經典認知思想的束縛,提出認知是一個動態的、情境的、身體的和非表征的交互過程。瑪格利特·威爾遜(Margaret Wilson,2002)認為具身認知具有“情境性、時間壓迫性、環境承載認知功能、環境是認知系統的組成部分、認知是為了行動、離線認知也需身體支撐等六大特征”。由于過分關注身體和環境,具身認知科學沒有強調認知過程中的社會性活動,特別是符號活動的作用,使得認知科學的研究仍然無法擺脫唯我論。因此,在涉及到認知的統一性與多樣性關系以及他心問題的時候,具身認知研究仍然顯得理屈詞窮。
1 具身認知的社會性研究趨向
近年來,一些學者逐漸認識到了具身認知所面臨的危機,不能將認知還原為身體的大腦神經,否則就會“忽視人類的高級認知能力和文化對認知的影響。所以,只有通過嵌入社會,認知的具身進路才會得到完善”(常照強 等,2013)。 邁克爾·安德森(Michael Anderson,2001)認為目前的具身認知研究需在生理、進化歷史、實踐活動和社會文化等四個方面進行補充。埃德溫·哈欽斯(Edwin Hutchins,2010)指出:“未來的30年,認知科學的研究方向應該是認知的社會性和文化性問題。”因此,我們需要對具身認知的理論基礎進行反思。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大批的學者開始從實踐活動和社會文化方面對具身認知進行研究。肖恩·加拉格爾(Shawn Gallagher,2015)通過對自閉癥和嬰兒模仿的研究,認為人類天生具有具身主體間性的能力,而且會在以后的認知發展中起到關鍵作用,人類基本的認知技能如感知、分類和推理通過身體與環境在社會實踐的互動過程中產生,“即使那些最基本的認知技能也會受到特殊的社會環境影響,我們可以將其稱為社會負載” (Shore,1996:4)。崔中良和王慧莉(2016)通過分析后期維特根斯坦的思想,指出認知的發生應該建立在生活世界、實踐和游戲之中。張積家和馬利軍(2013)論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會實踐思想是實現具身認知的途徑。具身認知逐漸從身體分析向主體間性、社會性、實踐性維度轉向。身體不僅表現為物理構造和神經系統,而且還表現為社會制度和規則影響與規范的社會身體。喬丹·茲拉特夫(Jordan Zlatev,2007)通過對語言認知的研究提出第三代認知科學,認為語言互動在認知的產生和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認知表現出具身的集體合力傾向,因此認知不僅具有具身性,而且還具有主體間性。這些研究從主體間性、社會實踐等方面探討了具身認知的社會性,但只是對具身認知的一個共時的側面來探討社會性在認知中的作用,并沒有從進化歷史的角度探討認知是如何從社會活動和符號互動、特別是語言互動中生成的。
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喬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 Mead)通過研究社會行為和符號互動在心靈和自我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反對行為主義和平行二元論,指出人類的心靈具有具身性、社會性和符號互動性,他認為整個西方對意識的心理學和生理學研究都基于自我中心主義和唯我論的思想基礎,這要求我們采用實用主義的觀點將意識和認知的研究放入具體的情境和社會中(Mead,1925)。米德的符號互動論思想對具身認知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加拉格爾(S. Gallagher)指出:“影響情境(具身)認知的主要哲學家是杜威、海德格爾、梅洛·龐蒂和維特根斯坦,但是也應看到如:詹姆士、喬治·米德、伽達默爾……等的影響。”(Gallagher,2009:36)*由于第二代認知科學的多學科性和多流派性以及強調的重點不太一樣,因此會有不同的名詞來指稱第二代認知科學,如,情境認知、具身認知、延展認知、嵌入認知、生成認知等等,它們之間相互關聯和相互批評,但是總體上都反對第一代認知科學。加拉格爾由于強調認知的社會性,因此將他的認知思想稱為情境認知,但是他也認為情境認知從廣義上來說也可以稱作具身認知。因此,美國實用主義中的社會性和符號互動性研究將會成為具身認知社會轉向的重要思想來源,對米德認知思想的研究可以加強具身認知歷時的社會和符號維度探索。
2 符號互動論與認知
作為美國實用主義的重要奠基人,米德除了直接對詹姆斯、喬西亞·羅伊斯(Josiah Royce)、查爾斯·庫利(Charles Cooley)、杜威等人的思想進行社會性深化和延伸之外,還對清教倫理、科學實踐精神、達爾文進化論和德國唯心主義進行轉化和應用。米德的認知思想依托于其社會心理學思想的論述,順勢于自休謨以來對以笛卡爾為代表的心靈實體理論的批判,反對身心二元論和以靜止的、孤立的心靈為載體的認知思維觀,認為人類早期心靈和意識的產生來自個人和社會的辯證互動(Marková,1987:104)。雖然人類的心智現象似乎表現為內部私人現象,但是不能離開世界和他人而獨立存在,始終堅持研究無機物、有機物、動物、人、社會乃至整個宇宙的整體系統。
2.1認知的符號互動性
認知的情境性強調認知并非一個靜止的形式或狀態,而是一個過程和活動,它發生在具體的情境之中(Bredo,1994)。在杜威看來,“認知行為一定離不開所處的特定自然情境與社會文化情境。就前者而言,認知行為是生物體與自然環境的互動;就后者而言,認知行為是生物體與社會情境的互動”(孟偉,2015:61)。米德繼承和擴展了杜威的情境思想,認為情境性更多地表現為社會互動,包括了身體、自然世界、社會活動和符號互動在內的整體系統的互動。雖然認知依存于身體和世界的交互,但是,認知應該排除人類個體自我反思和脫離符號互動內化的幻象,認知從本質上說是一種社會行為和符號互動行為,“社會互動性是我們心靈的結構”(Mead,1932)。傳統的具身認知觀認為,認知發生在大腦-身體-環境之中的一種耦合狀態,而米德認為認知是一個身體-世界-他人的三維動態互動過程,因為“在有機體和它的環境之間劃分出某種情境的用意很困難”(米德,2012:143),認知無法擺脫社會束縛。米德的闡述比杜威更加深刻,他認識到自然情境與社會情境、有機體與情境之間都無法分割,因此情境包括多重視角,任何視角都是對一個有機體活動場域的闡釋,身體與周圍環境黏著在一起,而身體活動及所帶來的意義則與社會無法分離。一方面,認知的整個過程發生在社會情境中,受社會情境的制約而蒙上社會性的薄紗,“認知并不存在于如希臘哲學中的大腦或身體內部,而是與整個身體器官和社會活動聯系在一起的社會性存在”(Mead,1982:148);另一方面,認知的情境性還包括有機體對自然和社會情境的能動性改造。情境作為整體先于個體作為部分而存在,部分要根據整體來說明,但個體與情境之間是雙向決定的,情境決定機體和機體決定情境一樣充分(Mead,1972:412),人類、世界和社會的互動會改變人類的認知范圍和認知方式,如:火的使用改變了人類語言中食物范疇的劃分,因此人類的認知與社會互動和符號互動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的關系。
2.2認知是一種態度
米德強烈批評笛卡爾的心身二元論,否認心智是一個與身體平行的孤立實體,“在大腦的結構之中,根本不存在任何把大腦的某些部分從身體分開而作為中央控制部分的東西”(米德,2012:26),同時也沒有一個獨立的心靈在控制著人類客觀身體。米德認為心智與身體活動密切相關,應該將心智和身體翻譯成為一種同時適用于這兩個領域的語言,因此米德嘗試使用社會行為來指人類心靈和身體的統一,如果我們將它翻譯成認知科學的語言,就是心靈和身體統一在具身的社會行為中。這里要強調的是,雖然米德是一個唯物主義者,但他并不同意將認知活動看作是大腦神經的運動或者是純粹的物質,也不同意將心智活動限制在個體水平之上(Madzia,2013)。
米德的時代是華生等行為主義心理學比較盛行的時期,但是,他并不贊同行為主義將心智還原為單純的行為而否定心智。米德認為,認知的基本材料是“活動而不是神經束;而且,活動既具有開始的階段,也具有發生的階段,既具有內在的側面,也具有外在的側面”(米德,2012:8),開始的階段和內在側面是被行為主義所忽略,但是也是研究的重點。米德指出人們生活在意義世界,我們將會或者很可能操縱我們的所見所聞(Mead,1964:294),因此,對于物體的認知就是對物體的使用和操作方式。幼兒通過自己與諸物體的接觸、操縱以及使用了解物體的意義,例如:對于一個兒童來說,鐵鍬是某種用來挖東西的工具(Mead,1982:132)。當面對一個物體時,不同的人會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如:當我們看到一匹馬,一個人會飛身騎到馬背上,一個人會站在它前面拍照,這就是米德所說的行為的內在方面,即行動態度。行動態度是社會行為的非命題的和亞人的開始,也可以說是行動的準備階段。“如果一個人正在接近一把錘子,那么,他的肌肉就做好了隨時抓住捶柄的準備,這種活動的后期階段都存在于其前期準備階段之中。”(米德,2012:12)同樣的情況也在命題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命題態度作為表達主體與命題之間的認知關系,經常出現在一個命題的前半部分,而這就是命題表達的準備階段,如:
(1)Ithinkthat both books share the same moral.(BNC-Written)
(2)IbelieveACET has an important part to play in this process.(BNC-Written)
(3)Weregretthat we are unable to answer multiple queries that do not comply with these instructions.(BNC-Written)
在這三個命題中,think、believe和regret 作為命題態度,在命題的一開始就表達了命題主體對接下來要陳述的事件的認知,因此,認知即態度。兩個人看到同樣一個事物而產生了不同的行為態度,對于同一事件采取了不同的命題態度,證明了人類的不同認知方式。
態度有一個運行于活動的開始和結束的目標朝向,通過對環境負載的探索來不斷地調整行為方式直到活動的解釋。最近,神經科學研究也證實了米德的認知態度觀,在理解他人行為的時候,鏡像神經元會去模仿他人行為,并為接下來的感知和動作做準備。里佐拉蒂(G. Rizzolatti) 和 西尼加利亞(C. Sinigaglia)(2008:50)指出:“因為我們在操作,所以我們在看;因為我們能夠看見,所以我們能夠在操作。這說明我們的視覺和我們的感覺運動器官互相連通,我們看到手和眼睛是相互引導的,我們用手看,我們用眼睛觸摸。”因此,米德認為人類的認知先于抽象自我的產生,認知植根于每個個體都擁有的生理-心理土壤之中,因此,認知是以活動作為其產生和運作的基座,通過態度而表現出來。
2.3姿態對話涌現認知
活動通常會經歷沖動、知覺、操作和完成四個階段,身體的沖動喚起知覺的反應,知覺的產生會導致個體產生對對象的直接操縱,最后實現沖動的完成。活動(act)包括個人行為和社會行為,個人行為是社會行為的個體表現,但是我們無法將個人行為從社會行為中完全區分開來*米德將社會行為定義為:“在這種行為中,可以發現釋放沖動的起因或者刺激存在于生物的特征或者行為舉止之中。社會行為包含一個以上個體的合作,其對象是某種社會對象。”(米德,2012:8)。個人活動涉及個體的生理和心理層面,為認知產生提供了基礎,使得機體有了認知的潛能。但認知的產生是需要“把經驗世界與有機體的全部活動聯系起來”(米德,2012:111),因此就需要個人行為進入到社會互動中。人類的全部生活經驗都與社會互動行為關聯,并且都在某種層面上展現出生活的樣態。米德認為社會活動是認知發生的場所,而非相反,“意識是行為的涌現(emergence),認知非但不是社會活動的前提條件,社會活動反倒是它的前提條件”(米德,2012:19)。認知在個人活動中表現為態度,在社會活動中就是姿態(Mead,1982:36)。由于個人活動與社會活動不可分割,社會活動并不是個人活動之和,因此米德認為姿態不是態度的疊加,姿態與態度其實是認知的兩個視角,態度更加突出個人,而姿態更多地涉及互動雙方。凱文·布思(Kelvin Booth,2013)指出:“米德具身認知思想中的兩個核心概念是態度和姿態。”
通過引述米德的姿態互動思想,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2008:24)指出:認知不是刺激和反應的直線型模式,而是動態的相互影響模式,它包括了身體與周圍環境之間的動態協調,還包括自我與他人交互過程中的動態調整。米德指出:姿態互動不只是人類獨有,一只狗在看到另一只狗發出咆哮的聲音的時候,它會不自覺地咆哮起來:對剛出生的嬰兒吐舌頭,這個嬰兒也會跟著吐舌頭,因此,在姿態對話中互動雙方并不需要意識的參與就會出現對應的姿態。在姿態對話中,只有意義自然呈現之后,關于意義的意識才會涌現出來(米德,2012:83),此時的意義具有客觀性,也就是說客觀意義是意識和認知產生的前提條件,只有將意義作為客觀對象的時候,意識和認知才會涌現,而意義作為客觀對象的前提是由于他人對自己行為的反應,同時從他人的反應中看到自己的行為,即采取他人的態度來回看自身,如“通過父母或者看護人不斷向幼兒演示自己的動作,兒童才理解‘球’是某種可以抓住和拋擲的東西”(Mead,1982:134)。米德通過對客觀意義的論述來表現這樣一個事實,即“認知的出現是社會互動的沉淀,需要人們更多地使用他人的態度,之后才能夠在扮演他人的角色中顯示自己的態度”(Mead,1982:86)。因此,認知在本質上是社會的,是姿態對話雙方在互動過程中的涌現。
2.4符號互動產生高階認知
雖然認知的產生與身體、情境和活動密不可分,同時這三個因素為認知的產生和發展夯實了堅實的基礎,但是,人與動物的認知并沒有進行區分。米德認為人類與動物的區別是高階認知,高階認知產生于符號互動,因此,他對符號在認知中的作用格外關注。符號包括了行為符號、聲音符號和書寫符號等,米德更注重有意義的聲音符號(或者稱為聲音姿態)。“通過聲音姿態比通過面部表情更容易使自己介入并把握自己”(米德,2012:65),而在聲音姿態中的有意味的符號是心靈產生的直接原因。心靈是通過由處于某種社會過程或者經驗脈絡之中的姿態對話組成的溝通而產生的,而不是溝通通過心靈而產生(米德,2012:54)。 “認知是一個重建的過程,思想是認知過程的一部分,語言重建是認知行為的重要本質”(Mead,1982:3-4),也就是說在有聲符號互動中自我才從無數的他人中凸顯出來,語言作為一種典型的符號互動方式是認知產生和發展的機制。米德將聲音符號泛化為語言,語言符號之所以重要在于語言在互動中所具有的雙重作用,即能同時對他人和自身產生相同的效應。語言在人類經驗的發展方面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即這種刺激可以像影響另一個人那樣影響這個說話者本身(米德,2012:75),因此,語言產生了兩個交際效果:交流的社會語言維度和自我溝通的個體社會化維度。在這兩個維度中,語言的自我溝通功能更為重要,它能夠產生自我反思能力,因此,高階認知是發生在符號互動過程中的身體活動的生存經驗的基質上所產生的過程。社會符號互動過程是人類生存過程的一個整體,但是這個整體是由無數的社會符號交往所構成,這個整體同時也會通過社會活動或互動滲入到任何既定的個人的具體經驗中,并在這個人的行為中顯現出來,認知也在這種互動行為過程中出現,從而表現出一種社會性。因此,個體就成為一個具有認知意識的完整的自我,自我也因此表現出一種與他人交際的外部認知和與自我交際的內部認知的過程,認知時刻表現出社會性和交際性。正如米德所說:“思維的確切含義是,把作為對象的椅子與椅子這個語詞聯系起來的過程由人們在社會中完成,并且因此而加以內化的過程。”(米德,2012:117)米德通過符號性社會交往論述心靈的本質,使得心靈具有發生學的維度,心靈成為一個不斷發展的、不斷變化的過程,從而擺脫了笛卡爾的心靈實體及靜態的認知觀。
米德還從發展心理學的角度論述符號互動在個體認知發展的兩種方式:一種是沒有規則的游戲(play),另一種是有規則的游戲(game),兩者都是學習的過程,也是認知不斷從低級向高級形式的過渡,同時也表示兒童主動地、積極地和有意識地學習的過程,這與動物的無意識游戲是完全不同的。在沒有規則的游戲中,兒童會自言自語和扮演他人。兒童的自言自語是對與他人對話的拓展,兒童通過對他人語言的模仿,將這些語言按照自己的方式進行復述,同時將這種語言進行私有化和內化,認知由此得到發展。在扮演他人角色的時候,兒童會通過想象的方式扮演社會中出現的不同的他人模型,但是這種扮演是個人的,并沒有發展出一個角色不同的自我,他(她)就是這個角色。游戲是兒童進行有規則的活動,規則和他人在游戲中起到對兒童的約束性,在與他人游戲的過程中兒童的社會參與能力獲得了極大發展,兒童的行為表現為一種約束性和他性。通過有規則游戲的逐漸發展和完善,這種游戲方式會通過內化的方式深化到兒童的內心,他人更加表現為一般性的和規則性的態度。可以說這在很大程度上將自我進行分裂,表現出了一種他性,認知在這種自我的他性中逐漸提升。認知在游戲中產生和發展,游戲是社會性對認知的滲透,也是兒童通過模仿和積極地學習而達到社會認知的過程(米德,2012:150),游戲是認知提升的實踐場。因此,認知不管是從兒童發展視角,還是與世界以及與他人的交互中,符號互動都是對認知的發展和高階認知產生的方式。
2.5 主我-客我在語言交流中發展認知
米德繼承了詹姆士的多重自我和喬伊斯關于自我和非我的區分,將自我分為主我(I)和客我(me)。主我是有機體對其他人的態度做出的反應,而“客我”則是一個人自己采取的一組有組織的其他人的態度(米德,2012:193-194),兩者都必須與社會互動和符號互動中的經驗相關聯,其中符號互動中的語言交流使得自我的分化成為可能。主我是自我主動的與世界和他人的符號交互,交互的過程是認知產生的過程。但是主我的認知并不是反思的,而是一種無意識的認知過程。與主我同步出現,客我在自我的符號互動中也逐漸凸顯。當自我與世界和他人交互的時候,人們開始嘗試使用他人的視角和目光來反觀自身。隨著符號互動的深入和主我與客我的涌現,自我和客我開始交互和對話,主我和客我進入不斷轉換視角和循環的過程中。在語言交流中“我”作為與“你”相關聯的指稱詞出現在會話中,“我”和“你”的指稱意義出現,“我”的出現要以“你”作為前提條件,而“你”帶著與我不同的他異性使得“我”具有你的特性,我與你會出現指稱的互逆性,因此,“我”就同時具有“我”和“你”的特性,自我分類為主我和客我。主我前進的同時也意味著客我的后退,但是主我始終無法擺脫客我的限制。因為時間的制約,主我會隨時變成客我,同時客我也是主我不斷進取和創造的基礎。主我-客我關系作為個體與世界聯系的方式:主我不斷采取客我的角色,主我不斷地通過客我的方式來沉淀于記憶中,同時主我也不斷地在客我的基礎上來創新和突破自我(Valsiner,2010)。自我內部的對話時刻都在發生,此一時刻的主我就會變成彼一時刻的客我。主我和客我的語言對話使得認知逐漸從社會性向個人性轉移,個人性也更加顯現為社會性,因此,認知的主我-客我的互動是人類高階認知產生和發展的必經之路。按照心智理論的觀點,人類在三歲的時候會出現“心智理論(Theory of Mind)”,心智理論的一個重要意義就在于視角的轉換,正是在這個階段兒童才會具有站在他人的視角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用他人的眼光看自身,同時人類的理解和推理能力得到提升,這其實就是主我和客我的對話和視角的轉換。另外,主我還代表了個人的自由、進取和創造力,而客我代表了社會的制約、限制和傳統,自我總是在這兩種狀態中不斷地徘徊,因此主我可以采取多重視角來進入到客我的場域中,而客我也可以從多層維度來反觀主我。正是由于主我的存在才使得我們無法完全認識自我,但是也正是因為客我的存在,我們才能夠認識主我的可能性和對自我的更深入了解。主我和客我不斷地變化和超越,二者處于一種動態的符號交互之中,認知在這種交互中不斷地發展和變得復雜。因此,我們說認知在不斷進步、完善和提升,這就是人類自我的主我和客我的持續對話和互動。
2.6 符號互動內化統合認知
由于借鑒了馮特的姿態理論,米德提出了他的互動理論,但是互動理論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這些互動都是發生在外部的人類活動,而我們通常認為認知和心靈似乎是在人類身體內部,那么如何實現這種內、外相通則是米德認知思想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米德除了繼承實用主義在本體論上和知識論上反對二元論將認知從人類身體內部排除之外,還吸收了喬伊斯對人際現象中的情緒氛圍的內化思想。米德認為心靈和自我的形成與個人對外部經驗的內化有關,“內化是指人類的認知涌現于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外部社會經驗通過滲入的方式形成內部社會經驗”(Mead,1910)。內化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無意識的內化,一種是有意識的內化,前者主要反映在認知的初級形式,即社會活動互動中。在活動的四個階段:沖動、知覺、操作和完滿,都是在參與主體不自覺地參與到活動的互動中的,參與者通過交互獲得了操作經驗而與他人達到一致,從而將外部活動事件轉化為參與者內部的經驗能力和技巧。有意識的內化是在符號互動中,自我和他人、主我和客我的對話中有意識的內化。主我通過對他人和客我的審查而達到對以往經驗的重新整合,在整合的過程中主我會有意識地模仿他人和認知客我,在這種對話中,關于他人和客我的經驗得到整合和概念化從而實現內化。符號互動內化不僅使得人類的經驗和認知能力得以提升,同時也在不斷地塑造自我,在交際雙方的互動中,通過內化作用將這種互動方式和內容內化于個人經驗中(Mead,1903),從而使得自我逐漸采取他人的眼光來看待自己,主我和客我也會同時顯現,同時人類的互動從外部互動延伸到內部主我-客我的互動,人類的認知也逐漸達到反思的水平。但米德認為內化不是一個被動消極的過程,而是一個積極的自我發展過程,人們通過在符號互動中的表達、反應和模仿從而達到不斷地提高和驗證個人以往經驗。人們在符號互動過程中由于受到規則的約束而不自覺地將規則內化,但是同時自我也會在現有的規則基礎上創造和操縱某些規則。因此,符號互動的內化在認知的產生、發展和提升的各個階段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將認知的各個階段和時間串聯起來,從而達到對認知能力的整合。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發現米德已經擁有了具身認知的基本思想,但是更多地反映了與當前具身認知思想的不同。米德所謂的認知的身體性更加強調與身體活動的統一,它以社會性為背景,在社會互動的前提下,指出認知是一種態度,認知涌現于姿態的互動中,而符號互動是認知發展的高階形式,在人類自我形成和認知統合中起著關鍵作用。米德也強調認知的情境性和邊界性,但是這里的情境是社會性的,也是無法脫離人的符號互動的、帶有人類面紗的情境,認知的邊界不在身體之內也不在身體之外,而是充斥于整個的符號互動中,是一種動態的場。
3 米德互動式具身認知思想的意義
通過對米德的認知思想研究,可以看到具身認知并不能擺脫社會活動對認知的影響。社會性不是一個后來的、強加的認知因素,而是自始至終都滲透于認知之中的成分。因此,對米德的認知思想的深入研究能讓我們認識到當前具身認知研究的不足,同時為認知科學研究指出了社會性轉向的可能,并為具身認知的社會性研究供了理論基礎。
首先,米德的認知思想拓展了認知科學研究的范圍。米德的主要思想是將認知放在整個社會活動中進行考察,強調認知科學研究應該放入到對社會活動(特別是符號互動)的研究之中,不能只停留在物理和生理這樣的固態研究中,更應該關注社會和他人的動態互動研究,才能對認知進行全面和整體性的研究,認知才能回歸到生活的本真狀態,因為“一個物體就是對行為的邀請”(Mead,1972:280)。米德的認知思想使得認知科學研究堅持了兩個連續性:(1)低等生物和高等生物在認知上是連續的,并不是完全隔離開的;(2)低階認知能力和高階認知能力是連續的,我們不能在推理中完全脫離情緒和知覺的作用。米德將傳統認知觀中的認知與對象統一于社會行為中,從而打破了認知的內外之分,同時也克服了認知邊界的內外和延展性問題。出于對笛卡爾內在主義的反對,外在主義強調認知的邊界不限于大腦,克拉克(A. Clark) 和查爾莫斯(D. Chalmers)(1998)認為認知可以擴展到皮膚和顱骨之外,并且將其思想淵源歸結為梅洛·龐蒂對盲人手杖使用的論述。米德對于認知的邊界比梅洛·龐蒂更加深刻,他認為認知的邊界不在大腦、也不在身體之內,認知是非固定地點的、動態的和分散于整個社會過程中的,認知并沒有固定的邊界而是一個場(Mead,1922)。認知在符號互動中得到擴展,如“教育過程就是由這種使社會反應進入個體心靈的過程構成的,它使個體以多少有些抽象的方式接受共同體的文化媒介”(米德,2012:292),即以語言溝通。認知的擴展不是從個人的認知延展到他人之心最后整個的認知成為一個普遍性的、有規則的過程,認知活動一開始就是通過自我與他人的交互,將他性滲入到自身的場域中,因此,認知在自我與他人的交互中產生并逐漸得到深化,從而實現認知向更高級和更復雜的維度提升,認知總是處于一個未完成的和未封閉的狀態。米德的認知思想加深了人們對傳統認知科學研究中的身心二元論和唯我論思想的認識,促使人們逐漸向具身認知社會性研究邁進。
其次,米德的認知思想對當前具身認知研究提供了社會性轉向的可能。具身認知強調認知的情境性、身體性和動態性,否定自笛卡爾以來將認知放入一個孤立的、靜態的實體性自我之中,將認知看作是耦合的身體與世界相互作用的涌現,因此,認知就成了僅僅發生在個人身體上的活動。然而,這種具身認知研究進路并沒有看到真實的認知發生過程。從米德的哲學思想中,我們看到他對笛卡爾思想中的唯我論的強烈批判,他將認知的場域進行擴展,不僅擴展到像杜威這樣的外部情境之中,而且還將社會活動中的各個元素都作為認知發生的必要條件,從而完全否定了笛卡爾關于心靈的自我中心主義思想。米德認為“人之所以為人,就在于人不僅是在身體基因、神經上為人,更在于在經驗、社會行為和主體間性上的人性”(Zlatev,et al., 2012:12)。因此,具身認知具有社會參與性,認知的產生和發展需要有他人的參與和互動,在互動的意義中涌現認知,這也是將隱藏在認知科學研究中的唯我論完全刪除,使得具身認知研究不是建立在一個孤立的自我之中而是在與他人的互動中,而且正是在這種與他人的交往中,認知才能涌現和發展,人類所獨有的認知特點才能凸顯出來,即認知的具身主體間性和符號性。米德同時從共時和歷時兩個角度對心靈的產生、發展和構造進行研究,從而使得具身認知研究進入一個新的維度,為具身認知研究社會性轉向提供了可能。按照米德的觀點,具身認知雖然表面上將先驗自我給消解了,但是又將孤立的身體作為認知的主體,這并沒有完全解決個人主義的問題。米德認為我們需要將自我的心靈融入身體的社會活動和符號互動中,才能認識真正的自我。因此,我們認為米德的認知思想為具身認知研究的社會化提供了理論基礎。米德對認知的社會性和互動性研究,不僅促進了具身認知科學的社會性轉向,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具身認知科學研究的實用主義基礎,實用主義本身就含有現象學所強調的認知的情境性、身體性和動態性等思想成分。具身認知雖然大量引用了現象學的思想,但是并不是完全擺脫了英美哲學而轉向現象學,而是在英美哲學基礎上吸收現象學,這與詹姆士、杜威和米德等人的實用主義思想有極大關系。
最后,米德認知思想的研究重新確定了米德在西方哲學研究中的重要性。米德的認知思想不僅使得實用主義的研究從對自然情境的關注轉向社會互動,“使得自我意識的研究以社會性為起點,從而擺脫了西方的個人中心主義”(Carpendale et al.,2011)。米德在分析人類心靈和思維時,創造性地提出了思維是一種姿態對話和符號互動,互動的雙方是自我與他人、主我與客我的溝通,通過自我與他人的互動來衍生出主我與客我的符號溝通,不僅使得人們擺脫了自我作為哲學研究的絕對中心的觀點,而且還從生成的角度展現自我與他人、認知與符號互動是無法分離的部分。米德并沒有否定自我,其目的是要指出心靈不能被刪除,無心之身的存在并非人類,也不能將心靈還原為物質的或者亞人層面。自我絕不是心靈的起點,而是身體在與世界和他人互動時所表現出的自性。由于自我同時具有主我和客我的兩個方面,米德將自我放在一個與他人在符號互動中相同的地位,這就使得西方哲學研究的中心發生了轉移,從自我中心主義到符號互動中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既是一個自我也是一個他人,因此自我既有自性又有他性。米德還指出人類的反思、推理等高級認知能力與自我和他人、主我和客我之間的符號互動無法分開,都是在語言的互動中涌現,因此就將認知和自我的研究推向了語言研究,這也為西方哲學的語言轉向提供了思想基礎。可以說米德的哲學思想推進了西方哲學的研究和轉向,同時與后期胡塞爾、海德格爾、梅洛·龐蒂等大陸現象學家的思想有很大的相通性。
參考文獻:
Anderson, M. L. 2003. Embodied Cognition: A Field Guide [J].ArtificialIntelligence(1): 91-130.
Booth, K. J. George H. Mead. 2013. Embodied Mind and the Mimetic Basis for Taking the Role of the Other[G]∥ Hrsg. Tom Burke.GeorgeH.MeadintheTwenty-firstCentury. Lanham:Lexington Books, 137-148.
Bredo, E. 1994. Reconstructing Educational Psychology: Situated Cognition and Deweyian Pragmatism.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J].EducationalPsychologist, 29(1): 23-35.
Carpendale, J. & T. P. Racine. 2011 . Intersubjectivity and Egocentrism: Insights from the Relational Perspectives of Piaget, Mead, and Wittgenstein [J].NewIdeasinPsychology(29): 346-354.
Clark, A.& D. Chalmers. 1998. The Extended Mind[J].Analysis, 58(1): 7-19.
Clark, A. 2008.SupersizingtheMind:Embodiment,ActionandCognitiveExtens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4.
Gallagher, S.2009. Philosophical Antecedents to Situated Cognition [G]∥ Robbins, P. & M. Aydede.CambridgeHandbookofSituatedCogn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35-53.
Gallagher, S. & S.Varga.2015. Conceptual Issues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J].CurrentOpinionPsychiatry(28):127-132.
Hutchins, E. & C. M. Johnson. 2009. Modeling the Emergence of Language as An Embodied Collective Cognitive Activity [J].TopicsinCognitiveScience(3): 523-546.
Hutchins, E. 2010. Cognitive Ecology[J].TopicsinCognitiveScience(2): 705-715.
Madzia, R. 2013. Mead and Self-embodiment: Imitation, Simul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Taking the Attitude of the Other[J]. ?sterreichischezeitschriftfürsoziologie, 38(1):195-213.
Marková, I. 1987.HumanAwareness:ItsSocialDevelopment[M]. London, UK: Hutchinson,104.
Mead, G. H. 1903. The Definition of the Psychical[J].DecennialPublicationsofthePniversityofChicago, 3 (1):77-112.
Mead, G. H. 1910. What Social Objects Must Psychology Presuppose?[J].Journalofpsychology(7): 174-180.
Mead, G. H. 1922. Behavioristic Account of the Significant Symbol [J].TheJournalofPhilosophy(19): 157-163.
Mead, G. H. 1925. The Genesis of the Self and Social Control[J].InternationalJournalofEthics(3): 251-277.
Mead, G. H. 1932.ThePhilosophyofthePresent[M]. London: The Open Court Company Publishers 90.
Mead, G. H. 1964.SelectedWritings:GeorgeHerbertMead[G]∥ A. J. Reck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ad, G. H. 1972.ThePhilosophyoftheAct[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ead, G. H. 1982.TheIndividualandtheSocialSelf[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izzolatti, G. & C. Sinigaglia. 2008.MirrorsintheBrain:HowOurMindsShareActions,Emotions,andExperienc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ore, B. 1996.CultureinMind:Cognition,Culture,andtheProblemofMeaning[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alsiner, J. & R.V. D. Veer. 2010. On the Social Nature of Human Cognition: An Analysis of the Shared Intellectual Roots of George Herbert Mead and Lev Vygotsky[J].JournalfortheTheoryofSocialbehaviour, 18(1): 117-136.
Wilson, M. 2002. Six Views of Embodied Cognition [J].PsychonomicBulletin&Review, 9(4): 625-636.
Zlatev, J. 2007. Embodiment, Language and Mimesis[G]∥ Ziemke,T., Zlatev, J. & R. Franck.Body,Language,Mind.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97-337.
Zlatev, et al. 2012. Intersubjectivity: What Makes Us Human?[G]∥Zlatev, J., Racine, T P., Sinha, C. & Itkonen, E.TheSharedMind:PerspectivesonIntersubjectivity.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16.
常照強, 張愛民, 魏屹東.2013. 心靈科學的重構: 尋找缺失的意義期[J]. 科學技術哲學研究 (5): 62-66.
崔中良, 王慧莉. 2016. 后期維特根斯坦具身認知思想研究[J]. 科學技術哲學研究 (6): 34-38.
孟偉. 2015. 身體、情境與認知——涉身認知及其哲學探索[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喬治·H.米德. 2012. 心靈、自我和社會[M]. 霍桂桓,譯,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張積家, 馬利軍.2013.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身認知思想及其價值[J]. 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5): 93-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