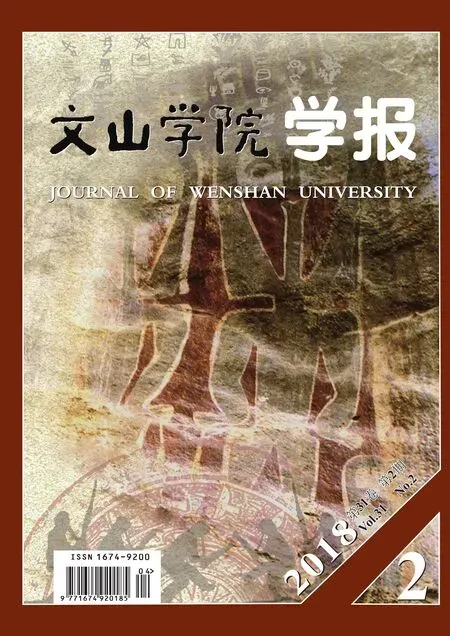劉紹棠運河文學中的政治與非政治狀態下的寫作
馬琳娜
(云南師范大學 文學院,云南 昆明650500)
一、作家劉紹棠的生平
劉紹棠1936年出生在北京通州的儒林村,13歲開始發表作品,是50年代中國文壇上的“神童作家”。劉紹棠是一個多產作家,在他近五十年的創作生涯中,共創作了14部長篇小說,27部中篇小說,上百部短篇小說。其中僅有一篇是描寫大學生的,其余全部是描寫北方運河岸邊的田園生活。在其描寫田園風光和充滿人物性情的作品中,我們看到了“運河之子”劉紹棠對故土的熱愛和對家鄉父老恩情的感激。劉紹棠出生的通州,就是那三千里京杭大運河的北端起點。“通州在府東45里……通州上拱京闕,下控天津。潞、渾二水夾會于東南,幽燕諸山雄峙于西北。舟車輻輳,冠蓋交馳,實畿輔之襟喉,水陸之要會也。”
劉紹棠的成長經歷跟“運河”有著深深的聯系。他的父親在北京的布店當學徒,像個文雅商人。劉紹棠是家里的長子且是個蒲柳人家的子弟。劉紹棠曾多次說過,在他有生之年曾有三十多年是在農村度過的,而且就是在他的家鄉大運河兩岸。他曾說:“我是一個土著作家,只能寫些土氣的作品。”他還說過:“我喜歡農村的大自然景色,我喜歡農村的泥土芬芳,我喜歡農村的寧靜和空氣清新,我更熱愛對我情深義重的父老鄉親和兄弟姐妹們。”[1]1他的作品表現了京東運河平原不同歷史時期的風土人情和社會風貌,向讀者熱情地展示了他的家鄉——運河邊上的鄉風水色及人情百態。
二、政治背景下對傳統美學的追求和政治解構
從劉紹棠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誠摯的情感,謳歌社會主義進步的人和事,雖然有些作品有概念化的弊病,在抒情寫景時突然把改革政策和政治概念插入作品中,使得作品有概念化和突兀的感覺,打上了政治意識形態的烙印。在《蓮房村人》中一個外號姜夠本兒的人,“自從他呱呱墜地的那一天,他就沒有守過本分。身為農家子弟卻是個游手好閑的耍貨”[2]。姜夠本兒是倒賣西瓜的個體戶,在文中確實對他的評價很低,“他是個體戶”“走私販子!”在文中利用政治意識形態來簡單地評價一個人物是有偏頗的。劉紹棠的有些作品是政治運作下的產物,被很多批評家視為“某種政治表態”,因此對劉紹棠的作品分析僅僅停留在政治話語運作方式。這是一種對話語專制系統的批判和拒絕,具有相當深刻的意義,“他不僅提供了政治立場而且提供了歷史的立場”[3]。但是從另外一方面來講,這種批評有很大的局限性,容易單方面的流于貶斥,簡單地對作家作品下結論,沒有深入地分析文本中的意義和價值。福柯的“話語”概念就是被常常抽象化成一個功能結構或一種壓迫和統治機制進行批判。福柯的權威形象成為批判者的“話語”庇護。在對劉紹棠小說研究中,我們發現在政治化的傾向中,有非政治化的運作,這就可以把他小說放在一個更復雜的視野和背景上來討論,從另一個角度探究作家作品中的復雜性,而不是簡單的看待。我們也可以這樣認為,劉紹棠的作品也具有時代的烙印,他的作品帶有比較濃重的政治功利性,這種文化形式既區別于純粹的傳統文化,又有傳統文化的影子。他的作品有別于“原生的民間文藝形式和意識形態”,但是作為文化產品又具有明顯的“本土化”“大眾化”的特點。這樣的作品并非全部來自于農村生活,也受到國外作家如肖霍洛夫的現實主義影響。劉紹棠也認為藝術就應該來源于生活,忠實的表現生活。《虎頭牌坊》就是真人真事改編的,作家力求還原最真實最有生命力的生活的作品。劉紹棠比較成功的作品中時代背景只是作為一個側面,多數描繪的是在時代背景下“家鄉的新人新事,家鄉的可歌可泣的歷史,寫父老鄉親兄弟姐妹們的多情重義,寫‘我的’家鄉那豐富多彩而又別具一格的風土人情”[4]。在非政治下有政治性的運作,正因為有了非政治性的元素融入才能超越政治性的局限。但是非政治也和政治保持著密切的聯系,相互滲透相互妥協。
(一)民間道德審美規范融入政治主題
例如在《蒲柳人家》中,作品政治化傾向只是作品中的一個意識形態的背景。文章開頭描寫了充滿平靜生活的一幕,何滿子是個六歲可愛的小娃娃,因為貪玩愛撒野被爺爺用栓賊扣拴在葡萄架的立柱上,何滿子的奶奶一丈青大娘和她的老頭子“何大學問”吵架,從大人們只言片語中何滿子知道爺爺在口外有一個相好的年輕奶奶。爺爺平常不和奶奶頂嘴吵架,但是這次卻理直氣壯起來。何滿子心里盤算著,他也想和爺爺去口外,覺得那個年輕的奶奶也一定會疼他,疼他的人越多越好。何滿子被爺爺栓在葡萄立柱上覺得不自由,希望她的救星趕快到來。他的救星就是望日蓮姑姑。鄰居望日蓮是個勤快善良的姑娘,跟何家關系密切,她是隔壁杜家的童養媳,經常帶著何滿子去河灘割草。她像疼愛自己的子侄一樣疼愛何滿子。作者把民間生活秩序的和諧理想首先呈現在讀者的眼前。
與這種和諧理想的場面相對的是杜家,杜家還沒出場作者就從介紹望日蓮開始著筆,從側面描寫杜家為人刻薄、心術不正。望日蓮是杜家的童養媳,“可憐兒來到杜家,一年到頭天蒙蒙亮就起,燒火做飯、提水、喂豬、紡紗、織布、挖野菜、打青柴”,從早忙到晚。但是“夜晚在月光下還要織席編簍子,一打盹兒就要挨她婆婆豆葉黃的笤帚疙瘩,身上常被擰的青一塊紫一塊”[5]。杜家還沒出場,從對待望日蓮就知道杜家代表民間秩序的破壞者,破壞民間的和諧秩序。杜家的每一次出場都是平靜生活的反動者,破壞一切美好的事物。在之后的出場中,杜家兩口子各懷鬼胎,杜家的兒子被奉軍抓伕一去不回頭,何家想為望日蓮出頭另找婆家,但是花鞋杜四垂涎望日蓮很久,一直想把兒媳婦望日蓮占為己有,動起了亂倫的賊心。他老婆豆葉黃想利用望日蓮當做招蜂引蝶的幌子。杜家在一開始的行為就是反民間秩序,亂倫、欺壓童養媳、破壞望日蓮和周檎的婚姻。杜家在成為政治敵人之前早就成為了民間倫理秩序的破壞者,是擾亂和諧的罪魁禍首。所以在下文的政治斗爭中能激起對杜家人的憎恨。在劉紹棠隨后的小說中出現了政治的因素也是把矛頭指向杜家,民間秩序破壞者同時也是政治上的敵人。杜老四這個類型化的人物對民間社會的基本單位——家庭和其延續機制進行破壞,是農村和諧秩序的破壞者,當成為政治的對立面時,更容易激發讀者對他的憎恨。在最后的結局中杜四被制伏,因為給他撐腰的雷麻子已經溺斃身亡,這個村子又恢復了以往的平靜,周檎和望日蓮結為夫婦,播下了革命的火種。在劉紹棠的作品中,政治力量不過是民間道德秩序及民間美學的外衣。在外衣的隱藏下作者發揮自己的長處描寫貼近生活的人和事,才能更深地打動讀者,激發讀者對小說的情感共鳴。
(二)民間道德秩序對政治意識形態的妥協
在《蒲柳人家》中,一個以一個非政治性展開的故事在最后的結局中加上了一個政治性的結尾。杜四和雷麻子商量,自治政府警察廳下來一個十萬火急的公文,懸賞緝拿京東共產黨頭子周文彬,賞金五百塊大洋。他們為此打起了壞主意,卻被墻外的何滿子聽到,回頭告訴周檎這兩個人想抓住周文彬,還要把周檎的心上人賣給董太師。周檎和村民布置好陷阱殺了雷麻子,又打消了狗頭軍師杜四的囂張氣焰,預示著新生力量的勝利和壯大。這樣的模式代表了大眾意識形態,也為新的政治力量做了宣傳的作用。政治和文學兩者相互滲透。類似的作品還有《瓜棚柳下》《地火》。
三、非政治化運作中的地域文學
“地域文學”,又稱為“文學地域主義”,是十九世紀后期到二十世紀初期在美國風行一時的文類。廣義的地域文學即“帶有異域風情的文學,這種文學往往被融進了具體地域的精神、風貌、人文氣息”。狹義的“地域文學”具有多種解釋。廣義的“地域文學”與“地方色彩文學”容易混淆。那什么是“地域文學”與“地方色彩文學”呢?在《美國女性地域作家:1850—1910諾頓文選》中給出了這樣的解釋:“地方色彩文學的敘述者是外來人,以居高臨下的姿態描寫當地的人和事。而地域文學則是以平等的姿態從當地內部角度來描寫,反映地方人文環境,目的是獲得讀者的認同和接受。”“地域文學的特質就是要求地域文學作品的作者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但不可以是旅行家。對于地域文學中的本土作者和第二故鄉作者而言,他們賴以寄存的是血濃于水的故鄉記憶、情感記憶以及文化記憶,將這些記憶符號運用在文學作品中,可以增加地域特色。”[6]
劉紹棠正是這樣一個作家,他扎根本土,人生的青少年時期和成年后被打為“右派”時期都生活在他的家鄉,所以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描寫家鄉的運河灘上發生的故事,用自己的創作回報故鄉,把對故鄉運河的愛凝聚筆端,運河猶如一個烙印深深地印在作者的心里。他向我們描繪了一幅二十世紀的家鄉人文風俗。當然劉紹棠的創作受到了個人人生經驗的影響,剛剛從農村出來到北京沒多久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又回到家鄉。剛剛成為了一個城市文人,因為政治的原因又重回到地方,使他重新收集和創作。知識分子和農民之間的緊密接觸促進了地域文化傳統之間的交換和轉型。在當時的社會政治背景下,劉紹棠描繪農民的生活狀態和思想情感,地域文化是他小說的突出特點。同時,濃厚的地域范圍、方言俚語、鄉土氣息現在讀來也不失其色彩和原味。
四、劉紹棠地域文學在作品中的體現
劉紹棠的小說喜歡在政治生活外衣下描寫大運河如畫的風景,鄰里之間和諧共處的生活,充滿了童趣和理想,作品散發著清新明朗樂觀的風格。劉紹棠從小就受到傳統文化的熏陶從而喜歡聽書,大學期間還曾逃課去聽書,對傳統的藝術有很濃厚的興趣。他曾回憶到“事過半個多世紀,我閉上眼睛還能看見,一個頭上腳下一絲不掛的小男孩,嘴里啃著黑紫色的窩頭追在說書人身后,跟唱聽書”[1]49。他對家鄉父老一直懷揣著最真摯的熱情,熱情地去謳歌家鄉的人和事,這跟他的人生經歷有關。劉紹棠的整個童年在兵荒馬亂的抗日戰爭中長大,從小接受黨的教育和領導,受到父老鄉親的關愛。劉紹棠4歲那年,北運河鬧土匪,有一回土匪三更半夜進村綁票,全家逃散,還是一名叫大腳李二的大伯爬墻上房,下到院里走進屋去,帶他脫離險境。5歲那年因為他貪玩偷偷溜出門外捉鳥,一腳踏空,掉進水里,失去知覺,幸虧老叔正在放牛看到了他,才得以不死。6歲時他在田間追野兔摔倒后被茬子扎傷喉嚨,是一位姓趙的老爺子給他急救。7歲那年他得了癰疽,一位姓田的老爺子找來偏方妙手回春。劉紹棠經歷了1957年和十年內亂兩次厄運,他完全可以像其他作家那樣把兩段生活反映出來,但是他從小經歷過土匪搶劫和日本侵略華北平原的動蕩生活,是同共產黨一起成長起來的忠誠黨員,他堅信用自己的理想和希望貼近人民最真實的生活和思想來描寫親愛的故鄉大運河。他筆下的故鄉有這樣的幾個特點:
(一)和諧理想的運河景致和田園風光
劉紹棠對運河有著特殊的情懷,這使他的作品具有獨特的審美意蘊。在作家筆下的運河是這樣的,“一出北京城圈兒,直到四十里外的北運河”“北運河一出北京的通縣縣境,到河北省的香河縣串了個門兒,拐個彎進去天津市的武清縣,卻又從河北省的安次縣擦身而過,一條河把三個省市的四個縣栓在了一堆兒。跟北運河并肩而行的是京津公路,水旱兩路像親哥倆”“通縣自古就是京東首邑,元、明、清三代,大運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動脈”[7]。可以看出作者對自己的故鄉是帶著自豪和欣賞,作為“運河之子”,大部分都在寫大運河,從地理環境和其歷史意義來講述這片故土。“大運河”這片土地上包含著自然地理文化和社會環境文化兩種,自然地理文化是指地理位置、地形特征以及氣候等因素在與人類相互作用的過程中所形成的人化的自然;社會環境文化包括民族、民風、政治經濟等人在社會活動中所產生的種種精神和物質的成果。“大運河”對作者的影響是多方位的,而且地域對文學的影響,實際上通過區域文化這個中間環節而起作用。即使自然環境,也是逐漸與本區域的人文因素緊密聯結。所以劉紹棠小說的地理環境、人文環境、社會生活相互滲透、相互融合。在這樣一個美麗的地方,滲透著作者的熱愛之情,這樣的運河養育了一群民風淳樸的人。“十八里運河灘,像一張碧水荷葉;荷葉上閃爍一顆晶瑩的露珠,那邊是名叫柳巷的小小村落……村外河邊一片瓜園……瓜園里,坐北朝南,柳梢青和女兒柳葉眉埋下八根柳樁立柱離地三尺支起兩件瓜棚,也叫瓜樓。”在這樣充滿鄉村田園的景致中有一個瓜農柳梢青,“早已人過四十天過午,年交五十知天命了。瘦骨嶙峋的大高個兒,大步流星的兩條鷺鷥長腿,刻滿深深皺紋的瓦刀臉……”他會種瓜還會武藝,“十歲那年也是在巴掌大的瓜園里,他爬上一棵老龍腰河柳。運河上,客運和貨運大船,高高的桅桿扯滿了白帆,好似行云流水”[8]。這里把大運河的景色和柳梢青這個人物融入其中,把自然地理和人文環境相結合,給我們呈現了一個和諧溫馨的田園景色。
(二)農耕文明和牧歌生活的抒寫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鄉村人口占據了國家人口的絕大多數,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曾長期在整個社會經濟結構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雖然這些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已有所變化,但中國社會的鄉土性并沒有大的改變,加之現代意義的城市在二十世紀初才剛剛誕生,因此中國的民族文化心理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鄉土文化之上的,具有較強的鄉土性。鄉土性的社會結構和鄉土性的文化心理,造就了許多人尤其是遠離故園鄉土的人們的特有的鄉土情結,作家也概不例外。”[9]劉紹棠在病重之時還想回到家鄉的土地上進入小說里描寫的許多情景中。他在病重時更加懷念故鄉,他是故鄉的崇拜者,想念自己的父老鄉親。二十年來在運河灘上,跟父老鄉親一起土里刨食,后來少年得意一帆風順的到北京讀了大學成為城里人,雖然也會下鄉體驗生活,但是就像作者說的“不過是水上的浮萍菜湯里的油”。劉紹棠就像希臘神話中的安泰俄斯(Antaeus)只有貼近大地才能獲取源源不斷的力量。對作家而言,運河灘就是創作的源泉。在作家看來,體驗生活和真正的融入生活兩者的感受有很大不同。只有真正的融入才能描寫出更感人的作品。所以在五七年又重新回到運河,家鄉父老對他的愛護,成年后更能深刻體會周圍的生活。對劉紹棠而言,那段時期的歲月坎坷與他個人的得失相比,是得大于失的。他認為“在農民身上,盡管存在著小生產者的種種缺點,但是更具有勞動人民的純樸美德,保持著我們偉大民族的許多優良傳統”。又因為“在我遭遇坎坷的漫長歲月中,家鄉的農民不但對我不加白眼,而且盡心盡力地給以愛護和救助;人人在劫難逃的十年,我獨逍遙網外,并且寫出了作品”。在《瓜棚柳巷》中柳梢青和女兒柳葉眉在十八里運河灘的柳巷村外的河邊有自己的一片瓜園,父女倆相依為命住在瓜棚里,別看是個小瓜棚,后窗外垂柳依依,掛起一幅飄動的柳簾。瓜棚下有青柴,灶臺輕煙渺渺,鍋臺上擺放著紅土瓦盆、貓耳綠罐、青葫蘆瓜瓢、藍花飯碗、大肚兒鹽缸……這樣寧靜的田園生活雖然清苦卻充滿了溫馨的氛圍,一片片的綠色映入讀者的眼里和心里,清新明朗的空氣在蔓延,是牧歌似的生活和理想。柳梢青是個種瓜的好手,每到栽瓜點豆時節他的瓜園充滿了撲鼻的香氣。劉紹棠善于寫傳奇故事,也帶有牧歌色彩,結局都是充滿著理想和希望。
(三)熟練優美的鄉間俚語
語言是文學的第一要素。劉紹棠在描寫農村的風土人情鄉間景物的同時,更注重家鄉俚語的運用。他不但在人物對話上使用農民口語,而且在敘事上也盡量使用地方口語,使作品具有突出的地域特色的語言、生動活潑的人物性格和濃郁的生活氣息,克服了同類小說常見的語言分裂。在劉紹棠的作品中運用地域性的鄉間俚語并不是像《暴風驟雨》那樣僅僅是描寫農民時才用,這樣只是在形式上的模仿,其他的敘述仍然是知識分子的話語系統。而劉紹棠雖然也是知識分子但是他描寫的是最熟悉的家鄉,所以對方言俚語比較熟悉,在其他敘述時也盡量用地方的語言去描繪,不會讓作品整體有割裂的感覺。這點對于劉紹棠也并非難事,他前后在農村生活了三十年,自幼習慣講方言土語,有深深的戀鄉情結。民族和地域的因素對于作家的寫作自然緊密相聯。作家在創作時,依然與充滿生機活力的生活保持著近距離的關系。這正是作家劉紹棠具有的地域優勢,由于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特殊位置形成了與周圍事物的反差,在反差中得到新的認同和接納就需要尋求一個共同的環境,那就是劉紹棠筆下的政治環境引入小說創作。這樣就具備了廣泛的傳播與推廣。他對家鄉的土語和鄉間俚語具有高度的認同和接納,認為是“最生動活潑,富有詩情畫意。農民口語的最大特點一個是具體,一個是形象。使人看得見摸得著”[10]。在《荇水荷風》中,形容爺爺耳聾嚴重,“炒豆子似的連天響也不眨一眨眼”。形容剛正不阿的人是“桑木扁擔寧折不彎”。在《瓜棚柳巷》中形容花三春尖叫是“貓爪了似的尖叫,鳳凰落地不如雞”,語言形象生動活潑,可以想到花三春是個烈火心性,刁蠻不吃虧的潑辣女人。這樣的語言在劉紹棠小說中舉不勝數。這些口語具有突出的地方色彩,具體生動活潑,運用自如,不露痕跡。在對具有地域特點的鄉間俚語的吸收過程中,劉紹棠并非全盤接受,而是棄其糟粕取其精華,民間鄉間土語有著藏污納垢的特點,但是作家摒除糟粕對其進行古典的改造,才使得作品具備更多的美學特征。
劉紹棠在文學創作中的政治與非政治狀態中,并沒有因為政治性掩蓋了他的作品,相反在非政治中加入了地域性的因素,使得作品具有超越性、大眾性、民間審美性。
[1] 劉紹棠.我是劉紹棠[M].北京:團結出版社,1996.
[2] 劉紹棠.蓮房村人[A]//劉紹棠中篇小說集[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267.
[3] 孟悅.《白毛女》演變的啟示兼論延安文藝的歷史多質性[M]//再解讀大眾文藝與意識形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51.
[4] 劉紹棠.蒲柳人家二三事[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98.
[5] 劉紹棠.蒲柳人家[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6.
[6] 姚斌潔.地域文學的審美審視與反思[J].沈陽:沈陽工程學院學報,2016(1):80-84.
[7] 劉紹棠.京門臉子[M].廣州:花城出版社,1991:39.
[8] 劉紹棠.瓜棚柳巷[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7:3.
[9] 費孝通.鄉土中國[M].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社,2013:29.
[10]劉紹棠.鄉土文學四十年[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