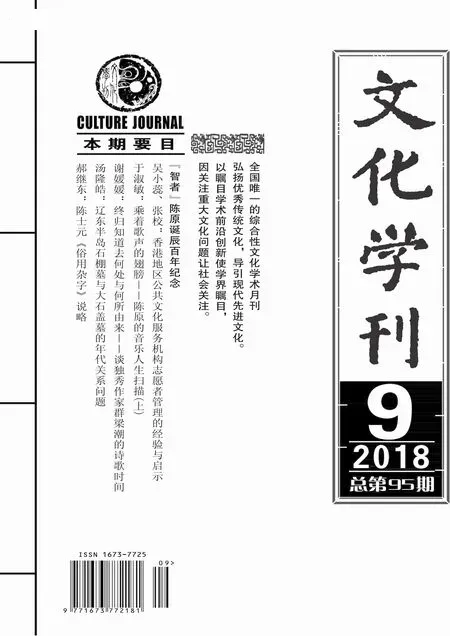“禮”與“仁”視角下孔子的鬼神觀探析
南俊琪
(川北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語言文學系,四川 廣元 628017)
作為中國儒家文化的經典,《論語》中最讓人迷惑和最具爭議的問題莫過于對鬼神的論述。通常情況下,人們會根據“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1]及“子不語怪、力、亂、神”[2]來判斷孔子是不相信鬼神的,依據“未知生,焉知死?”[3]來認定孔子只言人事,否定人死為鬼,甚至有學者由此推斷認為孔子是唯物主義的思想家。那么,孔子真的不相信鬼神嗎?孔子是一位唯物主義者嗎?他的鬼神觀到底是如何的呢?這些問題只有仔細解讀《論語》及孔子生活的時代的思想文化,才能給予一個較為清晰的闡釋。
一、《論語》中鬼神言論的解讀
如前所述,如果僅僅依靠《論語》中“敬鬼神而遠之”“子不語怪、力、亂、神”等就斷定說孔子不相信鬼神,似乎是個武斷的做法。通讀《論語》,細心的讀者會發現,《論語》中有很多關于鬼神的論述都顯示出孔子是相信鬼神的。以下舉例說明。
第一,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4]此句中的“鬼”,既可指鬼神,也可指已經亡故的靈魂。由這句可以看出,孔子并不是不相信鬼神,相反,他相信鬼神并強調人們要按照規范的禮儀來祭祀鬼神。如若孔子不相信鬼神,那么他所言說的祭祀又有何意義。
第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5]表明孔子是非常重視鬼神及祖先祭祀的,而且他特別強調祭祀時內心要虔誠。
第三,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禱久矣。”[6]對于這一句,學界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認為孔子生病向神靈禱告,說明他非常迷信天地鬼神;也有人認為孔子向神靈禱告很久了,但病情未見好轉,說明他對鬼神持有懷疑態度。但筆者認為,從最后一句“丘之禱久矣”可以看出,孔子向鬼神祈禱的事實是存在的,不管這種禱告有沒有結果。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對于鬼神祭祀之事并非是全盤否定和排斥的。
第四,“耕牛為之骍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7]從這一句中可以看出,孔子一方面相信有山川之神的存在,另一方面,他也十分重視祭祀時所用的祭品,認為要用長著紅毛、牛角整齊的牛犢來祭祀,才會獲得山川之神的護佑,給人民帶來福祉。
通過上述對《論語》中涉及鬼神祭祀言論的分析,可以看出孔子并不是不相信鬼神,對祖先神靈及鬼神祭祀也不是完全反對的。相反,他認為鬼神祭祀時要親祭,要虔誠,并強調鬼神祭祀要按照“禮”的規范來進行,才有可能給人們帶來福祉。由此可知,孔子是相信鬼神的。那么我們又該如何去理解和看待這個問題呢?
二、鬼神祭祀與“禮”
要更好地理解孔子的鬼神觀,必須從孔子所處時代的社會制度、思想文化觀念入手。一般認為,孔子所處的時代在春秋末期,這一時期正是原始氏族社會的宗法制向地域國家制過渡的時期。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周王室為核心的氏族統治體系開始松動,原始的公社共同體的社會結構逐漸瓦解。周天子雖然保有天下共主的權威,然而卻是名存實亡,對于當時的政治局面并沒有實際的操控能力,許多當時的貴族都拋開周室陳規,以經營商業、土地兼并為基礎,迅速成為新興階層并富裕壯大,“壞井田,開阡陌……王制遂滅,僭差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萬”[8]。經濟上的強大使他們有了政治上的奪權野心,在軍事上不遺余力地發展壯大自己,開始了連綿不斷的土地兼并戰爭,最終導致沿襲氏族部落聯盟體系建立起來的周王室統治制度的土崩瓦解。“周室衰”“王制滅”“禮法墮”成為當時社會的真實寫照,完全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而孔子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大動蕩、大變革的歷史時期。
站在時代的轉折點上,面對諸侯戰爭、社會混亂、禮崩樂壞的社會局面,孔子主張維護沒落的氏族貴族的利益,他以一種保守的姿態極力保衛和恢復“周禮”。所謂“周禮”,主要指在周代初期確定的維護氏族統治體系的一整套典章、制度、規范、禮儀等。“周禮”產生于殷周時期的宗法體制中,它最大的特點就是有明確而嚴格的上下等級、長幼尊卑的秩序規定。而從起源上來說,“周禮”是在原始巫術禮儀的基礎上產生的,作為原始禮儀,在當時社會生活和政治活動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可以組織和團結氏族成員進行生產和生活,進而維護整個社會的安定和諧。《荀子·禮論》記載:“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9]由此可見,在當時的社會狀況下,“禮”對于先民的生存發展、團結聚居,以及國家治理、社會穩定等方面的重要性。
依據先秦典籍《禮記》的記載,“周禮”名目繁多,內容龐雜,然而,“其起源和其核心則是尊敬和祭祀祖先”[10]。究其原因,就是由于祭禮在原始禮儀的形成過程中具有原初性和本源性的意義,而“周禮”就是將以鬼神先祖祭祀為核心的原始禮儀加以系統化的改造和擴展,從而形成了一整套適合于周代宗法制統治需求的制度規范。《禮記·祭統》言:“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禮;禮有五經,莫重于祭。”[11]對于包括天地、鬼神、祖先在內的祭禮在整個“周禮”中的作用及地位,生活在周代末期的孔子肯定有非常明確的認識,所以《論語·堯曰》云:“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12]可以看出,孔子將喪禮、祭禮與人心的向背、人民的溫飽、國家的興亡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這也就充分說明了為什么在《論語》中孔子要反反復復談及關于天地鬼神及祖先祭祀。
既然孔子力圖要維護周代上下有別、長幼尊卑有序的等級觀念,那就不得不重視和恢復“周禮”,而要恢復“周禮”,自然繞不開涉及鬼神及祖先祭祀的祭禮。所以,從維護和恢復“周禮”的目的性來看待孔子的鬼神觀念,或許就更容易理解孔子鬼神觀的真實面目。在《論語》中,孔子不止一次地強調鬼神祭祀時要按照“禮”的規范和要求進行,對各種僭越等級和違背禮制的祭祀活動深惡痛絕。《論語·八佾》云:“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13]這里,孔子對魯國當政者違背祭禮的做法及越禮犯上的行為極為憤慨。還有《論語·八佾》:“季氏旅于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14]泰山祭祀是天子的專權,而季孫氏只是魯國的大夫,按照周禮的規定,季孫氏是無權祭祀泰山的,但他竟然違背“禮”的規定執意祭祀,孔子認為這是一種“僭禮”行為,所以對其進行了嚴厲的批判。由是觀之,《論語》中孔子鬼神言論的矛盾性也就不足為怪了。在筆者看來,孔子信不信鬼神的存在其實并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在于孔子是以鬼神祭祀的言說來說明“禮”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通過鬼神祭祀來維護“周禮”。也就是說,事鬼神要以“禮”的規范為準則,在《論語·為政》篇五中,樊遲問孔子何謂禮,孔子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15]在孔子看來,無論是生時事人事或是死時事鬼神都要遵循禮的規范和約束。
三、鬼神祭祀與“仁”
孔子思想的兩大核心是“禮”與“仁”,“禮”是外在的行為規范,“仁”是內在的道德追求,“仁”為“禮”提供心理基礎,“禮”為“仁”規定行為節度,二者相互統一,融為一體。孔子言:“克己復禮為仁”,這個“禮”自然也包括在孔子看來極為重要的祭禮。細究來看,孔子一方面將鬼神祭祀看作恢復周禮的一個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孔子又將鬼神祭祀視為達到人倫教化,使“民心歸于仁厚”的重要方式,通過祭祀祖先神靈,來維持和肯定他所設想的等級秩序、倫理綱常以及社會穩定的人文理想,這才應是孔子鬼神觀的核心所在。《論語·學而》中曾子言:“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16],人死為終,所言喪禮,遠指祖先,所言祭禮,朱熹注:“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于厚……故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于厚也。”孔子在這里所言說的喪禮、祭禮都是在講要為現世的人事服務。在孔子看來,喪禮、祭禮不單是一種宗教活動,它還肩負著更重要的使命,即通過喪祭之禮的儀式活動寄托和培養人們對父母及祖先的情感,要讓人們記住父母祖先的良好品德,從而撫慰在世者,凝聚人心,激發人們為現世的生活而努力,由此可見,孔子對鬼神祭祀的重視,并非是要將人們引向虛無縹緲、神秘不可知的彼岸世界,相反,是要人們關注現世人生,關注此岸世界的道德倫常。而依照儒家關于“忠”與“孝”的觀念,“孝”是“忠”的基礎,一個人若能夠對父母祖先做到“慎終追遠”,那么他肯定就是一個孝子,而孝子是不可能不為國盡忠的。同時,孔子對統治階層實施祭禮也提出了一定的希望和要求,《論語·泰伯》中言:“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黼冕。”[17]孔子對于禹的祭祀行為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禹作為執政者的榜樣,生活簡樸,祭祀時也表現出謹慎、虔誠的態度,是值得贊揚的。在孔子看來,一個國君只要能行虔敬的祭禮,以廣大的德行和仁政教化人民,從而達到上行下效、化育人民的效果,民德自然會變得敦厚。這樣一來,孔子就將鬼神祭祀的活動內化為了一種關于道德、倫常的“仁”的追求,把本是宗教的鬼神及先祖的祭祀活動轉化成了一種不需服從于神的個體的人格自覺、道德完善與社會政治理想,這與春秋時代的宗法政治觀念相適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用道德教化引導人民,用禮制規范人們的言行,使人民有羞惡廉恥之心,民心自然歸于仁厚,政治自然清明,那么,家庭、社會及國家就可以得到安定,進而實現孔子治國理政的目標和理想。
李澤厚先生指出,儒家并未將現實人生的情感寄托與心理期盼引向外在的神靈崇拜和神秘境地,而是將其消融和內化在以親緣關系為主的人與人之間的世俗關系中,從而使“構成宗教三要素的觀念、情感和儀式統統環繞和沉浸在這一世俗倫常和日常心理的綜合統一體中,而不必去建立另外的神學信仰大廈”[18]。這一評價一針見血地道明了孔子鬼神觀念的核心指向。由此,關于孔子鬼神觀念的許多問題也便迎刃而解。實際上,孔子的鬼神觀是統一于他的社會、政治、人生等方面的人文理想的,他將一種原始的宗教文化轉化成為一種人文文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鬼神是否真的存在,對孔子來說已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引導人們重視現世生存中生的價值,積極入世,按“禮”的規范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按照“仁”的要求實現道德與人格的自我完善,進而實現孔子心目中“仁者愛人”的倫理模式、“為政以德”的政治抱負和“仁義禮智”的社會理想。就像有學者指出的那樣:“上古以來中國傳統的這套禮制既是文化的,又是宗教的,也是政治的。”[19]
這里還有一個問題,即在過去的研究中,有學者斷章取義地判定孔子是有神論者或是無神論者,進而展開“迷信”與“反迷信”的是非判斷、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派系斗爭。在筆者看來,這是有失偏頗的,也是一種研究的偏差和曲解。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忽略了孔子所生活的時代、社會、文化的特定歷史語境;另一方面是沒有深究孔子鬼神觀念的核心指向,也沒有將孔子的鬼神觀念放在其“禮”與“仁”所構成的整體的思想框架中加以分析,需要研究者注意和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