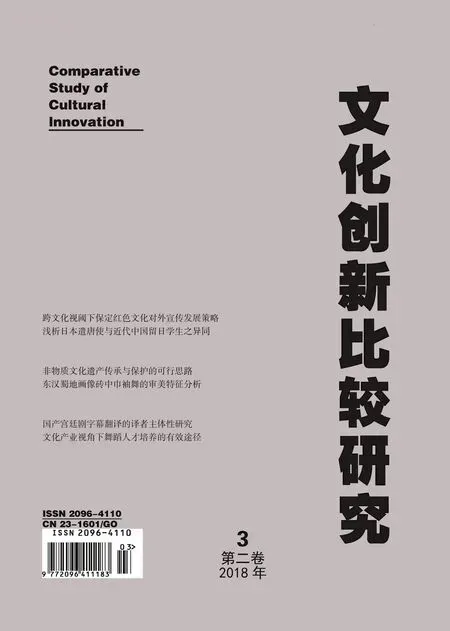以《在酒樓上》為例解讀魯迅小說的敘事與抒情
羅功宇
(仙桃職業學院,湖北仙桃 433000)
許多學者認為,從敘事抒情方式的角度而言,《在酒樓上》是一篇最富魯迅氣氛的小說。此處所講的魯迅氣氛,即魯迅先生身上所存在的特殊精神氣質在其文學創作、尤其是小說創作中的投影。眾所周知,魯迅先生的文章向來追求“物外之言,言中之物”,他頭腦中那深邃復雜的思想與厚重的民族情感總是在他的筆下以各種姿態呈現。
1 魯迅的《在酒樓上》
《在酒樓上》是魯迅于辛亥革命期間創作的小說,以對話體的方式,描繪出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的時代變革與當時知識分子的一般面貌。
小說全篇以“我”與另一主人公呂緯甫的對話為主線。第一個“我”在文中僅僅作為一個故事的轉述者而存在,第二個“我”才是整個故事的真正講述者。即呂緯甫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主人公,“我”只是作為外在環境中客觀存在的一個物化的人,是一個能夠從他的講述中了解其故事經歷及思想情感的人。文中的“我”與舊時好友呂緯甫因種種原因分別了將近十年,十年后卻意外在石居酒樓相遇,于是便上酒長談。在整個對話過程中,呂緯甫是主要的講述者,他始終掌握著話語的主動權。而“我”只是作為他故事講述的傾聽者。
十年前他與“我”都是積極上進、滿腔熱血的青年知識分子。在這次相遇中,呂緯甫向“我”講述了在這分別的十年中他所經歷的人生故事。歷經種種生活情景之后,仿佛只是飛了一個小圈子,十年后的他,便又回到了原點。但是相對而言,“我”的人生經歷卻是彷徨的,在這回家的旅途中與十年前好友呂緯甫的偶然相遇,使我得以把他的人生經歷與“我”進行對照。從中,“我”似乎也看清了這十年來自己的人生軌跡,“我”是如何從清醒到迷茫,從奮進到消沉。這次對話之后,“我”對自身似乎有了更為清晰的了解,并由此對我今后的人生目標加以探究。
魯迅將主體滲入小說的形式進行敘說。《在酒樓上》的敘述者“我”與呂緯甫是自我的兩個不同側面或內心矛盾的兩個側面的外化,全篇小說具有自我靈魂的對話與相互駁難的性質[1]。
2 《在酒樓上》中魯迅式的敘事與抒情
《在酒樓上》所表現的敘事抒情方式,是魯迅小說中特色較為鮮明的一部。它在形式上具有魯迅思想一般的先鋒性。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從《在酒樓上》對魯迅小說的敘事抒情進行分析。
2.1 《在酒樓上》的敘事特點分析
通過對《在酒樓上》的品讀,不難發現其敘事特點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是簡化情節設置,強化情感表達。情節設置的簡化,往往能使得文章的敘事信息更加具有文字效率,并且強化作家自身情感的表達。《在酒樓上》就是如此,第一敘述者“我”只是在逃避無聊中走到一石居,無意中與舊時好友呂緯甫相遇,于是坐下交談,事后便只是沿著各自的來路返回。交談中主要所說的,不過是“遷墳”、“送紙花”等一些平常的事件,并無劇烈的矛盾沖突產生。但就是在這個隨意的敘事環境中,通過主人公的講述與“我”的傾聽,卻散發出強烈的迷茫孤獨等情感。在對小說的故事情節淡化后,似乎傳統意義上的故事性已從《在酒樓上》消失了,但這反而給小說對于更加廣闊的精神世界的探索提供了空間。
二是敘事節奏平緩,故事講述從容。對于故事的講述是否從容,情節推進是否平緩,對于小說創作者的語言敘述能力是一個極大的考驗。現代小說自古典小說發源而來,受其影響較大。我國古典小說由于與傳統的說唱表演密切相關,使得在故事的講述過程中,作者極易加入自己的主觀評斷,急于對書中人物或事件表達自己的看法。因此,一般都顯得過于急促。但是在他后來的作品中,明顯地體現著對自身這種敘事方式的反思與改進。《在酒樓上》兩位主人公的相遇、交談、離去,都顯得那么的不經意,卻又水到渠成,不著一絲刻意的痕跡。整個故事的講述從容平淡,敘事節奏舒緩平和,少有自身的主觀臆斷夾雜其中。這是魯迅先生高超敘事技藝的體現,也是他對文學創作精益求精的結果。
三是意象多元塑造,生活氣氛強烈。我們可以看到,《在酒樓上》這一作品中,魯迅對于自然環境的描繪與對生活意象的塑造都有非常強烈的真實性與多元性。在以往魯迅的文學創作中,對自然環境的描寫總是顯得隨意簡潔,而且他所寫的故事多發生在寒冷的秋冬季節,如《祝福》、《藥》等。《在酒樓上》也是如此,小說開篇的“深冬雪后,風景凄清”寥寥八字,就把整個故事中的自然環境描繪出來,并且與故事講述的主體,即“我”和呂緯甫的實際心境聯合起來,塑造出多元化的情感意象[2]。
2.2 《在酒樓上》的抒情意旨解讀
就《在酒樓上》簡潔委婉的敘事風格看來,其抒情方式無疑是間接的托言表志,即借文中人物之口,敘述表達自己內心的情感志向。其中可看到包含魯迅所特有冷峻的抒情意旨。
首先,從《在酒樓上》看到已經覺醒者的求索。“我”在文中作為一個相對覺醒過來的人,回到家鄉之后,真切感受到了滄海桑田的悲涼,這時的“我”感到彷徨與無奈。此時的家鄉已經不再是簡單的人文環境,而是對于那個時代如“我”一般的覺醒者們所處的社會境況。在那個封建勢力依舊強大的社會環境中,少有的覺醒者往往面臨著如文中“我”一般的孤獨與困惑,但卻仍堅持著對光明溫暖的上下求索,這也是《在酒樓上》的主要抒情意旨。
其次,表達的是“旁觀者”對于“自我”的參照。《在酒樓上》中的“我”為了打發時間,獨自一人到了酒樓,并與呂緯甫相遇長談。呂緯甫經歷十年的困頓生活之后,早已沒有了那時奮進積極的精神面貌,如今回到生活的原點,整日渾渾噩噩。其中的“我”極少參與到呂緯甫的講話當中,使得我能夠更加客觀清晰地從傾聽者的角度,在他的身上進行自我的參照,并通過這種旁觀者的自我關照,進行自我的蛻變提升,從而形成一個全新的“自我”。
最后,追求的是旁觀者蛻變形成新的自我。《在酒樓上》中,“我”經過與呂緯甫的相遇交談,看到了一種渾渾噩噩、隨隨便便的生活狀態,“我”的苦悶也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排解。他的話解答了“我”心中諸多的疑惑煩惱,促使“我”繼續往前求索。毫無疑問,“我”和呂緯甫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著魯迅先生自己的影子,他們內心都有過那個時代知識分子普遍存在的迷茫與困頓,但是在經過對他人的審視與自身的觀照之后,都蛻變成新的自我。
3 從《在酒樓上》看魯迅小說的敘事與抒情
較之魯迅其他的小說情節設置,《在酒樓上》中的故事情節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簡化設置。在對文中的主要矛盾,即熱情奮進的過去與混沌消沉的現在的矛盾進行講述時,魯迅合理地做出了重點的選擇。他在文中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對過去的講述,而是著重于當下的描寫。這樣的敘事模式,不僅強化了小說的矛盾沖突表現,使其更具有批判性。而且在藝術抒情上,通過多種意象的跨時空鏈接,更加委婉,更加詩化。這些特征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可以看到。此外,還可以發現魯迅小說敘事抒情的許多其他獨到之處[3]。
3.1 魯迅小說敘事抒情視角的多樣性
遍觀魯迅的小說作品,其敘事視角多種多樣,這都是創作者內心復雜情感的文學表現。魯迅的小說往往呈現出一種互相攻訐的復合式敘事,在這種敘事結構中,創作者本身與書中人物的觀點可能并不一致,兩者甚至在書中發生爭論。
在《傷逝》中,魯迅利用涓生的自我獨白將小說主人公與讀者拉開距離,但是隨著故事情節的進展,又使讀者對敘述者產生懷疑。讓看似統一的敘事語調,因為這個冷靜的敘述者的存在產生復調敘事的效果。在《孔乙己》中,魯迅利用各種反諷的情節對話設置,獲得了一種特殊的藝術效果,與一般的冷漠調侃不同,這種角度的敘事使得敘事者在讀者面前的權威地位受到威脅,并且在那獨白敘述的話語間充滿了藝術張力[4]。此類不一而足。魯迅先生小說中呈現出來的各種復調敘事與反諷結構,是他內心深處對懷疑精神及歷史思考的表達。
3.2 魯迅小說敘事抒情時間線的多樣性
與傳統作家的小說創作相比,魯迅的小說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跳出了線性時間敘事的單一性,更多呈現出來的是回環往復的復雜時間線。
由于外國文藝思想對魯迅的影響較大,他小說的敘事時間也逐漸由傳統走向現代。這一點在他的《吶喊》、《故事新編》中可以明顯觀察到。《狂人日記》中魯迅運用意識流的敘事方式,表現出狂人天馬行空、無所約束的思維模式。在《傷逝》、《孔乙己》中,都是通過敘述者對過去的回憶反思展開,打破了線性時間的限制,拉近了小說主人公與讀者的距離。魯迅小說中這些多樣的全新的敘事抒情方式,賦予了他小說作品與眾不同的哲學韻味[5]。
3.3 魯迅小說敘事抒情的詩化藝術風格
無論是在《在酒樓上》,亦或魯迅其他小說創作中,都帶有濃厚的詩化藝術風格。這體現在對憂郁的愛情,故鄉的風俗,童年的追憶等一系列寫作對象的詩意描繪之中。
《在酒樓上》中的“深冬雪后,風景凄清”,《社戲》中的“月色便朦朧在這水氣里”等等,魯迅先生的抒情方式,就如水墨畫般,雖寥寥幾筆,卻意境無窮,給人以詩意的美感。此外,魯迅小說中的詩意抒情,還通過人物情感迸發來表現。這些情感的迸發,或是因為追憶童年,或是因為感懷過往,或是因為嘆傷愛情。正是通過環境與情感的雙重營造,與讀者內心產生共鳴。這種在小說中詩化的藝術抒情形式,是魯迅小說對中國現代小說的獨特貢獻。
4 結語
《在酒樓上》的敘事抒情方式,帶有強烈的魯迅個人特色,無論是其簡潔的情節設置還是平緩的敘事節奏,都值得后繼者推敲學習。而由《在酒樓上》這部作品觀之,魯迅那先鋒性的哲學思考、創新性的敘事抒情,其實早已融入到他其他各類作品的創作之中。對于魯迅小說中敘事抒情特色的研討,今后也許將成為魯迅文學研究中的又一熱門課題。
[1] 張箭飛.魯迅詩化小說研究[M].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3:33
[2] 錢理群.心靈的探尋[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30
[3] 張箭飛.魯迅詩化小說研究[M].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3:30
[4] 馮芙蓉.魯迅小說的詩意特征[D].蘭州大學.2011:22
[5] 韋勒克、沃倫等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M].北京.三聯書店.1984: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