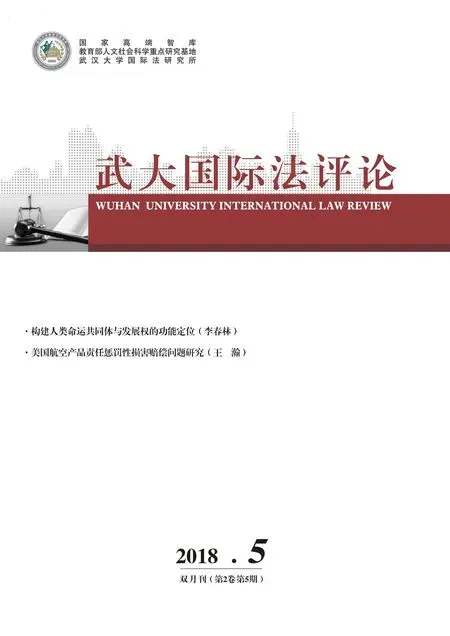美國航空產品責任懲罰性損害賠償問題研究
王 瀚
懲罰性損害賠償(punitive damages),也稱為示范性賠償(exemplary damages)或報復性賠償(vindictive damages)①在美國,“punitive damages”,“vindictive damages”和“exemplary damages”都是指懲罰性損害賠償,或是指在侵權情況下賠償數(shù)額超過了實際的損害。,它是普通法系國家的一項重要制度②Morris&Clarence,Punitive Damages in Personal Injury Cases,2 Ohio State Law Journal 216(1960);Prosser,Exemplary Damages in the Law of Torts,70 Harvard Law Review 517(1957).,是指侵權行為人故意實施某種不法行為,或實施惡意的莽撞行為時,以對行為人實施懲罰和追求一般抑制效果為目的,法院在判令行為人支付通常賠償金的同時,還可以判令行為人支付高于受害人實際損失的賠償金。它并非以補償受害人的實際損失為目的,而是作為補償性賠償之外的一種附加判處制度,其目的在于“懲治和制止不法行為”,“它不僅宣示了法院對被告行為的不認可,而且意在制止行為人重犯這種行為,并且有可能進一步制止其他人效法這種行為。”①P.F.P.Higgins,Elements of Torts in Australia 45(Butterworths 1970).
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在以美國為代表的英美法系國家的產品責任損害賠償實踐中較為普遍,而在大陸法系國家產品責任立法、司法實踐中很少被采納或是被規(guī)定嚴苛的適用條件。近年來,隨著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產品責任立法的相互影響、融合、趨同,該制度在全球范圍內得以廣泛適用,但在一些特殊的產品侵權責任領域,該制度仍存在適用混亂的情況。下文將結合美國法院的實踐,嘗試探討航空產品責任這一特殊領域中,懲罰性損害賠償適用的必要性、適用條件以及該制度在華沙公約體系②以華沙公約為核心的華沙公約體系(Warsaw System)包括8個法律文件:1929年《統(tǒng)一國際航空運輸某些規(guī)則的公約》;1955年海牙《修訂統(tǒng)一國際航空運輸某些規(guī)則的議定書》;1961年瓜達拉哈拉《統(tǒng)一非締約承運人承擔國際航空運輸?shù)哪承┮?guī)則以補充華沙公約的公約》;1971年《經海牙議定書修訂華沙公約的危地馬拉議定書》以及1975年修訂華沙公約的4個《蒙特利爾議定書》。和蒙特利爾公約③該公約于2003年11月4日生效。中國是第94個締約國,該公約于2005年7月31日對我國生效。截至2018年4月1日,該公約擁有中國、美國、歐盟、日本、加拿大等主要航空大國和地區(qū)在內的131個成員(130個主權國家和1個區(qū)域性組織),https://www.icao.int/secretariat/legal/List%20of%20Parties/Mtl99_EN.pdf,2018年9月30日訪問。下的限制與突破等問題,以期更好地保護航空事故受害人的權益,減少司法沖突和判決結果不公現(xiàn)象。
一、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墓δ芗霸诋a品責任領域適用的分野
(一)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男再|爭議與功能
懲罰性損害賠償相對于補償性損害賠償而言,給予侵權行為人的威懾力較大,警戒程度較高。有學者認為懲罰性損害賠償不具備補償?shù)奶攸c而只有刑事懲罰④劉靜:《產品責任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151頁。的特點或犯罪的性質⑤I.H.Ph.Diederiks-Verchoor,An Introduction to Air Law 191(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6).。換言之,懲罰性損害賠償其本質并非填補性的,而是報復性(retributive)和遏制性(deterrent)的。就適用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乃痉ㄕ叨裕且运椒w系執(zhí)行對行為人惡行的處罰,其目的應在于填補刑事懲罰體系的漏洞,而非取代刑事懲罰⑥黃居正:《蒙特利爾公約的第一個十年:國際航空運送人責任統(tǒng)一規(guī)范的新面向》,《東吳法律學報》2010年第4期,第167頁。。懲罰性損害賠償作為一種懲罰被告的方式,追加對原告的經濟賠償,已在英美法國家得到廣泛認可①目前,承認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钠胀ǚㄏ祰野绹⒂⒓幽么蟆拇罄麃啞⑿挛魈m等,但上述各國對于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倪m用目的與范圍則有不同解釋。See J.G.Fleming,The Law of Torts 241-242(The Law Book Company Ltd.1992).。在這些國家,實施懲罰性賠償?shù)哪康拇篌w可歸納為三種:(1)削弱侵權行為人的經濟基礎,防止其重新作惡,同時防止社會上的其他人模仿侵權行為人的行為;(2)鼓勵受害人對不守法的侵權行為提起訴訟,激發(fā)他們同不法行為作斗爭的積極性;(3)對原告(受害人)造成的財產損失或受到侵害的精神損害進行高額的經濟補償。
(二)歐美國家產品責任領域適用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姆制缗c趨勢
在產品責任案件中,是否設置懲罰性損害賠償,不同法系國家有不同的做法。美國是普通法系國家承認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的代表性國家。目前,美國大多數(shù)州都采納了這一制度。美國的一些聯(lián)邦法案如《謝爾曼法案》、《克萊頓法案》、《聯(lián)邦消費者信用保護法》、《聯(lián)邦職業(yè)安全與健康法》等都對懲罰性損害賠償作了規(guī)定。美國《侵權行為法重述》也對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作了規(guī)定。《侵權行為法第二次重述》第908條第1款規(guī)定,“懲罰性損害賠償是在補償性賠償或名義上的賠償之外,為懲罰該賠償交付方的惡劣行為并阻遏他與相似者在將來實施類似行為而給予的賠償。”第2款規(guī)定,“懲罰性損害賠償可以針對因被告的邪惡動機或他莽撞地無視他人的權利而具有惡劣的行為作出。在評估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臄?shù)額時,事實裁定人可以適當考慮被告行為的性質、被告所造成或意欲造成的原告所受損害的性質與范圍以及被告的財產數(shù)額。”尤其在產品責任案件中,大多數(shù)陪審團更愿意給原告判決懲罰性損害賠償以懲戒制造商,且許多州的法院對陪審團認定的懲罰數(shù)額不加限制。有些法院即使在補償性賠償已經很顯著的情況下,仍支持懲罰性賠償額②Ian Awford,Punitive Damages in Aviation Products Liability Cases,10 Air Law 7(1985).。例如,美國阿拉巴馬州法院1991年11月判決巴克斯特醫(yī)療保健公司賠償受害人布倫達·圖爾(因作隆胸術致填充物硅膠滲入胸部,引起肉芽瘤)217.5萬美元,其中懲罰性損害賠償為200萬美元③參見劉靜:《產品責任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頁。。又如,1981年格林蕭訴福特汽車公司(Grimshaw v.Ford Motor Co.)案④Grimshaw v.Ford Motor Co.,119 Cal.App.301751,174 Cal.Rptr.348(1981).中,陪審團認定,被告蓄意銷售處于危險狀態(tài)的汽車,判處其賠償1.25億美元的巨額懲罰性賠償金。
大陸法系國家在產品責任立法、司法實踐中很少有像美國那樣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對此制度通常不予采納。不僅如此,不少國家的法律或本地區(qū)的區(qū)域性公約還就有關人身損害最高賠償限額作了明確規(guī)定。這主要是因為大陸法系國家嚴格區(qū)分公法與私法,強調公法與私法具有不同職能的緣故,如行政法、刑法等公法的任務是懲罰犯罪和不法行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私法的任務是協(xié)調私人之間的利益紛爭,對受害人所受的損害給予補償和救濟,維護個體之間的利益平衡,私法責任(即民事責任)具有完全的補償性,不具有懲罰性。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因具有“懲罰、懲戒、遏制”功能,其實質上是一種公法責任而非私法責任,將其作為民事責任納入私法體系,與公法、私法的嚴格區(qū)分觀念及私法的基本原則不相符①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guī)定》,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頁。。例如,在德國法中,一般情況會拒絕適用懲罰性賠償,因其認為民法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法律,一方不能夠懲罰另一方。如聯(lián)邦德國《產品責任法》第10條就規(guī)定:(1)如果人身損害是由于一項產品或有同樣缺陷的數(shù)種產品產生,賠償義務人在不超過1.6億馬克之最高額度內負擔責任;(2)對多數(shù)受害人應負的賠償額,超過第1款規(guī)定的最高額時,每一筆賠償額應在其總額不超過最高額限度內按比例減少。
從德國立法規(guī)定我們不難看出,雖然對賠償額作了限制,但是其立法設定的最高額度較高,其實施效果與美國規(guī)定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并無兩樣。如德國一樣,通過規(guī)定較高的賠償額足以對不法制造商進行懲戒和對受害者給予保護,不失為保護消費者免受缺陷產品威脅的有效手段。但是,近年來,有的大陸法系立法和實踐也慢慢開始接受懲罰性損害賠償。例如,中國2010年《侵權責任法》第47條、2014年修訂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55條都明確規(guī)定適用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臈l件及范圍等,這也足以顯見產品缺陷侵權對社會的危害性和該制度所發(fā)揮的價值優(yōu)勢以及實施的必要性。
二、航空產品責任領域適用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谋匾约捌鋬r值
航空器通常在萬米高空高速運轉,加之航空產品科技含量高,事故具有突發(fā)性,事故原因調查和取證難等特點,一旦發(fā)生重特大航空事故②中國民航部門在實際業(yè)務上現(xiàn)仍使用“航空事故”的稱謂,并且按照航空器上的人員傷亡情況和航空器的損壞程度,將航空事故分為三類,依次是:特別重大事故;重大事故;一般事故。,往往面臨兩種慘局:一為幾乎全部旅客失去寶貴生命(包括航空公司的機組人員)或貨物毀損;二為價值幾億的高昂的航空器毀損,沒有修復的可能性。由此,當航空器在設計、制造、裝配等任何一個細微環(huán)節(jié)出現(xiàn)問題而發(fā)生產品責任事故時,作為航空運輸消費者的旅客或托運人和作為航空器使用人或所有人的航空公司或融資租賃公司所遭受的人身、財產等方面的損失將比任何其他產品責任的危害要大得多,尤其是給旅客及其家屬造成的傷害將是終身的、難以恢復的。因此,航空器及其每一個零部件在設計、制造、組裝以及民航主管當局在頒發(fā)適航證時必須嚴把質量關口,絕不容許有任何閃失和馬虎。
鑒于許多因產品質量瑕疵造成人身和財產損失的航空事故的血的教訓和慘痛代價,筆者認為,不管是承認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的英美法系國家,還是拒絕適用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的大陸法系國家,在國際航空產品侵權責任領域適用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尤為必要和恰當。該制度在這一特殊的、具有災難性后果的侵權領域適用具有天然的土壤和必要性,對航空器制造商提高產品質量和關注產品安全、履行注意義務具有很強的警示作用,對防止產品責任事故的發(fā)生也具有一定的抑制效果。對此,英國著名航空法學者伊恩·沃福德(Ian Awford)教授直言,“在英國法上,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淖饔檬聦嵣显谒星闆r下是不存在的,除非在一些特別的航空訴訟案件當中。”①Ian Awford,Punitive Damages in Aviation Products Liability Cases,10 Air Law 2(1985).伊恩·沃福德教授一語道破了該制度在航空責任領域中適用的必要性。該制度必將在航空產品責任領域發(fā)揮應有的制度價值:
第一,它可以有效遏制生產有質量缺陷的航空產品,促使生產者、設計者等各流通環(huán)節(jié)的責任主體以注重產品質量、提高產品安全性為工作宗旨。只有使相關主體承擔巨額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加大違法者的生產成本,使其像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于生產者的頭上,才能迫使其不斷改進生產工藝,不斷進行技術革新,嚴格管理,提高產品質量,確保人身財產安全。
第二,它可以激勵廣大航空事故受害人積極行使產品侵權訴訟權,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剝奪生產者的隱性侵權利潤。通過國內法規(guī)定高額的懲罰性賠償金,對制造商、銷售者、進口商等產生威懾作用,可以使其違法行為有所收斂。例如,在2004年中國發(fā)生的包頭空難案中,由于中國法院判處的較低的損害賠償不足以滿足受害人的索賠請求,受害人家屬隨后利用美國產品責任法中規(guī)定的巨額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向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郡高等法院起訴飛機發(fā)動機制造商(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和飛機總制造商(加拿大龐巴迪公司)。
第三,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撫平受害人的創(chuàng)傷,制裁制造商的不法行為,實現(xiàn)法律的公平與正義價值。設立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不僅可以使受害人得到與其損害相當?shù)难a償,而且可以得到實際損失之外的賠償,使受害人在心理上和經濟上達到平衡與慰藉,從而切實保護航空事故受害人的利益。同時,它也是各國產品責任立法日益國際化、趨同化發(fā)展和保護相對弱勢一方消費者權益的客觀需求。
三、航空產品責任領域適用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囊c實證分析
根據(jù)英美法系國家航空產品責任的立法及司法實踐,可知在航空產品責任訴訟實踐中適用懲罰性損害賠償須滿足四個條件:
第一,在主觀條件上,侵權人是故意、惡意、毫不關心他人權利或具有重大過失,即明知是缺陷產品仍然生產或者銷售,放任不良結果的發(fā)生。美國1982年《產品責任法》規(guī)定,如果有明確的證據(jù)證明損害是由于行為人毫不顧及受害人的安全造成的,行為人應負懲罰性賠償責任。在里奇訴塞斯納航飛機公司(Ridge v.Cessna Aircraft Co.)案①Ridge v.Cessna Aircraft Co.,117 F.3d 126,132(4th Cir.1997),applying Virginia Law.中,針對一起直升機墜毀傷亡事故,原告對制造商提起了故意和重大過失的訴訟。然而,法院裁定原告并不能獲得懲罰性損害賠償,因為制造商的行為和意識沒有達到不顧其他人安全的嚴重程度。又如,在泰勒訴穆尼飛機公司(Taylor v.Mooney Aircraft Corp.)案②Taylor v.Mooney Aircraft Corp.,2006 WL 3386642,7(E.E.Pa.21 November 2006).中,空難受害人財產的代理人以飛機飛行控制系統(tǒng)的抽空泵動力源失效為由,對航空器制造商提起了死亡訴訟。該案法院并未判決受害人從制造商處獲得懲罰性損害賠償,其理由是,制造商完全符合所有可適用的法規(guī),包括含有所有提示飛行員當動力不充足時警示儀器的規(guī)則,并認為近30年來,抽空泵一直適用于航空業(yè),并被大多數(shù)飛機制造商適用,F(xiàn)AA已認可了飛機的總體設計,并且也簽發(fā)了失事飛機的適航認證。
第二,在客觀條件上,要有具體的、嚴重的損害事實,這種損害事實不是一般的損害事實,而應當是造成嚴重損害的事實,即造成飛行員、乘客或地面第三人等死亡或者健康受到嚴重損害。這種損害事實僅限于他人嚴重的人身健康損害,而不包括財產損害,即使財產損害再大也不能課以懲罰性賠償。例如,1984年在美國新澤西州法院審理的哈珀訴塞斯納飛機公司(Harper v.Cessna Aircraft Corp.)案中,原告指控被告制造的塞斯納飛機的座椅存在設計缺陷,在起飛行時座椅滑動,造成一名飛行員死亡和多名乘客嚴重的身體傷害(serious injuries),陪審團決定給予被告4億美元的懲罰性損害賠償,但是,被告制造商不服,提起了上訴③Ian Awford,Punitive Damages in Aviation Products Liability Cases,10 Air Law 7(1985).,最后,該上訴被法院駁回。又如,在1971年加利福尼亞州法院審理的羅斯丁訴萊康明案(Rosendin v.Avco-Lycoming)中,該事故中的一名乘客受到嚴重的身體傷害,陪審團決定判處被告承擔10.5億美元的懲罰性賠償。①Ian Awford,Punitive Damages in Aviation Products Liability Cases,10 Air Law 7(1985).
第三,在因果關系上,上述主觀故意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應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即被侵權人的死亡或健康嚴重受損是因為侵權人故意或惡意生產或者銷售缺陷產品造成的。受害人不僅要證明損害的發(fā)生,而且還要證明該損害是由行為人的不良行為所致。在1983年佛羅里達州地區(qū)法院審理的派珀飛機公司訴庫爾特(Piper Aircraft Co.v.Coulter)案②Piper Aircraft Co.v.Coulter 17 Avi.18,163(Fla.Dist.Ct.App.1983).中,佛羅里達州、田納西州、威斯康星州以及阿拉斯加州一致認為懲罰性賠償可以對負有嚴格責任的航空器制造商進行評估。該案法院認為,即使制造商主觀上不存在疏忽,也可以裁決給予被告懲罰性損害賠償,其根據(jù)在于嚴格責任以過錯為前提,將這種嚴格責任的結果加之被告具有的“足夠的惡劣行為”(sufficiently egregious conduct)足以支持判給懲罰性賠償。該案中,原告聲稱派珀航空器制造商已知道飛機的門閂有缺陷,知道在其投入使用之后會發(fā)生危險,并且制造商在后來的模型中改變了門閂的設計。派珀航空器制造商同時又被指控認為沒有警示飛機具有潛在的缺陷門閂,并且制造商故意破壞了所有與飛機缺陷問題有關的文件。
第四,必須依附于一般的補償性賠償,即懲罰性損害賠償不能單獨存在,它不是獨立的請求權,必須依附和存在于一般的補償性損害賠償基礎之上,兩者之間在損害賠償上必須具有一定的“合理關系”③Ian Awford,Punitive Damages in Aviation Products Liability Cases,10 Air Law 7(1985).(reasonable relativity)。例如,在皮斯訴比奇飛機公司(Pease v.Beech Aircraft Corporation)案④Pease v.Beech Aircraft Corporation 38 Cal.App.3d 450.,113 Cal.Rptr.416(1974).中,上訴法院在充分考慮陪審團的決議后,判決飛機公司在此航空器產品缺陷責任事故中賠償死亡的四個人4.5億美元補償性損害賠償?shù)幕A上,又對制造商課以17.25億美元的懲罰性損害賠償。
另外,根據(jù)英美法系國家法院審判實踐的特點,陪審團是否對被告給予懲罰性損害賠償以及在多大額度內給予賠償?shù)臎Q議往往對法院最終的判決結果產生很大的影響,甚至有可能會直接左右法官的判決意見和傾向。當然,在大陸法系國家中,陪審團也的作用也不容小視。
懲罰性損害賠償在有陪審團參與的航空產品責任訴訟實踐中往往出現(xiàn)兩個非常重要的、關呼當事人切身利益的適用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
其一是給予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暮侠硇詥栴}。即航空產品責任訴訟常常在法律和技術專家之間圍繞尖端和復雜的產品設計和制造缺陷問題展開不同意見的辯論,但整個案件的最終問題卻是由根本不懂航空和工程技術的陪審團來作出決定或者至少受到他們的直接影響。他們一般既不可能輕易理解被告提出的事實和證據(jù),也不可能在復雜案情中理解和分析問題的本質,因此,把懲罰性損害賠償武器的權利放在以證據(jù)為裁判前提卻又不懂證據(jù)事實的這些“門外漢”陪審團的手中來行使,其結果很有可能是不公平的。①Ian Awford,Punitive Damages in Aviation Products Liability Cases,10 Air Law 9(1985).
其二是給予多大額度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即在陪審團的決議意見下,使法院最終判決原告獲得懲罰性損害賠償,但這種結果也是被告所不情愿接受的。盡管沒有人否認對空難事故受害人的同情或憐憫,但是這種金錢賠償決不能消除受害人所受到的身體或精神上的傷害,一般的補償性賠償也僅僅是法律尋求恢復傷害人傷痛的一種方式。由此,在審判實踐中,很可能會產生原告律師利用陪審團對處于弱勢地位的受害人或其家屬的憐憫情緒,從而使陪審團最終作出懲罰性損害賠償決議的數(shù)額比補償性賠償?shù)臄?shù)額高出過多,產生過度賠償?shù)那闆r,從而對民事法律救濟體系產生不利的影響。
四、華沙公約體系和蒙特利爾公約下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南拗婆c實踐突破
通常情況下,航空產品缺陷責任事故發(fā)生在航空器承擔旅客、行李或貨物運輸?shù)乩砦恢玫膭討B(tài)變化過程中,單純的、靜態(tài)的航空產品責任事故一般不會發(fā)生,同時,這類責任事故往往交織航空運輸責任和產品責任,受到兩類責任體制的調整。因而,在發(fā)生航空產品責任事故時,受害人是否可以獲得懲罰性損害賠償很可能會受到兩種不同責任規(guī)則體系的約束和影響,即一類是統(tǒng)一性的國際航空運輸責任規(guī)則體系(華沙公約體系和1999年蒙特利爾公約);另一類是國際、區(qū)域和各國國內有關產品責任的法律體系。由于這兩類責任體系對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囊?guī)定和適用情況不同,因此,適用不同規(guī)則,受害人所獲得的賠償結果也不相同,這也直接影響了受害人權益的保護和判決結果的一致性。
在調整國際航空運輸承運人責任的華沙公約體系下,即使原告認為承運人存在有意的不良行為,要減損公約的賠償限額以使其獲得懲罰性損害賠償,在美國相關巡回法院的實踐中基本上都被予以限制和否定。
在美國,首先考慮這一問題的是受理弗洛伊德訴東方航空公司(Floyd v.Eastern Airlines)案①Floyd v.E.Airlines,872 F.2d 1462(11th Cir.1989),rev’d on other grounds,499 U.S.530,113 L.Ed.2d 569,111 S.Ct.1489(1991),applying federal law.的第十一巡回法院。在該案中,法院認為,盡管華沙公約沒有明確規(guī)定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膯栴},但是,根據(jù)華沙公約的文本、結構以及立法歷史可知,華河公約僅規(guī)定補償性損害賠償可以得到實現(xiàn)。法院不折不扣依據(jù)(relied heavily upon)華沙公約第17條的規(guī)定,認為“承運人應該對在發(fā)生乘客傷亡情況下造成的損害或乘客遭受的其他身體上的傷害承擔責任”。為了社會利益,法院認為懲罰性損害賠償不應判罰作惡者,也不會支持受害人的請求。②Floyd v.E.Airlines,872 F.2d 1462,1486(11th Cir.1989),rev’d on other grounds,499 U.S.530,113 L.Ed.2d 569,111 S.Ct.1489(1991),applying federal law.
該案法院同時還認為,懲罰性損害賠償與華沙公約所確立的補償性賠償?shù)呢熑误w制相沖突。這樣一種賠償將與華沙公約“提供一種全面和統(tǒng)一的由華沙公約所調整的航空公司的責任體制”的目的相沖突,違反了華沙公約自身在一些法院可以得到實現(xiàn)而在其他法院不能得以實現(xiàn)的統(tǒng)一性目標。因此,華沙公約優(yōu)先本國法,排除了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恼埱蟆"跢loyd v.E.Airlines,872 F.2d 1462,1487-1489(11th Cir.1989),rev’d on other grounds,499 U.S.530,113 L.Ed.2d 569,111 S.Ct.1489(1991),applying federal law.
另外,審理該案的法院還拒絕了原告認為華沙公約第25條④1929年華沙公約第25條規(guī)定:“(一)如果損失的發(fā)生是由于承運人的有意的不良行為,或由于承運人的過失,而根據(jù)受理法院的法律,這種過失被認為等于有意的不良行為,承運人就無權引用本公約關于免除或限制承運人責任的規(guī)定。(二)同樣,如果上述情況造成的損失是承運人的代理人之一在執(zhí)行他的職務范圍內所造成的,承運人也無權引用這種規(guī)定。”創(chuàng)立了一個請求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莫毩⒃V因的爭辯。華沙公約第25條規(guī)定,“如果承運人存在有意的不良行為的過失,那么,承運人就無權引用本公約關于責任限額的規(guī)定”。該條的意圖僅僅是為了避開(remove)該公約第22條關于承運人的責任限額,而不是創(chuàng)立一個獨立的訴訟權利。⑤Floyd v.E.Airlines,872 F.2d 1462,1485-1489(11th Cir.1989),rev’d on other grounds,499 U.S.530,113 L.Ed.2d 569,111 S.Ct.1489(1991),applying federal law.
在華沙公約的訴訟案件中,懲罰性損害賠償在紐芬蘭甘德爾(Gander)發(fā)生的一起空難中也未被適用⑥In re Air Crash Disaster at Gander,Nfld.,684 F.Supp.927(W.D.Ky.1987),applying federal law.。正如弗洛伊德案一樣,受理甘德爾案的法院解釋華沙公約第17條限制了乘客的補償性損害賠償①In re Air Crash Disaster at Gander,Nfld.,684 F.Supp.927(W.D.Ky.1987),applying federal law.See also Mertens v.Flying Tiger Lines,341 F.2d 851,858(2d Cir.1965),applying federal law.在該案中,考慮到懲罰性損害賠償很可能被包括在賠償金中,華沙公約明顯把這一問題留給締約國的國內法來決定。。同樣,在華盛頓特區(qū)法院審理的大韓空難案②In re Korean Airlines Disaster,932 F.2d 1475(D.C.Cir.1991),applying federal law.中(In re Korean Airlines Disaster),懲罰性損害賠償也未被法院支持。該案涉及1983年大韓航空公司007航班空難中死亡的137名乘客的集團訴訟。在為期三周的審判中,地區(qū)法院的法官錯誤地相信在《華沙公約》訴訟下,懲罰性賠償是可以支持的,并以故意的不法行為判定航空公司承擔懲罰性的賠償。陪審團也發(fā)現(xiàn)航空公司有故意的不良行為,裁定給予50億美元的懲罰性賠償。然而,在上訴中,華盛頓特區(qū)法院作出決定認為,華沙公約第17條的措辭描述了一種補償性或事實上的損害責任,而懲罰性損害賠償具有報復性(retributive)和威懾性(deterrent),撤銷了這種強有力的懲罰性損害賠償裁決。法院根據(jù)起草華沙公約的記錄和注釋,認為締約當事國曾經考慮過懲罰性損害賠償,并認為這種有意的不良行為的結果在華沙公約下并不創(chuàng)立獲得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臋嗬跧n re Korean Airlines Disaster,932 F.2d 1475,1485-1490(D.C.Cir.1991),applying federal law.。
然而,通過分析懲罰損害賠償?shù)男再|,可以發(fā)現(xiàn),該制度并非絕對不能適用于國際航空承運人損害賠償訴訟之中。畢竟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哪康脑谟谔幜P完全忽視它人人身安全和健康的具有明顯惡意和嚴重疏忽行為的加害人。在該公約體系下的一些早期判例實踐中,確實也不乏存在承運人或指揮監(jiān)督的機械師在駕駛或維修上有嚴重疏忽的情形④關于國際航空承運人故意或重大過失在實務上的具體案例,參見黃居正:《航空承運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臺灣本土法學》2006年第80期,第235-240頁。。在司法實踐中,一些法院也以承運人有重大過失或惡意為由,有支持原告獲得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呐欣@纾诩~約南部和東部地區(qū)法院對華沙公約體系下的懲罰性賠償?shù)囊庖娋痛嬖诜制纭|部地區(qū)法院主審法官Platt在洛克比空難⑤In re Air Disaster in Lockerbie,Scot.,733 F.Supp.547(E.D.N.Y.1990),applying international law.中就認為懲罰性損害賠償在華沙公約下不能得到支持;然而,南部地區(qū)法院的法官Sprizzo在卡拉奇空難⑥In re Hijacking of Pan Am.World Airways,Inc.Aircraft at Karachi Int’l Airport,Pak.,729 F.Supp.17(S.D.N.Y.1990),applying New York and international law.中卻作出相反的裁決,他認為華沙公約第24條①1929年華沙公約第24條規(guī)定:“(一)如果遇到第十八、第十九兩條所規(guī)定的情況,不論其根據(jù)如何,一切有關責任的訴訟只能按照本公約所列條件和限額提出;(二)如果遇到第十七條所規(guī)定的情況,也適用上述規(guī)定,但不妨礙確定誰有權提出訴訟以及他們各自的權利。”并不妨礙原告以何種訴因提起訴訟,即使法院裁決華沙公約第17條在通常情況下會阻止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倪m用,但是,它并不妨礙在華沙公約第25條規(guī)定的有意不良行為情況下獲得懲罰性損害賠償②In re Hijacking of Pan Am.World Airways,Inc.Aircraft at Karachi Int’l Airport,Pak.,729 F.Supp.17,20(S.D.N.Y.1990),applying New York and international law.。同時,Sprizzo法官總結認為應該用條約平實的語義來解釋糾紛事實,在條約通常語義下,懲罰性損害賠償是可以得到支持的③In re Hijacking of Pan Am.World Airways,Inc.Aircraft at Karachi Int’l Airport,Pak.,729 F.Supp.17,20(S.D.N.Y.1990),applying New York and international law.。
鑒于洛克比案和卡拉奇案在懲罰性損害賠償適用上存在嚴重的分歧,兩案被訴至第二巡回法院,上訴法院對此問題作出統(tǒng)一結論,認為在華沙公約責任體系下,即使存在有意的不良行為,也不能判處懲罰性損害賠償。如果這樣做的話,將與該公約限定承運人責任的目的相左。另外,法院認為華沙公約第17條僅對補償性損害給予賠償,在本公約的賠償范圍內,懲罰性賠償由聯(lián)邦法來規(guī)定。在存在有意不良行為的情況下,華沙公約第25條也不會授權判定懲罰性損害賠償,因為它沒有超越第17條的規(guī)定。④In re Air Disaster at Lockerbie,Scot.,928 F.2d.1267,1280-1287(2d Cir.1990),applying federal and international law.
為了從根本上終結對這一問題的長期困惑,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艾拉以色列航空公司訴特森(El Al Israel Airlines,Ltd.V.Tsui Ynanr Tseng)案⑤El Al Israel Airlines,Ltd.v.Tsui Yuan Tseng,525 U.S.155,142 L.Ed.2d 576,119 S.Ct.662(1999).中非常明確地(unequivocal)指出,華沙公約在損害賠償上規(guī)定了排它性的訴因,沒有任何條款表明可以適用懲罰性損害賠償。事實上,該案也確定了懲罰性損害賠償被排除在華沙公約損害賠償體系之外。⑥Miller v.Cont’l Airlines,Inc.,260 F.Supp.2d 931,939-940(N.D.Cal.2003),applying California and federal law.
為了避免產生無盡的實踐爭議和實現(xiàn)國際航空私法的統(tǒng)一實施,2003年在全球范圍內批準生效的對華沙公約體系進行現(xiàn)代化和一體化的、全新的1999年蒙特利爾公約在其第29條①蒙特利爾公約第29條(索賠的根據(jù))規(guī)定:“在旅客、行李和貨物運輸中,有關損害賠償?shù)脑V訟,不論其根據(jù)如何,是根據(jù)本公約、根據(jù)合同、根據(jù)侵權,還是根據(jù)其他任何理由,只能依照本公約規(guī)定的條件和責任限額提起,但是不妨礙確定誰有權提起訴訟以及他們各自的權利。在任何此類訴訟中,均不得判給懲罰性、懲戒性或者任何其他非補償性的損害賠償。”中第一次明確規(guī)定了在任何損害賠償中,均不得判給責任人“懲罰性”、“懲戒性”等非補償性損害賠償。這是新公約在原有華沙公約責任體系下新增加的條款,該公約明確排除了適用懲罰性賠償?shù)目赡苄浴R簿褪钦f,航空運輸中的損害賠償是補償性、恢復性的,必須在“恢復性賠償原則的基礎上提供公平賠償”②Montreal Convention of 1999,Preface.,這是公約序言中闡明的基本賠償原則。不論受理案件的法院適用何種法律概念,也不論所判給的賠償是明顯懲罰性的還是暗含懲罰性的,只要在性質上是懲罰性的,都不允許。③中國民用航空局政策法規(guī)司:《1999年統(tǒng)一國際航空運輸某些規(guī)則的公約精解》,中國民用航空局政策法規(guī)司(內部發(fā)行)2005年版,第199頁。在實踐中,慣常適用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拿绹ㄔ海苍?008年適用蒙特利爾公約的判決中④In re Air Crash at Lexington,Kentucky,2008 U.S.Dist.LEXIS 11255,8(Ed.Ky.2008).,正式確認了這一解釋原則對法院地的拘束力。該判決認為,蒙特利爾公約本身所提供的是有限的、排他的(exclusive)損害賠償目的,專屬法院不得借此解釋擴充損害賠償?shù)姆秶蛢热荩ㄈ绾w懲罰性的損害賠償),以免破壞公約建立的國際航空運輸承運人責任統(tǒng)一規(guī)則的目的。
至此,不論是華沙公約責任體系,還是蒙特利爾公約責任體系,在侵權人存在故意的不良行為或其他惡意行為的情況下,受害人意欲獲得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脑V求在國際運輸統(tǒng)一責任體系下已不可能得到支持,從而結束了華沙公約責任體系解釋不統(tǒng)一的時代。受害人要想獲得超過實際損害的懲罰性損害賠償,則只能以其他訴因(如航空缺陷產品的侵權責任),通過訴諸規(guī)定有該賠償內容的國內侵權責任法來進行索賠,這也是目前國際空難受害人為突破國際運輸公約有限責任限額的最好途徑和方法。受害人通過借助航空產品的制造商在不同國家(尤其是歐美航空器制造大國)有營業(yè)行為、侵權事故發(fā)生地和行為地不在同一國家或地點、受害人的不同國籍等連結點因素,利用美國或其他國家國內民事訴訟法“長臂管轄”①長臂管轄是美國民事訴訟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其主要應用理論是當被告住所不在法院所在的州,但和該州有某種最低聯(lián)系(minimum contacts),而且所提權利要求的產生和這種聯(lián)系有關時,就該項權利要求而言,該州對于該被告具有對人管轄權(雖然他的住所不在該州),可以在州外對被告發(fā)出傳票。(long-arm jurisdiction)規(guī)則和“最密切聯(lián)系原則”,通過受理案件所在地法院的國內法中關于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囊?guī)定實現(xiàn)自己的訴求,從而在國際航空責任事故索賠訴訟中,開辟了獲得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男峦緩健?/p>
五、中國有關航空產品責任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牧⒎捌渌伎?/h2>
中國產品責任立法是否應設立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學界存有不同觀點。有學者認為不應規(guī)定懲罰性損害賠償,因為侵權責任法是民事責任,損害賠償以“填平”為原則,在損害之債中,償大于失或者償小于失,都是違反民法中的公平和平等原則的,必須償與失相當才符合民事立法的要求。②黃名述:《產品質量民法原理探析》,《現(xiàn)代法學》1993年第5期,第22頁。也有學者認為應設置懲罰性損害賠償,因為該制度除了意在補償損失、價格轉移、責任保險及危險控制外,還旨在剝奪生產者的隱性侵權利潤,以鼓勵受害人提起產品責任訴訟③劉靜:《產品責任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頁。。
從中國的立法現(xiàn)狀來看,早期的立法,如1986年《民法通則》、2000年修訂的《產品質量法》并沒有明確規(guī)定懲罰性損害賠償。但最新的立法,如2010年通過的《侵權責任法》已明確規(guī)定了懲罰性損害賠償,該法第47條規(guī)定:“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另外,2014年最新修訂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55條也進一步確認了懲罰性損害賠償在侵權法保護受害人時代的地位和價值。該條規(guī)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shù)慕痤~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3倍;增加賠償?shù)慕痤~不足五百元的,為五百元。法律另有規(guī)定的,依照其規(guī)定。經營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務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費者提供,造成消費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受害人有權要求經營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五十一條等法律規(guī)定賠償損失,并有權要求所受損失2倍以下的懲罰性賠償。”上述兩部法律對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囊?guī)定,是中國立法在人本化價值趨向下的必然選擇,有利于侵權人提高其注意義務,從而避免類似情形再次發(fā)生。
在中國現(xiàn)代民法所要求的“人的全面發(fā)展”的價值趨向下,最新立法設立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毫無疑問完全具有必要性和現(xiàn)實性。但是,通過細致對比發(fā)現(xiàn),以上立法對懲罰性賠償額的規(guī)定卻不盡相同,有的立法明確規(guī)定了受害人獲得懲罰性賠償金的限額范圍,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55條規(guī)定了產品經營者對所受損失“賠一罰三”的賠償額度。又如《食品安全法》第96條第2款規(guī)定了消費者可以向生產者或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10倍的賠償金。而有的立法則未明確規(guī)定懲罰性賠償金的數(shù)額,如《侵權責任法》第47條只是籠統(tǒng)地規(guī)定了被侵權人有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shù)臋嗬瑢r償額度未劃定具體賠償標準。這里的“相應”,主要是指被侵權人要求的懲罰賠償金的數(shù)額應當與侵權人的惡意相當,應當與侵權人造成的損害后果相當,與對侵權人的威懾相當,具體賠償數(shù)額由人民法院根據(jù)個案具體判定。
關于限額的設定問題,學界目前大體存在兩種意見①參見肇晶:《剖析產品侵權案件的懲罰性賠償規(guī)則——以〈侵權責任法〉為視角》,《北京政法職業(yè)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第84頁。:一種認為既然《侵權責任法》沒有明確規(guī)定懲罰性賠償?shù)臄?shù)額,那么,就屬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疇,可以由法官根據(jù)具體案件的實際情況自行判決;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侵權責任法》不宜對具體審判問題規(guī)定得過于瑣碎,懲罰性賠償金的數(shù)額可以是造成受害人人身損害損失的2~3倍,具體限額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將來出臺的司法解釋中規(guī)定更為恰當。對此,筆者傾向于第一種觀點,認為懲罰性損害賠償?shù)臄?shù)額,在實際審判過程中,可由法官依據(jù)案件的具體情況和最高于2001年出臺的司法解釋意見規(guī)定的各類考量和判斷因素進行自由裁量和綜合權衡,作出一個科學、合理的裁決。事無具細,實踐中發(fā)生的不可預料的侵權行為和侵權類型形形色色,有時侵權的主體和對象不盡相同,有時發(fā)生的場合和地點也不盡相同,如果一味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55條一樣規(guī)定具體的賠償標準,那么很可能會導致不公平的結果,甚至有可能會削弱這一制度“懲罰”、“威懾”和“遏止”的功能和價值。
根據(jù)世界上大多數(shù)國家的立法和司法實踐,同時結合中國近年來的立法動態(tài),筆者認為,中國在修訂《民用航空法》和《產品質量法》以及未來在制定《民法典》時,應明確針對航空產品制造商或承運人等責任主體的侵權損害行為規(guī)定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達到一般法與特別法內容協(xié)調一致,實現(xiàn)中國民事立法科學性、穩(wěn)定性、體系性的價值目的,實現(xiàn)法制統(tǒng)一,以免實踐中出現(xiàn)“同案不同判、同法不同解”的現(xiàn)象。②王利明:《法治現(xiàn)代化需要一部“百科全書”》,《人民日報》2014年9月30日,第5版。在世界航空制造業(yè)發(fā)展相對成熟的階段,在航空產品責任以及運輸責任領域規(guī)定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完全具有經濟上和道德上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它不僅可以對生產者進行經濟上的懲罰,具有威懾作用,而且還可以在道德上對生產者的過錯行為進行譴責和懲罰,從而補償受害人的損失,這在實踐上較為可行,在心理上也得到普通大眾的認可。
六、結語
鑒于航空產品責任事故的災難性后果,航空產品責任損害賠償除了包括具有私法性質的補償性賠償外,在司法實踐中,還可考慮判決制造商承擔具有公法性質的懲罰性賠償,使相關責任主體在補償性損害賠償之外,承擔額外的經濟負擔,使其不敢、也不能疏于關注產品的安全性能,這樣既可以提高航空活動的安全性,又可以有效保護受害人的權益。鑒于航空產品責任常常交織運輸責任和產品責任,受害人既可以提起運輸責任訴訟,也可以提起產品責任訴訟,但是兩類責任體制對懲罰性賠償?shù)囊?guī)定并不一致。調整運輸責任的國際公約(包括華沙公約體系和蒙特利爾公約)和大多數(shù)國家(包括中國)的國內航空法并不承認懲罰性損害賠償,而調整產品責任的國際公約和國內產品責任法卻明確承認懲罰性損害賠償(尤其是英美法系國家)。在發(fā)生航空產品責任事故時,受害人是否可以獲得懲罰性損害賠償受兩種不同責任規(guī)則體系的約束和影響。訴因不同,受害人所獲得的賠償結果也不盡相同,有時往往會出現(xiàn)同案不同解的現(xiàn)象,直接影響到受害人權益的保護。近年來,在國內外司法實踐中已明顯出現(xiàn)了當事人以產品缺陷為由提起產品責任訴訟的訴訟泛濫傾向,現(xiàn)有運輸責任體制備受“冷落”和“詬病”。因此,有必要在運輸責任領域例外性地規(guī)定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從而有效保障當事人的權益,化解司法沖突和不公現(xiàn)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