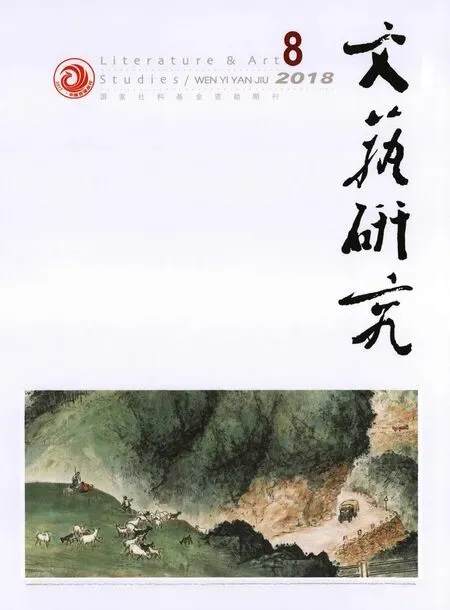作家的中產(chǎn)階級(jí)化與21世紀(jì)長(zhǎng)篇小說鄉(xiāng)村想象的幾種方法
雷 鳴
如何把鄉(xiāng)村書寫得真切而生氣淋漓?我們自然會(huì)想起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上那些為完成自己的創(chuàng)作而深入生活、落戶農(nóng)村的作家。柳青為寫《創(chuàng)業(yè)史》,在陜西長(zhǎng)安縣皇甫村落戶達(dá)十四年之久;周立波為寫《山鄉(xiāng)巨變》亦從北京回故鄉(xiāng)湖南益陽安家落戶,與農(nóng)民生活在一起。雖然他們由于時(shí)代語境之囿,創(chuàng)作難免帶有理念化的痕跡,但是他們對(duì)那個(gè)時(shí)代農(nóng)村現(xiàn)實(shí)生活的深入體驗(yàn)和細(xì)致描繪,頗多可圈可點(diǎn)之處。
當(dāng)下的中國(guó)作家卻極少有人真正深入鄉(xiāng)村,大多在城市里過著穩(wěn)定富足的中產(chǎn)階級(jí)生活,正如作家韓少功所說:“現(xiàn)在的作家都開始中產(chǎn)階級(jí)化,過著美輪美奐的小日子,而且都是住在都市。”①韓少功此言并非虛妄。按照社會(huì)學(xué)家陸學(xué)藝的觀點(diǎn),中產(chǎn)階級(jí)群體主要以腦力勞動(dòng)為主,工資是其主要的收入來源,穩(wěn)定、高額的收入給中產(chǎn)階級(jí)帶來相當(dāng)?shù)南M(fèi)能力、一定的閑暇時(shí)間及較高的生活水準(zhǔn),并且這個(gè)階層有一定的文化素養(yǎng)和公民意識(shí)②。因此,當(dāng)下有一定影響力的作家,自然可歸于中產(chǎn)階級(jí)的行列。一是他們大多收入穩(wěn)定,要么是“專業(yè)作家”,要么供職于作協(xié)系統(tǒng)的大報(bào)、大刊,一些知名作家甚至跨入了“新富階層”。二是他們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如“60后”作家畢飛宇、韓東、李洱、邱華棟都畢業(yè)于知名高校,年輕一代的“70后”作家,如徐則臣、付秀瑩,更是京城名校的研究生畢業(yè)。尤其是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作家進(jìn)入大學(xué),如王安憶、閻連科、畢飛宇等紛紛在知名高校擔(dān)任教職,其生存方式之“學(xué)院化”,似乎也表征著作家的“中產(chǎn)化”。
當(dāng)然,作家的身份、社會(huì)地位、所處階層與文學(xué)作品的風(fēng)格特征,并非一一對(duì)應(yīng)的關(guān)系,絕非一階層只有一階層之文學(xué)。事實(shí)上,列夫·托爾斯泰出身貴族,亦不妨礙他訪問貧民窟,深入了解城市底層生活,寫出人道主義色彩濃厚的作品;魯迅彼時(shí)作為教授和作家的收入,完全可歸入富人階層,但絲毫不影響他的作品表現(xiàn)對(duì)弱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zhēng)”。但寫作者生活環(huán)境(或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世界觀、藝術(shù)觀、個(gè)性、氣質(zhì)的差異,還是會(huì)或顯或隱影響到作品的內(nèi)質(zhì)與樣貌。當(dāng)下中國(guó)作家的中產(chǎn)階級(jí)化的生活方式、世界觀、藝術(shù)觀必然帶來與之相應(yīng)的美學(xué)話語。誠(chéng)如程光煒?biāo)裕骸爸挟a(chǎn)階級(jí)時(shí)代造就了中產(chǎn)階級(jí)文學(xué),而中產(chǎn)階級(jí)文學(xué)又以特殊的形象符號(hào)描繪了中產(chǎn)階級(jí)時(shí)代的價(jià)值觀念、思想感受和心理情緒。”③
綜觀21世紀(jì)長(zhǎng)篇小說之鄉(xiāng)村敘述,已經(jīng)中產(chǎn)階級(jí)化的作家書寫對(duì)他們而言隔膜、遙遠(yuǎn)的鄉(xiāng)村時(shí),總是以深浸于都市所養(yǎng)成的中產(chǎn)階級(jí)趣味,預(yù)設(shè)種種觀念定制、覆蓋他們“看不見的鄉(xiāng)村”④,表達(dá)他們的價(jià)值觀念、思想感受和心理情緒。由此,形成了幾種流行的“套路”,亦暴露出21世紀(jì)中國(guó)文學(xué)鄉(xiāng)村書寫的諸多隱憂。
一、高密度知識(shí)的填充術(shù)
現(xiàn)代以來,中國(guó)作家對(duì)鄉(xiāng)村的書寫形成了幾種固定的敘述方式:一是魯迅的決絕批判式,勾勒鄉(xiāng)村的破敗與眾生的愚昧,以啟蒙、喚醒民眾;二是沈從文的繾綣懷戀式,敘述浪漫的湘西記憶,建立人性美好的“希臘小廟”;三是趙樹理、柳青、周立波等的革命理念規(guī)劃式,改寫從前魯迅的“哀歌”與沈從文的“牧歌”式鄉(xiāng)村形象,塑造清新、明朗的紅色鄉(xiāng)村;四是莫言、陳忠實(shí)的民間與傳統(tǒng)觀照式,試圖考察鄉(xiāng)村社會(huì)之變遷并反思?xì)v史。上述幾種格式的鄉(xiāng)村敘事,由于各自視野的局限性,難免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真實(shí)的鄉(xiāng)村生活。但不管怎樣,他們展開的鄉(xiāng)村想象的基底,是鄉(xiāng)村人倫風(fēng)情的描述與鮮活人物形象的塑造,尤其沒有拋棄對(duì)鄉(xiāng)村生活豐富細(xì)節(jié)的描摹。
那么21世紀(jì)的中國(guó)作家如何書寫當(dāng)下的鄉(xiāng)村呢?顯而易見的是,居住在都市的作家過的是同質(zhì)化的生活,鄉(xiāng)村生活經(jīng)驗(yàn)極其貧乏,即便有些鄉(xiāng)村生活的體驗(yàn),也是多年前擠牙膏式的童年記憶,新的生活經(jīng)驗(yàn)基本上來自各類媒介。如莫言曾坦言:“對(duì)于我們50年代出生的這批作家來說,想寫出反映現(xiàn)在農(nóng)村的作品已經(jīng)不可能。我們對(duì)農(nóng)村已經(jīng)疏離,很難去體驗(yàn)它真實(shí)的變化。”⑤閻連科也曾自我批評(píng)道:“連我自己,做小說的時(shí)候,對(duì)于鄉(xiāng)村的描繪,也是不斷重復(fù)著抄襲別人的說法……而實(shí)際上,村落真正是個(gè)什么,溝壑的意義又是什么,河流在今天到底是什么樣兒,我這個(gè)自認(rèn)是地道的農(nóng)民的所謂作家,是果真的模糊得如它們都沉在霧中了。”⑥因此,不難發(fā)現(xiàn),近些年來,寫鄉(xiāng)村的小說出現(xiàn)不少雷同、撞車或“抄襲”的現(xiàn)象。這在很大程度上緣于作家對(duì)鄉(xiāng)村的認(rèn)知、敘述,依賴于書齋里獲得的媒體信息,缺乏腳踏實(shí)地去感知與體驗(yàn)。如劉繼明2004年發(fā)表于《山花》的小說《回家的路究竟有多遠(yuǎn)》,與李銳2005年發(fā)表于《天涯》的小說《扁擔(dān)》,素材皆來源于中央電視臺(tái)《今日說法》的一期節(jié)目“千里爬回家”;賈平凹《高興》據(jù)農(nóng)民工千里背尸回家的報(bào)道改寫而成,閻連科《丁莊夢(mèng)》的“本事”亦是見諸媒體報(bào)道的河南上蔡縣的“艾滋病”村。
雷同的都市生活處境,對(duì)作家創(chuàng)作構(gòu)成極大挑戰(zhàn),如何在都市逼仄的書房?jī)?nèi)閃展騰挪,表現(xiàn)斑斕裂變的中國(guó)當(dāng)代鄉(xiāng)村呢?“中產(chǎn)階級(jí)卻又并不僅僅意味著某種程度的資產(chǎn),不僅僅意味著物質(zhì)生活上的小康,還意味著有文化,有教養(yǎng),意味著某種程度的知識(shí)文化水平。”⑦于是,對(duì)從鄉(xiāng)村生活抽身而退的“中產(chǎn)化”作家來說,在文本中表現(xiàn)自己“有文化、有教養(yǎng),意味著某種程度的知識(shí)文化水平”,或許是本階層的趣味所致,亦是一種對(duì)鄉(xiāng)村隔膜之后無可奈何的選擇。廣西作家鬼子道出了自己的心曲:“你們說鄉(xiāng)土文學(xué)城市化,符號(hào)化了,你要使寫作逃脫這種模式,最后無非也是發(fā)現(xiàn)或發(fā)明另一種‘鄉(xiāng)土’,我估計(jì)走著走著,還是另一種符號(hào)。可能關(guān)鍵是哪種符號(hào)更可愛。”⑧對(duì)于受過良好教育的作家來說,或許選擇文化知識(shí)來發(fā)現(xiàn)或發(fā)明一種“鄉(xiāng)土”更可愛。
因此,21世紀(jì)以來,中國(guó)作家似乎更愿意展示自己的專業(yè)修養(yǎng)、知識(shí)水平,好以炫耀的筆致表現(xiàn)自己的知識(shí)與文化優(yōu)勢(shì),借助所掌握的民俗、歷史、宗教、經(jīng)濟(jì)、地理等專業(yè)知識(shí),搭建鄉(xiāng)村敘述的框架或道具,以彌補(bǔ)對(duì)當(dāng)下鄉(xiāng)村生活的陌生造成的缺漏。由此,21世紀(jì)小說的鄉(xiāng)村書寫出現(xiàn)了一種懸置鄉(xiāng)村故事、拋棄鄉(xiāng)村生活質(zhì)感的趨向:不屑講述鄉(xiāng)村現(xiàn)實(shí),復(fù)現(xiàn)鄉(xiāng)村人生,對(duì)鄉(xiāng)村生活細(xì)節(jié)的編織也沒有耐心;鄉(xiāng)村不再是一個(gè)生活的空間,而變成了涵納高密度知識(shí)的容器。
先以郭文斌的《農(nóng)歷》為例,雖然作者試圖以農(nóng)歷節(jié)日為切入點(diǎn),描摹詩意氤氳的鄉(xiāng)村生活圖景,以此喚起傳統(tǒng)文化精神,但也正是由于極度迷戀于此,小說不惜大段引用傳統(tǒng)文化經(jīng)典,如孔子和老子的經(jīng)典著作、《朱子家訓(xùn)》《孝經(jīng)》《心經(jīng)》等,還大量插入民謠、古詩、對(duì)聯(lián)、議程詞和一些劇本。作者似乎難以逃脫掉書袋之嫌疑。再看李銳的《太平風(fēng)物——農(nóng)具系列小說展覽》(由系列小說構(gòu)成,姑且視為長(zhǎng)篇),販賣知識(shí)之嗜亦非常明顯,系列小說以元代縣尹王禎所著的《王禎農(nóng)書》中提及的十六種農(nóng)具為主題,每種農(nóng)具作一篇小說。除《顏色》《寂靜》兩篇以外,其他小說都包含農(nóng)具圖片、王禎寫的文言文、引自《中國(guó)古代農(nóng)機(jī)具》的說明文等知識(shí)性構(gòu)件。盡管小說試圖通過書寫農(nóng)具在現(xiàn)代化沖擊下的命運(yùn),來借喻農(nóng)民傳統(tǒng)生活方式所遭遇的尷尬和現(xiàn)實(shí)處境的無奈,但小說中的圖片與文字、文言與白話、史料與虛構(gòu),以超文本的方式拼貼在一起,仿若古代農(nóng)具博覽之解說修辭。同樣,阿蠻寫土家族聚居地石柱縣有關(guān)蜀繡的小說《紀(jì)年繡》,也是一部高密度的知識(shí)化小說,如賀紹俊所批評(píng)的那樣:“我在讀《紀(jì)年繡》時(shí),一方面感到知識(shí)量非常大,另一方面又感到阿蠻對(duì)于自己的儲(chǔ)藏太不吝嗇。”⑨
此外,關(guān)仁山的《日頭》亦有夸耀知識(shí)、文化元素過多堆積之弊。小說多次寫魁星閣、狀元槐、天啟大鐘等意象以象征中國(guó)傳統(tǒng)的精神,連人物的命名(如金沐灶)、人物之間的沖突(金家與權(quán)家)也暗含了中國(guó)文化中的五行(金沐灶:金、木、水、火、土)及運(yùn)行規(guī)律(“金”克“木”)。小說還不斷使用《金剛經(jīng)》《道德經(jīng)》《圣經(jīng)》等文化經(jīng)典來表達(dá)主題,有時(shí)借人物之口直接講解文化知識(shí),比如金沐灶作如此思考:“儒家的入世;佛家的因果輪回;道家的清靜無為,追求長(zhǎng)生不老,得道升仙;基督教追求信、望、愛。我看來,這些宗教在最高宗旨上意見不一,甚至爭(zhēng)得厲害。可是細(xì)想想,入口不同,最終的道理是一致的。”⑩不得不說,這般高密度、高濃度文化內(nèi)涵的注入,必然會(huì)沖淡鄉(xiāng)村生活的質(zhì)感。與此類同的,還有孫惠芬的《上塘?xí)贰_@部小說采用地方志的文體,確有其新穎與獨(dú)特之處,但缺陷也十分明顯。作者把上塘村按照“地理”“政治”“交通”“通訊”“教育”“貿(mào)易”“文化”“婚姻”和“歷史”等九個(gè)方面進(jìn)行劃分和敘述。正是這種地方志的書寫方式,使文本中充斥著大量的有關(guān)解釋、說明上塘村的風(fēng)俗民情、地理位置、經(jīng)濟(jì)發(fā)展、社會(huì)狀況的文字。盡管作者也試圖表現(xiàn)鄉(xiāng)村生活的日常狀態(tài),但由于解釋、說明的知識(shí)性文字過多而遭遮蔽,此時(shí)的作者仿若全知全能、喋喋不休的上塘村“導(dǎo)游”。
正是由于對(duì)知識(shí)、文化符號(hào)的過度追求,這些小說類似于民俗學(xué)讀物、地方志、古代文化知識(shí)匯編。閱讀它們,你幾乎看不到當(dāng)下鄉(xiāng)村綿密細(xì)致的日常生活,很少能見到真實(shí)的充滿血肉與肌理的鄉(xiāng)村生活樣貌,很少能觸摸在21世紀(jì)鄉(xiāng)村裂變期,農(nóng)人們豐富的內(nèi)心世界與精神變遷。讀者看到的只是知識(shí)層巒疊嶂的“七寶樓臺(tái)”,卻沒有豐盈搖曳的人倫情感以及鄉(xiāng)村生活的綿密針腳與生動(dòng)韻味。這種依靠知識(shí)、文化填注的鄉(xiāng)村小說缺乏文學(xué)所需要的明敏、鮮活的感性維度,文學(xué)性自然會(huì)大打折扣。
美國(guó)作家亨利·詹姆斯認(rèn)為:小說可以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它確實(shí)在企圖再現(xiàn)人生……不消說你如果沒有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感覺,你就不會(huì)寫成一部好小說?。確實(shí)如此,作家只有企圖再現(xiàn)鄉(xiāng)村人生、有對(duì)21世紀(jì)鄉(xiāng)村現(xiàn)實(shí)的感覺,才能寫出好的鄉(xiāng)村小說。賈平凹在21世紀(jì)的長(zhǎng)篇小說給了我們正面的啟示,《秦腔》《帶燈》等作品或書寫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鄉(xiāng)村遭遇的潰敗,或敘述當(dāng)下鄉(xiāng)村基層政權(quán)的百態(tài),雖然也有小說地域背景的知識(shí)性成分,但作者致力于還原鄉(xiāng)村生活本然的“肉身”狀態(tài),以密實(shí)的生活細(xì)節(jié)洪流,勾描著當(dāng)下鄉(xiāng)村的細(xì)密紋理。何以能如此?事實(shí)上,賈平凹不只是處于書齋、紙上寫作的狀態(tài),他不時(shí)體驗(yàn)、融入當(dāng)下鄉(xiāng)村生活,感知鄉(xiāng)村生活之枝枝蔓蔓的變動(dòng),如他在《帶燈》“后記”中所說:“幾十年的習(xí)慣了,只要沒有重要的會(huì),家事又走得開,我就會(huì)邀二三朋友去農(nóng)村跑動(dòng),說不清的一種牽掛,是那里的人,還是那里的山水……不能說我對(duì)農(nóng)村不熟悉,我認(rèn)為已經(jīng)太熟悉了,即便在西安的街道看到兩旁的樹和一些小區(qū)門前的豎著的石頭,我一眼便認(rèn)得哪棵樹是從西安原生的哪棵樹是從農(nóng)村移栽的,哪塊石頭是關(guān)中河道的,哪塊石頭來自陜南的溝峪。”?
二、寓言化表意的妝容術(shù)
除以知識(shí)作為鄉(xiāng)村敘述的填充料之外,還有一種明顯的趨向,即同樣不屑忠實(shí)地表現(xiàn)21世紀(jì)鄉(xiāng)村的復(fù)雜現(xiàn)實(shí),而熱衷于運(yùn)用理性思維和哲學(xué)思辨的方法改寫或重構(gòu)鄉(xiāng)村,借助寓言化的方式,對(duì)鄉(xiāng)村的歷史與現(xiàn)實(shí)加以變形、扭曲,以便闡釋某種理念。“所謂寓言性就是說表面的故事總是含有另外一個(gè)隱秘的意義……因此故事并不是它表面所呈現(xiàn)的那樣,其真正的意義是需要解釋的。寓言的意思就是從思想觀念的角度重新講述或再寫一個(gè)故事。”?也就是說,寓言化的鄉(xiāng)村書寫,背后隱含著作家想要強(qiáng)烈表達(dá)的思想觀念,內(nèi)置著作家智性思考的隱喻功能。簡(jiǎn)言之,鄉(xiāng)村成了作家意念的“酒杯”,以澆作家個(gè)人智性思考的塊壘。
這種回避當(dāng)下現(xiàn)實(shí),或致力于現(xiàn)實(shí)之夸張、變形的寓言化寫作傾向,閻連科近年來創(chuàng)作的小說可為代表,其《日光流年》《受活》《炸裂志》等長(zhǎng)篇小說均可以視為寓言化文本。《日光流年》里見不到鄉(xiāng)村生活的豐富肌理,多的是各種荒誕的情節(jié):這個(gè)叫三姓村的地方流行著名叫“喉塞”的可怕疾病,村人都活不過四十歲;村民為活過四十歲翻地?fù)Q土,年輕的男人去賣自己的皮,女人出去賣淫;為了巴結(jié)公社領(lǐng)導(dǎo),村主任鼓動(dòng)村民獻(xiàn)出黃花閨女。毫無疑問,這部小說是一個(gè)現(xiàn)代寓言,旨在反思中國(guó)政治文化與民眾生存狀態(tài)的關(guān)系:愚昧導(dǎo)致對(duì)權(quán)勢(shì)的崇拜,權(quán)勢(shì)又更加劇了民眾的愚昧。《受活》同樣具有寓言性質(zhì),小說重點(diǎn)描述殘疾人的生存世界“受活莊”,是如何一步步地納入現(xiàn)代性體制的過程,又如何在這個(gè)過程中經(jīng)歷了失樂園的痛苦。小說展示的生存圖景極具特異性:受活莊是由殘疾人組成的世界,村民個(gè)個(gè)身懷絕技,要成為受活莊人的前提是殘疾;縣長(zhǎng)柳鷹雀要購(gòu)買列寧遺體,在縣里建紀(jì)念堂,并以此吸引游客、發(fā)展旅游,以便帶動(dòng)全縣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不難看出,故事基于對(duì)鄉(xiāng)村歷史、現(xiàn)實(shí)的有意變形與荒誕化,暴露出作者過于明晰、強(qiáng)烈的表意焦慮:即對(duì)建立理想生存方式與形態(tài)的“鄉(xiāng)土烏托邦”的思考。《炸裂志》雖然借用志書這一似真模式,但依舊采用寓言化的寫作方式,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而所謂‘炸裂志’,表面上看是‘炸裂’這個(gè)地方的市志,而實(shí)際則是中國(guó)之‘炸裂’的‘國(guó)志’,也就是說,《炸裂志》以‘寓言’的方式表現(xiàn)了整個(gè)中國(guó)的‘炸裂過程’。”?當(dāng)然,上述寓言化寫作也顯示出閻連科不囿于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傳統(tǒng)寫法,試圖追求審美變革的敘事野心。從他提出的“神實(shí)主義”概念亦不難窺見:“神實(shí)主義疏遠(yuǎn)于通行的現(xiàn)實(shí)主義。它與現(xiàn)實(shí)的聯(lián)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的是仰仗于人的靈魂、精神(現(xiàn)實(shí)的精神和事物內(nèi)部關(guān)系與人的聯(lián)系)和創(chuàng)作者在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上的特殊臆思。”?客觀地說,這種“特殊臆思”的寓言體式,的確擴(kuò)張了小說的話語內(nèi)涵與藝術(shù)張力,但一味以寓言化作為小說表達(dá)意義的唯一手段,未免讓讀者厭惡并產(chǎn)生精神疲憊,也表明作者在小說創(chuàng)作上存在著滿足于自我復(fù)制、自我循環(huán)的短處。
范小青自《女同志》之后就潛心于鄉(xiāng)村敘事,無論是《赤腳醫(yī)生萬泉和》還是《香火》,雖然都充滿荒誕感,但寫實(shí)仍是主脈,而小說《我的名字叫王村》卻是現(xiàn)代主義色彩濃厚的寓言式寫作。小說的開頭就有卡夫卡《變形記》的色彩:“我弟弟是一只老鼠。當(dāng)然,這是妄想出來的,對(duì)于一個(gè)精神分裂病人來說,想象自己是一只老鼠,應(yīng)該不算太過分吧。”?作品的情節(jié)非常簡(jiǎn)單,就是扔掉與尋找的過程,隱喻著現(xiàn)代人的身份迷失與悖論式生存。患有精神分裂癥的弟弟不但禍害鄉(xiāng)鄰,還影響了“我”(王全)的婚姻,整個(gè)家族便做出決定:把弟弟扔掉。扔掉之后,“我”內(nèi)心卻縈繞著深重的罪惡,父親見“我”魂不守舍,就讓我外出尋找弟弟。在“我”尋找弟弟的途中,鄉(xiāng)村百態(tài)逐一暴露,但完全是荒誕不經(jīng)的。同時(shí),“我”在尋找弟弟的過程中也被當(dāng)成精神病,“我”說不清自己的身份,也說不清弟弟的身份。范小青表示:“這樣的設(shè)置是想通過側(cè)面來寫人生的疑惑與不確定,在人的一生中有許許多多解不開的迷惑和疑團(tuán),有許許多多的未知和不確定,如果用正常的眼光來看待這個(gè)不正常的世界,顯得無趣和蒼白,所以,試圖用不正常的眼光來看這個(gè)不正常的世界,會(huì)產(chǎn)生雙重的變形的效果,荒誕、離奇,寫起來更有趣味。”?這一哲學(xué)命題被嫁接到鄉(xiāng)村故事中,綿密的鄉(xiāng)村生活細(xì)節(jié)在追求所謂思想深度與普遍寓意的文本中失去了蹤跡,鄉(xiāng)村故事成了包裹作家理念的外衣。正如有研究者所論:“這也顯示出作者的精英主義立場(chǎng),她恐怕早已失去了感受真正鄉(xiāng)村的能力,只能避實(shí)就虛地寫作‘借鄉(xiāng)村的酒杯,澆個(gè)人心中的塊壘’的現(xiàn)代故事。”?
如果說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是一個(gè)披著鄉(xiāng)村外衣的有關(guān)現(xiàn)代人身份迷失與悖論式困境的寓言,那么趙蘭振的《夜長(zhǎng)夢(mèng)多》(第一部)則是一個(gè)借村莊敘事,表達(dá)有關(guān)個(gè)體存在的荒謬與虛無的寓言。小說中主人公翅膀替父親在塘邊守夜,看守等待分配的魚堆,他鬼使神差地抱著那條傳說中的大紅鯉魚睡著了,竟然被親戚正義當(dāng)成了向上爬的梯子,被人掛上“社會(huì)主義淡水魚強(qiáng)奸犯”的紙牌游街示眾。多少年后,翅膀回到故鄉(xiāng)依然痛不欲生,心里唯一的那份美好,在他回來時(shí),亦頃刻崩坍,感覺世界一切虛無,因?yàn)樗匆娏肆钭约夯隊(duì)繅?mèng)繞、宛若仙女的女孩何云燕,在一場(chǎng)吵架中,從自己的褲襠里,拽出血呼淋啦的紙巾,像糊膏藥一樣貼到了男人的頭頂上。在這里,作者書寫了個(gè)體的孤獨(dú)、異化、憂郁、破碎,有明顯的加繆、卡夫卡、博爾赫斯的氣息。小說很難看到村莊的現(xiàn)實(shí)面影,有太多馬爾克斯、福克納式的寫法,作品中的噓水村,又叫南塘,被作者描寫得充滿神性又陰森可怖:南塘邊上有指縫結(jié)著冰碴,穿著棉襖的無頭鬼;南塘的夜空飄著神出鬼沒的綠瑩瑩的燈籠;南塘的湖底有神秘的洞穴,有噴血的大紅魚……小說中人物亦有著奇詭怪異色彩,項(xiàng)雨迷戀嬸子的豪乳,樓蜂最喜閹公雞,以錘子敲豬崽的腦殼,正義患有血腥氣沖天的血手怪癥。
新疆作家劉亮程當(dāng)年以散文《一個(gè)人的村莊》《風(fēng)中的院門》描寫詩意鄉(xiāng)村的豐富肌理而蜚聲文壇。2006年,他出版的第一部長(zhǎng)篇小說《虛土》卻陷入了寓言化寫作的窠臼。小說通過描寫一個(gè)虛擬、靈異的鄉(xiāng)村世界,表達(dá)著孤獨(dú)與死亡的主題。林白的《萬物花開》通過腦袋里長(zhǎng)了五個(gè)瘤子的鄉(xiāng)村少年的獨(dú)特視角,呈現(xiàn)鄉(xiāng)村生活的荒誕怪異。小說的寓言意味十分明顯,表現(xiàn)出作家對(duì)未經(jīng)規(guī)約和壓制的生命本能的思考,其寓意正如小說標(biāo)題“萬物花開”所示——任何事物都有其自然存在的方式與生長(zhǎng)權(quán)利。
以寓言化的方式書寫中國(guó)鄉(xiāng)村并非始于21世紀(jì)。縱觀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史,尋根文學(xué)是這一創(chuàng)作模式的始作俑者。韓少功的《爸爸爸》即是有關(guān)民族文化思考的現(xiàn)代寓言,小說刻畫的白癡丙崽具有象征意義,他是一個(gè)永遠(yuǎn)保持童稚狀態(tài)、退化返祖的怪物,是集骯臟、蒙昧、粗鄙、丑陋于一身的民族文化劣根的象征體,作者通過這個(gè)形象表達(dá)了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審視與批判。莫言的《紅高粱》、王安憶的《小鮑莊》、李杭育的《最后一個(gè)漁佬兒》亦是如此。公允地說,小說的寓言化傾向是對(duì)中國(guó)當(dāng)代小說中那種教條化、平面化現(xiàn)實(shí)主義的矯正,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文本的思想容量與意蘊(yùn)張力。但寓言化也容易為了一種預(yù)定的思想“深度模式”,而舍棄“生活原則”,把豐富的生活場(chǎng)景限制在理念的框架之中,人為地將多維度的生活符號(hào)化、儀式化。在這一點(diǎn)上,尋根小說之弊很明顯。
時(shí)至今日,上述寓言化的21世紀(jì)長(zhǎng)篇小說,在處理生活上以先在的理念預(yù)設(shè),步了尋根文學(xué)的后塵。這些作家或無法廓清層出不窮的新的復(fù)雜現(xiàn)實(shí),或缺乏直面當(dāng)下的勇氣,只好粗暴地懸置了鄉(xiāng)村現(xiàn)實(shí)的豐富性,以所謂哲學(xué)沉思、微言大義,把對(duì)世界的智性思考看作小說的首要目的,鄉(xiāng)村的現(xiàn)實(shí)情態(tài)僅僅是作者表達(dá)理念的道具與錨地。
如果說尋根小說將鄉(xiāng)土敘事帶上寓言化的軌道,乃是當(dāng)時(shí)出于對(duì)加快改革步伐的熱切盼望,用隱喻的方式反思傳統(tǒng)文化,那么21世紀(jì)作家的鄉(xiāng)村寓言化書寫,除了追求自己創(chuàng)作上的美學(xué)變革外(雖然這種現(xiàn)代主義寓言式隱喻的方法已經(jīng)非常老舊),筆者以為,似乎還有更復(fù)雜的原因。首先是以思辨之長(zhǎng)補(bǔ)經(jīng)驗(yàn)之短。當(dāng)下大多數(shù)作家居于都市,遠(yuǎn)離鄉(xiāng)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穿插于世界繁華都市,瀏覽于名山大川之間,參加各種筆會(huì)、座談會(huì)、評(píng)獎(jiǎng)會(huì)、演講會(huì)大概就是他們書齋以外的生活。偶有回鄉(xiāng),恐怕也是‘省親’式的榮歸故里。這樣‘高居云端’的寫作,怎么可能觸及底層‘新的現(xiàn)實(shí)’和‘深的現(xiàn)實(shí)’”??雖然他們?nèi)狈︵l(xiāng)村生活經(jīng)驗(yàn),但理性、思辨卻是其所長(zhǎng),以“怎么寫”(寓言化)來掩蔽“寫什么”(鄉(xiāng)村現(xiàn)實(shí))的蒼白與單調(diào),成了很多作家揚(yáng)長(zhǎng)避短的策略。有些作家也意識(shí)到了在鄉(xiāng)村生活現(xiàn)場(chǎng)的重要性,如寫有“神農(nóng)架系列小說”的陳應(yīng)松表示:“以為遠(yuǎn)離我們視線的存在就不算存在,遠(yuǎn)離城市生活的生活就不算生活,是極其糊涂的。我寧愿離開那些優(yōu)雅時(shí)尚的寫作,與另一些伏居在深山中的勞作者殷殷的問候和寒暄。”?其次是中產(chǎn)階級(jí)化的精神趣味使然。正如前文所述,21世紀(jì)的中國(guó)“專業(yè)作家”或“職業(yè)作家”已經(jīng)跨入“中產(chǎn)”之列,已經(jīng)超越了追求基本生存需要的階段,更在意心靈體驗(yàn)等精神層面的滿足。以寓言化小說表達(dá)哲學(xué)思辨,進(jìn)行對(duì)世界的智性思考,正是“中產(chǎn)化”作家這種精神需要的文學(xué)化表現(xiàn)。費(fèi)斯克指出:“中產(chǎn)階級(jí)趣味和大眾趣味的區(qū)別,不僅在于前者對(duì)距離和絕對(duì)性的看重,也在于它缺乏樂趣和某種共同體的感覺。”?這樣一種夸示智性、與現(xiàn)實(shí)拉開距離的寫作邏輯,或許正是作家與大眾趣味拉開距離的原因。
三、都市視野的移置術(shù)
正如前文所述,當(dāng)下書寫鄉(xiāng)村的作家大多定居于都市,即便過去有鄉(xiāng)村生活經(jīng)驗(yàn),也早就成了遙遠(yuǎn)的、不再更新的記憶。深受都市文化浸潤(rùn)的他們,少有直接而鮮活的鄉(xiāng)村生命體驗(yàn),擺脫不了以隱性的都市視野作為觀照鄉(xiāng)土的方式。與此同時(shí),鄉(xiāng)村小說的讀者也大多是城市讀者,出于商業(yè)邏輯,鄉(xiāng)村書寫也必須契合都市人的期待視野,把他們的價(jià)值觀擺在優(yōu)先位置。因此,21世紀(jì)很多作家筆下的鄉(xiāng)村想象,大多寄寓著都市主流階層對(duì)鄉(xiāng)村的情懷與記憶,鏡像般地映照著當(dāng)下都市主流群體(或曰中產(chǎn)階層)的現(xiàn)實(shí)處境與精神訴求。
一是將都市欲望化想象植入鄉(xiāng)村現(xiàn)實(shí)。自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消費(fèi)主義文化逐漸深入到中國(guó)社會(huì)的各個(gè)層面。欲望是消費(fèi)主義發(fā)生的動(dòng)力源和最終訴求,“在過去,滿足違禁的欲望令人產(chǎn)生負(fù)罪感。在今天,如果未能得到歡樂,就會(huì)降低人們的自尊心”?。這種追求欲望滿足的消費(fèi)文化,被當(dāng)下的一些作家植入鄉(xiāng)村書寫中,文本里大量堆砌著物欲崇拜、享樂主義的符號(hào)景觀,欲望被裸呈于鄉(xiāng)村大地之上。其中最突出的表現(xiàn),就是許多文本不約而同地寫到了鄉(xiāng)村男女的偷情故事。賈平凹的《秦腔》雖被評(píng)論家譽(yù)為“廢鄉(xiāng)”之作?,但小說所寫的偷情之事卻反復(fù)出現(xiàn),淋漓盡致地寫了夏慶玉與黑娥、三踅與白娥、翠翠與陳慶之間的偷情場(chǎng)景。閻連科的《堅(jiān)硬如水》也大肆渲染高愛軍與夏紅梅的偷情。付秀瑩2016年的長(zhǎng)篇小說《陌上》雖然在表現(xiàn)鄉(xiāng)村生活的豐盈質(zhì)感方面很突出,其筆下的芳村氤氳著鄉(xiāng)村生活的氣氛,但敘事功效不大的偷情元素卻在文本中被多側(cè)面地展示,似乎作者在有意炫耀和展覽作為看點(diǎn)的鄉(xiāng)村“性趣”。如小說中多次寫到香羅、望日蓮、瓶子媳婦、春米等女人在辦公室、小汽車、莊稼地與男人偷情;小說中有權(quán)有勢(shì)、敢闖敢干的男人,如大全、增志、村支書建信、秘書劉銀栓,則無一例外地都喜歡“偷腥兒”。
何以在鄉(xiāng)村現(xiàn)實(shí)的描寫中,男女偷情的局部元素被強(qiáng)化與放大呢?這種滿載偷情元素的鄉(xiāng)土敘事背后,其實(shí)隱藏著都市中產(chǎn)階級(jí)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的愿望,有學(xué)者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現(xiàn)實(shí)生活中中產(chǎn)階級(jí)就關(guān)注自我欲望的極大化滿足,就追捧炫耀性消費(fèi)和富有刺激性的偷情——因?yàn)樵谥袊?guó)當(dāng)前的社會(huì)背景下,炫耀性消費(fèi)和偷情頻率是中產(chǎn)階級(jí)文化身份最有效的表達(dá)方式、是中產(chǎn)階級(jí)顯示財(cái)力、能力和地位的最佳形式。”?此言得之,21世紀(jì)中國(guó)作家之所以熱衷于書寫鄉(xiāng)村偷情故事,實(shí)際上是在兜售情欲,乃中產(chǎn)階層都市人心態(tài)的投射,只不過是把都市情欲的幻夢(mèng)挪至鄉(xiāng)村野地,更添幾分新奇、刺激的色彩。
二是以都市人的懷舊心態(tài)把鄉(xiāng)村伊甸園化。鄉(xiāng)村總是被刻意塑造為都市的對(duì)立面,當(dāng)作矯正和平衡城市文明的一種力量,這實(shí)乃都市發(fā)展建構(gòu)的產(chǎn)物,更多是都市人的視野與心態(tài)使然。赫伊津哈指出:“幻想著回歸自然的懷抱,憧憬著牧羊人式的純真生活,這一夢(mèng)想最為強(qiáng)烈也最為持久。”?尤其當(dāng)工業(yè)化、城市化日益加速之時(shí),這種夢(mèng)想更為強(qiáng)烈。因?yàn)椋瑢?duì)于久居都市的人而言,鄉(xiāng)村仿佛是一個(gè)可以寄托美好情感和回憶的地方,是一個(gè)逃避現(xiàn)代性惡果的“桃花源”,可以緩解焦慮、彌合創(chuàng)傷。為此,文學(xué)作品就著力書寫鄉(xiāng)村的純潔靜謐,其中的鄉(xiāng)村沒有貧困、勞作、污穢,只有令人神往的田園風(fēng)光、閑情逸致和美好人性,鄉(xiāng)村生活被完全理想化、詩意田園化。這種寫作路向,在中外文學(xué)史上一直未曾間斷。早在英國(guó)伊麗莎白時(shí)期,著名詩人西德尼和斯賓塞便對(duì)鄉(xiāng)村生活的恬靜、淳樸予以贊頌,后來的浪漫派詩人華茲華斯、柯勒律治、濟(jì)慈等亦是把鄉(xiāng)村視為工業(yè)文明和城市生活的救治之方。就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史而言,沈從文、廢名、汪曾祺、遲子建等作家的創(chuàng)作都在這一思想脈絡(luò)上。
21世紀(jì)以來,一些長(zhǎng)篇小說或?qū)⑧l(xiāng)村復(fù)雜現(xiàn)實(shí)徹底詩意化,唯有民風(fēng)淳樸、人心善良、生活寧?kù)o、溫情氤氳;或?qū)⑧l(xiāng)村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張力和倫理道德深層裂變,化約為一首清澈動(dòng)人的牧歌,只有自由、和諧與靜穆;還有的傾向于挖掘邊地鄉(xiāng)土世界的傳統(tǒng)風(fēng)俗和生活方式,以構(gòu)建都市人難得一見的文化奇觀。方英文的《后花園》凸顯了這方面的主題,小說寫一個(gè)大學(xué)教師宋隱喬因解決內(nèi)急下了車,被啟動(dòng)的火車遺棄在陜南農(nóng)村的青山綠嶺中。裝有他各種身份證件及手機(jī)的行李都留在了火車上,作為現(xiàn)代性符碼的身份證和手機(jī)的遺失,暗喻著他與現(xiàn)代性的告別。他來到了一個(gè)叫娘娘窩的村莊,那里純潔安詳、美妙和諧,人置身其中享受著詩意的安頓。趙本夫的《無土?xí)r代》設(shè)想了一個(gè)具有鄉(xiāng)村詩意化的木城:“月牙兒落得很快,緊接著就是滿天繁星。天也一下子暗下來。大地上的一切都變得朦朧而神秘了。荒野的風(fēng)漫進(jìn)木城,大大小小的樹木和玉米地都發(fā)出簌簌的聲響。”?更多的小說則書寫詩意浪漫的邊地鄉(xiāng)土世界,如安妮寶貝的《蓮花》、黨益民的《一路格桑花》、楊金花的《天堂高度》、七堇年的《大地之燈》等文本也都極力渲染邊地鄉(xiāng)村原生態(tài)風(fēng)景的美好,是奇異、純潔、神圣、充滿著浪漫氣息和脫俗氣質(zhì)的“香格里拉”,是產(chǎn)生純美愛情或升華精神格調(diào)的天堂。
21世紀(jì)中國(guó)作家這種將鄉(xiāng)村伊甸園化的寫作方式,除了是對(duì)過去文學(xué)傳統(tǒng)的慣性沿襲外,還與滿足當(dāng)下中產(chǎn)階級(jí)的審美需求相關(guān)。恰如溫迪·J.達(dá)比所說:“具有審美愉悅的田園風(fēng)光是這樣創(chuàng)造出來的:把農(nóng)業(yè)過程、農(nóng)業(yè)勞動(dòng)者,甚至整個(gè)村莊從視線里清除出去,留下無人的、如畫的風(fēng)景,使特權(quán)觀賞者能夠觀賞純粹的畫面。”?因此,21世紀(jì)長(zhǎng)篇鄉(xiāng)村小說構(gòu)建這種伊甸園式的鄉(xiāng)村神話,其實(shí)隱含著當(dāng)下中國(guó)都市中產(chǎn)階級(jí)的精神境遇與心理代償愿望:期望鄉(xiāng)土世界的純凈美好,作為逃避環(huán)境污染、生態(tài)破壞、信任斷裂等現(xiàn)代性惡果的避難地,同時(shí)亦期望文本中的鄉(xiāng)土世界成為“故鄉(xiāng)”,以疏解他們遠(yuǎn)離故土的失落和懷念。正因如此,作家就很難顧及全面洞悉鄉(xiāng)村現(xiàn)實(shí)的綿密肌理,也無暇剖析農(nóng)民精神世界的幽微了,唯有提供與都市景觀截然不同的“詩意”或“奇觀”景象,供都市人把玩。
結(jié) 語
顯然,21世紀(jì)長(zhǎng)篇小說以文化展演之“知識(shí)填充”、智性夸示之“寓言表意”、心理代償之“都市置換”,作為想象和書寫鄉(xiāng)村的三種方法,無疑是中產(chǎn)階級(jí)的審美邏輯和話語體系建構(gòu)的審美程式,表現(xiàn)出創(chuàng)作主體強(qiáng)烈的中產(chǎn)階級(jí)趣味。這種躲在象牙塔里以精英主義心態(tài)來書寫鄉(xiāng)村的弊端很明顯:以這種方式書寫鄉(xiāng)村,只能是一種無關(guān)痛癢的“自己和自己玩”的紙上游戲;作家筆下的鄉(xiāng)村只能是一種蒼白而空洞的觀念化鄉(xiāng)村,與鮮活而實(shí)在的鄉(xiāng)村相去甚遠(yuǎn);作家也無法體察當(dāng)下農(nóng)民生活與精神的本然狀態(tài)。
在《致斐·拉薩爾》的信中,恩格斯曾有過精辟的忠告:“我們不應(yīng)該為了觀念的東西而忘掉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東西,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亞。”?雖然今天要求已經(jīng)“中產(chǎn)階級(jí)化”的作家們住在農(nóng)村,與農(nóng)民生活在一起不太現(xiàn)實(shí),但他們完全可以接續(xù)現(xiàn)實(shí)主義令人尊敬的“體驗(yàn)生活”之傳統(tǒng),從書房走向村野,對(duì)21世紀(jì)的中國(guó)鄉(xiāng)村投以深情的關(guān)注,以擴(kuò)張自己對(duì)鄉(xiāng)村新的感知,而不是每天沉迷于都市中產(chǎn)階層生活之安逸,依賴媒介化的農(nóng)村信息,自戀地意淫遠(yuǎn)方的鄉(xiāng)村大地。
① 韓少功:《作家的創(chuàng)作個(gè)性正在湮沒》,載《探索與爭(zhēng)鳴》2006年第8期。
② 參見陸學(xué)藝主編《當(dāng)代中國(guó)社會(huì)階層研究報(bào)告》,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頁。
③ 程光煒:《中產(chǎn)階級(jí)時(shí)代的文學(xué)》,載《花城》2002年第6期。
④ 何平:《新世紀(jì)鄉(xiāng)村文學(xué):文學(xué)鄉(xiāng)村與現(xiàn)實(shí)鄉(xiāng)村的偏離》,載《文藝報(bào)》2012年10月31日。
⑤ 田志凌、孫曉驥:《新鄉(xiāng)土文學(xué):文學(xué)離今日鄉(xiāng)土有多遠(yuǎn)》,載《南方都市報(bào)》2007年3月15日。
⑥ 閻連科:《返身回家》,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版,第52頁。
⑦ 王彬彬:《“中產(chǎn)階級(jí)氣質(zhì)”批判——關(guān)于當(dāng)代中國(guó)知識(shí)者精神狀態(tài)的一份札記》,載《文藝評(píng)論》1994年第5期。
⑧ 參見《2004·反思與探索——第三屆青年作家批評(píng)家論壇紀(jì)要》,載《人民文學(xué)》2005年第1期。
⑨ 賀紹俊:《阿蠻〈紀(jì)年繡〉:典型的知識(shí)寫作》,載《文藝報(bào)》2016年1月25日
⑩ 關(guān)仁山:《日頭》,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4年版,第302頁。
? 亨利·詹姆斯:《小說的藝術(shù)》,楊烈譯,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下冊(cè),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11—512頁。
? 賈平凹:《帶燈》“后記”,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4年版,第356—357頁。
?弗雷德里克·杰姆遜:《后現(xiàn)代主義與文化理論——杰姆遜教授講演錄》,唐小兵譯,陜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頁。
? 劉汀:《〈炸裂志〉:書寫中國(guó)現(xiàn)實(shí)的另類文學(xué)標(biāo)本》,載《中國(guó)圖書評(píng)論》2014年第4期。
? 閻連科:《發(fā)現(xiàn)小說》,南開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182頁。
? 范小青:《我的名字叫王村》,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3頁。
? 周韞:《范小青談新作,每個(gè)人都可叫“王村”》,載《中華讀書報(bào)》2014年8月27日。
? 徐剛:《小說如何切入現(xiàn)實(shí):近期幾部長(zhǎng)篇小說的閱讀札記》,載《南方文壇》2016年第1期。
?邵燕君:《與大地上的苦難擦肩而過———由閻連科〈受活〉看當(dāng)代鄉(xiāng)土文學(xué)現(xiàn)實(shí)主義傳統(tǒng)的失落》,載《文藝?yán)碚撆c批評(píng)》2004年第6期。
? 陳應(yīng)松:《靠大地支撐》,載《小說選刊》2003年第8期。
? 約翰·費(fèi)斯克:《理解大眾文化》,王曉玨、宋偉杰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頁。
? 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趙一凡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9年版,第117頁。
?參見《秦腔:一曲挽歌,一段情深——上海〈秦腔〉研討會(huì)發(fā)言摘要》,載《當(dāng)代作家評(píng)論》2005年第5期。
? 向榮:《想象的中產(chǎn)階級(jí)與文學(xué)的中產(chǎn)化寫作》,載《文藝評(píng)論》2006年第3期。
? 約翰·赫伊津哈:《中世紀(jì)的衰落》,劉軍等譯,中國(guó)美術(shù)學(xué)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頁。
? 趙本夫:《無土?xí)r代》,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第361頁。
?溫迪·J.達(dá)比:《風(fēng)景與認(rèn)同——英國(guó)民族與階級(jí)地理》,張箭飛、趙紅英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頁。
? 恩格斯:《致斐·拉薩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