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面
王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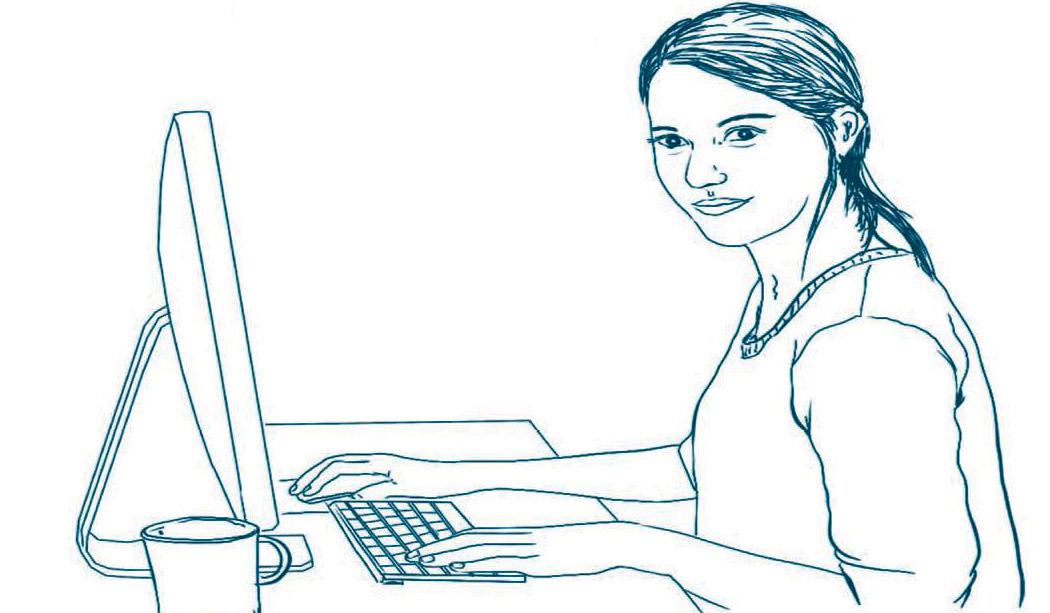
行走世間,誰都想體面點。穿戴得干干凈凈,打扮得整整潔潔,出落得大大方方。樹活一張皮,人活一張臉。這張臉,就是體面。
有沒有面子,對相互陌生的人來說,首先是看外表。男人頭發(fā)梳得紋絲不亂,甚至油光可鑒,胡子刮得寸草不生,如剝光的雞蛋,走在街上,神氣活現(xiàn),自覺很有面子的樣子。女人出門前,第一樁事就是收拾自己的臉,描眉畫唇,涂脂抹粉,哪怕有再急的事,也要稍加淡妝,容不得半點馬虎。女人這張臉,是名副其實的面子。臉面有了,接著就是穿戴。魯迅對上海男人要面子的穿著,曾有十分精彩的描述。他筆下,住在石庫門里的上海男人,睡覺之前,總要將西褲折出一條縫,然后小心翼翼疊壓在枕頭底下,第二天出門時,原樣拿出來穿上,褲子照樣筆挺,不見絲毫褶皺,衣衫鮮亮夾著包上班去。這就是過去“只重衣衫”的某些上海人的體面。所謂“可以沒有里子,不能沒有面子”,也由此而來。當時,上海女人要體面的流行說法是:長得可以不漂亮,穿得不能不漂亮。
過去經(jīng)濟條件比較拮據(jù)時,“赤腳穿皮鞋,赤膊穿西裝”的現(xiàn)象時有所見。這種滑稽趣相,只是證明,面子比里子重要得多。因為這樣才顯得體面。
體面是一種自我感覺,也是給人的感覺。有面子的體面只是表象,真正的體面是由體及面,是內(nèi)涵的折射,也暗含著修養(yǎng)與氣質(zhì)的高低。
體面與貴賤無關,與廟堂之高和江湖之遠無關,與財富多少無關。有人腰纏萬貫,揮金如土,出入燈紅酒綠場所,過著醉生夢死的日子。更夸張者,手腕上戴著500萬元金表,希望贏得周遭羨慕的目光,自覺無上體面。殊不知,此種體面,虛榮其外,虛空其心。同是富者,李嘉誠在世上算得上出類拔萃了,可他手腕上戴了20多年的,是只售20多美元的普通手表。李嘉誠戴著這樣的表與商業(yè)巨頭會晤,與各國政要見面,肯定覺得是得體而合面的。由此折射李嘉誠的體面觀,不是虛浮輕飄,而是自我感覺里的踏實與滿足。他很有條件用幾百萬元甚至幾千萬元買個表來“體面”一下,但這不是他會去做的事。體面是一種相適應于內(nèi)在的自我認知和滿足。一個空洞的軀殼,就是貼滿金涂滿銀,光可鑒人,自以為體面得很,卻照出了空虛淺薄。因為不得“體”,面上的光彩,也就扭曲、錯位,毋寧說是出丑。
所謂“繡花枕頭一包草”,所謂“打腫臉充胖子”等老話,便是對那些“蹩腳體面”者的形象寫照。
《老殘游記》中有這樣一句:“體面一些的人,總無非說自己才氣怎么大,天下人都認識他。”顯然,體面有時是一種社會身份的表征,是周遭社會對自己的認定,以及受此軟環(huán)境所影響的個人自我認定。
一般人的印象中,孩子大學畢業(yè),進了銀行或保險公司,考上公務員進了政府部門,就是找到了體面的工作,走出走進,自覺體面,全家人也跟著有面子。如果過了若干年,公司給加薪或給予升遷提拔,那個體面,就更不用說了。其實,體面在于社會身份的體認,在于你周遭環(huán)境的價值取向與審美趣味。就比如在一個理智良性的環(huán)境中,做大學教授固然體面,小學教師和幼兒園老師也應該同樣風風光光;在摩天大樓里做白領固然體面,在風里雨里來回奔跑從事快遞工作,自食其力甘苦自知,也不應覺得有失體面;開豪車拎名牌包招搖過市,沒有太多人驚訝于這樣的“奢侈體面”,而騎單車背帆布包串街走巷,大多數(shù)人安然于這種簡單的體面;在掌聲鮮花里走上紅地毯,成功的體面令人欣羨,而冬日里迎著寒風在大街上揮動掃帚,勞作的體面令人肅然起敬……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體面,不同的崗位有不同的體面。社會健康價值觀清正了,體面就不再流于表層的虛榮,而是一種實在,一種由內(nèi)而外的氣質(zhì)和自信。
當然,體面最直接地由自我內(nèi)心感受所決定。若做不到淡定與平靜,而是在乎別人的認可,那在一個不知體面為何物的社會中,你最有可能跟在別人或勢利或高低搖擺的目光中,氣喘吁吁。
(易茗摘自《解放日報》2017年11月12日 圖/錦躍)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