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鵝
唐鳳華
我的母親是個勤勞善良的農村婦女,每天都忙忙碌碌的,她養育了我們兄妹八人,雖然目不識丁,可說起話來一套一套的,總是富有哲理,母親身材瘦小,一張標準的瓜子臉,一雙大眼睛慈眉善目的,她為人隨和,從沒跟誰紅過臉,左鄰右舍的,誰家缺東少西的,她總是解囊相助。
母親最忙的時候是每年的三四月份,爸爸的話就是“你媽又犯癮了”一個鵝毛墊子、一個溫度計,加上個長方形的木頭框,蓋上些閑置的被褥,放在炕頭上,就是媽媽的孵化工具,到第七天晚上開始照蛋,我擠到媽媽身邊,欣欣然見證了一個蜘蛛大小的生命在蛋殼里旋轉著,到三十天后就能聽到咣咣的敲擊聲,小鵝在里面待得不耐煩了,也有的一聲不響,這時母親便挽起袖口,開始做“剖腹產”手術了,把蛋皮挑開,露出鵝嘴,鵝雛就不會憋死了,母親嘴對嘴地喂它們水喝,小鵝們也毫不客氣地張開大嘴,吸吮著母親送給它們的玉液瓊漿,這些吃小灶的鵝雛,吸收著營養,不再東倒西歪了,一天天歡實起來,等小鵝長出翅膀,爸爸甩動著長鞭,大部隊就出發了。我家住在村西頭,離西水泡子四五十米遠。小鵝一出門就邊走邊捋草,扇動著翅膀在水中玩耍,到晚上一個個歪歪著嗉子,昂首挺胸就像凱旋的戰斗英雄,我把院門關得窄一點,認真地清點查數。等再大一點這些鵝干脆就在水泡子里“長托了”。等水要結冰時,各家開始到水泡子邊吆喝自家的大鵝。
記得我上二年級時,有一只大雁鵝遲遲沒有回家,三姐放下書包就去找鵝,還有個姓王的姐姐,她家也丟了一只鵝,小姐倆搭伴東頭西頭、前屯后屯找了個遍,也不見蹤影,幾天后,王姐家的鵝找到了,三姐還是一心找鵝。又找了十多天,連個鵝毛都沒找到,當時“找鵝”是家里的頭等大事。這只大雁鵝是我的最愛,因為二十多只鵝里,它唯一不是白色的,由于長得像大雁,媽媽給它起了名字叫大雁鵝,這只大雁鵝也是媽媽嘴對嘴吃小灶長大的鵝,大雁鵝你究竟在哪里啊?
一個春暖花開的星期天,媽媽讓我到離家三里多路的興隆去賣鵝蛋,我挎著一筐鵝蛋拎著小我四歲的妹妹到興隆道北老商店門口賣鵝蛋,快中午了,一位衣著整齊的中年男人(后來才知道他是興隆醫院的競大夫)問我:小孩,包了兩毛二行嗎?我說:行。于是我手里攥著六塊六角錢,邊蹦帶跳地跑回了家,我第一次嘗到了貨幣交換的滋味,心里樂開了花。中午吃飯想不到家人漫不經心的對話,令我食不下咽。上午那只大雁鵝回來了,爸爸眼尖,一眼看見那只丟了一冬天的大鵝回來了,興沖沖的樣子,伸長脖子咯嘎直叫,鵝們像久別的親人一樣叫成一團,可沒想到村里的一位大嬸不期而至,她說來找鵝,母親是個精明人,一眼看透了事情的來龍去脈,笑著說:“大妹子,這鵝你喂了一冬天,也在你家下完了蛋,現在一個啞巴牲畜轉彎抹角一里多路奔回家,咱們就遂了鵝的心愿吧。”可大嬸卻說:嫂子,這鵝是我家的。“你說是你家的你有記號嗎?我家的鵝一出蛋殼我就在右巴掌外側剪一剪刀,你看看個個都有個豁口清一色。”媽媽的話說得大嬸無言以答,低頭走了。
看著大嬸遠去的身影,母親心一軟改變了主意,抓起這只鵝不由分說攆上大嬸,塞到她懷里,大鵝掙扎著、哀叫著,聽到這兒、我眼淚涮涮地流下來。大雁鵝呀,你多像一個被拐賣的小孩,歷盡千難萬險回到親人懷抱,可是又讓親人把你當成了討好別人的工具,我在心里責備母親,你真傻,明明是自家的鵝,為啥要送給別人,母親看透了我的心事說:“你太小、長大了就知道了咱家鵝多,不差這一個。”我回答道:“家里鵝多你還找?”“兩碼事,一紙書來只為墻,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媽媽的話讓我疑惑不解。
十多天后,我剛剛淡忘這件事,三姐又宣布了一個爆炸性新聞:“那只鵝回去后,不吃不喝,想家絕食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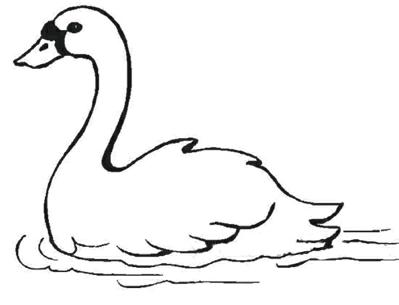
我氣得直跺腳,可憐的大鵝啊,你可不是一只呆頭呆腦的大傻鵝,你是個有靈性的生命,是媽媽用愛把你喂大,你對家的思念甚至超過了有思想的人類,有多少不孝子女不懂報恩,不思雙親,你經歷了怎樣的撕心裂肺,才讓你痛不欲生,才讓你橫下心來,才讓你選擇了以死抗爭。第二天上學,我擦干了眼淚,為紀念這只冤屈的靈魂,為鵝報不平,給那家拿走我家鵝的一個姐姐起了個綽號:“大雁鵝”。漸漸地,綽號傳開了,我心里的氣也消了許多。
歲月悠悠、花開花落。二十多年后,母親身體日漸消瘦,她患的是肺心病,經常住院,在母親面前唯一能讓我感到滿意的是我在1995年寫了一篇《婆婆裝聾不作啞》的文章,發表在農墾報生活之友欄目上,這篇文章歌訟了母親在兒子和媳婦吵架時,不護短,將心比心,為兒媳婦爭理,是個通情達理的好婆婆。
母親最喜歡聽我給她讀這篇文章,那天在管局醫院,我和母親面對面坐在床上,我有表情的朗誦,母親目不轉睛地注視著我,沉浸在往事的回憶之中,那一刻熱血在母女心中回流,靈魂在相互欣賞,幸福在眉宇間傳遞。可惜幸福太短暫,我的文章太短小,媽媽的評語是:“寫得好,我這輩子沒文化,是個睜眼瞎。”這是最后一次評語,也是她的遺言。三天后,一九九六年一月二日,凌晨一點半鐘,她還自己起床去的衛生間,在上床后就一睡不起了,沒有一聲呻吟,沒驚動任何人,她曾經告訴過我:我走后,你們都好好過日子,不要難過,你們對我太好了……
這是一個滴血的凌晨,風使勁地撕扯著,骨肉分離,肝腸欲斷,母親的身體在變涼,我的淚水在結冰,可愛的老母親,安詳地走了。帶著微笑,帶著些許的遺憾走了,化作一縷青煙一片白云,只有不盡的思念伴隨著歲月千絲萬縷……
感謝您嘔心瀝血,粗茶淡飯,讓我們吃的有滋有味,一個一個膀大腰圓,您卻日漸消瘦,八十多斤的體重,還樂呵呵地叫我們“個半人”,您燉的大頭菜燉大鵝,獨一無二,天下一絕,大鵝的色香味仿佛就在眼前,閉上眼睛舌頭根出汗了,口水只往肚里咽,您明知道咱家的口糧緊張,卻常把糧票塞給鄰居李二娘,您說她家男孩子多,可自己去撿凍土豆,碾成細面包黑面蒸餃,您把愛送給了別人,您也是一個幸福的人,聽著您的呼吸,撫摸您溫柔的小手,感受著您人格的魅力,感謝您給了我一個幸福的童年,一個與愛相伴,豁達大度的人生,眨眼間一個轉身,我雖然已經鬢染霜花,但對您的思念與日俱增。

曾幾何時,淚水與思親常伴,此刻淚水化作墨香,在白色的箋紙上游走,心靈受到震撼,母親的形象更加豐滿,母親常說自己沒文化,是個睜眼瞎,究竟什么是文化呢?作家梁曉聲概括為內心的修養,無需提醒的自覺;以約束為前提的自由;為別人著想的善良。按照他的意思,那么我的母親也應該是個文化人,我還是半信半疑,又面對面地請教了一位文友,她說:“一個人有沒有文化,跟她識字多少、讀書多少都沒有關系,有學歷的人不一定有文化,沒學歷的人不一定沒文化”。
我終于恍然大悟,我的母親原來也是一個“文化人”,真遺憾是我的無知造成了母親帶著遺憾而去,母親,今天女兒要為您重寫“墓志銘”,您,我的母親——是一位勤勞善良心明眼亮的文化人!母親,您聽到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