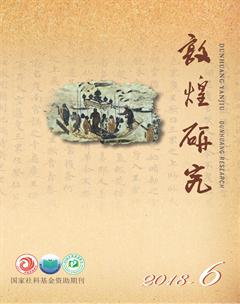四川廣安沖相寺定光佛龕像研究
符永利 王守梅
內容摘要:四川廣安市肖溪鎮的沖相寺石窟是一處重要的隋唐石窟寺,其中開鑿最早的定光佛造像,題材特殊,造型獨特,內含豐富的歷史信息。通過樣式類型分析,可看出此尊定光佛像在發展變化過程中屬于簡化類型,所飾的太陽紋頭光在沖相寺石窟中有一定的典型性。這種頗具特色的頭光可能是由古印度犍陀羅起源,經西域、河西從天水、漢中傳入巴中,再經巴中沿渠江傳至沖相寺。定光佛造像的著衣方式也獨具特色,而其手印更蘊涵特殊含義,應表現的是本生授記和三童子緣。該龕造像反映的是早期定光佛信仰,屬于正統信仰,與五代之后流行的晚期閩西定光佛信仰不同。隋代之所以在此開鑿這尊定光佛像,最重要的原因是受到求得授記、祈愿成佛思想的影響。
關鍵詞:沖相寺石窟;定光佛;類型;年代;造型;頭光;服飾;信仰
中圖分類號:K878.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06(2018)06-0038-11
沖相寺石窟位于四川省廣安市廣安區肖溪鎮沖相村八組,地處渠江上游北岸臺地上,距廣安城區60多公里,地理坐標為N30°42′20.41″,E106°54′48.21″(圖1)。據我們2012年調查資料顯示,沖相寺尚存摩崖龕窟58個、造像261尊(不計浮雕)、題刻77幅以及大小不等的崖墓14座。主要分布在大雄寶殿之后的定光巖及其東西兩側以及獅子山的崖壁上,東西綿延約200余米,自西向東通編58號。作為定光佛道場的沖相寺,最著名的當屬定光佛龕,此龕編號為K26,位于定光巖中段正面上方偏左側,在此面巖壁的最高處,位置顯著,造像獨特,研究價值頗高,也是沖相寺石窟中保存較為完整的一龕造像。
關注此龕造像的學者并不多,相關研究論文僅見四篇,如劉敏先生的《廣安沖相寺摩崖造像及石刻調查紀要》[1]、《廣安沖相寺錠光佛石刻造像考略——兼論錠光佛造像的有關問題》[2],另有翁士洋的《廣安沖相寺與定光古佛信仰》[3]、楊洋的《四川廣安沖相寺石窟研究》[4]。劉敏先生的調查開展較早,為后來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并對造像特征作了初步歸納,同時提出一些可供探討的問題,頗具啟示意義,但由于某些客觀原因,文中存在尺寸數據有誤、細節描述偏差較大等問題。翁士洋先生主要討論定光佛信仰,認為沖相寺定光佛造像反映的是正統信仰,而非五代宋初興起的定光佛民間信仰。楊洋的碩士論文在第四章將沖相寺定光佛造像與其他地區的同類造像作了比較,揭示出表現在時代、服飾與手印諸方面的特殊性,也對其重要價值有了進一步認識。總體看來,沖相寺定光佛造像研究仍舊存在一些問題:第一,調查方面的基礎數據有待實地復核,予以重新糾正確定;第二,造像特征需要深入而全面地歸納提煉,涉及到頭光、肉髻、面相、體型、姿態、身體比例、著衣方式、手印等方面;第三,需將其置于更宏大的中外定光佛造像體系之中,相互比較,于分類定型中認識其在歷史上的地位以及相關的傳播源流等問題;第四,特殊手印的含義不明,有待解讀。本文僅就部分問題試作論述,請專家指正。
一 基本概況
沖相寺定光佛龕(編號K26),為外方內圓拱形龕制,龕寬170、高242、深75厘米。龕內正壁雕一尊立佛,像高220厘米;頭后雕有圓形頭光,內飾放射狀鋸齒紋,圓光外為彩繪的尖桃形,并有彩繪的身光一直延伸至龕沿;磨光高肉髻,面相較方,彎眉睜眼,鼻口略殘,神情莊重,額頭稍窄,下巴渾圓,長耳厚大,頸飾三道;窄肩,身著雙領下垂式袈裟,胸下衣紋呈U字形,衣角下部飾有萬字紋;雙手向身體兩側半伸,左手掌心朝上,右手掌心朝下;腰下著長裙,赤雙足各踩一朵仰蓮圓踏。踏下為長方形低臺(圖2、圖3)。
二 年代問題
定光佛造像的年代一般被認為是隋代,直接依據是龕外左側壁上的一則楷書題記,內容如下:
永……(熙)……/王知球寫同……父(與)子向……/先發心……主……沖相寺/定光(佛)并給貢木□未慶訖會……/銘意(題言)□清者……(會)……先……/……財帛公□□慶(開)/皇□年十一月十八日設(齋)題謹記/永(為)福□□記/”。
由于風化嚴重,僅能釋讀部分字句。由題記可見,定光佛龕像當開鑿于隋代開皇年間(581—600)。
又據立于唐開元六年(718)的《大唐渠州始安縣沖相寺七佛龕銘碑》載:
佛法尊于皇唐。修龕者,使持節、渠州諸軍事主長史丁正已也。……按部始安,遂屆于藥寺。其寺,隋開皇八年流江郡守袁君等所立。皇朝奏修祠額,寺有石跡,削成建造此龕。[5]
這里顯示,沖相寺本名藥寺,建于隋開皇八年(588),唐改名沖相寺。《廣安州志》卷39又云:“唐初賜額曰‘沖相,自宋齊至唐均隸始安縣,宋元均列渠江縣。”此處又表明沖相寺在宋齊之時已經建立。而民國《重修沖相寺記》中又載有“(沖相寺)創于晉,稱靈山,梁(大)同為藥寺”等。筆者贊同翁士洋先生的見解,即“沖相寺確切的建造年代,據傳為晉代,有待考,但至少可以確定在隋開皇八年前已經建立”,“隋開皇八年流江郡守袁君等所立的并非是寺院,而是石刻佛像。”[3]沖相寺石窟的始鑿年代當在隋開皇八年。
再從現存龕窟的分布區域及造像特征來看,分布在定光巖中段正面巖壁的龕窟是時代最早的,而定光佛龕又處此壁頂部中間,俯臨全境,位置尊崇,按順序也應是此區最先開鑿的。故可將開鑿于隋開皇年間的定光佛龕,明確置于具體的開皇八年(588)。
此后定光佛龕應當經過后世多次裝修,但基本原貌未變。現可明確的有兩次,主要集中在明清,一次是在明萬歷三十三年(1605),一次是在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明代萬歷題記見于定光佛龕左側,豎排兩行,楷書,內容為:“萬歷三拾三年□……/始□裝功德……”。可見這是一次裝修功德活動。清代道光裝彩之事見于《裝修沖相寺佛像石記》,此則題記位于定光佛龕下方,涉及的相關內容為:“……是歲十月二十七日,吾族好事者裝彩定光古佛,父老云集,恭讀圣諭,以宣揚天子之雅化……郡庠蘇穆如謹記。大清道光戊申冬月朔四日,鐫石工許世興刻。”蘇穆如曾在沖相寺設館兩年,對此事比較熟悉,而且裝彩定光佛像的也是蘇氏之族人。
三 樣式類型
以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而論,可以確定為定光佛的造像多為立像,也有跏趺坐式,有單體圓雕造像、背屏式造像,亦有造像碑,石窟造像中除了圓雕之外,還有浮雕、壁畫等形式,質地不一,形式多樣。此處僅按組合關系作為標準,將之分為五型。
(一)A型:七佛組合
七佛中的定光佛,即迦葉佛[6]。釋迦之前的六佛是指毗婆尸佛、尸棄佛、毗舍浮佛、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其中前三佛屬于過去莊嚴劫佛,而后三佛以及釋迦佛則屬于現在賢劫佛,彌勒佛屬于未來星宿劫佛。故在一般的七佛造像中,定光佛造像是存在的,只是無有特殊標識,除非題名之外,無法具體分辨到底是哪一尊。
一般呈并排形式,按坐、立姿態的不同,可分為兩式:
1. A型Ⅰ式:跏趺坐式
實例如云岡第10窟后室南壁拱門與明窗間的方形帷幕龕內,七佛均結跏趺坐,中央佛舉右手,兩側三佛均施禪定印。
2. A型Ⅱ式:立式
實例如云岡第13窟南壁中層,在窟門與明窗間的三個屋形龕內雕七尊立佛,佛像均為波浪發式,著褒衣博帶式袈裟,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施與愿印。
(二)B型:三佛組合
三佛組合造像中,一般會有“儒童布發”{1}的情節作為其標識。按是否處于三佛的核心主尊位置,可以分為兩式:
1. B型Ⅰ式:處于三佛中的左側或右側
實例有阿富汗肖托拉克石雕三佛造像,年代在公元4~5世紀。三佛均呈立像,中間為現在世釋迦牟尼佛,比較高大,左右代表過去世的定光佛與代表未來世的彌勒佛略低。定光佛位于右側,缺頭部,右足前跪一童子,以發布地,表現的正是“儒童布發”故事[7]。
2. B型Ⅱ式:處于三佛的中間主尊位置,著重凸顯了定光佛的地位
實例有云岡第18窟,年代在云岡第一期(453~465),正壁主尊為立佛,高15.5米,東西兩壁各有一尊立佛,高9.1米,小森陽子先生根據主尊右下方的小像可能是儒童,將其判定為定光佛[8]。
(三)C型:與弟子、菩薩組合
定光佛為龕內主尊,立式造型,左右或脅侍二菩薩,或脅侍二弟子二菩薩,與其他諸佛造像的組合形式相似。可以分為兩式:
1. C型Ⅰ式:一佛二菩薩組合
實例見于龍門古陽洞北壁西部比丘尼法行造像,為帳形龕,龕內雕像已不存。據大村西崖著《中國美術史·雕塑篇》附第474圖看,龕內主尊為立佛,發愿文云:“永平三年(510)四月四日,比丘尼法行□用微心,敬造定光石像一區并二菩薩,愿永離煩惚,無有苦患。愿七世父母,□緣眷屬,現在師徒,亦同此福。亦令一切眾生,咸同斯慶。”由發愿文可知,造像為定光佛脅侍二菩薩。
2. C型Ⅱ式:一佛二弟子二菩薩組合
實例亦見于龍門古陽洞北壁,位于此壁下部,龕內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主尊是菩薩裝的立佛,有發愿文曰:“延昌三年(514)□月十二日,清信女劉四女為亡□造定光像一區。”這尊定光佛特殊之處在于身著菩薩裝。
(四)D型:本生或因緣故事組合
主要表現授記及三童子獻施。按照表現內容的不同,又可分為三式:
1. D型Ⅰ式:授記本生
跟定光佛相關的授記本生,其實就是孺童本生故事,按照情節表現的復雜程度可以分為兩個亞式:
(1)D型Ⅰa亞式:單個場景的單幅表現形式。
一般選取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情節來反映故事主題。儒童本生常見的情節主要為儒童散花或者布發,此式主要表現其中的一個場景,屬于一圖一景式。
僅表現儒童散花情節的圖像實例,多見于克孜爾石窟,如第100號窟右甬道外壁、第69窟主室右壁右側及第163窟的定光佛壁畫等[9]。
僅表現儒童布發情節的造像實例,可見于云岡石窟,僅作一立佛,儒童長發披地,佛像蹈足而過,主要在第19-1、11-16、5-10、5-11、13-16、15、34、35、38、39等窟[10]。
(2)D型Ⅰb亞式:一圖多景或連續畫面形式。
在定光佛立像周圍,將儒童買花、散花、布發、騰空的授記故事多場景式或連續性地予以表現,這種具有故事情節的、合并多個片段的畫面構圖,被稱之為合并敘述[9]。此式造像,在犍陀羅地區主要采用浮雕形式,時代多在公元2~3世紀,畫面中孺童從買花、散花、布發到受記騰空,出現了四次,定光佛則以高大的形象占據畫面中心位置,如拉合爾博物館所藏出土于西克利的犍陀羅浮雕、現藏大英博物館的浮雕儒童本生像。亦有簡化形式,如省略買花或騰空的儒童形象,亦有略去賣花人的,如中亞迪爾發現的犍陀羅立佛(日本私人收藏),頭光上浮雕七寶蓮花,足側有童子作五體投地狀,主要表現散花與布發掩泥兩個場景,其中散花則用頭光中的蓮花表示,并未出現儒童形象。
另一處典型的實例在云岡石窟,出現了大量表現儒童本生故事的造像,亦多為浮雕形式,主要在云岡中期和晚期,尤以晚期最盛,據統計約有17幅[11],其中構圖最詳的是第10窟前室東壁的儒童布發畫面(圖4)。
2. D型Ⅱ式:三童子獻施因緣
此式造像常表現為立佛,左手或右手持缽低垂,下有三童子相攀肩而蹬,其中一童子雙手捧物欲投入佛缽中,稱作“定光佛并三童子”題材{1}。
此式實例多見于云岡石窟,云岡早期如第18窟南壁既已出現,至云岡晚期數量驟增,如第19-1、5-11、5-38、5-39、25、29、33、34、35、38、39等窟均有此類造像[10]106。另外,河北邯鄲峰峰礦區鼓山響堂山石窟水浴寺西窟也發現有北齊時期的此式造像[12]。
3. D型Ⅲ式:授記、三童子同時組合表現
將儒童本生與三童子獻施兩種題材放在一起表現。例如河南浚縣浮丘山北齊四面造像石的北面中龕(圖5),在立佛和三童子的外側,還雕有一尊手持蓮花的男像和兩尊女像。手持蓮花者即為儒童,其旁女像為賣花給儒童的王家女瞿夷及侍女。據經典所載,這個王家女瞿夷也同時得到了授記。這是以獻花表現授記本生的故事,也有采用布發情節的,如河清三年(564)梁罷村碑,立佛右下作童子獻施,左下則為布發掩泥,共用一尊定光佛立像,表現兩個故事情節,且呈左右對稱布局。
(五)E型:單尊形式
定光佛為立式,獨尊,大體可分為兩式:
1.E型Ⅰ式:并不出現儒童的人物形象,僅以蓮花等物來象征或者暗示故事情節,并成為辨別定光佛身份的特殊標識。蓮花在此表示儒童散花。
實例1:單體圓雕立像,出土于犍陀羅的西克利,現由歐洲收藏家收藏。此像為圓形頭光,波浪紋發髻,身著通肩裝佛衣,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抓衣角,赤足立于方臺座上,與當地出土的其他諸佛造型無異。所異者在于,頭光中浮雕六莖蓮花,底座正面飾三朵蓮花。
實例2:單體圓雕立像,出土于犍陀羅的塔波拉,現收藏于東京Matsuoka藝術博物館。此像圓形頭光內浮雕兩莖蓮花。
2.E型Ⅱ式:單尊立像形式,并無其他暗示或象征物,僅靠造像題記方可判定身份。
沖相寺定光佛造像即屬于此式(圖6),龕內除了定光佛立像,并無儒童、童子之類人物,亦不見蓮花之類象征物。但造像本身已存在能揭示其定光佛屬性之潛在標識,這就是雙手所施的特殊手印。這種手印雖然在常見的定光佛像甚至其他佛像都很難見到,但它所體現出來的意義正代表了定光佛的本身標識。手印問題下文將予專論,此處不贅。
綜合上述分類定型可以看出,代表過去佛的定光佛像,起初一般出現在七佛、三佛組合中,地位并不突出,也存在與其他諸佛一般無異的造型和組合,根本不含有自身的任何特色。隨著佛教的發展及傳播地域的變化,定光佛逐漸在造像中得到重視,授記本生尤其得到強調,造像中熱衷于刻畫此類故事情節,著重表達“求得授記”的成佛思想。這一現象在北朝比較盛行,晚期尤甚。廣安沖相寺定光佛像所開鑿的年代(開皇八年)雖已進入隋代,但南北仍舊沒有進入真正統一,事實上還屬于北朝晚期,定光佛造像的出現便是受此風所染的結果。不過,沖相寺的定光佛像與北方相比,其實已是這類造像的簡化形式,其源可追溯至犍陀羅地區的作法,只是簡化得更加徹底,連外在的象征物諸如儒童、蓮花等統統省略掉,只專注于定光佛本尊,且以之作為一龕主尊,甚至將其安排在當時定光巖整個造像區的最高位置,不可不謂對定光佛的尊崇已經遠超前代。而在造型設計上卻設置了獨特的手印,不借助外物只靠造像本體來突出定光佛的特質,這是此前所未見的。
四 太陽紋頭光
背光是佛教造像背后的光圈式裝飾圖案,一般處于佛教諸尊像的頭部或身后,包括頭光和身光,這是佛“三十二相”中“眉間白毫”和“長光一丈相”的表現,屬于佛本體的一部分[13]。背光表現的是佛的神圣偉大,象征光明和智慧,代表著佛的熾盛,表示的是普照一切無所障礙的超常的光,同時又可以起到裝點佛身的效果,能反映出各時代造像樣式和造像者的審美觀[14]。沖相寺定光佛的身后亦表現有背光,為外桃形內圓形{1}雙層頭光,圓光中雕刻放射狀的鋸齒紋一圈,桃形頭光上部及身光為彩繪而成。這里要討論的是圓光中雕刻的一圈鋸齒紋,又被稱作太陽紋{2}。下面試對這種特殊頭光紋飾的形制類型、流布及寓意等,略作分析。
首先來看一下這種裝飾紋樣在沖相寺石窟中的表現情況。據初步統計,58個龕中發現有鋸齒紋頭光的有K1、K23、K26、K43、K45、K47、K50共7個龕,單體實例有13個,其中用于主尊佛像的4例、弟子5例、金剛力士4例。按照形制可以分為兩型:
(一)A型:尖桃形頭光
圓形頭光之外表現尖桃形外層頭光,主要見于主尊佛像。其中按桃形光中是否有紋飾再分為兩式:
1.A型Ⅰ式:尖桃形光比較小,內素面不見紋飾,此式僅1例,即K26定光佛。
2.A型Ⅱ式:桃形外層頭光比較大,內鏤雕不同的紋飾,或如意卷云紋,或纏枝忍冬紋,前者紋飾如K45主尊,后者紋飾則有K47、K50主尊。
(二)B型:圓形頭光
不表現桃形外層頭光,僅為圓形頭光,主要見于弟子、力士造像。按是否雕有裝飾紋帶,亦可分為兩式:
1.B型Ⅰ式:沒有裝飾紋帶,主要有K1右側弟子、K43左右二力士、K45左右二力士、K47左側弟子。
2.B型Ⅱ式:圓形頭光外再雕一圈裝飾帶。主要有K23左右二弟子、K50左側弟子,凸棱圈間隔的光圈帶中浮雕菱形、橢圓形等幾何紋,相間排列,菱形中有凸起的小橢圓狀物,形似眼目。
由以上分析可見,這種頭光紋飾可以用作主尊佛像,也可用作脅侍弟子或護法力士,似乎并無神格方面的限制,但在表現形式表現出佛教世界的等級觀念,其中A型與B型之間的區別,就是為了強調這種等級差異。同時A型Ⅰ式與A型Ⅱ式的區別,主要是時代特點表現出來的差異,也從一個特定角度反映出K26的開鑿時代要早于K45、K47和K50。同時,K1、K23、K43、K45、K47、K50所表現出來的這種類似性,反映了它們時代相近,尤其是K43與K50在龕窟形制、規模大小、造像題材與組合等所表現出更高程度的相似性{1},更印證了這一點。經分析排比,這7龕的年代有隋、盛唐,亦有中唐,盛唐最多,可明確這種頭光紋飾在沖相寺石窟的流行時間范圍,當在隋至中唐。
至于太陽紋這種頭光的源流、寓意問題,限于篇幅,僅作略述。經初步考察,這種頭光紋飾首先產生于古印度犍陀羅地區,目前所見最早的實例是阿富汗Paitāva出土的舍衛城雙神變的佛傳浮雕,現藏法國吉美博物館[15],時代在公元2—3世紀,立佛右手施無畏印,左手下垂握衣角,大圓形頭光內的邊緣飾有一圈鋸齒紋,齒紋較小,排列細密,形如連續的小正三角形,這當屬于早期形態。此佛肩膀表現升騰的火焰,而在另一件阿富汗紹托拉克出土的相似造型的造像上,身光邊緣所飾即為火焰紋,所以Paitāva造像頭光中的鋸齒紋其實表示的也是火焰,只是為了與佛肩寫實的火焰相區別而設計成這樣,其用意相同,都是表現光明的。
太陽紋頭光在犍陀羅地區出現以后,又受到希臘太陽神造型因素的影響,出于對太陽的崇拜,這種頭光紋飾開始發生變化,齒紋更加尖長犀利,變得更加形似太陽光芒{2}。如現藏東京的釋迦牟尼佛銅坐像[16],制作于公元3世紀,為跏趺坐式,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角,圓形的頭光不大,邊緣處被制作成放射形的鋸齒狀一圈,形如佛頭后照耀著一個光芒四射的太陽。在這里,鋸齒已經成為頭光造型的一部分,而不是僅僅作為可有可無的附屬裝飾,這應屬于發展型。此外,犍陀羅作品中還有一件巴雅說法佛石坐像[17],坐姿、手印與上述一件造像相同,圓形頭光內的邊緣部分浮雕一圈太陽紋,三角形齒紋中有個別造型變得腰部有些圓凸。時代較晚的作品,如印度北方邦班達縣出土的佛陀銅立像,屬于笈多時代,約在公元400年前后,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角,頭光顯得很大,邊緣制作成一圈鋸齒狀,稍異的是光線末端呈現小圓球形[18]。這兩件實例可看作變異型。
太陽紋頭光隨著佛教而東傳,先至新疆地區,發現的實例并不多,但這種東西承接的橋梁作用卻不容忽視。再往東,這種紋飾出現在敦煌莫高窟已是公元6世紀初期,按徐玉瓊對莫高窟北朝佛像背光裝飾紋樣演變過程的劃分,屬于第三階段(525年之前至545年),表現較多的則在第四階段(多屬北周時期,545—585),并認為這種鋸齒式火焰紋應是來源于古印度、西域地區,具體來說應是“對迦畢試佛教造像背光中鋸齒紋變異后融合產生的新紋樣”[19]。河西其他石窟目前還未見到太陽紋頭光。中原北方地區,在石窟造像的盛地如山西云岡、洛陽龍門亦基本未見。長安造像圈中目前也沒有發現較多實例。
唯獨比較流行的地區在四川,除了廣安,如廣元、巴中、安岳、夾江等地均有發現,尤以巴中地區最為多見。具體來說,廣元地區最著名的兩處石窟中,皇澤寺未見,千佛崖僅有1例;巴中地區主要分布在北龕和西龕,南龕1例,北龕7例,西龕9例,水寧寺1例,涉及10個龕,共18例;安岳臥佛院1例,夾江千佛巖2例{1}。這些實例,不出上文對沖相寺石窟太陽紋頭光所作的類型分析范圍。在施用的尊神身份上,增加了地藏與菩薩;佛中可以判定具體身份的有菩提瑞像、釋迦、阿彌陀佛、定光佛等;時代范圍大約從隋至晚唐,其中盛唐最多,達到12龕,其次為隋代和初唐,中唐、晚唐則最少。與犍陀羅及西域、河西等地相比較,以巴中及廣安沖相寺為代表的四川石窟中的太陽紋頭光表現出了極強的地域特色:一是以石窟造像為主要表現形式,采用鏤刻技法的占多數;二是放射狀的鋸齒造型更多地繼承了犍陀羅地區的發展型,齒紋更長更尖,外圍以閉合的圓形繼承中又有創新;三是尖桃形外頭光的引入,以及裝飾紋帶的多樣化,不僅可以強調等級觀念,而且還可以增添時代氣息。
由于成都本地出土的南朝佛教造像中不見此種形式的頭光,故推斷沖相寺太陽紋頭光的來源需要考慮北方因素。一般而言,四川石窟以川北的廣元和巴中為首傳之地,再由北向南波及其他地區。在太陽紋頭光方面,沖相寺石窟與巴中石窟表現出比較多的“親緣”關系,不僅形制相近,而且多伴有天龍八部等像,尤其是在時代上能產生一種早晚關系,在類型上巴中更為全面,似存在近似“母子”般的關系。因此,我們初步推測此種太陽紋頭光的傳播線路,應是從古印度犍陀羅地區起源,傳至西域地區,再到敦煌等河西走廊,然后經由天水、漢中南下,過米倉道而至巴中,最后沿南江、巴河、渠江傳至廣安沖相寺。至于安岳、夾江兩地的太陽紋頭光,可能又是另外一條傳播線路。
五 著衣方式
沖相寺定光佛像的著衣方式亦具特色。此前有研究者將之確定為“身著U形羅紋袈裟”[1]或者為“菩薩裝”,認為“(定光佛像)服飾為三層,內為僧衹衣,中間為無袖無開縫裙披,外為通肩風披”。[2]楊洋在碩士論文中描述道:“定光佛身披雙領下垂式袈裟,周飾U形衣紋,中間三角形衣角(上飾萬字紋)垂至膝下,下露百褶長裙,內衣大袖口直懸腕下呈三角形。”[4]16以上所述均有不同程度的偏差,為此將我們觀察的結果陳述于下。
依佛本制,纏縛于佛及僧眾身上的法衣常有三種,稱為三衣,各有不同的名稱,為求簡單方便,按照陳悅新引《十誦律》的作法,簡化僧伽梨為上衣,郁多羅僧為中衣,安陀會為下衣[20],其實可以簡單理解為外衣、中衣和內衣。從領口與袖口(圖7、8)進行仔細觀察后發現,定光佛上身著有三層佛衣,內為雙領下垂式的內衣,比較輕薄貼體,為窄筒袖;中衣和外衣均較厚重,都為一塊長方形的棉布,并無衣領和衣袖。中衣橫披,中間部位從后頸覆下至胸,左右兩側覆雙肩及雙臂,兩擺從手臂等距離垂下;外衣從右肩披垂至胸,再橫向左側搭垂于左肘部,外衣覆蓋了整個右肩和右臂,繞搭左肘又覆蓋了左前臂,胸以下垂成三角狀衣襟。外衣四個角,一個垂于雙膝間,上飾有“萬”字紋,另一個角垂于左手下,另外兩角垂于體后兩側。腰下系裙,這點是沒有疑問的。這種著裝方式比較特殊,目前筆者仍未找到與之相同的實例。不過根據內衣與中衣雙領下垂、外衣袒左搭肘的特征,可以命名為雙領下垂外衣搭肘式。
六 手印含義
沖相寺定光佛像特殊的手印,長期以來學界未作出合理的解讀。常見定光佛像的手印一般為無畏印,或抓握衣角,或向下伸手托缽,極少見到這種雙手斜伸、一掌朝上、一掌朝下的手印(圖9、10)。楊洋曾解釋說:“這種一手托天、一手覆地的手印,”顯示的是“定光佛佛法的無際無邊和天地間唯我獨尊的顯赫地位,反射出沖相寺地區對定光佛無比的推崇和濃厚的信仰”。這種說法沒錯,是從佛像表面動作和氣勢上來認識的,但放在其他佛像身上也是可以成立的,流于寬泛,而不中的。劉敏先生指出:“這種手印除此佛外尚無前者,亦無后例。其創作構思是否與儒童接受定光佛授記有關,亦待進一步進行考證。”這為我們解讀這種特殊手印指明了方向。定光佛之所以為定光佛,就是有著不同于他佛的特質,這種特質正是開鑿者們需要著力挖掘和表現的。所以解讀其手印,亦當從定光佛本身的特性去入手。
不妨先提出我們的觀點:定光佛雙臂自然斜伸,手指并伸,右手掌心朝下,表示為釋迦前世儒童進行授記,可暫稱作授記印;左手掌心朝上,表示接受三童子獻施,當是定光佛與三童子緣。
從前文論述可知,定光佛造像中一般最常表現的就是授記本生、三童子獻施,以至于儒童、三童子、蓮花等可以作為辨別定光佛身份的標識。但沖相寺定光佛龕像中并無這些形象,我們說它是一尊簡化的定光佛造型,但并不代表它就沒有這方面的內容,只是這些內容由顯性變為了隱性,由直觀的表現變成了暗示性的象征。
關于授記,造像體系中似并無明確規定的手印。但是佛教經典中載明,授記之時有摩頂的動作,而摩頂正是佛手下伸,掌心朝下的。《法華經·囑累品》云:“釋迦牟尼佛從法座起,現大神力。以右手摩無量菩薩摩訶薩頂,而作是言:‘我于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修習是難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今以付囑汝等:汝等應當一心流布此法,廣令增益。。”《地藏菩薩本愿經》云:“又于過去,不可說不可說阿僧祇劫,有佛出世,號獅子吼如來。若有男子女人聞是佛名,一念皈依,是人得遇無量諸佛摩頂授記。”《楞嚴經》云:“(普賢菩薩)白佛言:‘若于他方恒沙界處,有一眾生,心中發明普賢行者,我于爾時乘六牙象,分身百千,皆至其處。縱彼障深,未得見我。我于其人暗中摩頂,擁護安慰,令其成就……我自現身至其人前,摩頂安慰,令其開悟……十方如來,持此咒心,能于十方摩頂授記。自果未成,亦于十方蒙佛授記。”可見,摩頂是為付囑大法,或為預示當來作佛之授記的常用動作。摩頂在石窟造像中的直觀圖像,我們可從云岡羅睺羅因緣、雕鷲怖阿難入定緣中看到,如云岡第9窟前室西壁、第19窟南壁、第38窟東壁所表現的釋迦佛摩頂羅睺羅的場景[10]108-110,第38窟南壁則表現有釋迦佛摩頂坐禪阿難的場景[10]125-126(圖11)。按此,沖相寺定光佛右手可以理解為授記印,那么定光佛所授記的無疑便是釋迦前世儒童了。
沖相寺定光佛的左手掌心朝上,呈托物之狀,與云岡第12窟前室東壁的定光佛立像(圖12)的左手動作類似,唯一不同處是僅僅缺少一只缽。按照定光佛立像左右兩個題材的對稱布局原則,既然右手授記用以表現儒童本生,那么左手便應表現童子獻施,因此佛像左手掌心朝上動作的含義正是托缽接受獻施。這兩種不同手印在定光佛造像上的結合,是因為植善根與授記均是成佛的基本前提條件,表達的主題無非就是期望將來成佛而已。
總之,這種掌心朝下的手印表示的應當是定光佛為儒童摩頂授記,而手掌心朝上,表示接受三童子敬施,此處表達這兩個特定故事的方式不是形象化的雕刻特定人物或器物、蓮花等,而是設計采用了兩個獨特的手印,更多地帶有暗示性或象征性。省略掉以往造像中常出現的受記的儒童和佛手中所托的缽,三童子的造型等也一并略去,體現出的是定光佛晚期造像的簡化特色,帶有濃厚的時代性與地域性(時代較晚,地域靠南)。
七 定光佛信仰
定光佛屬于過去佛,因授記釋迦牟尼將來轉生為佛而著名。由于現世釋迦牟尼已涅槃,而過去佛、未來佛又很遙遠,于是在功利性很強的民間信仰中,便將過去、未來佛統統引入到現世中來。一如五代布袋和尚契此被作為彌勒的化身一樣,定光佛也出現了轉世化身,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便是閩西的定光和尚。這種后期的定光佛更多地屬于民間信仰,是中國化的產物,與圣僧信仰有關。有研究者將早期的定光佛信仰稱為正統信仰,即尊崇印度佛教原始之佛菩薩信仰,而把后期的定光佛信仰劃屬民間信仰,即尊崇中國佛教民間產生之佛菩薩信仰[3]。這種認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研究沖相寺定光佛造像體現出來的定光佛信仰,必須要與后期的民間俗神信仰區別開來。
按理說,定光佛是過去佛,早在久遠劫前已經離開娑婆世界,因此信徒更多的是信仰現在佛和未來佛,對待過去佛可能只是像對一般佛菩薩那樣表達單純的恭敬和祈禱,在信仰層面的地位遠遠不如釋迦牟尼佛和彌勒佛。但如沖相寺石窟對定光佛的尊崇,卻是前所未有的,那他們又是出于何種緣由來信仰定光佛的呢?其實,對定光佛的崇拜源于其授記的本生故事,因為真正讓功德主們關注和追逐的主旨應該是定光佛授記成佛的最終結果,而非定光佛本身。云岡第5—11窟中的儒童本生雕刻中,將原來佛經中記載的少年修行者儒童(釋迦前世),竟表現成了身著俗裝的邑人信眾形象[10]19-20。功德主將定光佛所授記的儒童換成了自己的形象,所表達的希冀再清楚不過,那就是迫切求得授記的祈愿。
從文獻看,求得授記成佛的思想,在當時社會上已經十分流行。如北齊文宣帝對著名高僧法上“事之如佛”,“乃下詔為戒師,文宣帝常布發于地,令(法)上踐焉”[21]。效法儒童布發,希望求得授記成佛的還有高昌王。高僧釋慧乘于大業六年(610)“奉敕為高昌王麹氏講金光明,吐言清奇,聞者嘆咽,麹布發于地,屈乘踐焉”[21]939。可見北朝至隋時期,這種求得授記成佛的信仰需求很興盛。沖相寺定光佛造像當是在這種信仰需求下所產生,更由此將原本是藥寺(可能供奉藥師佛為主)的沖相寺改為了定光佛的專門性道場。
結 語
定光佛龕是沖相寺石窟開鑿年代最早的一龕,應開鑿于隋開皇八年。其類型屬于定光佛造像的簡化樣式,不僅省略了為之授記的儒童,而且不見象征性的蓮花,在三童子獻施的表現中亦將三童子略去,同時也省掉了手中所托的缽。拋開了外在的人物與法器、供具,那么如何表現定光佛的特質?為解決這個問題,工匠設計出了掌心向下呈摩頂狀的授記印和接受獻施的手心朝上的受施印,體現了獨具匠心的藝術創造。以獨特的手印來暗示這兩個本生和因緣故事,是沖相寺定光佛像的與眾不同之處。同時,定光佛像的太陽紋頭光、雙領下垂外衣搭肘式著衣方式也是其獨特之處。單以太陽紋頭光來考察,可知此種圖案應是起自古印度犍陀羅地區,東傳西域和河西走廊,向南經米倉道至巴中,由巴中再傳至廣安沖相寺。在太陽紋頭光與巴中地區有較多相似性,暗示出沖相寺與巴中地區具有更深的親緣關系。同時在所有可以確認的定光佛石窟造像中,沖相寺的定光佛像年代偏晚,且分布地域最靠南,這也是其表現出來的特色之一。另外,以定光佛為全區最受崇敬的對象,建成為專門的定光佛道場,這也是少見的。定光佛像所體現的信仰也是與當時的歷史背景、現實需求密切相關的。總之,沖相寺定光佛龕像是研究早期定光佛信仰的絕好實物資料,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參考文獻:
[1]劉敏.廣安沖相寺摩崖造像及石刻調查紀要[J].四川文物,1997(3).
[2]劉敏.廣安沖相寺錠光佛石刻造像考略——兼論錠光佛造像的有關問題[J].中華文化論壇,2003(4).
[3]翁士洋.廣安沖相寺與定光古佛信仰[J].空林佛教,2013(6).
[4]楊洋.四川廣安沖相寺石窟研究[D].南充:西華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5]龍顯昭.巴蜀佛教碑文集成[M].成都:巴蜀書社,2004:32.
[6]賀世哲.關于十六國北朝時期的三世佛與三佛造像諸問題(一)[J].敦煌研究,1992(4).
[7]鄧健吾.麥積山石窟的研究及早期石窟的兩三個問題[C].天水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中國石窟·天水麥積山.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227-228.
[8][日]小森陽子.曇曜五窟新考——試論第18窟本尊為定光佛[C].云岡石窟研究院編.2005年云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研究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324-338.
[9]耿劍.“定光佛授記”與定光佛——犍陀羅與克孜爾定光佛造像的比較研究[J].中國美術研究,2013(2).
[10]趙昆雨.云岡石窟佛教故事雕刻藝術[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10:104.
[11]趙昆雨.云岡的儒童本生及阿輸迦施土信仰模式[J].佛教文化,2004(5).
[12]劉東光.響堂山石窟造像題材[J].文物春秋,1997(2).
[13]封鈺,韋妹華.佛教雕塑背光圖像的象征意義[J].東南文化,2010(2).
[14]顧虹,盧秀文.莫高窟與克孜爾佛教造像背光比較研究[J].敦煌學輯刊,2014(4).
[15][韓]李姃恩.北朝裝飾紋樣——五六世紀石窟裝飾紋樣的考古學研究[M].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246.
[16]趙玲.印度秣菟羅早期佛教造像研究[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2:167.
[17]李靜杰.中國金銅佛[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244.
[18][美]羅伊·C·克雷文,著.王鏞,方廣羊,陳聿東,譯.印度藝術簡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78-79.
[19]徐玉瓊.莫高窟北朝佛像背光裝飾紋樣特征及其演變[J].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5).
[20]陳悅新.5—8世紀漢地佛像著衣法式[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26.
[21]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卷第八·齊大統合水寺釋法上傳[M].北京:中華書局,2014: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