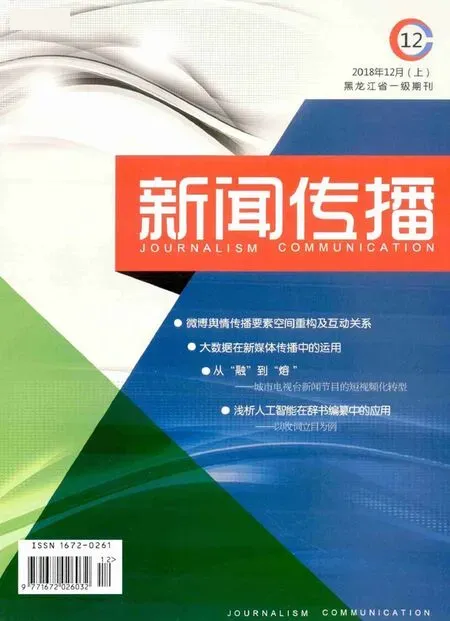符號學視閾下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策略研究
(安徽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蕪湖 241000)
一、符號學相關理論概述
符號學是研究符號表意的一門科學,國內符號學著名學者趙毅衡認為,“符號是被認為攜帶意義的感知,沒有意義可以不用符號表達,也沒有不表達意義的符號,沒有意義可以不用符號來解釋,也沒有不解釋意義的符號,符號學即意義學。”[1]索緒爾認為符號由“能指”和“意指”組成,羅蘭·巴爾特同樣認為“符號是一個包括能指和所指的復合詞”[2]。皮爾斯提出了著名的“符號三元論”,他將符號分為“再現體”、“對象”和“解釋項”,其中“再現體”就相當于索緒爾“二分法”中的“能指”,他將索緒爾“二分法”中的“所指”分為了“對象”和“解釋項”兩個部分,強調了符號接受者對于符號意義的影響。后來的內涵符號學將“元語言”和“內涵概念”結合起來,葉爾姆斯列夫提到的“外延”與“內涵”也恰巧對應了皮爾斯所提出的“對象”和“解釋項”。艾柯指出,外延是“所指物在文化上得到承認的潛在屬性”,而內涵“未必對應所指物在文化上得到承認的潛在屬性”[3]。
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在《文化的解釋》中說道:“我所采納的文化概念本質上屬于符號學的文化概念。”[4]他認為符號學“提供一種語言,是符號行動所必不可少的自我表達-即文化在人類生活中的角色-得到實現”。[5]符號學在傳播學的發展過程中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傳播學家馬歇爾·麥克盧漢的許多傳播學理論中多處使用符號學的相關理論,符號是人類傳播的一個介質,人類通過符號交流信息。
二、中國文化對外傳播面臨的困境之符號學分析
(一)符號“任意性”下西方媒體對中國文化的“神話制作”
長期以來,世界傳播領域始終由西方主導著話語權,西方長期以來對中國進行著“神話制作”。賽義德在《東方主義》中曾經說過:“東方被東方化了,不是因為它通過19世紀一般的歐洲人所認為的普通方法被發現‘具有東方色彩’,而是因為它可以被東方化,也就是說,它經受了東方化。”[6]“任意武斷性”是符號所普遍適用的,符號的能指與所指既是基于社會習俗的規定,又是沒有理據的,符號和意義的結合方式不需要進行論證。西方媒體通過各種符號組合向國際社會傳達著中國文化,他們將自己意圖的意義置于文本之中,把自己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融入這些文本之中,將選擇過濾后的中國文化傳達給世界,這種神話制作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歪曲了國際社會對于中國文化的理解,中國故事常常被妖魔化。
(二)不同社會文化語境下國際社會對中國文化符碼的無效解碼
克利福德·格爾茨認為只有在一定的社會文化語境中,才能了解交際行為之后的意義,才能使得文化符碼能有效解碼。文化符號作為一種能指優勢符號,能指不需要明確地指向所指,而是獨立形成一種自身的價值,如果置于另一種不同的文化體系中,這種能指所創造的價值和意義可能就不復存在了。國際社會傳播領域里,中國文化符碼的解碼深受多元文化的社會文化語境影響,各國文化、社會和個性結構等都不盡相同,形成了非常復雜的意義語境,這加劇了不同國家和民族的人民對中國文化解讀的難度。
(三)“解釋項”下中國文化符號“接受度”問題的亟待解決
傳播過程是信息“編碼-譯碼-解碼”的循環過程,傳播最終的效果與解碼的過程密不可分。拉斯提埃爾認為,對于符號表意來說存在接受原則,即愿意或者不愿意接受符號所攜帶的意義,這是一種基于受眾個體差異性的原則,對符號傳達和表意效果有至為關鍵的影響。中國的對外傳播中存在很多僅僅是進行宣傳而沒有進行傳播的現象,一味的宣傳式和灌輸式的傳播并不能使中國文化被國際社會所接受和認可,這種不足一定程度導致一些受眾對了解甚至接受中華文化產生負面情緒,從而導致中國文化符號的“接受度”下降。
(四)“符號載體”多樣性下對外傳播中文化符號載體的不足
符號載體作為發送者意圖的承載者,是符號過程中充當中間環節的存在,任何符號都需要符號載體,文化符號亦是如此。趙毅衡在《符號學原理與推演》中舉例,“文字是載體,印刷是媒介,圖像是載體,電視等是媒介。”[7]中國的對外傳播活動其實非常多,但是沒有將中國文化充分地載入這些文化符號載體中,這些文化符號載體的能指所能體現的所指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在對外傳播中,我們缺少更多類型的文化符號載體,很多情況下是官方發聲,缺少民間社會的文化符號互動,這也限制了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
三、從“符號三元論”看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策略的完善
(一)從“對象”到“解釋項”——確保國際社會對中國文化的正確解讀
“解釋項”在符號的過程中直接影響到符號傳達和表意的效果,文化符號的解碼直接關系到對“對象”的解釋,我們要重視從“對象-解釋項”的過程。全球化浪潮下,意識形態作為文化的元語言是紛繁復雜的,文化符碼的有效解碼必須要深入社會文化語境,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需要更多關注受眾個體的差異性,要考慮到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選擇適合某一地區的方式進行傳播。
劉建明曾在《全球化語境下中國媒介對外傳播的策略》一文中建議采用西方的敘述方式去講述中國故事,在中國媒介對外傳播從業人員隊伍中更多地引進外籍人員以減少跨文化傳播受眾的心理排斥感。[8]除此之外,筆者認為,還可以利用中國文化與其他文化的共性進行中國文化的宣傳,在相似的文化語境之下,對中國文化的接受度會大大提高。除此之外,我們還要提高自身文化符號載體以及其攜帶意義的可信度,媒介的公信力需要提升,不要刻意去隱瞞負面的內容,要做到公開、公正、公平,及時、準確、客觀。
(二)從“對象”到“再現體”——加快對中國文化符號載體的優化
“對象”到“再現體”的過程是一個符號化的過程,這個過程與人的主觀能動性密切相關。中國在對外傳播文化的時候,應該賦予中國文化符號載體以更多的文化意義,體現出自己的一套文化價值觀,增強這些文化符號載體的文化內涵。作為中國文化符號的發送者,我們要將意圖意義盡可能地轉變為文本意義,同時要減少文化符號載體中的“噪音”成分,使得對外的文化傳播能夠傳遞更多賦有意義的文化符號。
洛特曼注重闡明“再現體”和“對象”之間的關系,認為敘述文本主要有兩種途徑,一種是語言符號的形式,通過文本篇幅的擴展來敘述,另一種是圖像符號的形式,通過變形和內部成分的換位來敘述。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過程中要注意敘述的方式和方法,遵循國際公認的客觀真實性和新聞專業主義,外交場合里用詞用句的精準和恰當,中國文化紀錄片從拍攝到后期制作都經過仔細地斟酌等,從而能將我們想要傳遞的中國文化更好地融入它的符號載體中,使得中國文化能夠更好地被感知。
詹姆斯·羅爾認為,商業社會語境中的文化就是一種資本,可以被消費。正如羅爾所認為的一樣,在資本全球運作的環境下,文化可以成為一種全新的資本形式。中國文化也可以成為一種資本,除了各種文化產品外,中國的文化風格、文化理念也可以被“消費”。如同張碧認為的那樣,“文化生產相對于此前的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加依賴各種科技手段的促進和推動。”[9]全球化浪潮下,中國文化想要成為一種資本,需要依托先進的科技手段,我們需要借助新的媒介技術向全球傳遞中國的文化符號、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把中國文化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