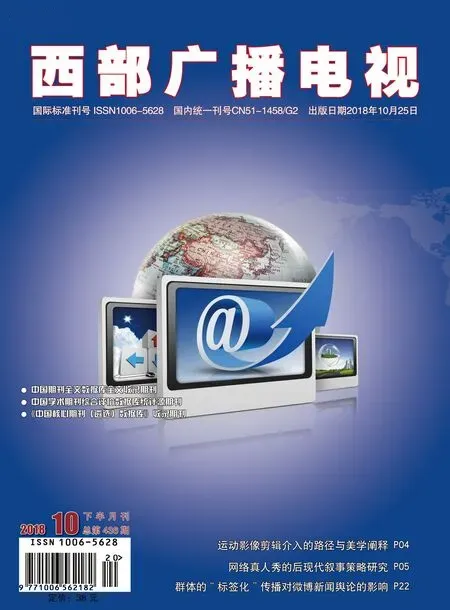網絡真人秀的后現代敘事策略研究
柳 珊 鄭 錚
(作者單位:同濟大學藝術院傳媒學院)
近年來,隨著電視綜藝節目的迅速發展,網絡平臺看準了這種既能增加商業收益又能吸引受眾觀看的節目類型。從2013年開始,網絡綜藝節目中的重要類型——網絡真人秀逐漸進入網絡受眾的視線。優酷土豆的《侶行》,芒果TV的《明星大偵探》,愛奇藝的《愛上超模》《中國有嘻哈》等一眾播放次數破億,廣告投資上千萬的節目與電視“綜N代”有了一搏之力。不論從節目選題還是形式,網絡綜藝節目與電視綜藝節目相輔相成:網絡平臺為電視綜藝節目的題材借鑒提供了新生內容的培育田地,電視平臺為網絡綜藝節目的形式推廣提供了成熟的策略指導,兩個平臺的綜藝節目都給受眾留下了不少熱議的話題,但討論度最高的依然是真人秀節目中的人物以及與人相關的敘事。
1 后現代敘事策略下的平民化身份制造
1.1 新型身份建構下的人物元素——“平民化”的角色設定
作為真人秀,“假定情景”建構讓受眾投入到故事情節中。在特定情景中,參與者的角色設定是基于真人秀的無主角敘事形成的,豐富每個人物的個性與情感,形成沒有具體主角的敘事,能夠讓觀眾最快記住每個人物。角色設定的特征一般是“典型化與陌生化”[1]。
“典型化”在網絡真人秀中主要體現在節目的“選角”。比如,愛奇藝的《愛上超模》第三季,選擇的角色雖然都是模特與網紅,但每個人又有另一個身份:內心細膩外表高冷的婁清,通過變性浴火重生的汪欣蕾,高挑美麗已為人母的韓紅盼,等等。在比賽進行過程中,每個人的性格逐漸轉化:婁清一反外表的冷漠,展現“老大哥”仗義執言的一面;汪欣蕾在不斷的質疑中逐漸讓身邊的人和自身認同自己的女性身份;韓紅盼在選手們共同生活時承擔了“老媽”的角色,卻依然有柔軟脆弱的一面。這樣的人物設定首先讓每個參與者的身份符號化,進而用平凡人的性格特點消解原本的印象,“制造”出與受眾相近的特點,使受眾因為平民化的身份制造產生身份認同。
“陌生化”是俄國學者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一種美學創造原則,強調“以作者或人物似乎從未見過此事物,而不得不以陌生的眼光把事物原原本本地具體描寫出來,從而使藝術的描寫不落入套板反應,產生一種奇特的新鮮感”[2]。網絡真人秀中明星的角色設定便有此特性,比如,《明星大偵探》第二季的撒貝寧,現實生活中身為法制頻道主持人,他在節目中被封為“狗頭軍師”,因為每次在分析案件時總是頭頭是道,最終的嫌疑人永遠判斷錯誤。節目后期制作更是將這一特色“發揚光大”,撒貝寧不再是嚴肅法律的代言人,反倒成為偶有失誤的平凡人。明星卸下光環的“陌生化”過程讓受眾在觀看節目時獲得更多樂趣。
“典型化與陌生化”是網絡真人秀對電視平臺的繼承,但網絡在角色設定中同樣有不同于電視的部分。由于網絡承載著后現代主義的特色,它的“非權威性”[3]在真人秀中體現為參與者的“平民化”,這一特色也與網絡平臺的審查較松散有關。節目中,每個人物的嬉笑怒罵均被記錄,連撒貝寧都能說出“你為愛情鼓過掌么?”這樣文雅的段子,可以說與電視中展現的正能量甚至是“精英化”角色有所區分,更為“真實地”(也是虛構地)構建了人物平民的一面,使年輕人在網絡真人秀中見到更容易認同的“身份”。
1.2 塑造平凡人身份認同感的敘事情節——參與者的沖突與受眾的對抗
真人秀中往往是合作與對抗并存,這樣的情節設置能給受眾留下懸念與沖突。在沖突時,受眾可能會對人物產生同情或厭惡,王思敏在對后現代敘事的解讀中“認同與同情應該不是相克而是相生的”[4],這樣的情緒能夠在行進過程中人為“制造”出對不同人物的認同感。然而,與電視真人秀不同,由于網絡受眾對于節目內容的選擇更個性化,網絡真人秀的情節元素往往會向對抗更激烈的方向發展。
典型案例就是2017年暑期在愛奇藝播放的《中國有嘻哈》,由于嘻哈(hip hop)本身風格的原因,選手的性格都比較直接且以自我為中心,在節目中疲勞就想退賽,生氣就會罵人。尤其在一位人氣選手創作了諷刺其他選手的歌曲后,沖突達到頂峰,選手GAI就在節目中表示要用說唱“干掉”對方,甚至在之后使用了“格殺勿論”這樣劍拔弩張的詞匯,對抗的情緒在節目中逐漸濃烈。沖突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面,和睦的競賽內容很難達到受眾認同的“真實感”,激烈的情節讓節目內容與“平凡人”生活中的場景重合,參與者也慢慢成為生活中身邊的普通人。網絡受眾就是在這樣“制造”的戲劇化情節下了解嘻哈文化,從而產生認同。然而,這樣的沖突往往不是正面的,更有甚者可能升級為語言暴力,如何控制沖突成為網絡真人秀節目亟待解決的問題。
真人秀中,電視的“紀實性”與“戲劇性”[5]博弈通常會在節目進程中體現,但在網絡真人秀中,對抗的敘事主體可以不再是真人秀的參與者們,普通受眾同樣可以加入到節目對抗情節的建構,這顯然提升了普通人在節目中的地位。《明日之子》中,比賽全程直播,除前期評委對于自己賽道選手有選擇權外,排名前9的選手都是由觀看直播的受眾投票決定的。這種增加參與度的投票對抗雖然對于節目流程并沒有太多影響,但對于節目內容的塑造來說,受眾作為“讀者”的身份慢慢被顛覆,逐漸以“敘述者”的身份進入節目中,選手的選擇成為增加受眾參與感的情節,這種結合更能引起觀看者的認同感,拉近選手與受眾的距離。在后現代敘事理論中,“我們的身份是被制造出來的,制造者是敘事的作者和讀者,制造的車間就在敘事的情節里。”[6]受眾的互動在敘事中的作用被放大,平凡人的身份被放大,代表的不再是一個具體的個人,而被制造成一種具有決定權的力量。通過使用網絡這一媒介,權力的轉移讓網絡真人秀情節更不受控,更加具有懸念。
1.3 以制造平民身份為主的敘事角度——復合焦點敘事
電視真人秀通常使用“不完全零視角”[7],其中,零度聚焦視角能夠全方位感受人物和事件,然后結合內外聚焦視角補充人物形象。網絡真人秀的敘事角度則主要是內外聚焦視角結合,更多是內視角聚焦。表現最明顯的是《明星大偵探》,由于本身是推理類的真人秀,對于劇情的推進需要以懸念為主,受眾與劇情人物的視角一樣,在探索中了解人物性格與事件的真相。內聚焦視角能更清晰地剖析每個敘事身份,“敘述視角具有定位功能”[6],以主觀視角觀察敘事過程中的人物性格,有助于受眾在體驗中產生認同,在推理類真人秀中更能投入到情節中,加強受眾現場感。在排查“真兇”時,運用外聚焦視角,不將每個人的心理展現出來,為最終的結果留下懸念。可以說,內外視角的切換完全是為這種“以制造身份為主”的敘事內容而服務的。
在這一視角的基礎上,“小敘事”的敘事方法顯得尤為重要。以往的真人秀都是以線性敘事為主要敘事結構,因為這樣能夠表現時代背景的大敘事結構,但利奧塔爾說過,在后現代社會,大敘事失寵了,小敘事得志了,廣播變成了窄播,廣告不再追求廣而告之而是定向告之[6]。可以說,在網絡這個新興媒介中,線性敘事正逐漸被“小敘事”取代。生活本來就不會像電視節目一樣被安排得當,真人秀更應“真實地”甚至是“出乎意料地”反映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比如,在電影中已經使用的“網狀敘事”,幾個角色可能有交叉與影響,但需要彼此保證各自的獨立性與重要性[8]。這種“去中心化”的后現代敘事已經符合現階段真人秀的發展,更貼合于以復合焦點敘事為主的網絡真人秀。
1.4 服務于身份認同的敘事內容——垂直細分的主題選擇
對于真人秀節目內容而言,電視真人秀因為電視媒介的特點更多選擇民生類內容。“電視既可以看作是家庭行動的中心,又是行動的源泉”[9]。家庭的特性讓電視適合“合家共賞”,對于以收視率為重要衡量標準的電視真人秀必然會選擇涵蓋受眾喜好的節目主題,比如,音樂、游戲、旅游等,在環節設置中同樣要考慮全年齡層受眾的觀看體驗。網絡真人秀與電視平臺上不同,受眾對節目的選擇更有指向性。網絡真人秀處置細分主題選擇的意義就在于尊重不同受眾的喜好,使節目主題定位更加精準而小眾,初步滿足受眾個性化需求。比如,《愛上超模》喜歡觀看的受眾大部分對時尚感興趣,《明星大偵探》著眼于喜歡推理小說的受眾,《侶行》吸引想要窮游探險的受眾,《中國有嘻哈》針對音樂類型內熱愛嘻哈音樂的受眾。網絡真人秀制造的場景都是符合節目主題的,不會為了討好大眾選擇更加老少皆宜的表現形式,選擇的參與者也更符合特定受眾審美。只要選擇正確的觀眾群體,使用正確的宣傳手段以及剪輯技巧,才能俘獲一大批忠實觀眾,同時在二次傳播中收到更好的效果。
在具體傳播層面,雖然網絡真人秀有垂直定位受眾的特性,但為了更高的收益,節目需要受到大眾歡迎。對于增加更多觀眾,網絡真人秀大多會邀請明星,使用宣傳手段讓小眾化情節變成全民共享的現象級節目。比如,《中國有嘻哈》讓一種在國內較少人喜歡和了解的音樂類型通過吳亦凡等明星的加盟,以及對明星身份的“陌生化”和流行語“你會freestyle么?”的病毒性傳播,將節目打造成總播放量超過26.8億,微博主話題#中國有嘻哈#閱讀量高達68億的超級話題,成為“小眾題材,大眾跟風”的真人秀節目。
2 網絡沖擊下的電視文化反思
麥克盧漢說過“媒介及訊息”,不同的媒介平臺所裹挾的內容必然有所區別。伊尼斯的傳播偏向論是啟發他的重要觀念之一,該理論認為媒介基本上都有一定的偏向,或是有利于空間上的延伸或是有利于時間上的延續。至今為止,電視以及網絡的發展已經逐漸突破伊尼斯所敘述的科技發展水準,但對于新媒介而言,時間與空間的偏向性依然存在,僅是側重點不同。相較于電視真人秀,網絡真人秀的敘事發展結合了網絡媒介本身的時空特點,更能體現后現代敘事中對于傳統敘事的“解構化”“多樣化”與“政治化”[6]。娛樂當道的今天,網絡媒介對主流文化的消解是否能夠在真人秀中重構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從敘事角度看,網絡真人秀已經為我們帶來了未來敘事的發展前景。
2.1 對電視真人秀敘事以及電視文化的“去精英化”影響
從媒介角度來探討,網絡所具有的時間碎片化特性是對時間有統治作用的電視的巨大沖擊。電視對于社會有決定性作用,其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電視作為有固定時間版塊的媒介,每一檔節目的播出時間、時長、敘事都在電視臺的安排之下。受眾作為被動的信息接收者,對于節目的掌控多停留在更換頻道上,特定時間觀看特定節目是電視媒介對受眾產生的巨大影響(當然網絡電視不在討論之列)。對于時間的強掌控讓電視文化所傳播的主流文化成為精英化的代名詞,權力更多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這使得電視文化在社會結構與文化形態中占主導地位[10]。
然而,現階段,中國正處于多種價值觀相互博弈的時代,精英文化的削弱不可避免。網絡作為一種科技發展的新興產物,讓普通受眾對“時間”的掌控權回到自己手中。從安東尼·吉登斯的自我實現角度來看,網絡媒介促進受眾建立個人時區(zone of personal time)[11],這是對個人時間的充分掌控。從網絡綜藝節目的角度出發,除視頻網站在特定時間發布節目內容的硬性條件外,受眾可以通過快進、回看等方式控制節目進程,形成個性化觀看方式。網絡媒介重視普通人的權力,在網絡價值取向與電視精英文化取向的逐步碰撞中必能凝聚出一種能夠普世的主流傳播思想,為今后的電視節目發展以及主流文化傳播形成助力。從原本網絡上單一、小眾的情感宣泄,過渡到之后電視文化中感性與理性相結合的價值理念,最終形成有中國特色的電視娛樂精神。
2.2 對后現代網絡“群體”身份認同的深入構建
后現代敘事理論中,身份認同的解讀格外重要,但在原本的網絡文化中,身份認同的構建是相對不健全的。網絡寫作中,主體的匿名性雖然為作者贏得了自由,但集體的隱身很難讓受眾對他人的觀點產生首肯[3]。網絡真人秀的出現成為網絡身份認同構建的方式之一,由于真人秀本身的屬性,參與者的匿名將成為不可能。另一方面,讀者對于敘述者的認同將不僅僅建立在對人物本身的認同上,更多是建構在網絡真人秀循環往復的沖突與對抗之中。或者從另一個可能性來說,在矛盾中,我們發現自身與“他者”的不同,從而進一步承認自我的存在性[12]。
曼紐爾·卡斯特在《認同的力量》一書中談到:認同不再是傳統意義的“角色設定”,而是一種意義來源,涉及自我建構和個別化的過程[12]。身份認同對于主體意識的喚醒與現階段不同媒介塑造身份屬性的過程不謀而合。由于電視與網絡的空間屬性不同,二者對于身份認同的構造重心也是不同的。對于中國而言,1982年原上海電視廠第一條彩電生產線竣工,標志著電視正逐步走入每個中國家庭中,原本高消費的電視成為了每家每戶的必備家電,電視節目的播放地點也從公共社區回歸到了家庭中。每個人接收信息的必需性讓電視建立了客觀存在的空間,家庭成為最好的互動場地以及探索世界的窗口,每個人的身份認同塑造在固定空間中得到強化,家庭觀念的塑造成為電視節目中不可或缺的內容。
但是,網絡媒介打破了這一固定空間,虛擬空間的建立讓信息接收突破了家庭壁壘,受眾不需要在特定地點進行互動與交流,喜好的選擇更加自由。網絡讓受眾成為一個個節點,人與人的交互關系形成網狀結構。在網絡上,不分地點的實時互動讓人們根據自己的個性與愛好組成不同的“群體”,個性化的受眾選擇在網絡媒介上成為可能。視頻網站就是根據這樣的受眾特性制造更加小眾的視頻節目,從而進一步促進對網絡“群體”的身份認同。網狀的權力結構同樣打破了原本立體的階層結構,讓受眾感受到地位的提升。與此同時,“平民化”身份認同能夠讓多元價值觀進行交流,網絡空間的受眾認為任何事物不僅僅是單向度的,他們更期望看到雙面甚至是更復雜的價值碰撞。這鼓勵了受眾自我意識的覺醒,從而在理念交流中明確自身認同觀念。這樣平等化的交流方式更增加了受眾對“群體”的認同程度,通過將相同目標、相同興趣的人聚集起來的方式,受眾重新掌握了話語權,在網絡節目中選擇自身代言人,比如,網絡受眾票選出《明日之子》的冠軍是毛不易。權力的回歸讓人們更加認同自己所處的網絡空間,逐漸將自己從由電視媒介組建的“家庭”節點中抽離出來,投入到價值取向更接近、話語權更大的網絡“群體”身份中。
2.3 對“后現代”大眾文化的影響
現在,我國大眾文化可以總結為“現代化”與“后現代化”博弈的時期。從張頤武的角度來看,他通過對電影的大量分析總結出我國現階段正處于“現代化”的進程中,主要表現在“公民”與“消費者”或者“英雄”與“凡人”的辯證互動[13];從王岳川的角度來說,他認為我國已經處于“后現代化”的“解構”之下,由于文化工業的產生,大眾文化因為多元文化的沖擊失去了“它性”,在消費主義的影響下,大眾媒介逐漸流于感官刺激,深度正在被平面化所替代,受眾逐漸被“麻痹”[14],這些分析也正與拉扎斯菲爾德認為大眾文化有麻醉作用十分相似。后現代主義本身就含有“解構”的思想,它是在“現代性”啟蒙主體性和理性的基礎上,對“現代性”價值徹底批判的精神,后現代不是一個時代的標簽,而是一種思維的方式,其中去中心化,反正統性,多元性等都是該主義的特征[15]。
網絡雖然不屬于大眾媒介之一,但網絡媒介所裹挾的后現代化思想將會對社會產生不可逆的影響。曼紐爾·卡斯特提出的“網絡社會”,就是一種在網絡技術的發展下的新型社會模式,他認為“網絡化邏輯會導致較高層級的社會決定作用甚至經由網絡表現出來的特殊社會利益:流動的權力優先于權力的流動。”[14]權力的階級分布不再是立體的,而是扁平化的;“一旦主體被建立的時候,它不再是以公民社會為基礎,因為公民社會已經在解體之中,主體的建立是公社/公共/社區抵抗(communal resistance)的延長。”[14]計劃性認同能夠讓人確立主體,而建立主體之后,重構公民社會將成為可能。在這樣一個前提下,網絡文化對于“平民化”身份認同的建構將十分有意義:網絡文化會影響大眾文化的傳播方式。價值觀的影響可以不再是自上而下的“指導”,可能會成為具有反饋機制的“交流”。網絡本身就是一個去權威化的公共場域,具有話語權的傳播者除原本的媒體與國家外,會有部分下降到受眾手中,就像網絡綜藝節目的節目流程正逐漸受到觀眾的選擇一樣,對于價值取向的傳播也潛移默化受到受眾反饋的影響。
以網絡平臺為傳播媒介的網絡真人秀作為網絡綜藝節目的類型代表,從敘事角度塑造了“平民化”的身份認同,受眾在觀看的同時能夠建立個性化的個人時區以及“群體”的身份認同,網絡文化這種與傳統主流文化有所偏差的價值觀輸出,是現階段對我國大眾文化百家齊鳴的最好解讀,雖然不能說具有后現代特性的網絡文化已經能夠重構現階段的大眾文化,但不得不說,網絡文化的發展正在為大眾文化的轉變提供一條可行的路徑,對于今后的影響尚需要時間去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