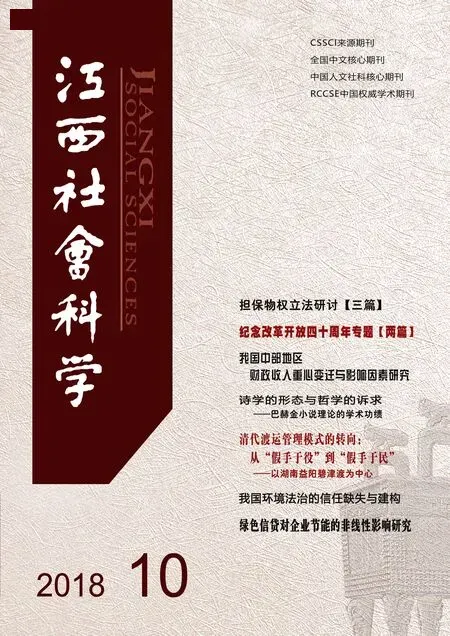中國禮貌文化研究的范式及理論建構
國際禮貌研究始于Lakoff在1973年提出的三條禮貌規則——不要強加、給予選擇和友善[1]。之后,學者們提出一系列有關禮貌的語用學理論,主要包括20世紀末Brown和Levinson的面子理論[2]、Leech的禮貌原則[3]、Fraser和Nolen的“會話契約說”[4]、Fraser的“社會規范說”[5]、Aijmer的框架理論[6],以及21世紀初Spencer-Oatey的人際關系管理論[7]、Arundale的面子構建理論[8]、Locher和Watts的“關系活動論”[9]等。綜觀這些研究我們發現,現有的禮貌理論幾乎都是由西方學者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提出的,而關于中國文化中禮貌現象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對西方理論的調整、修改或補充上。可以說,到目前為止,學界對中國文化背景下禮貌現象的原創性研究仍舊十分匱乏。然而,中國作為東方文明的代表,有著與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中國式禮貌也必然有著不同于西方式禮貌的獨特內涵,因此有必要對中國式禮貌的文化獨特性展開專門研究,這不僅有利于深化我們對中國式禮貌的認識,也有助于促進國際跨文化交流。
此外,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尤其是21世紀以來,國際禮貌研究在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上也發生了一些轉變。本文將結合這些轉變探討當前應該如何對中國式禮貌進行原創性研究及理論建構。我們認為,要深入挖掘中國式禮貌的文化獨特性,需要以中國傳統的禮文化為基礎,用建構觀的視角對禮貌現象進行審視,此外,還要特別重視漢語本族語成員的理解和判斷(即交際參與者視角),具體研究方法可以采用會話分析研究方法對自然發生的真實語料進行分析。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揭示中國式禮貌的深刻內涵和獨特本質。
一、以中國傳統禮文化為基礎
禮貌研究初期,學者們致力于提出具有文化普遍性的禮貌理論,其中最具影響力的當屬面子理論和禮貌原則。面子理論認為,面子是禮貌概念的核心,所謂禮貌,就是要最大限度地降低對面子的威脅。該理論的提出基于兩個普遍性假設——“面子”和“理性”:首先,個體都具有正面面子和負面面子,而且隨時可能遭到威脅;其次,說話人被賦予根據交際目標選擇語言策略的精確模式。面子理論問世后迅速引起強烈反響,但很快就受到挑戰,尤其是該理論中禮貌的“策略性”本質和“負面面子”概念被質疑對其他文化,尤其是東方文化,缺乏解釋力。例如,Ide區分了兩種不同的禮貌:策略性禮貌和程式化禮貌。策略性禮貌是交際者實現交際目標的手段,與交際意圖緊密相關;程式化禮貌與個體在某一等級社會中的角色和義務有關[10]。日本文化側重后者,即判斷某一言語禮貌與否要看其是否符合當前等級關系和交際情景所期待的共享規約。Matsumoto指出,日本文化不強調個體的獨立性和自主權,即所謂的“負面面子”,而是強調個體在某一團體中與其他成員的關系以及被其他成員接納和認可的程度。[11]Mao指出,由于中國文化對團體和諧的重視超過個體自由,“面子”更是一種社會現象,而非“個體的心理需求”,同時,對“關系”的強調也說明“負面面子”的不適應性。[12]與面子理論不同,禮貌原則把禮貌理解和歸納為六條準則:策略準則、慷慨準則、贊譽準則、謙虛準則、一致準則和同情準則。同樣,該理論的文化普遍性也受到質疑。顧曰國指出禮貌原則并不能完全解釋中國的禮貌現象。他從中國傳統文化出發,對Leech提出的策略準則和慷慨準則從行為動機層和會話表達層進行了修正,提出符合中國文化的貶己尊人準則、稱呼準則、文雅準則、求同準則等準則。[13]
不難發現,人們對經典禮貌理論的質疑和挑戰大多集中在中西文化差異方面[14],這說明不同文化中禮貌的內涵是不同的,這使學者逐漸從尋求具有普遍解釋力的禮貌理論轉向對禮貌文化獨特性的關注和研究。因為不同文化傳統深刻影響著內部成員對禮貌的認識和理解,因此我們對中國式禮貌進行研究時,要首先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解釋的線索和資源,而與中國現代禮貌聯系最密切的當屬中國傳統的禮文化[15],正如顧曰國所說,“現代的‘禮貌’與古代的‘禮’是有歷史淵源的”[13]。
眾所周知,禮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古代的“禮”是一種社會制度或一套行為法則。《禮記》談到中國古代“禮”的起源:“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以窮,使欲不窮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也就是說,禮起源于人類的欲望和欲望難以滿足之間的不平衡,“先王”劃分人與人之間的差別界限,使人的欲望不要越過這個界限而得以滿足,因此“禮”也成了平亂獲治之本,“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荀子·王制》)。[13]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的“禮”是維護社會等級差別的一種社會制度或行為法則。
當代中國的“禮貌”顯然不能等同于古代的“禮”,但不可否認,中國傳統的禮文化對當代中國的禮貌文化產生非常深刻的影響。雖然如今“禮貌已不再作為維護現行社會等差的行為法則,而是作為不分差別、供人們效仿的行為規范”[13],但和古代的“禮”一樣,現代“禮貌”的關鍵要素之一也是“尊敬”。《墨子·經上》把古代的“禮”解釋為“禮,敬也”。《曲禮上》中也有類似的論述:“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同樣,“貶己尊人”也是中國當代禮貌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一點不僅被顧曰國明確列為中國禮貌原則的一個準則,也得到了一些實證研究的證實。例如,對恭維言語行為進行的會話分析研究表明,“貶己尊人”的文化制約著當代中國人對恭維進行回應的方式。[16]
當然,“貶己尊人”只是中國傳統禮文化影響現代中國式禮貌的一個方面,要深入全面地揭示中國式禮貌的內涵,就要從中國傳統禮文化中汲取更多更豐富的營養。例如,在下面這個交際過程中出現了一種中國特有的、不同于西方的禮貌現象,要解釋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就要從中國傳統禮文化中尋找線索。
A:這是給你的,我看你需要。
B:你這是干嘛?
A:沒什么好東西,你就戴吧。
B:那哪行呀,這得多少錢呀?
A:不值錢,你就戴吧。
B:不行不行,我得給你錢。
A:我說了不值錢,挺適合你的。
B:真不好意思。
A:你就別客氣啦。
B:那謝謝啦!
這是一個典型的中國文化背景下人們送禮物和收禮物的交際過程。A送給B一條項鏈作為禮物,B并沒有馬上接受,而是表達了拒絕。面對B的拒絕,A并沒有放棄,而是繼續堅持把禮物送給B,然而,B依然沒有接受A的禮物,這樣給予——拒絕的模式持續出現,直到A再一次堅持,B才真正接受A的禮物,并表達感謝。很顯然,這一過程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中給予禮物——接受禮物并表達感謝的發展路徑。對中國人而言,直接接受別人給予的禮物是不禮貌的,只有經過兩到三次拒絕之后再接受才是禮貌的;對于給予禮物的人來說,在遭到對方首次拒絕時不能放棄,而要堅持,只有持續堅持到對方接受才是禮貌的。
那么如何解釋中國文化中這種特有的禮貌現象呢?我們可以從中國傳統禮文化倡導的 “真誠”和“平衡”兩個維度去理解。對A而言,因為要表現出真誠,他必須反復多次地給予禮物,哪怕遭到B的不斷拒絕。對B而言,他要確保A是真誠的才能接受這個禮物,因此他會通過反復拒絕來驗證A是否真誠。同時,在此過程中,A和B都必須做出一些“平衡”。對A而言,一方面要保證這個禮物不是強加給B的,另一方面又不能讓B覺得A認為他非常欠缺或想要這個禮物。對B而言,一方面要不能因為拒絕接受禮物而傷害A的面子,另一方面又不能讓A覺得自己貪得無厭。正是基于以上方方面面的因素,A和B的交際過程才會出現多個給予——拒絕的回合[17]。
由此可見,中國傳統禮文化為我們研究中國式禮貌提供了豐富的解釋資源,因此,要對中國式禮貌進行原創性研究和理論建構,我們需要以中國傳統的禮文化為基礎,從中尋找中國式禮貌的歷史演變線索或形成因素,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發現中國式禮貌的獨特本質,才有可能提出具有中國文化獨特性的禮貌理論。
二、采用建構觀視角
傳統禮貌研究的另一個特點是普遍采用規約觀視角。總體而言,禮貌的規約觀認為禮貌話語就是符合某種社會規約的話語。比如,“社會規范說”認為:“每個社會都有一套由比較明確的規則組成的社會規范,這些規則對特定語境中的行為、事態或者思維方式做出規定。”[5]符合這些規范的行為被評價為積極的,違背這些規范的行為被評價為消極的。“會話契約說”認為,交際中人們受會話契約制約。會話契約指交際中基于雙方社會關系,可依據語境變化進行調整的規則、權利和義務。禮貌就是根據會話契約的條款進行的交際活動。框架理論認為,規約化禮貌的運作機制,是交際者根據儲存在頭腦中的現成的禮貌范式對具體語境做出反應,這些禮貌范式是交際者在與周圍環境尤其是與社會語境相互作用的過程中獲得的。由于禮貌范式是基于特定社會文化背景形成的禮貌形式與特定語境的對應關系,因此判斷某一話語是否禮貌必須要參照特定的社會文化規約。禮貌原則的各項準則實質上也是一系列人們在交際中需要注意并遵守的社會準則。即使是面子理論也沒有脫離對社會規約的觀照。因為交際者判斷面子傷害程度、選擇禮貌策略所參照的三個變量(雙方的社會距離、權勢差異以及行為的強加程度)也是社會變量,需要從普遍接受的社會規約的角度來衡量。
不難看出,禮貌的規約觀關注點主要在于禮貌話語是如何產出的或者說話人如何選擇禮貌話語,因此是以說話人為導向的。然而,禮貌歸根結底是一種存在于人們互動交往過程中的現象,沒有人際互動,禮貌現象就不復存在,因此必須把互動交往過程中的所有參與者都納入考慮范圍。換句話說,我們不僅要考察說話人如何產出禮貌話語,同時也要考察聽話人如何理解和判斷禮貌話語。規約觀的另一個問題是其所基于的編碼—解碼的交際觀,即人們的交際過程就是說話人對其話語進行編碼,聽話人再對說話人話語進行解碼的過程。然而,簡單的編碼—解碼的交際觀并不能解釋人們互動交往的復雜過程,無法解釋交際意義是如何在交際雙方的互動過程中協商產生的。鑒于以上兩點,禮貌的規約觀視角已不再適用于新時期的禮貌研究。我們認為,要對中國式禮貌展開研究和理論建構,應該采用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即建構觀視角。
建構觀視角的核心思想是禮貌為交際雙方在互動過程中共同建構的結果。這一新視角不再基于簡單的編碼—解碼的交際觀,而是基于一種新的交際觀,即交際的聯合共建模式。交際的聯合共建模式認為,在交際過程中,交際雙方互相制約對方對話語的理解和產出,進而共同推進會話不斷展開,其共建的過程可以產生非累加的交際效果[18]。交際的聯合共建模式充分考慮了交際的動態性、交際參與者的主動性,以及交際雙方的協同合作和相互制約,因此更加符合人際互動交往的本質。基于這一互動的交際觀,我們認為,采用建構觀視角對中國式禮貌展開具體研究時,考察的內容應該是漢語本族語交際者如何在真實、具體的交際活動中共同作用、相互制約,實現禮貌的動態建構過程。具體來說,我們考察的內容不再是怎樣的話語是禮貌話語,或者說話人根據什么來判斷話語是否禮貌以及禮貌程度如何,而是交際雙方是如何在具體會話過程中將某一話語建構為禮貌話語的。因此,禮貌不再是某一話語或行為的本質屬性,而是由交際者在具體交際過程中建構起來的一種臨時性特征。
例如,上例中B在第一次拒絕時說:“你這是干嘛?”如果從傳統規約觀的視角來看并不是禮貌的(甚至是不禮貌的),因為它既沒有減少對交際對方面子的傷害,也沒有增大對交際對方的贊揚,甚至起到相反的作用。然而,如果從建構觀視角出發重新審視這句話,我們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在這個動態的交際過程中,B的話語“你這是干嘛”是在回應A的話語。由于A的行為是給予B禮物,B通過這句話執行的行為是拒絕A的給予(而不是質疑或批評A)。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別人給予禮物時要首先表示拒絕,如果立刻接受就會被認為是沒有禮貌或者沒有教養。正因為如此,B的話語并不是不禮貌的,而是非常禮貌的,因為B非常直接地拒絕了A的給予。換句話說,B正是通過拒絕的“直接性”把話語建構為禮貌話語。另一方面,A再次執行了給予的行為,并未對B的話語表現出任何不滿,這表明A也認可B的回應是禮貌的,至少沒有認為它是不禮貌的。也就是說,A通過繼續執行給予這個行為(而沒有挑戰B話語的合適性)把B的話語“你這是干嘛”構建為禮貌話語。因此,在這個具體的交際語境中,B的話語“你這是干嘛”是禮貌的,而且這種禮貌性不是該話語的內在屬性,而是由交際雙方共同建構出來的。
由此可見,采用建構觀視角對中國式禮貌現象進行審視,能夠揭示禮貌協商的動態過程,能夠得出更加客觀、真實、符合交際實際的結論。
三、重視交際參與者視角
傳統禮貌研究的第三個特點是普遍采用研究者視角。經典禮貌理論可以說是理論提出者基于自己對社會交往的認識和對禮貌現象的觀察、思考提出的理論框架。例如,面子理論把“面子”這一概念作為闡釋禮貌現象的核心,認為禮貌的本質是使用各種策略減少對面子的傷害。禮貌原則從社會基本價值觀的角度闡釋禮貌的本質,認為禮貌就是遵守一系列有助于人際和諧的價值觀。“會話契約說”將禮貌的本質歸結為人們對交際過程中各種契約、條款的遵守。事實上,這些理論無論從哪個角度對禮貌現象進行闡釋,都是基于理論提出者自己的觀察、判斷和思考,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理論提出者“已有的內在的語言知識”[19]影響。由于社會、文化以及個體差異,很難保證理論提出者對禮貌現象的理解和判斷與交際活動的參與者一致。尤其是作為大學教授的研究者大都屬于中產以上階層,他們對禮貌行為的判斷難免帶有自身所在階層的烙印,因此不一定適用于大眾階層。
由于禮貌是一種文化現象,是全體社會成員共有的文化資源,因此,要研究某一社團中的禮貌現象,就是要研究這一社團的內部成員是如何共同認識和理解禮貌現象的,而不是看研究者個人的理解。因此,我們認為,要真正揭示中國文化背景下禮貌現象的本質,就要研究漢語本族語成員作為具體交際活動的參與者是如何理解交際過程中出現的禮貌現象的。也就是說,我們應該采用交際參與者視角(而非研究者視角)對中國式禮貌現象進行研究。事實上,這也是解決當前中國禮貌研究中存在的問題、促進中國禮貌研究健康發展的最重要、最關鍵的一步。正如文章開頭所提到的,目前中國的禮貌研究仍停留在對西方理論的調整、修改或補充上,原創性研究仍舊十分匱乏,在現有研究中我們很難找到從漢語本族語成員視角出發的研究,也很難找到能夠恰當解釋中國式禮貌本質的理論研究。要突破目前的困境,首要任務就是要深入研究和挖掘漢語本族語成員是如何判斷、理解和認識禮貌話語的。只有他們的判斷才是真正客觀的判斷,也只有基于漢語本族語成員的共有判斷,我們才有可能發現中國式禮貌的內涵,提出中國本土化的禮貌理論。
從交際參與者視角研究中國式禮貌,決定了我們首先要進行大量的實證性研究,然后才有可能進行理論建構。實證研究是自下而上的研究,即先收集、分析語料,再在語料分析的基礎上總結規律;而理論研究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研究,即研究者先提出一個理論,再用該理論去解釋具體現象。我們之所以要先進行實證研究,是因為只有在實證研究中我們才能發現漢語本族語成員在具體的交際活動中對中國式禮貌現象的理解和判斷,而只有依托這些實證研究得出的結論和證據,我們才有可能提取出中國式禮貌的內核,進而建構出能夠真正解釋中國式禮貌內涵的原創性理論。
從交際參與者視角研究中國式禮貌,也決定了我們進行研究的基本單位必須是由漢語本族語成員參與的完整的交際語篇,而不能是單個的、脫離語篇的孤立話語。因為只有在完整的交際語篇中,我們才有可能得知交際參與者是如何理解交際中所涉及的禮貌現象的,也只有在完整的語篇中,我們才有可能找到他們理解的證據。例如,要判定上例中B的話語“真不好意思”是否禮貌,我們就要將其放在完整的語篇中考察,而且要看交際參與者(而非研究者)是如何理解這一話語的(盡管很多時候二者的理解是一致的)。A將B的這一話語評價為“客氣”,由此可見A把B的話語理解為禮貌的。在最后,B對A表達了感謝,并沒有對A把他的話理解為“客氣”表示異議,由此可知,B認可了A對其話語的理解,即承認自己的話語“多不好意思”就是在表達客氣和禮貌。因此,我們可以說,B的話語“多不好意思”是禮貌的,而且這一結論不是基于研究者的判斷,而是基于交際參與者的理解以及從交際語篇中找到的證據得出的。
從交際參與者視角研究中國式禮貌,能夠盡可能排除研究者主觀猜測對研究結果的影響,因此更加客觀、合理,應該加以提倡。
四、采用會話分析研究方法
當采用建構觀視角和交際參與者視角對中國式禮貌進行研究時,我們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必須能夠滿足這些新視角提出的新要求。禮貌的建構觀視角要求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能夠揭示禮貌的動態生成過程;交際參與者視角要求研究方法能夠幫助研究者客觀地提取交際參與者對禮貌現象的判斷以及判斷的依據。這些都是傳統的禮貌研究方法,如語篇填充法、問卷調查、角色扮演和采訪等不能達到的,因此我們提議采用會話分析這種基于自然發生的真實語料、沒有理論預設、重視交際互動過程、并且能夠獲取客觀證據的研究方法對中國文化中的禮貌現象展開研究。
會話分析是Harvey Sacks和Emanuel A.Schegloff于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發展起來的一種社會學研究方法。它的誕生主要受到美國著名社會學家Erving Goffman有關社會秩序的思想和Harold Garfinkel的民俗方法學(ethnomethodology)的影響。[20]受前者的啟發,會話分析認為人們的互動交際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有內在規律和秩序的,會話分析就是對會話的內在組織結構和內在秩序的研究。受后者的影響,會話分析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歸納法,而非自上而下的演繹法。會話分析的研究目標是對人們執行行為和理解他人行為的方法進行描述,觀察對象就是人們進行交際的過程本身。該研究方法反對基于假設的研究路徑,因為這種先提出理論假設的研究路徑會影響研究者對真實世界的觀察,一些與研究假設不符的現象就會被過濾掉。相反,它采用的是在客觀審視自然會話的基礎上對觀察到的規律進行概括的研究路徑,因此是一種基于大量觀察的歸納研究,而不是受某種理論假設驅動的演繹。[21]
會話分析的核心原則是會話的序列組織,這是會話分析研究方法區別于其他交際互動研究方法的根本特征之一。對會話分析而言,交際者當前的話輪受前一話輪的影響和制約,同時也影響著下一話輪的出現,因此,每一個話輪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要理解某一話輪中話語所執行的行為,必須參考該話輪出現的序列位置。當同一話輪設計出現在不同的序列位置時,它執行的行為就會不同。[22]另外,會話分析強調使用自然發生的真實交際作為語料。它只認可通過錄音或錄像收集的自然發生的真實語料,不接受其他定性研究采用的語料收集方法,如訪談、觀察記錄、角色扮演等,因為這些方法都無法準確記錄具體情境中發生的交際細節,有可能被一些理想化的形式所代替或者被研究人員人為操控,也無法真實全面地反映所觀察現象的多樣性和代表性,更無法像錄音或錄像一樣回放來爭取同行的審視和認可。因此,對會話分析而言,只有自然發生的真實交際才是可接受的語料來源。
為什么要提倡采用會話分析研究方法對中國式禮貌進行研究呢?第一,會話分析對自然發生的真實語料的堅持,保證了我們在進行中國式禮貌研究時,研究對象的確是發生在中國文化背景下的由漢語本族語成員所參與的真實交際活動,也可以保證我們發現的規律是中國文化背景下的禮貌規律,當某一規律不同于西方式禮貌時,我們可以判斷這是中國文化中所特有的禮貌現象,因而也可以結合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對此做出解釋。第二,會話分析對會話序列組織的重視可以保證我們對中國式禮貌現象的審視是動態的建構觀。如上所述,會話分析認為,會話序列中的每一個話輪都既受前一話輪的制約,也同時影響著下一話輪的出現,即交際參與雙方互相影響、制約對方的話語的產出和理解,這表明會話分析不僅把交際活動看作動態的過程,而且還提供了分析這種動態性的手段,因此運用這一方法,我們可以發現交際雙方是如何在具體的交際活動中共同作用、相互制約,實現禮貌建構的動態過程的。第三,會話分析對序列組織的重視也可以保證我們對中國式禮貌的研究采用的是交際者視角。會話分析中對某一話輪所執行行為的判斷主要依據交際對方對該話輪的理解,這一理解可以從交際對方在下一話輪的回應中看出。如果采用同樣的方法來分析禮貌現象,我們就可以從下一話輪中看出交際對方是如何理解當前話輪中的話語禮貌與否的。而且,交際者對某一話輪中話語禮貌與否的正確理解、不解甚至誤解都可以在之后的序列中得以展現和證實。這樣,把對每一個“當前話輪”的分析綜合起來,我們就可以發現在整個交際活動中,交際參與者是如何理解和判斷其中涉及的禮貌現象的。
總而言之,會話分析研究方法能夠滿足建構觀視角下和交際參與者視角下對禮貌研究的新要求,因此可以很好地用于對中國式禮貌文化的研究中。
五、結 語
在國際語用學界,禮貌研究已有近半個世紀的歷史,也取得了非常豐碩的研究成果。遺憾的是,目前對中國文化中禮貌現象的原創性研究卻寥寥無幾,這導致我們對中國式禮貌內涵的認識還遠遠不夠。本文主要探討了在當前形勢下應該如何對中國式禮貌進行研究和理論建構。從研究視角上說,我們應該以中國傳統的禮文化為基礎,采用建構觀視角和交際參與者視角對具體交際活動中的禮貌現象進行審視;在研究方法上,我們提倡采用會話分析這種基于自然發生的真實語料、沒有理論預設、重視交際互動過程、能從交際過程中獲取證據的研究方法。只有采用客觀、科學的研究視角和方法,才能得出合理、站得住腳的結論,才能真正揭示中國式禮貌的獨特內涵,進而建構出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禮貌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