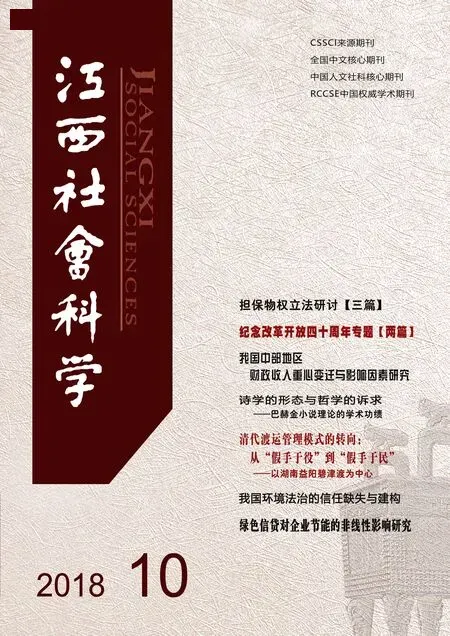弗理契藝術社會學思想在中國的接受(1921—1933)
弗理契(Фриче,Владимир Максимович,1870—1929)是蘇聯的文學史家、批評家和藝術社會學家,他第一次建立了較為系統的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他在十月革命前的主要著作有《西歐文學史綱》(1908)《西歐現代派主潮》(1909)等,20年代后轉向藝術社會學研究,主要著作有《普列漢諾夫與科學美學》(1922)、《西歐文學發達概論》(1922)、《弗洛伊德主義與藝術》(1925)、《藝術社會學》(1926)等。弗理契在美學上的最大貢獻是建立了馬克思主義藝術社會學,發展了普列漢諾夫的“科學美學”。他不僅同普列漢諾夫一樣以唯物史觀的方法考察文藝之發生、發展,還嘗試建立一定的社會形態與一定的藝術典型適應的美學科學系統,不過問題在于,他簡化了普列漢諾夫所強調的文藝與經濟、階級的復雜關系,將文藝與經濟基礎、階級直接相關聯,歪曲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忽視了文學生成的內在審美機制以及藝術家的個性。蘇聯在十月革命以后的很長時間將弗理契的藝術社會學思想視為文藝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主流,但在1928年至1930年、1932年到1936年間,蘇聯分兩階段展開對弗理契藝術社會學的批判,前者是從學理上批判他的機械主義和公式主義,后者則將學術討論擴大為政治斗爭。弗理契藝術社會學思想及其在蘇聯的命運影響了各國社會主義運動。
弗理契藝術社會學思想給中國現代文論與文學以重大的影響,尤其是弗理契一派的庸俗社會學思想。初步統計,自1921年起弗理契文藝著作在現代中國的翻譯與出版有32篇(本)①,共30種,其中“藝術社會學”相關著作有19種,且《藝術社會學》這本書在當時被廣泛傳播與討論;他本人在現代時期的學術地位通常與普列漢諾夫、盧那察爾斯基并列②。不過,弗理契藝術社會學思想在現代中國的“輝煌”卻與他在當代文論研究中的落寞形成對比。以往對弗理契藝術社會學思想在中國的接受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維度:其一,對弗理契庸俗社會學思想的批判;③其二,討論弗理契藝術社會學同中國文學理論的關系;④其三,弗理契藝術社會學對文學創作的積極影響;⑤其四,從文獻資料上對翻譯到中國的弗理契著作進行梳理。⑥從現階段研究可以發現,研究者們盡管關注的具體問題不同,但就“弗理契藝術社會學與現代文論的關系”卻得出肯定與否定兩種截然相反的結論;另外,對弗理契文藝思想及相關闡釋性文獻整理還很不完備。那么,弗理契藝術社會學在中國的命運到底如何?造成其命運變化的原因是什么?同一理論家在不同時間段對弗理契的態度是否不同?本文將解決以上這些問題,并嘗試以弗理契藝術社會學在中國的接受為視角,探討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的曲折路徑。
一、弗理契藝術社會學的理論初識與完全接受
1921年,胡愈之翻譯的弗理契《鮑爾希維克下的俄羅斯文學》開啟了弗理契文藝思想在中國的接受,不過這篇短文只是對十月革命后蘇俄文壇的介紹。耿濟之在1924年翻譯的《中產階級勝利時代的法國文學》的《譯者附志》中指出:“本篇是俄人佛利柴所著《西歐文學發達概論》(1922年出版)中的一章。佛氏此著系用‘經濟史觀’的眼光以研西歐文學,欲給讀者證明‘社會的經濟如何影響文學’。”[1]耿濟之第一次將弗理契在研究歐洲文學時使用的新方法介紹到中國,但他沒有明確提出“藝術社會學”這一概念。
在弗理契藝術學著作未大量翻譯到中國以前,中國學界只是從留日進步青年處知道弗理契在1929年去世,且知道他是當時世界上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藝術學者,如汪馥泉的《俄國藝術學者傅理契之死》、馮乃超的《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的文獻》、馮雪峰的《藝術社會學之任務及諸問題》(弗理契著)編者附記中都對此作了說明。不僅如此,馮雪峰還指出弗理契“走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美學’之創始者蒲力汗諾夫所指示了的路,并且將蒲力汗諾夫所奠的基礎加以深崛發展;至謪理契底 《藝術社會學》,其間極鮮明地呈現著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體系底發展和向完成去的痕跡”。[2]左聯機關刊物《拓荒者》在1930年第1期的國內外文壇消息中介紹了弗理契之死,并將他定位為馬克思主義藝術學的衛兵,打破了觀念論的陣營。[3]
弗理契的藝術社會學思想很快被大量翻譯到國內,有《藝術社會學的學術會議的報告》《藝術風格之社會學的實際》《藝術社會學之任務及諸問題》《藝術之社會的意義》《藝術上的階級斗爭與階級同化》《藝術社會學》《工業發達在現代歐洲文學上的反映》《歐洲文學發達史》《藝術作風與社會生活的關系》等,幾乎是當時弗理契在中國的全部譯著。譯者和闡釋者對弗理契藝術社會學思想的選擇有兩方面原因:其一,與20世紀20年代以來中國古典文論轉向現代文論過程中對“藝術社會學”的接受大背景相關,其二,與當時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中國的流行有關。1930年2月第1期的《文藝研究》在介紹陳雪帆譯弗理契的《藝術社會學》的廣告中說弗理契創立了新學說,從社會學經濟學的觀點檢討古今東西的藝術作品。“科學的藝術論叢書”之《唯物史觀的文學論》的書后廣告中宣傳劉吶鷗譯《藝術社會學》時表達了相似的觀點。[4]1930年,劉吶鷗譯弗理契的《藝術社會學》被標上“馬克思主義文藝論叢(1)”的字樣。劉吶鷗認為這本書“否定了以前的藝術論,補充了以唯物史觀來研究藝術的霍山斯坦因,蒲力汗諾夫等新的藝術論”,“建立了科學的藝術社會學之建設的最初的基石”。[5](P367-368)然而,作為馬克思主義藝術論著的《藝術社會學》(劉吶鷗譯)最終未被列入魯迅、馮雪峰主編的“科學的藝術論叢書”;據施蟄存回憶,當時左翼理論界認為該書有資產階級觀點。[6](P335)
盡管譯者和批評家的思想傾向各異,接受弗理契文藝思想目的不同,但共同認可了他的馬克思主義藝術學。中國學者對弗理契藝術社會學思想的最初認識是對日本弗理契評價的完全接受:弗理契是世界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藝術學者,完善了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普列漢諾夫藝術論。進入1930年以后,學界才有了對弗理契藝術社會學思想的獨立反思。
二、弗理契藝術社會學的缺陷反思及其價值的相對肯定
20世紀30年代,整個中國批評界沉溺于對弗理契及其思想的緬懷、贊美與認同中,凌岱發表了《藝術社會學之是非:讀弗理契著藝術社會學》一文。這篇文章是目前找到的較早從學理立場出發比較客觀思考弗理契“藝術社會學”的。凌岱在文中指出十月革命后蘇聯的社會科學向煽動性、宣傳性、實用性發展。弗理契參加無產階級革命,但不是共產黨員,是以學者的姿態同情革命,這樣他的藝術社會學缺少煽動性、宣傳性,更有真理性。馬克思的《資本論》《政治學經濟學之批判》是社會學向經濟領域的發展,而弗理契把馬克思主義引到藝術領域。弗理契并不是第一個將社會學的原則、方法、觀點引用到藝術領域,或是將藝術主題歸入社會學范疇的,但他是集大成者,他試圖探討藝術是如何與每個時代的經濟形式相適合的,且每個經濟形態形成了如何與之對應的典型和形式。[7]更為重要的是凌岱從三方面指出弗理契藝術社會學的問題:其一,把藝術社會學作為社會科學的一門是不行的,這意味著將一切現象加以系統的、組織的、一般化考察,而藝術是不能加以一般化而概括的。不過,藝術可以加以社會學的研究。其二,弗理契討論怎么樣的藝術適合社會發達的每個時代,怎么樣的社會產生怎么樣的藝術,犯了削足適履的毛病。他將材料裝入既定的公式內,選擇適合自己說教的材料。其三,弗理契對藝術外表的形象沒有涉及,而這恰好是藝術的唯一特色。藝術之外的形象與某個社會的形體和一定的經濟組織關系,是不能用經濟條件來解答的。
在凌岱對弗理契藝術社會學思想的批判后,是胡秋原對弗理契“藝術社會學”的批判。胡秋原在《藝術社會學·譯者序言》中肯定了弗理契用社會學-經濟學的觀點檢討古今藝術,將史的唯物論的新方法與新標準擴大了藝術研究,但他更大的貢獻在于對弗理契機械主義和公式主義的批判。當下研究對胡秋原的弗理契批判已經達成共識,這里不再贅述,但相關批評文獻除了《藝術社會學·譯者序言》之外,還有《佛理采之樸列汗諾夫論》[8]和《藝術作風與社會生活之關系》[9]兩篇譯文的注釋。需要指出的是胡秋原的批判建立在對以藏原惟人為代表的日本普羅文學對弗理契的批判的反思上,而藏原惟人的觀點又來自蘇聯對弗理契的第一次學術批判。⑦可見,這一時期學界不再盲目追隨日本的觀點,開始有自己的分析。
雖然胡秋原批評弗理契藝術社會學中存在的問題,但他在后來左翼批評弗理契的觀點時堅決為普列漢諾夫和弗理契作學術價值上的辯護。胡秋原接受了弗理契的觀點,即不能以孟塞維克否認普列漢諾夫在文藝上的遺產,不能過于狹隘粗笨地理解文藝的階級論,更不能機械地理解文藝之黨派性。[10](P13-14)《關于文藝之階級性》中胡秋原提出要像弗理契一樣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在階級矛盾中理解文學;意識到弗理契提出的文藝上階級斗爭與階級同化的價值,但也提出不能將階級性的反映看成簡單的公式,忽略階級性是種種復雜心理之錯綜的推動,受社會傳統及他國階級傳統影響。[11]顯然胡秋原認可弗理契以經濟、階級分析文藝,但受普列漢諾夫影響,提出要警惕弗理契的公式主義,即將文學和階級直接對應。
胡秋原、凌岱都肯定了弗理契以經濟學-社會學的方法對古今中外的藝術考察,且同時指出其藝術社會學思想中存在的機械主義和公式主義錯誤,凌岱還指出弗理契藝術社會學思想中對美學要素的忽略。胡秋原并非只在理論上對弗理契藝術社會學思想進行辨析,還以在普列漢諾夫藝術思想審視下的弗理契思想批評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發展中的庸俗社會學傾向。無論是凌岱還是胡秋原,都展示出中國學者在理論輸入過程中的獨立思考,然而,緊迫的革命現實很快剝奪了文學研究中的獨立思考。
三、蘇聯弗理契批判的引入與弗理契藝術社會學批判的政治轉向
從1932年起,蘇聯文藝界重新開始了對庸俗社會學的批判,且這次批判被納入到對“拉普”的批判和清算中。“拉普”批判過彼列維爾澤夫-弗理契的“庸俗社會學”,且在文學上提出“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反抗觀念論、機械論,[12]但“拉普”是站在“為了普列漢諾夫的正統”的立場上的。蘇聯的這次批判主要以列寧的黨派性觀點批評普列漢諾夫的客觀主義,并將普列漢諾夫藝術觀點上的錯誤歸于他孟什維克的錯誤政治立場,自然受普列漢諾夫影響的弗理契也被同等對待。由此,先前的學術討論演化為政治批判。蘇聯的弗理契批判幾乎同時影響了弗理契在中國進入1932年以來的命運。寒琪的《讀者顧問:世界革命文學》[13]、魯迅譯的《蘇聯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現狀》(上田進著)、適夷譯的《偉大的第十五周年文學》(上田進著)⑧、黃芝威譯的《普列漢諾夫批判》(IB著)都介紹了蘇聯的弗理契政治批判。
實際上,瞿秋白早在1932年1月完成的《論弗理契》一文已經批評了弗理契藝術社會學思想中存在的問題并指出,其一,弗理契無意中批評了普列漢諾夫的“五段論”忘掉了階級性,并作出補充和修正,也認識到普列漢諾夫政治上的“孟什維克”,但在文藝批評時仍然無法脫離普列漢諾夫的客觀主義,認為“黨派的文藝批評”是主觀的。其二,弗理契犯了“邏輯主義”錯誤,“想在一般真理的簡單的邏輯的發展之中去找到對于具體問題的答復”,“沒有充分的估計藝術發展的歷史的具體性,而只想要找出最一般的發展規律。”[14]瞿秋白不僅從學理上指出弗理契的錯誤,更從黨派的政治立場將弗理契的錯誤歸于其政治上的孟什維克傾向。
瞿秋白的文章發表后,李華卿隨即發表《為樸列寒諾夫而辯護——駁宋陽〈論弗理契〉之謬誤》,從學理上回應瞿秋白,但他沒有注意到瞿秋白弗理契批判的政治意圖。這篇文章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視了。李華卿認為,學術研究應當是“虛懷若谷”的,不能因政治問題而詆毀學術貢獻。瞿秋白對普列漢諾夫和弗理契的批判表明中國對科學的藝術論的接受過了不加否定的萌芽與介紹階段,而有了反思與批判,但瞿秋白的批判缺少獨立的立場,只是對西歐和蘇聯的弗理契批評現狀的全盤介紹。李華卿認為,其一,普列漢諾夫并不是僅從生物學和地理學討論文藝。其二,普列漢諾夫不但沒有忘掉階級,反而使階級問題深入上層建筑各個部分;弗理契的補充也是不必要的,因為普列漢諾夫的“五段論”不違背馬克思根本原則,且具體化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觀點。李華卿認為瞿秋白不懂人類是政治的動物,政治的法律的上層建筑中包含著階級斗爭。[15]李華卿有意識地回到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辨析普列漢諾夫、弗理契、瞿秋白的思想是可貴的,不過,從后來弗理契批判走向可知這篇文章對糾正弗理契的政治批判沒起到很大作用。
左翼的弗理契批判具體體現在對胡秋原的批判當中,并且已超越藝術社會學上升到對弗理契整體思想評價。周揚指出胡秋原的口頭上的階級論錯在受弗理契的影響,否認蘇俄對普列漢諾夫的批判,否認列寧階段的文學理論。[16]然而僅在半年前,周揚還在翻譯《弗洛伊特主義與藝術》時肯定了弗理契的馬克思主義方法。[17]可見,隨著形勢的變化周揚從肯定弗理契的藝術觀點轉向批判弗理契思想的孟什維克主義傾向。
馮雪峰將弗理契視為世界上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藝術學者,且在1929到1931年間翻譯4篇弗理契的文章。然而進入1932年,他轉變了對弗理契的態度,體現在他對胡秋原的批判中,他認為胡秋原受普列漢諾夫-弗理契的影響,不心服列寧黨的文學,不承認普列漢諾夫藝術理論中的孟什維克,不認識虛偽的客觀主義的錯誤。[18]可是,馮雪峰在1946年再版的《現代歐洲的藝術》新加的《譯者序記》中肯定了弗理契研究在學術上的價值,并指出其在1932年前后對蘇聯的弗理契批判一無所知。[19](P332)顯然馮雪峰的觀點是前后矛盾的。
瞿秋白在學理上批評了弗理契藝術社會學思想本身的機械主義和公式主義傾向,但受蘇聯弗理契批判影響,瞿秋白、周揚、馮雪峰等左翼批評家不僅以列寧主義的立場批判弗理契的孟什維克錯誤、藝術理論的客觀主義,還批判受弗理契客觀主義影響的胡秋原。與對弗理契藝術社會學思想的學術探討相比,左翼更側重對弗理契進行政治批判,這實際上是左翼政治路線的“列寧主義”轉向在文學上的體現,但是左翼將文藝與階級直接對應,反而犯了弗理契藝術社會學中的機械主義錯誤。
以上考察了弗理契藝術社會學思想在中國1921年到1933年之間的接受。需要補充的是,雖然從1930年之初起左翼從政治立場出發將弗理契批判推向高潮,但學術界并沒有就此接受左翼的“定論”,相反,一些批評家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前后重新站到學術立場研究弗理契藝術社會學思想。本文并不將此列為一個單獨的問題進行討論,因為文獻相對分散,對中國現代文論的發展影響較小。不過為了保障問題史脈絡的清晰,彌補以往研究中對這部分文獻的忽視,在此仍要列出相關研究文獻。主要文獻有李梨的《讀“藝術社會學”后》(《中國新書月報》1933年第3卷第2、3期),向培良的《盧納卡爾斯基論》(《矛盾月刊》1933年第1期)、《〈藝術社會學〉書評》(《青春周刊》1934年第3卷第4期)、《評茀理契〈藝術社會學〉》(《六藝(上海)》1936年創刊號),西望的《“弗理契批判”的批判》(《時事新報·每周文學》1936第25期),馮雪峰的《現代歐洲的藝術·譯者序記》(中華全國木刻協會新藝術叢書社1946年)以及蔡儀的《茀理契的“藝術社會學”方法略論》(《文訊》1948年第9卷第2期)。這些文章或是參照西方文藝思潮,或是基于中國理論現實對弗理契藝術社會學思想重新做出評判。可以說,中國的文學理論走上更加豐富和自覺的階段。此外,辛人在1935年又翻譯了甘粕、石介的《弗理契主義批判》(《盍旦:文藝、哲學、歷史、雜文月刊》1935年第1卷第2期),林煥平在1940年翻譯了高沖陽造的《佛里契批判》(《民風》1940年第1期),這兩篇文章主要是日本學界對弗理契的機械主義和公式主義的批判。
四、結 語
根據筆者的統計,1921—1933年間中國對弗理契藝術社會學的接受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理論初識階段、學理反思階段和政治批判階段。整個20世紀20年代受日本左翼文學界的影響,中國將弗理契視作是世界第一的馬克思主義藝術學者,并以他的客觀主義的文學研究方法來闡釋新文學的發生。進入20世紀30年代以后,隨著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深入發展,蘇聯和日本對弗理契藝術社會學立場的進一步傳入,批評界對弗理契的藝術社會學展開了深入的學術研究與激烈的政治批判,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后批評界才較為自覺地思考弗理契藝術社會學的價值與不足。胡秋原等肯定了弗理契藝術社會學在研究方法上的貢獻,但更從學理上批評了弗理契藝術社會學中存在的機械主義和公式主義問題,并警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中的“左傾”趨勢、對文學自身規律的忽視;左翼除了從學理上批評弗理契藝術社會學的機械主義和公式主義錯誤,更以列寧主義的“黨派性”觀點批評弗理契對普列漢諾夫客觀主義文藝觀的繼承以及對主觀的黨派批評的拒絕,并將弗理契的錯誤歸于他政治上的孟什維克主義傾向。不過,在文藝實踐中,左翼卻犯了與弗理契同樣的將文藝與階級斗爭直接對應的錯誤,走上庸俗社會學的道路。庸俗社會學思想給中國文壇造成了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惡劣影響,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才在政治和學理兩個層面得到徹底的清算。在左翼的弗理契政治批判之后,客觀主義的弗理契被剔除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的范疇,左翼的批評理論進入列寧主義階段。弗理契藝術社會學思想在中國的接受,顯示了緊張的現實斗爭對細致學術思考的褫奪,反映了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中國化是一個不斷選擇、反思、批判、建構的過程,同時也提醒我們在當下的批評中要警惕庸俗社會學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侵害。
注釋:
①雖然本文的研究對象為1921年到1933年間弗理契藝術社會學思想在中國的接受,但為了對弗理契藝術思想在現代中國的接受有整體把握,文獻的搜集與整理以1949年為界限。主要有:福栗許《鮑爾希維克下的俄羅斯文學》(愈之譯,《東方雜志》1921年第16號)、佛利柴《中產階級勝利時代的法國文學》(耿濟之譯,《小說月報》1924年第15卷)、傅利采《繪畫底馬克思主義的考察》(朱靜我譯,《創造月刊》1928年第2卷第5期)、Maksimow《藝術社會學的學術會議的報告》(馮乃超譯,《思想月刊》1928年第3期)、V.茀理契《作為文藝批評家的伏洛夫司基》(畫室譯,昆侖出版社1929年5月)、傅利采 《社會主義的建設與現代俄國文學》(蔣光慈譯,《文藝講座》1930年第1冊)、Friche《藝術家托爾斯泰》(馮乃超譯,《文藝講座》1930年第1冊)、傅利采《藝術上的階級斗爭與階級同化》(許幸之譯,《文藝講座》1930年第1冊)、茀理契 《藝術之社會的意義》(洛生譯,《新文藝》1930年第2卷第1期)、茀理契《藝術風格之社會學的實際》(洛生譯,《新文藝》1930年第2卷第2期)、V.茀理契《藝術社會學之任務及諸問題》(雪峰譯,《萌芽月刊》1930年第1卷第1、2期)、V.茀理契《巴黎公社底藝術政策》(雪峰譯,《萌芽月刊》1930年第1卷第3期)、V.茀理契 《現代歐洲的藝術》(雪峰譯,大江書鋪,1930年6月)、弗理契《藝術社會學》(天行譯水沫書店,1930年10月)、V.M.Frice《工業發達在現代歐洲文學上的反映——摘譯自:“歐洲文學發達史”》(林適文譯,《文學生活》1931年第1期)、V.茀理契《毀滅·關于“新人”的故事》(隋洛文譯,大江書鋪,1931年9月)、佛理采《藝術社會學》(胡秋原譯,神州國光社,1931年)、V.Friche《論樸列汗諾夫之藝術論》(胡秋原譯,神州國光社,1932年)、弗理契《歐洲文學發達史》(沈起予譯,開明書店,1932年4月)、弗理契《弗洛伊特主義與藝術》(周起應譯,《文學月報》1932年第1卷第1期)、佛理采《精神分析學與藝術》(胡秋原譯,《讀書雜志》1932年第6期)、佛理采《樸列汗諾夫與藝術之辯證底發展問題》(胡秋原譯,《讀書雜志》1932年第2卷第9期)、弗理契 《二十世紀歐洲文學》(樓建南譯,新生命書局,1933年2月)、Friche《藝術作風與社會生活之關系》(胡秋原譯,《學藝》1933年第12卷第2號)、茀理契《三個美國人》(蘇伍譯,《春光》,1934年第1卷第1期)、弗里采《柴霍甫評傳》(毛秋萍譯,開明書店,1934年);佛里契《藝術底將來》(聶紺弩譯,《中華月報》1934年第2卷第8期)、傅利棄《藝術家底悲劇》(白濤譯,《譯文》1935年第2卷第6期)、V.弗利契《人與文學·藝術家的悲劇》(胡風譯,桂林南天出版社,1942年10月)、弗理契《藝術社會史概說》(劉汝醴譯,《月刊》1946年第1卷第3期)、弗里采《都市的藝術:藝術社會史概說之二》(劉汝醴譯,《月刊》1946年第1卷第4期)、弗里采《新的藝術——藝術社會史的概說之三》(劉汝醴譯,《月刊》1946年第2卷第1期)。本文中Фриче,Владимир Максимович 譯為弗理契。對這些文獻簡單分析可知,其一,Фриче,Владимир Максимович的中文譯名寫法多、不統一。其二,當時批評界對弗理契的關注經歷了從他作家作品的研究到他的藝術理論,且重點在藝術社會學思想。其三,翻譯者身份構成復雜。其四,發表的刊物及出版社性質也并非都與左翼有關。其五,對弗理契著作的譯介在1930年左右達到高峰,主要集中在1930年到1933年之間。
②分別根據劉慶福在《普列漢諾夫的文藝論著在中國之回顧》和《盧那察爾斯基文藝論著在中國》的統計,普列漢諾夫在現代中國有13種譯文;盧那察爾斯基在現代中國有47種譯文。在當下的研究中,多有學者探討普列漢諾夫、盧那察爾斯基對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的發展影響,截至2018年3月,中國知網上“普列漢諾夫”與“現代文學理論”相關文章有17條,“盧那察爾斯基”與“現代文學理論”相關文章有2條,“弗理契”與“現代文學理論”的相關文章有3條。
③對弗里契庸俗社會學思想批判的相關研究成果有:周平遠《20世紀30年代初胡秋原的庸俗社會學批判》(《南昌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林偉民 《中國左翼文學思潮》(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劉永明《左翼文藝運動與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早期建設》(中國文聯出版社,2007年)等。
④討論弗理契藝術社會學同中國文學理論關系的研究包括:溫儒敏《從學科史考察早期幾種獨立形態的新文學史》(《中國文化研究》2003年春之卷),吳元邁《一個并非過去年代的故事——弗里契與文藝學中的庸俗社會學問題》(《中文學術前沿》2012年第1期,杜吉剛、周平遠《“左聯”時期國際路線下的馬克思主義文論譯介》(《南昌大學學報》2013年第5期)等。
⑤涉及弗理契藝術社會學對文學創作積極影響的成果有:劉婉明《前所未有的時代——唯物史觀、新感覺派與左聯文學批評》(《上海文化》2012年第2期)、王志松《劉吶鷗與“新興文學”——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接受為中心》(《山東社會科學》2013年第10期)等。
⑥對翻譯到中國的弗理契著作進行梳理的成果有:趙憲章《二十世紀外國美學文藝學明著精義》(江蘇文藝出版社,1987年)、林精華《蘇俄文化之于二十世紀中國何以如此有魅力》(《二十一世紀》網絡版2006年7月號)、李今《三四十年代蘇俄漢譯文學論》(人民出版社,2005年)、汪介之《回望與陳思——蘇俄文論在20世紀中國文壇》(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等。
⑦參看(日)藏原惟人《藝術社會學底方法論——讀弗里采底〈藝術社會學〉》(禹玄譯《煤坑》1932年第20期)。
⑧參看(日)上田進《蘇聯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現狀》(魯迅譯《文化月報》1932年第1卷第1期)、《偉大的第十五周年文學》(適夷譯《文學月報》1932年第1卷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