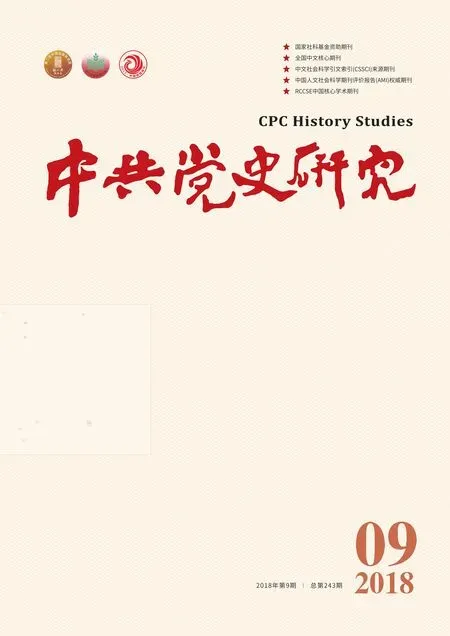知青史研究應該關注和探討城鄉經濟關系問題
趙 文
50年前開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把上千萬青年從城市送往農村。這場政治運動不僅給農村帶來了大批接受“再教育”的城市知青,也通過下鄉知青結成的網絡渠道,給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與城市隔絕的鄉村帶去了生活日用品、生產設備、文娛用品、銀行貸款等各種城市產品和資源,豐富了閉塞鄉村與現代城市之間的經濟往來,從一個側面沖擊了計劃經濟體制下僵硬固化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和城鄉關系,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村的經濟發展。這是知青運動背后一段特殊的經濟史,值得關注和探討。
一、知青史研究的“瓶頸”突破與城鄉經濟關系研究
知青史研究迄今已走過40多年的歷程,取得過一些高質量的研究成果,20世紀90年代還曾掀起過研究的高潮[注]當時,定宜莊、劉小萌分別撰寫《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年)》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史衛民、何嵐著《知青備忘錄——上山下鄉運動中的生產建設兵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劉小萌等著《中國知青事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顧洪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和《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中國檢察出版社,1997年)等,形成了一個知青史研究的高潮。參見金光耀:《后知青時代的知青歷史書寫》,《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4期。。然而高潮過后,知青史研究總體上進展緩慢,“民間熱,學界冷”“情感性回憶多,學理性探究少”的狀況至今仍未有大的改觀。
知青史研究之所以陷入遲滯狀態,原因在于面臨兩大瓶頸:一是學科定位不明,研究的理念、思路尚未跳出政治事件史框架。由于知青運動總體上從屬于“文化大革命”,所以研究者慣常采用政治運動史的范式對其進行研究,習慣于圍繞“原因—經過—結果—評價”的思路,對事件本身進行平鋪直敘的描述和分析,這使得相關研究重復、雷同、單調而“碎片化”,少了史學研究的厚重、豐富、立體與多元。因此有學者指出,知青運動與“文化大革命”密不可分,所以要用“政治運動史”的研究框架,同時,知青運動與社會各方面緊密聯系,所以還要用“社會生活史”的研究框架,二者缺一不可,而后者更基礎、更富有彈性[注]金大陸:《中國知青研究的學科定位及其理論建設的若干問題》,《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2期。。二是史料收集整理和開發利用工作滯后。涉及知青運動的史料主要有運動過程中形成的各級政府檔案、報刊資料、知青日記和書信等。其中最有價值的是原始檔案,但目前這些文獻大多未經系統整理,同時由于政治敏感性的原因,對研究者的開放程度有限。在缺少充足、高質量史料的情況下,想要開展深入細致的研究,拿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是比較困難的。
作為知青史研究的組成部分,知青運動中的城鄉經濟關系研究對于突破上述“瓶頸”具有一定價值和意義。一方面,知青運動中的城鄉經濟關系研究具有跨學科性質,跳出了政治運動史研究的傳統框架,拓展了知青史研究的新領域。城市知青上山下鄉某種意義上是一種有組織、有計劃的大規模移民,與之相伴的必然有知青輸出地與接受地之間的各種經濟往來,包括安置經費劃撥、物質援助、銀行貸款乃至藥品發放等,這種經濟往來實際上反映了勞動力、資金、技術、設備等生產要素在城市和鄉村之間的流動,而這些都屬于區域經濟史、社會經濟史等學科的研究范疇。另一方面,知青運動中的城鄉經濟關系研究所需檔案史料的政治敏感性相對較低,查收利用相對便利。近來出版的《中國新方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史料輯錄》(七卷本,金光耀、金大陸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年)等文獻集,已經為從城鄉經濟關系史角度深化知青史研究提供了史料方面的可能。
二、知青運動與城鄉二元結構
新中國成立后的城鄉關系一直是學術界關注和研究的重點。目前學術界對于計劃經濟時代城鄉關系的主流觀點是:城鄉二元結構日益凸顯,城鄉關系呈現一種分離、割裂的狀態。如張化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的一個時期里,比較先進的工業與落后的農業同時并存,城市的現代化社會與傳統的農業社會相互并行。城鄉經濟流通渠道狹窄、滯塞,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穩固,是這一時期城鄉關系的主要特點之一。[注]張化:《建國后城鄉關系演變芻議》,《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2期。劉偉認為,1949年至1978年的30年是我國城鄉關系逐漸走向分離、二元結構日益凸現的時期,并由此派生了城鄉對立的二元經濟結構和體制[注]劉偉:《建國后黨的城鄉政策調整與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
上述觀點總體上是不錯的,然而并未反映出計劃經濟時代城鄉關系的全貌。筆者發現了不少上海、北京等城市對知青接受地農村進行經濟支援的史料,這些材料說明,在知青運動這樣的特定歷史時期、特殊歷史條件下,彼此分立的城鄉之間廣泛存在著形式多樣的經濟聯系,這在一定程度上沖擊、改變了城鄉二元分立、隔離的格局,為農村社隊企業和集體經濟的發展創造了一定的條件。[注]由于知青運動在全國各地的開展情況存在差異,所以運動中的城鄉經濟聯系以及城市對鄉村的經濟支持在范圍和程度上有所不同,但這種聯系的確廣泛存在。尤其是“株洲模式”在各地推廣開來后,城鄉之間的經濟聯系以及城市對農村的支援成為一種全國范圍內較為普遍的現象。“株洲模式”是1973年知青政策調整后,最先在湖南省株洲市出現的一種知青安置模式。這種“廠社掛鉤”安置知青的新做法,變分散插隊為集體安置,變學校與社隊對口安置為廠礦企事業單位與社隊對口安置,變主要依靠農村單方面做好安置工作為動員城鄉兩方面共同來做,一定程度上調動了城鄉、工農兩個方面的積極性,在實現知青自給、改善住房條件、發展社隊經濟等方面顯示出優越性。參見劉小萌:《中國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當代中國出版社,2009年,第270頁。
1968年12月22日,毛澤東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號召,掀起了知青運動的高潮。隨后十多年,大批城鎮青年涌入農村,帶給當地的不僅僅是人口結構和流動狀況的改變,更重要的是給計劃經濟時代的農村帶來了一種全新的、復雜的經濟關系。
一個地區經濟的發展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包括勞動力、原材料、能源、資本、技術等要素的投入。計劃經濟時代的城鄉二元體制限制了各種生產要素從城市向農村的流動[注]1958年以后,由于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和嚴格的城鄉戶籍制度,城鄉之間的生產要素自由流動被完全禁止,代之以政府的計劃調撥和交換。參見武力:《1949—2006年城鄉關系演變的歷史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2007年第1期。,知青運動則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覺地充當了打破城鄉二元分割體制的角色,為知青接受地獲取相關資源提供了特殊路徑。農村干部充分運用知青運動帶來的新的人際關系和工作聯系,極力促進當地與知青輸出地之間的城鄉經濟交流。他們或者寫信要求物資援助,或者直接到城市尋求經濟資源。如1969年下半年至1970年3月底,上海市知青辦接待了外地來滬要求物資支援的單位約1250批次,其中既有省一級的,也有生產隊一級的[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下鄉上山辦公室關于上海支援外省物資設備問題的報告》(1970年),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228-2-229-36。。而知青輸出地出于鼓勵知青扎根農村、減輕城市人口壓力、確保城市社會穩定等需要,或主動或被動地通過經濟手段撫慰下鄉知青,為知青接受地提供了大量生產、生活物資以及銀行貸款等經濟支持。例如,上海市革委會對于知青接受地農村要求物資援助的態度是“原則上凡能辦的盡力支持”[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下鄉上山辦公室關于上海支援外省物資設備問題的報告》(1970年),上海市檔案館藏,檔案號B228-2-229-36。,進而對上海知青比較集中的安置點進行了大量援助。
需要指出的是,以物質支持為主要形式的知青輸出地與接受地之間的城鄉經濟往來,主要是當政者為了鞏固知青運動所采取的權宜之計,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夾雜著許多政治上的考慮,尤其在運動后期廣泛學習“株洲模式”,實行廠社掛鉤、集體安置知青后更是這樣。盡管如此,這種城鄉經濟往來還是有意無意地打破了國家對于物資流通的嚴格限制,勾連起現代城市與封閉鄉村之間的經濟聯系。就此展開研究,將有助于更加準確地還原計劃經濟時代的城鄉關系,也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認識知青運動。
三、對于推進知青運動中城鄉經濟關系研究的一些思考
目前,有關知青運動中城鄉經濟關系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一些通史性質的知青史著作雖對此有所涉及,但研究得并不深入。筆者目力所及的專題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林升寶的《“文革”時期上海對各相關省區知青接收地的經濟行為研究》和韓起瀾(Emily Honig)、趙小建的《知識青年與毛澤東時代的農村經濟發展》[注]參見林升寶:《“文革”時期上海對各相關省區知青接收地的經濟行為研究》,碩士學位論文,上海社會科學院,2011年;韓起瀾、趙曉劍著,羅湘衡譯:《知識青年與毛澤東時代的農村經濟發展》,《毛澤東思想研究》2016年第1期。其中后者原載于《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總第222期(2015年6月),原題為“Sent-down Youth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oist China”,作者名音譯有誤,“趙曉劍”應為“趙小建”。。總體而言,這還是一個尚待挖掘的新領域。對于推進這一領域的研究,筆者有如下幾點思考和建議:
第一,要明確知青運動中城鄉經濟關系研究的對象。根據不同的對象,可將這一研究分為廣義、狹義兩種。廣義方面,基本等同于“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城鄉經濟關系研究,因為知青運動脫胎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路線,內嵌于“文化大革命”運動之中,所以“文化大革命”時期凡是涉及知青、知青運動的關于城鄉經濟關系狀況、特點、變化的題目,尤其是城鄉經濟關系與知青運動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等,都可以納入研究范圍。狹義方面,主要研究知青運動時期知青輸出地與接受地之間的經濟往來及其對當地經濟發展的影響。從生產要素流動的角度出發,狹義研究的對象可包括:(1)勞動力轉移(知青、農民轉移至非農崗位的情況,轉移的過程、特點、途徑、條件等);(2)資金和資源的流動(知青輸出地投入的資金、資源總量和結構,知青安置經費、銀行貸款等的劃撥和使用等);(3)人才和技術的支持(對知青、農民的技術培訓、技術支援等);(4)社隊企業建設、鄉村集體經濟發展(對知青接受地社隊企業的設備物資支持,集體經濟發展中的小作坊援建等)。
第二,要采用比較的、多學科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知青運動中的城鄉經濟關系,不能脫離知青運動本身。由于各地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千差萬別,知青運動在不同地區的推行及其所引發的城鄉經濟關系變化必然會有所差別。例如,北京、上海都是直轄市,知青運動中都跨省安置了大批知青,但因為上海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地位比較特殊,所以兩地對知青接受地進行支援的方式方法便有所不同。為此,需要采用比較的方法,深入探討知青運動中城鄉經濟關系不同變化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和規律。與此同時,知青運動中的城鄉經濟關系研究具有跨學科性質,離不開對城鄉政治關系、社會關系、文化關系、生態關系及其相互之間聯系的研究,也離不開對其外部環境等的探討,因而有必要汲取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其他學科的養分,通過多個角度對其進行全面而深入的剖析。
第三,要有問題意識,對現實世界有所關照。當下的一些史學研究者滿足于孤立地看待研究對象,缺乏大視野、大格局,缺少對現實問題的關注,使研究陷入“單面化”“碎片化”的狀態。研究知青運動中的城鄉經濟關系時,應該盡力避免這種狀況,要有問題意識和人文情懷,努力做到立足歷史、關照現實、放眼未來。筆者在研究中注意到,知青運動中的城鄉經濟關系變化對于知青運動的延續、當地的經濟發展,以及知青的生產、生活乃至其成長發展都或多或少產生了影響。知青運動與城鄉經濟關系之間相互作用,影響延續至今。例如,一些留在當地的知青通過各自的城市資源,帶領農民發展鄉村現代經濟;一些回城后逐漸嶄露頭角的知青依然牽掛當年插隊的地方,繼續通過各種途徑回報農村;一些當時為知青服務而籌建的小作坊如今已經成為當地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力量。直至今日,那些曾經接受知青的地方政府,依然將知青當作發展地方經濟的重要資源,不少曾經當過知青的企業家在他們插隊下鄉的地方投資辦廠、鋪路架橋、興辦學校,甘為第二故鄉的發展作貢獻。因此,要把知青運動時期的城鄉經濟關系變化放置在新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歷史脈絡中去考察、審視和體悟。唯有如此,我們的研究才能對當前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城鄉經濟關系和城鄉一體化發展等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