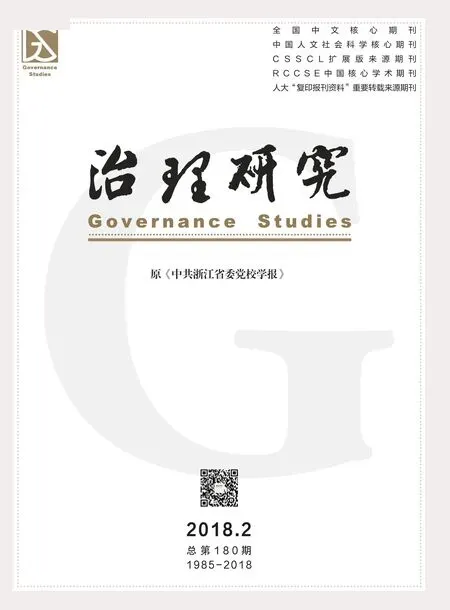秦漢政制構造原理榷論
□ 李 霞
影響中國歷史兩千余年的古代政制,定型始自秦漢,功用完善于唐宋,弊端顯現于明清。本文主要聚焦于中國古代政制之肇始與定型階段。*參見勞榦:“從儒家地位看漢代政治”,《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33頁(“近代政治制度大多始于秦漢,至今雖有若干受西方影響,但中國傳統還是存在的。甚至于新的法律,其中還保有固有的法律精神,這仍是從秦漢沿襲而來”)。一般認為,春秋戰國系中國古代歷史之一大變局,除“禮壞樂崩”之外,更重要的是,為一種全新類型的政制之塑造提供了契機。秦始皇雖“執棰拊以鞭笞天下”,開啟了統一大帝國背景下古代政制模式的創建與嘗試,但古代政制模式的真正定型實完成于漢代。因此,錢穆先生說“秦之統一與其失敗,只是貴族封建轉移到平民統一中間之一個過渡”*錢穆:《國史大綱》(新校本)(上),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36頁。,是有道理的。當然,這并不否認秦在中國古代政制之創建與嘗試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貢獻。
在中國古代政制定型化的過程中,既無經驗可循,亦無理論、邏輯之指引,此一古代政制實在是社會之變遷、文化之積淀、情勢之所趨、一時之權變等因素混合作用之結果。
一、古代帝國早期的歷史困局
在地域與政權組織空前的大帝國里,如何“永久地維持皇室的統治權力”,不僅是“始皇滅六國后面對著的空前大問題”*張蔭麟:《中國史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頁。,也是漢高祖倉促間無從應對而漢武帝繼“文景之治”后仍在不斷嘗試解決的問題。
秦始皇在統一天下之后、漢高祖在即帝位之初,面臨著一個共同的困局:新生政權及其穩定性受到內外諸多勢力或因素的嚴酷威脅。面對如此危機,首要之舉是找到一種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予以迅速化解。假如倉促之間的選擇只是權宜之計的話,那么,為了帝國的長治久安,還需要在危機化解之后,繼續在現實情勢的基礎上尋求更為穩定而有效的控制模式,即(1)通過何種方式實現古代帝國直接而有效的控制。
接著,依據歷史的邏輯與現實的形勢,新生政權的執掌者總要面對來自舊有政治勢力及其統治下社會民眾在思想觀念上的挑戰與質疑,從而不得不從思想或者觀念上(2)為新生政權的正當性進行論證。進而,在論證之后,為了進一步鞏固新生政權、加強對帝國的控制,又需要(3)創建或編造一套適于時宜的理論或者學說,應對原有政治勢力的挑戰,化解社會民眾的質疑,推動并磨合帝國政權機構的運轉。
然而,維持一個空前龐大的古代帝國秩序,除了強力的控制、思想與文化的統一之外,至少還需要解決兩個問題,即(4)中央朝廷與地方治理之間的政治關系,以及(5)如何選擇以及選擇什么樣的治國策略,如何實現以及在實現過程中如何修正預選的治國策略。也只有處理好這兩個問題,才會使“實現帝國的有效控制”成為可能。同時,在認識、辯明上述諸問題并且嘗試提出解決問題方案的過程中,特別是在某些關鍵的歷史時刻,仍然不得不認真對待“人”發揮的作用。
在中華帝國早期(公元前3世紀后期至公元前1世紀中期)約170余年間,上述這些問題糾葛在一起,使這個空前龐大的古代帝國陷入一個又一個的現實困境,在挑戰古代帝王的政治智慧與政治決斷的同時,也為構造一個舉世矚目的古代政制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歷史機緣。從現代人的視角來看,或許可以將“古代政制構造”作為一種認識古代社會深層結構的暗碼,通過對這一暗碼的解讀,嘗試分析并理解深埋在帝王將相的荒冢與浩如煙海的史冊之間古代政制賴以建構的社會基礎及其基本原理。
二、古代政制的構造及修正
上述臚列的問題糾葛在一起,共同構成了帝國早期面臨的歷史困局,而作為統治集團核心的帝王將相,將如何在政治實踐中面對與解決這些問題,以及在這一過程中如何一步步完成對古代政制模式的選擇、構造與修正。
(一)通過強力的控制
無論是秦始皇嬴政還是漢高祖劉邦,在親掌政權或者即皇帝位之時,均是在經過連年兵革戰亂后而求其內政之寧息,為了在短時間內實現對政局或者帝國秩序的完全控制,他們不得不采取盡可能直接而有效的策略與措施。具體包括:(1)禁止民間私藏兵器,“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避免或壓制地方反抗;(2)在全國范圍內“治馳道”,以迅速掌握各地信息,及時處理地方事務;(3)略取邊地,修筑長城、亭障等軍事要塞,以防御或者驅逐匈奴、戎胡之人;(4)嚴刑峻罰,強行甲兵,以防止或者鎮壓朝廷內外諸侯大臣的反叛。*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卷六,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204-206、216頁;以及《史記·高祖本紀》卷八,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321-331頁。通過這些極具強制性的武力措施,秦漢初期的統治者比較有效地實現了對整個帝國的直接控制。
(二)“終始五德之傳”
為了應對此前的政治勢力及其統治下社會民眾的挑戰與質疑,秦代及漢代初期的統治者不得不想方設法從思想觀念上論證自身政權及其對帝國控制的正當性。鑒于此,公元前221年,天下初定之際,秦王嬴政便以“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后世”為由,下令丞相、御史、諸博士及群臣“議帝號”,百官議定帝號為“泰皇”,嬴政更為“皇帝”,自稱“始皇帝”,甚至企望“后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卷六,第201-203頁。
在“名正言順”之后,秦始皇開始選用齊國士人“終始五德之傳”的學說,根據陰陽五行相生相克之理,論證“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然后合五德之數”。為了進一步論證秦政權的正當性,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東行郡縣,“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禪梁父”。緊接著,又先后在之罘、瑯邪、碣石、云夢、會稽等地祭祀虞舜、大禹,并“立石刻,頌秦德”。*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卷六,第207-222頁。
至漢代,據史載“高祖斬白蛇”之故事,借老嫗之口稱,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對此,應劭解釋為,秦祠白帝,“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隨后,沛縣起兵之際,“祠黃帝,祭蚩尤于沛廷,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也”。*班固:《漢書·高帝紀》卷一,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5-7頁。可見,漢初統治者也在嘗試運用“終始五德之傳”來論證其政權的正當性,恰如班固贊語所言,“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班固:《漢書·高帝紀》卷一,第59頁。
公元前166年,魯人公孫臣與丞相張蒼圍繞“終始五德之傳”展開辯駁。公孫臣上書陳請“終始傳五德事”,聲稱“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建議“當改正朔服色制度”;而丞相張蒼卻“推以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表示反對。次年,“黃龍見成紀”,應驗了公孫臣之說,故而漢文帝“復召魯公孫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下詔“親郊祀上帝諸神”。*司馬遷:《史記·孝文本紀》卷十,第363頁。
可見,秦始皇和漢初諸帝均不約而同地借用“終始五德之傳”來論證自身政權及其對帝國控制的正當性,在社會心理層面迅速贏得了較為普遍的社會信任,或者至少是在相當程度上消解了民眾的懷疑,取得了一定的社會效果。
(三)從“焚書”、“坑儒”到“罷黜百家,表彰六經”
在依憑武力控制帝國秩序,借用“陰陽五行”與“封禪祭祀”證明自身政權的正當性之后,秦漢初期的統治者迫切需要一套完整而適于時宜的理論或學說,作為其控制與治理國家的基本原理。公元前213年,仆射周青臣與博士淳于越圍繞“封建”與“郡縣”展開辯論,秦始皇令群臣商議,李斯趁機主張“焚書”,一方面,強調遵守和維系中央朝廷政令的權威;另一方面,強化和鞏固“事皆決于法”的政制構造。*參見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卷六,第217-218頁。
秦始皇采納了李斯的建議,頒發“焚書令”。次年,因侯生、盧生等誹謗逃亡,秦始皇“使御史悉案問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陽”,扶蘇諫言“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秦始皇不僅未予采納,反而命扶蘇隨蒙恬戍守邊郡。*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卷六,第220頁。至此,在李斯等人的努力下,法家哲學高居廟堂之上,而儒家思想及其他諸子學說暫隱于江湖。
西漢初期,高祖劉邦對先秦諸子學說既沒有明顯偏好,也從未想從中選取一種作為治國的主導思想。略顯吊詭的是,從個人本性看,劉邦將“豎儒”掛在嘴邊,明顯對儒士有一種厭惡心理;但從治國角度看,他又對儒家學者及其政治思想與政制方案另眼相待。例如,公元前195年,經魯國而“以大牢祠孔子”。*班固:《漢書·高帝紀》卷一,第56頁。之后,雖然文帝“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于禮義”*司馬遷:《史記·孝文本紀》卷十,第366頁。,武帝“鄉儒術,招賢良”,甚至準備依據儒家思想建構古代政制,但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甚至因趙綰、王臧等儒者“欲議古立明堂”及“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而案殺之,以致“諸所興為者皆廢”。*司馬遷:《史記·孝武本紀》卷二,第382頁;亦可參見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卷一百二十一,第2710頁。從政制構造的主導思想看,這一時期大體上是黃老之術對儒家思想的壓抑。
迄竇太后崩,武帝發布征賢良文學詔,旨在察問“古今王事之體”,“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以致“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司馬遷:《史記·孝武本紀》卷二,第382頁;班固:《漢書·武帝紀》卷六,第115頁;以及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卷一百二十一,第2707、2709頁。然而,武帝并不限于將賢良文學之士籠絡于廟堂之上,以論證“古今王事之體”,而是還想方設法扭轉自商鞅變法以來整個社會形成的功利的、無信無義的人際關系。公元前128年,武帝下詔,嘗試通過法律手段推行教化,強令官吏察舉孝廉*班固:《漢書·武帝紀》卷六,第119頁。,以期移轉民間風俗,為政權之鞏固奠定相當的社會基礎。
在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的背景下,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參見班固:《漢書·董仲舒傳》卷五十六,第1901-1918頁。,不僅回復了武帝關于“古今王事之體”的察問,更為之草擬了一幅由“正心—任德—教化—均布—更化”構成的古代政制藍圖,而構造這一政制的前提是“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于是,在“隆儒”的基礎上,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對冊”,“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班固:《漢書·武帝紀》卷六,第150頁。
(四)“封建”與“郡縣”之辯
在借“推終始五德之傳”及“封禪祭祀”論證政權正當性的過程中,帝國統治者仍然要面對如何處理中央朝廷與地方治理之間的關系問題。公元前221年,丞相衛綰建議采用周制,立國封王,鎮治地方。秦始皇下令群臣商議,多數大臣表示贊同。廷尉李斯卻提出異議,認為“置諸侯不便”。*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卷六,第204頁。秦始皇贊同李斯的意見,并且指明導致東周列國紛爭的原因正在于分封諸侯。故而,秦始皇分天下以為郡縣,企圖通過委派官吏和巡行郡縣實現對帝國的控制與治理。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仆射周青臣頌贊秦政以及始皇之威德,“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然而,博士齊人淳于越卻亢意直言,接衛綰之踵,再次提出效法殷周封建之制。*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卷六,第217頁。對于周青臣與淳于越圍繞“郡縣”與“封建”而展開的駁難,秦始皇并沒有簡單地強制要求遵守先前推行郡縣的法令,而是下令群臣商議。對此,丞相李斯重申推行郡縣制的立場,并強調遵守法令的意義: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卷六,第217頁。
至漢代立國之初,擺在統治者面前的至少有兩種治理國家的模式及經驗:殷周的封建制與秦的郡縣制。但在他們看來,周行“封建”享祀八百年,秦行“郡縣”歷十五年而亡,偌大一個歷史教訓,無論是劉邦還是他的謀臣,似乎都不得不選擇“封建”。即位之初,劉邦先后分封了諸多異姓諸侯王及列侯,實際上,這也是高祖的“權宜之計”,畢竟“與天下同利”*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卷八,第321頁。是其獲得并維系帝位的基礎。此時,漢“朝廷所須防備的只有諸侯王,列侯在政治上是無足輕重的”。*張蔭麟:《中國史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頁。隨后,異姓諸侯王逐漸被劉氏宗親替代,不僅實現了“王同姓以填天下”*班固:《漢書·荊王劉賈傳》卷三十五,第1481頁。的初期政制架構,還訂下“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司馬遷:《史記·呂太后本紀》卷九,第337頁。的“白馬之盟”。
在漢高祖的政制謀劃中,經過血親網絡過濾而成的“家族封建”政制模式顯然優于宗親異姓雜封的“殷周封建”政制模式,然而,這也是劉邦政治幼稚的表現,未能看清在龐大帝國殘酷的政治現實面前,血緣紐帶根本無力維系中央對地方諸侯王國的控制與約束,因而必須尋求其他更為穩定而有效的政制模式與制約方法。二十年后,賈誼洞察到劉邦未能看清的這一問題,諫告文帝“患之興自此起”,力陳“封建之患”的根由,甚至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概言之,即“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分化”政策。*參見《新書》“藩傷”、“藩彊”、“五美”諸篇,賈誼:《新書校注》,閻振益、鐘夏校注,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37頁、第39-40頁、第67-68頁;亦可參見班固:《漢書·賈誼傳》卷四十八,第1718-1719頁。此處所引疏文即通常所稱的《陳政事疏》,亦稱“治安策”,是賈誼政治思想的代表作之一。雖然文帝在政治實踐中部分實踐了賈誼的方案,但未能有效解決問題,以致這一始終未能消解的矛盾終于激化而成“七國之亂”。在這一矛盾從潛隱到爆發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位與賈誼具有相當的政治洞察力,且提出更具針對性的政制改革方案的人物——景帝時期的御史大夫晁錯。
為了推行“削藩”政策,晁錯向景帝上書力陳“封建之弊”,指出封諸侯“分天下半”而“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根據晁錯的建議,景帝先后下詔削楚東海郡、吳豫章郡及會稽郡、趙河間郡及膠西六縣。此后,武帝繼續推行賈誼、晁錯等人秉持的“分化”政策,雖留分封王侯之事,但在諸多限制下已形同虛設,根本無力對抗中央朝廷,從而使地方治理之權事全部納入郡縣制度之內。因此,張蔭麟先生將“七國之亂”稱為“漢朝政制的大轉機”*張蔭麟:《中國史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頁。,是相當允當的。
(五)從“事皆決于法”至“德主刑輔”
自商鞅變法以降,秦以法家思想立國,至平定天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作制明法,臣下修飭”,“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秦始皇“剛毅戾深,事皆決于法,刻削毋仁恩和義”,任用李斯,厲行法治,“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以至于“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皆遵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及至秦二世,“遵用趙高,申法令”,“用法益刻深”。*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卷六,第203-223、227、228頁。然而在厲行法治的過程中,卻“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以致“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班固:《漢書·刑法志》卷二十三,第929頁。概言之,在先秦諸子學說中,秦朝選擇了法家的法治思想,并作最嚴厲之推行,從而在“專任刑罰”的基礎上構造了一種古代帝國的政制模式。
盡管漢高祖初入關時,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馀悉除去秦法”*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卷八,第307頁。,但其后因“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國蕭何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班固:《漢書·刑法志》卷二十三,第929頁。,實際上,從政制初步構造的角度講,主張“漢承秦制”是比較恰當的。惠帝、高后時,用蕭何、曹參為相,“以無為之法填安百姓”,以致“依食滋殖,刑罰用稀”。及至文帝即位,反思“亡秦之政”,改革刑制,以“愷弟君子”、“為民父母”之意“化行天下”。*班固:《漢書·刑法志》卷二十三,第929-931頁。
公元前156年,景帝下詔,命廷尉與丞相商議修訂律令,于是,提出了一套由“計償費,勿論”、“坐臧為盜”、“奪爵免官”以及“罰金”“沒入所受[臧]”等階梯式刑罰構成的吏治律令的修訂方案。然而可惜的是,這一修訂律令方案是否被采行,史籍未載。但有史書明確記載的是,自公元前145年起,景帝連續五年頒發詔令,要求吏民遵行法令,尤其強調依法治獄、治吏的重要意義。*參見班固:《漢書·景帝紀》卷五,第101頁、106-109頁。
至漢武帝時,無論是基于政治實踐的現實需求,還是受到儒家學說的觀念影響,開始將“百姓之未洽于教化”*班固:《漢書·武帝紀》卷六,第122頁。作為政制構造的核心考量因素之一,從而在“漢承秦制”的基礎上運用先秦諸子學說——當然,核心是儒家思想——修正已初具模型的古代政制。顯然,這些修正舉措絕非單純向世人宣揚所謂的“仁圣之心”,更重要的是,借儒家學者倡導的殷周禮制之名變革或修正秦及漢初以來占據支配地位的法家的法治主義政制模式。
三、“士”在古代政制構造中的地位及作用
在古代政制構造及其修正的過程中,帝王在重大事件或困境中的政治決斷與選擇當然至關重要,但影響或促使帝王做出政治決斷的因素卻是復雜而多元的,除了帝王自身的主觀條件以及社會環境的客觀因素之外,至少還有一個值得認真對待的問題——面對重大事件或者困境時,究竟是哪些人以什么樣的方式影響、甚至決定著古代帝王的政治決斷與選擇,以及這些人在古代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思想傳統、文化特征等。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錢穆先生的觀點——漢代政府是一個“代表一般平民社會的、有教育、有智識的”并且“由全國各地之知識分子即讀書人所組成”的“士人政府”*參見錢穆:《國史大綱》(新校本)(上),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160頁;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6頁。——或可呈現一條值得深入的路徑。
(一)李斯及其對古代政制的初步建構
為實現對統一帝國的有效統治,秦始皇在平定六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不乏在政制建構層面上的嘗試與努力,在這一政制建構過程中,李斯既是不可或缺的,同時也極具代表性。李斯是楚國上蔡人,“年少時,為郡小吏”,追隨荀況“學帝王之術”,在分析戰國形勢之后,認為“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且“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故而選擇輔佐秦王建功立業。隨著為“天下一統”之“帝業”的謀劃計策的鋪展與實現,李斯逐漸受到秦王的重用,由郎而為長史,為客卿,為廷尉,及至平定天下后,官至丞相。公元前213年,李斯借評議淳于越諫言效法殷周封建之機,建議禁私學、去詩書、以吏為師,秦始皇采納李斯的建議而頒發了“焚書令”。此外,在“明法度,定律令”,“同文書”以及“巡狩,外攘四夷”等政制建構與帝國控制方面,李斯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司馬遷:《史記·李斯列傳》卷八十七,第2231-2237頁。
從楚國小吏躋身帝國公卿之列,李斯審時度勢,運用“帝王之術”實踐了個人建功立業的雄心。然而,秦始皇死后,在趙高的威逼利誘下,身居丞相位的李斯卻與趙高合謀矯詔賜死扶蘇,立胡亥為太子,即二世皇帝位。隨后,秦二世采納趙高的意見,“更為法律”,案殺群臣諸公子,以致“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眾”。此時,在政制構造的理念上,李斯雖然與趙高存在決然的分歧,但在政治的高壓下,迫不得已上言“獨制督責之術”,以“阿二世意,欲求容”,而朝廷“事皆決于趙高”。李斯又不甘數十年營造之功虧一簣,嘗作最后一搏,“上書言趙高之短”,卻被趙高誣以“謀反”之名,“腰斬咸陽市”而“夷三族”。*參見司馬遷:《史記·李斯列傳》卷八十七,第2238-2250頁。
(二)賈誼及其關于古代政制的理想與闡釋
經歷秦末戰亂之后,漢初約法省禁,與民休息,天下和洽,但同時,漢家王朝也面臨著四伏的危機。無論是為了避免重蹈亡秦之覆轍,還是為了實現劉氏政權對帝國的有效控制,漢文帝開始嘗試逐步修正奠基于秦代而為漢代繼承的古代政制。在這一社會與政治背景下,除了具體的制度變革外,迫切需要有深刻洞察力與遠見卓識的政治家,為統治者指明潛伏的危機與癥結所在,并為之提供更具長遠眼光的政制改革方案。從歷史上看,足以堪此重任者正是賈誼。*關于賈誼早年經歷的簡介,可參見司馬遷:《史記·賈誼傳》卷八十四,第2192頁。
文帝時,河南郡守吳公(曾學事李斯,而李斯與韓非一起共事荀子)因賈誼少時“能誦詩屬書”且“通諸子百家之書”而“幸愛”之,或可推斷,賈誼的政治思想與荀子的學說可能有某些共通之處,甚至一脈相承,從而有別于孔孟傳統的儒學思想。例如,在分析漢初封建諸侯問題及解決方案時,賈誼指出“仁義恩厚者,此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勢已定,權已足矣,乃以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眾髖髀也,釋斤斧之制,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刃不折則缺耳”。*賈誼:《新書·制不定》卷二,第71頁。
在詔議對策之時,賈誼“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馀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司馬遷:《史記·賈誼傳》卷八十四,第2192頁。文帝雖未予直接采納,卻“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后因列侯周勃、灌嬰、張相如及御史大夫馮敬等人構陷賈誼“專欲擅權,紛亂諸事”,而疏離賈誼,適以為長沙王太傅。此后,文帝仍欲重用賈誼,但在封侯建國的問題上,兩人或有分歧,賈誼數次上疏諫言削藩,文帝不聽,以致賈誼郁郁不得志而終。*參見司馬遷:《史記·賈誼傳》卷八十四,第2192、2201-2202頁。盡管如此,但賈誼構造帝國政制的理念及策略卻得到后世的沿襲與實踐。
(三)晁錯及其對古代政制構造理論的實踐
與賈誼的“郁郁不得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大致處于同一時期、同樣具有敏銳洞察力的晁錯*關于晁錯早年經歷的簡介,可參見司馬遷:《史記·晁錯傳》卷一百一,第2399-2400頁。,后者的政治生涯始終處在文景時期最激烈的政治旋渦中心。晁錯身為太子家令時即已看清“封侯建國之弊”及“更定法令之需”,故而“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雖然文帝未予采納,卻因“奇其材,遷為中大夫”。及至景帝即位,任命晁錯為內史,經常與其商討政事并采納其建議,“法令多所更定”。隨后,晁錯“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因而與公卿列侯宗室之間產生極端的矛盾。公元前154年,吳楚七國“以誅錯為名”起兵反叛,景帝在兩難之間采信竇嬰、袁盎的建議,“令晁錯衣朝衣斬東市”。*司馬遷:《史記·晁錯傳》卷一百一,第2400-2401頁;亦可參見班固:《漢書·吳王劉濞傳》卷三十五。
晁錯早年“學申商刑名于軹張恢先所”,后“以文學為太常掌故”,又“受《尚書》伏生所”,其中,“申商刑名”是以申不害、商鞅為代表的法家學說,伏生所講《尚書》實為儒家思想在齊魯之間的流傳,由此推斷,晁錯的政治思想及其實踐或可兼備儒法兩家之論。然而,晁錯“為人陗直刻深”,雖然在對漢初“封建之弊”的判斷上與賈誼同樣是正確的,但在推行“削藩策”時,“更令三十章”,試圖用嚴刑峻法“侵削諸侯”,以致“諸侯皆喧嘩”。*司馬遷:《史記·晁錯傳》卷一百一,第2399-2401頁。結果,不幸淪為中央朝廷與地方諸侯政治博弈祭壇上的犧牲。至于對晁錯及其建言的評價,誠如謁者仆射鄧公所言,“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司馬遷:《史記·晁錯傳》卷一百一,第2401頁。
(四)董仲舒及其對古代政制的哲學構建
在秦漢政制構造過程中,有一個無法回避的關鍵性問題——如何創建一套合于時宜的理論學說,既可鎮治其他政治勢力的挑戰,又可化解社會民眾的質疑,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推動并磨合帝國政權機構的有效運轉。無論從社會環境的變遷,還是思想文化的積累,抑或政治現實的需求,迄至漢武帝時,歷史發展到了這樣一個關節點上,提供了這樣一個契機,而最終站在這個關節點上且抓住了這一契機的人,就是“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意義特為重大”*徐復觀:《先秦儒家思想的轉折及天的哲學的完成——董仲舒〈春秋繁露〉的研究》,《兩漢思想史》(二),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68頁。的漢儒董仲舒。*關于董仲舒早年經歷的簡介,可參見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卷一百二十一,第2714-2715頁。
秦時初創的古代帝國政制,至漢武帝時,在政治實踐中呈現出了相當的問題與弊端,無論是實踐者,還是思想者,在對現實的觀察過程中也積累了相當的洞察與反思,并且嘗試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方案。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董仲舒將“陰陽”、“五行”等學說注入儒家思想之中,建構起了一個以“天”為核心的政治哲學體系,希望能通過“更化”或者“改制”來修正既有政制之不足,從而將此前的“法家政治”轉化成理想中的“儒家政治”。*徐復觀:《儒家對中國歷史運命掙扎之一例——西漢政治與董仲舒》,《學術與政治之間》,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357頁。
相對于“秦政權缺乏社會基礎”來說,至兩漢時期,“中國真正地熔鑄成為一個完整的個體。這一段熔鑄的過程,不在漢初的郡國并建,不在武帝的權力膨脹,而在于昭、宣以后逐漸建立起政權的社會基礎”,而這個基礎恰恰是“士大夫在中央與地方都以選拔而參與其政治結構”。*參見許倬云:《西漢政權與社會勢力的交互作用》,《求古編》,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336、355頁。然而,無論從“士人”階層形成的漸進過程,還是秦漢帝國建構的政治實踐來看,恰如前文所述,至少在公元前3世紀至前1世紀時,具有獨特政治哲學思想與治國理論的“士人”,已經開始在選擇重大政治決策的歷史時刻突顯其重要意義,并且開始于古代帝國日常的政治實踐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